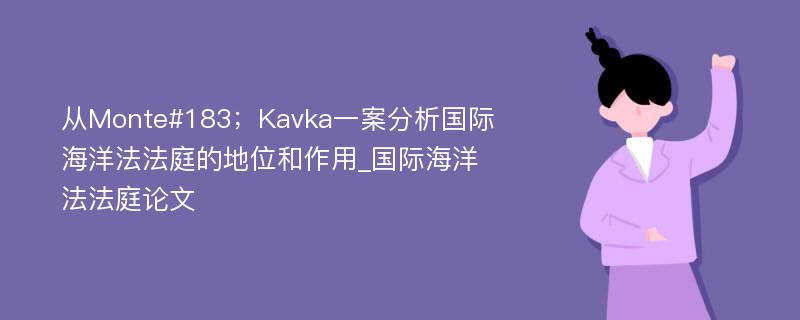
从“蒙特#183;卡夫卡”号案析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洋法论文,法庭论文,蒙特论文,卡夫卡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2)01-0034-07
国际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是依据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设立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目前《公约》缔约方已达135个(包括一个国际组织),其中有26个国家就争端的解决方式作了选择。[1]但国际海洋法法庭自1996年8月1日成立至今,登记处理的案件只有8个。首次实践是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的“塞加”号案(“迅速释放”);第2号案仍是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的“塞加”号案(“临时措施”和“实质问题”);被登记为第3、4号案的分别是新西兰诉日本、澳大利亚诉日本的“南方金枪鱼”案,请求法庭规定“临时措施”,法庭决定两案程序合并;第5号案为巴拿马诉法国的“卡莫科”号案,是“迅速释放”;第7号案是智利诉欧洲共同体的“关于在东南太平洋养护和可持续开发箭鱼群”案(“实质问题”);第8号案是伯利兹诉法国的“大王子”号案,也是请求“迅速释放”。本文引用的“蒙特·卡夫卡”号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第6号案(塞舌耳诉法国),还是请求“迅速释放”。
纵观法庭的实践,其所处理的案件大多是关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的,说明法庭在此类案件中具有独特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庭目前只在此类案件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拟结合典型案例来分析、探讨法庭在处理国际海洋法争端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法庭对“蒙特·卡夫卡”号案的审理
(一)案件背景
“蒙特·卡夫卡”号(Montt Confurco)[2]是悬挂塞舌尔国旗的捕鱼船,属于塞舌尔注册的蒙太克轮船公司。该船于1999年10月2日在塞舌尔登记注册。塞舌尔为该船颁发了证件号为710的在国际水域捕鱼的许可证。
2000年8月27日,“蒙特·卡夫卡”离开路易斯港去南海(印度洋)捕鱼。2000年11月8日11点25分,在法国克尔格仑群岛(the Kerguelen Islands)的专属经济区巡弋的法国“花月”号护卫舰上的船员登上了“蒙特·卡夫卡”号。“花月”号船长指责“蒙特·卡夫卡”号船长:1.没有向克尔格仑群岛行政长官宣告它的存在以及船上装载的鱼的数量;2.没有获得法律规定的事先授权就进行捕鱼;3.企图避开或已避开负责监督捕鱼活动的代理人的调查。以上是“花月”号船长的2000年第1号调查记录。紧接着在2000年11月9日,“花月”号船长又起草了第2号调查记录,其中记载扣押了“蒙特·卡夫卡”号捕获的鱼、航海和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船只和船员的证件等。11月20日,法国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蒙特·卡夫卡”号于11月8日早晨7点出现在距克尔格仑群岛以西90英里的法国专属经济区内,且该船并未声明要进入该专属经济区。在该船上发现了大量捕鱼工具以及1580吨捕获的鱼,价值约900万法国法郎。同日,法国方面请求圣保罗初审法院批准扣押船只,且要求先付9540万法国法郎的保证金加上诉讼费该船方可获释。初审法院批准了对船只的扣留并裁定保证金数额为5640万法国法郎。
塞舌尔方面辩称:2000年11月7日上午十点,“蒙特·卡夫卡号”位于南纬47°40′,东经63°30′,不在法国水域内。当时该船正打算去位于国际水域的Williams Bank(不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最后几周的捕捞。为了走最短的路线且不穿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CCAMLR)规定的区域,该船决定朝东南方向横穿克尔格仑群岛法国专属经济区,以便尽快到达。塞方还说明,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可能通知对方,“花月”号上的官员登船检查时也注意到了该船的传真机只能收不能发。塞方还说,“花月”号官员并未在其船上发现鲜鱼,也未在其船的甲板上发现任何捕鱼的设备,所有1580吨鱼都是冻鱼。他们也没有伪装其船的名字和船旗的任何企图。
法方不同意塞方的上述陈述,坚持认为其船位于距克尔格仑群岛以西90英里处的专属经济区内,且在被发现前已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并进行了捕鱼。另外,传真机坏了并不能说明无法通知法方,因为船上还配备了无线电话设备。
(二)诉讼当事双方的请求
2000年11月20日,塞舌尔农业和海洋资源部部长致信国际海洋法法庭书记官长,授权雷蒙先生(代理)和简先生(副代理)依照《公约》第292条(注:《公约》第292条: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
1.如果缔约国当局扣留了一艘悬挂另一缔约国旗帜的船只,而且据指控,扣留国在合理的保证书或其他财政担保经提供后仍然没有遵从本公约的规定,将该船只或其船员迅速释放,释放问题可向争端各方协议的任何法院或法庭提出,如从扣留时起十日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则除争端各方另有协议外,可向扣留国根据第二八七条接受的法院或法庭,或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
2.这种释放的申请,仅可由船旗国或以该国名义提出。
3.法院或法庭应不迟延地处理关于释放的申请,并且应仅处理释放问题,而不影响在主管的国内法庭对该船只、其船主或船员的任何案件的是非曲直。扣留国当局应仍有权随时释放该船只或其船员。
4.法院或法庭裁定的保证书或其他财政担保经提供后,扣留国当局应迅速遵从法院或法庭关于释放船只或其船员的裁定。)代表该国就“蒙特·卡夫卡”号渔船事件向法庭提出申请。2000年11月27日,塞舌尔的两位代理人代表该国向法庭提出了要求法国释放渔船和船长的请求。法庭11月27日发布命令,定于12月7日、8日对申请进行审讯。11月30日法国外交部去信通知法庭书记官长,任命麦克尔先生为其代理人,另外有简·埃尔先生和杰克奎斯先生作法律顾问,以便出庭应诉。
按照《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75条第2款(注:《法庭规则》第75条第2款:当事一方在审讯中的最后一次陈述结束时,其代理人在不重述其论据的情况下重读该当事方的最后诉讼主张。由该代理人签署的该最后诉讼主张的书面文本的副本应送交法庭并转交当事另一方。)的要求,塞舌尔(原告)方面在请求书中宣称:
1.国际海洋法法庭依照《公约》第292条有审理今天所提交申请的管辖权;
2.当前的请求书是允许提出的;
3.法国违反了《公约》第73条第4款,(注:《公约》第73条第4款:在逮捕或扣留外国船只的情形下,沿海国应通过适当途经将其所采取的行动及随后所施加的任何处罚迅速通知船旗国。)没有通过适当途径将扣留“蒙特·卡夫卡”号船的事项通知塞舌尔;
4.法方设定的担保在数量上、性质上和形式上都是不合理的;
5.关于“蒙特·卡夫卡”号船长:
(1)注意到法方没有遵守《公约》有关立即释放被逮捕的船只的主人的规定;
(2)请法国立即释放船长而无需提供保证金;因为船只和货物已是合理保证,且考虑到他是欧洲人这一事实及不可能判他入狱。
(3)注意到法方没有遵守《公约》第73条第3款(注:《公约》第73条第3款:沿海国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违犯渔业法律和规章的处罚,如有关国家无相反的协议,不得包括监禁,或任何其它方式的体罚。)而对船长进行了非法监禁。
6.法庭应当考虑到被扣留的货物、捕鱼设备、鱼饵及汽油都构成了保证金的一部分,且根据我们的计算,上述物品价值980万法国法郎。
法国在答辩状中称:
法国政府以前述事实和法律考虑为基础,同时保留修改和补充这一提交的权利,要求法庭拒绝代表塞舌尔共和国的请求,并宣布和判决:
1.法国主管法院所裁定的保证金是合理的;
2.2000年11月27日塞舌尔代表向法庭提出的请求书是不允许提出的。
(三)法庭对管辖权的裁定
原告塞方指称被告法方没有遵守《公约》第73条的规定迅速释放船只和船员,且认为被告设定的保证金是不合理的。双方没有在从扣留起10日内达成将此事项送交其他法院或法庭的协议,因此,根据《公约》第292条,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此诉讼请求具有管辖权。
法庭认定,塞舌尔和法国都是《公约》的缔约国。塞舌尔1991年9月16日批准《公约》,1994年11月16日《公约》开始对其生效。法国1996年4月11日批准《公约》,《公约》于1996年5月11日起对其生效。塞舌尔作为“蒙特·卡夫卡”号的船旗国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塞舌尔方面已按照《公约》第292条第2款由其代表提出诉讼请求,且该请求书满足《法庭规则》第110条和第111条(注:《法庭规则》第110条和第111条规定了“请求迅速释放”的申请提出的条件和申请书本身应具备的内容。)的规定。被告没有对法庭的管辖权提出质疑。出于以上原因,法庭认为对此请求具有管辖权。
法庭一致通过,依据《公约》第292条,法庭对于塞舌尔于2000年11月27日提交的诉讼请求有管辖权。
(四)法庭对法方是否违反《公约》第73条第3款、第4款的裁定
原告塞方认为,使“蒙特·卡夫卡”号船长处于法院监视之下构成了事实上的拘禁,严重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违反了《公约》第73条第3款。其进一步指出,塞方没有收到对其船只扣留的适当形式的通知,从而认为法方违反了《公约》第73条第4款。
被告法方认为,根据《公约》第292条,法庭的权限并未扩大到可以对原告的上述指控作出裁决。它进一步认为对方的指控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它否认法院的监视就等同于拘禁,因为这样的监视并未剥夺船长的自由。而且11月10日,法国将此事书面通知了塞舌尔驻巴黎总领事。在“卡莫科”号案中,法庭曾裁定有关违反《公约》第73条第3、4款的指控是不允许提出的。
法庭在“卡莫科”号案中曾认定,《公约》第73条第2款在《公约》第292条有相应规定,法庭对在保证金或其它财政担保提供后法方仍未执行迅速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的案件具有管辖权。然而,《公约》第73条第3、4款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条款,因此法庭不能受理这样的申请。[3](P.59)根据《公约》第292条第3款,法庭处理关于释放的申请,并且应仅处理释放问题,而不影响在主管的国内法庭对该船只、其船主或船员的任何案件的是非曲直。因此,法庭一致通过,塞舌尔关于法国未遵守《公约》第73条3、4两款的指控不能提出。
(五)法庭对法方是否未遵守《公约》第73条第2款的裁定
原告塞方认为被告法方没有遵守《公约》第73条第2款“被逮捕的船只及船员,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后,应迅速获得释放”。
法庭对此一致通过,关于法方未遵守《公约》第73条2款的请求可以提出;以19票对1票,认为原告提出的指控是理由充分的;以19票对1票,判决法国在收到由法庭决定的保证书和其他财证担保后应立即释放“蒙特·卡夫卡”号及其船长。
原告认为圣保罗初审法院裁定的总额达5640万法国法郎的保证金非《公约》第73条第2款意思范围内的“合理的保证书和其他担保”,法庭应当行使其权力,依照《公约》第292条确定合理的保证金并命令提交保证金后释放船只以及无需保证金就释放船长,理由是他不可能被判入狱。原告认为保证金的数量应该为220万法国法郎。
法庭的观点是保证金不应太过分且不应与所称侵犯的严重性无关。《公约》第292条是用来确保沿海国在根据其第73条第2款确定保证金时要基于对相关事实的合理评估。
法庭指出,“蒙特·卡夫卡”号船长没有通知法方该船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法庭进一步指出,船上配有能够发送和接受电讯的无线电等设备。
圣保罗初审法院认为船上的1580吨鱼应有一半是在法方专经济区内捕获的,但法庭认为这一推断与其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法庭认为其掌握的情况不足以证明这1580吨鱼捕自何方,也不足以证明“蒙特·卡夫卡”号在法方专属经济区内停留了多久。
法庭经过全盘考虑并以事实为根据,认定法国圣保罗初审法院裁定的5640万法国法郎的保证金是不合理的。法庭认为保证金应为1800万法国法郎。1580吨鱼等值于900万法国法郎(法方所估算,塞方无异议),剩余的保证金900万法郎除双方另有协议外,应以银行担保的形式支付给法国。
法庭据此以17票对3票裁定,保证金和其他财政担保的构成为:(1)900万法郎作为法国当面没收的1580吨鱼的等值货币;(2)总价900万法郎的保证书。法庭一致通过,保证书应以银行担保形式提出,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以其他方式。法庭以18票对2票裁定,仅当法方握有的财政担保的货币等价值不足以支付法国国内法院最终判决决定的数量时才可动用银行担保。
至此,“蒙特·卡夫卡”号案获得了合理的解决。
二、《公约》赋予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处理“请求迅速释放”案件方面以独特地位
前已提及,法庭登记的8个案件中4个案件纯粹是关于“关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的。法庭依据《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及时审理并做出了合理判决,证实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解决此类海洋法争端方面的独特作用。而这种独特作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整个争端解决机制有关,是《公约》缔约国赋予的。
《公约》第287条第1款规定:
“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应有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方法,以解决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a)按照附件六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b)国际法院;
(c)按照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
(d)按照附件八组成的处理其中所列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争端的特别仲裁法庭。”
该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解决海洋法争端有多种审理机构,而且这四个机构处于同等地位。二是缔约国可以自由选择同等地位的审理机构,坚持了自由选择解决方法原则。
该条第3至5款规定:
“3.缔约国如为有效声明所未包括的争端的一方,应视为已接受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
4.如果争端各方已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该程序。
5.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
这样就赋予了依据《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一种剩余备用作用。[4](P.209)国如果在将管辖权交给不同法院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则该争端应提交附件七规定的仲裁;如果在一个已就所选择的法院做出声明的国家和另一个没有做出这种声明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则该争端应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如在作出声明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而这些声明在发生争端时被认为尚未生效,或者没有作出声明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则该争端仍应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解决。《公约》将这种剩余备用作用赋予依附件七设立的仲裁法庭而不是国际海洋法法庭。但是,由于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固定的和事先组成的,附件七规定的仲裁法庭则需临时协议组成,后者费时费力;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由《公约》缔约国选举产生,仲裁庭仲裁员由当事各方协议指派,后者的当事方似乎更能体现自己的意志,但前者在解决争端时更无倾向性;国际海洋法法庭适用《公约》以及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范来判案,而仲裁法庭在适用法律方面带有更大的任意性。所以,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门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可以更有效地解决海洋法争端。
事实上,尽管国际海洋法法庭只是四种适用强制程序的法院或法庭的一种,也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仍是偏重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庭已处理的8个案件已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法庭对“蒙特·卡夫卡”号案的审理表明,《公约》第292条关于被扣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规定使国际海洋法法庭处于重要地位。如前所述,只要是《公约》缔约国,在扣留国和请求国不能就释放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请求国可直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释放申请,而不必拘泥于双方依据《公约》第287条所作的选择。这种管辖权的强制性确保了法庭的权力。而法庭根据《法庭规则》第112条规定应好不迟延地审理此类案件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判决,(注:《法庭规则》第112条规定此类案件应优先审理,且不得迟于收到申请书后15天进行审讯,审讯结束后不得超过14天应开庭宣读判决。)这保证了法庭处理此类案件的效率,也实现了法官们在制定《法庭规则》时坚持的目标:能够以“众所关注的高效率和最小的耽搁和花费”处理递交给它的案件。[5](P.541)法庭在“塞加”号案、“卡莫科”号案及“蒙特·卡夫卡”号案中都作出了成功判决,在合理确定保证金数额、敦促扣留国释放被扣船只和船员方面起到了国际法院(ICJ)、仲裁法院或法庭无法替代的作用。(注:国际法院(ICJ)、仲裁法院或法庭都没有绝对的强制管辖权。)实践证明国际海洋法法庭处理关于“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海洋法争端行之有效。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法庭在处理关于“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海洋法争端时要受到《公约》第292条第3款的限制,即处理释放问题,不应影响扣留国的国内法庭对该船只、其船主或船员的任何案件的是非曲直的判断,扣留国当局仍有权随时释放该船只、其船主或船员。法庭在“塞加”号案中对此作了说明。此外,关于“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请求只能由船旗国或经授权的船旗国代表提出,如果一国不是被扣船只的国籍国,则无请求权。在“大王子”号案中法庭据此驳回了伯利兹的诉讼请求。[6]
三、客观认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处理海洋法争端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一方面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处理海洋法争端中处于中心地位。
国际海洋法法庭除了在处理关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的海洋法争端方面起重要作用外,还有两方面的独特地位:
(一)《公约》第290条有关规定临时措施的条文让国际海洋法法庭起到在“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案件中同样的作用。荷兰代表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曾建议,如果争端各方都只接受了仲裁法庭的管辖,那么,应由另一常设机构来规定临时措施,因为该临时措施可能有必要在仲裁法庭组成前予以规定。[7](P.22)《公约》第290条第5款对此确定的机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依据该款,将争端交付仲裁的情况下,在仲裁法庭组成之前如需要规定临时措施,争端各方可协议由任何法院或法庭来规定(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如在请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那么则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关于区域内活动时,则由海底争端分庭)依据《公约》规定来行使规定临时措施的权利。当然,受理争端的法庭一旦组成,对这种临时措施可予以修改、撤销或确认。国际海洋法法庭处理的“塞加”号案的第二个诉讼程序是“临时措施”,被登记为第3、4号案的“南方金枪鱼”案也是关于请求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诉讼,法庭分别作了不指示“临时措施”和指示“临时措施”的裁定。[8]
(二)依据《公约》第287条第2款,缔约国对四种法院或法庭的选择并不影响缔约国对“区域”内活动的争端接受海底争端分庭的管辖。尽管海底争端分庭有其独立性,但毕竟合并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当中,以法庭分庭形式出现。所以,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解决“区域”内活动的争端方面,起着其他法院或法庭所不具有的作用。但法庭目前还无此类实践。
综上所述,尽管《公约》第287条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其他法院或法庭处于并列地位,而且,是仲裁法庭而不是国际海洋法法庭起剩余备用作用,但是从《公约》的相关条文及各国的态度来看,国际海洋法法庭(包括海底争端分庭)在解决海洋法争端中会起到独特作用。特别是上述关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规定“临时措施”以及有关海底争端的案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任何缔约国都必需接受。(注:依据《公约》第309条,除非本公约其条款明示许可,对本公约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所以,任何缔约国都不得以保留的方式排除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上述三类案件的管辖。)
我国1996年5月15日批准了《公约》,今年是我国批准《公约》5周年。迄今,我国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尚无实践,但我国海岸线漫长,除个别地方,大部分沿海海域存在与其它国家划界问题。尤其在我国南海海域,一些国家抢占我岛屿,逮捕我渔船及渔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关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实践,研究其规约和规则,对我国无论是主动起诉还是被动应诉都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并非解决海洋法争端的唯一法律机构。
依据《公约》第287条,国际法院、仲裁法庭、特别仲裁法庭亦具有解决海洋法争端的职能。截止1999年11月,有24个国家依据《公约》第287条作出选择声明。其中希腊、坦桑尼亚、乌拉圭只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佛得角、克罗地亚、芬兰、德国、意大利、阿曼、葡萄牙等既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也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澳大利亚、德国、葡萄牙还接受仲裁或特别仲裁;智利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及特别仲裁;阿尔及利亚、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只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古巴和几内亚比绍则只表示反对国际法院对任何类型的争端的管辖;埃及只接受仲裁;乌克兰接受仲裁和特别仲裁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对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问题的管辖。[9]可见,这24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既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也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与只接受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的国家不相上下。
在实践中,国家也并非把海洋法争端只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近期,厄立特里亚诉也门的主权问题及海洋划界案提交给了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10]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的双方在加勒比海的海洋划界案、西班牙诉加拿大渔场管辖权案、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芬兰诉丹麦的大海峡通过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疆界问题案、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吉丹岛和西巴丹岛主权问题案等则提交给了国际法院。[11]
综观国际海洋法法庭、常设仲裁法院及国际法院对海洋法争端的处理,可以看到,凡是涉及到海域划界或领土争端的案件,国家大多愿提交国际法院或交付仲裁;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指示临时措施的案件才交付国际海洋法法庭。到目前为止,国际海洋法法庭只审理了一起渔业案(南方金枪鱼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各国对待三机构的态度及约束三机构的条约或文件的规定。争端当事方在仲裁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常设仲裁法院自1993年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注:常设仲裁法院通过了一系列任择性仲裁规则,扩大其仲裁主体;设置了和解、调停和斡旋等机制。)会提高仲裁解决海洋法争端的地位;国际法院55年的历史,尤其是它在解决海洋法争端方面积累的经验使得国家更愿意利用它。但国际海洋法法庭会逐步提高其在解决海洋法争端方面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解决海洋法争端的专门性国际司法机构,还因为《公约》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赋予它在有关“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规定“临时措施”以及有关海底争端的案件方面以强制管辖权,赋予它可以受理国家以外的实体包括个人的诉讼。而且,随着《公约》缔约国普遍性增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实践增多,人们必然会去重视、研究并利用国际海洋法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