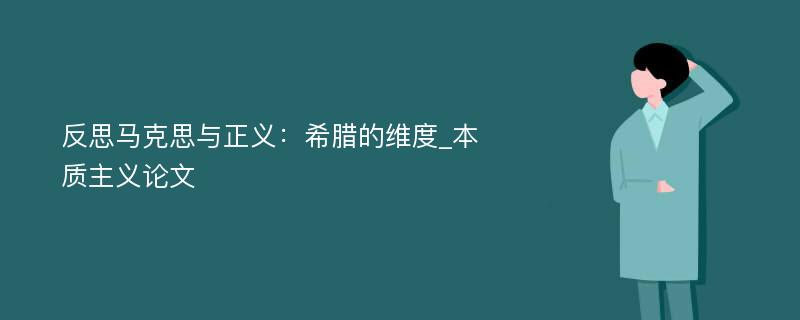
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希腊论文,维度论文,正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伦理身份问题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在英国,N.杰拉斯( Norman Geras) 发表的文章对澄清这一问题中的关键点作出了很大贡献。(注:N.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见杰拉斯:《革命文献:马克思主义论文》( London:Verso,1986年版) 。初次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85年第150期;以及《将马克思带到正义:补遗与反驳》,载于《新左派评论》1992年第195期。1985年那篇文章包括关于马克思与正义这一主题的书籍与文章的完整书目,1992年的文章增订了该书目。R.佩弗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版) 的第2、3章和整个第二部分中详细讨论了北美学界的争论。)本文将论证,对马克思思想的希腊维度的理解有助于澄清暗含在其社会理论中的伦理观点的起源,在论证这一问题的同时,我将对杰拉斯的立场作出一些批评。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中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蔑视伦理话语,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争论中的道德主义的干预,也一以贯之地持反对态度,曾宣称,“共产主义者根本不宣讲道德。”(注:K.马克思与F.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选集》( London:Lawrence,and Wishart,1976年版) 5,第247页。以下,《选集》后面的数字表示卷数。)他没有兴趣抽象地讨论,如何以及为何个人应以道德上可辩护的方式对待他人这样的问题,并认为资本主义要么毁灭了道德,要么就是将之变成一个弥天大谎。(注:K.马克思与F.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选集》( London:Lawrence,and Wishart,1976年版) 5,第247页。以下,《选集》后面的数字表示卷数,第73页。)首要任务是直面物质生产过程中社会痛苦的深层原因,用道德规范来支撑社会主义思想的企图则被视为是对这一任务的偏离。(注:这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得到了解释,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了多种社会主义文献。见《选集》6,第507-517页。)然而,他的著作充满了对资本戕害人性的力量的愤慨描述,这些描述是用明显的道德语言表达的。虽然总的来说我理解拈出马克思思想的伦理维度的尝试,但我仍将证明,杰拉斯把这种张力当作“无处不在的矛盾”(注: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第56页。)的做法错了;不诉诸他的论断——“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这么想”(注: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第36页。),也能阐明马克思的立场。我将证明,马克思对正义采取的是一种“有限相对主义”( qualified relativism) 的立场,他承认资本主义就其自身来说是正义的,但他也揭示了,从由资本主义自身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替代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正义是有限的、不足的。我质疑杰拉斯的结论,此结论认为,马克思通过援引支配生产资料的“普通的道德权柄”( generalized moral entitlement) 隐隐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而这种权柄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权利。(注: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第45页。)最后,我不同意他的下述观点: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为社会主义的奋斗中无需最终目标。
杰拉斯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一个真实而又根深蒂固的矛盾: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同时又用道德的语言来谴责它。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正义的,因为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正义标准。例如,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说,资本主义契约的内容是正义的,“只要它符合并适应这一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资本论》( Harmondsworth:Penguin,1981年版) ,第3卷,第460-461页。)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注:马克思:《选集》24,第84页。)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明确地否认了下述观点:当资本家获利时,出卖劳动力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01页。)或者,他们上当受骗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31页。)另一方面,马克思用道德语言谴责资本主义,这在杰拉斯看来就等于认为它是不正义的。在《资本论》第1卷的许多地方,马克思把获取剩余价值描绘成“抢劫”、“偷窃”、从工人那里“榨取掠夺物”以及“盗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38、728、743、761页。)在其他一些地方,他用朴素的语言将之称作“赃物”和“窃取异化劳动时间”。(注:可分别参阅,《剩余价值理论》(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69年版) ,第2章,第29页,以及《大纲》,见《选集》29,第91页。)杰拉斯的结论是,马克思做出了超历史的道德判断,尽管他同时认为对每一生产方式来说所有的正义原则都是特定的,不能用它们去评价其他生产方式中的实践。
一些学者认为,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正义观和同时用道德语言批判资本主义,这二者之间并不必然构成矛盾。G.布兰科特( George Brenkert) 、S.卢克斯( Steven Lukes) 和A.伍德( Allen Wood) (注:(注:J.布兰科特:《马克思的自由伦理学》(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年版) ;A.伍德:《对正义的马克思式的批判》及《对胡萨米的回应》,见M.柯恩等:《马克思、正义与历史》(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ss,1980年版) 。)已分别论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基于诸如自由和自我实现等价值观,而非基于以永恒原则为基础的正义概念。J.麦卡尼( Joseph McCarney) 认为,我们不一定要从与正义概念相当的理论水平上来看待那些马克思用来描述剥削的道德语言。他提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相对特定的社会秩序”的正义和具有“某种超历史意味”的评价区分开,因为毕竟,把正义当作“受时代环境的约束并具有明确的词法规定的”(注:J.麦卡尼:《再论马克思与正义》,见《新左派评论》1992年第195期,第34-35页。J.麦卡尼之前论述了,马克思的道德观念与其社会理论不相干。见J.麦卡尼:《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London:Verso,1990年版) ,第172-174页。)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麦卡尼基本是正确的,但当杰拉斯要求出具证明以支持并解释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时,其要求也十分合理。(注:N.杰拉斯:《将马克思带到正义》,第62-65页。)在下文中,我将试图阐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是一个“有限相对主义”的概念,并试图揭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早年浸润于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结果。
马克思的伦理立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他的人的本质的概念,此概念是杰拉斯极力捍卫的。(注:N.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 London:Verso,1983年版)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过,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是其社会理论的伦理基础。(注:此论述略述于,王尔德:《马克思与矛盾》( Aldershot:Avebury,1989年版) ,第23-27页。以及王尔德:《伦理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批评者》(London:Macmillan,1998年版),第2章。)马克思认为,使我们特别地成为人的是我们创造性地和社会地进行生产的能力,这一生产概念将思与行结合在一起。人类劳作的产品是我们特殊性的物质证明,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注:《选集》3,第302页。),但在前后相续的诸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者并未感到这种力量是他们自己的,广大生产者从未控制过生产过程。历史始终在实现着人的本质,但总是以扭曲或歪曲的形式进行。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了不可避免的结构矛盾的全球系统,在其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生产者控制生产过程并使其存在与本质和谐一致的机会,从而宣告了人类社会“史前史”的终结。(注:《选集》29,第264页。)这一观点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反映出马克思与古希腊思想的持久联系。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并未简单地运用事实性语言来定义人的本质,而是暗示它应该被完成。人的本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既定的完成,被马克思用史诗般的语言构想为持续而漫长的阶级斗争旅程的终点。
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的不公正时,用了明显的辩证法语言。杰拉斯指责马克思在证明平等交换转变为不平等交换的过程中采用了“辩证法的狡计”。(注:《选集》29,第27页。)在《大纲》( Grundrisse) 中,马克思提出,“通过一种特殊的逻辑,资本方的财产权辩证地转化为对异化产品的权利……无偿占有异化劳动的权利。”(注:《大纲》,见《选集》28,第386页。)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商品生产(与其自身内在的法则一致)经过了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财产法则必须经过辩证的颠倒,以使其自身变成资本主义占有的法则。”(注:《资本论》第1卷,第733-734页。)在等价交换的表象背后潜藏着剥削的本质。通过揭示隐藏在等价物之自由交换的花言巧语背后的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马克思还展示了权力( power) 是如何从生产者那里抢夺过来,又以货币或资本的形式作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力量呈现在他们面前。(注:同样的表述还用于1857年(见《选集》28,第132页)和1844年(见《选集》3,第212页)。)工人在与资本家交换其劳动能力时,“被迫放弃了它的创造力,就像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自己的长子权的以扫( Esau) 一样。”(注:《选集》28,第233页。)这一自由的丧失铭刻在资本主义的显形过程中,而劳动力的买和卖则产生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马克思来说,剥夺工人劳动的创造力是对人的本质的扭曲。杰拉斯反对说,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契约的对错时诉诸辩证法只能把问题搅乱,因为工资关系要么是等价交换并因此是正义的,要么不是,而“一物不能是其反面”。他总结说,评论者对这一问题的困惑因而就是“马克思自己语焉不详的结果”(注:N.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第27-28页。)。如果对照杰拉斯早年研究马克思对现象/本质的区分的著作,(注:N.杰拉斯:《本质与现象: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的诸方面》,见《革命文献》,第63-84页。)他对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所作的连根拔起式的批评就有些令人吃惊了。但这就要求我们更仔细地思考马克思关于本质与现象的著作,及其如何与他著作中所暗含的伦理立场相适应。带着这些问题,现在我将转而讨论马克思思想的希腊维度。
希腊维度
在由黑格尔的幽灵及其颠覆者费尔巴哈所主宰的思想环境中,马克思开始锻造自己的社会理论,但更为遥远的古希腊的声音也回响在19世纪初德国的哲学讨论中,这对马克思的教育特别重要。我并不想以牺牲黑格尔为代价,来抬高亚里士多德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产生的影响,说它是起主要作用的,(注:正如H.卢巴兹在《马克思的亚里士多德维度》一文中所做的。见1977年4月1日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相反,我宁愿从以下这个假定出发,即,黑格尔于共同体( Sittlichkeit) 的观念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都大大得益于他们各自对古希腊哲学的汲取。(注:关于亚里士多德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影响,可参阅D.迪普:《变形的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G.麦卡锡编辑的《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理论与古典学》(Savage,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1992年版),关于黑格尔可参阅,A.伍德:《黑格尔的伦理学》,见F.贝瑟编辑的《剑桥指南·黑格尔》(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年版)。)随着J.温克尔曼( Johann Winckelmann) 对古希腊艺术的重新发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希腊迷恋:( Graecomania) ”的倾向。(注:H.梅维斯:《卡尔·马克思与希腊古典学对十八世纪德国思想的影响》,见麦卡锡编辑的《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M.德·高尔耶( Michael De Golyer) 提到了德国的希腊“崇拜”,柏林毫无疑问是古典学的中心,而1831年开始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一个现代版本则使这一“崇拜”达到极至。(注:M.德·高尔耶:《马克思发源地的希腊之声》,见麦卡锡编辑的《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第117页。)马克思在中学以及后来在大学时沉浸于希腊和拉丁文化之中,他的藏书中有许多希腊和罗马的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原文形式的。(注:可参阅,M.德·高尔耶:《马克思发源地的希腊之声》,第115页。在1861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他的许多古希腊文本在18世纪50年代居住于科隆时散佚了。(见《选集》41,265页)关于他在学校的学习,可参阅,S.普拉维尔:《卡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Oxford:Clarendon,1976年版),第1-4页。)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原创性比较,而这一论文的准备工作需要遍读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将亚里士多德称作“天才”、“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注:K.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2、153页。)他认为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启蒙的最伟大代表”和“真正彻底的古代启蒙者”。(注:《选集》1,第73页;《选集》5,第141页。)
马克思一生都在不断温习史诗作品,我们首先来考察其哲学与表现在这些史诗作品中的古希腊文化的伦理学的亲缘性。如J.安娜斯( Julia Annas) 所写的,古希腊伦理学的中心要素是整全性,事物聚集、和解之感。(注:J.安娜斯:《幸福的道德》(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年版),第1章。)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有很好的例证:凭着通过艰苦经历获得的完整感,暴行与受难这两个极端得到了和解。在所有的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对马克思影响最大,他甚至将这一虚构人物描绘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注:见《博士论文》的前言,《选集》1,第31页。)普罗米修斯(“预见者”)从诸神那里偷来火,并以之增强了人的力量。诸神报复他,将他绑在岩石上数千年。晚上他受苦寒,白天一只鹫鹰啄食他的肝脏,但他忍受了这些痛苦,最终获释并与大神宙斯和解了。(注:在神话中是这样的。而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结局是他被锁链缚在岩石上,其解决留给了另一部悲剧。这个剧本没有保存下来。)这种只有通过壮烈斗争的经历才能获致的最终和解是马克思哲学著作的一个主旋律。例如,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无产阶级革命把敌人打倒在地,“只是为了使他从大地重新汲取力量,再次更有力量地立于他们面前,因其无比巨大的目标一次次卷土重来,直到有一天,一切返回都不可能了。”(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选集》11,第106-107页。在《法兰西内战》中他表达了类似的情感,见《选集》22,第335-336页,在那里他提到工人阶级的“漫长的斗争”和“英雄的决心”。)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引用乔治·桑的话总结说,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注:《选集》6,第212页。)
我认为,古希腊伦理哲学照亮了暗含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的伦理学,而这种伦理哲学的特殊要素是: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正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与马克思的本质主义的相似性,(注:在英国,这一观点最重要的鼓吹者是S.麦考,见《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London:Duckworth,1985年版),第58页;一些美国学者为前面引用的G.麦卡锡编辑的《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一书撰写了文稿;还可参阅M.瓦迪:《马克思:思考可能之事的人》(Paris:Meridiens Klincksieck,1992年版)。)如S.麦考( Scott Meikle) 所指出的,马克思首次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翻译成德文,在该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什么使我们与其它动物不同。(注:S.麦考:《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第58页。马克思摘录《动物学》的手稿写于1840年,现存于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协会。马克思在之后一年摘录了休谟的《人性论》,这显示了他对人性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这份手稿也存于阿姆斯特丹档案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端处就奠定了其本质主义的基调:
“所有事物都从其功能与能力产生出其本质特征;而这遵循下述原则:如果它们不再能实行其功能了,我们就不应当说它们还是与之前同样的事物,而只能含混地说它们还拥有与之前同样的名称。”(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年版),E.贝克编辑翻译第6页。)(注:1253a20到23,可参考中译本,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第9页。中译文为:“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体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译者)
对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来说,我们的社会性与理性都是人的本质的要素,而运用这些能力必须是一个人的固有功能。亚里士多德关注公民德性方面的自我发展,而公民最终必须有机会对真理进行沉思,从而达至幸福( eudaemonia) 。(注:A.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从荷马时代到二十世纪的道德哲学史》(London:Routledge,1995年版),第7章。)马克思认为,构成人的本质的不仅仅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人类当然是道德的动物,但我们的特殊性显示于我们的生产、我们有意识的生活活动之中。他把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目的( telos) 。只有消除了私人财产,易之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这一人的本质才能被全人类实现。这里所设想的是一个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普遍共同体,若没有这一共同体,我们就不是完全自由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其成熟著作中,马克思显得离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概念更近了一些。正如我们在前一节看到的,早期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共同劳动与相互交换的令人愉快的经验表现其自由,但在《资本论》等3卷关于自由的著名段落中,他认为只有当我们完全免于需要的时候,真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59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较前部分中所评论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除非其他人去工作(不仅是工作,还包括对工作的监视),否则自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预想,可以运用合作规划与先进技术使必要劳动时间最小化,从而实现自由。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亚里士多德想象出自动机这样的理想生产图景,以使人类无需劳动。(注:《资本论》,第1卷,第532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对借贷的蔑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靠借贷获利“否定了正义”,因为它基于“相互欺骗”。高利贷者“被人憎恨理所当然”,因为他使用货币想达到一定目的,而货币非为此种目的而被创造。(注:《资本论》,第1卷,第267页,可比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8-29页。)换句话说,便于商品交换是货币的本质,而高利贷者在扭曲这一本质。亚里士多德指责商人是唯利是图者( kapelos) ,因为他们的行为损害了使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纽带。蒲鲁东的追随者提出,可以通过更“纯洁”的方式运用货币——例如,“劳动货币”这样的方案。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排除了这种观点,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明,他赞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思考。(注:马克思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作为该书的开始,这表明,在马克思形成对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的思想进程中,亚里士多德是多么重要,见《选集》29,第269页。此处还有六处引用,有些是希腊文。)
人们拒斥本质主义的通常理由是,它落入了从“实然”推出“应然”这一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陷阱中。我们如何能从用事实性和描述性的语言来界定的本质推导出道德承诺?确实,人类因其社会创造力而在本质上是人,但这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本质的实现应被看作是在道德上可欲的目标。R.诺曼( Richard Norman) 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认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并不依靠本质主义的论证来表明自我实现这一目标是正当的,他所依靠的是经验的论证。也就是说,马克思指出,如果人的存在继续被异化,就会产生广泛的不满。(注:R.诺曼:《道德哲学家:伦理学导论》(Oxford:Clarendon,1983年版),第176-178页。)此言诚然,但这并未使马克思的论证变得不那么本质主义。我们要记住,本质的定义绝非完全事实性的,它包含着价值。A.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说,在前提中,尤其是那些功能性的前提中,常常包含价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是用功能性的术语表达的——他把“人”和“活得好”的关系与一个竖琴(手弹竖琴)弹得好联系在一起。(注: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道德理论研究》(London:Duckworth,1981年版),第54-56页。)马克思则将人的本质置于我们的社会创造能力之中,而这包括我们以道德的方式规范生活的能力。人之为人的东西包括“应然”,因此事实上我们是在从“应然”推出“应然”。在《马克思与伦理学》一书中,P.凯因( Philip Kain) 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与马克思的本质主义的相似之处,并正确论述了,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深植于我们的本质之中。他承认从非道德前推出道德结论是不合理的,但如果真实世界的事实已经含有价值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事实推出价值。(注:P.凯因:《马克思与伦理学》(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年版),第30-32页。)麦金太尔与凯因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之为人的看法包含着价值,他们的论述是正确的;正如M.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c) 所总结的,在马克思那里,“实然”总是充满了“应然”。(注:M.马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评》(Ann Arbor,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3年版)。)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物的本质是其目的( telos) ,“在一个存在者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终极形式。”(注:S.麦考:《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第179页。)长久以来,目的论这一哲学观念已不再进行,它常常被等同于非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因为它按照一个目的或者终极因来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发展。但是这种了解并不神秘,例如,只有当我们知道一粒橡子的自然发展会产生出一棵橡树时,我们才能理解橡子的本质。我们可以扩展这一视角,帮助我们弄清楚历史发展是什么意思。黑格尔正是这样做的,在《历史哲学》中他声称,“整个世界的终极因”是人类自由的不断展开。(注:G.W.F.黑格尔:《历史哲学》(New York:Dover,1956年版),第19页。)马克思采用了目的论的方式,而并非仅只宣称历史必然性,他还试着揭示“控制特定社会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消亡及其被另一更高社会机体替代的过程的具体规律”。《资本论》的一位评论者对马克思的方法做出的这番描述,被马克思赞许地接受了,认为它准确地概括了自己的辩证的方法。(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2页。)
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思考了,为什么即使产生希腊艺术与史诗的环境与他自己时代的环境已截然不同,人们仍不断从它们那里获得巨大的审美快感: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注:《选集》28,第47-48页。)
这种在更高水平上重现孩子所揭示的真理的吁求,揭示了他自己的思想的目的论性质。他把历史想象成是奥德修斯式的跋涉,寻找安宁的家的漫游。在他即将献身共产主义之际,马克思评论说,自由的感觉已同古希腊人一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它能够“再次将社会转变成为了其更高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人类共同体,转变成民主国家。”(注:《选集》3,第137页。)比起黑格尔的评价来,在这里,古希腊的“自由”概念得到了马克思的更高评价。正如H.梅维斯( Horst Mewes) 所评伦的,马克思可被看作是“受发生在18世纪德国的古代与现代的对话影响”的最后几个重要人物之一。(注:H.梅维斯:《卡尔·马克思与希腊古典学对十八世纪德国思想的影响》,见《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第21页。)马克思视共产主义为人类自由的实现、漫长斗争过程的合理巅峰。
目的论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但S.麦考认为马克思的目的论思想并不涉及某种“神秘学”——在这种神秘学中,未来因果性地按照现在运行;或者,目的论式的变化是“隐秘目的之计划的实现”——他言之有理。(注:s.麦考:《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第11页。)目的论论证并不意味着终极因代替动力因发挥动因的作用。(注:s.麦考:《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第170-171页。)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目的论的,因为它把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是不可改变的,而其终结亦被看作不可避免的。但他所设想的另一途径却要通过努力斗争来争取,受既定环境的限制,并不保证成功。当然,当马克思在一些论战文章中写到无产阶级的未来胜利时,他确实太有把握了。例如,在1848年他宣称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1871年他提到了某种“更高形式,当前社会受其自身经济动力驱使而不可抵抗地趋向它。”(注:可分别参阅《共产党宣言》,见《选集》6,第496页,以及《法兰西内战》,见《选集》22,第335页。)目的论的方式可能会激发这些过度的预言,但它也使我们去检验内在的趋势,从而预计可能的结果并相应地制定策略。与杰拉斯相反,我之后将论证,目的论的方式并非不需要最终目标,只是它坚持,要给那些最终目标注入严格的现实感。
马克思对人类自由这一目标的承诺,是否意味着他认为一个完美的社会即将来临?这是卢克斯对马克思的漫画,他将一种马克思所没有的完美主义强加给马克思,这种完美主义暗示着一种既无不满又无野心的惬意生活。(注:S.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Clarendon Press & Oxford Univesity Press:Oxford & New York,1985年版),第142页。)卢克斯注意到了马克思对权利( Recht) 的道德充满蔑视,他强调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并总结说,“哪怕是高等的、社会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天使也需要权利。”(注:S.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Clarendon Press & Oxford Univesity Press:Oxford & New York,1985年版),第99页。)马克思批评诉诸权利的作法,认为这使个人有权利对抗国家,从而提供了虚假的达至社会和谐的保证,而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分离这一问题却未被触及。他不同意仅靠许诺“人的权利”,而不改变一个异化的、私有化的社会的结构,就能实现人的解放。(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选集》4,122页。)他还注意到,一旦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权利所能提供的政治解放或民主就会被扔到一边去。(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选集》11,第114到118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马克思如卢克斯所说的那样,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给法律留下任何位置。对马克思来说,权利属于资产阶级国家,而资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它反映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社会明显也需要统治与管理机构,不过它们不再构成马克思所定义的国家,因而法律不会等同于权利。卢克斯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天使”把马克思断然拒斥的浪漫主义强加于马克思身上。他所设想的人类解放不需要天使,只需要民主来消除最后的“敌对的社会生产关系”。(注:《选集》29,第263-264页。)随着真正人类历史第一次开始展开,各种差异自然仍会继续,但这些差异将不再基于剥削或压迫。这里所假定的并非完美的一致,而是真正的民主认同以决定如何解决这些差异。(注: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年版) 中优美地描述了这一伦理最终目标,他展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怎样以人性的方式解决离婚、异议和犯罪。)没有意见的差异就没有什么可批判的了,而批判恰是马克思自己所期望的在未来社会中的职业。(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选集》5,第47页。)
现在回到正义概念上来。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在论述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关系时,多少有些含混,而马克思很熟悉这些论述。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赞扬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分析政治经济中的价值形式的思想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1页。)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商品要能公平交换,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可通约。测量的标准是需求,而这是通过货币这一手段表现出来的。然而,虽然货币表现了可通约性,但这并未解释可通约性。马克思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认识到劳动是商品价值中的一般要素,这是因为他生活在基于人的不平等之上的奴隶制社会:
除非人类平等的观念成为永久固定的流行观点,否则价值表现的秘密——各种劳动,因为而且只要它们是一般人类劳动,就是平等和等价的——就不会被发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2页。)
马克思提到的段落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5卷,这一卷主要是讨论正义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的观点强调了公平与互惠,如果他采用劳动价值论的话,其观点就会具有激进的涵义,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会为奴隶设立正当权利。这显然并非其意图,然而马克思可以从此处以及《政治学》中对高利贷的谴责那里获取大量的弹药,用以批判政治经济学。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强调均衡互换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公平交换的基础,而把“过度与不及”的极端指斥为不正义的。没有互惠就没有社会联结,因而城邦也就不可能团结在一起。(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Harmondsworth:Penguin,1976年版),第182-187页。)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号称在劳动契约中有互惠与公平,但这种社会产生了大量“过度与不及”的极端,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也是无法维持的。M.德·高尔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与马克思的“平等”概念是“‘共同体’这同一个概念的正反两面”。(注:M.德·高尔耶:《马克思发源地的希腊之声》,第129页。)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的人应当受到平等对待,但他愿意接受特定社会已有的社会等级。马克思致力于寻求全人类的平等,这是其著作的伦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壁鸠鲁的哲学有力地吸引了青年马克思,伊壁鸠鲁致力于无幻象的生活,这一点特别打动马克思;他把伊壁鸠鲁描绘为“最卓越的无神论哲学家”。(注:《选集》5,142页。)伊壁鸠鲁把自由看作是免于恐惧;而恐惧常常是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因而知识对克服恐惧就至关重要了。伊壁鸠鲁处在雅典民主衰落之后,就避开政治,选择精神平衡与肉体愉悦的沉思生活,这种状态就是心神安宁( ataraxia) ,其特征之一是作为非工具性目的的友爱。(注:J.加斯金:《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导论》(London:Everyman,1995年版),第xxiii页,及第xl-xli页;P.米特希斯:《伊壁鸠鲁论友爱与利他》,见《牛津古代哲学研究》(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年版),J.安娜斯编辑。)尽管从骨子里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但我觉得他的构想(个人从知识获取力量,免于恐惧,从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我实现并得到解放)中有伊壁鸠鲁的声音在回响。(注:凯因在《马克思与伦理学》中有类似观点,见该书第198页。)
在1839年的笔记中,马克思摘抄了第欧根尼·拉尔修( Diogenes Laertius) 记述的伊壁鸠鲁关于正义的观点,以此为其博士论文做准备。马克思在边白上所做的特别着重号明确显示出其重要性。(注:《选集》1,第410页,可比较J.加斯金编辑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导论》(London:Everyman,1995年版),第10页;M.德·高尔耶是唯一注意到马克思对这些段落的兴趣的潜在重要性的学者,见《马克思发源地的希腊之声》,第128-129页;关于伊壁鸠鲁论正义的讨论,可参考J.安娜斯:《幸福的道德》,第293-302页。)事实上,在他6年后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马克思称赞伊壁鸠鲁是社会契约理论的创始人时,他所引用的文本证据就是上述段落。(注:马克思:《选集》5,第141页,他还称赞伊壁鸠鲁对古代宗教的攻击。)伊壁鸠鲁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相互关系中,并依其是否有利于相互关系而变化;曾经正确的,如果不能实现其本来目标了,就不再正确了。假设有人制定了一个正义体系,如果它对每个人有效,那么它就具有正义这一“本质”,而这种有效性有其社会基础。如果事实上这种体系无助于“相互交往”,那么它就丧失了正义这一本质。伊壁鸠鲁用似非而是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正义的观点:
总的来说,此正义对全体都有效(因为它在相互交往中有用);但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全部其他可能条件使此正义并非对全体都有效。(注:马克思:《选集》1,第410页。)
此处的关键词是“全部其他可能条件”,因为它指出了正义的更高形式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正义必须建基于从本质上说来是可能的东西的基础上。伊壁鸠鲁以这种方式将一种历史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之后我将论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讨论“平等的权利”时正是这么做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伊壁鸠鲁来说正义的更高形式不在未来,而在刚刚过去的时代,在民主时期,而马其顿对希腊的胜利摧毁了这一时期。(注:G.F.帕克:《从泰勒斯到伊壁鸠鲁的希腊哲学简介》(London:Edward Arnold,1967年版),第177页。)他说,过去的正义体系失去了其作用,但仍包含正义的概念或本质,因而对那些“不让自己被空话迷惑的人”来说仍是正确的。这是用公民不服从来论证,这等于是诉诸道德良心。因而伊壁鸠鲁对正义持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而其教诲的核心以促进心神安宁为导向。他的原则与其说是社会性的,不如说是个体性的。其原则是对民主共同体的失败所导致的问题的道德超越,但关于正义的段落指出了达到社会和谐的可能性。另外,颇为有意思的是,他关于货币的腐化力量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的观点相同,而马克思所采纳的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伊壁鸠鲁认为,金钱“轻易地夺去了荣誉的力量与优美,因为……不论人们生下来多么有力,多么优美,他们都遵从更富有的人的领导。”(注:卢克莱修:《物性论》,见J.加斯金编辑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导论》(London:Everyman,1995年版),第295页。)
马克思的伦理学:有限的相对主义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对正义的观点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法律正义或“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引自《哥达纲领批判》,见《选集》24,第87页。)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然而马克思讨论剥削时明显满腔义愤。他做出的这一谴责是建立在何种伦理基础之上的?为何他将自己对不公正的指控与正义概念区分开?以这种方式他可以有效地揭示对正义和公平的自由主义要求中的不一致,以道德现实主义的方式他可以揭露资本主义正义的虚伪。马克思既把劳动契约说成是“正义的”,又把它说成是“偷窃”,这是为了强调资本主义正义体系中的现象与本质的差异,从而揭露其辩解性的伪装对资产阶级的偏袒。马克思试图揭露出,资本主义道德要求全是伪善的话,例如,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他嘲讽说:“把普遍的剥削称为普遍的兄弟联合,这种想法只可能在资产阶级的脑袋里产生。”(注:K.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讲》,见《选集》6,第464页。)这是个有趣的例子,因为事实上马克思偏好自由贸易,因为它是进步的,而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方向的估计中,这意味着自由贸易会加速社会革命。如果马克思说自由贸易有助于产生一个完全不正义的社会,他会发现自己很难支持它,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去揭露资产阶级的正义、公平和兄弟联合等概念对本阶级的偏袒。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评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等的权利”的观点,这是马克思的有限相对主义的最明显的证据。他说资本主义分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注:K.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讲》,见《选集》6,第84页。)引号暗示了可能有其他更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标准。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用相似的笔调写道,“每一种财产的社会形式都自有一套‘道德准则’”。(注:《选集》22,第505页。)在《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被消灭,“平等的权利”就是按平等的标准——劳动——来进行分配,但个人的体力与能力不同,所以平等的权利会产生不平等的报酬。此处关键点在于,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等的权利胜过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平等的权利,因为“原则与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注:《选集》24,第86-87页。)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等的权利将不再只是现象,它将成为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给予的报酬,将是透明的。然而,这仍基于个人报酬,仍可能在社会中产生不同的等级。假如能够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免费供应按照公众同意的数量增加,他更倾向于作为“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的法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选集》24,第87页。)马克思选择后者隐约出于一个信念,它比基于个人报酬的分配更公平。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诉诸的公平标准是什么?
S.塞耶斯( Sean Sayers) 的论证方式更接近于说明与捍卫马克思的观点,尽管他的文章遭到了杰拉斯的强烈批评。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并不是用超历史的标准,而是用从资本主义自身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标准来评价资本主义。(注:S.塞耶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载于《加拿大哲学期刊》,1989年增刊第15卷,第96-99页;还可参考塞耶斯:《马克思与现存的社会主义》,见D.麦克莱伦与S.塞耶斯编辑的《社会主义与道德》(London:Macmillan,1990年版),第50-51页。)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评论,在那里马克思推测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形式”来看,总有一天财产私有制会显得荒谬,正如奴隶制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显得荒谬一样。(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11页。)塞耶斯的论证符合马克思的本质主义与目的论的视角,他的这种视角得益于他接触古希腊——当然,还有黑格尔,而进步观念是其核心。(注:塞耶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第90页。)杰拉斯反对说,只要引入进步观念,我们就必定乞灵于“超验的标准”以比较两种不同的社会,从而发现它们在哪些方面更优越。(注:杰拉斯:《将马克思带到正义》,第43页。)他认为诉诸进步并不能给出一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某物有价值或值得奋斗。他还坚持认为,如果要论证历史的社会主义结局从道德角度来说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我们必须提出这么做的“相应普遍的、伦理上贴切的”标准来。(注:杰拉斯:《将马克思带到正义》,第44-45页。)如果我们给出上述关于进步的标准,我们就是在提供普遍的评价标准,从而不能否认马克思使用了这样的标准。
我已经论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目标是社会创造力这一人的本质的完成,但除非满足特定条件,否则这一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要认识普遍的或超历史的正义原则,这种要求的问题恰恰在于,表述这些原则变成了超越历史的。这表明,我们用来评价一个社会的标准,恰恰是那个社会所没有的。这是用新的形式代替了旧有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马克思坚持认为道德的社会来源高于任何其他来源。塞耶斯引用了英国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一段有趣的话,其大意为,所有道德都是“相对的”,而且必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化( realisation) 之本质意味着经历诸时期的演进,处于某一个时期的存在并不就是终结。布拉德雷重复了本质主义的论证:每个时期都实现了人的本质,但并非完全实现,只有在之后的时期我们才能看到前一个时期的不足,但“对权利法则的要求自身,若脱离一切时期,则是在要求不可能的东西。”(注:塞耶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第91页。他引用了F.H.布拉德雷的《伦理研究》(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年版),第190,192页。)我想这种有限相对主义对马克思来说是正确的,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与黑格尔亦然。资本主义劳动契约有其正义,但这种正义付诸实际时工人感到明显的不公平,马克思对两者之间的张力做出了辩证的表述,这一表述显示出资本主义正义是如何产生出其对立面,并乞求与人的潜能的完全实现相符的解决方法的。
现在回来看杰拉斯的观点,他说马克思隐约把对生产手段进行社会控制的道德权柄当作一种自然权利,这就产生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并未这么做,但他明显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会把这种权柄当作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给予自身。尽管他的观念中有自然主义的因素,但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使得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社会,这种自然权利论证中的“自然权利”术语,就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被使用的。如D.布克胡斯特( David Bakhurst) 所说,马克思反对永恒道德原则的观念,他坚持认为,所有的规范法则都是由特定共同体创造与保持的。(注:D.布克胡斯特:《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排他主义:对斯蒂芬·卢克斯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回应》,载于《国际实践》,1985年5(2),第210-211页。)布克胡斯特在捍卫马克思的道德观念的一致性时更进了一步。他认为马克思承认,道德的问题通常可以在我们实践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基础上得到解答,而进行道德判断是一种始源于社会化并随社会交往活动发展的知觉能力。这种观点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有信心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普遍主义的虚伪,却不需要提出另一种类似的普遍主义。自由社会的道德是由那个自由社会自己决定的。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创造力这一人的本质的完全实现的表现。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它使伦理规范重新成为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并使马克思所向往的雅典民主式的伦理精神的出现成为可能。
没有最终目标的政治?
说白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抗拒地产生一场趋向于社会主义的运动,而马克思高估了这种趋向的程度。对那些仍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唯一能使人类走向繁荣昌盛的体制的人来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它使人类走向邪恶,使人性走向毁灭。我认为当马克思这么做时,他并未诉诸传统的道德主义,但我不同意杰拉斯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最终目标。杰拉斯承认,不用道德化的批评,马克思仍能对资本主义做出有力的科学分析,但他坚持认为,这并不能为包含在马克思对道德论证的敌视中的“不足做出辩解或补偿”(注: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第56页。)。他从《法兰西内战》中引用了下面这段话作为马克思的不良做法的例证:
工人阶级知道,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解放以及现有社会被其经济动力所趋向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历漫长的斗争,必须经历一系列改变环境与人的历史进程。他们没有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除了解放那些旧有的衰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注:《选集》22,第335页。)
杰拉斯抱怨说,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否认了最终目标的有效性,只留下“内在运动与上述的解放”。(注: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第55页。)然而把“更高社会形式的因素”解放出来的过程,暗示着多种选择和大规模的转变,在此处它被当作唯一可实现的最终目标;换句话说,解放新社会的因素就是一个最终目标。(注:此处的but的意思是“除了”,而逗号不起作用。但我们应注意,此处马克思是在用一门外语(英语)写作。)事实上,在初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说是把生产的社会形式从“奴隶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注:《选集》22,第491页。)上述文字写于那种足以震慑除最勇敢者之外的人退出政治斗争的灾难性暴行之后,马克思想要向那些受压迫者保证,他们并非只能依靠虔诚的希望,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并非无所不能。在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的结尾处,马克思写道,“工人阶级会将这些烈士铭记在心,”在这里马克思以一个共同的主题为前提,这个共同主题是由共同记忆激起的,它含有道德意义。“那些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们”将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注:《选集》22,第355页。)马克思很清楚,追求最终目标对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对残酷无情的压迫的强烈仇恨会驱使人们行动。然而,他也建议,要分析在既定条件下和环境中什么是可以达至的,并用分析的结果来指导行动。他这么做当然是正确的。
( Lawrence Wilder," Marx and Justice Revisited:The Greek Dimension" ,原载Studies in Marxism No.5,1998)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学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伦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