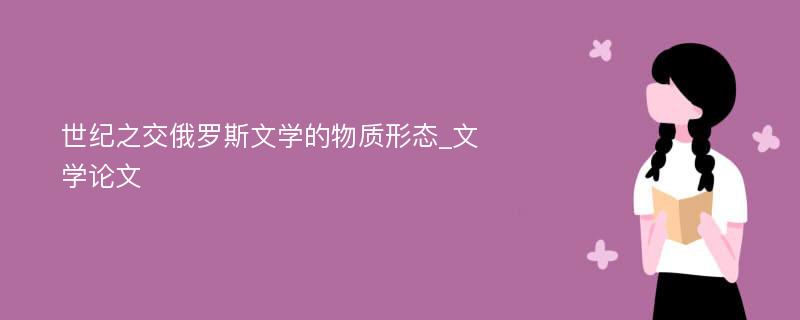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物质性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性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俄罗斯论文,形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由来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纪之交”这一概念突然成为俄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 一。人们甚至把普希金时代用来表明空间分界的“疆界”或“门槛”的概念扩展为表达 时间的专有名词,如“两个世纪交界”或“新世纪门槛”等。宗教思想家弗·索洛维约 夫、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和安德列·别雷、新现实主义文学家高尔基等,都不止一次地 撰文谈论过“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运用这 种概念探讨社会文化转型和文学特征再一次成为俄国人文学科的热门课题,并且波及到 国际斯拉夫研究界,如二○○○年七月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的国际学 术研讨会就以“新世纪门槛上的俄罗斯文化”为题。不过,这类概念并非纯粹的时间术 语,正如“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指向一八九○至一九二○年代的白银时代,对于新俄 罗斯而言,它也是表达自一九九一年开始直至目前还未完结的一个历史性概念,于是又 相当于“解体后的俄罗斯”或西方学术界的“后苏联”(post-soviet)概念。 苏联时代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苏联末期又追求文学的反官方意识形态性,而苏联 解体后的历史变迁则使文学在整体上逐渐趋于非意识形态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了语 言艺术的自然变异;与此同时,世界各大国在最近的十年普遍进入了以信息技术革命为 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它以广告、音像制品和网络媒体对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改变 和影响为特征),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艺术自然也要被这个信息革命时代所改造。如此一 来,当代俄国文学在技术操作层面上与苏联以及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 同,也就是说,支撑当代俄国文学存在的物质性形态已迥异于过去,也正是因为这种巨 变,才导致了语言艺术在叙述策略和叙述方式上的变化。
从文学消费总量上来说,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是大不如以前了。但是,新俄罗斯语言 艺术在叙述样式、价值观追求、流派分野、作家群划分等方面,比过去反而要复杂得多 。具体说来包括:由另类文学演变为一个重要潮流的后现代主义(维·佩列文、德·普 利戈夫等),试图重建新国家文学的新古典主义(西方因此而称新俄国文学为后苏联文学 ),力求恢复俄国斯拉夫主义传统的“新根基派”(以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为代表), 追求文学各种价值自足性的“另一种散文”(如库拉耶夫的幻想性叙述、巴列耶的自然 派叙述、伊斯坎德尔的讽刺性先锋主义)以及在西方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在新俄罗斯 也流行开来的女性主义文学等。文学的这种状况主要是通过文学类杂志所发表的文本显 示出来的,由此,要理解现今俄国文学的复杂程度、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等,我们就不 能不去探讨文学类杂志由苏联时代那种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份的发行量是如何演变为今 天不足万份的社会学现象,以及这种变化与整个俄国社会生活的变革、读者分流和文学 地位改变的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来谈论当代俄国文学,无疑会造成对其实际 本体意义理解的某种偏离,或会夸大其审美的或社会的价值,或缩小乃至否定当今文学 存在的积极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对解体后俄国文学发展的判断主要依据文学杂志这类 物质性载体(当代俄国文学生产制度的变革造成少有作家不经由杂志中介而大量推出单 行本作品的,甚至可以说,不通过杂志这种渠道文学生产就不可能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因此,对反映俄国文学实际状况的物质性形态进行社会学分析,既能为我们准确了解 当代俄国文学提供一个重要的通道,也是我们文学研究中一种有益和必要的尝试。
文学的物质性形态之一:文学类杂志的种类和结构变化
俄国素以文学杂志的种类繁多而闻名,而其近十年来的变化如何呢?可以肯定地说,文 学界并没有因为社会向私有化转轨或文学重要性的降低而出现一片凋零。
首先,《新世界》、《十月》、《各民族友谊》、《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和《 涅瓦》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文学期刊不仅没有消亡、外移,或变成非文学杂志,甚至 没有缩小篇幅,相反却继续保留了严肃高雅的面目,也依旧代表着俄国文学的主要成就 、发展方向并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作者和读者群。或者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依旧还是 文学生产的中心,它们仍保留着相当的文学生命力。
除此,几乎俄罗斯的每个州、自治共和国和边疆区都保留了一种以上的文学报刊,其 中有些地区性文学杂志还相当有名,如萨拉托夫州作家协会主办的《伏尔加》月刊、西 伯利亚科米自治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北方》双月刊等。而且,这些地方刊物依旧有佳 作出现,许多著名老作家的名字就常出现在如《西伯利亚星火》这样的杂志上;其次, 地方性杂志所刊载的内容也并无地域性局限。以《北方》杂志的二○○一年第一、二期 为例:弗·扎哈洛夫的论文《悖论中的悖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未来俄罗斯》显示,作 者在思考和表述的方式上与中心城市的学者并无差异,而尼·别列雅斯洛夫的《面对必 然革新的现代俄罗斯文学》一文更显示了作者的独到之处。该文声称:比起任何一种装 帧豪华的杂志来,当代大量的(尤其是外省的)文学类杂志继续坚持传统立场,在塑造和 影响读者的精神面貌方面可能意义更大。当然,传统文学以及支撑这种文学的杂志如何 吸引读者,如何与标新立异的大众杂志和先锋文本竞争,则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重要文本也出现在地方杂志上,如亚·伊 万琴科的小说《组合字》就发表在《乌拉尔》(一九九二年第二至四期)上,叶·波波夫 的力作《前夜之前夜》刊发在《伏尔加》(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上,德·普利戈夫的力作 《革命:两个扬声器的广播悲剧》也发表在《伏尔加》(一九九○年第十期)上。
文学类杂志目前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很少完全依赖财政拨款,即使 继续隶属于某地作家协会,也常与某基金会合作或得到同名称的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 那些在九十年代出现的刊物尤其如此。如创刊于一九五七年的文学月刊《莫斯科》现已 不仅属于俄罗斯作家联盟,它还属于“《莫斯科》杂志劳动合作社”;一九九一年创办 于特维尔市的综合性文艺季刊《俄罗斯外省》现主要靠尔仁尼琴基金会支持;插图本文 艺类杂志《Ванг百科全书》现已改由“祖国”基金会和东正教会基金会主办(刊物 也随之变成了宗教童话和神话作品集),等等。
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变化甚至也发生在文学研究类杂志上,有的还是享有国际盛誉的 老刊物,如:关心文学创作现状和文学思潮变化的双月刊《文学问题》与《文学评论》 ,研究俄国古典文学遗产的双月刊《俄罗斯文学》(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普希金之家 ”主办),介绍和评论当前国外文学的月刊《外国文学》等。而大型民间文学研究杂志 《新文学通报》、《俄罗斯杂志》、《新文学评论》和《紧急储备品》等在九十年代异 军突起的刊物更是如此。它们不仅改变了杂志生存方式的结构,而且还大大影响了专家 们思考文学问题的方式。其次,它们办刊的国际化程度很高,许多编委是来自欧美斯拉 夫学界的著名学者,其发表的不少文章直接来自国外的作者;在对俄国文学研究的论题 和方法上,它们力求参与国际斯拉夫研究界的不同潮流,并试图与国际的文学研究惯例 接轨。而苏联时期研究文学的主流做法,如今大多已让位于对文学现象的学理性研究, 例如对俄国文学的民族主义、俄国后现代主义的多重意义的探讨,就与以上文学研究杂 志的推波助澜息息相关。
近十年来,文学类杂志的办刊思路也有很大的改变。如今,纯粹登载文学作品的刊物 已十分少有,大多是文学文本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而且文学作品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大 型综合性文学月刊《莫斯科》的文学作品比重已下降到不足五分之三,有时甚至低于二 分之一,而书评、文学评论,尤其是对俄罗斯的重大文化现象的研究常常要超过五分之 二。大量篇幅的研究和随笔类文章大有改变办刊方向之嫌。但是,文学新人并未因此而 大大减少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的街道》始终坚持扶持各种身份的作者,无论你是工 人、农民、医生,还是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墓场工作人员等,它始终向热爱文学创作 的人敞开着,很多人的处女作都见于此,因而它在读者和作家的心目中有不低的地位, 发行量也始终保持在万册以上。不仅如此,老杂志《莫斯科》、莫斯科作协于一九九五 年创办的文学月刊《“A”圈》、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学习》等也继续 热衷于提携新人,在每篇作品前都会有关于作者处女作或在该刊初次发表作品的情况介 绍,使文学新人大为感动。这可能也是十年来俄国文学保持活力的又一个原因所在。
总之,培育俄国文学的阵地,关注以及研究俄国文学的平台在苏联解体后事实上仍正 常存在,且在有些地方还相当茂盛,人们甚至还不断在开辟新的领地。当然,这种坚持 是很不容易的。很难想象,在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的发行量降至不足二百份时,由科学 院文学语言分部和阿斯特拉罕国立师范大学合办的《俄罗斯文艺学》月刊(一九九三年 创刊)却推出了白银时代作家布宁的纪念专刊;而发行量一直在三千册左右的大型民间 文学研究双月刊《新文学评论》,也以厚重的文学研究成果在不断导引着学术界。
文学的物质性形态之二:文学杂志如何面对市场
适时变化是俄罗斯的文学类杂志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苏联的解体不仅 导致反官方意识形态作品的降温,还伴随来了全球化的民族主义热潮。于是,文学期刊 在办刊宗旨上必然体现出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一九九五至二○○一年间的很多举国性 纪念活动是以纪念文学家普希金为名而进行的,或者说,在文学名下进行的纪念卫国战 争胜利五十五周年(二○○○年),纪念俄国海军建立三百周年(一九九六年),纪念卫国 战争发生六十周年和纪念莫斯科建立八百五十周年(一九九七年)等活动,把原本地域性 的、专门化的,甚至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活动演变成了全民性的文化运动。面向中学生 、素以普及文学经典知识为己任的《文学在中学》及其副刊《文学课》也焕发了强大的 生命力。自一九九八年以来,它出版了多种有影响的丛书,其中供中学生阅读的民族文 学经典文丛就达三十余种。为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八十周年,该杂志在二○○ 一年第五期开辟了专刊“我们的精神价值”。其中鲍·塔拉索夫的《最好的人……纪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正面人物》一文强调,好人是有教养的普通人,他懂科学而不 带传统的偏见。文中配上了著名画家的插图,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很受中学生喜欢;该 期还刊登了莫斯科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柳·特鲁宾娜的重要文章《我相信俄罗斯》,讨论 了俄国著名诗人勃洛克和别雷所创造的种种历史意象,把相当复杂的文学现象介绍给中 学生。选题的这种变化,使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杂志密切了自身与读者及作者的关系 ,它们同《事实与论据》、《莫斯科共青团》、《商人》、《今日》、《独立》等非常 有影响的报纸一道,共同掀起了大众文化批评运动。在改变文学功能、作家形象和促进 社会进步的同时,它们也使自身避免了灾难性的命运。
然而,某些积极的举措和调整并未使文学杂志避免其发行量一落千丈的悲惨命运。其 情形与苏联时期那种动辄上五六位数字的发行量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新世界》一九八 八年第九期的发行量达百万以上)。但状况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几份刊物并非持续 恶化——发行量虽处于变动状态,杂志却未必是在不断的边缘化。《新世界》、《十月 》、《莫斯科》、《文学学习》、《外国文学》、《各民族友谊》和《青年近卫军》等 重要杂志近年来的发行量都在一万份左右波动。而这种波动说明,不同的读者群、不同 的审美选择正在形成过程中。不过,中学生文学杂志则是另一种景观:《文学课》这份 指导中学生阅读的月刊发行量一直在不断增加,一九九九年第八期是三万七千五百份, 而二○○一年第五期则达到四万二千份;《文学在中学》的发行量目前也超过四万份, 而《青春》则不低于一万五千份。这种情形的出现,得益于俄国一贯的传统,即在基础 教育中强调通过阅读民族文学经典来提高学生素质,强调文学作品的正面价值以及对文 学新人的不断扶持。而一九三二年创办的《儿童文学》,如今成了探讨儿童成长中美育 问题的理论性杂志。尽管其文字浅显,配图生动,但发行量仍跌至三千份。发行量数字 是残酷无情的,这种情形对那些地方性文学杂志的生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如很有 影响的《伏尔加》至二○○○年已经降到不足千份。
不过,即便如此,这种变化并未影响到文学类杂志的信誉、内容和质量。整个杂志的 总体篇幅基本上不缩减,甚至有扩版的趋势,也不刊发通俗性的畅销作品,并改变了八 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文学杂志以反主流意识形态为特色的做法,试图更务实地面 对文学审美、民族精神建设和时代的全球化问题。如《莫斯科》等大型传统杂志每期都 在刊发著名学者讨论苏联文学史、当代俄国文学走向等问题的长文。
更有意味的是,各刊物还积极通过互联网提高文学类刑物的影响,密切杂志同世界读 者和作者的关系。几乎所有大型文学类杂志都向国际公布了自己的网址和电子信箱,如 《新世界》的网址是http://www.novosti.online.ru,《十月》是http://www.infoart .ru,《旗》是znamlit @ dialup.ptt.ru、http://www.infoart.ru/magazine/znamia ,《莫斯科》是www.moskva.cdru.com或lijurmos @ cityline.ru,《各民族友谊》是d n @ mail.sitek.ru,《青春》是unost-contrast @ mail.ru,《伏尔加》是volga @ m ail.saratov.ru,《特维尔生活报·特维尔新文学副刊》是http://homepages.tversu.r u,《文学评论》是http://www.rema.ru/komment/litoboz/litoboz.htm,《涅瓦》是h ttp://www.nevajournal.spb.ru,《“艺术-彼得堡”杂志中的文学》(现代俄罗斯散文 、诗歌、文艺学和文学综合性双月刊)是http://www.art.spb.ru/lit/index.html,《 世界文学》是http://www.ibamedia.com/ibamagaz.ru,《文学俄罗斯》是http://www.litrossia.ru/,《俄罗斯文学》是http://www.liter.ru,《网络语言艺术》是http:/ /www.litera.ru/slova/等等。这种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塑造本民族文学形象的做法,对 改变俄语文学在世纪之交的边缘化窘状可能会有些积极作用,在客观上促使了国际社会 有可能更方便地去关心俄国文学。
文学类杂志注重塑造自己形象的方式远不仅限于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还包括维护历 史上所积累的印记,并在新的条件下扩展这种历史声望。其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大部分 杂志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目录的左上方或右上方标明该刊性质。《十月》、《涅瓦》、 《新世界》和《各民族友谊》之类最重要的杂志是这样,其他刊物也如此,如:《文学 学习》标示“一九三○年由高尔基创办的文学-哲学杂志”并保留有高尔基的头像;《 文学在中学》题有“一九一四年创办的中学文学教育杂志”;《莫斯科》则是“一九五 七年由莫斯科作家协会创办的俄罗斯文化杂志”;《青春》是“一九五五年创办的文学 、文化教育杂志”;现由作家联合会和国际斯拉夫书面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我们同时代 人》杂志仍标明是“一九五六年创办的文学月刊”;《旗》乃“一九三一年创办的文学 和社会政治类月刊”并保留着苏联国徽图案。这种标志性文字或符号非常有意义,它直 接规定了这些刊物不会刊登违背其宗旨的通俗畅销作品,否则刊物就会有通俗化的倾向 。著名的例子是一九六一年创办的杂志《探索者》现在取消了“文学月刊”提示,也的 确变成了侦探、幻想和传奇类的畅销杂志;一九五○年创办、面向农村读者和作者的文 学杂志《乡村青年》易名为《功勋》后,也随之变成了侦探小说专刊;原来由内务部机 关主办的《警察》改名为《盾牌与宝剑》后取消了刊物性质提示,事实上也已成了现代 侦探小说专刊。这种变化的确改变了杂志的命运,发行量也随之大涨。《盾牌与宝剑》 的发行现已达三万份,而《功勋》也维持在万余份。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俄国的 通俗文学作品常常由专业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并有专门的装帧设计。因为,俄 国的文学杂志难以实现雅俗并存!
文学的物质性形态之三:需要补充说明的三个问题
首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已成为独联体国家的俄语文学杂志 。语言艺术在世纪之交本已遭受大众文化的侵袭,而这些独联体国家所兴起的非俄语化 运动、人口的稀少、俄语读者群的日渐缩小、文学国际化程度的低下等原因,直接导致 了这些国家俄语文学杂志的生存危机。或者说,除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等少数地区的文学 之外,少有引起国际学界重视的独联体国家文学。《文学格鲁吉亚》在一九九九年作为 季刊的发行量是一百五十份,二○○○年改成半年刊后发行量仅五百份;《文学亚美尼 亚》二○○一年第一期仅一千册,而《文学阿塞拜疆》在二○○○年的发行量才四百份 。这些杂志曾试图通过国际互联网改变边缘化状况,或改变存在方式,但种种努力均无 济于事。如一九三三年由哈萨克斯坦创办的《自由》或《辽阔世界》现在由作家联盟和 哈萨克报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但其发行量也仅千余份。这种结果诚如九年前吉尔吉斯 作家艾特玛托夫所言,是俄语把吉尔吉斯这类小民族文化推向了世界,如果取消俄语, 他们将会退出国际社会。
需要补充说明的另一点是,在描述世纪之交俄国文学的发展情形时,我们主要依据的 是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新世界》、《十月》、《旗》、《各民族友谊》、《莫斯科》、 《青年近卫军》、《文学学习》和《涅瓦》等杂志。如果考察十年来俄国文学研究的学 术史,则要依据上文提及的那些专门的文学研究类杂志。然而,俄国文学发展和文学问 题的学术研究并非完全受限于文学类和文学研究类杂志。或者说,世纪之交所有重要文 学作品不是都问世于上述文学或文学研究类杂志。后现代主义是最近十年俄国重要的文 学景观,然而其许多重要作品却问世于其他报刊,如:作家弗·索罗金的代表作《达豪 一月,散文诗》发表于社会综合性报纸《今日》(一九九四年总第十三期),米·乌斯宾 斯基的《一次大型会议的纪录》则刊于另一份综合性报纸《明天》(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亚·屠格涅娃的力作《盲目史》发表于《黄金时代》(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等等;同样 ,评判十年来俄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状况也不能仅限于上述文学研究类杂志 (不否认《新文学评论》在一九九八年第二期、一九九九年第五期开辟的“俄罗斯后现 代主义”研究专刊对促使人们认识俄国本土后现代主义问题的重要作用)。很多重要文 章都发表在其他杂志上,如马良文的《神话与后现代主义传统》载于《罗格斯》一九九 一年第一辑,而《语词或文字》、《独奏》、《出版之所》、《艺术世界》、《电影艺 术》等也发表了不少俄国学者讨论民族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文章,特别是《哲学问题》也 常常推出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专刊(如二○○一年第八、十二期)。这种情形使后现代主 义在俄国与它在其他国家一样,不仅成了大都市的文学创作景观,也不仅只是文学研究 者才关心的论题。
最后还要提及一对矛盾现象。十年来,久负盛名的《文学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显 而易见的原因是不变革改革时代所确立的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办刊宗旨。世纪之交所要求 人们的不再只是破坏传统、批判历史和诋毁过去,而是去建构民族所需要的精神信仰, 特别是去实践自己特有的建设性使命。当今的《文学报》没有去履行这个使命,因而其 声望自然让位于《书评周刊》、《独立报·书评周刊》、《今日》、《文学俄罗斯》等 。与之相反,大多数文学或文学研究类杂志却在极力鼓励当代读者重建对民族的信念和 在俄罗斯生活的信心。创办于一九二七年的《小说报》(实为周刊)不断选载了苏联时期 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一九九九年第五期重登了别洛夫的《乡村之晨》),一九三六年创办 的艺术和社会思想双月刊《词语或文字》也在不断重登苏联文学名家的名作或回忆录( 二○○○年第一期重登了邦达列夫的《瞬间》),《旗》杂志则常常重登历史名人的日 记或介绍关注民族精神问题的新作。诸如此类的民族主义或历史诉求使其读者群相对稳 定,其发行量也始终在万份左右。特别是《俄罗斯外省》更充满着苏联情结:二○○○ 年第二期的开篇是斯大林肖像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庆祝红军抗击纳粹德国胜利大会上 的发言;二○○○年的第三期是著名老作家拉斯普京在接受索尔仁尼琴文学奖仪式上维 护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发言;二○○一年第二期的开篇是为纪念二战爆发六十周年而积极 评价苏联贡献的文章。《词语或文字》也有这个特点: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纪念普希金诞 辰二百周年的专刊注重的是对诗人民族主义的阅读;二○○○年第一期借纪念基督教二 千年而强调东正教对俄国的重大意义;二○○○年第二期和二○○一年第三期则分别是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和二战爆发六十周年等。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为何美国著名斯拉夫学者艾娃·汤普逊在《帝国知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一九九 九)一书中认为,索尔仁尼琴和女性主义作家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等人的诸多文学叙述体 现了俄国殖民主义的诉求。
总之,世界之交的俄语语言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固守传统诗学的规范去 判断俄国文学的发展变化,也许会发生叙述危机;若按原来文学理论范式审视之,我们 将会无所适从。在考察文学生态环境本身的诸多变化,探究深刻影响纯文学创作的社会 状况和严肃文学的命运时,我们还可通过报刊和网络等种种文学的物质性形态的状况, 去感知社会阅读趣味的转向以及知识分子纯粹的审美性精神活动,由此,我们才可能恰 当地发现俄国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或某些局限,而不仅仅限于对文本进行伦理学的道德评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