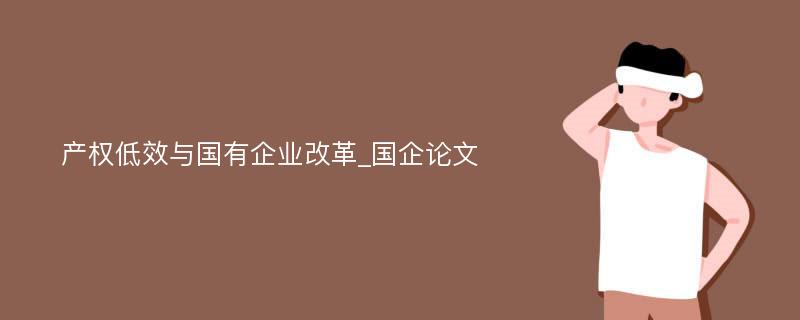
产权低效与国有企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改革论文,产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2001年,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显著,国企数量减少了33.6%,职工减少49.55%,赢利额增加46.5%,减亏35%。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一半左右的国企亏损,亏损额达2000亿元。而在此期间大量资源仍源源不断注入国企,其资产总额增加30.3%,负债却增加了33.6%,总资产报酬率仅为3.3%,低于银行的利率。虽然国企也依照现代企业标准进行了改制,甚至许多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但即使如此,国企效率仍然低下,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低效与其独特的产权制度密不可分。国有产权制度直接导致了市场竞争失败的不可信威胁和监督制衡机制的缺乏。
一、国有企业退出的“不可信威胁”
所有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最终都取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成为一个可信威胁,而如果企业经营不存在失败,那么任何的积极进取似乎都是多余的。而国有企业的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政过程,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往往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会给予它们支持,所以“破产”对于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信威胁。
科尔奈教授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中,在政府干预非常强烈的情况下,照样会有软预算约束,而软预算约束造成做决策时可以不对其财务后果负责,因为一旦发生了错误决策,反正总有其他的人或机构把他解救出来,为他弥补损失,这样市场竞争失败对于他来说就是“不可信威胁”。计划经济有大量错误投资,但之所以能沿袭下去,是因为亏本了以后国家给补贴,或者再追加贷款,或者通过其他办法救助。在人们对这些有预期以后,可以对任何决策根本不负责任。因此,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约束的核心问题是承诺的可信问题。事先任何人都会说预算是硬的,但问题实质是既成事实之后会怎么样:约束是否可信,是看事后项目不好是否会下马还是企业经营不善是否会关闭甚至破产。那么这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研究发现有多方面原因。第一,追加约束的人以及机构的目标和动机。如果政府在乎就业或出于其他的政治动机而非纯经济考虑,那么政府就更可能事先软化约束。第二,权力的结构。如果某人或机构的权力大,他就有能力在事后重新谈判,这就导致约束软化。第三,资源的集中程度。当某人或机构控制的资金太多时,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会导致对他人预算约束的软化。第四,信息的集中程度。信息多有时会使约束软化。基本原因是事后信息多使得事后的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使得事后重新谈判的空间增大。这就导致事先制定约束容易被改变。约束的可信度由多方因素——动机、权力、资源和信息来决定。研究表明,政府的政治动机往往使经济约束软化。
就国有企业的性质而言,政府是不希望国有企业破产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除了向财政缴税收外,还要向国家上交利润,哪一个所有者希望自己的企业破产?所以国家想方设法尽量让国有企业存续下来。可见,很多国有企业还存在着“退出壁垒”,市场竞争失败对于它来说自然是“不可信威胁”。
二、监督制衡机制流于形式
就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来说,银行和外部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能力、动力和制度方面的支持来积极地监督和影响公司行为。国有企业的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政过程,银行作为债权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时所享有的有效权利很微弱。总体上看,国有商业银行也受困于国有非金融企业类似性质的公司治理问题:它们至多只有弱的利润动机。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意味着银行不能用所有权来加强它们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并对公司施加更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会给予它们支持,这种做法使信贷决策更多地取决于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而不是企业本身的优劣,从而弱化了银行评估和监督公司行为的动力。我们知道,由于上市公司股东众多,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是“公共产品”或巴泽尔意义上的“公共域”。股东对上市公司行使监督权必须全方位搜集信息,这需要付出成本,但是一个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所带来的利益会为所有的股东集体分享,因此,单个股东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履行监督权。股东作为产权主体恪守用脚投票是“消极自由”,行使监督权是股东的“积极自由”,由于监督的公共产品性质,中小股东监督上市公司的成本太高,因此,中小股东除了消极地“用脚投票”外实际上别无选择,这一部分权利基本上无条件地放弃了,投资者更多地行使消极自由是理性选择。
从内部监督来看,对代理人行为的监督并不完善。一般说来,对代理人的监督应该由委托人来完成。国有经济的终极委托人——公众个人没有任何剩余索取权,不会因为关心企业效率得到任何能感受到的经济回报,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动力与代理人建立制衡关系。国有经济第二层次的委托人——政府,这种委托权最终要落到政府官员身上,他们掌握的最终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并不对称,这时,政府官员手中的控制权就成为一种“廉价的投票权”,经营者只要花一定成本就可以收买这种廉价的控制权。这就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干预企业经济中只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滥用控制权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代理权监督力度不够的原因。
可见,就国有企业来说,无论是内部人还是外部人都有弱的监督动力,监督机制极不完善。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新兴和发达市场都存在的公司治理不良行为说明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公司治理模型。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首先应该能在出现系统性问题前发现缺陷所在,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并且能够迅速地采取纠正措施。这样一个体系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企业存在市场失败的现实威胁,还包括建立在市场参与者自身利益基础之上、力求培育一套具有制衡机制作用的有效监管体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国有企业的低效与其独特的产权制度密不可分。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倾向于弱化“市场竞争失败”这一对企业的现实威胁,弱化国家的监管能力。而所有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最终都取决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成为一个可信威胁,取决于监管能力。因此可以说,如果不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公司治理的持续改善就难以获得。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只能是干预经济和弥补市场缺陷,国有企业只能存在于那些私人资本不能投资的或者不愿投资的行业和部门。而私有经济能投资的行业和部门,国有经济应该,也必须撤出。国有资产分步骤、有条理、有规则地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是改革的关键。最近成立的“国资委”正是适应这种需要横空出世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除了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外,引进机构投资者,加强市场监督,加大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从业人员中的分享程度也是促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必不可少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