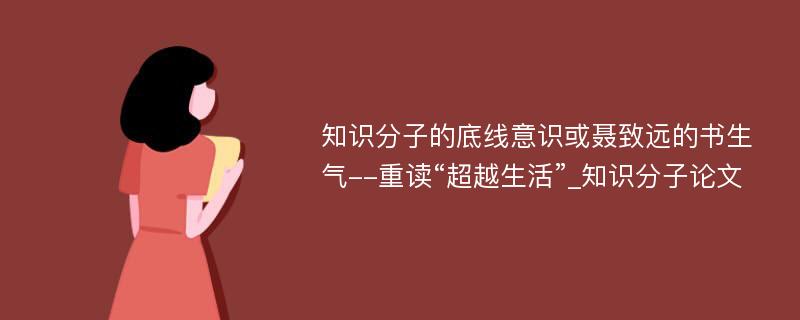
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或聂致远的书生气——重读《活着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书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底线论文,致远论文,生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阎真的《活着之上》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在去年的2014年11月下旬。那时候,承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是《收获》杂志,而它刚一面世就被路遥文学奖的一审评委注意到了,遂被推荐上来。因《收获》发表时有删节,萧夏林先生便向作者要来足本电子版,发送给二审评委进一步审读。记得当时我是先读了二十页左右的电子版,便决定把它打印出来,以便读得更加仔细真切。我把字号调成5号字,用A4纸,整整打印一百五十页。 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我整个儿沉浸在阎真所描述的世界里。聂致远的苦苦挣扎、赵平平的斤斤计较、蒙天舒的如鱼得水、大学校园中的蝇营狗苟,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在作者严谨、逼真的现实主义笔法面前,我的记忆被不断激活。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边的许多故事,我甚至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我是不是哪天也去写一部反映校园生活的长篇之作?我在高校已厮混三十年之久,掌握的素材可是一点都不比阎真先生少啊。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得马上确认它的价值和位置。此前我曾读过阎真的《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曾读过张者的《桃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邱华栋的《教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比较的维度之一。与此同时,我还要与当年读过的路遥文学奖一审评委推荐上来的其他五部长篇(分别是叶兆言的《很久以来》,载《收获》2014年第1期;程小莹的《女红》,载《小说界》2014年第1期;刘庆邦的《黄泥地》,载《十月·长篇小说》2014年第2期;叶弥的《风流图卷》,载《收获》2014年第3期;贾平凹的《老生》,载《当代》2014年第5期)进行比对。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坐标中,我意识到《活着之上》是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目前把高校生活写得很真实、很到位的一部优秀之作。尽管它还谈不上完美,但在今天,能够写出这样的诚实之作已很是难能可贵了。于是,在路遥文学奖第四次评审会暨终评会上,我把这一票投给了《活着之上》。 2015年3月底,首届路遥文学奖颁奖会在青岛举行,而其中的一个会中会是“《活着之上》与阎真现象研讨会”。我仔细聆听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发言,以此与我当初的阅读感受印证、对比。听过之后,我决定重读一遍这部小说,以便把那些飘浮的思绪固定下来,也想看看这一遍还能读出什么东西。 这一次,我读的是阎真先生的赠书——《活着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 学院中人读《活着之上》,是很容易把自己代入其中的。比如,当我在开篇不久便一前一后读到“那是1982年,我十岁”和“再一次看到《石头记》是十七年后。那一年我考上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乘火车去北京上学”(P4)时,我立刻便推算了一下主人公聂致远读博的时间。那是1999年,而那一年也正是我来北京读博的日子。所不同者在于,我比聂致远大约十岁,也比聂致远幸运一些。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了麓城师大工作,而我则留在了京城教书。 这个时间点的设计应该有一些意味。因为再去推算,聂致远读大学的时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他又接着攻读硕士学位。也就是说,当聂致远在麓城师大求学之际,他便遭遇了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的强劲旋风。而到他读博士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又开始全面扩招,市场化之风已穿透了高校的四面围墙。新世纪之初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于他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饭碗,却又预示着他必然会经历个人生活最为困顿的一个时期。因为对于一个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票子、房子、孩子等等显然至关重要,而这一切的获得又得靠他在大学里的表现和晋升。但问题是,经过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学院已非风平浪静的港湾,学术和学问也不再是钱钟书所谓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加上学术行政化、学院产业化已开始显山露水,聂致远的安身立命之本便也风雨飘摇了。想一想十多年前,网上既有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教职的《辞职报告》广为流传(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不满高校的学术行政化和学院产业化)①,也有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妙文细数高校弊端,更有南京大学董健教授在大声疾呼——《“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我们就可以知道聂致远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人文环境了。而这也正是所有的大学师生不得不面对的时代氛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活着之上》中满目看到的都是钱、钱、钱了(纯粹是出于好奇,我在电子版中通过“查找”统计,这部小说直接写到“钱”字的地方达五百九十五次之多)。买房子搞装修需要钱,生养孩子需要钱;弄下小学编制得托关系找门路,需用钱铺路;出书发论文要交版面费,也得使钱打点。在小说中,一方面是赚钱、省钱、攒钱,这是聂致远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囊中羞涩又成为他一再窘迫的原因——赵平平为聂致远买了张卧铺票,但“在火车上我一直躺着,上厕所也匆匆忙忙,赶快回来躺着,不躺就对不起那张卧铺票”(P39)。赵平平经常性的说法是:“钱到了我的手里,你知道的,就缝到肉里面去了,拿出来肯定是要动手术。”(P237)这些细节把聂致远夫妇对钱的爱惜写到了极致;而另一方面,则是校领导按潜规则送钱办事、大把花钱、权钱交易,这又成为90年代以来的时代风尚——当聂致远感到自卑时,他曾这样想到:“现实就是现实,不论我怎么想,钱都不会理我,权也不会理我,你不去找它,它会主动找你?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我能螳臂当车吗?”(P223-224)如此看来,时代话语或时代风尚已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催人世俗,诱人庸常,劝人好好活着,逼人向着形而下运行。如果不在这股力量面前俯首称臣,那便是自讨没趣自讨苦吃,甚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聂致远必须面对的“典型环境”。 当时代风尚拖人下行时,聂致远是痛苦的,因为他既有自己向往的精神标高,又有他必须坚守的价值底线。小说一前一后都写到曹雪芹和《红楼梦》,写到了聂致远对曹雪芹遗迹的寻觅,显然富有深意。在一个价值混乱价值失范的时代,学历史的聂致远无法在现实世界找到价值依托,便只好退回古代,去“伟大的传统”中汲取向上的元气。“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说到底自己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惭愧,惭愧。”(P32-33)这是聂致远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它不断提醒着主人公不能与这个充满铜臭气的时代握手言和。于是,他读博期间虽然为一个企业家写传记挣了四万块钱,但在更大的诱惑面前(孟老板愿出十万块钱请他写一部传记)他却踩住了刹车。因为老板的爷爷当年开过“满洲制铁”公司,曾与日本人合作十多年。他不愿意把黑的写成白的,昧着良心篡改历史,肆意吹捧,最终还是拒绝了老板的请求。这便是聂致远的底线,而这条底线也若隐若现,成为他后来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赵平平是把钱缝到了自己的肉里,那么聂致远则是把这条底线埋在了自己的心中。它不时会浮现出来,敲打着聂致远的生活,提醒着聂致远的行为,追问着聂致远活着的意义。 然而,也恰恰是这条底线,成了聂致远反复痛苦、时常纠结的根源。因为这个时代逼人下行的力量太大,而引人上行的力量又如此缥渺。在强大现实的挤压面前,这种上行之力常常被消解、化解。它本来就细若游丝,最终又常常归于虚无。于是,聂致远每往前走一步,都意味着有可能跨过那条底钱,而当他心中警钟长鸣时,他又收回了跨出去的那只脚。他并非那条底线的坚定守护者,便只能在底线附近五里一徘徊了。比如,当官员的女儿范晓敏不去上课不参加小考却通过院里的金书记打招呼想拿到高分时,聂致远是非常气愤的。然而在压力面前,他退缩了。“我开始写了个八十分,涂掉,改成九十,又涂掉,最后给了八十六分,在改动的分数旁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分数没有给其他同学很大的伤害,也不至于让他们来戳我的背脊。金书记他们不会满意,可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当他把信息发给金书记却没有得到回信时,他又开始感到不安了。“想想这件事真的做得窝囊,金书记不高兴,蒙天舒不高兴,范晓敏不高兴,连我自己也不高兴。还算对得起那些学生,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可真的把范晓敏的成绩提到最前面去吧,我实在又做不出,那我以后就不要再说那些圣人之言了,说了也是个让学生在心中鄙夷的笑话。”(P195) 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细节。在这个细节中,聂致远显然意识到了底线的存在,但当他在给80分还是90分之间犹豫时,这条底线其实早已松动了。而86分的成绩固然说明他还有所坚守,但他坚守的那条底线已不断后撤,早已不是原来那条底线了。而且,即便已经后撤,他也没有如释重负,而是觉得更加不安,因为他驳了领导和老同学的面子,甚至有可能得罪了领导。也就是说,在权力、人情等等强大的世俗力量面前,仅仅扭曲自己是不够的,他必须完全消灭自己心中的良知;仅仅松动底线也是不够的,他必须彻底摧毁让他为难的底线意识。而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细节,作者让主人公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实如此骨感,我不能在一个骨感的世界上去寻求一份丰腴的浪漫。”(P17) 当聂致远活得如此纠结时,他的同学蒙天舒却混得风生水起。为了在学校里有靠山,他可以找聂致远提出互换硕士导师,因为他已提前打听到童教授将担任院长;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可以向聂致远提出要求,借用其硕士论文中的一章“过渡”一下;为了与学界建立关系,他在别人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当起了志愿者,特意去接送名教授名编辑给人留下好印象;为了领导的出席,他可以在吃饭时把聂致远切掉,尽管身为权威刊物主编的“师兄”是聂致远请来的。正是因为蒙天舒有靠山、善公关、会拉关系,能跑项目,他的论文评上了“优博”,他很快破格晋升了教授职称,他顺利当上了副院长,前景一片光明。而他之所以能够样样如意,是因为他信奉“屁股中心论”(屁股决定脑袋),早已参透了学问的秘密:“如今是做活学问的时代。死学问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P59)而所谓“活学问”,便是把学术活动的“活动”看作中心词,只有通过“活动”,才能让学术变成生产力,进而让它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本”。在这个问题上,蒙天舒早已观念更新,甩开了聂致远几十里地,因为尽管后者已不再把学问看得那么神圣,但毕竟依然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除了身体,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了。”(P43)——这是聂致远反复念叨的一句台词。而在蒙天舒那里,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学问的丝毫敬重或敬畏。对于他来说,学问只是达到其目的的一种手段。 显然,蒙天舒是没有底线意识的。而一旦拿掉了这条底线,他与时代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前所述,当时代风尚拖人下行时,正是聂致远心中的那条底线在与其较劲。它固然已构不成什么抵抗,但毕竟也制造了一些摩擦,形成了某种阻力。这样的人多一些,时代战车下行的速度或许才不至于风驰电掣。然而,底线不再存在,心中便无顾忌;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时候,个人与时代便不再紧张对立,而是成了它的愉快合作伙伴。而时代对他们的回报也相当丰厚,他们靠山吃山,呼风唤雨,上下其手,要啥有啥。可以说,正是有了蒙天舒们的存在,当下的学院才争来了诸多“资源”,似乎也产生了巨大“活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学术行政化、学院江湖化中,大学精神变得形销骨立,一步步走向了陷落。有人曾经说过:“在中国学术界,没有一点匪气是不能成为‘学科带头人’的。”②蒙天舒倒还谈不上什么匪气,但他却有一种江湖气和市侩气。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学界许多人的影子。在聂致远的价值评判体系中,这些人肯定是俗人,但他们无疑又是这个时代的红人。或者说,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同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境界才被大大地拉低了。 因此,在作者“二元对立”似的描述中,聂致远显然代表着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而蒙天舒则是这一群体中的另一种类型。如今虽是“多元共生”,但只要蒙天舒这一“元”得势且长势喜人,那就势必会挤压聂致远那一“元”的生存空间,最终让其无地自容。结果,聂“元”被消灭,蒙“元”很繁荣,我们不得不重新进入“一元主义”时代。也许在小说不动声色的描绘背后,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便是这样一个沉重的事实。 我似乎应该谈一谈我读这部小说时所意识到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聂致远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被作者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在小说中,聂致远也常常以知识分子自许和反思(书中直接提到“知识分子”的地方有二十六次,大都与聂致远的自我反思有关),但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吗?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苦读多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信仰、追求和人文关怀。同时我也注意到,可能是因为主人公研习的是中国历史,作者便没让他进入左拉、萨特等人的价值谱系,进而去接通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资源,而是让他立足中国本土,成了古代士人传统的守护者。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值得认真关注: 清高,这本来是一道心灵防御底线,就那样被轻易突破了,因为你不可能对身边的人“搞到”无动于衷。商人想搞到钱,不想搞到就不是商人了;从政者想搞到位子,不想搞到就不是从政者了。这是生活现实。知识分子想“搞到”学问和社会责任,不想搞到就不是知识分子……可这不是生活现实。学问更多地成为了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也许,应该理解他们,就像理解我自己。可是,理解之后,人们看到的是那种悄然无声的心灵衰微景象。这让我想起刚进大学那年,在一个晴朗而凉爽深秋的下午,我拿着那本《宋明理学史》到麓山去读,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我随意地翻开书,正好瞟见了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一瞬间我激动不已,比中学时读到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名句还要激动。这是我的使命,我的道路,我的信仰,我的毕生追求。那时太阳正在落山,麓江上泛着金色的波光,在麓江对岸,麓城的高楼一望无垠,色彩缤纷,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之中。看着夕阳徐徐降落,我感到有一轮红日在心中缓缓升起。(P70) 把张载的名言作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历史学家许倬云也曾把这四句话加以分析,进而区分了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③。不过,若是仔细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其中隐含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士人传统尽管有着生成知识分子的重要元素,但它显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并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价值定位成功对接。比如,清高关联着自我修身养性之后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它是心理人格层面的内容,还缺乏必要的社会担当意识;又比如,士大夫中固然不乏说真话者,但真话往往又被纳入君臣关系的结构框架。它们体现在“进言于君”之中,出现在庙堂之上,却不能有效地延伸于社会,萨义德所谓的“向权力说真话”的力量还无法完美体现。阎真让聂致远活在士人的价值体系中,于人物的身份和专业而言固然水到渠成,但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个古代知识分子传统本身已存在着一些问题,而离开了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在西方是左拉以来的传统,在中国是鲁迅以来的传统)的支撑,知识分子的价值结构就不可能刚健硬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之所以有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新传统,就是因为它汲取了士人传统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之精华。这至少是一个双维结构。然而,在聂致远那里,我们却只是看到了一种“单向度”的选择与依傍。这样,他的价值底线就既缺少现代意识的浇灌,也不大可能应对更为复杂的现实处境了。 聂致远痛苦纠结的原因概源于此。表面上看,他似乎守着一种精神资源和价值体系,但是面对当今这种现实格局,仅仅在“致良知”“知行合一”“义利之辨”等层面反躬自省,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或者也可以说,他所坚守的古代知识分子传统只能使他退回内心,在道德的自我完善层面寻寻觅觅,却又因其先天缺陷,无法给他提供一种与现实对垒乃至交锋的强大武器。说得更明确一些,这种传统使人温柔敦厚的时候多,让人金刚怒目的时候少;它鼓励人收心内视,却不大赞成拍案而起。于是,每当聂致远面对现实问题,他便不得不回到“义利之辨”话语圈套之中,结果只能是自我纠结一番了事。这其中固然有性格原因,但又何尝不是传统力量的引导所致?他需要跳出这种圈套,在更大的视野之中和更高的境界之上反观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进而调整自己思考的路径,激发自己抗争的勇气,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与其说他缺乏这种能力,不如说是作者封堵了他这样做的通道。这样,他也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小”知识分子,他甚至走进了阿多诺的描述之中:“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④ 因此,我只能说聂致远身上有一种书生气或书呆子气,却并不觉得他具有多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小说中反复写到了聂致远的“认真”,而“你就是太认真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又成为别人规劝他的最好用词。这便是书生气或书呆子气。书生气当然是值得保护的,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的周汝昌就曾揭示过它的正面价值:“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⑤不过,在我看来,凡事认真且看不开、想不通虽然也是知识分子气质的基本表征,但如果这种认真只是限于与自己较劲,却不能向外拓展乃至出击,那就既限定了它的格局、气象和境界,也让主人公戴上了某种作茧自缚的精神枷锁。最终,他已无法走出他所自设的那座心狱之城了。我特别注意到,从小说开始,聂致远便处在一种心灵“受伤”的状态。而每一次的创伤体验,只是让他在形而上的信仰和形而下的利益之间徘徊一番;或者说得刻薄点,是在当婊子和立牌坊之间揣度一番,但此后他却依然故我,老调重弹,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叙事症候。 不妨来看看聂致远的“伤情”。当他拒绝了给老板写传记时,“小许的口吻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一种挫伤。”(P47)当他知道徐晓敏要竞争班长的岗位自己作为班主任却又拦不住时,“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这渺小让我感到屈辱。”(P93)当他怕学生给他差评而准备给不来上课的学生放水时,“这样想着我感到了屈辱”(P149)。当赵平平以打胎“威胁”他时,“我心里都非常憋屈。可这憋屈不能说,得憋着。”(P167)当范晓敏的预期不在于考试仅仅及格时,“这让我非常气愤,不来听课,不参加小考,还想拿高分!太气愤了!”(P190)当蒙天舒让他向当主编的师兄推荐他自己的一篇稿子时,他接受了任务,但随即感到“心里有点窝囊”(P252)。当请师兄吃饭蒙天舒即把他切掉时,“我心里发堵”(P256)。如此看来,从聂致远出场到他“捡漏”拿到教授职称为止,他的“认真”只是让他有了生闷气的理由,他敬奉的圣人之言,其功能之一只是为了“榨出皮包下面藏着的‘小’来”。他从头到尾都在自我反省受折磨,顺着同一个频率起伏波动,却始终没有长进,更看不到多少抗争的迹象,让人感到压抑。也许聂致远写出了当今学院知识分子的某种共性特征,但是他的个性却因此消融在普遍性之中。也许聂致远这个人物是可信的,但是在我看来却并不可爱,因为在他的精神结构中,士人传统虽时常把他托向天空,但现代犬儒主义又往往把它拉下地面,甚至常常是后者战胜了前者。因此,如果说在物化时代蒙天舒已是功利主义的代表,那么聂致远则应该是犬儒主义的典范。作为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都已异化,所不同者只在于,蒙天舒已然堕落而浑然不觉,以为这就是新常态;而聂致远则是在清醒之中慢慢陷落,他虽然痛楚满满,伤痕累累,但是我们能否从这种痛楚和伤痕中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却是大可存疑的。 走笔至此,我想到了路遥文学奖终评会上一些评委对《活着之上》的议论。有人说,这部小说缺少理想主义之光;还有人说,这部小说的人物是功能生人物。路遥文学奖颁奖前夕,我的一位师妹(她与聂致远年龄相仿、高校教龄也大体相当)读完这部小说之后也给我写来邮件。她在肯定这部小说的同时也感到很不满足:“我只是觉得主人公其实还不足以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就我接触的学者而言,真还有不少人恪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坚守一份清洁的精神默默前行,这是我心中的光亮。”所有这些说法都让我深思。我在想,虽然全国一盘棋,但北京的高校与地方院校是不是依然有所区别,以致我所看到的高校景象与阎真小说中所描述的并不完全一样?是不是因为阎真把聂致远、蒙天舒都写成了“单向度的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才无法完整揭示,学院生活的复杂性也才无法全面呈现?是不是因为阎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让他更关注庸常的现实,理想主义的火花才不容易闪现?因为他在一次对谈中曾有如下表白:“我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这对我来说意味着零距离地贴近生活。”⑥“零距离地贴近”是毫无问题的,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也需要出乎其外拉开距离审视,从而让作品的“向上”之姿坚定一些,进而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品格? 当然,话说回来,尽管我指出了这部小说所存在的问题,但我并不否认它在当下出现的现实意义。恩格斯曾经对拉萨尔说过:“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⑦我的批评意见亦可作如是观。 2015年4月30日 ①陈丹青:《退步集》,410—4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转引自黄应全:《〈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随感录》,http://www.199.con/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618607。 ③许倬云:《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Theodor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E.F.N.Jephcot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p.39. ⑤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⑥吴投文、阎真:《〈活着之上〉——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http://book.ifeng.com/a/20150227/12949_0.shtml。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6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