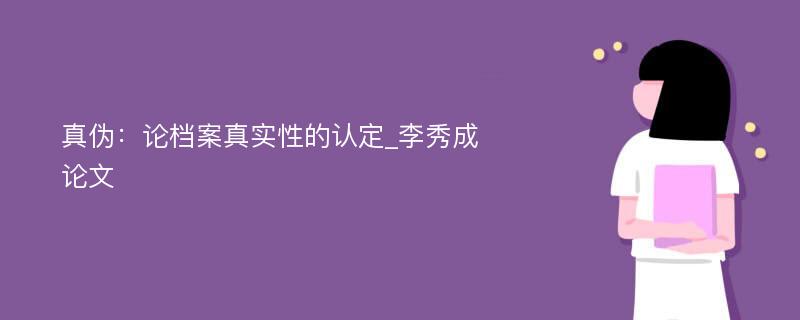
真的假的:档案真伪鉴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伪论文,档案论文,真的假论文,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1)05-0012-03
档案是信息大家庭中社会信用等级最高的一种信息资源,承担着维护历史真实的重大社会职责。维护档案的真实是档案工作者的天职。然而,不仅在传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未进行过档案真伪的鉴辨,在古今中外的档案鉴定理论中,也未将档案真伪的理论探讨纳入研究视野。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随着档案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档案社会化服务的进行,档案的真伪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质疑,在平时,笔者不只一次地受到局外人的诘问:“档案馆的档案能信吗?也有在基层档案室工作的朋友反映:单位里的报表、数据、汇报里虚假成分颇高,把这些材料当档案留存有意义吗?对档案真伪的疑问具有社会的广泛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什么是档案的真,什么是档案的伪,在实际工作中向社会提供真实的档案,从而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一、档案之“真”:是历史活动的印迹
对于什么是“真”档案,目前档案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这样描述档案的“真”:“档案只要其自身存在就没有‘假’的,而都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实际上否认了“假”或“伪”档案的存在。这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难以消除社会公众对档案的疑虑,也等于排除了档案管理人员在档案真伪鉴定中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发挥。[1]刘耿生在其《档案真伪论》一书中对档案的“真”持保留态度,认为档案有“真”有“伪”:“由于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从理论上讲,它的真实程度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文献”,而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也往往对档案造成不良影响,致使许多档案存在‘失真’,‘失实’,‘失时’和‘失辨’等状况,”即为“伪误档案”[2]。这实际上是从内容上去判断档案的真伪,把档案的真伪与档案内容的真伪混为一谈了,而忽视了档案与来源的对应关系这一重要特性。赵跃飞则认为:“一是档案形制过程的真实,即档案形制过程的原生态(形制的真实);二是档案所载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历史事实(内容的真实)。二者缺一不可。”[3]已经开始从档案的特性上去看待和鉴辨档案的真伪,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但仍把内容的真实作为档案真伪鉴辨一个重要指标,则又落入了传统认识的窠臼。
从以上观点来分析,大家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档案的真实性要高于其他文献。那么,档案就一定具有与其他文献不同的特点。我们从档案的特性中去分析其为什么在真实性上要高于其他文献,就不难认识档案的“真”。
人类的历史活动是真实存在的,不论其是否合理,或者荒谬,都是一种历史存在,也无所谓真假,是不可能更改的。档案是社会生活的分泌物,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只要是历史活动中产生形成的原始记录都是“真”的,也就是说,存在即真实。档案的真伪并不取决于其内容与历史事实的吻合程度,而取决于是否是社会活动中的原生性信息。内容虚假的档案,只要它是原始的记录,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是当事人活动的真实记录,作为档案,它应该是真实的。从原始记录中挑选出来作为档案保存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即使为了保管和利用的方便,从载体形式上也可能不是原始的了,但一定要以法律规定和社会认可的技术手段保证其内容的原生性,从而保证其真实。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档案是我们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最真实的信息材料。
同时,档案与其他信息材料不同,档案带有其产生时的许多原始特征,如内容、载体、信用标记等,构成多要素的信息的综合体。虽然我们利用的是档案的内容,但载体(原料、工艺、成分、品种等)、信用标记(印章、签字、文件版式、水印、密钥、元数据等)是保证其内容真实性和原生性的要素,是档案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只有档案的诸构成要素均为真时,档案才是真的,若其中一项为假,即使鉴定档案内容是真的,也不能因此肯定档案为真。如德国《明星》画刊抛出的《希特勒日记》,从内容着手鉴辨的文件和历史专家一致认为是真的,而从原始特征入手的专家则提出了不同看法:经检验,在紫外线照射之下,六个文本所用的纸张里面都有一种物质叫漂白剂,而这种漂白纸张的物质直到二战以后才开始使用。手稿用四种墨水写成,没有一种在二战期间被使用过。通过测量墨水中氯化物的蒸发,科学家们鉴定出这本本应写于1943年的日记实际问世时间才不到1年,最终被认定为伪造。因此,内容的真伪并不是鉴辨档案真伪的决定性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档案的真实实际上是判断与其对应的产生形成过程的真实,与档案内容无关,只要能确认是形成者(即来源)在其活动中产生的,并得到了载体、信用标记等特征的证实,我们就可以认定档案为真。从档案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没必要也没能力去鉴辨档案内容的真伪,档案内容的真伪应该留待利用者去鉴辨。
二、档案之“伪”:被放错地方的历史真实
按照辩证法的认识,有“真”就会“伪”,没有“伪”,也就无所谓“真”。对于档案之“伪”,传统的认识均是从档案的内容入手,以档案内容的“伪”来确定档案的“伪”,是沿用了历史学家们对史料真伪鉴辨的基本思路,而没有顾及到档案的特性和社会功能。档案是作为一种历史证据留存的,其重要功能是证实一种历史行为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档案内容在反映历史事实时的吻合程度。而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记录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准确,同样一件历史事件由于主观原因和所处角度的不同,参与者和旁观者的描述也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能苛求记录内容的完全真实。譬如,我国“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产生的许多档案的记录内容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不合常理和生活逻辑的,但我们不能因之否认这些档案的真实性,而归之为“伪”档案,否则,我们就难以正确认识那段历史。恰恰是这些档案能让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档案之“伪”呢?
第一,档案与形成者的对应关系的错置和误判,就构成档案之“伪”。传统的档案管理实践中没有档案真伪鉴辨的工作环节,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真伪鉴辨理论,是因为档案管理者对档案的来源能够严格的控制,在划分全宗时进行了严格的鉴别,一般不会出现错置和误判,对档案的真实性具有自信。这反映出档案真实性的关键是来源的真实确定。而今天,档案来源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对档案的来源的判断要比以往要困难得多,也直接导致“伪”档案出现的可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甄别。
第二,档案与其对应的历史活动的时空错置,就构成档案之“伪”。档案是历史活动即时即景的原始记录材料,时过境迁,或事后追补的记录材料,如回忆录、口述史料等都不能构成该历史活动的档案。这需要我们从语言特点、载体特征、记录方式、信用符号等方面去分析档案与其对应的历史活动的吻合程度,如若不符,即为“伪”档案。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添加、涂改、增补,破坏其原始特征,都可能使档案由“真”成“伪”。
第三,档案与形成者的记录特征和信用标记不吻合,就构成档案之“伪”。为了提高档案的可信度和证据性,在档案形成时,形成者还会有意识地在档案中作些标志,如签名、印章、水印、电子签名等。记录特征是形成者受其主客观条件控制而无意识留下的痕迹,标记则是形成者为加强内容的可信度和法律效用而主动设置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档案的DNA或“指纹”,这是其他信息所不具备的基本要素,即档案的凭证要素。正是这一要素使档案在众多信息种类中具有最高信用等级,否则,将会等同于一般信息,而失去了档案的重要价值,使档案不成其为档案。
第四,新型载体档案,如录音、录像、照片、电子文件等,为长期保管需要而转录时,应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否则,则构成档案之“伪”。新型载体由于失去了原始载体的保真作用,则需要在技术方面予以弥补,如电子签名、密钥技术和水印技术等,以保证档案内容的原生性和真实性。简单地进行档案信息数字化,在原始特征逐渐缺失的情况下,如没有法定的技术规范,失去信用保障,无异于大量地制造“伪”档案。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档案之“伪”,并非出现在档案的产生和形成之时,而是在档案管理的过程之中,对档案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和处置,或者是有意混淆,人为造成档案之“伪”。
三、档案“真”“伪”:决定于管理者良知、学识和能力
就像历史没有假如一样,档案没有真假之分。任何在社会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原始记录都是一种真实存在,都是与其对应的历史活动的真实反映。但在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者的误判或失误,则可能导致“伪”档案的出现。档案“真”“伪”之间其实没有天然的鸿沟,只要理顺了档案形成者与其历史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档案之“伪”也能转化为“真”,反之,“真”也能成为“伪”,两者之间是存在转化的可能的。
第一,要准确判断档案的形成者,即来源。档案管理中的来源原则同样也应该作为档案真伪鉴辨的一个基本原则,只要把档案与其形成者准确对应,那么档案就是真的。如清朝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自述,判断其真伪,则需判断其真实作者是谁,如能依据其他材料证实作者是李秀成,这份自述,要作为李秀成的档案,则是真实的;如能确认作者是曾国藩,这份自述,可作为证实曾国藩作伪的档案,则是真实的。当然,在确认是曾国藩伪造和不能确认李秀成所撰的情况下,而又作为李秀成的档案,则是伪档案。
第二、要准确判断档案载体。档案载体是随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不断发展演变的,这使档案载体不可避免地带有档案形成时期的诸多难以仿造的特征,时代赋予档案的这些特征,形成了档案之间的细微差别,通过对载体的这些差别的细致判别,则能确定档案的真伪。
第三、要准确判断档案信用标志。档案上的标志原本就是防止事后被人伪造而采取的技术性措施,如手印、印章、防伪标志等,通过对这些标志的比对,便能避免误判而形成“伪”档案。同时,通过笔迹、格式、书写习惯、用语、记录方式等与形成者的特征进行比对,从而寻求其正确的归宿。
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无法要求形成者能真实记载历史事实,也无法保证收集保存的档案在内容上都是真实的,但我们有责任保证档案的“形制过程”的真实,而不能在我们的手里出现伪档案,而使每一份档案的“形制过程”都还原其“原生态”,成为真档案,这是对我们良知、学识和能力的综合考验。
因此,档案真伪的鉴辨,关键在于对档案来源的甄别,同时要根据档案的其他原始要素确定档案的“形制过程”的真实,任何误判和管理失误,都可能造成档案之“伪”。档案是我们真实的历史脚印,也许并不都很光彩,但却是历史事实。档案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维护历史的真实,责任重于泰山。
收稿日期:2011-08-07
标签:李秀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