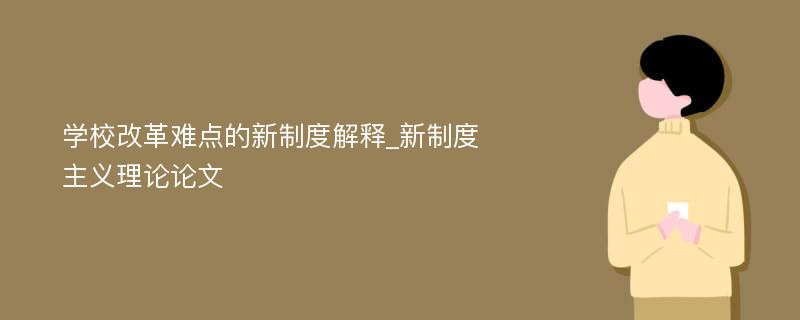
学校变革困难的新制度主义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难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5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1-0042-13
从历史上看,各种致力于提高和改善学校教育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但学校真正发生改变的却很少。学校在各种铺天盖地的改革举措前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和抵抗能力,似乎远超出改革者的预期。改造学校为什么会如此困难?本文将以新制度主义作为分析视角,尝试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解释。
一、学校变革的困难与已有解释
(一)比“登月”还难的学校变革?
美国的约翰逊(L.B.Johnson)总统说过:“解决我们国家所有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教育。”在当代社会,教育承担着这样“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可能正是出于教育近乎无所不能的想象,在历史上,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实现理想社会的努力从未间断过。而所谓教育改革,是指为了纠正和改善各种社会与教育问题而对学校进行改革的行动。[1] 社会经常要求学校作出某些重大的改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要求。所以,作为教育的主要服务机构——学校一直处于巨大的变革压力之中。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纷纷出台教育改革方案,要求学校改善教学质量以提高国家竞争力。改革者为了实现学校变革的目的,不断升级改革举措:从“调整局部”(fix parts)开始,到“改造人”(fix the people),再到对整个学校进行“调整”(fix the school),最后到“调整”整个系统(fix the system)。[2] 许多改革者甚至提出,如果学校再不进行有效改变,那就索性取消公立学校制度。[3] 但尽管如此,学校并没有表现出许多明显的变化,现在的学校与半个世纪之前并没有很大的差别。[4] 虽然在每次改革过程中,学校似乎都作出了某些重要改变,但这些改变大都不具可持续性。[5] 这种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都曾经存在。
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和冷战时期是两个被广泛认为发生了重大学校变革的历史阶段,但这期间学校真正发生的变革也远不如现在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大。[6] 而且这种现象也并非只出现在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在其他类型的国家中,真正的学校变革同样也是困难重重。我国当前所进行的课程改革是1949年建国后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历经了这么多次改革之后,我们的学校变化了多少呢?以减轻学生负担为例,早在1951~1966年间,国家就发布了八条有关“减负”的文件。[7] 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它依然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任务,半个世纪的改革也很难让学校少布置点家庭作业。同样,如果翻开以往历次课程改革的文件,我们会发现各次改革有许多目标是一致的,如要求学校改变教学方式、改变课程结构等。但学校真正发生的变革依然很少。
学校具备一些强大但又不为人所知的能力和资源,来应付和消解各种各样的改革压力,维持自身的稳定性。而且,学校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远远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以1966年全美教育研究协会(NSSE)出版的一本题为《变革中的美国学校》的年鉴为例,它认为被变革情绪所笼罩的学校将会发生爆炸性(explosive)的变革;变革之后的学校将无年级之分,也没有独立的(self-contained)教室,教师实行小组教学。[8] 但事实上,所谓爆炸性的学校变革根本没有发生。世界上每所学校依然有年级和班级,授课方式也都以单个教师为主。
“人类都可以把自己送上月球,还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呢?”在管理学界,人们经常用这句话来激励成员。但对于教育改革者来说,人类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实现登月计划,却无法在很长的时间里改变一所学校。
(二)对学校变革困难的一些已有解释
学校为什么未能如改革所要求的那样,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学校教育效能?对于这个问题,许多研究者曾作出了不同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学校变革的问题。他们认为人,尤其是教师是所有改革的关键,学校之所以未能实现各种改革理想,关键问题是教师或者缺乏改革的热情,或者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课程改革关键在于教师”,这句口号就是这类解释的一个例证。当前教育研究中的许多文献都是基于这个解释。
第二类则从学校管理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学校变革的困难或必要性。这种解释认为,学校是一个由官僚结构所控制的组织,而官僚结构的特性是保守、反对变革,对外界要求反应缓慢。只有改变学校的这种管理体制,学校才能真正适应外界要求,提高教育效能。这类解释现在也非常流行,各种各样的学校变革方案,如教育券改革、新公共管理等,都与这类解释密切相关。
这些解释都抓住了问题的某些方面,对于理解学校教育与学校变革也有意义,但是,就“学校变革为什么如此困难”这个问题而言,都还存在不足之处。
仔细分析这两种解释,可以发现其背后仍然基于一种把学校视为封闭组织或系统的假设。“学校中出现的问题”被等同于“学校的问题”,研究者往往从学校内部来解释学校的各种低劣表现,而没有从一个更大的视野和背景来思考这个问题。[9] 事实上,这种思维方式在整个教育研究领域中是非常普遍的。教育研究者通常假定教师和校长的行为模式完全是由教育原则所决定的,认为“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而鲍尔(S.J.Ball)明确指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社会结构与政策背景都会极大地影响教师和校长的教育行为[10]。格雷斯(G.Grace)也认为,“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和危机,其实都只是教育政策在深层历史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外在矛盾表现”[11]。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组织理论已充分证明,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并不是封闭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在环境系统保持着复杂而直接的联系。[12]
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些解释是错误的,但至少这些解释所关注的要素并不是影响学校变革的最大变量。其背后或许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或力量在维护着学校的稳定,只是改革者对此还不清楚,因此需要寻求一些更好的解释。
二、新制度主义及其研究取向
(一)什么是新制度主义
过去二十年中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在多个领域迅速崛起,并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招牌性标语和热门词汇。[13] 尽管新制度主义广为采用,其定义却缺乏统一的说明和界定。要理解新制度主义,需要了解什么是制度、为什么成为“主义(-ism)”以及新旧制度主义有何区别。
关于制度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个体或组织的行为,制度是如何形成以及制度是如何变化的。[14]
怎么理解“主义”呢?一些研究能被冠之以“主义”主要因为这些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些信仰即主义的核心内容。大部分有关制度的研究都“相信”制度会对各种社会行为和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可以用制度来解释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结构。[15] 在方法论上,制度主义反对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制度主义认为,各种社会行为模式和特征并不能完全还原为个体的行为,社会结构并不完全是个体或者组织追逐各种利益而形成的集合体(aggregation)。[16]
为什么叫新制度主义呢?首先,可从时间维度来区分新旧制度主义。制度主义有着很长的历史,但随着行为主义的崛起,制度主义进入长达几十年的低谷。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人们发现用单一的行为主义来解释社会结构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寻求各种结构化解释的理论重新出现,制度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崛起。为了更好地描述其发展轨迹,制度分析领域的两个重要人物马奇(J.M.March)和奥尔森(J.P.Olsen)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新制度主义。[17] 于是,就有了新旧两种制度主义。
其次,新制度主义是对旧制度主义的一种发展。朗慈(V.Lowndes)从六个分析维度来描述新旧制度主义的发展:从关注组织到关注规则(rules);从只关注正式制度,到同时关注非正式制度;从静态的看制度,到关注制度的动态性;从不关注价值,到持价值—批判的立场;从关注整个制度系统,到关注制度的内在成分;从认为制度是独立于环境的,到认为制度是嵌入在特定背景当中的。[18]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新旧制度主义的区分也只是粗线条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有一些早期的制度主义研究在特征上已经是“新制度主义”了。
(二)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和研究取向
新制度主义并非源自特定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的思潮,内部的多样性是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新制度主义标签下,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流派。霍尔(P.Hall)和泰罗(R.Taylor)对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划分最为经典。他们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历史学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大流派。各个流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流派里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19]
斯科特(W.R.Scott)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类。他认为,制度包含三方面要素:规制的(regulative)、规范的(normative)和文化—认知的(culture-cognitive)。它们构成了制度的三个主要成分,是三根支撑制度的“柱子”(pillars of institutions)。对制度不同面向的强调,就产生了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20]
各流派在对有关制度如何塑造行为、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迁等基本问题上假设各异,形成不同的研究取向。霍尔和泰罗认为,新制度主义存在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计算取向(calculus approach)和文化取向(cultural approach),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般都持计算取向,文化取向则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较为普遍,而历史学制度主义往往采取折中的态度。[21] 这两种取向可以对应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逻辑,前者信奉的是后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后者则强调适当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22]
斯科特认为,不同的制度要素体现着不同的机制和逻辑[23]。本文则选取文化—认知取向作为主要分析视角。这一限定和选择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正如上文所述,新制度主义内部不同的分析视角对现象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整合各家视角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主要的分析视角;二,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从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来研究学校教育,大多是持认知—文化的研究取向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或者是组织制度主义(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尤其是被称为“斯坦福学派”的制度主义[24],所以这一选择更有利于本研究更好地建基于前人的成果;第三,从社会与文化的(socio-cultural)分析视角来进行政策研究和教育研究,已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未来几十年最具发展潜力和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方向[25]。
(三)“文化—认知”的制度分析
“文化—认知”包含两个要素:认知和文化。新制度主义者首先强调认知结构或者图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认为个体之所以做某件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正如斯科特所言:“服从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觉察到还有其他的行为形式;遵从常规做法是因为它们被理所当然地作为‘我们做事情的方式’。”[26] 如一个学生想去上课,他总是自然地走向教室而不会走向寝室。在这个行为过程中根本没有利益和规范的考虑,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与心理认知学派不同,新制度主义在强调认知对行为的影响之外,更关注塑造特定认知图式的整个文化意义系统。用连接号把文化和认知这两个要素组合起来,是因为特定认知解释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外部的文化系统所塑造的[27]。
有关文化意义系统对个体行为与认知结构的影响,持文化—认知取向的新制度主义者大都从韦伯那里汲取学术养料。韦伯认为,任何社会行为过程都必须经过意义的协调(mediate)。个体不是直接地与外界刺激物发生机械的联系,而是首先赋予外界信号以某种意义,然后再输出特定的行为动作,这个行为被个体认为是恰当地表达了自己所希望表达的意义。所以,人类的交往过程就是在不断赋予意义和表达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要保证交往各方能对特定的现象和符号作出类似的理解,否则有序的社会交往就不能产生。例如,在上课过程中,想发言的学生就会举手,教师和其他学生都能理解这一行为。各方之所以会对行为和符号能有一个大致类似的解释,是因为在特定的场域中,交往各方共享一套特定的意义和符号系统,这套系统会以一种近乎标准化的运作方式对各种现象进行自动“解码”,它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软件系统”。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这样的意义系统。[28]
因此,一些被认为是“自然”的行为,如果置于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下,就会变得非常突兀和怪异。例如,学生一想到上课就会走向教室,这只是由于我们共享一套特定的教育制度,我们知道什么是“教室”、“教师”、“学生”、“上课”等等东西,“去教室上课”才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如果在一个没有类似教育制度的社会里,这些行为就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当我们认为应该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潜在地做一整套事情。[27] 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人类行为,我们都不应该把它看作是“自然”的、脱离于社会环境的,而是应该把它放置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来理解。
三、制度逻辑与学校变革
(一)组织域中的制度逻辑
学校以及学校教育背后负载着一套稳定的意义系统,这套意义系统决定了哪些行为能被阅读以及如何被阅读。理解了学校和学校教育的这个性质之后,就可以更为具体地把背后深层的教育制度与学校及学校教育实践联系起来。
新制度主义认为,意义系统或者制度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抽象程度存在,而且不同层次领域的制度对特定对象的影响性质和力度都是不一样的。[30] 一般来说,制度形态越抽象,它所能解释的范围就越宽,但是它与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松散和间接。所以,需要基于不同的问题需求选择不同的分析层级。对于本研究来说,“组织域”(organizational field)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析层级,因为它对特定组织与个体行为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是最能体现新制度主义分析效力的层级。[31]
“组织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迪马吉奥(P.DiMaggio)和鲍威尔(W.W.Powell)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组织域是指一个组织生活区域(area),在这个生活区域中有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规范机构和其他一些生产类似服务和产品的组织。[32] 布迪厄(P.Bourdieu)则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提出,场域(field)是社会的真正实体,因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33]。
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生存于特定的组织域中。学校的组织域就是由学校、(社区)家长群体、政府管理部门、大学、考试机构、公司、教师教育机构、出版社等组织所构成的一个关系系统。
组织域中的所有组织都有其正式和非正式的价值观、规则、习俗和利益,它们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中不断碰撞与交往。久而久之,组织域也会与组织内部一样,发展出一套制度来控制和管理不同组织之间的交流。[34] 组织域中的制度也与其他层级的制度一样,包含斯科特所说的规制的、规范的和文化—认知的三个要素,这些要素都以不同的作用机制使各种组织行为结构化和模式化。如果仍然先从文化—认知角度来看制度的话,那么在学校的组织域中所发展出来的制度,其实就是一套共享的符号意义系统。它为各组织提供了如何解释各种行为和现象的一套认知模板和符号概念。这就是制度逻辑。
所谓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是指一套控制着特定组织域中各种行为的信念系统。[35] 制度逻辑也是一套“组织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它为组织域的参与者提供了有关它们应该如何开展行动的指南。[36]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各种各样的行为其实都是被制度逻辑所“编程”(programmed)后的结果。制度逻辑是学校背后的神秘力量。
制度逻辑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赋予有关组织以“身份”。因为,任何个体和事物在与外界交往接触的过程中,都必然要面临身份的问题。[37] 身份的确定是交往的基础。任何组织与学校进行交往,首先需要对“什么是学校”形成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就是制度逻辑赋予学校的合法身份。
身份一旦确定下来,就潜在地规定了学校应该怎么做。各方在与学校交往的过程中也会对学校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做有一个预期。因此,为了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能够在组织域中继续得以生存,学校就会发展出一套相应“学校教育法则”(grammar of schooling),以对学校教育的各种行为与要素进行结构化控制,使之呈现某种可预期与可识别的稳定模式(pattern)。所谓学校教育法则是指那些用以组织学校教学行为的规则结构与惯例。[38] 那些在不同学校中都存在而且比较稳定的行为规则与结构,就是学校教育法则作用的结果。例如,对学生进行年级划分、对学生进行分班、在一个封闭的课堂进行教学、基于学科内容的学习、基于单个教师的授课、把学习时间划分为大致相同的课时等等。
任何行为一旦被结构化和模式化,同时就意味着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根据具体的外在环境及时变化。所以,学校教育法则的存在就会使学校教育脱离变化了的教育需求与环境。例如,由于“基于学科内容的学习”这一法则的长期存在,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知识的完整性与综合性的要求。即使改革者在最初没有直接指向学校教育法则,但当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学校教育法则的限制。因为,深层次的变革必然要对那些长期存在于学校教育当中、但已不适合当前社会需要的行为惯例或者结构进行改变,如“研究性学习”就要打破以往基于学科内容教学的惯例。
但是,学校教育法则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由特定的制度逻辑所决定的。换言之,学校教育法则只不过是组织域中各方对学校所赋予的身份的自然展开而已。所以,任何深层次的学校变革必然迟早会对制度逻辑提出变革要求。
(二)制度逻辑的稳定性与学校变革的困难
承上所述,任何深层次的学校变革必然对制度逻辑提出变革要求。但是,制度逻辑一旦形成,就极具稳定性,改变制度逻辑非常困难。这是由制度逻辑的特征决定的。
1.制度逻辑的形成是“集体行为”,单方面的改变很难成功
正如上文所说,制度逻辑是组织域中的各方经过不断的交往和妥协而形成的,它是集体行为的结果。制度逻辑一旦形成,组织域各方的交往就会以此作为基础,成为“集体生活”的必需。所以,制度逻辑赋予学校以特定的身份,不仅仅是学校与制度逻辑之间的“一对一”关系,而是涉及学校与其他各方以及其他各方之间的“一对多”、“多对多”关系。因为,各方与学校的交往以及其他各方之间与学校有关的交往,都是建基于它们对学校身份的共识。尽管这种特定的身份规定对学校来说,可能不是最优的,但是从整个组织域的层面上来说,这样的一种定义是保证各方顺利进行交往的重要安排。
迈耶(J.W.Meyer)和罗文(B.Rowan)认为,美国社会赋予学校的合法身份和定义是“在一所达标(accredited)的学校里,一个被认定合格(certified)教师向一群注册了的学生传授一些规定的课程”[39]。基于这种身份认识,大学会根据科系来培养相应的教师;出版社会根据科目、年级来出版课程教科书;公司也会对毕业年级学生制定录用计划;认证机构就会按照年龄、学分或者考试成绩等标准对学生进行审核、注册等等。只有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各方才能“读懂”对方在做什么,组织域也才能因此得以顺利运转。如果其中一方突然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那么相关的交往行为就会立刻变得困难起来,组织域中的生态就会受到威胁。例如,尽管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说,“基于学科内容的学习”在很多时候都不是最优的。但是,如果学校因此而进行重大变革,代之以跨学科的教学,那么大学如何培养教师呢?如果不基于学科知识的权威性,考试机构如何能对学生的成绩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一系列新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由此可见,如果学校变革威胁到制度逻辑,那么这种改革行为就会被组织域中的各方视为“单方面毁约”行为,组织域的已有生态系统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排异反应”。这时,改革的学校也就会立刻感受到有一个类似韦伯所说的“铁笼”(iron cage)一样的东西在笼罩着它,它会极力把学校拉回原有的位置[40],“让学校像个学校的样子”。
所以,在这样一个由制度逻辑所维系的精致的组织域中,制度逻辑把各方都有效地捆绑在一起,任何改变都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从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要求各方围绕着学校教育的要求重新“协商”制度逻辑。但是,通常改革者很少能够具备这样的能量来操纵整个组织域,更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智慧来对制度逻辑进行人为的设计。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一些研究者提出,除非由社会和公众再来对学校教育的职责和身份进行重新深入、公开的大讨论,否则真正的学校变革难以实现,即使偶尔出现,也不能持续。[41]
2.制度逻辑可以自我“神化”,使之免于理性的质疑和冲击
制度逻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信念,它不是直接服务于技术性的需要。也正是如此,它就存在被(工具)理性质疑的危险。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应该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来自理性思考的质疑和冲击是制度逻辑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压力。
对个体来说,认知的不协调会带来不安,于是会产生一套防御机制来自动剔除那些可能威胁自己信念的信息。集体作为整体也是如此,它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信念不受威胁,就会通过各种保护机制把制度逻辑与外界的理性世界“断耦”(decoupled),使之免于被质疑和冲击。
迈耶和罗文曾分析社会如何保护自己有关学校的信念不被理性质疑而采取的措施。[42]“在一所达标(accredited)的学校里,一个被认定合格(certified)教师向一群注册了的学生传授一些规定的课程”,这是公众对于什么是学校教育的一种信念。在这种逻辑下,一所没有开设历史课程的高中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而学生在教室里究竟学到多少历史知识则是次要的。但是,从理性上说,学校教育的核心是“教与学”,社会之所以创办学校,家长之所以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学习到所需要的知识。所以,社会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尴尬,各方就达成一个默契,即不对学校教室内部的教学行为和效果进行严格的审查,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信任逻辑”(logic of confidence)。信任逻辑类似于考夫曼(E.Goffman)所说的“面子工程”(face work),它在维持其他组织和个体的面子的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43] 它的基本运作逻辑是:既然是一所合格的学校,我们就应该相信它不会叫语文老师去教历史课程;既然历史老师是大学培养出来的而且经过认证的,我们就应该相信他能恰当和有效地把课程内容传授给学生;既然学生能通过考试机构的认证,我们就应该相信他掌握了我们要求他掌握的历史知识。
在这种逻辑和保护机制下,理性质疑变成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它把各方都已经捆绑在一起,对任何一个环节的质疑都可能引发一连串危机,威胁整个社会系统。于是,“就会产生一些所谓不可讨论或者禁忌的话题。尽管对于这些东西大家都清楚,但是却不能说。如果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放在公众论坛上讨论,那就会引发严重问题。正是这样……就有必要把一些东西‘神化’,让有些东西不说出来,使之成为一种例行习惯和仪式(ritual)”[44]。至此,制度逻辑就完成了自我“神化”(as a myth),成功地在它与技术需求之间塑造起一个宽阔的缓冲地带,使之免于理性质疑的冲击。
3.个体往往无法意识到制度逻辑的影响,因此很难被有意识纠正或改变
制度逻辑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往往是在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是如此的过程中施加影响的,避免了被当事者进行有意识纠正或改变的可能性。
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行为习惯和认知假设,事实上背后都体现着制度逻辑的力量。在一个制度化程度越高的环境中,习惯性行为和“理所当然”的假设就会越多。反过来,习以为常的行为越多,个体越是难以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纠正和改变制度逻辑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学校教育恰恰是这样一个充满习惯性行为的领域,这也是新制度主义者把学校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经验上,很容易发现学校教育存在许多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并不是“自然”的东西。如为什么每个学校都有年级、班级之分,为什么每节课都是由一个教师、而不是一群教师在授课,为什么学校的课程是以学科为单位,为什么每节课的时间都差不多等等。具体到课堂教学行为,杰克逊(P.W.Jackson)指出,在课堂中教师的许多教学行为都是依习惯做出的,即使在课后教师也是经常解释不清楚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45]
在很多时候,大家事实上是在不知不觉中“践行”(enacted)和复制着制度逻辑。正如“钱币的两面”,人们在无意识地“践行”着制度逻辑的同时,也会无意识地剔除其他一些“新异”的观念和行为。[46] 既然有这么多的行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就会有大量有别于这些行为的想法和建议,被当做“匪夷所思”、“幼稚可笑”而被自动剔除。但正如达令·哈蒙德(L.Darling-Hammond)所说的,在学校教育中,大家经常阻止那些可能导致尴尬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也许恰恰在潜在上是最为重要的东西。[47]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样“一来一去”的过程,当事者自身却往往是无法意识到的。既然当事者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几乎谈不上如何有意识去纠正或改变了。也正是由于人们经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在许多时候,一些看似致力于改变制度的努力,事实上是在强化制度。例如,用国家行政的力量来要求学校进行“校本管理”,是在改变还是强化国家管理?因此,在没有把支撑学校教育行为背后的制度逻辑明晰化之前,许多改革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它非但难以改变制度逻辑,而且在客观效果上还强化了制度逻辑。
四、结论与有待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任何深层次的变革必然要设法突破学校教育法则的规限,但学校教育法则并不是学校自己所建立的法则,而是学校遵从制度逻辑的结果。归根结底,深层次的、可持续的学校变革必然会对制度逻辑提出改革要求。但是制度逻辑是组织域各方共同建构起来的,任何变革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改革者往往不可能具备相应的能量来平衡各方的要求,所以单方面的改变很难获得成功。而且,制度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神化”,它有着强大的保护机制使之能够免受理性的质疑,使得改革者难以组织有效的批判和攻击。最后,对制度逻辑的“践行”和复制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因此,个体即使具备改革的意愿,也很难有意识地抵制制度逻辑的影响。以上种种因素和结构决定了深层次的、可持续的学校变革非常困难。
但以上的分析还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论轮廓,新制度主义要更为精确地解释学校教学行为以及学校变革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进一步说明和研究的课题。
首先,学校制度逻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组织域中存在着一个制度逻辑,结构化地控制着学校教育的各种行为。但是对于制度逻辑的具体要素及其关系是什么,目前的研究都还未能作出系统的说明。但正如福瑞兰德(R.Friedland)和阿福德(R.R.Alford)所说的:“不知道制度逻辑的内容,我们就不可能具体地解释哪些类型的社会关系会对组织或者个体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48] 可是,要勾勒出支配学校教育行为的制度逻辑的主要内容,是一个非常庞大和艰辛的研究课题。它需要我们从现代教育制度形成的起点来追溯教育制度的演化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一些关键要素并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许多新制度主义分析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49]。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从结构上说,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借鉴西方而建立的,但远在现代教育制度成形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一套全国性的非常系统和精致的科举制度,它对当前学校教育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这两股不同的力量和逻辑是如何“打造”出当下中国学校教育的制度逻辑呢?回答中国学校所面临的制度逻辑的任务,只能由我国学者来承担。
其次,制度逻辑是如何变化的?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制度逻辑是非常稳定的,而且也分析了造成制度逻辑难以变革的原因。但是,制度逻辑并不是不变的。不过,既然制度逻辑是如此的稳定,那它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新制度主义所面临的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新制度主义的已有理论框架中,它很难解释制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50],所以,如何才能更好地解释制度变化就成了制度主义者在过去几年中的一个最重要任务[51]。
第三,制度逻辑扩散的机制是什么?在本文的分析中,制度逻辑对组织行为的决定作用得到了强调,但事实上,组织和个体作为具备能动性的行为者,在制度逻辑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制度逻辑的扩散不是简单的、单向的流动,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学校变革,需要更为具体地分析制度逻辑与组织、个体之间的作用机制。事实上,如何更为准确地描述制度变迁和扩散背后的机制问题,也同样是当前新制度主义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52] 因此,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学校变革的困难,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校教学行为和学校变革,而且也将有力地促进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
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曾荣光教授与卢乃桂教授,他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制度分析的深刻见解,但文中可能的谬误则与两位先生无关。
标签: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学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