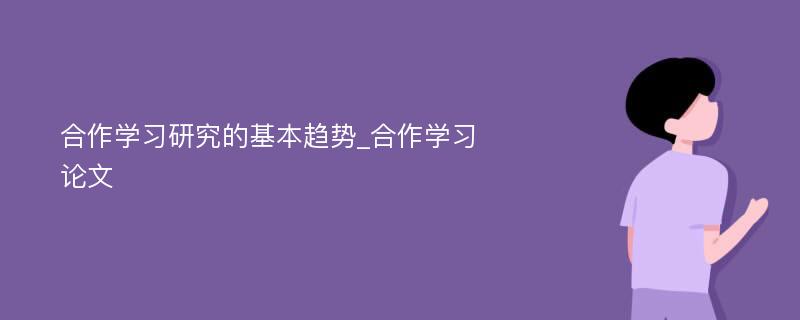
合作学习研究的基本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势论文,合作学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作学习是当前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被誉为当代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但合作学习作为一种古老的教育观念和实践早已存在。1806年,合作学习小组的观念从英国传入美国,受到美国教育家Park、Dewey等人的推崇并被广为应用,19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了现代合作学习理论[1] (pp.4-11)。1960年代中期,D.W.Johnson & R.T.Johnson等人在明尼苏达大学开始训练教师,指导他们如何采用合作学习进行教学,并创立共同学习中心,总结合作学习的相关研究,探讨合作学习的本质和成分,构建合作学习的理论模式,并进一步将理论细化为具体的教学策略和程序。1970年代晚期,R.E.Slavin也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提出“学生小组成就区分法”(Student' s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s,简称STAD)[2] (pp.60-66);而加州大学的Elliot Aronson也提出拼图法(Jigsaw)合作学习策略[3] (pp.75-79)。1980年代中期合作学习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从1990年代起,合作学习研究的影响日益扩大,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德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尼日利亚、中国等国的教育领域。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合作学习研究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以前合作学习研究虽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也有几个领域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1.适用条件不明确。D.W.Johnson & R.T.Johnson回顾了过去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合作、竞争以及个体学习方面的研究,总共有520个实验研究,100多项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出现在不同时期,被试年龄不同,学习任务类型也不同,采用的自变量不同,对因变量的测量也多种多样,但总体结果都证明了合作学习的有效性[4] (pp.18-21)。2000年,D.W.Johnson & R.T.Johnson和Stanne在对合作学习方法所作的一项元分析中指出,有超过900项的研究确认了合作学习比竞争的和个人主义的努力学习效果要好[5]。
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合作学习的效果优于个体学习,但也有研究证明合作学习并非永远有效。学生的个性、学科的特点、学习任务特征等各不相同,合作学习并非在任何教学条件下都是最佳的教学组织形式。但合作学习的适用条件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对此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2.评价体系不完善。有效的合作学习策略要因学科、学习任务以及学习者个性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评价合作学习的方法也不能一成不变,应当多元化。例如,对刚开始进行合作学习的学生和已经具有较多合作经验的学生,评价的标准应有所不同;合作学习的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的努力,教师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如何评价教师在合作学习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深入研究。构建系统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才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对合作学习做出科学的评估。目前的合作学习评估多注重学生最终的学习成绩,忽略了合作学习的其他因素评估。
3.合作学习策略单调。西方的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领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开发了小组成绩分享法、小组—游戏—竞赛法、切块拼接法、共学式、小组调查法、合作辩论等多样化的合作学习策略。D.W.Johnson & R.T.Johnson(1993)的研究发现,当学习具有以下五个要素时,合作是有效的:积极互赖、面对面的相互促进与互动、个体和小组责任、人际和小组技能和小组[6] (p.89)。但这些观点只是粗线条的策略描述,没有深入研究责任扩散、群体极化、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社会干扰等心理因素对合作学习的影响。在合作学习实践中,角色分工不明,成员的参与机会不均等,个别成员控制小组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直接影响合作学习的效果。此外,对于合作小组的认知策略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限制了合作学习的深入探讨。
4.教师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的监控与介入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教师的参与,合作学习就容易流于形式,或者出现偏差,导致学习效率低下。在合作学习中,教师要充当“管理者”“促进者”“咨询者”“顾问”和“参与者”等多种角色,旨在促进整个合作学习过程的顺利进行,以提高学习的效率。但综观1990年代以前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多把目标锁定在学生身上,很少关注教师的作用,致使教师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定位很不明确。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合作学习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团队理理念融入到合作学习中
“合作学习”的英文表达方式很多,例如,group learning,cooperative learning,collaborative learning等,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将合作学习称为team learning,可见合作学习中的团队理念已引起学者的重视。
关于什么是合作学习,不同的心理学家有不同的定义。英国著名学者Light和以色列著名学者Me Varech(1992)认为,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小组中共同学习的学习环境。加拿大著名教育心理学家Winzer(1995)认为,合作学习是由教师将学生随机或有计划地分配到异质团队或小组中,完成所布置的学习任务的一种教学方法[7] (p.28);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学习中心的D.W.Johnson,R.T.Johnson(1999)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学生共同学习,以完成共同的学习目标[8] (pp.67-74)。
综观世界各国合作学习专家的观点,合作学习的内涵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1)合作学习是以小组为主体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2)合作学习主要是一种同伴之间的合作互助活动。(3)合作学习是一种目标导向活动。(4)合作学习强调集体受奖励,同时也重视个体责任的划分。(5)合作学习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比较突出。
从合作学习的内涵来看,不是随便找几个学生凑到一起就可以产生高效的学习,合作小组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较高的凝聚力,能使其成员从中找到满意的归属感和较高的荣誉感,小组成员之间知识结构及个性特征互补,而且彼此坦诚、信任,学习的投入程度高,整体运作效率高,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高效的合作学习效果。而这些高效合作学习小组的特征与团队的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可以说,合作小组的构建正在融入团队的理念。
2.对于合作学习中的认知过程分析更加深入
合作学习的认知研究逐渐为学者所重视,并把焦点放在了合作性知识建构过程研究和合作小组成员的认知风格研究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认为,合作性知识建构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个体知识建构阶段。学习材料呈现后,个体分别将他们自己的心理模型与目标材料相比较(个体理解监控过程),并将个人的心理模型与其他人相比较,这就是合作性理解监控过程[9] (pp.47-77)。当前的研究认为,由于每个人都有孤立的、不同的知识基础,使得个体间在解释和推理上存在差异,即认为心理模型(或个人知识结构)是造成合作过程中每个人表述差异的原因。二是合作性联合建构阶段。合作者之间试图协调在个体知识建构阶段检测到的差异,小组集体讨论的结果使其成员对个体心理模型做出调整。合作性建构活动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精制,指个体增加、修改或更正另一个人的描述[10] (pp.379-432);商讨,指相互交换意见共同形成一个完整观念;冲突,主要是对认知冲突的合理化[11] (pp.399-410)。认知心理学传统上以个体为单位来分析学习过程,这显然不能完全揭示合作学习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最近的研究大量采用口语报告编码分析的方法,对合作条件下知识建构过程做出了精细的分析,这类研究将成为整合认知建构与社会建构研究的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组成员的认知风格也引起了合作学习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04,Dawson Hancock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学生的同伴取向与合作学习的动机和成绩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具有高同伴取向和低同伴取向的学生分别进行为期15周的课程合作学习训练,同时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技能、积极互赖、成员个体责任分工、合作技能和小组学习活动的训练。课程结束后,评估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成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高同伴取向和低同伴取向的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然而高同伴取向的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显著高于低同伴取向的学生[12] (pp.159-166);2000年,Alan Ramsay,Dean Hanlon和David Smith分析了大学会计专业学生的认知风格与其合作学习的偏好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考察了认知风格的四个维度:外向/内向、感觉/直觉、思维/感情、判断/感受和合作学习偏好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小组成员的合作学习偏好与其认知风格的外向/内向维度显著相关,外向者更喜欢合作学习提供的社会益处。外向/内向特质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信念在学生的合作学习偏好上存在交互效应[13] (pp.215-228)。Hutchinson & Gul认为,不应该强迫学生选择不适合他们认知风格的学习方法,教育者应该在学习方法方面为学生提供广泛的选择余地,允许学生从中选择最适合自己认知风格的学习方法。
3.对于适宜合作的小组学习任务特征的进一步明确
合作学习的经验表明,并不是任何的小组学习任务都能调动小组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学者认为小组学习任务应具备如下几个特征[14] (pp.72-75)。
(1)开放式的学习任务,任务的完成需要复杂的问题解决技巧。小组学习任务有两大类:一类是常规性的,学生遵循清晰的、详细的程序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或预见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利用词典解释单词,总结一段话等学习任务,学生通过认真遵守指令,运用熟悉的信息、公式或记忆中的材料就能完成任务。这类任务往往与真实的生活无关,没有必要进行小组合作;另一类是开放性的。这一类任务往往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或模棱两可性相关,学生可以设计一个实验,建构一个模型,或者调和有争执的不同观点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制定不同的计划、探索多元的问题解决路径、提出多种合理的方案。这一类任务要求学生能够分享各自的不同经验,使他们的信念和观点合理化。在完成这类任务的活动中,学生不仅要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和评估,还要讨论问题的前因和后果,探询相反的观点,形成共识,最后得出结论。因此,开放式的学习任务适合小组合作来完成。
(2)内容多元化的小组学习任务,为学生创造表现其智慧的多种机会。单维的学习任务测量的是单一的技能,因此常使这方面有优势的学生取得成功,另外的学生遭到失败。学生很容易得出结论:某些学生是聪明的,某些学生是愚笨的。这种刻板印象固化了学生在班级中的地位,从而影响其在小组中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而内容多元化的小组学习任务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有利于发挥他们的多种潜力,提出不同的问题解决策略,从而为小组做出贡献。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小组成员各显其能,改变其在班级的固定的等级地位,认为每个同学都是聪明的,从而调动其学习积极性。
(3)任务的完成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的积极互赖和个体明确的责任分工。需要小组成员之间彼此依赖、明确分工、密切合作的学习任务更能引起学生合作的兴趣,通过合作探讨能够使有争议的观点达成小组共识,或者提出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如果学生单独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合作学习就会流于形式,浪费时间和精力。
(4)有清晰的小组成绩评估标准。合作学习任务的完成要有清晰的评价标准,让学生明白老师将如何评估他们的学习成绩,如何评估小组和个体的努力。Alexander W.Chizhik以中学生为被试,考察不同的小组学习任务类型(唯一答案和多种答案)对于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小组成员参与合作学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多种答案任务条件下,有相似的表现,但男性在唯一答案条件下,能给出更好的建议,但在多种答案情况下,女性往往能给出更多的解释[15] (pp.63-79)。
4.关于小组结构特征的研究
因为小组的构成直接影响小组学习活动的开展与学习成绩的好坏,因此关于小组结构的研究近来很是活跃。主要研究成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异质小组与同质小组。异质小组主要是指由不同性别、家庭背景、能力水平等特征的学生构成的学习小组;而同质小组成员的这些情况是相近的。1996年,Slavin简要地论述了小组构成对于合作学习的可能影响[16] (pp.43-69),认为异质小组是通常提倡的分组方式,其依据是异质小组合作学习优于班级学习成绩。但将异质小组学习和同质小组学习相比较时,结论却很不相同。
Lou et al.(1996a,1996b)在一项元分析中直接比较一个班内的同质小组和异质小组学习情况,他们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同一个班内,异质小组的学习效果优于同质小组吗?二是小组构成的学习效果依赖于学生的能力水平吗?三是合作学习能够提高异质小组中所有学生的学习成绩吗?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班内,异质和同质小组的学习效果之间有较显著的差异。然而同质小组学习与异质小组学习相比哪个更优越,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对于能力低的学生而言,异质小组学习效果明显优于同质小组;中等能力的学生在同质小组中受益要明显大于异质小组中;对于高能力的学生来说,小组能力构成对其影响没有显著差异[17]。低能力学生同质小组学习效果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完成小组学习任务的集体无能感所致。根据Webb的理论,小组内个体的学习效果依赖于其关于给予或接受的解释情况,例如,中等能力的学生在异质小组组中可能既没有充当指导者也没有充当被指导者的角色,而是随大流,因此他们在完成小组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忽视,今后的研究应该找出改变中等能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的角色和任务的方法。也需要研究克服高能力学生和低能力同伴合作时产生的抵制情绪[18] (pp.21-39)的方法。
(2)结构与非结构小组。D.W.Johnson & R.T.Johnson认为只是随意地将学生放在一个组中,期望他们一起工作,并不会产生预期的合作学习效果。只有当小组是有结构的,学生理解人们期望他们做什么,期望他们如何在一起工作时,合作学习的潜力才会最大程度地被开发[19] (pp.173-202)。这就意味着小组任务是已确立的,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能意识到需要他们为完成小组任务做出贡献,并且同伴之间要彼此帮助。教会小组成员学会人际交往和小组合作的技能,以促进和同伴分享、相互尊重的态度产生,冲突产生时,具有解决冲突的意愿,了解小组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当这些条件存在时,小组成员就会感觉到自己被同伴接纳,同时他们也可能被激发出更大的学习热情,取得更大的学习成绩。这正是结构小组的特征,而非结构小组则不具备这些特征。
Robyn M.Gillies以223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结构与非结构小组的合作学习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小组中的成员比非结构小组成员更意愿与他人一起完成被分配的任务,结构小组成员彼此之间能够提供更精细的帮助和支持。而且由于结构小组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与同伴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比非结构小组中的成员产生更强的小组凝聚力和相互学习的社会责任意识。结构小组中的成员表现出较少的非合作行为和偏离任务的行为,能够倾听同伴的意见,分享并交流观点和信息[20] (pp.197-213)。
(3)同伴地位对合作学习的影响。合作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其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情况必然不一致。这一因素对小组成员的学习是有重要影响的。Paulttelloyd和Elizabeth G.Cohen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学习小组成员地位差异的程度可以直接预测地位低的成员在合作学习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即地位低的学生对小组学习活动的参与程度往往也低[21] (pp.193-216)。
Ian A.G.Wilkinson和Irene Y.Y.Fung也考察了小组构成对合作学习的影响[22] (pp.425-447)。在教师主导下的同质小组中,同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循环进行的。而在同伴导向的异质能力小组中,同伴效应直接源自小组互动和同伴之间的讨论,通过这些途径达到认知的重新建构、认知复述、问题解决和其他高水平的思考。此外,在不同种族、性别构成的小组中,同伴的效应源自学生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根据他们在小组内感知到的地位和相对影响而产生的。他们认为这些同伴效应与教学过程相互影响,最终调节了小组构成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此外,新近的合作学习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合作学习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还将合作学习的范围由中学向两端延伸,即向下推及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学生,向上推及大学生乃至成人学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