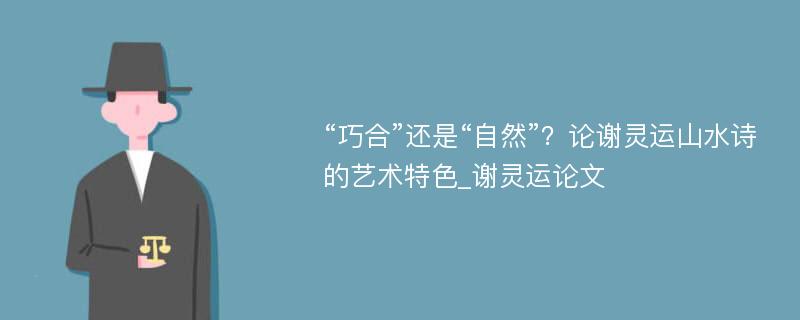
“巧似”抑或“自然”?——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征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自然论文,艺术论文,谢灵运论文,山水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9)02-0039-04
关于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特征,文学史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一种观点认为谢诗尚“巧似”。钟嵘《诗品》说:“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1]9与此相关,论及谢灵运诗歌创作态度时,宋人黄庭坚云:“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1]507(《韵语阳秋》)清人方东树云:“康乐固富学术,而于《庄子》郭注及屈子尤熟,其取用多出此。至其调度运用,安章琢句,必殚精苦思,自具炉锤,非若他人掇拾短订,苟以充给,客气假象为陈言也。”[2]146二人都提到了谢诗创作中的“炉锤”之功。而所谓“炉锤”之功,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对词语进行精心选择、反复推敲、刻意加工。经过这样千锤百炼、穷力追新,以此来“极貌以写物”,以此达到“巧似”之境界。
另一种观点认为谢诗风格“自然”。鲍照在评论谢灵运与颜延之诗之优劣时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3]881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1]13-14二人都是在赞美谢诗风格的自然。与此相关,论及谢灵运诗歌的创作态度时,就不是强调“炉锤”之功了,而是另外一种说法。宋人吴可《学诗诗》曰:“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唐皎然《诗式》曰:“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4]118把谢诗风格之自然归诸“参禅”、“性情”、“空王之道”(即佛道)。
然则谢灵运山水诗之艺术特征究竟是“巧似”还是“自然”?谢灵运之于诗歌创作是不废“炉锤”之功,还是得“空王之助”、“直于性情”、妙手偶得,二者是矛盾的还是具有某种辩证关系?我们认为,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不废“炉锤”之功,反复推敲,摛藻炼句,力求“巧似”,山水景物描写努力追摹自然之真、巧夺造化之妙,以至于有些句子达到了“自然”之境界。
一 “巧”,即思巧,指构思方面,使作品具有“理趣”或“神理”
诗歌中山水描写贵在传神。诗人往往以貌取神,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山水景物之神韵就会在读者的想象中产生。谢灵运则不然,他的笔下“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白居易《读谢灵运诗》),对所写景物进行细致的描摹刻画。然而这样做的弊病就是容易使景物过于实在,从而失去其神韵。但是,谢灵运经过巧妙的构思,抓住景物的“神理”,使琐屑的景物各个自足,展现出生命的美。
在文学创作中,“神”这一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创作主体之“神”。如在《文心雕龙》中,有《神思》篇,其中的“神思”指创作主体的联想和想象。二是创作客体之“神”。指作者笔下所描写的人物或自然景物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此处,我们讨论的正是创作客体之“神”,具体来说,就是谢灵运笔下的山水景物的精神风貌。
“理”可以理解为规律,是谢灵运的最高哲学概念,他所信奉的各种学说,终归一个“理”字。“理”既存在于诗人的主观意识里,还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就像道家所讲的“道”,佛家所讲的“真如”。谢灵运在描写山水景物的时候,经过巧妙的构思,使“神理”贯注其间,使景物描写不仅形似,而且气韵生动。
如何才能使“神理”贯注其间呢?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说:“大约匠心独造,少规往则,钩深极微,而渐近自然,浏览闲适中,时时浃洽理趣。”[5]532就是说创作主体要抛弃一切规则的束缚,驰骋神思,体会、把握山水景物的规律和极细微的特色,再用语言表现出这种规律和特色,追求与自然的无限接近。万物之所以呈现这样或那样的状貌,自然有它的道理,亦即“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把握住了这种“理”,所描写的山水景物就会接近自然。在谢灵运的诗歌中,我们发现,凡是传神的景物描写,首先必然符合自然之理;其次,诗歌是人类的精神产品,蕴含着作者独有的情感意趣。自然之理与作者的情感意趣相融合,诗歌才能具有神韵理趣。今撷取几例,试作分析:
(1)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过始宁墅》)
以上两句诗烘托出一种静谧的氛围。没有一丝风,白云在山间弥漫,青黑的山石在其间若隐若现,好像被白云环抱。如果风吹云走,白云就抱不住幽石了。山石、白云虽然无言,一个“抱”字却传达出静谧的信号,隐含着自然之理。翠绿的竹子倒映在清清的溪流中,既无激流猛浪,又非死一般的沉寂,而是回荡着阵阵涟漪,平添了灵动的韵味。关于作者的情感意趣,体现在两个动词的运用上:一是“抱”,白云好像有了生命,有了情感,轻轻拥抱沉睡的幽石;一是“媚”,绿篠仿佛绿衣少女,与清涟眉目传情。绿篠与清涟之间融入了作者独到的体验,使景物描写韵味悠长。
(2)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诗句描写黎明时分诗人沿溪而行所见的景色。山岩之下,云雾涌动开合;花瓣上露珠晶莹,滚动欲滴。首先说自然之理:黎明的山间,太阳还没有出来,云雾较多,时开时散。浓浓的雾气容易结为露珠,露珠多了,就会滚动滴落。其中,“方”字、“犹”字用得传神。“方”是方才,云雾方才合拢,说明云雾起初是散开的状态,这样就描画了一幅云雾开合涌动的图景。再者,诗句中只出现了“合”的动作,“开”的动作需要你用联想去补充,形成云雾涌动的想象效果。“犹”是仍然,花瓣上的露珠仍然在滴落,说明雾气之重,露珠之多。这两个字的运用,不仅使画面具有立体感,还暗示了时间的长度,更接近自然的真实。这两个字的运用,诚可谓巧矣!
大自然生生不息,变化无端。按照佛家的观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佛的化身。“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山水景物表象为“色”,空幻而灵动。这种自然,也是蕴含了作者佛家观念的自然。面对这景物,作者的情感是由欣赏而生的淡淡的喜悦和轻松的心情。作者说:“情用赏为美。”(《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又说:“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同上)两句之中,融合了作者的自然之理、佛家之意、喜悦之情。
(3)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
诗句描写了作者游南亭时傍晚所见的景色。大雨过后,稠密的山林中清凉怡人;红日西坠,远远的山峰遮住了半个太阳。作为自然之理,雨后本该清凉,此不必说。关键是清凉存在的状态,作者用一个“含”字把这种状态表现无遗。雨后的清气,视之不见,即之可感,弥漫在密林之间,一个“含”字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这种状态。作者巧用这一字,达到了妙造自然的效果。
作者所描绘的山林落日图是一幅立体的图景。“密林”乃是近景,与远峰对比就可以想见。“余清”是触觉描写,更暗示了“密林”之近。落日为远景,作为衬托的远峰,可谓中景。这样,近景密林、中景远峰、远景落日构成了一幅立体的雨后山林落日图。作者用巧妙的构图,力求追摹自然之真,若非得自然之神理,何以至此?
至于作者的情感意趣,只能结合全篇来看。作者感慨时光匆匆、老年将至,流露出决心归隐的情绪。这两句的景物描写,清冷的山林恰似作者落寞的心情,半隐的落日更会勾起伤逝的情怀。
谢灵运巧妙地把自然之理、个人的情感意趣融入景物描写之中。在构思过程中,作者可能没有这么细致的理论思考,但他强调的是“匠心独造”、“钩深极微”,尽量让诗句符合心中的自然,无论是冥思苦想,还是妙手偶得,最终的目的是心中的神理意趣“猝然与景相遇”(叶梦得《石林诗话》),也就是刘勰所谓“契机者入巧”(《文心雕龙·丽辞》),这样就达到了创作中的大巧。
二 “似”,即形似,指刻画方面,极貌写物,穷形尽相,力夺造化之功,臻神似之境
刘宋时期,“情必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成为创作风气。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谢灵运笔下的山水景物追求形似。但不是一般的形似,而是极貌写物、穷形尽相,追求自然主义的细节的真实。同时,他又高出自然主义,蕴含着玄学的“真意”。这样,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就不是徒具其表的无生命的“山水”,而是蕴含自然真意,具有生命活力的“真”山水。
细节的真实首先包括水流、山石、花草等事物的形状的如实描写,往往一字传神。如:“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登江中孤屿》)一个“乱”字,描画出水流的形状。江宽流急,虽没有浪花飞溅,但急流激起的水波呈混乱的流线状,如一幅工笔画,细微传神之处如在目前。一个“媚”字,把孤屿写活了。我们似乎看到孤屿有了生命,在江流中呈现娇媚的风姿。传统的中国文论认为这种手法叫做移情;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任何形式都具有表现性;而在谢灵运看来,或许是山水在以形媚道,传达着难以言传的真意。再如:“白芷竞新苕,绿蘋齐初叶。”(《登上戍石鼓山》)从状物的角度讲,“绿蘋齐初叶”五个字之中,就有三个字在状物。“绿”描写水草的颜色,“齐”描写水草叶子的形状,“初”代表叶子刚刚抽出,是嫩叶。真是穷形尽相,极力巧构形似之言。不过,能够传达景物神韵的还是第一句,描写白芷和新发芽的芦苇竞相生长,一个“竞”字,烘托出水草蓬勃的生机。他描画的不是一幅画,而是真正的自然。
谢灵运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其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绘画观念的影响,明代谢榛评论道:“谢灵运‘池塘生春草’,造语天然,清景可画,有声有色,乃是六朝家数,与夫‘青青河畔草’不同。”[6]46因此,在他的诗里非常注意色彩、光线、色调以及绘画技法的运用。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中,有“白日”、“绿柳”、“红桃”等意象。在《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一诗中,有“碧涧”、“红泉”等意象。如果把谢灵运的诗歌比作一幅画的话,它不是素雅的水墨画,而是秾丽的水粉画,着色鲜明的意象为他的诗歌增添了斑斓的色彩。至于光线的运用,也不乏其例。如他的《过瞿溪山饭僧》,作者起首写道:“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交代了诗人的游踪:早晨,诗人迎着初升的太阳,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又在流水朝阳的辉映中,来到小溪的岸边。诗人的行踪笼罩在流水朝阳的辉映中,给人的感觉明媚而神圣。他的另一首《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描写了傍晚的暮色:“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由于林密壑深,到了傍晚,山间光线暗淡了下来;晚霞也变得模糊起来。高明的画家为了表现微妙繁复的自然,不仅注意光线的运用,还要注意色调的运用。如:“青翠杳深沉”(《晚出西射堂》)、“夕曛岚气阴”(同上),运用的是暗色调;“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运用的是明色调。说到绘画技法运用方面,首先要知道谢灵运本身就是画家,在当时画坛占有一席之地。就当时绘画技巧来讲,已经注意到了构图的层次和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宗炳《画山水序》曰:“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谢灵运把这种绘画的手法也运用到了诗歌的构图中了,如前所述,诗句“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诗中有画,就运用了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另外如:“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七里濑》)“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过白岸亭》)都是远景与近景对举。他的《登江中孤屿》也是先描绘了近景“乱流”和“孤屿”,然后再描写空水一色、云日辉映的远景作为背景,这样就出现了绘画的立体效果。
谢灵运不仅注重字词的锤炼,力求一字传神,把山水景物的形象,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还把绘画的技法运用于诗歌创作,注意色彩、光线、色调等技法的运用。我们知道,诗歌是一种艺术,不是自然,但是,谢灵运调动一切表现手法,追摹自然。从他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诗句确实达到了形神兼备、接近自然的境界。为了追求“巧似”,谢灵运殚精竭思、苦苦心摹神会,宋朝的张镃说他“炉锤之功不遗余力”,[7]616(《诗学规范》)刘克庄说他“一字百炼乃出冶”,[8]481(《江西诗派小序》)足见其用功之深。《诗品》转引《谢氏家录》说:“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1]14也说明他诗中妙句来自于苦苦思索后的灵感闪现,并非全凭才气率意而为。
当然,谢灵运的山水诗并非大部分达到了“自然”之境界,历代诗评家所称道的诗句也屈指可数,他的很多诗句也有艰深晦涩、生造词语之弊。由此可见,力求“巧似”是谢灵运山水景物描写努力的方向,为数不多的句子达到了“自然”之境界。少数如“初发芙蓉”的诗句并非一味妙悟而得,也并非“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而是在千锤百炼的基础上,穷力追新、力求“巧似”,“巧似”之极,便达到了“自然”之境界。
收稿日期:2008-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