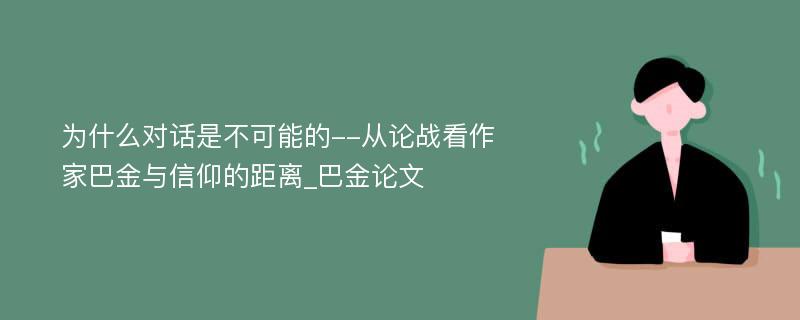
对话何以不可能——从一场论战看作家巴金与信仰的距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能论文,论战论文,巴金论文,距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8-0107-09
上篇 论战的详述
巴金研究中,对巴金和英国神甫赖诒恩①的辩论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缺。主要是因为赖诒恩在论战中发表的文章没有被整理出来公开发表。就已有的资料来看,这场论战始于1943年底,展开于桂林《广西日报》的副刊“漓水”②。巴金晚年回忆说:“赖诒恩是广西桂林礼拜堂的神父,从香港来的,英国人。他在礼拜堂放些唱片,搞些文化宣传活动,很多人捧他。(笑)我给他抬杠。”③根据当时采访巴金的李存光回忆,这场辩论“除了分清是非因而要予以批驳外,实际还有所指,即间接批评林语堂”④。当时的情景是,林语堂1943年秋回国,发表许多演说,提倡心理建设,力主和平哲学。在《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说中,林说:“自信心不立,就是没有心理建设,没有心理建设,物质的建设,便感困难。”此文发表后,郭沫若、田汉等相继撰文驳难。巴金虽未驳斥,但就在此时,他读到了赖神甫的论文《在西方的山巅上》,文中引用林语堂的观点。林氏问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特别关心提高世界生活标准,而忽略了提高道德标准呢?巴金读完得出结论说:赖神甫同林语堂一样,都主张提高道德标准,反对提高生活标准。故此撰文批判,赖诒恩提笔反诘,论战就此展开。
第一回合:亟待提高的是道德标准还是生活标准?
巴金在1943年12月17、18日发表《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他说:赖神甫同林语堂一样,都主张提高道德标准,反对提高生活标准。巴金认为“提高道德标准”是统治阶级和帮闲阶级最喜欢讲的,平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呼吁,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没多大用处,是因为他们对“道德”并不理解。巴金质疑:我们的道德标准在什么时候降低了呢?现在的标准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呢?巴金认为神甫只谈道德的堕落,而对道德生活为何降低没有说明。巴金说:“道德的堕落便是从大多数人生活标准的降低这一事实来的。”救济的唯一方法正是提高生活标准。
然后,巴金从近代功利论、直观派哲学家和进化论这三派来介绍研究道德的学问——伦理学。巴金称自己相信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道德学说。具体来说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这五点。巴金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是建立在功利的“天国”这种“酬劳的允许”之上的。他提出了以下质疑:“为什么要有‘地狱’的威吓呢?单是‘爱的福音’不能改造世界吗?在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大部分西方国家中,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赖神甫所说的‘堕落现象’?为什么基督教的两大基本原理‘平等’和‘对于危害的宽恕’,会被中世纪教会所反对,为什么到现在它们在一般信奉者中间会成为具文?为什么这个入神,这个伟大的道德教师的‘山上垂训’常常会被忘记,而单是仪式神话,天国的传说,却普遍地存在着呢?”接下来,巴金声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道德标准并未降低过,面对战火中的苦难,“撇开大多数人的幸福和痛苦来谈道德,等于抓起一具枯骨来硬给他装上一个灵魂!”最后,巴金用抗战中的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向这位英国神甫提出了质疑。
几天后的12月23日,赖诒恩发表《走向较好的世界——赖诒恩神甫答巴金先生》,回应说他和巴金相左的地方只是在于他们对“生活程度”和“道德标准”理解的不同。赖诒恩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从来没听到过任何道德哲学的人都在渴望人变得更好。“今日世界上这些东西(更诚实、更公正、更爱真理)的需要改善,在我看来殊无证明的必要。他同意说对饥饿线上的人民只谈道德是一件残酷而无用的行为,但这对比较道德和生活标准哪个更重要并没有关系。即使巴金所说的“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都达到,人类仍需提高道德标准;但相反地“假如公正和人道被实行而凶暴与贪婪被消灭了之后,则提高生活程度一类的话也不需要再谈了”。赖认为阻挠人类幸福的不是财产、机会、机器或资源的缺劣,而是缺少“善意的增加”。
接着,赖诒恩说他和巴金都同样悲痛地感到人类的苦难,但是改变的根本方法仍在于“人类本身有更大的善意”。“我们现在正计划着消弭战争,……祛除贫乏,和实现世界和平——所有同样的计划以前都失败了,我们能如此乐观,希望现在可以成就这些东西吗?惟有人类比以前更愿意做完成这些东西所必要的牺牲,这目的始能达到。现在,人类或各国是否有做这些牺牲的迹象呢?……就我个人来说,我看不见这种迹象的丝毫。但是因为一切都以它为依据,所以我期待道德标准的提高比期待任何旁的东西更逼切。唯有这才能使这种迹象有望。”因此,他谈到提高道德标准的方法,“唯有通过宗教始有可能”。
第二回合:道德还是财富,何者更好?
对此,巴金在12月26、27日发表《什么是较好的世界》回应:“赖诒恩神甫的答复很使我失望。”巴金着眼于当下的苦难,认为赖诒恩的观点没有爱和同情,“只有约旦河施洗者的威吓和警告,这甚至还与耶稣的教训与行为相反,耶稣实际上是一个最有人性的人神。基督教在罗马势力的摧残下能够发展,就全靠了这一点人性”。巴金借此阐述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当时是以反抗富人堕落之贫民的新宗教这个姿态出现的。它提倡对受压迫的牺牲者之爱来代替对一个复仇上帝之恐惧和对体现自然界恶势力的人格化的神之恐惧。它的道德教师不是一个复仇的神,不是一个僧侣,也不是一个知识阶级的思想家,他只是一个平民,一个简单的木匠,它的最初的信从者里面并没有罗马人。”
对于什么是较好的世界,巴金又回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对于如何走向较好的世界,巴金拒绝了宗教:“宗教能给人以心灵的慰安,却不能满足人的饥饿。”对于赖诒恩的唯一方法——“人类本身有更大的善意”,巴金认为“单是好意不能完成什么事情,犹如单是善心绝不能治人重病”。之后,巴金以宗教裁判所为例子对“撇弃了爱,撇弃了人民的幸福来谈宗教”进行了鞭挞。文末,巴金用耶稣的话对赖诒恩提出了警告:“‘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是仁爱的主的声音,也正是对他的仆人们说的。或者准备跟他走进天国,或者离开他去吧——在宗教的仆人面前,再没有第三条路。”
赖诒恩大概意识到巴金误读了自己所谓的“生活标准”和“道德标准”,所以在31日发表的《何者较好?财富抑廉耻心》中,将两者转化为“财富”和“廉耻心”。他对巴金将自己的观点从“提高道德标准更为重要”理解成了“反对提高生活标准”表示抗议:“我所关怀的,只是相对的价值问题。”赖说巴金企图把这个单纯的问题转化成一个“普罗阶级的争论点”是没有用的。“说他们(沦陷区)必须先达到一个较好的生活标准,然后他们才能顾虑到道德标准,好像二者是互相摈斥似的,这未免有点荒谬了。假如沦陷区内的人民完全不顾及道德价值,他们大可以做汉奸以改善其生活状况。巴金先生是不是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呢?我深信他决不会如此想。所以他不应该说他们在生活状况未获得改善之前可以暂时不顾及道德的问题。”对巴金所提出一系列问题,赖说它们离题太远,他不想作答。
第三回合:生活的改善能带来道德的提高吗?
1944年1月6日,巴金发表《关于道德与生活问题的一封信——致〈广西日报·漓水〉编者》,再次主张应该“先”是人民的衣食教育达到一个高的标准,再谈道德标准。因为在战争中生活标准实在降得太低了,而道德标准并未降低过。对一般人来说他们一生连梦也梦不到财富,却有了够多的廉耻心。巴金声明“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就说过,就‘大多数人’而论,则我们的道德标准现在并没有降低,用不着提高。只是生活标准降得太低了,提高的需要倒是很迫切的。赖神甫倘使不回答这两句话,则他对我的一切答复都是‘离题太远’”。
面对许多读者的参与,赖诒恩在1月31日、2月1日、2月2日连续发表长文《两个标准》详细回答了巴金的六个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并未降低,为何要提高?提高到怎样程度?”赖认为虽然道德学说和理论没有降低,但道德实践降低了,而提高的方法就是让大部分人的生活更能履行道德原则。对第二、三、五个问题“为何反对提高生活标准”?赖诒恩重申他没有反对过这个,他反对的是将提高生活标准作为提高道德标准的方法。对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撇开了道德本身,而谈道德标准”?赖认为道德就是上帝自己(即善本身)。在上帝以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道德都只是一种不完美的“特殊的善”。第六个问题,即对基督教会的质疑,赖认为假如基督徒当中有不实行基督教义的现象,那是因为教诲和实践之间的差异。
之后,赖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道德标准是否有改善之必要?第二,假如有,这改善可能由提高生活标准而达到吗?第三,假如人人有了生活的满足,那他们是否都会过着道德的生活?之后他自己作答:首先,道德标准当然要改善。其次,他举了贫民窟、毫无道德的上层阶级、历史上许多为提高人们生活的革命的失败来说明此假设的可笑。再次,神甫以贫穷举例:贫穷的起源不是财富的偶然,而是贪婪和自私。人所做出的立法和社会革命的补救是暂时而不完全的,除非它的原动力是极大的善意。“我们确应把粮食运给沦陷区的饥饿民众……但除非世界的道德标准是被提高了,否则战争会再将临,使他们的命运比以前还坏。世界上的道德标准假如有了最后的改善,也会减少了无辜的人民以痛苦的新战争的危害。这好像在疟疾流行期中治疗民众一样。给他们以药是必要的。但根本上尤其重要的是采用预防的办法。两件事在实际上都是必需的,但基本上却有轻重之分。改善道德标准就等于对社会施用预防办法。它和提高生活标准的努力是同时进行的,但根本上比它重要。”
最后,赖神甫批评了那种认为国家这个公共机器将消灭贫乏甚至取代道德的理论,并提出自己对道德的看法:“德性不是一件暂时的,不是一件在科学秩序的新世界上没有地位的东西。没有它,这些动人的梦想甚至不能局部实现。人不是机器,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作统一磨具制造出来的东西:他们不会自动地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和愿望。他们是有个人的愿望和私欲的动物,而这些愿望和私欲时要用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它控制的。……因为对于公共利益的类似的梦想,在过去常常被毁于个人自私心的礁石上。这些梦想……唯有在人类的道德标准已经提高了之后才会这样做。”论及提高道德标准的方法,“我只能指出经验,它显示了没有宗教,德性是不能长久旺盛的”。
对于赖认为辩论的出发点只是对那些不满于东方生活标准的人,巴金在2月24、25、26、27日发表《读〈两个标准〉》表示反对:“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声明我们谈生活标准、谈道德标准,都是就大多数人立论的。”
针对赖神甫为证明道德标准的低落而列举的私生活上不诚实、傲慢与残忍的增加、家庭生活的堕落等现象,巴金认为他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把少数人的行为来代表多数人;第二,没有解释“个人的自私心”的来源;第三,无立论的根据,没有用事实或理论来证明他的“信仰”。对于赖提出的“自私心”,巴金列举了动物界、野蛮人、现代人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种种事实,证明达尔文的观点:道德意识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本能。
赖认为本次辩论只是一个有关相对价值的“单纯的问题”,故视巴金的教会堕落、宗教裁判所等问题为超出范围。巴金反对说:“道德是不变的,它的教条,它的标准却常常因时代、地域或种族而改变。……赖神甫以为我同他辩论的只是‘两个标准的孰高孰低’,其实,我所争的却是这一点:道德并非脱离人类生活而单独存在的。人没有‘为道德而遵守道德’的义务。道德是为了帮助人类谋幸福,求发达与繁荣而存在的。人类的完满的生活便是道德的目标。”巴金再次解释他所谓的“生活”这个名词也包含着精神的部分。生活标准的意义就是:“每个家庭能够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因为赖曾根据以上的话得出结论说:“巴金先生的论点是:‘道德就是以善为目的意向;万塞提所建议的目的是善,所以善的目的构成道德:因此我们不需谈道德,只求达到这个目的便可。’”巴金强烈反对:“我引凡宰特的话不过用它比较具体地解释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我素来就不高兴用‘善’这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个字太抽象了。一般人都把合于道德的行为叫做‘善’,要是不先把道德这个东西弄清楚,只说道德的目的是‘善’,岂不是等于没有说!……”而赖诒恩为了避免“公开传教”之嫌的论说方式也让巴金觉得:“东拉西扯,左弯右拐,叫人抓不住他的中心点。”最后,巴金断言赖诒恩的基本论点就是传教。一谈到宗教,巴金又回到了宗教裁判所:“赖神甫难道能够说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不是虔诚的信教者?黑暗时期的教会领袖不是‘宗教的仆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提高道德标准,反而接连制造残杀拷打的惨剧?我相信神甫回答不出这个‘为什么’的。因为那原因正是我在第六个问题中所指出的:撇开了人民的幸福来谈宗教。结果呢?结果——不是毫无用处,便是回到宗教裁判所去!甚至赖神甫也不能够抹煞历史的教训。”
参战者的观点以及巴金之后对辩论的补充
这场论战除巴、赖二人之外,参战者众多。作者们见仁见智,支持巴金的为大多数。《救亡日报》记者何家英直接将靶子对准林语堂:“林博士久居美国,丰衣足食,他哪里知道祖国大多数人生活究竟如何?……在可能的条件下去要求战时的合理的生活标准的提高,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道德不过的行为。”⑤吕之陈以统计数字上犯罪的增加为理由对赖表示理解⑥,但立刻遭到了唐德鉴的强烈反驳,唐以为吕之陈等类支持赖诒恩的人“把人类历史的演化之看作一两个人的事情,而不能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看出它的起因,这是一般人的毛病。离开了事实的本质,而只抓住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已为立论之根源”⑦。
许多作者表示出对论战所囿的狭窄圈子的质疑:“希望大家不要老困在什么标准与什么标准的圈子里,而应讨论一下循什么道路去达到这个。”⑧参战者提出辩论应该有着比较切实的题材以及具体的内容,他们希望论战能够深入下去,并提出了应改进的方面。
《读〈两个标准〉》发表后,赖诒恩沉默了。巴金在不久后写的《怎样做人及其他》中,继续批评赖诒恩:“这位天主教的神甫关在教堂里制造人性,可是事实上他却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然而要是他放下《圣经》,走出他的圈子……他便知道,不但人,便是动物也是有道德的。”“至于人的自私与贪欲,社会的不满,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它们并非起源于个人的自私心。”
下篇 巴金和基督教的距离
“启蒙”的姿态
一直以来巴金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概念化的。但是抗战中,他与基督徒编辑林憾庐⑨与邻相伴,林憾庐那其乐融融的家庭、谦卑乐观的品格,无不吸引着巴金。以至于巴金尝试创作一部小说(即《火》第三部)来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⑩也在这部小说里,巴金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洋溢着爱的美满家庭。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对基督信仰新的认识基础上巴金和赖诒恩之间能有更深入的对话,但是辩论中双方却认为对方一直在误会自己,背离了自己的原意,甚至离开本题。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辩论流于表面、字据和争吵,却无法碰触到巴金思想或基督教思想中的精髓?当我们细读论战文本时,就会发现巴金始终采取一种激昂犀利的、战斗性的、毋庸质疑的语调。他常说自己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说话。显然,他将神甫摆在一个“外国人”的立场,又将其和林语堂一道摆在御用文人的位子上。巴金强大的论述使得辩论无法对话,神甫多次说巴金这样的态度只能夸大他们的不同,而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辩论更像是一场学说秀,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巴金早期论文中的概念和学说。那真正接近于生命本源的矛盾、思索和追问都看不到的。巴金穿上无政府主义的“铠甲”代表中国大众斗志昂扬地站在读者面前,这种态度体现了“五四”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从而使这场辩论充满了理论和激情而缺少了理解和对话。甚至当时关注辩论的读者也撰文提出辩论的收获便是“那么贫弱的一点点”。(11)
在以林憾庐为原型的《火》(第三部)中,主人翁田惠世的信仰多次受到“试探”,这是他受试探的一个心理片断:“‘为什么经过了一千九百多年人们还不能好好地生活呢?一个声音在他心里问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主?’他抬起头望天,找不到一个回答……在他脑子里便渐渐地浮现了贫穷、残杀、痛苦的景象,他仿佛落进了罪恶的海里……他不禁绝望地低声对着天嚷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不难发现这些“试探”与巴金在辩论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如出一辙,显然巴金把自己对基督信仰的观念投射进了田惠世的精神世界,不知不觉中田惠世渐渐重建出一套离彼岸世界越来越远的“主的教义”:“牺牲代替谦卑、伪善的说教,用爱拯救世界,使慈悲与爱怜不致成为空话,信仰不致成为装饰……”当情节发展到苦难来临,这样的“试探”完全战胜了田惠世,他在儿子死去时说:“主啊,为什么要流这些血?为什么不放过这个天真的孩子?难道这是公平?难道这是你的旨意?……主啊,你给万物以生命,你创造光明和福佑。可是为什么让暴力在我们这里散布痛苦和死亡?仁慈的主啊,请你垂听你仆人呼求的声音。……我们并没有罪。……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惩罚呢?……我没有罪……”至此,巴金那套进化论的“上帝观”已经淹没了田惠世,死前他发出和巴金笔下许多非宗教者一样的叹息:“还我的儿子来!”(12)
同样的一个丧子的主题,我们可以回到鲁迅的笔下。《祝福》中“祥林嫂”丧子后的精神世界聚焦在她问“我”的三个问题上: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我”这样回答前两个问题:“也许有罢,——我想。”“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当第三个问题被牵出来时我说,“‘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笔者之所以摘选这个片段,一是可以比较鲁迅和巴金在处理主人公因丧子之痛而追问到终极世界时的写作方法;二是已有评论者发现了祥林嫂发问中基督教的“幽灵幻影”。(13)如果说田惠世投射了巴金自己的话;祥林嫂同样也正是代表着那个,“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14)。当作者鲁迅以启蒙者的目光审量着祥林嫂的追问时,他就以小说中的“我”予以反应。有趣的是面对祥林嫂,一个如此需要“启蒙”的精神求乞者,“我”的态度竟是“说不清”。恰恰就是这“说不清”所隐含的自我斥责、怨怼、毁弃而又不甘于此的生命状态把读者的导航针拨动到了彼岸世界。
同样的主题,在巴金的小说《还魂草》中,小女孩面对着姐姐的死亡,她唯一的希望在于能栽种出“我”曾告诉她的还魂草。但是“我”却毫不客气地粉碎了小女孩复活的梦:“利莎,我说的是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想了。”“我”那启蒙者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话语几乎是带给了小女孩心灵的毁灭。小女孩说:“我晓得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同我在一起,今天就在这席子地下……”(15)
从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辩论还是作品,巴金对彼岸世界触及之限度,是跟他的写作手法有关的:“巴金总是一个主观的、全知的评论者。他力图指导读者的思想。他很少运用这样一些老练圆熟的技巧如含蓄、或旁敲侧击的手法、讽刺或模棱两可的花招,或是以叙述为表掩其真意。……即使当他广泛地采用和意识流密切相关的倒叙手法时,他仍然不能抑制自己不作一个无所不晓的作家。”(16)巴金对于宗教,有一套根植于进化论的严密体系。他继承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宗教观,也受到“五四”对宗教批判的深刻影响。启蒙的姿态和澎湃的感情使得巴金在创作过程中常常禁不住要跳出来或者挤进去说话,他一边慷慨地回答着主人公对终极世界的所有疑问,一边创造出故事情节来证明自己观念的正确。巴金自己也说:“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林憾庐)的说教……可是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17)陈思和在《巴金传》中曾如此描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代一下子把他们抛出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轨道,把他们抛到思想的旷野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使他们本能地为这种独立思想和独立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沮丧……他们拼命地寻找,去寻找那些可以代替自己独立地承担责任的思想——某种现成的集体原则,以便把自己依附于其中。”(18)但是,当巴金将这些原则和学说“启蒙”进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说《火》这部作品是失败了。同样在辩论中,巴金再一次温习克鲁泡特金的道德学说,再一次将自己依附于无政府主义道德观。他对于赖诒恩所作的那些激烈的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启蒙的姿态,甚至还可看作他在爱国主义激情的刺激下时,特意选定的一种表述方式。
宗教裁判所与凡宰特事件
这场辩论里,巴金引用了法国小说家尤敬·西德小说《巴黎的神秘》中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责备基督对人们过于仁慈的情节;还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中类似的场面。他列举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将其作为攻击赖诒恩的一个证据。尽管,赖诒恩神甫多次解释说宗教界内部少数人的错误不能代表整个基督信仰,但是这个解释似乎对巴金没什么作用。几回合辩论的最后,巴金这样结尾:“撇开了人民的幸福来谈宗教。结果呢?结果——不是毫无用处,便是回到宗教裁判所去!”在小说《火》中,文淑和田惠世的辩论,也是一旦涉及宗教裁判所,就不要再辩论下去了。在其他论及基督教的文章中,宗教裁判所多次被提及并且成为巴金和基督信仰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和不能言说的禁区。巴金研究者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单单将宗教裁判所当作攻击基督信仰的力证,似乎并不是公正全面的态度。既然20年代“非基运动”中那种将基督教义和违背基督教训的教会分开对待的态度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为什么在巴金的笔下,这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19)
要解开这个疑问,不能不回到“凡宰特萨珂事件”。凡宰特和萨珂本是两个旅美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4月15日,美国麻省发生抢劫杀人案,政府逮捕了无辜的他们并作出杀人罪的判决。之后整个欧美的工人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救援活动,但是二人还是于1927年8月23日被烧死在电椅上。凡宰特(Vanzetti)在巴金的生命中扮演着启蒙老师的角色,当凡宰特受害时,无法遏制的愤怒激起了巴金的热情,促使他走上文学道路。一生之久,深扎在巴金身上的凡宰特的梦没有改变——“我希望每个家庭能够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20)这段话是巴金早年在巴黎邂逅凡宰特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的生活》(也译作《我的生活的故事》)时,牢牢抓住他的心的段落,这场辩论中,这段话被巴金用来描述什么是“提高了的生活标准”,几乎在每篇论战文章中出现。
了解凡宰特萨珂事件,我们会发现此类“冤杀无辜”的强权制度的确和中世纪冤杀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有相似之处。有意识地,或是潜意识地,巴金把不公正的执法机关和宗教裁判所等同起来。所以,在以此为主题的小说《电椅》和《我的眼泪》中,巴金才写到:“电椅同牧师连接在一起,这就是基督教的文明吧。”(21)“好一个希望的刑罚(电椅),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采用的差不多。”(22)巴金是如此深刻地把自己和凡宰特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以至于“电椅事件”成为他自己灵魂的一个分水岭,羞耻和愤怒也深深埋在了巴金的心中。从起初他就持定了一个不饶恕、不对话的态度:“我有一个先生,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23)可以说当论战中“宗教裁判所”映入巴金眼帘时,他那种不可思议的固执和激愤使得辩论无法对话。
凡宰特描写自己精神生活的话曾给巴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巴金也曾描述自己说:“不过我走进沪县的街市,仍然只是这个轻松的身子,我的两手并不曾沾过一滴别人的血。”(24)这一种对自我人格完善的绝对自信使他不但拒绝基督教对原罪和救赎的解释,也拒绝由此而来的无条件的忍从和爱。小说《爱的十字架》中,主人公面对具有无限牺牲之爱的妻子一家时,选择了逃避:他宁可在无限的负罪感中沉沦至死也不接受这样的饶恕和拯救。也许真和鲁迅的感受相同,巴金觉得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爱和忍从是没有牢固根基的。(25)巴金笔下的爱,追本溯源仍本于他在辩论中所再三申述的——进化论基础上的道德:“为了保身和传种。”
随着时代的变迁,“巴金发现了人的不完善,同时又隐约感到了这不完善背后的巨大历史原因,看到了五四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在中国的现实命运。这深化了他的悲剧感受,把他的悲哀引向深远”(26)。巴金说:“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是要人类普遍地感到悲哀。感到着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显然,这可以被消灭的“悲哀的来源”不是基督教义所谓的“原罪”,巴金将这悲哀归咎为社会制度,或是制度在人心中的内化(比如“高老太爷的鬼魂”,“觉新性格”,“封建”(27)等)。以此为出发点,他反省自己在红卫兵的皮带之下“自报罪行”“认罪服罪”的本质,他思索“文革中是什么让人一下子变成了兽”?却不承认人有与生俱来的兽性或罪性;他用“信神”分析“文革”中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强调因为信“神”,人放弃了做人的权利,才造就了兽。当批判聚焦于“非人”的制度时(例如宗教裁判所或“文革”),受害者自身的局限和软弱就退居其次了:死者因着勇敢的死获得“重生”;无论是俄国的虚无党人还是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李大钊,都会因“死得其所”而被巴金封为圣徒,死遮掩了一切的罪,个人的问题在巨大的制度错误的面前无足轻重。有研究者认为巴金对罪恶的认识使巴金的作品的真实感打了折扣(28),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使得巴金晚期的忏悔意识存在局限和遗憾(29)。显然,这种思考继承了五四“立人”的价值准则——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将不合理的制度和宗教本质紧密联系起来的思维批判的方式,让他离一切“神本”的宗教越来越远。
对话的可能性
在托尔斯泰笔下,基督信仰和无政府主义融合可以生出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经典人物;为什么在巴金身上无法进行呢?除了前文所论及的巴金的写作方式、启蒙姿态、进化论的思想体系、以及凡宰特事件的独特经历之外,也和巴金身处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土壤有关。“实际上,巴金对于上帝并不感到兴趣,他的理想是:人类至上,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上帝观念,借能满足和鼓励他的宏愿,于是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密封的宇宙之中,而不能奔逸到天上。在他这个密封的宇宙内,既没有灵魂和上帝,那么对人类种种痛苦的棘手问题,便得不到一个圆满的解答。巴金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来,可是他已感觉到解决这问题的困难,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他的心灵上引起了不可疗愈的忧郁与不安。”(30)可以说这种“不可疗愈的忧郁与不安”是产生伟大文学的根源和本质,但是中国现代的启蒙意识形态是由秉承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敌基督”价值的知识分子们构造的,即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不乏信仰的迷惘和渴望,但至少在意识领域,这种迷惘和渴望是不允许存在的,更不允许公诸于众的。这一土壤与西方被基督教熏染过千年的精神土壤完全不同。
似乎有两个巴金。一个启蒙者巴金,另一个是孩童般的巴金:“做小孩的时候在那所空阔的衙门里我也曾跟着母亲拜过神。母亲告诉我,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大公无私的。一对蜡烛,一炷香,对着那一碧无际的天空,我跟着母亲深深磕下头去。向着那明鉴一切的神明,我虔诚地祷告着:我求他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带来和平。我求他让我看见每个人的笑脸,我求他不要使任何人哭泣。然而神似乎不曾听见我的祷告。神的宝座也许是太高,太高了。”(31)当巴金以第一个巴金的姿态出现并且发言时,他刻意地拒绝并且摒弃着孩童般的巴金的梦和疑惑,他站在全能上帝的地位上毫不犹疑地批判:梦,“终究会醒过来”;死,“我不怕……我有信仰”(32);罪恶,“人排除自私是可以办到的……但可以逐步解决。为什么要悲观呢”?(33)那种对自我人格的确信及对未来乐观的精神,带来对彼岸救赎的坚决拒绝。
但在巴金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一类,如高觉新、陈剑云、周如水、汪文宣,还有“将军”的妻子们:他们谦抑地在逼仄的角落里把自己的存在缩到最小,祈祷着,忍耐着,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不问这牺牲是否有意义。这一类懦弱无力,但又不缺少道德的“觉新”们似乎代表着基督人性的这一面。“这使他们像是《圣经》故事中受难的使徒,但这种受难却毫无‘崇高感’,只能供人悲悯。他们是背十字架的人,但他们不是基督,决不会有人在他们头上画出光轮。”(34)巴金对这一类“圣徒”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恶他们如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懦弱,另一方面他却发现自己身上有他们抹不去的影子。
但当第二个巴金在黑夜里思索时,他特别多地触及“死”和“梦”的主题,他剥去这些“觉新们”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他与这些罪人一同苦恼,又一同破裂和忍从着。有意或无意地,巴金会透露出自己毕竟不是造物主也不是救赎主的谦卑,透露出他对基督神性向往又抵触、迫切又胆怯的矛盾心态。他引用耶稣的宣告,同时也无奈地叹喟着自己毕竟不能如此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但是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35)这些不多的、隐藏在巴金作品角落里的叹喟和渴望或许才是最接近于文学和基督教在本源上的共鸣之处的——向表现人的内心经验挺进。
注释:
①赖诒恩(Thomas F.Ryan S.J.,1890-1971):英国人,耶稣会神甫,长期在香港从事教会工作,香港沦陷后他来到桂林,曾在西南商业专科学校任教。著作有:《耶稣会士在中国》、《百年故事:一八五八年至一九五八年宗座外方传教会在香港》、《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时期水深火热中的耶稣会士》、《香港天主教指南》等。
②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第2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③李存光:《巴金访谈录——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他》,见李存光主编:《我心中的巴金》,第1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④李存光:《巴金传》,第24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⑤⑥见《广西日报》“漓水”副刊,1944-03-06,1944-03-05。
⑦见《广西日报》“漓水”副刊,1944-03-13。
⑧见翁实夫在1944年1月8日《广西日报》上发表的《循什么道路》。
⑨林憾庐(1891-1943),牧师林至诚之子,林语堂的三哥。他曾为鲁迅主编的《奔流》撰稿,曾编辑《宇宙风》。1938年10月20日,巴金、萧珊、林憾庐等五人一起逃离广州,在漓江东岸福隆街找到住所,巴金住在林憾庐隔壁,共用一个天井,巴金还借用林家的一个房间作书房。
⑩巴金,《怎样做人及其他》,载《人间世》二卷一期,1944-05-01。
(11)观战者张独冰在1944年2月7日的《广西日报》副刊上撰文说:“如果始终让问题停止在道德标准和生活标准提高的先后顺序上面,也许真要像一切观战的人们相同,觉得有点替自己的长期观战感受委屈。……假如,问题不向一个新的,或者更主要的,有着比较切实的题材以及具体的内容上面发展而止于此,那么,无意的,唯一的争论收获便是那么贫弱的一点点。”他建议:“能够使论争深化地转向和人们的需求更主要和切实的题材以求具体内容的建立。”
(12)以上引文均见巴金:《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3)“所以这样的难题,与其让作为中国新知识精英的鲁迅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如找一个牧师来解答更明白、流畅、坚定与有效。如果是那样的话,祥林嫂的未来会怎样,恐怕就要另作考虑了。然而,牧师的身影终究未曾出现,基督教的‘幽灵幻影’似乎始终若隐若现,然又终篇停留于暗处。”叶隽、黄剑波:《〈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载《思想战线》,2007(1)。
(14)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提到鲁迅的本质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文学的鲁迅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一个矛盾统一”。见[日]竹内好:《鲁迅》,第12页,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15)巴金:《还魂草》,见《巴金选集》,第7卷,第435、43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6)[美]内森·K·茅:《巴金》“结论”,见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资料》(下卷),第35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7)巴金:《〈火〉后记》,第3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8)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9)“五四时期有一个普遍的理解即把基督教中的基督精神与以世俗教会为代表的有违基督精神的做法区分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如20年代‘非基运动’初起之时,陈独秀就主张将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区别对待。冯文淑则常常是把这两者纠缠在一起的,因此,面对田惠世,她的争辩有时是缺乏说服力的。”刘丽霞:《论〈田惠世〉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一点启示》,见陈思和、辜也平主编:《巴金: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0)巴金:《谈〈灭亡〉》,见《巴金选集》,第7卷,第109页。
(21)(22)巴金:《电椅》,见《巴金选集》,第7卷,第135、135页。
(23)巴金:《〈灭亡〉序》,见《巴金全集》,第4卷,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4)巴金:《在沪县》,见《巴金全集》,第13卷,第3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5)鲁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曾说:“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还是虚伪。”见《且介亭杂文二集》,第1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6)赵园:《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见陈思和编著:《解读巴金》,第19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
(27)巴金:《关于〈激流〉》,见《巴金全集》,第20卷,第6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8)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章中写到:“巴金既然拒绝个人意志与罪恶互为因果的看法,因此他小说的真实感就打了折扣。他也写坏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赦免了他们的罪,只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社会制度才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个人。”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9)陈思和指出巴金在《随想录》中的忏悔仍是一种“忏悔的人”的忏悔,并未达到现代层次上“人的忏悔”。他的忏悔仍停留在具体和阶段性的层次上,并未达到人对自身认识范畴局限性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见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第2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0)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162页,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
(31)巴金:《〈神鬼人〉序》,见《神鬼人》,第2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
(32)巴金:《我离开了北平》,见《巴金全集》,第12卷,第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3)巴金:《1986年5月10日致林梅信》,见《巴金全集》,第24卷,第1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4)赵园:《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见陈思和编著:《解读巴金》,第193页。
(35)巴金:《生命》,见《巴金选集》,第7卷,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