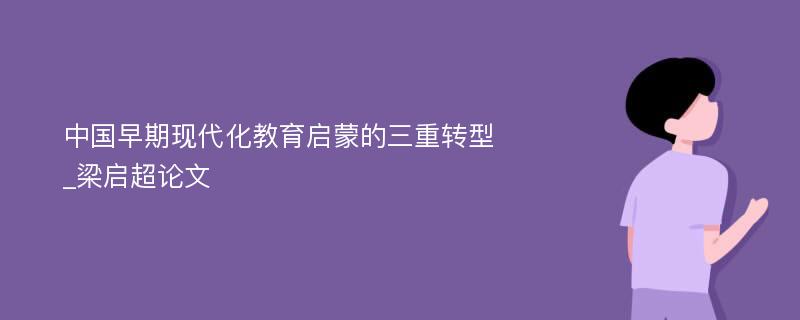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教育启蒙的三重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蒙与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是在启蒙价值观念引导下展开的。现代化是启蒙精神的现实化,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启蒙精神之上的。启蒙精神则是贯穿教育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教育现代化则是启蒙精神展开的过程,也就教育启蒙的过程。那么,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启蒙又呈现一种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一、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中国教育启蒙的路径转换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教育启蒙不是单向度、内生型的启蒙,而是多向度、外生型的启蒙,经历了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的思想历程。近代中国教育启蒙呈现出一种外生型的启蒙路径选择,从技术层面的形式变革到思想层面的观念变革都显现出一种外生型态势。面对积弊丛生、扼杀人性的教育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希望在传统教育框架内整饬学校,通过大兴经世致用之风以恢复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药方只贩古时丹”。①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仅仅在传统内部寻医问药已不能应时务,先觉的知识分子通过“开眼”看到世界的先进,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救国图强。
(一)复兴传统与内部整顿
晚清教育衰败不堪,千疮百孔。士子(学生)整日与空疏无用的训诂考据义理之学为伴,以应付八股考试。这样,广大士子(学生)困于科考,智慧锢于官学,“疲精神耗力于无用之学”,而致使“心术坏而义理固”。“衰世”之“无才”,则是因学校之废、教化不兴。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对人才的禁锢、束缚、杀戮,学校成为屠戮人才、戕残人性的场所;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荒废已久,如“官学积渐废弛”,“教官多混耄”,学风颓败。
面对如此蒙昧的教育现实,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若变世事,需要整饬学校,复兴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一方面,反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轻视考据学的做法,认为它迂腐而无用。”②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承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经世之学,关注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反对空疏之学,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朴学”。正是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晚清政府开始着手对学校进行整顿,整治科场积弊,重整儒学。1837年,道光皇帝在《振兴学校折》的批阅中指出:“着直省督抚学政严加整顿,通饬教官,务当敬教劝学,无负乃职。其不能砥砺士节、扶持名教者,即行严参惩办。至各省书院延请院长,原为激励人才而设,近日竟有荐而不到馆者,有甫经到馆旋取修金以去者,并有不到馆而上司代取修金转付者,殊属有名无实。着直省督抚各体察情形,核实整顿,务使馆无空旷,士有师承,勉副朕崇重实学之意。”③
虽然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整顿官学、崇重实学、敬教劝学,来振兴教育,以“兴贤育才”,但这些措施很快流于表面、疲于应付。无论是在教育形式,还是教学内容方面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崇重实学’、‘认真教督’、‘勿任虚糜’、‘循名责实’等等,只不过是历代封建王朝同类谕旨中俯拾可见的‘习惯术语’。从这个角度来说,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作为传统教育主体的官学和书院,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④
虽然教育在现实层面尚未能取得丝毫突破,但令人欣喜的是,经世致用之风却唤醒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走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尊古守旧的风习,开始“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了思想启蒙的第一步,开始批判反思旧有事物,不再固守传统、盲从盲信,要求变革教育现实。经世致用之风习的渐盛,不仅为教育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先期的思想准备。
(二)质疑传统与吸纳西学
面对危机,基于经世致用的学校振兴计划也已落空、流于形式。中国知识分子慢慢认识到囿于传统框架的教育变革已经不能应付“世事”之亟变。在这个“千古变局”之中,需要有新的突破,才能保种、保国、保教,才能实现现代化。这种“以变促保”的突破首先体现为质疑传统、吸纳西学,建立新式学校。
开明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从“抵制”到“认同”,认识到西技是“奇技”而非“淫巧”,西方列强之所以强于中国则在于其“技术”优势,“彼夷之长技,正乃吾国则短缺”。魏源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⑥这样才能“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⑦正是在开明知识分子的促动下,晚清政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下,开启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自强运动。
在教育方面,新式学校陆续建立。新式学校除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学习格致、算学、化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等现代知识。新式学校与传统学校有着迥异的差别。“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具备了近代学校的某些特点,并为其后的学校沿袭发展。”⑧新式学校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中国教育的血液里自此开始流淌着现代细胞,呈现一种启蒙之开端景象。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从此在中国开始变成现实。
随着思想启蒙的深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深感洋务运动的弊端,而倡言维新,关注制度与思想层面的变革。在短短的一百天里,维新变法把19世纪6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零星的、渐进式的教育改革,推到了顶峰。⑨虽然维新仅百日而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搭起了一个骨架。“它加速了科举制的灭亡,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轨道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⑩晚清之后,伴随着现代启蒙价值观念的传播,蔡元培等师辈们与“五四”“新青年”开始了对“传统礼教”“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的无情批判,积极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等启蒙价值,倡导人性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以“改造国民性”、养成健全人格为主旨。
洋务运动后,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直面现实、反思传统,认识到复兴传统以达至启蒙的艰难,更认识到借鉴西学推动启蒙的必要。在这种“保旧”与“纳新”争论中,中国教育启蒙的路径已经悄然发生转换,从内向型的复兴传统转向外向型的全面借鉴。对西学从排斥到吸纳,从技术层面转向制度、文化、思想层面,从技艺器物的学习到自由、民主、科学观念的引入,中国教育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
二、从中西之争到新旧之别:中国教育启蒙的话语转换
从启蒙的本意上来说,启蒙是人类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不断突破旧有事物的束缚,迈向新的境遇,是一个纵向性的发展过程。由于近代中国教育启蒙在路径选择上呈现出一种外生型态势,所以教育启蒙话语方面就呈现出“中”“西”“新”“旧”之争。在前期主要囿于中西之争的泥淖之中,一方面要求实现“新”“旧”更替,另一方面要求划清“中”“西”之界限,两组话语相互交织于中国教育启蒙的过程之中,往往以“中”“西”之异来否认“新”“旧”之别;到了后期,话语范式才发生转换,从空间上的“中西之争”转换到时间上“新旧之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话语范式。少数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西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古今或新旧关系,力图在新旧框架内,全面学习西方,“兴学校”以“新国民”,“改造国民性”,实现教育启蒙。
(一)“中”“西”话语范式与形式变革
由于传统文化情结根深蒂固,或由于统治阶层的利益驱使,中国知识分子起先仅仅承认“西学”之为“用”,西方科学技术仅仅是“器”而非“道”。“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藐视中华。”(11)“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2)经过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阐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中体西用”的观点逐渐凸显,最终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而成形,并成为早期教育启蒙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范式下,新式学校要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只有这样新式学校所培养之人,才能“中学素有根柢,人品向来端纯,深知宗法圣贤,兼以博览典籍,……均有可用之人”,才能“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背叛之弊”。(13)教育启蒙的出发点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来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局,以维护传统的封建制度,“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
无论是在教育宗旨方面,还是课程安排方面,晚清教育都极力强调“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对“西学”也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中学”在新式学校中占有重要位置,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忠孝节义仍然是学生的立身之本,以“中学”为基,以治身心。在教学内容、课程安排上都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中学”的经史子集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学钟点规定特别多。除大学堂专设经学科及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设有经学大义及群经流源外,中小学堂所占授课时间尤为特别。”(14)
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器物”上的不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西学之才,但并未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思想层面上的不足,仍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正如蒋廷黻分析的那样:“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方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毫无科学机械常识,此处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的,无需学习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15)
在“中西之争”的话语范式下,教育变革主要局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取其之长,补我之短,捍卫皇权。故此,新式学校对西学的学习仅仅停留于器物之用层面,而未深入思想层面。“科举依然举行,八股照样考试,小楷犹是练习,《四书五经》、《孝经》及《圣谕广训》犹必日日诵习。”(16)
(二)“新”“旧”话语范式与观念变革
在“中西之争”的话语范式下,“西学”仅仅是“中学”的补充,其现代启蒙价值并未被充分认识到。新式学校所培养之人,过多关注“西技”方面,较少关注“西政”与“西教”方面,同时在“西技”方面,又过多关注语言文字方面,而对科学技术也只是“粗习皮毛”。(17)
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器物变革层面背后的问题。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社会大众则“漠然无所见”,何以如此?大概的原因则在于前期的教育仅止于器物技艺层面,民智未开。“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于穷理劝学。”(18)“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19)所以,新式教育不仅要在数量上获得发展,还要普遍学习西方,不论西艺还是西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不可。(20)
中国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潮中已经开始跳出“中体西用”的话语范式,大力提倡教育变革,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新民德。“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1)“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2)“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3)“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专论有《学校》、《科举》、《学会》、《师范学校》、《幼学》、《女学》、《译书》等篇章。
学习西方不能仅仅立足于“器物技艺”,不能囿于“中体西用”的话语范式,“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西政与西艺,“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24)
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中国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对西方的认识由误解、恐惧、排斥到借鉴学习,经历了从视西方为“夷”到承认其“新”的认识过程。如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9世纪——引者注)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而在90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的含有赞许的意思。”(25)
这种话语范式变化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中”“西”“新”“旧”的关系,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近现代历史则揭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一定的地域性差异,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26)中国教育启蒙在话语范式上从“中西之争”转化为“新旧之别”,教育启蒙也正是在“中西之争”中逐渐实现了“新旧更替”。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走向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的大趋势。若还持有二元对立的割裂观念,沉迷于“中西之争”的话语之中,争论孰优孰劣,现代化历程中的教育启蒙也是难以展开的。
三、从救亡造材到启蒙立人: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转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教育启蒙不仅在路径选择上、话语范式上实现了转换,还实现了一种从救亡造材到启蒙立人的主题转换。(27)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兴学校”以“育人才”,但所育之“人才”在不同历史阶段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一种从器物技艺层面上救亡造材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启蒙立人的主题转换。前期主要着眼于人的工具性价值,人仅仅被理解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教育仅仅培养救亡所需之“材”,以应救亡之需,而未认识到觉醒国民思想的重要价值;而后期则着眼于人的本体性价值层面,把人理解为自足性的目的,教育则要唤醒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以期启蒙立人,而后自强。
(一)关注人的工具价值与救亡造材
面对救亡时局,中国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西方科技并非“奇技淫巧”,开始认识到西方强,强自“西学”。林则徐、魏源、郑观应等先觉者认识到不能一味的固守传统,闭目塞听,而需向西方学习,采西学。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逻辑:如欲富强,则需制洋器;若制洋器,则需采西学;若采西学,则需兴学校;所兴学校,需以中学为基,西学为辅。
在这种教育逻辑下,人仅仅是一个保种保教的材料,教育仅仅是强国富民的工具,教育变革首先关注人的工具性价值——救亡之材料。这样,所兴学校以培养各种制器之人才为直接目标,以应洋务之需,富民强国;所育人才也着眼于人的器物技艺之层面,仅仅为救亡之“材”料,存在着明显的工具性倾向,并没有充分关注到人的思想观念层面。遵循这样一种工具性目的,新式学校虽然在课程设置上凸显出“西学”特色,但仅限于“器物技艺”层面,“中学”仍是立身之本,纲常伦理仍是教育的基础,“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可见,新式教育主要局限在器物层面,而未深入关注到人的本身,人的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只是“材”,变法之“材”、强国之“器”。洋务教育倡导的不是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落脚点是“救亡”,是封建统治的延续。
纵观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戊戌维新的“穷理劝学”,还是清末新政的“废科举、兴学校”,都仅仅围绕着“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救亡”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主题词,近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也是起因于民族救亡的需要,救亡也是“采西学”、“兴学校”的目的。
在这种价值观念下,近代中国教育开始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新式学校蓬勃兴起。这些学校虽然培养了一批具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之“材”,通晓外国语言,浅识科学技术,但这些所造之“材”的精神世界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圣贤经典”之中,价值观念仍囿于忠君尊孔,崇古媚上,并未实现真正觉醒。
(二)关注人的本体价值与启蒙立人
“传统忠孝”之体,焉有“现代科技”之用?国民若未得到一场精神洗礼,未经历一场思想启蒙,一切现代化的器物之“材”都不能发挥作用,都只能是舍本求末之举。针对国民的思想状况,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开始了一项国民启蒙的工作,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唤醒国民,走上了思想启蒙的道路。
正是基于启蒙的价值诉求,梁启超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8)而新国民的培养则有赖于教育,“新之有道,必自学始。”所以,教育要以“新民”为第一要务,把国民从睡梦中“唤醒”,自立于世。虽然梁启超也是出于救亡之需来倡导教育变革,培养新式人才,但他的思想(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已经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29)西方之长者皆需学习,中国之短者皆需采补,不论西艺与西政,同样还需“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30)采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精神来重铸中国国民性,倡导“新国民”。
封建纲常伦理、忠孝节义等思想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使其盲从权威,在朝屈从君王,在家屈从父兄。社会的主导价值是“服从”,行为规范是忠君尊父,夫唱妇随。这样一来,社会就陷入服从而非自由、专制而非民主、奴役而非自主的境遇,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同样,在这样的社会中,哪怕是引入再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济于事,洋务运动的失败则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变革之后,技术器物的变革才有更大的意义,否则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教育需要改善“国民性”,实现国民觉醒,独立人格,才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
教育的落脚点要从技术层面转移到思想层面,教育启蒙的主题要从救亡造材转移到启蒙立人,从培养器物之才转移到唤醒国民意识。教育要“使人成人”,而不能“使其成为器”。“盖教育者,将教之育之使成人,不但使成器也,将教之育之使为国民,不但使邀科第的美官而已,亦不但仅了衣食之谋而已。”(31)这样,正好暗合了康德在1784年所提出的命题,“按照人的尊严去对待并不仅仅是机器的人”。新式教育必须从器物技艺层面向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层面转变,由救亡之才向祛魅立人转换,培养新国民。“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团结”,(32)“要之使其民备有人格(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性智识体力皆包于是),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33)
正是在“人”的旗号下,中国知识分子把唤醒国民意识,进行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从“药方只贩古时丹”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复兴传统”到“中体西用”再到“全面学习”,从形式上的现代化到思想上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实现了启蒙路径、话语策略、启蒙主题的三重转换。在转换过程中,中国教育启蒙徘徊前进。
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的历史主题下,普遍认识到国家富强需要唤醒国民的思想意识,使沉睡着的芸芸众生觉醒为自主自由之国民。若无新国民,难以保种、难有强国,奴隶之国,何谈富强。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探寻出了一条“求富强——育人才——兴学校”的路线。这样,强国富民的救亡任务自然就与立人祛魅的启蒙任务合二为一。
启蒙精神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健全的个人主义”开始影响中国教育,“独立自主人格”的养成也成为知识分子的教育目标。启蒙“立”人,立独立自主的自由人。兴现代学校,以“育”现代国民。现代学校要彰显国民个性,倡导学术自由,推崇学校自我治理,为了民主的社会。现代教育除了培养人的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能够自动、自主、自治、自立,享受人之为人的权利,使人有尊严的生活,而不屈从于外在权威,不为木偶,不做傀儡,不依附他人,从而拥有完全之人格。
无论是往昔的教育启蒙,还是今日的教育改革都不能仅仅着眼于人的工具性价值,还要破除“奴化”与“物化”的教育,以人为目的,捍卫人的尊严与价值。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张力,中国教育启蒙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①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3页。
②(25)费正清、刘广京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4页,第196页。
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七《学校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册。
④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⑥魏源:《海国图志》卷三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093页。
⑦魏源:《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6页。
⑧⑩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147页,第328页。
⑨在维新变法期间,“有关文化教育领域的上谕据粗略的估计即有近40项,在短短的103天,平均每隔三天即有一道教育方面的谕旨发布。”这些谕旨主要涉及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与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堂等方面。具体参见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3页。
(11)薛福成:《筹洋刍议》,见丁守和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12)冯桂芬,《采西学议》,见丁守和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13)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见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14)(16)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41页,第597页。
(1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17)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二《礼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18)(19)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第306页。
(2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
(21)郑观应:《学校(上)》,见丁守和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22)(23)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第14页。
(24)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丁守和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0页。
(26)如西方学者冷纳认为,西方模型只有在历史的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则是全球性的,现代文化表现为西方文化的形态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具体可参见D.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转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梁漱溟认为,“西化”就是“世界化”,西方文化在当时不仅仅属于西方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文化。西方文化不是地域性的概念,而是文化形态的问题(具体见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2-385页)。冯友兰对于中西文化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东西文化不再是简单的地域性关系问题,而是新旧文化问题。“一般人所谓的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这(东西文化——引者注)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具体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244页)
(27)关于近代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转换这一问题,限于篇幅关系笔者将会在其他相关论文中详细地加以论述,这里仅仅作简要的论述。
(28)(29)(3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6页,第5页。
(31)严复:《教授新法》,《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32)(33)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见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第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