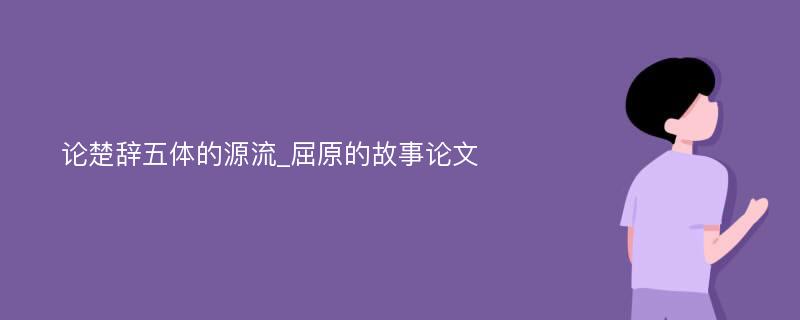
楚辞五体源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源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129-08
一、楚辞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突破瓶颈
中国楚辞学是在汉代奠定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屈原作传,他在屈原列传中提到了屈原《离骚》、《怀沙》、《天问》、《招魂》、《哀郢》几篇作品,并将《渔父》写进屈原传记。司马迁还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他确认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被王逸断为宋玉的作品有《九辩》和《招魂》。《大招》一篇,王逸说:“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王逸是屈原同乡,也是楚辞作家,生活在东汉时期,人们普遍相信他的观点大体可靠,因此在此后近两千年,中国楚辞学基本遵循王逸《楚辞章句》所奠定的格局。
要突破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最大的瓶颈是横亘在学者心中的一个顽强信念:“汉人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据。”除非有地下文物出土,证明某一篇楚辞不是屈原所作,否则绝大多数学者不愿意接受其他新的说法。应该说,这种无征不信的态度是正确的。王逸生活的年代大约距屈原沉江近四百年,说王逸“去古未远”是可以的,王逸《楚辞章句》的许多说法应该来源于前人,说他“必有所据”也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国楚辞署名权是在特定著述习俗之下形成的。战国时期,只有学派或流派的宗师有署名权,弟子后学一旦服膺某种学说,就必须按照宗师的思想和文风从事写作,如果他们的作品被收录进宗师文集,他们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署名权归于宗师,因此战国的子书往往是一个学派或流派的合集。例如,《论语》在记载孔子语录的同时也收录曾参、有若、子夏、子游、子贡、颜回、子张等弟子的语录。《墨子》一书实际上是整个战国墨家学派的总集。《庄子》中的外篇和杂篇被公认为是庄子后学之作。《荀子》中也收录了弟子后学的作品。有些战国诸子作家考虑到自己的名声不够,不惜采用托名的方法,署上古今贤哲之名,借助于他们的巨大声名,使自己的作品得到流传。如《管子》一书,其中虽然收录有春秋管仲遗说,但书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出自战国稷下黄老学者之手,他们要借管仲之名来传播自己的学说。《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兵法的真正作者是“诸侯之客”,署的却是魏公子之名。《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壹、天一、神农、封胡、黄帝、蚩尤、风后、力牧等人的作品,全是战国诸子百家托名之作。楚辞创作是战国著述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战国著述习俗的影响,因此应该将楚辞署名权放到战国著述习俗之下考察。屈原由于创作了“奇文”《离骚》,成为南楚诗坛无可争议的盟主。按照战国的署名习俗,那些后学弟子有责任和义务按照屈原的思想感情和文风从事创作,某些无名氏的楚辞作品也会与屈原作品放在一起,这些作品的署名权归于屈原。①
令人振奋的是,近几十年来陆续有地下文物出土,为我们突破两千年楚辞学格局的瓶颈创造了条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残简,证明在战国后期以主客问答为形式特征的散文赋已经基本成熟,这为人们确定宋玉一批散文赋的著作权提供了佐证。2008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收有一篇《凡物流形》,其形式与《天问》相近,这说明战国南楚存在这种有问无答的作品。2011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中,收有与《桔颂》形式相近的《李颂》,此外还有骚体的《有皇将起》和《鶹鷅》以及咏物的《兰赋》。这些出土文献为楚辞研究提供了参照。
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我们认为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下面对楚辞五体源流试加论述。
二、骚体
战国南楚骚体是楚辞的主干,骚体作品包括《九歌》、《离骚》、《九章》、《远游》、《九辩》以及上博简《有皇将起》和《鶹鷅》,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
南楚骚体作品的源头既不是北方的《诗经》,也不是先秦古籍中那些一鳞半爪的楚歌。它起源于楚国早期社会以巫娼习俗为核心内容、以巫术歌舞为形式的巫文化艺术。世界各国早期艺术都与当时原始宗教习俗有关,楚骚这一文体也是从楚国早期社会原始宗教习俗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南楚巫娼习俗的核心内容是以性爱娱神。在早期楚人心目中,神灵都是一些钟情于性爱生活的风流情种,要想取悦于这些神灵进而求得他们的赐福,首要条件是满足他们的性爱需求。因此楚人挑选那些风情万种、能歌善舞的男觋女巫,作为迎神娱神的使者。除了以美人娱神之外,楚人还以美花、美草、美酒、美歌、美舞、美乐作为以性爱娱神的辅助手段。因此,以性爱娱神最终落实到以美娱神。当南楚巫娼习俗与祭神歌舞结合起来的时候,早期楚辞文化就诞生了,在这种巫文化艺术活动中诞生的以表现巫娼习俗为内容的巫歌就是早期的楚辞作品。《九歌》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南楚早期社会的祭神巫歌。王逸把《九歌》说成是屈原被放逐到沅湘时为当地土人所作,朱熹则说《九歌》是屈原在沅湘民间巫歌的基础之上加工改写,这些说法都不一定可靠。《九歌》最初可能是民间祭神巫歌,它的作者应该是那些从事祭神活动的巫觋,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过历代许多无名艺术家的加工传唱,最后从民间传入宫廷,经过宫廷巫师的艺术整理之后,成为宫廷祭神乐歌。《九歌》本是无名氏之作,因其形式与《离骚》相近而被与屈原作品放在一起,最终系于屈原名下。《九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性爱娱神,它的主题是歌咏神灵之恋和神巫之恋,是一组深情绵邈的优美情歌。②《九歌》以神灵的爱情生活作为祭歌主题,这与北方《诗经》中的祭神乐歌大异其趣。《九歌》初步奠定了楚辞骚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的文体特征,它的诗句中间多用“兮”字,多写与性爱生活有关的芳草美人,表达惆怅失意的情绪和缠绵悱恻的情感,在句式上回旋往复一唱三叹,这些后来都成为楚辞骚体的必备形式特征。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如果没有伟大的天才诗人屈原的出现,如果没有屈原由于政治失意而转向巫术的特殊经历,楚辞骚体艺术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始宗教艺术的水平,楚辞也只能产生像《九歌》、《招魂》之类的宗教巫歌。屈原对楚辞文化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将战国士文化精神注入楚辞文化之中。所谓战国士文化,是指以战国士林为创造主体、以平治天下为政治目标、以思想解放自由创造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思潮。战国士文化精神就是以士林阶层的思想学说平治天下的主体精神。屈原出身贵族,曾一度跻身于上层决策集团之中,但他的思想情趣与情感气质均属于士林阶层。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屈原敏锐地感受到战国士文化大潮的冲击,比任何人都更多地禀受时代的灵气:与此同时他又深受南楚巫文化艺术的浸润,吸吮着巫文化艺术的乳汁。通过屈原个人的特定文化素养和特殊政治际遇,战国士文化与南楚巫文化得以成功融合,而这就是《离骚》赖以诞生的文化土壤。屈原早年在政治上春风得意,可是由于奸臣嫉贤谗害而被楚王疏远,他满腔忠愤无处诉说,在楚国当时浓郁的巫风环境中,便自然地转向巫术,试图通过巫术降神来为自己找到一条政治出路。而要求助于巫术,就会自然地沿用南楚以性爱娱神的形式,借鉴南楚祭神巫歌《九歌》。《九歌》因此成为《离骚》的先驱作品。③
《离骚》极有可能是屈原在经历一系列的长时间的巫术降神活动之后,再经过艺术构思而创作的。《离骚》中的许多内容应该是巫术活动的真实记述,而不完全是艺术虚构。诗中许多艺术意象可以从《九歌》找到来源。《离骚》继承了《九歌》以性爱娱神的巫娼习俗,这集中体现在诗中的芳草美人描写上。主人公所求神灵多为女神,诸如女媭、宓妃、简狄、二姚等,主人公“求女”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与女神缔结姻缘。他试图以性爱取悦女神,进而求得女神的指点与赐福,帮助他走出极度悲苦的困境。主人公披服花草的艺术现象也直接来源于《九歌》,香花美草作为主人公以性爱娱神的辅助手段,可以增添性的魅力。《离骚》中大段异彩纷呈瑰丽无比的天国神游以及关于巫咸降神、问卜灵氛等巫文化现象,与《九歌》中神灵在巫术幻境中飞翔升降的描写一脉相承。甚至《九歌》中那种低回感伤、缠绵悱恻的情感以及回旋往复的韵律,也被《离骚》完全继承下来。《九歌》中许多诗句在《离骚》中得到沿用和点化。《离骚》学习《九歌》而又超越了《九歌》,它鲜明地体现了战国时代的文化精神。《离骚》的灵魂即为战国士文化精神。屈原在《离骚》中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导夫先路,就是要充当楚王政治上的引路人。屈原试图通过取得楚王的信任,使自己平治天下的方略得以实现,使楚国政治走上昌明大道。屈原在《离骚》中提出了一些平治天下的方略,诸如举贤授能、遵循法度、服义用善、以德为治等等,这些都是战国士林的热门话题。屈原在《离骚》中表示要培养一种纯粹、芳洁、一尘不染的品质,培养一种与日月争光的人格,这与战国士林刻意修身砥砺品质是一致的。《离骚》主人公热烈向往的伊尹、傅说、吕望、宁戚式的君臣相遇“两美必合”故事,也是战国士林共同憧憬的理想境界。《离骚》艺术现象应该从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的结合上去理解。《离骚》比兴正处在由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转化的过渡形态。例如,诗中的芳草美人一方面保留了《九歌》中的性爱内容,另一方面由于主人公受到战国士文化的浸染和对自身巨大价值的意识觉醒,因而有意识地以香花美草作为自身美好品质、人格、才能的比喻或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芳草美人就由宗教观念内容向比兴艺术形式转化。又如,《离骚》主人公“求女”的基本意义是通过冥婚女神而求得神灵赐福,但主人公的“求女”又与屈原关于两美必合、君臣默契的理想境界交融在一起,因而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主人公对理想政治境界的追求,而这种理解实际上就由宗教内容转化为艺术形式。其他如天国神游、占卜降神等既是巫术活动的真实记述,但在另一方面,巫术给主人公指明出路以及主人公对巫术的最后否定,又与屈原内心经历的去与留的矛盾斗争大体相符,因而也可以从比兴上去理解上述巫术现象。《离骚》的比兴形态早于《诗经》,尽管它产生的时代比《诗经》要晚几百年。《离骚》与《九歌》一样表现了对美的强烈追求,但《九歌》的美学是一种宗教美学,而《离骚》由于吸取战国士文化精神,因而它的美学处在由宗教美学向现实美学过渡的形态。《离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巫文化的想象力和战国士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表现缠绵悱恻的情感、追求美丽的词藻、行文的回环往复方面,都在学习巫歌的基础上而将它们推向极致。尤其是楚辞的篇幅在屈原手中得到空前的拓展,《离骚》共373句,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罕见的长诗。《离骚》是楚辞最壮丽的代表作,它奠定了屈原在南楚诗坛上无可争议的地位。此后楚骚创作进入了一个以屈原为宗师的仿作时代。
《九章》是《离骚》的卫星作品,绝大多数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都刻意仿效《离骚》,甚至在具体诗句运用上也多有因袭的痕迹。《九章》的内容基本上是《离骚》的重复和引申,它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意群:讴歌主人公与日月争光的美好品质与卓越才能;抒发主人公为楚王师的宏伟抱负和平治天下的火热激情;诉说主人公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冤屈和放逐后内心所经历的报国无门而又难以割断情丝的种种缠绵悱恻情感;表达主人公九死未悔不改初衷的坚强意志和保持清白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愤怒指斥楚国党人陷害忠良和楚王的昏暗不明。这五大意群都可以从《离骚》中找到母题。当然《九章》也不是毫无新意,例如,《惜往日》称楚王为“壅君”,这种激烈态度是《离骚》所没有的。《九章》具体记述了屈原放逐行吟的路线和踪迹,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屈原后半生的宝贵材料,清人林云铭即根据《九章》而理清了屈原后期行踪。《九章》中的《桔颂》,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形式上都独树一帜,在《九章》中属于另类。《九章》中可能有屈原本人的作品,如《哀郢》、《涉江》,但绝大部分作品应该出于熟悉屈原生平行事的后学之手。《远游》创作的时代较晚,它的作者一方面谙熟屈原及其后学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对道家、神仙家学说造诣极深,借用《离骚》神游天国的形式来表现游仙思想,将屈原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精神偷换为游仙的欢悦。《远游》虽然偶尔点化《离骚》的诗句,但背离了屈原的思想感情,因而它的作者不一定是屈原弟子后学,至多是一个楚骚爱好者。
出现在战国后期的宋玉《九辩》在骚体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篇名作的价值在于,它在楚辞文化衰落、时代即将由士林平交王侯转入君主专制统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唱出“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新主题,从而将骚体主调由《离骚》为王导夫先路而转向个人的怀才不遇,这个主题在此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广大士林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强烈的共鸣。《九辩》的出现成功地解决了骚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问题,汉人骚体创作名义上是学习屈原而实际上更接近宋玉,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的骚体创作都是如此。
上博简《有皇将起》的作者从事贵族子弟教育,他担心弟子因“速长”而有“不善心”,要求弟子“周流天下”。《鶹鷅》批评鶹鷅“欲衣而恶枲”、“不织而欲衣”,主旨略与《诗经·魏风·伐檀》相近。仅从内容还看不出这两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不过它们与屈原的故事无关,也没有骚体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感旋律。
三、天问体
《天问》是楚辞中形式最为奇特的一篇,它一口气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都是有问无答,如同一个问题集。虽然它有诗的韵律,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像诗。自从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以来,历代《天问》研究者都把《天问》视为屈原抒情言志之作。关于《天问》之“志”的内涵,历代学者提出“舒愤说”和“讽谏说”两种观点。前者如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认为屈原作《天问》是“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后者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天问〉序》中,则认为屈原作《天问》不仅是渫愤舒愁,更重要的是表达“讽谏楚王之心”。
2008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收有一篇《凡物流形》,这篇竹书有甲、乙两个版本,甲本现存30支竹简,846字,乙本有21支竹简,601字。作品前半部分就物体形成、生死由来、天地鬼神等问题发出一系列疑问,例如:“凡物流形,奚得而成?流形成体,奚得而不死?既成既生,奚呱而鸣?既拔既根,奚后之奚先?阴阳之凥,奚得而固?水火之和,奚得而不厚?问之曰:民人流形,奚得而生?流形成体,奚失而死?有得而成,未知左右之请?天地立终立始,天降五度,吾奚衡奚纵?五既竝至,吾奚异奚同?五言在人,孰为之公?九区出诲,孰为之逆?吾既长而或老,孰为侍奉?鬼生于人,奚故神盟?骨肉之既靡,其智愈障,其缺奚适?孰智其疆?鬼生于人,吾奚故事之?……”竹书整理者曹锦炎指出:“《凡物流形》是一篇有层次、有结构的长诗,体裁、性质与之最为相似、几乎可以称之为姐妹篇的,当属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为不朽之作——《楚辞·天问》。《天问》也是有问无答,全诗三百七十四句,就内容可以分为四章和一个尾声。……用王夫之的‘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来概括楚竹书《凡物流形》篇,也是十分妥贴的。虽然《凡物流形》的内容和思想比不上屈原《天问》的‘奇气纵横,独步千古’(夏大霖《屈骚心印》),其文采词藻也稍逊一筹,但其‘创格奇,设问奇’(同上),与《天问》一样,的确是别具一格。非楚人之浪漫性格,焉能有此诡丽奇谲之作品?因此,从文章体裁,与《天问》内容的参照,以及文字的地域特色等,我们将《凡物流形》篇归入楚辞类作品。”④《天问》有了姐妹篇,这是《天问》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它使我们对此类提问体楚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将竹书《凡物流形》与《天问》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两篇“问题集”式的作品之间有同有异。它们都是针对自然和人事现象提出疑问,都是有问无答,两篇作品都是以四字句为主,都喜欢采用上句叙述、下句发问的句式结构,问句之末都有韵律,这是它们相同或相近之处。它们的相异之处也很多,两篇作品的规模有大小之分,《天问》凡一百七十四问,而《凡物流形》只有四十三问;《天问》中关于神话传说、殊方异物、古今历史的诸多疑问,是竹书《凡物流形》所没有的,《天问》所询问的知识领域比《凡物流形》要恢宏、广阔、深邃、奇诡得多,两篇作品的知识水平和想象能力不在同一个层级;《天问》哲学意味很浓,并有鲜明的巫文化色彩,篇中所问多为普通民众很少思考的虚的问题,而《凡物流形》所问的则是物体形成、生死由来、天地、鬼神、日月、阴阳、水火、风雨、雷电、草木等比较实在的经验问题,其中看不到南楚特有的巫文化痕迹;《凡物流形》前后论题似有转换现象,前半部分询问自然,后半部分则强调如何从“貌言”取人,以至于有人认为它是由本来完全不同的两个文献连接在一起的,⑤而《天问》则通篇一气呵成。还有,《凡物流形》的疑问词多用“奚”、“孰”、“何”字,而《天问》的疑问词则多用“何”、“胡”、“焉”、“安”、“孰”、“几”字。从《凡物流形》“吾既得百姓之和,吾奚事之”来看,它的作者似乎是一位有封土食邑的人,而《天问》则没有这样的暗示。
虽然《凡物流形》内容比《天问》要浅,形式要稚嫩,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准确判定这两篇作品孰先孰后。《凡物流形》对《天问》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作为一个参照系,可以证明在战国南楚存在着询问宇宙、历史、自然现象的“问题集”这一类的楚辞作品,而这些天问体作品无非是表明楚人对宇宙、历史、自然、人事诸多奥秘的浓厚兴趣、巨大困惑和探寻欲望,其中并无作者的主观情感寄托。这类作品产生的背景,是战国时代的知识大爆炸。如果我们以这种目光来读《天问》,就可以还原《天问》探索宇宙、历史、传说奥秘的本来面目,就能够剥离两千多年来《天问》研究中关于屈原寓有生命体验、寄托主观感情的成分,从而重新确立《天问》研究的格局。《天问》既无寄托,那么它就不一定是屈原之作,它之所以系于屈原名下,其原因与《九歌》、《九章》相同。
《天问》、《凡物流形》在战国“奇文郁起”,在后代亦无继作。
四、招魂体
属于招魂体的楚辞作品有《招魂》和《大招》,这两篇作品都是出于楚国招魂习俗。它们的写法,用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招魂》用语气词“些”,《大招》则用语气词“只”。《招魂》要比《大招》写得更精致,因而历来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招魂》为屈原所作,王逸《楚辞章句》则认为《招魂》的作者是宋玉。在所招对象上,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宋玉招屈原生魂,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认为是屈原自招,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认为是屈原招楚怀王生魂,马其昶《屈赋微》、郭沫若《屈原研究》力主屈原招楚怀王亡魂,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认为是招楚君的生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认为是屈原招楚国国魂,林庚在《招魂地理辨》一文中认为是屈原招楚国阵亡将士亡魂。意见如此五花八门,而且都是出于后人推测,这本身就说明将《招魂》著作权归于屈原大有问题。《招魂》作者既非屈原亦非宋玉,而可能是楚国宫廷巫师。它同样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从雏形到定稿,应该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它的最后写定应该是在战国中后期,与屈原生活年代相距不远,这从它接受战国诸子铺张扬厉的风气中可以见出。至于所招对象,则不一定要局限于楚怀王、顷襄王或屈原,而应该视作楚国宫廷通行的招魂词,即它对任何一个楚王都适用。从《招魂》开头“魂魄离散”、“恐后之谢,不能复用”之语来看,所招的应该是死魂,即楚王去世之后,由宫廷巫师举行巫术仪式,招唤他的离开躯体的魂灵不要迷失,而要回到楚国王宫。招魂这一习俗不仅存在于战国南楚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古今中外,甚至在今天中国某些农村地区仍然存在。招魂的共同点是以具有诱惑力的事物吸引魂灵归来。《礼记·礼运》载:“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这可能是最早也是最简单的招魂词。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记载了中国古今的招魂习俗,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记述了世界各民族的招魂习俗,当代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她的硕士论文《彝文经籍中的祭祀诗研究》中记载了彝族的招魂词。我们将古今中外的招魂词与《招魂》、《大招》相比,竟然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就告诉我们,不要人为地给《招魂》、《大招》增添诸多主观寄托。《招魂》、《大招》原来是楚王宫廷通行的招魂词,它们本来是无名氏作品,因为形式与骚体相近而被人们归入楚辞一类,于是后代学者便将它们说成是屈原或宋玉、景差的作品。
五、散文赋体
南楚散文赋创作盛行于战国后期,特别是在顷襄王时期达到高峰,它的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98年顷襄王即位,下限是公元前238年荀子罢官,整个创作时段约60年左右。宋玉是南楚散文赋的最大作家。宋玉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但都未注篇名。长期以来,宋玉作品得到后世公认的只有《九辩》一篇。《文选》、《古文苑》以及明人辑录的《宋玉集》中收录了宋玉的一些散文赋,这些散文赋曾被前人疑为托名之作,理由是战国后期还不可能出现那样成熟的散文赋。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残简,虽然只有二百多字,但它证明在战国后期以主客问答为形式特征的散文赋已经基本成熟,因此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宋玉散文赋的著作权问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收录一篇托物咏志的《兰赋》,这进一步证明咏物赋在战国已经成熟。现在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相信,《文选》、《古文苑》所载的宋玉诸赋,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都是出于宋玉之手。其他如《文选补遗》以及明人所辑《宋玉集》中的《微咏赋》、《报友人书》、《对友人问》、《对或人问》、《高唐对》、《郢中对》等作品著作权,还有待继续探讨。
南楚散文赋的来源有迹可寻,它从此前诗文中吸取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从此前神话、寓言中借鉴了艺术虚构的智慧,从战国诸子百家散文中学习铺张扬厉的手法,并从楚骚体中获得了艺术营养,由此形成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定文体形式。
南楚散文赋的创作主旨可以分为娱乐、讽谏、纪事、咏物几类。宋玉等人往往通过创作散文赋来娱乐楚王。《高唐赋》和《神女赋》的故事主角是楚王与巫山神女,宋玉创作楚王与巫山神女性爱故事的动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编一个黄段子,给楚王逗乐。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实行多妻制,后宫佳丽如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女人,大概就只有神女了。现在,宋玉写一位神女自动提出来要与楚王交欢,这既满足了楚王的文学娱乐需求,又迎合了楚王潜意识中的情欲。《登徒子好色赋》写宋玉辩驳登徒子对他的人身攻击,《讽赋》写宋玉回击唐勒的谗言,《对楚王问》是宋玉对自己名声不好的辩白,这几篇散文赋从表面上看是宋玉自我辩诬,实际上也是轻松幽默、逞才斗智的娱乐作品,当然其中多少反映了一些封建宫廷中同僚间尔虞我诈的恶劣习气。《风赋》将自然界的风区分为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说雄风是如何宁体便人,而雌风又是何等生病造热,这可能是宋玉为了满足楚王高人一等的特定心理而有意生出的一篇文字。《大言赋》、《小言赋》是战国后期南楚上流社会的一种语言游戏,赋中几位人物各说一段大话或小话,宋玉为此赋,可能多少有些与唐勒、景差之徒比才量力的意味。此类大言、小言没有多少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但对训练人的思维和想象力有一定帮助。自《尚书》、《诗经》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大都承载着宗教祭祀、政治讽谏、道德教化、惩恶扬善等功能,那种以纯粹娱乐审美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并不符合中国文学传统。楚国出现宋玉等人以娱乐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应该与它作为蛮夷邦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与战国晚期士人人生抱负的降低以及政治地位的下降也有一定的联系,可能还与顷襄王对辞赋的特殊爱好有因果关系。在重视讽刺教化的中国传统文学园地,以娱心悦志为宗旨的楚国辞赋,构成一道别具情味的风景线。不过它们也表明宋玉等人为了一己的生存,而自甘用文字取悦楚王,换来一点君主的垂青和奖赏,沦落成优孟一类的俳优人物,这开启了汉代皇帝将辞赋作家俳优蓄之的恶例。有些南楚散文赋带有讽谏意味。《唐勒赋》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见神奇。赋中贬斥“今之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专家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宋玉《钓赋》借钓鱼一事为喻,劝谏楚王,表达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荀子《赋篇》体物写志,类似于猜谜语,在娱乐的同时多少也有些讽谏的意味。上博简《兰赋》借兰草抒写自己的情趣志向。王逸《楚辞章句》将《卜居》、《渔父》系于屈原名下。如果我们将这两篇散文赋看作是纪实作品,那么它们就是以第三者的目光记述屈原行事,在性质上与战国诸子散文中弟子记载其师言行的作品相近。当然也不排除艺术虚构的可能性,因为仔细研读就可以发现,这两篇散文赋是根据《离骚》的情节写成的。《离骚》中有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系列巫术描写,《卜居》可能就是根据《离骚》中这些巫术内容虚构了屈原问卜郑詹尹的故事。《渔父》写一位具有道家意味的渔翁劝告屈原从俗的佚事,而《离骚》中女媭詈骂、灵氛占卜等情节都有混同世俗、随波逐流的思想倾向,或许《渔父》正是按照《离骚》这些情节写成的。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卜居》、《渔父》都不是出于屈原本人之手,而应该是屈原弟子后学之作,或者是同情了解屈原生平行事的辞赋作家的作品。
散文赋在战国后期悄然兴起,虽然它的地位与影响比不上骚体,但在汉代枚乘、司马相如等人手中,却演绎成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的一代之文体。
六、楚歌体
楚歌是指楚人口头吟唱的民歌,这些楚歌大都失传,只有少数载入文献。楚歌与骚体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句中或句末运用语气词“兮”字,都有大致的韵律,句式散文化,在抒情上都有情意绵长的特色。两者不同之处体现在:在篇幅上,骚体长而楚歌短;在创作方式上,骚体多为案头创作,而楚歌则是即兴吟唱矢口成韵;在主旨上,骚体多抒发失意情绪,而楚歌既表达惆怅、愤懑、失意、感伤,也可表达赞美、爱慕、劝谏;在地方色彩上,骚体需要“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需要有香草美人、求神问卜的事象,而楚歌除了用楚声咏唱以外,不需要具备其他楚国地域色彩和巫文化事象。
由于楚歌与骚体形式相近,于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楚歌视为骚体的先驱,以为屈原是在学习楚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的《离骚》。这种观点需要作一些修正。屈原《离骚》的先驱作品是《九歌》,《九歌》的先驱应该是那些祭神巫歌,巫师们最初创作祭歌的时候,在形式上应该接近那些口头唱出的带有“兮”字的楚歌,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祭歌的篇幅。但是在内容上,巫师们主要歌咏以巫娼习俗为核心内容的巫文化事象,这样早期楚辞与楚歌就渐渐地区分开来了。屈原《离骚》在继承《九歌》的基础上,又注入战国士文化内容,这一点更是楚歌所不具备的。因此在《离骚》与楚歌之间,还有着一段太长的距离,如果以《离骚》直接上承楚歌,那就未免显得太粗放了。
如果我们仅仅将楚歌与骚体比较,就会误以为楚歌是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民歌,这些特色包括:句中运用“兮”字,句式或长或短,大致押韵。其实只要检索先秦文献就可以发现,句中用“兮”、句式散文化、大致押韵的民歌并非都是楚歌。例如《孔子家语·辨乐》所载《南风歌》,《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吕氏春秋·音初》所载《候人歌》,《韩诗外传》所载《夏人歌》,《史记·伯夷列传》所载《采薇歌》,《说苑·善说》所载《越人歌》,《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载《佩玉歌》,《晏子春秋·外篇》所载《岁暮歌》,《晏子春秋·内谏下》所载《穗兮歌》,《列女传·辨通篇》所载赵简子时《河激歌》,《孔丛子·记问》所载孔子所唱《大道歌》和《唐虞歌》,《列女传》所载鲁陶婴所唱《黄鹄歌》,《新序·节士》所载《延陵季子歌》,《吴越春秋》所载《日夕歌》、《乌鹊歌》、《离别相去辞》、《河梁歌》,《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武灵王时《鼓琴歌》,《吕氏春秋·乐成篇》所载魏襄王时期百姓歌颂吴起的《邺令歌》,《战国策·燕策三》所载燕国壮士送别荆轲时所唱的《易水歌》,《荀子·正名》所载《长夜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秦章华大夫所唱《遵大路歌》和《寤春风歌》,⑥全都是句中带“兮”字、句式散文化、大致押韵的歌谣。这些歌谣从时间上说,从上古到战国后期,从地域上说,北到燕赵,东到齐鲁吴越,西到秦魏,它们的形式与楚歌几乎没有多少区别。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句中用“兮”、句式散文化、大致押韵是先秦大部分歌谣的共同特色,楚歌是先秦歌谣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楚歌有某种地域特色的话,这种特色在声而不在歌词。
真正可以称之为楚歌的作品其实很少。《论语·微子》所载《凤歌》,《孟子·离娄》所载《沧浪歌》,宋玉《讽赋》所载《岁暮歌》,可以视为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楚歌的代表作。此外尚有《说苑·至公》所载《子文歌》,同书《正谏》所载《楚人歌》,不过这些楚歌中都没有“兮”字。楚歌的真正兴盛是在西汉时期。
以上楚辞五体虽然有互为渗透、相辅相成的一面,虽然有恢诡、绮靡、瑰玮、耀艳的共同特色,但更多的是各自独立的发展。对楚辞五体作适当的区分,梳理各自发生发展的脉络,特别是根据战国署名习俗而将某些楚辞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这样做在情感上虽然难以被部分学者所接受,但它可能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也有利于确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注释:
①其实王逸《楚辞章句》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他把《离骚》称之为“经”,而将从《九歌》到《九思》的楚辞作品称为《离骚》的“传”,“传”是对“经”的阐释和发挥。
②《九歌》中只有《国殇》没有性爱内容。
③姜亮夫在《楚辞今绎讲录》中指出,《离骚》是从《九歌》发展而来的。这一论断非常正确。
④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
⑤参见浅野裕一:《凡物流形的结构新解》,《简帛网》2009年2月2日。
⑥《诗经》中也有不少作品运用“兮”字,不过《诗经》中这些用“兮”字的作品多由几章构成,它们多经过乐师加工,与即兴口头歌唱的楚歌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标签:屈原的故事论文; 楚辞论文; 中国习俗论文; 文化论文; 楚辞章句论文; 诗经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屈原论文; 天问论文; 九歌论文; 九辩论文; 战国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远游论文; 楚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