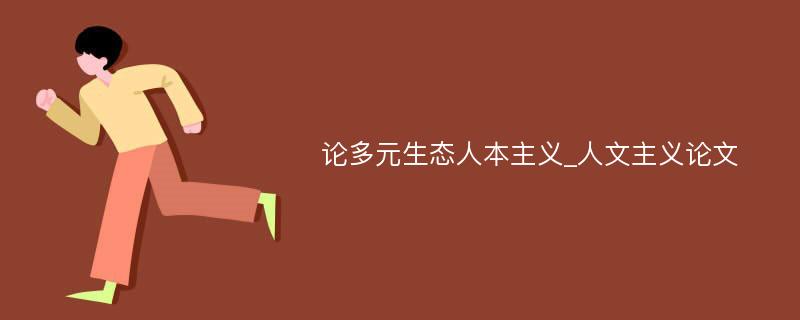
论多元的生态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工业化引发的,在此之前人们不曾或几乎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因为该问题当时还没有成为显性问题,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是因为人对它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而是自然本身的缘故,人们考虑的倒是如何把握和控制环境,即要战胜自然环境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自二战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态环境问题很快成为第一、第二世界的现实问题。随着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接踵而至。鉴于此,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专著、论文,呼唤全球的关注,也期望人类有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一
中国学术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心基本上始于80年代,到了90年代,则成了学术关注点之一。中央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则是解决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矛盾的一个战略方案。至今,学术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论著。在笔者所见到的学术著作中,特别看重佘正荣先生的专著《生态智慧论》(注: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佘先生从事生态哲学研究已多年,在《生态智慧论》中已基本形成他的“生态人文主义”理论。笔者很欣赏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几大关系的范式划分,虽说这种范式划分不完全符合人类发展史,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本文在概述佘先生的生态人文主义理论基础上,还想对“生态人文主义”理论作进一步的反思。笔者认为“生态人文主义”理论还需进一步澄清,认为生态人文主义和不同的哲学世界观有直接的联系,大体上可以将生态人文主义分为两类: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和宗教的“生态人文主义”。而宗教的“生态人文主义”又可以分为非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和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佘先生的生态人文主义显然属于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
佘先生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采集狩猎时代的人与自然混沌同一性意识、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人文主义”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人文主义”阶段,而现代正转向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主义”。
从人类诞生之时到农业文明兴起之前,在数百万年之久的采集、狩猎时代,人类是以极其简单的石制、木制的工具,以采集、狩猎、渔捞等劳动方式,去直接获得来自上界赐予的产品。人类在这一很长的时期内基本上还只是自然生态系统食物网的一个环节,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作用只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食物链从而反馈到生态系统中去。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是以生态规律占支配地位的原始的人和自然共同进化的方式。原始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处于混沌的神秘状态。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大约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驯养动物、种植庄稼,于是带来了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佘先生认为,人类已从自然生态系统直接的食物链的制约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建造自己生存的人工自然环境。在其中,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仿效自然、利用生物规律和生态规律进行有机物质再生产的过程,它是动植物有机体同周围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人工过程。佘先生进一步认识到,在农业文明中,由于传统农业大都采取粗放经营方式,刀耕火种、广种薄收、耗尽地力、掠夺性地开发自然,没有重视从外部经常补充相应的物质和能量,结果在局部地区逐渐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状态,以致带来严重的自然灾害。
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通过与自然的密切交往,通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对自然规律的经验把握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自己和自然的区别,同时又深深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对自然的依赖性,认识到人类必须和自然建立一种和谐一体的关系。
佘先生认为这种自然人文主义在西方不明显,在东方文化中,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西方文化中,之所以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和继承古希腊的近代理性传统的缘故。基督教传统和自然主义相对立,近代理性主义明显的对象化思维也难以和自然主义相协调。
佘先生提出道家的自然观是典型的自然人文主义。我认为,这样说,既对又错。说对,是因为道家思想确实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人文主义色彩;说错,是因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基础是有很深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后面我将视其为非人格的宗教“自然人文主义”。
以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利用不断发展的理性技术,把自然界的改造作用从农业文明中的生态系统扩展到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系统,直到整个地球生物圈。人类的活动影响了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生物圈循环。人类利用工业技术所发展起来的强大物质力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无生命的人工物质系统。
这样一种物质系统是与自然对立的,人与自然处于全面的异化关系之中。这种异化的根源自然在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作者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必然造成个人中心、集团中心、民族中心、国家中心、西方中心,亦强化着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着把他人、异族文明和自然界当作征服和奴役对象的价值观。
全球生态危机已向这种科技人文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若想不在这场挑战面前毁灭,就要转向新的生存方式。佘先生为我们设计的蓝图是生态人文主义。
佘先生认为,在新的生态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必定是生态人文主义。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自觉地利用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人文主义,是按照生态世界观及其科学方法论来积极发挥人类维护和促进自然进化的人文主义。
二
笔者认为,生态人文主义至少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本文拟将生态人文主义加以细分,以丰富生态人文主义的内涵,希望全世界各地区、民族以生态人文主义共同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共同缔造一个和平、安全、和谐和多元的生态人文主义世界。
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生态人文主义世界观。大致说来,人类对世界的解释分自然主义的和宗教的解释两类。根据自然主义的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是物质运动、自然进化的产物。这种理论排除宗教的解释,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都视为由于人类的无知或愿望的投射而引起的。
依据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有机的关系。历史上的人类,由于人口数量的有限,理性、科技力量的有限,人对自然的总体性干预是有限的,不至于从整体上影响生物圈的稳定性。但工业化和人口这两个参数的变化,很快改变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形象。人类成了超级怪兽。这个怪兽陷入理性的迷幻之中,绝对地崇拜理性,相信科学技术能够排除一切障碍、解决一切难题。但是,自然本身的法则并不是由人在一定时空领域中的认识所决定的。当人类在不断向自然攫取的同时,自然界的承受力在一天天地下降,首先出现局部性危机,很快地就出现了普遍性危机。这种危机的矛盾开始针对的是自然界中的其它生命体,但随后也就殃及人类自身。
有识之士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远非人原先设想的那么简单,认识到自然本身的变化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因而,70年代后,有的学者提出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注: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卞崇道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在我看来,共生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变种,因为自然与人类共生本质上并不存在,人类只是害怕自己的毁灭而采取一种相对节制的态度而已。共生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我们也许还不宜给予过早的评论。但显然地,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它肯定人类的需要,但并不真的考虑万物本身的需要,只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平衡角度考察。共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归于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
在理性上,我们无法证明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是错误的,当然,也无法证明它是正确的。但我们从功能主义角度考虑,这种世界观对人类生存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之所以不能证明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之真理性,原因在于我们人类理性本身的有限性。理性的最高境界和意志武断几乎是等同的。事实上,人类的存在不在于其真理性,而在于其功能性。正因为这样,便有了宗教的“生态人文主义”。
三
宗教的“生态人文主义”有非人格型的,也有人格型的。道家传统、佛教传统和不二论的印度教传统可以发展出非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犹太教传统、基督教传统、伊斯兰教传统和有神论的印度教传统则可以发展出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的基质是道,道化生万物,万物归于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人类也是道的化生之物,但人类在宇宙自然中有特殊的地位,被老子视为四大之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第25章)
老子进而提出在以道为中心的宇宙图景中,人的构成性地位是效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
老子看到人违背这一原则的严峻后果,挖掘出人违背这一原则的根据和解决的出路。老子警告说,人违背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失道,将导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万物无以生,将恐灭。”(第39章)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失道局面,原因在于人太认同自己的身体,老子称之为“大患”,说穿了,这就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因此,消除大患的方法自然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老子从人的角度(最高是“欲不欲”的圣人境界,对常人则倡导“少私寡欲”)破之,以恢复人在宇宙中切实的构成地位。
佛教传统本身的生存方式就预言了一种基本的生态人文主义。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Buddha Nature),故持“莫杀生”之诫,这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有序化。佛性的本源是法,法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要体悟正法、弘扬正法,就当唯法是从。佛教界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观念,使万物和平,这更加显明佛教出世性和人世性的结合。一个正法昌盛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和谐的。
佛教节欲、素食、简朴的生活方式自古至今都没有成为自然的侵害者,相反,佛教寺庙之地往往是绿化最好的地方,能量消耗最少的地方。
我们认为,以法为中心的佛教生态人文主义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它以法为最后归依,但又在这世上证悟它、弘扬它,看轻物欲。事实上,佛教本身即便不去明确建立一种生态人文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表现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似乎不用担心佛教传统以及虔诚的佛教徒会成为自然的对立面、敌人。
我们进一步认为,佛教对涅槃的渴求和对物欲的轻视这两点可以使佛教传统的众生成为自然的朋友。当今佛教国家或地区也会大量出现环境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因为一个佛教国家,也是一个世俗国家,其经济、工业、商业活动与其它国家是一致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处在现代性之下,都受制于现代生活方式。
因此,佛教传统自然所达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有赖于众生的切实实践。单有理论、观念,没有行动是空的。我们认为,在现代性的阴影之下的佛教传统需要反省自身传统,切切实实规定自己的战略,从而达到正法昌盛,万物和祥的境界。
不二论的印度教和佛教很相近。它的最高范畴是梵(Brahman)。根据不二论的最伟大的阐述者商羯罗的解释,世界是虚妄的,唯梵为真,灵魂(jiva)与梵同一。这种不二论思想完全是出世的,是灵修主义。不二论追求的人生意义不在这个物质世界,它对于世界并不执着。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都去追随商羯罗的不二论的话,社会将呈现为一片灵修的气息,物质财富不会有多大的发展,但人类的精神却会有大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并不可以称为社会发展,但它实质上推动了社会精神的发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生态环境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当然,众生追随不二论的话,工业文明也就无大必要了。
我们重温不二论的思想,目的不是全面转向不二论的世界观中,我们几乎不太可能全面拒斥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实际益处。即便灵修,也可利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如电子传媒、现代通讯设备、互联网络在灵修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管以道为中心,还是以法或梵为中心,本质上都是以非人格的绝对者(the Absolute)为中心。在哲学上,可以把人类生活设想得相当纯粹。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不那么纯粹了。我们认为,以非人格的绝对者为中心可以建构一种可能的“生态人文主义”范式。
这种非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它们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出于对世界的否定性理解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生态人文主义,后者则是出于对世界的肯定性理解而理性地追求的生态人文主义。前者看轻世界,鄙视世俗感官享受,后者肯定世界,重视世俗感官享受。前者把意义归于“道法自然”,证得涅槃和“梵我合一”,后者则把它归于物质自然。前者有超越性、神秘性,后者无超越性,尽管也有高峰体验。
其次,它们也有共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都强调自然本身应有的地位,对自然都具有亲和的态度。道家思想中,自然万物是道的外在展示,它们与道有内在联系,万物来自道,也归于道。佛教思想中,法无处不在,大乘佛教甚至认为“涅槃与轮回同一”,这个物质世界虽是不真实的,但也是法的展示之场所。佛教普遍强调万物有灵性(佛性),故与万物自然亲和也是十分真切的。根据不二论,梵为唯一真实者,物质世界则是虚妄不实的。尽管世界虚而不实,但作为个体生命,修行者重自然,要以清净、吉祥之地——这大概是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的圣地吧——为最佳的修行之地。喧嚣、热闹、污染之地绝不适合于灵性修持。
不同文化传统培养出不同的人类生存模式,事实上,就我们理性能力所及的范围而言,我们无法断定自然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好,还是非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好。这是不同类型的人类生活方式。
四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三个一神教。至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基督教中。由于犹太教的历史特殊性,她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自我的保存、维持上,对环境的关注还没有上升到主要议程。伊斯兰教传统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多为第三世界国家。
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多处在基督教传统之中。有的学术研究表明基督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理性事业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科学史家霍伊卡(Hooykaas)就持这类观点。
环境问题与科技理性有着内在联系,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深刻地反省过科技理性问题。如果环境问题是现代科技发展的自然结局,而基督教又被认为是致使理性发展者,那么,基督教对环境问题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不是基督教的产物,相反,是希腊理性精神和文艺复兴运动共同的产物。基督教一直来都是科技理性的“敌人”。
环境问题的责任显然不能归于基督教。但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一样都可以也应该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事实表明,基督教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远远胜过其它宗教。原因是,与其它宗教相比,基督教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在当今西方绿色和平运动中,就有一股力量来自基督教界。他们从基督教本身的角度来认识环境和处理环境问题。我们简单地考察基督教的生态人文主义:
从神学上说,世界是上帝的创造,人类则是创造的顶峰。上帝要人掌管大地,但不是叫人破坏大地。根据这一思想,基督教思想家可以抨击现代人对自然的无节制攫取。
人的生命在于有灵,而万物也依上帝的灵而存在,灵是贯通上帝、人类和万物的中介。有的基督教思想家明确承认万物所具有的灵性。这个灵在万物之中,正如《圣经》上说的,“主的灵充满全地。”(《所罗门智慧书》1:7)莫特曼(Jürgen Moltman)也说,“创造物的不同种类正是上帝这个具有创意的、赐生命的灵的不同表现。”(注:莫特曼:《公义创建未来》,邓肇明译,香港1992年版,第58页。)
由于灵的统一性,人与自然也应是一种合作的友好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利用也是有限度的。这一点具有大量的《圣经》依据:“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利未记》25:2-4),“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利未记》25:18)每隔7年让大地休息一次是蒙上帝赐福。耶和华要人们遵守安息诫命,若不遵循这一诫命,他会以特殊方式强迫大地领受安息:“我要使地成为荒场,……把你们散在列邦中……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利未记》26:32-34)
上帝为了让大地安息,其理由是很独特的:“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指以色列人)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利未记》26:42-43)为此,莫特曼提出“地球的安息:上帝的生态学”观念。(注)莫特曼:《公义创建未来》,邓肇明译,香港1992年版,第60页。)
基督教的生态学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但其落脚点是人,本质上是一种神本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这种神本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的最后理想是永久的和平(希伯来语shalom)。在那时,“藉着他……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和好了。”(《歌罗西书》1:20)
这里谈的主要是基督教的生态人文主义,但事实上,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有神论的印度教都可以发展出以神(上主、安拉和毗湿努)为中心的生态人文主义。
现在要讨论的是这种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和前面谈到的非人格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它们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它们各自所宣称的终极者不同,一是人格性的;另一是非人格性的。人格性的耶和华、天父上帝、真主安拉,怎么也不可能等同于道家的道,佛教的法、空、涅槃,印度教的梵。它们之间的区别如白天与黑夜。其次,它们也有共性。根据宗教的批判实在论和多元论假设[约翰·希克(John Hick)],它们分别代表人类对终极实在的两类回应方式。因此,建立在这两类实在基础上的宗教“生态人文主义”可谓一体两面,是可以相通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佘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两类“生态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的和宗教的。其中宗教的生态人文主义又可以分为非人格的和人格的宗教人文主义。这种划分本身就预示了生态人文主义的多元形态。我们之所以再加上两种生态人文主义,目的是肯定不同宗教传统建设地球生态家园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这既是对各宗教传统的肯定,也是对各宗教传统的呼唤,唤起不管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不管是信这种宗教的还是那种宗教的众生为克服地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为避免人类的自我毁灭,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携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