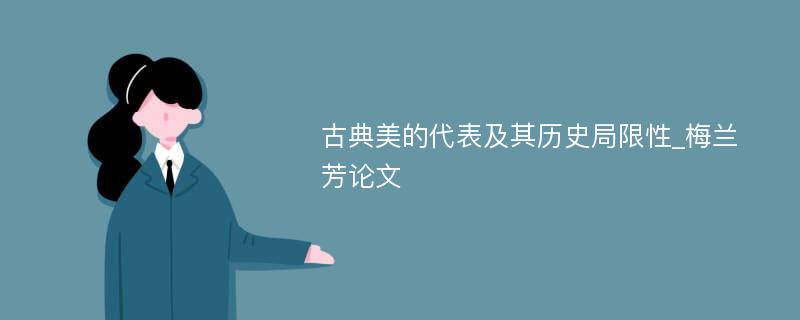
古典美的代表及其历史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限性论文,古典论文,代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梅兰芳是古典美的代表
古典美是一种美的历史形态,具体地说是指古典式的和谐的美。这种美的形态,它的突出的特点是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再现与表现、理智与意志、情感与理智自由的和谐的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讲,凡本质上和谐美的艺术就属于古典主义艺术的范畴,京剧自然包括在内。
古典美有两种形态:阴柔之美——优美;阳刚之美——壮美,与近代崇高不同。崇高这种美的形态,不同于壮美,更不同于优美。朱光潜先生说过,在自然界,崇高首先以数量上与力量上的巨大,引起人们的惊讶与敬赞,它还经常以突破形式美的一般规律的粗励形态,比如:荒凉的风景,无限的星空,波涛汹涌的磅礴气势,雷电交加的惊人场面以及直线、锐角、方形、粗糙、巨大等等,来构成崇高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特性的对象,一般地总具有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深刻过程。崇高就以这种美丑争斗的景象剧烈地激发人们的战斗热情和伦理态度。在艺术中,它的内容与主题多取材于重大的社会冲突、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其艺术形式也常常以粗犷坚硬等特色使人们不在精细的形式美上流连。总之,近代崇高在统一体中强调其矛盾、对立斗争的方面,因而它是激烈的、动荡的、不安的,而古典和谐美则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系、渗透、相辅相成的一面,所以是平舒的、单纯的、宁静的。京剧艺术由于偏向表现与时间,强调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但与近代艺术相比,它也是单纯、静穆的,即使是杨继业为国捐躯碰碑而死时的壮美,也与崇高大不相同。
为什么说梅兰芳是古典和谐美在戏曲方面的代表呢?
众所周知,梅派艺术易学难工,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梅兰芳是从总的方面来把握唱念做打各方面的平衡。据《舞台艺术生活四十年》一书记载,有一次他演《宇宙锋》,因当时嗓子不好,所以在身段表演上做过了头,事后他接受了一位朋友的批评,并说:“我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出某一部分的特点来的,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作风。这次偏偏违反了我自己定的规律。”解放前有一家报刊搞了一次“四大名旦分项技术调查”,包括扮相、唱腔、表演、武打、念白、台风等等。得扮相最高分的是梅兰芳,得唱腔最高分的是程砚秋,武打第一名是尚小云,念白第一名是荀慧生。平均分梅兰芳最高,因为他扮相之外的各项得分,多居第二位,且分数直逼第一名,这是梅兰芳“平衡发展”的最好说明。梅兰芳虽然没有什么奇特高难的身段动作,也没有什么奇绝艰险的吐字行腔,似乎易学得很,其实不然,这是“绚烂归于平淡”的表现,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表演稳重、圆熟、精确、自然,无论身段、台步、眼神、手势、水袖,一举一动,不仅姿势优美,而且与人物性格、思想、感情融为一体;他的唱腔,不以花俏、纤巧、变化奇特取胜,可无论柔曼婉转之音,还是昂扬激越之声,无不悦耳动听、感人至深,这是大巧之后的大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结果。这些都是以极深厚的艺术功力为基础的,看似易学,实则难工,更不用说做到唱念做打诸种形式的平衡发展了。
其次,难工还表现在唱念做打等表现形式在梅派艺术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浑然一体上。梅兰芳的表演从不在一枝一节上显露锋芒,而是自始至终都到达人物的灵魂深处。不仅一招一式不温不火,一腔一调和谐悦耳,而且这些都做为整出戏的一个要素,与其他的身段、表情、唱腔紧密配合,相辅相成,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使整个表演恰到好处,平中见奇,易中见难,处处与众不同,却又看不出不同为何。
梅兰芳的艺术将演员与人物、再现与表现、内容与形式、唱念与做打巧妙地组成了一个均衡、稳定、有序的统一整体。因而他所追求的美,他所塑造的人物,不是崇高艺术所具有的特征美,而是一种范本式的美。所谓范本式的美,就是恰到好处的美,就象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东家之子那样,“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太白,施朱太赤”。对此,张庚先生有过深刻的论述:“我觉得梅兰芳的艺术风格,初看似乎没有明显的特点,只觉得很完整、很美、很自然,一点做作扭捏痕迹都没有,好象本来就应当是如此的。”这种美就是古典和谐美,作为京剧这种古典和谐美的艺术的优秀典范,梅兰芳自然成了古典和谐美在京剧艺术中的杰出代表。
二、梅派艺术的历史局限性
古典美是以封闭的自然经济、素朴的辩证思维为基础的,它强调把杂多的或对立的元素组成为一个均衡、稳定、有序的和谐整体。排除和反对一切不和谐、不均衡、不稳定、无序的组合方式。它在和谐与不和谐、均衡与不均衡、稳定与不稳定、有序与无序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度。中国古代依据“执两用中”的素朴的辩证思维,把“中”看成这种和谐的唯一尺度,强调在矛盾双方中不走极端,相成相济,以取其中。凡是取其中的,就是合度、适度,否则就是过,就是淫。因之,以和为美,实质上便是以中和为美。远在春秋时代,人们就把五声谐和的音乐称为“中声”,所谓“中声之所止”,便把以“中”做为谐和的最高标准的观念,突出出来了。孔子和一些弟子也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在哀、乐、怨等情感的把握上都要求执中,反对走到“伤”、“淫”、“怒”的极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艺术,所追求和表现的就是古典主义的和谐美。《尚书·尧典》中早就提出:“八音克谐”,“人神以和”的思想。八音就是指用八种不同的质料作成的乐器,这些乐器发出的声音不同,但它构成的自由和谐的乐音却把人和神融合为一了。孔孟之道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温柔敦厚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传统诗教。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从美学观点来看,也就是理智与情感统一的和谐美。
另外,中和之美也正是梅兰芳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他在谈到唱腔时说过这样的话:“和为贵,有些炫奇取胜的唱腔,虽然致效一时,但终归是站不住脚的,同时风格也是不高的。”
随着近代开放的国际性的工业生产逐步代替古代封闭的农业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尖锐的两军对垒的阶级矛盾代替封建社会中古典式的社会冲突,随着近代形而上学思维代替古代素朴的辩证思维,随着近代的个性解放代替古代的等级专制,近代美学也逐步冲破古典的和谐美,打破了古代均衡、稳定、和谐、有序的美的理想,提出和运用对立、冲突、动荡、无序的原则,来结构和处理构成美和艺术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总之,就是以近代崇高及崇高型的艺术,代替了古典的和谐及和谐美的古典艺术。这股潮流自然影响到我们国家,影响到京剧艺术。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慷慨就义,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李铁梅的“仇恨入心要发芽”所带给观众的感受,首先都是压抑的、不和谐的、沉痛的,是一种痛感,然后才转化为快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种美就是崇高,这样的内容,中和之美是难以表现的。
作为古典和谐美在京剧艺术中的代表,梅派艺术自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比如:梅先生演过时装新戏,他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说:“时装新戏表演的是现代故事,演员在台上的动作,应该尽量接近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形态,这就不可能象歌舞剧那样处处把它们舞蹈化了。在这个条件之下,京戏演员从小练成功的和在台上用的那些舞蹈动作,全都学非所用,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势”。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苛求于梅先生的。那时,要解决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是不具备条件的。张庚先生说得好:“梅先生是大师,但他也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今天的歌舞水平比之四、五十年前不知道要高多少,那时除了在戏曲中间之外,根本没有专业的歌舞演员和团体。今天不仅各省有了职业歌舞团体,全国还有了很好的舞蹈学校和舞剧团,对于民间舞蹈和兄弟民族舞蹈的发掘整理也有了很大的成绩,这对于现代生活的歌舞化和用戏曲表现手段来塑造新人物,无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所有这些,岂是梅先生从前所能设想的呢?”“一位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是超不出时代去的,他当然有为后一辈所无法追及的地方,但文章决不会由他一个人做尽了,未来的无数艺术家,自有无尽的好文章等着他们去做。”
有人会说:梅兰芳是改革家,如果他健在,他会通过自己的艺术改革来克服这种历史局限性的。恐怕未必。
不错,梅兰芳是京剧改革的一位大师。他认为:“艺术本身不会永远站着不动,总是象前浪推后浪似的一个劲儿往前赶。”几十年来,他从未停止过改革,创造了花衫这个行当,改革了唱腔,改革了场面,改革了化妆,改革过舞台美术,对京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也应该指出,他的改革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的。
首先,他改革的客观依据本身就具有历史局限性,他常说:“一个演员必须随时注意观众的兴趣”,“观众是一面镜子,照耀着我们前进。”他改革的客观依据就是观众的反应。观众的反应,除了通过上座率和剧场效果了解外,主要通过他所结交的朋友,特别是京剧界以外的朋友,他们把观众的审美意识、欣赏趣味集中反映到他那里。对他影响最大的知交,有这么几位:1、冯耿光,曾留学日本,同情辛亥革命,参加过1912年的南北议和。袁世凯称帝时,他曾动员冯国璋反袁,冯国璋任总统,他被任中国银行总裁,这是个从封建阶层转变过来的资产阶级爱国人士。梅兰芳说:“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我在一生的事业中,受他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2、吴震修,也曾留学日本,任职于中国银行,此人博学多才,头脑清醒,是个出主意的“军师”式的人物。梅兰芳创新戏,他帮助找题材、选剧目,必要时还亲自动笔。3、齐如山,清末留学欧洲,辛亥革命后,主张京剧改革。自1912年起,以观众身份不断给梅兰芳的演出提意见,当时他已是很有声望的学者和戏剧家了。他于1914年参加梅兰芳的班社,担任编导。此外,还有诗人罗瘿公,画家吴昌硕、齐白石等。这些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高的造诣,对梅的品格、气质、艺术道路都有深刻的影响。经过他们重筛选后反馈给梅兰芳的意见,显然打着深刻的中和之美的烙印,他们不可能帮助梅兰芳走出古典和谐美的领地。何况梅对来自观众的各种意见也是要分析的,他说过,对观众的意见要分析,不能象《珠帘寨》李克用的唱词“一例全收往后抬”,因为那样就是不辨精粗美恶,就变成盲从了。与古典和谐美不相符的意见,他大概是不会接受的。
其次,他的改革为中和美所制约。这种改革强调用平衡、和解的方式解决矛盾,不强调矛盾的激荡和转化,因而它的发展是平面的循环的圆圈,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立体的螺旋。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运动观、发展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精华,但这种运动和发展,缺乏历史的指向,而且这种运动的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或者说是圆形的循环。《周易》说:“无往不复”。《老子》说:“火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这种循环的封闭性,限制了改革者的创造精神和革新精神。因而,它强调量变,不强调质变;强调相对静止中的运动,而不强调爆发式的突变,梅兰芳改革实践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主张改革要“移步不换形”。在讨论对旧剧改革时,梅曾说:“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它千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得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这种主张及其实践,发展了古典的和谐美,但用来创造崇高,比如《红灯记》中的主要审美范畴却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我指出梅派艺术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要否认梅兰芳的光辉成就和巨大贡献,我只是要说明这么一点: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古代的文化如何灿烂辉煌,它也必将为近代文化所代替。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崇高,将其引进我们的京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是有利于京剧的发展,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弘扬的——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可惜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近代崇高并不是美的历史运动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断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随着自觉的辩证思维代替形而上学思维,新的对立统一的和谐美也将否定近代的崇高。这是一种现代形态的美,它形式上是向古典和谐美的复旧,实质上是否定近代崇高之后的一种螺旋形的上升。在这种现代美的形态中,各种美学范畴又将出现一个新的相互渗透的融合,我们的京剧艺术以及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也必将迈向历史的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