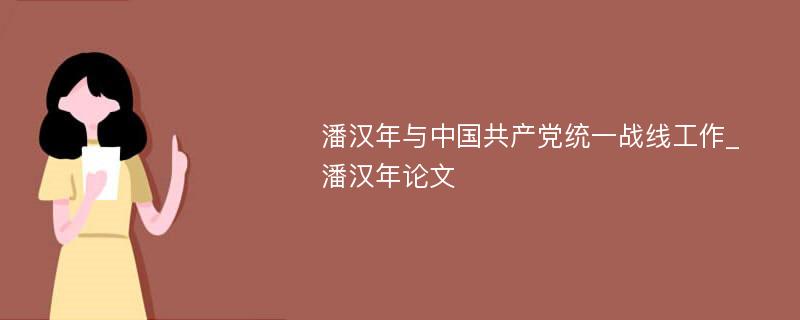
潘汉年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统战工作论文,潘汉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斗争岁月中,潘汉年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统一战线工作是其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
20年代末期,从事左翼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早在1924年,潘汉年就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潘汉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此后,他便在党的领导下,集中精力从事建立左翼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
1928年10月,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潘汉年找钱杏屯和冯乃超商量,发起组织文化界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1〕经过他的多方联络,找到沈端先(夏衍)、 朱镜我、周谷城、许德珩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于12月30日中国著作者协会正式成立。〔2〕
当时,党中央指示,“不要把这个组织的政治色彩搞得太鲜明,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3〕根据这一指示精神, 大会通过的《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集中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的政治统治以及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制,宣告成立的目的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改善经济条件与法律地位”,并且发扬与建设“中国文化”。〔4 〕这个组织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它是“革命文学小团体从分立到建成统一组织的一个过渡性组织”,是有“历史意义”的。〔5〕
现在一般的说法,“左联”是从1929年10月中旬开始具体筹建的。但是,据阿英回忆,“在是年5、6月间,潘汉年同志就同我谈过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6〕。 潘汉年为“左联”的成立作了以下努力:
首先,他在文化界党员作家中认真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精神,统一党内同志的思想。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潘汉年召集党员作家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广大党员作家立即停止对鲁迅等人的批评。同时,他还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统一文化界党员的思想,停止“革命文学争论”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潘汉年还同时发表了第一篇缓和“革命文学”论争的文章《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7〕。 文章就进步文化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应当就各种题材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这篇文章对于澄清文化界党内一部分同志的片面观点有一定的作用。
再次,潘汉年组织广大党员作家对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动员一些曾经和鲁迅进行过笔战的党员作家登门拜访鲁迅,作自我批评,消除隔阂。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多次同其他同志一起去看望鲁迅,听取鲁迅对发展进步文化运动的意见。经过诚恳周全的工作,终于完成停止内部争论,请出鲁迅担任左翼文化运动旗手的任务,从而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鲁迅曾经评价说:“潘汉年作为一个文学家还缺乏一些条件,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才能是非常突出的。”〔8〕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讲了话。“左联”成立以后,他又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 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文章谈到“左联”的任务时强调,要“加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理论的指导”,要求“左联”成员“坚决实行自我批判”,以“防止整个阵营中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9〕。
从1929年到1930年,潘汉年还参与组织领导了其他一些革命文艺团体的筹建工作,主要有:
参与发起筹备与领导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备的时间不长。在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先后派冯雪峰和潘汉年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虽然不太同意这种做法,但还是愿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 潘汉年在讲演中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10〕。
同盟成立不久,又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潘汉年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参与领导同盟的宣传工作〔11〕。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
参与领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
1930年3、4月间,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邓初民家里召开的,潘汉年、吴黎平、熊得山、朱镜我、邓初民、钱铁如、宁敦伍、王学文和冯乃超等10余人出席。会议具体商讨了“社联”的筹备工作〔12〕。会议以后,经过短期的筹备工作,于5月20 日召开了“社联”的成立大会。潘汉年、吴黎平等30余人出席。会议由宁敦伍主持,潘汉年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筹备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3〕。
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统一领导这些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潘汉年又参加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总同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8月26日, 召开了由“左联”发起的,由各个左翼文化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文总”,并推举“左联”、“社联”、“左美”、“左剧”、“书职”等团体组成执行委员会〔14〕。潘汉年又担任了“文总”的党团书记。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再到各个联的垂直的组织系统,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30年代初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三省以后,又向华北进逼。这时,国民党却继续在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则不断地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猖狂捕杀共产党和革命志士。
党组织为了潘汉年的安全,决定他离开上海。潘汉年于5 月下旬从上海抵达江西瑞金。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潘汉年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受党中央的委派,先后两次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谈判。
第一次是与十九路军谈判。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 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部队提议,在三项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10月下旬,十九路军派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到达瑞金。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来负责领导这次谈判工作,派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具体商谈。
经过几天谈判,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是为双方建立反日反蒋军事同盟作准备的。协定共有11项条款,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相互关系问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关系的初步形式。
10月底,潘汉年等又随同徐名鸿到福建省十九路军驻地,与十九路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磋商。与陈铬枢就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等问题进行了八次谈判〔15〕。还和李济深、蔡廷锴、陈友仁就政治、外交问题举行过几次会谈。此外,他还和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恢复输出输入商品贸易”问题进行了三次有效磋商〔16〕。这方面的谈判取得了具体成果。此后,不仅双方政府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而且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买卖,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还力促十九路军执行初步协定的有关条款,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
另一次是同陈济棠部的谈判。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有隔阂。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软硬兼施,迫使陈济棠同意参加“围剿”红军,并担任南线总司令,负责封锁赣粤边境。陈济棠表面上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调兵遣将围堵红军,暗中对红军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想同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1934年9月, 陈济棠派代表到江西瑞金,要求同工农红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朱德立即给陈济棠回信,表明愿意与陈部建立反蒋抗日军事同盟的诚意,并希望“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17〕
此后,双方商定在江西寻乌举行谈判。中共中央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讨论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谈判。10月5日, 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了给陈济棠所属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廷桢的信,信中写道:“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指潘汉年——引者注)、何长工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18〕
临行前,周恩来、叶剑英向潘汉年、何长工进一步说明了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同时还向他们交代了联络暗号等项事宜。
谈判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据何长工回忆,这次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 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阵的防区用陈部护照。这个谈判成果,受到周恩来的赞扬。
10月16日,陈济棠的代表向我方转达了陈为执行决议作出的三项决定:1.先暂时拨给我军弹药十余万发;2.解除封锁,恢复双方的贸易,盐和布准予放行,要我方设法在筠门岭转运苏区;3. 要求我方及早订出反蒋的军事计划。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长征的征途。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选择突围方向提供了依据。10月2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定,设有堵截红军,所以红军在11月初便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防区,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19〕。
30年代后期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 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日本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加深了同英美的矛盾,也影响了国民党的对外政策。蒋介石为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改善国共关系作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36年年初,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王明会晤,在商谈过程中,王明建议,谈判以国内进行为好〔20〕,并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潘汉年接受王明指派的任务后,同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交待了回国以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5月初,潘汉年等乘船到达香港, 他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陈果夫接到潘汉年的信后,立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冲到香港,同潘汉年会晤。张冲要潘汉年立即去南京具体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于是,潘汉年便随同张冲从香港乘船到上海,旋即转赴南京。张冲向陈果夫汇报后,决定先派曾养甫(国民党铁道部常务次长)为代表与潘汉年联系,待潘汉年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代表资格和有关谈判意见后,再到南京与陈果夫面谈。之后,张冲陪潘汉年会见了曾养甫。曾养甫要求潘汉年秘密去陕北。8月初,潘汉年通过刘鼎安排, 经党内秘密交通线去陕北。8月8日到达陕北。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
9月20日,潘汉年接受党中央的委派, 随身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离开陕北。此后,潘汉年在上海、南京等地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谈判联络。整个谈判联络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西安事变”爆发前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10月中旬,潘汉年到达上海。不几天,经张冲安排,他就会见了陈立夫。会谈中,潘汉年向陈立夫转达了中共《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对蒋介石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21〕,作了坚决的揭露与斗争。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三千改为三万,但是企图收编的反动立场没有改变。谈判实际上陷入了僵局。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张表示国共谈判不宣中止,中共可以对保留军队数目多要求些,也可以要求给一定的防地。潘对张说:我是来谈判合作的,并非毛泽东派来接洽收编问题的。又说:“章乃器等被捕更使我们对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表示极大怀疑。我是否再留此地,实有考虑必要”〔22〕。张立即向潘表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希望继续谈判。
(二)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急忙找宋庆龄,要宋庆龄帮助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宋庆龄答应了这一要求。随后她立即约见了潘汉年。宋庆龄问潘汉年,宋子文要见她,应如何应付他。潘汉年把党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办法的消息告诉她,主张她劝宋子文前往西安。后经宋庆龄安排,潘汉年又到南京在宋子文家里会见了宋美龄与宋子文。宋美龄要求潘汉年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不要杀蒋。宋子文还表示,只要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潘汉年郑重地向他们说明,据我们所知,张学良、杨虎城并没有杀蒋的意思。
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及时向陈立夫作了一通报,并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随后又向党中央报告,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飞赴西安。周恩来与两宋先后进行了多次会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谈判中,宋子文还指出,要中国共产党为他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23〕。党中央指定潘汉年承担这个任务。
(三)“西安事变”以后的谈判斗争。12月25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还命令中央军准备分五路进攻西安。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4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有损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地位,而且不利于解决西北善后问题。正当解决的办法是撤兵释张。
同日,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他将陪同张冲到西安,协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问题。收到潘汉年的电报后,毛泽东于次日致电周恩来、博古,向他们通报了潘汉年来电的内容,并提出了与张冲交涉的方针,电报针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要周恩来去南京谈判一事,指出:“两党关系之大纲领已与蒋磋商,并已明为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24〕。
同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向他通报了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各项条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以全权代表的身份与陈立夫接洽谈判,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介石、宋子文在西安与周恩来商定的各项条件,明确表示反对南京亲日派以及扣留张学良的行为。同时,他还与宋子文秘密联系,要求宋实践在西安作出的许诺。
1月上旬,潘汉年陪同国民党中央联络代表张冲去西安, 同中共中央接洽。潘汉年向周恩来汇报了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联络的情况,同时,周恩来又就同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方针对潘汉年进一步作了指示。
潘汉年返回南京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围绕着撤兵释张和划定红军防地,争取红军经费给养两大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交涉。
2月初,和平局面初步形成,但国民党中央军与东北军仍相对峙, 顾祝同部队尚未过潼关进入西安时,张冲以国民党中央联络代表名义找潘汉年,要潘陪同他去西安,向中共中央进一步接洽谈判事宜,并商量周恩来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问题。他俩在去西安途中,经过洛阳,会见了顾祝同、贺衷寒。顾祝同等提出,由张冲和潘汉年先带一人,经潼关去西安,在确保张、杨部队让他们自由到西安时,他们再去西安。潘汉年带着张冲方面的一个代表到西安向中央代表接洽后,2月9日重返洛阳,陪张冲、顾祝同再赴西安,并介绍他们和周恩来等人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磋商。
3月下旬,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谈判, 潘汉年陪同前往。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继续与宋子文谈判红军改编的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商谈政治合作问题。
至此,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为加强国共间的联系了解,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40年代为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而努力
解放战争后期,国内形势迅速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民主革命胜利在即。为了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在这中间势力集聚之地领导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从1947年开始,社会各界中上层人士陆续从内地、上海和海外来到香港。到1948年,这些人士的总数达千人以上。他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对此夏衍曾说,“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25〕。
在香港的两年时间里,潘汉年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一些重要部门的起义,为新中国的建设保存了宝贵的人材和物质财富。例如,当时担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因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强烈不满,于1948年4月愤然离职, 出国他往。在前往英国途中,经过香港,潘汉年知道后,根据党中央指示,与张骏祥、夏衍等做了钱昌照的工作,钱昌照表示同意党的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并布置了保存干部和物资事宜〔26〕。
又如,潘汉年还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上海海关起义。1948年11月,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必须同共产党联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他就派他的外甥到香港找到夏衍,了解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以后的政策。夏衍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潘汉年,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通过关系做了丁贵堂的工作,要他千方百计保护好上海海关的设备和资料,尽力使更多的海关人员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工作。同时,积极做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胜利完成了上海海关起义的任务。
此外,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带12架飞机起义,国民党空军少校俞勃(中共秘密党员)等人从南京架机起义等,也都是由潘汉年直接经办或参与组织的。
第二, 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准备, 组织各界著名人士赴解放区。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 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为了做好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指定由潘汉年和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磋商〔27〕。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等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广泛深入交换意见,讨论研究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及时沟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召开新政协问题上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了与各方的团结合作关系。
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各界爱国民主人士, 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其中大部分是从香港启程的。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李济琛、沈钧儒等大批民主人士得以安全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这件事“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由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28〕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在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潘汉年“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
回顾潘汉年同志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经历,有几个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他从事统战工作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宽,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屈指可数的。从20年代后期算起,他在这条战线战斗长达20余年,涵盖民主革命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他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多条战线奔波辛劳,成就卓著。
第二,他在长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这在党内也是不多见的。如前所述,在几次重要的统战工作中,党中央都派他出面与对手谈判联络,担当重任,这既反映出党中央对他的充分信任,也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确实有杰出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
第三,历史事实表明,他所从事的每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都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和困难,都肩负着艰巨的使命,而他都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顽强的毅力和妥善的方法正确处置,出色完成党托付的重任。
注释:
〔1〕〔3〕〔6〕吴泰昌:《阿英忆左联》, 《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2〕《海风周报》第2期。
〔4〕《思想月刊》1910年第1期。
〔5〕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7〕载《拓荒者》月刊1卷2期。
〔8〕笔者1987年8月17日访问潘锡年、潘可西的谈话记录。
〔9〕《拓荒者》1卷3期。
〔10〕《自由运动》第1期。
〔11〕《鲁迅研究资料》(四)第490页。
〔12〕冯乃超:《回忆社联成立前的一次筹备会》。史先民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第73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13〕《新思想月刊》第7号。
〔14〕《红旗日报》1930年8月27日。
〔15〕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择》第37辑。
〔16〕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广州文史资料》第1 辑。
〔17〕《朱德选集》,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19〕广州军区党史办公室:《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20〕季托夫著、杨圣清译、戴世吉校《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1〕《潘汉年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
〔22〕《潘汉年关于和宁方谈判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 年12月)。
〔2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4〕《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5〕〔28〕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回忆潘汉年》第9 页。
〔26〕夏衍1987年11月24日给笔者的信;张骏祥:《回忆解放前我与党的接触》,《新文化史料》1989年第1期。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第3页。
标签:潘汉年论文; 宋子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央军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统战工作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周恩来论文; 蒋介石论文; 陈立夫论文; 张冲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