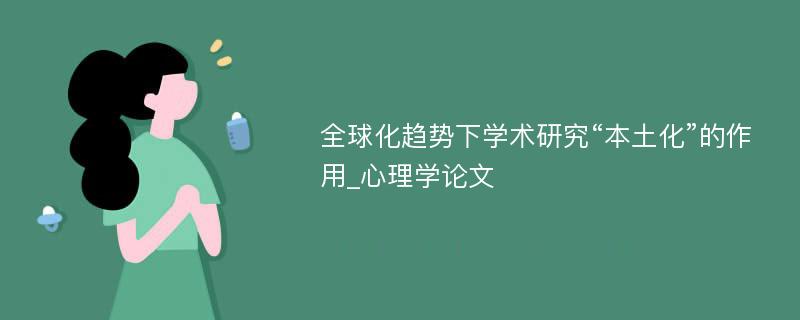
全球化趋势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戏目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目论文,本土化论文,学术研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在台湾地区,行为与社会学科的学者们关心学术“研究本土化”②的问题已有二十七八年的光阴③。在这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不少学者投入这样的学术运动之中,确实有了一定的成果④。但是,依我个人的看法,总的成果并不是那么耀眼,尤甚的是,整个运动似乎遭遇到瓶颈,甚至令人有着后继无力的感觉。譬如,杨中芳就认为,在华人世界里提倡“本土化”的先驱——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晚近即因受到台湾学术界强调所谓“国际化”之风气的影响,甚为重视国际学界对“本土化”研究的评价,力主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并向国际(其实,乃以美国为主)的学术研究潮流“靠拢”(杨中芳、杨宜音,2005:353—358、362)。⑤杨宜音即做了这样的评论:这样的导向其实只是一种跨文化研究,而非纯粹的本土化研究,因为“……写给中国人看的是同一文化影响下的差异或相同之处,以及找出其本土原因,而写给外国人看的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或相同之处,原因已经设定在文化上的不同了”(杨中芳、杨宜音,2005:357)。
我所以引述杨中芳与杨宜音对杨国枢之本土化立场的评论,目的并不在于加入她们的阵营,或乃至完全同意她们的论点,而只是希望透过她们的论述蕴涵的意思来隐示一些可能的端倪。⑥我要说的是:甚至连一向追随杨国枢坚持镇守“本土化”路线的学者都感受得到,即使如杨国枢这样一位提倡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先锋人物,到头来,也对自己坚持的主张立场有了某种程度的欲振乏力之感,甚至可以说,走到了一个必须考虑有所回转的十字路口。
其实,我真正要指陈的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酝酿,“本土化”(至少在台湾地区)所以面临一定的挑战,情形并不单纯地如杨中芳与杨宜音指出的,乃来自于华人学术界本身对自己之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期待与要求这样的结构性压力而使得其路线必须有所调整⑦,而是由内涵在“本土化”概念之中更为深层的认知因子使然的。正是这样之因子的存在,尤其并未在学术圈里获得适当的认识与共鸣,以至于使得“本土化”在诸多回道中徘徊摆荡,不但彳亍难行,阻碍多多,而且歧路纷扰多端,导使整个运动的推展倍感受挫。当然,话说回来,即使学术界的同人们对这个内在的因子有着共同的认识,却也未必立刻就可以使得“本土化”的表现成绩改观,因为,这中间又涉及一个现实的困境情势:西方的学术传统所形成的感知模式早已绵密而细腻地布了局,有着极具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毕竟,要颠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而稳固的基础,且已成为普世趋势的感知体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作为关心学术的基础问题的非西方社会学科的学者,我总认为,我们有义务认真思考这样的课题,尽管,现实上,我们或许并没有能力改变整个学术界早已几近被西方学术的特定感知模式完全侵蚀的现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情形极可能就是如此。其实,除非是基于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感情,我们并没有坚固的理由必须对西方学术的感知模式怀有敌意,以为非得予以完全颠覆不可。
二、经验实征思维模式下的“研究的本土契合性”说与其衍生论说
累积了数年的思考与诸多经验实征的研究成果,杨国枢为“本土化”提出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说法:研究的本土契合性乃是研究本土化之程度的判准⑧。至于什么才是“研究(的)本土契合性”,晚近,他整理过去持有的看法,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
不论采用何种研究典范、策略或方法,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课题选择、概念厘清、方法设计、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及理论建构)与研究成果(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与所建立的概念、理论、方法及工具),如能有效或高度显露、展示、符合、表现、反映、象征、诠释或建构被研究者之心理与行为及生态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族群的脉络因素,此研究即可为具有本土契合性。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的本土契合性,只有具有足够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才可称为本土化研究。以本土化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才可称为本土化知识。(杨国枢,2005:31)
在这个定义当中,不管它指涉的是被研究者之心理与行为所赖以形塑的生态、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或族群条件中的何者,杨国枢甚为强调呈现在被研究对象世界中的所谓“脉络因素”,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为了突显此一因素可能彰显其符合“本土契合性”的要义,杨国枢回到他在1997年对“研究本土契合性”所提出的分类,强调其中的两类:脉络化本土契合性(contextualized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CIC)与非脉络本土契合性(decontextualized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DIC)(参看Young,2000)。前者乃用来意指此一涉及生态、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或族群条件的“脉络因素”。他说道:
CIC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不但能有效或高度显露、展示、符合、表现、反映、象征、诠释或建构所研究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能有效或高度显露、展示、符合、表现、反映、象征、诠释或建构所研究之心理与行为所处的生态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族群的脉络因素。CIC亦可称为依赖脉络的本土契合(context-dependent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杨国枢,2005:31)
依循此一说法,杨国枢指出,他在1997年的论文中虽提到“脉络契合性”,但却未涉及CIC此一“依赖脉络契合性”。继而,他区分了“脉络契合性”与CIC此一“依赖脉络契合性”的不同:前者强调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要单独⑨与所研究之心理行为的脉络因素相契合,后者则强调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要与所研究之心理行为及其脉络所形成的整体组合⑩相契合(杨国枢,2005:31)。准此,二者的区分重点乃在于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要与所研究之心理行为及其脉络到底是以“单独”或“整体组合”的方式相契合的问题。尽管,两者之间如何区隔,作者并没有明确地予以阐明,但是,从其文脉来看,杨国枢在后来的论述中特别强调的,显然是舍“单独”,而以“整体组合”方式来谋求契合的课题。
依我个人的见解,于肯定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可以“单独”地与所研究之心理行为及其脉络相契合的前提下,杨国枢能够更进一步地强调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及其脉络所形成的“整体组合”,确实是碰触到了“本土化”的核心意涵,有了更能掌握人们身处之环境的“历史—文化质性”可能开展之意义的契机。然而,这样的说法是否真的妥帖地具有这样的契机,我个人仍然存有疑虑,值得在此进一步加以探究。不过,在探究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如何安顿他所举出之所谓DIC此一“非脉络本土契合性”的类型。他说:
DIC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能有效或高度显露、展示、符合、表现、反映、象征、诠释或建构所研究的心理与行为,但不必同时探讨其所存在的脉络因素。此种研究认为心理行为与其脉络不但在概念上是可以分割的,在实征操作上也是如此。研究者可以将所研究的心理行为视为研究的焦点,将其脉络视为该心理行为形成、存在及维持的既有条件,在研究心理与行为的本身时,其脉络可以暂时存而不论。……在此类研究中,心理行为现象是焦点,脉络只是静默的既存因素。研究者的主要责任是使其研究活动及成果与所研究的心理行为本身之契合性最大化。基于以上的特征,DIC也可以称为独立于脉络的本土契合(context-independent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美国的本土心理学中的主流心理学研究,大都采取此种本土化契合性,其中采取实证论与后实证论两种研究典范的美国心理学者,尤其偏好从事非脉络性的研究。采取这两种典范的华人心理学者,亦可从事非脉络化的本土化研究。(杨国枢,2005:32)
经过这样简扼的引述可以发现,在杨国枢的心目中,研究“本土化”的取径可以是强调“脉络”,也可以是把“脉络”悬搁不论。对于后者,只要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切确”地保证“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课题选择、概念厘清、方法设计、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及理论建构)与研究成果(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与所建立的概念、理论、方法及工具)”是掌握了心理行为现象本身的“本土性”,那么,(特别采取实征研究策略地)以“单独”(而不必是“整体组合”)的方式来探讨“变项”间的因果关系,就具有了完成“本土契合性”的正当性。准此,重视“整体组合”的“脉络”研究,只是完成“本土契合性”的一种可能的另类策略。顶多,它只是更具有说服力或更周延而已,并非绝对不能不具备的考虑要件。
在此,我愿意特别提醒,杨国枢这样主张“以‘单独’的方式来探讨‘变项’间的因果关系,就具有了完成‘本土契合性’的正当性”说法,诚如他自己明白指出的,是以“美国的本土心理学中的主流心理学研究”为基点来确立的。在这样的认知中,有一个极为根本的现象必须特别指明:美国作为领导整个世界学术研究之转向的第一强国,它的研究基本上即是美国“本土”的,根本就没有如边陲社会一般,有着“本土化”的提问,并让它成为议题的焦虑性需要。准此,对美国心理学家来说,美国的心理学不管主流与否,基本上可以说都是“本土”的研究。只是,在“强调经验实征之自然科学肯确普遍真理可证成的科学迷思”与“美国学术典范具绝对支配优势”此二现象的交互影响之下,美国的“本土”研究成果偷偷地越子位,特别是被留学美国之边陲社会的知识分子(或至其他西欧中心社会者可能亦然)供奉成具普世效准的知识,而以之作为从事研究的依据典范。(11)所以,“以‘单独’的方式来探讨‘变项’间的因果关系,就具有了完成‘本土契合性’的正当性”这样的说法,原则上只适用于具有主导优势的中心社会,并不能适用于有着“本土化”焦虑的边陲社会的学术场域,因为,这样的“本土化”焦虑所以产生,基本上,即因边陲社会的学者们日渐意识到中心社会的诸多“本土”研究因居绝对优势的地位,导致在认知上产生了严重的越位,而被当成是具普世效准的知识典范。
总之,当我们对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质性”予以“脉络”考虑,并将其看做只是完成“本土契合性”的一种可能另类策略的时候,无疑,它将有着“矮化”“历史—文化质性”对确立研究“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能具有不可或缺之深层意义的疑虑。我个人认为,杨国枢所以有着这样的主张,其中内涵一个至为关键的观念。简单说,这个观念即预设一个外在于个体之可观察(乃至可测量)的客观现象是“如实地”存有着。基本上,这样一个充满着实证主义色彩的认知立场,首先乃确立了现象的客观可征性,进而,纵然承认有着所谓“历史—文化质性”,这个质性乃被认为可以(也必然地)从可实征的现象所彰显的种种特征中“自然”地呈现出来,我们大可不必(也不可能)大费周章地来加以预设。易言之,研究的“本土性”既不是来自于研究者本身参酌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经验体验来形构“历史—文化质性”的想象预设,也并非关涉到语言的文化意涵问题,而是对于可实征的经验素材是否有了适当且客观的“契合”掌握。于是,“本土契合性”为的是确立科学的客观性,涉及的是后设可征性的经验真实的问题。“脉络”的考虑与否以及如何选择和定调的种种设想,不是形构和证成“本土契合性”的必要条件。提出“主体对‘历史—文化质性’的设定乃确立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就是不可想象,更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主张了。
这些年来,另一心理学家——黄光国教授(1999a,b,2005)从方法论的立场来审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他力主研究本土化还是要有一定的普同一致的“规矩”作为依据,而这一个普同一致的“规矩”的最终依据即是西方的科学哲学。他即这么说道:
科学哲学(则)是西方学者反思其科学活动所找出来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懂游戏规则,当然也可以“从做中学”,用“土法炼钢”的办法,慢慢揣摩,悟出其“窍门”所在。可是,我想强调的是:科学哲学毕竟不同于“禅门心法”,非要靠“身体力行”,才能悟得其中三昧。科学哲学只不过是西方科学家建构其“微世界”的“游戏规则”而已。倘若我们学会这些“游戏规则”,便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为甚么舍大道而不由,非要坚持“土法上马”,靠“两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摔得鼻青脸肿,还不肯悔悟?(黄光国,2005:76)
至于西方科学哲学传统中的众多“典范”,黄光国独独欣赏“建构实在论”,且认定这是当前西方科学哲学中最值得依靠的游戏规矩,可以用来作为对研究“本土化”的推动予以定调的方法论依据。他即说道:“……我从西方科学哲学的视阈,以‘建构实在论’的思想作为主轴,检讨了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方法论问题,希望能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奠下坚实的方法论基础”(黄光国,2005:75)。至于如何运用“建构实在论”来彰扬心理学本土化,他认为:
从建构实在论的角度来看,“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最主要的意涵之一,便是要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技术性思考”,建构各种“理论”或“模型”的“微世界”来描述:在其文化遗产影响之下,本土社会中的人们如何在其生活世界中和不同的社会对象玩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根植于其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又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黄光国,2005:69)
以此为基础,黄光国更进一步地主张采取所谓的“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即视问题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研究典范,而非以“本土/非本土”的两分方式来判定心理学研究的好坏(黄光国,1999a,b;2005:71)。
很显然地,既然在黄光国的心目中,“建构实在论”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典范,其可能蕴涵并推衍出来的是使得“心理学本土化”最主要的意涵之一在于成就西方社会科学的“技术性思考”,那么至少单就方法论的立场来说,“本土化”的问题更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因为“建构实在论”之“任何实在都是建构的”这样的基本命题已充分保证了“本土化”必然是内涵在“建构”之中的。于是,“建构实在论”本身即自动地保证了知识“本土化”必然是可能的。在此情况下,研究者自然就不必时时刻刻地把“本土化”的意识放在心上,而“本土/非本土”两分的思考方式也就跟着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作为“技术性思考”的方法论,“建构实在论”的要旨于是乎并不在于提供给研究者任何具体而可行的实际研究操作技术或策略或适当的概念语言的选择,而只是作为一种导引研究的基调,提供基本立场,如此而已。简单说,这个立场是:“肯定”任何社会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者以自己建构的“微世界”观来逼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语言游戏。因此,就对人的心理行为与社会现象推动实际观察研究的立场而言,整个问题乃转而在于,我们如何判定这个具语言游戏之特质的研究者的“微世界”观具有多大的正当性与价值(或谓其意义何在),可以作为逼近一般人之日常生活世界的依据?显而易见地,就此角度来看,“建构实在论”本身并无法有效地提供任何具特定历史—文化意涵的意义,更罔论对人们理解自己的处境有着怎样的启发作用。换言之,“本土化”的问题核心,并非如黄光国认为的,被安顿在确立西方科学哲学(特别指涉“建构实在论”)于方法论上作为游戏规则所彰显的绝对必要性。况且,情形是否即是如此,本身即有讨论的空间。依我个人的见解,研究的“本土化”毋宁有着更为深层的课题值得提问。除了方法论之外,它尚涉及认识论乃至存有论的层面;或说,至少必然涉及一些具特殊“历史—文化质性”的实质概念与经验命题。
进行到此,让我再举另一位推动“本土化”运动不遗余力的社会心理学家——杨中芳教授的见解来予以阐述,以彰显诸多致力于“本土化”运动的先驱学者们常持有的认知模式。在研究华人的心理行为时,杨中芳相当重视所谓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杨中芳,1993a,b;1999;2005)。以此一强调为基轴,她采取相当务实的态度罗列了一系列进行“本土化”实征研究的策略:
1.以实际观察当地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呈现的现象为研究素材,从中找寻值得做的研究问题;
2.用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及惯用的概念、想法、信念及经验来帮助审视、描述及整理问题中所显现的样式;
3.发掘当地人运用以彼此沟通及相互理解的意义系统,从而用之理解所呈现样式背后的意义;
4.凭着这一理解,提出一套对研究问题的解说或理论;
5.研制适合探研当地人的程序及方法;
6.来对解说或理论进行实征验证、延伸或推广;
7.从而建立更能贴切地理解当地人及对他们更有用的心理学知识。(杨中芳,2005:100)
根据上面的引述,杨中芳认为,最能具体体现重视“文化/社会/历史”脉络的所谓“从叶中求根”的研究策略,莫过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包含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以及对他们行动的解释等)中直接去寻找可以理解及解释其具体行动的背后的意义系统及意义。顺此策略而下,对“如何把‘文化/社会/历史’与个体的具体行动扣连”的策略选择,很自然地就是“个体生活在文化之中”这一有关“文化与个体之关系”的策略(杨中芳,2005:102;同时参看杨中芳,1993a,1999)。无疑的,杨中芳这样强调“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与人们行动背后的意义系统的主张,多少隐含着“本土化”乃具有着黄光国所认为之语言游戏的特质。尤有进之的,这更是指陈着,充分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际应对其“文化”脉络的行动策略是“本土化”的核心议题。平心而论,这样的主张已经碰触到了我心目中之“本土化”的核心要旨,即“历史—文化质性”之选择和确立的问题。只是,对此,她并没有提供更详细、系统且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而仅以上述实征研究的方法纲领给予我们一些步骤性的指引。至于她为“本土化”赋予肯定的理想期待标杆——“贴切地理解当地人及对他们更有用的心理学知识”,亦即呼应杨国枢所关切的具实证色彩的“契合性”问题,则只有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了。
三、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的“文化间际交互参引”说
与杨中芳一样,余德慧(1997)也强调“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对“本土化”的重要性。但是,不同于杨中芳所呈现的实体论立场以及把“本土化”定位为方法论之课题的主张,余德慧认为,“本土契合性”涉及的,基本上是以语言运用的文化意涵为基调所形塑之“陈述”性论述系统的发展问题。对此,余德慧提出所谓“历史救济”(12)的说法来加以申论。
作为心理学者,余德慧认为,心理学本土化的根本问题并非在于方法论或认识论上面出了问题,而是用来描绘现象的语言系统失妥。易言之,“本土化”的根本议题在于选择“适切”的语言来对所欲处理的对象予以陈述,因此,关键在于运用怎样的语言才得以宣称是“适切”(或谓“契合”)。对此一议题,余德慧指出:一则,借用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术语言与人们在本土经验上的感知模式脱了钩;二则,本土的文化场域又没有凝铸适当的心理语言,得以“适切”且具反身性地来阐述人们的心理状态。显然,在这样的双重“失协”情况下,企图回到传统对人们行为与社会现象所可能提供的“理想”论述典范[如儒家思想本身或其表陈之诸多核心概念(如孝道)的理想字义内涵]来作为研究“本土化”的切入点,基本上是一种以零星打点来进行的游击战方式,并无法充分掌握当前的人们实际对现实世界所做之行为反应的整体文化意涵,因而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无效的。
针对这样的现象,余德慧认为,一个比较恰适的做法是,先与传统的经典论述典范决裂,直接回到一般人在具历史向度的日常生活场域里实际展现的种种现象,特别是被经典论述典范刻意不说出或无意间予以忽略之“未说”(unsaid)且“先见”(pre-understanding)的文化体现部分(如问卜疗病)来加以考察,其重点乃在于从中凝铸足以反映人们之生命韵律的共享“文化样态”(13)(余德慧,1997:268;同时参看余德慧,1996)。因此,使用的语言不能完全受制于西方既有的心理学概念;它也不能被当成只是一种表达概念的工具;更不是内在于知识论的。毋宁说,研究时所使用的语言需要从历史的空隙之中去寻找、挖取(所谓“救济”),以俾能够展现本土的蕴生力,发挥文化特有的历史效果(余德慧,1997:241)。
顺着这样的思维轨迹,文化指涉的不是一个定型不变的静态实体,而是一种不断流动、更易的生成过程,尽管相对地来看,其中的“核心”成分可能持续存在,并没有明显地易动。准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东/西”两分思维模式来理解“本土化”现象,应当采取不同文化之间交叉互映的观念来接近。在这样的思维架构下,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更具体地为“文化间际交互参引”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综合阐述。其说法相当具有启发性,值得在此引述。(14)
首先,他们指出:
本土化之可行并非在本土传统论述的范围打转,而是在现代全球化知识的回流里,为己身文化取得陈述的视角,而这视角的取得则在于将己身文化的差异加入新的元素,而不是将他者(强势)文化直接覆盖于己身文化,使己身文化逐渐消退或被取代,亦即,他者文化一旦输入于己身文化,必须加以细切、打碎或混音,被本土陈述消解,这无关原来输入文化的“原典”正确与否。然而,实情经常是学界以他者文化是否可以增益本土文化为原则,径行接枝工程。严格来说,既日“接枝”,其实是移花接木,误识而已。(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b:12)
于是,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再度肯确,唯有以本地场域为本来发展陈述系统,才是真正所谓“本土化”的栖居所在;而所谓“本土契合性”的所在也得依靠“陈述”这样一个形式来确立,并非实证论者所谓的“实证的契合”(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b:12)。然而,实际上,我们如何能够如他们三人所愿的,避免对他者文化(在此,特指西方的现代学术典范)仅以“增益本土文化”为原则来进行单纯之移花接木的接枝工程,而得以让他者文化输入于己身文化后,起了细切、打碎或混音的作用,以俾使被本土“陈述”融化呢?
对此一有关心理学“陈述”的文化生成,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提出了所谓的“双差异折射”理论。对此,他们是这么说的:
文化间对话逻辑的观点在于:将他者的观点吸纳于关系项,使得他者文化所显示的内部差异系统被限定在其文化的意涵,不得溢出。然而,作为关系项的位置会是一种移动值,其差异强度与差异方向不应该只有“同一”(“华人文化也是如此差异着”)与“对立”(“华人文化则有相反的结论”)两个范畴,而是去探讨两种同体异形的差异(homological difference);亦即我们把两文化都视为独立的相关项,他者文化所获得的差异体系不应影射任何本土系统的差异,就如同橘子系统不介入橙子系统。本土文化的差异体系应当被提出,拒绝将他者的文化做平移吸纳,而是独立获得其自身差异的逻辑条件,然后才将两套差异的“形式”、“逻辑条件”以及知识论做比较,这时我们才透过比较指出本土文化的逻辑生成。这个知识生产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双差异折射理论”。(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165)
接着,他们以此理论描绘着“文化间际交互参引”的意涵和实际操作的基本策略原则,并提出这样的说法作为总结:
首先,文化差异绝不能一下子就跳跃到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必须确保各文化内部差异的本体性;也就是说,一个文化内部差异首先应是“意义生产的差异”,那是各个文化在自身的生活处境里头所孕育的“意义生成”,不能移植的部分。此差异使透过各文化内部自身的其他“后设系统”互相对差出来,例如“语言系统、后设语言系统”相对于“处境生成与建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这些差异系统以块茎(Rhizome)(15)的方式,以各种异质对立方式彼此相依相制,而形成协韵的生成。既然文化内部的差异系统是无可化约的,因此,文化内部的差异必须以自身为本体,其意义收成之脉络以系谱学的方法获得,而无法直接以与他者文化之交互参照来获得。(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165-166)
四、“本土化”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实践
行文至此,似乎已到了必须表明我个人对于“本土化”之基本观点的时刻了。总地说,基本上,我分享着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三人的立论。其实,他们所提出之以“文化间际交互参引”的“双差异折射”理论来阐述具“文化生成”意涵的“本土化”过程,与我个人过去十多年来对“本土化”的认知和主张不谋而合,只是他们以更为抽象的概念语言来予以陈述,为我的见解做了更为理论化的进一步脚注。(16)底下,就以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的论述为基础,对我个人过去提出的“本土化”主张再做一番整理,并从中粹炼出一些可以进一步思索的论题,尤其是确立探索的基本立足点和方向。
首先,我要再度特别指陈的是,揭橥有特定“客观先存”事实的实证主义观点,并不是我心目中为“本土化”议题设定的提问方式,因而,既然“契合性”依然可被视为重要的课题,问题的关键自然就不在于如杨国枢说的:
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也就是经由这样的一套共同因素与机制,才可保证当地心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所建构的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能够高度适合当地民众之心理与行为。(杨国枢,1997:77)
在这样的认知下,连带的,“本土化”的意涵自然就不会是企图透过对所谓“地方殊性”予以评比以来累积知识,并为获致自然科学一向强调的普同性铺路。再者,“本土化”涉及的更不是仅及于方法论的层面,容或这可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向度。更重要的毋宁是,它尚触及以语言(特别语意与语用)为基调的认识论,尤其有关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的根本问题。(17)
尤有进之的,既然“本土化”关涉到语言的问题,它也就不得不牵涉到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形式的文化演进意涵与其引生的感知模式问题,而这基本上是一个关涉到具知识社会学之反省批判的实践课题。准此立场来看,“本土化”本身即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是,它是发生在学术界的论述现象。更具体地说,这乃意味着,“本土化”基本上即是针对着“现代化”而至“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一个认知主体(特指研究社会与人之行为现象的学者)在经营知识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具“历史—文化质性”之回转反省工夫的社会实践行动。因此,“本土化”是一个以特定历史与文化条件为基础来省思的特定“社会”问题,涉及的是研究者的认知取向与再概念化(或谓二度诠释),包含着诸如议题的选择、陈述的设定、概念的铺陈、语言的掌握与诠释的取向等等的课题。在这中间,人们强调的是形塑并确立得以让人们(特指研究者)逼近世界的一种身心状态、文化感知模式与对时代氛围的适当定位(与选择)。其中,我们最可能且必须做的是,从中爬梳整个可能内涵或衍生的核心文化意义。
在这样的认知架构下,所谓知识社会学的取径,最重要的,乃在于帮助我们掌握潜藏在问题意识背后可能引生的特殊(特别是具“症候”潜在性的)“历史—文化质性”;连带地,更是希望借以有效地理解“本土化”可能回转出来之具摩荡攻错作用的“治疗”内涵,尤其,在予以推动时,它呈现的关键要旨。显然,在这样强调“历史—文化质性”之意义转折的情况下,“能否客观而高度契合”地掌握被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体现的“本身”并不是考虑的重点,甚至,这样的提问根本就不可能回答,因为我们既然无法确定被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体现的“本身”确实是(或应当是)什么,自然也就无从论及“能够客观而高度契合”的期望了。
假若我们把“本土化”定位为一种具实践行动性质的社会现象本身,并采撷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予以关照的话,它首先碰触到的是,在“传统/现代”与“本土/外来”的双元力量的双重攻错下,边陲社会的文化体现所面临的课题。就此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无疑地乃呈现在底下所标示的历史现象中:19世纪以来,以西欧与北美世界为代表的所谓中正社会夹持着优势的军事力量向亚、非、中南美等世界拓展,以谋求政治与经济利益,并同时宣扬基督上帝的理念。为了免于灭亡或遭受中心社会的完全宰制,许多边陲社会的人们认为,向中心社会学习以科学理性为主调而形塑的“现代”(特别是有关器用的科技)文化,乃自救必要之途。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中心社会的文化产生了一种优势影响的扩散作用,导使边陲社会的人们逐渐发现,他们所应向中心社会学习的,不能仅止于原本强调的科技器用面向,而是同时还得学习种种的制度形式。之后,他们又发现,应该学习(且深受影响)的根本乃在于文化思想、基本认知模式与行事理路等等涉及人们之意识和态度的深层面向。(18)这么一来,现实地看,一路学习到底,最后导致了边陲社会原本的整体文化传统产生了几近完全崩溃的情形,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主调几乎单向地朝向西方现代文明倾斜着。显然的,当这样的情形波及知识体系的营建时,我们不免发现,绝大多数的知识(特别是所谓的科学知识)都是自西方倾销而来的不折不扣的“舶来品”。
在这样的历史格局里,西方中心社会带给非西方边陲社会的一连串知识典范,基本上是一套极具体系性的“整体”,包括最基础的概念表意、基本预设、思考模式、理论架构、方法铺陈,乃至现实问题的认定、议题的选择等等,彼此之间莫不环环相扣,相互呼应。在这样几近完全倾斜的历史场景里,边陲社会学习到的知识,无疑地只是发生在西方特殊历史背景(尤指启蒙时期以后)之下的文化产物。透过“中心—边陲”不平等关系所导引的优势文化的倾斜扩散作用,这套来自西方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典范,遂成为看起来具全球“普同性”的知识体系(以及社会现象),有着确立绝对真理之后设性的现实效准作用。然而,在任何边陲社会里,本土(尤指传统)文化的力量都会有磁滞作用,尤其是有着悠久文明的社会(如中国与印度)。只不过,面对着外来之西方现代的系统化知识体系,本土传统文化的元素经常是以非系统,且理所当然而不待言说的姿态出现在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种种生趣活泼的文化故事(如谚语、儿歌、道德箴言等等)(19)。
如此一来,显而易见的,经过了一百多年之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劲冲击,当前边陲社会实际体现的文化现状,其实已是经过“外来(西方)现代”和“本土传统”两种文化彼此相互搓揉攻错而形成的一种混合的现代“本土”形式。假若允许我们相信文化有着所谓的历史原型的话,今天存在于边陲社会里的种种文化体现,已经看不见任何的纯粹历史原型(不管是外来或本土的)了。况且,特别就语言内涵的社会特质的角度来看,对来自西方之诸多基本概念的学习,边陲社会里的人们原本就极为缺欠让他们充分掌握西方文化之元神的认知能力与社会条件,因此,他们更是往往学不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原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冲击日久后,边陲社会对于本土自身的传统文化更是难以拥有回归历史原貌的能力,况且,现实地来说,也未必需要如此。总地来说,若说这是边陲社会的困境,那么,我们有的只是,在同时对外来(西方)现代与本土传统进行文化意义的移植时,总是因为时空背景的不同,不断有着几乎无以避免的双重误认与误释。
五、“全球化”下“本土化”所具文化解码的意义
今天,整体人类面对的现实是,以西方之“现代化”文明为主轴所经营出来的“全球化”已是,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更是导致边陲社会采撷西方现代的知识,乃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条件。在如此必须同时对“外来(西方)现代”与“本土传统”进行文化意义的移植,且误认与误释又无以避免的情况下,“本土化”基本上即是,也必须是从事着如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所指出的意义的“同质化”。在此,“同质化”乃意指“‘意义的朝己翻转’,亦即他者的文化生成被我夺取,我将之翻转成为‘我的视阈内部的意义生成’,而不必顾及其原来的意义脉络,也就是对他者文化的独异处的否定”(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166)。
依我个人的看法,情形显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意义的朝己翻转”的“同质化”现象,不只发生在与外来西方现代文化交接之际,在回溯本土传统文化的当刻也一样地出现。诚如前述,这样的意义平移,不管针对的是外来现代的或本土传统的,总是把原有的文化意义结构予以冻结,乃至破坏,而且,往往也同时将自身之经验如何被说的元神掠夺掉(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166)。情形是如此的话,问题的重点毋宁地乃转而在于,我们如何“适当”地同时对外来现代的或本土传统的予以“移位”,以来进行一个属于“本土现代”之自身文化的意义生成,而有着一定的历史(尤其,当前此刻的文化)意涵,用来启发人们的想象与期待空间,以开创更合理而适切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
在此,我个人同意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的说法。他们指出,文化间的差异不是用来区隔,而是攻错。“所谓‘攻错’指的是两个文化之间在相关领域上有所对应,但是对应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可以提供相互观看的斜角,也就是透过他者文化与母文化的不一致,产生母文化的问题意识,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成为思考的对象,并借着他文化的错位观点,对母文化的物象化过程进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机制”(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187)。
显然,以外来的现代西方概念来对照、挤挖、凸显本土的传统想法,乃是一种如余德慧(2002:172—173)与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163)所说的“文化间际交互参引”之“透过移位到外边,观看自己文化知识的性质”的策略。其中,与他们的立论不同的是,我个人采取接受历史现实的立场,特别强调外来之现代西方的诸多概念(与命题)在整个知识建制过程中确实具有着优势导引的位置,而这是寻找回转的分离点时极具现实之关键意义的决定枢纽。换句话说,就概念(与命题)使用的角度来看,“本土化”的首要功课是,在参照(且不可能完全舍弃)本土传统性所留存的文化磁滞效应的前提下,对来自西方的诸多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与基本命题进行具“历史—文化质性”的反思,以分辨其用来理解和解释本地社会与人们之行为时的“适用”性。一样的,这样的分辨也应当同时适用于检讨来自本土传统的概念与命题,以重新判定其运用于本土现代的“适用”性(20)。
在对概念与命题进行分辨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提示的是,不管整个检讨与判定的指向是外来的西方现代或本土传统的概念与命题,有一个基本工作是必须做到的,即我们都需要对概念与命题所承载的文化殊性的高低(或强弱)有所区分。简单说,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或命题本身内涵的文化质性承载着不同程度的历史殊性,需要加以区辨,否则,会产生严重的误识与误用,而有了“适用”性的问题。譬如,“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乃发生在西欧历史场景中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一个承载着“高”文化殊性的概念,一旦运用来分析或理解非西方的边陲社会时,着实有着“适用”性的疑虑。相反地,诸如“社会化”(socialization)或增强(reinforcement)的概念,基本上具有“低”文化殊性,用于描绘任何社会中人们的学习历程,相对的,可以说是“适用”的。同样的,过去费孝通(1993)提出诸如“差序格局”与“同心圆的社会关系”来作为刻画过去的中国社会的特质,在当时,容或是有着一定的贴切适用性,但是,用来刻画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大都会地区或某个特殊阶层),是否依旧有效或必须做修正,就有着再斟酌的必要了。因此,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就经验实征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对概念与命题本身以及其承载的文化殊性进行分辨判定时,依据的基本参照准点既不是过去的本土,也不是西方的过去或现代,而是内涵在“本土现代”中已呈显出文化“混合”特质的“现在性”。无疑的,对概念与命题本身以及其承载的文化殊性从事具时间序列意义的考古学或系谱学的考察,固然确实有助于我们掌握特定概念与命题的基本意涵,但是,到头来必须紧贴这个在经验面向上可征的“现在性”来进行理解与剖析,才可以说是整个“本土化”过程不可更易的基轴。余德慧(2002:172)与余德慧、林耀盛、利瓦伊伦(2007a:164)所说的“文化间际深度的交互参引渗透”,即为了丰富任何讨论到之概念与命题的此一“现在性”的知识内涵。
显而易见的,经验可征的“现在性”确立了本土文化的独立性。纵然它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底蕴而获得了一定的神韵,它所生成的意义毕竟还是人们自身在本土的特殊生活处境里所孕育出来的,是不能移植,也不可化约的部分。特别对边陲社会来说,这样的文化“现在性”的呈现,基本上乃反映着“外来现代”与“本土传统”两种文化基素以某种特定方式纠结混合的成形体现。它深植在人们潜意识深处,构作出一堆极为“吊诡”的基本思维模式与行事理路。准此,追本溯源地对其背后之哲学人类学存有预设的历史原型有着评比性的理解,并进行文化译码工作,遂成为一项必须探究的严肃课题(同时参看叶启政,1997)。
内涵在“本土化”中的文化译码,不只是以经验实征的方式针对文化的“现在性”进行事实性的确认,更是一项可能为人类未来文明架设理想的自我期许工程。易言之,“本土化”乃为(学者)知识分子设定了一种由自身自地处境出发的文化实践活动。在今天这样一个已明显“全球化”的时代里,此一以(学者)知识分子为主的“本土化”实践活动指向的,当然不会只是局限在谋求“契合”本土区域特性的经验实征考虑上面,而是进一步地期冀为西方现代性优势所主导的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注入另一股足以导引“质变”的回转力量。就此历史期待的角度而言,“本土化”意涵的,不只是针对特定区域之“现在性”的现实经验探索,更是对未来“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具“期待”性质的知性思考。换个角度来说,诚如在前文中提到的,它既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潜藏于当前人类文明(当然,特别指涉西方的现代理性文明)中之诸多问题意识背后的特殊“历史—文化质性”(特别是具潜在“症候”性的部分),连带的,我们更能借此回转出具“摩荡攻错”作用之“治疗”意义的文化内涵。
六、“本土化”具“留白”工夫的社会学意义——代结语
西欧世界出现以所谓“现代化”的形式来对人类予以“启蒙”,发展至今业已有两百多年了。特别是在科技理性的几近垄断支配下,固然,历来,许许多多的人们认为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带来无比的“进步”景象,但是,颇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人类整体文明似乎已面临着严重的灾难威胁,他们尚且不断地谋求改进与补救之道。在此,姑且不去细论问题是否严重以及灾难是否即将来临等等的经验可能性的问题,而让我们假定人类整体世界确实已有问题的存在(诸如能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地球的温室效应、人性的贪婪与奢华浪费等等),是一项不争的事实。准此,单就人类寻求理解、解释与化解之道的现实角度来说,我们固然不能,也不愿轻率地下结论说,西方人已经支付的努力是不够的、理解与解释是有误的或乃至提出的方案是无效的。但是,有一种现象却是常常可以看到的:针对“现代理性”所带出来的历史—文化场景而言,西方人基本上是“局内人”,长期惯性地承受了一个庞大而悠久之文化传统[特指来自希腊、罗马与希伯来的文化以及笛卡儿(Descartes)的主客双元的哲学观]的体系性的熏陶,他们对整个文明早已有着相当定型的感知模式与行事理法,以至于在面对当前的“困局”而谋求化解之道时,视阈往往被既有之感知模式的理路所限囿,缺乏孕育具颠覆性的“另类”回转契机。
然而,对具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非西方之边陲社会的人们来说,相对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他们原本就具“局外人”的特质,承受不同的历史—文化经验,而这些正是使得他们有着蕴生具回转作用之“另类”感知模式的机会。当然,此种机会要能蕴生,有一个条件是必备的,即此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特指学者)必须同时对本土传统与外来现代的文化基素,具有批判反思的意愿和能力。然而,一两百年下来,非西方之边陲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正在于孕育这样的批判反思意愿,尤其是能力。情形特别严重的是,诚如前文中陈述的,整个西方现代文明具有的压倒优势性早已促使整个边陲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往西方世界倾斜,这使得人们纵然对西方现代性有了批判性的反思,在现实里,还是难以有效地颠覆西方文明在边陲社会所搭构起来之绵密细致体系的基架,而让他们有了营造另类社会形态的可能契机,而这恰恰成为整体人类所面对的共业。
尽管,过去的历史显示,针对西方现代性引生的历史场景,非西方的边陲社会确实一直缺乏透过批判反思来颠覆以营造另类文明的实质机会,而且,甚至,在可预期的未来也未必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基本上,透过“本土化”的努力尝试,来自非西方边陲社会(特别是其文化传统)的“另类”感知模式,确实可以用来作为检讨内涵于西方现代性里的“历史—文化质性”(如“理性”所衍生的矛盾两难困境)及其可能潜涵的文化“症候”基轴,并借此回转出有效的“治疗”方案。在此,让我再说一遍:在人类未来文明必然走向“全球化”的不可逆趋势下,这正是“本土化”对探索“整体人类文明的发展应当往何处走”此一极为严肃的课题所具有的历史“使命”。
在我的观念里,对西方现代性内涵的“理性”历史—文化质性进行“症候”的揭示性考察,基本上即是针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留白”部分进行一种借由特殊例外的文化基素来启发崭新文化意义的翻转显露工作,以裨有着化解西方现代性带来之致命问题的契机。(21)显而易见,就契机蕴生的几率而言,非西方的社会即是提供这个特殊例外之文化基素最可能的来源。准此,“本土化”所进行的,基本上可以说即是一种针对语言“留白”予以对照彰显而臻至翻转的事业。对我个人来说,其终极的鹄的即在于拆解西方主流社会思想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以重建一个对未来人类文明的缔造具有着发挥想象力,且富启发性的“另类”感知模式与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命题,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实目的即是,借此经营一套更具前瞻性的社会论述,以提供给人类有着经营更“合理”之生活方式的机会。(22)
简单说,“留白”是被遗漏而不曾被说过,或不可说,或甚至是完全阙如的部分。基本上,它并不自在地存在于原有的形式之中,而是人们从既有原已充塞挤满的“整体”中以“创造”翻转的方式释放出来的另类“非凡而例外”的部分,是人们对既有的“整体”的理想图像进行具创造转化性的摩荡攻错而体现的一种同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的“发现”。借用Gadamer(1975)的说法,这即是一种“视阈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运用,而特别值得提示的是,它更是以与原有的“整体”内涵的理路具有着某种“拨反”(尤其是对反)回转而体现的部分(23)。准此,“本土化”即是,透过一个认识主体的本地特殊经验的立场,把已显开的“全球现代化”论说中内蕴的(对反)“留白”部分予以解蔽地开发,以彰显具有创造“另类”足以丰富人类之存在意义与价值之“历史—文化质性”的可能回转面向。譬如,针对现代化的冲击(而非现代性之“本真”内涵本身),由“人”本身之处境出发的一种具特殊历史质性的“感应”方式,即极可能是一种对我们所处之时代具有揭露“征候”特质的回转工夫。(24)因此,这样由“留白”而开显的“本土化”的基本课题,绝对不只是与既有的实际彰显现象谋求意义的“契合”(25)而已。况且,倾听“留白”散出的讯息,并不是为了在未来的世界成就“普遍平凡例行”的实征经验事实,而毋宁地是企图缔造另一个更具深刻“历史—文化质性”之意义,且又可开展进发的“特殊非凡例外”文化基素,以作为参照基架来回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理解和期待。如此,对人类的历史—文化处境而言,由“留白”而开显的“本土化”可以说是一种具反思性的人为努力,它给予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创造力之空间的机会。这样之创造力的发挥并非毫无根据,它乃指向于以具启发性的另类“历史—文化质性”为基轴来发射特定的理念期待,以作为创造新文明之社会动力的基础。
注释:
①基本上,本文乃作者在2000年写就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搓揉游戏——论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一文的延续(参看叶启政,2001)。其中有些论点不免有所重复,乃因为了让整个论述的理路顺畅而做的不得已安排。在此,尚祈读者见谅。
②为了行文方便,底下,凡使用“本土化”一词乃概指“研究的本土化”。
③对有关台湾地区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相关文献的引述,参看叶启政(2001)。
④其中,最有表现成绩的莫过于环绕着杨国枢创办的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至于杨国枢领导之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5)。
⑤另一个一向致力于研究“本土化”的心理学家黄光国在最近的著作中亦有类似的主张。他认为,目前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此刻,应当“走向国际,采取‘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遵守各种典范的游戏规则,严格实行应对的方法论判准,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是“拿‘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作为借口,在‘本土化’的盾牌之下,用‘素朴实在论’的方法,建构出‘独树一格’的‘理论模式’,自得其乐;或者用‘素朴实证主义’的方法,累积充满‘本土原味’的实征资料,以量取胜;甚至写些‘没有人懂,只有我懂’的文章,喃喃自语;然后自己办杂志,自己登自己的‘论文’,‘关起门来作皇帝’”(黄光国,2005:75)。
⑥在此,我无意完全同意杨中芳与杨宜音的见解,指陈杨国枢因主张以英文在所谓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即意味他已放弃本土化的立场。况且,我并没有其他更具说服力的充分具体证据来予以支持。但是,杨中芳与杨宜音两位可以说一直是杨国枢之“本土化”主张的追随者,她们对杨国枢之路线的调整有这样的评论,显然其内心的感受应是有着一定的“一手”且难以言喻的体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畅所欲言。因此,虽无任何具体的证据可以证实杨国枢已弃守“本土化”的路线,她们的评论还是有着一定的“拟情”性(empathic)的参考价值。
⑦这样的要求几乎已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地区之学术界判断学术成果之良窳与否之共同期待的标准,并实际行诸为奖赏制度。
⑧参看杨国枢(1997)与Young(1999,2000)。
⑨为了突显,笔者特别以黑体字形予以强调表示。
⑩理由同上。
(11)无论就认识论、方法论或实质的论述内容,都是如此。至于潜藏在整个经验知识体系背后之特定的哲学人类学存有预设,绝大多数的学者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更遑论认清其中种种有关人与社会之基本存在基础所内含的特殊意识形态了。
(12)余德慧(1997)于其文(特别是在标题处)中使用的是“文化救济”(cultural redemption)一词,而在文本中则使用“历史或文化救济”,似乎有意把“文化救济”与“历史救济”等同看待;也就是说,论及其中之一(如“文化救济”)即同时意涵其中之另一(如“历史救济”)。以宽松概约的立场来看,对此一用法,是可以支持的,因为二者确实相互扣连衔合着。但是,在此,我使用“历史救济”而弃“文化救济”不用,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个人认为,在讨论此一议题时,时间向度是最值得关注的根本因素,因此,使用前者比使用后者,相对地更能贴切而传神地把“本土化”之此一向度的深刻社会学意涵表达出来,且又能够把“文化”的意思蕴涵进去。另外,可以略加说明的是,英文的“redemption”一词原本承载着基督教“原罪”精神内涵之厚重的“赎罪”意思,但是,在此,我不使用“救赎”,而仍旧采用余德慧原用的“救济”一词,理由就正在于企图弱化西方原本的文化色彩,避免此一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厚重“赎罪”文化特质妄套在我们原无此意涵的文化底蕴之中,而衍生过多不必要之缺乏任何本土历史意义的“误识”。
(13)更广泛而抽象地来说,套用Lefebvre(1971,1991)的用语,即所谓的历史质性(historicity),亦即本文所使用的“历史—文化质性”。同时,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主张研究本土化的关键乃在于历史与文化意识的生成的说法,尚可参看林耀盛(1997)。
(14)同时参看余德慧(2002)。
(15)作者们明示出,此一概念引自Deleuze & Guattari(1986)。
(16)有关我个人对“本土化”的见解,参看叶启政(2001:第5—7章)。
(17)有关作者本人对此一立场的论述,参看叶启政(2001:第5—7章)。
(18)有关“文化优势的扩散作用”一概念的阐述,参看叶启政(1991)。
(19)更具体地来看,在华人世界常可看到的算命、风水、针灸、民俗治疗等等,就是最典型的极端鲜明的例子。
(20)此处所谓的“适用”性意涵的,基本上,不单纯是契合与否的问题,而是涉及对人类之未来社会处境是否有着足以引发具启发性之“历史—文化质性”的意义认定问题。
(21)此一研究策略的原始灵感来自Althusser(1979)。Althusser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最显著的成就乃在于,以所谓“症候沉默”(symptomatic silence)的方式,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看不见”(invisible)的部分予以颠倒披露。
(22)譬如,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即是针对潜藏在个人主义之信念背后的基本存有预设进行剖析,以用来理解消费社会的特征,并进而提出具回转契机之另类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如此对人类的形象有着另外的基本想象,可以用来作为重建与理解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基础。有关这样之取向的讨论,参看叶启政(2008)。
(23)在此,我所以使用这么拗口的说法,为的是避免落入Hegel所主张之具内在性(immanence)的“正、反、合”辩证思维圈套,而得以让现象的回转应变具有着更多可能的走向空间。
(24)由于此—议题涉及整个西方社会学思想中复杂的论述历史,在此,无法以简单语言说清楚。有关作者本人对此见解的论述,参看叶启政(2008)。
(25)更遑论实证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