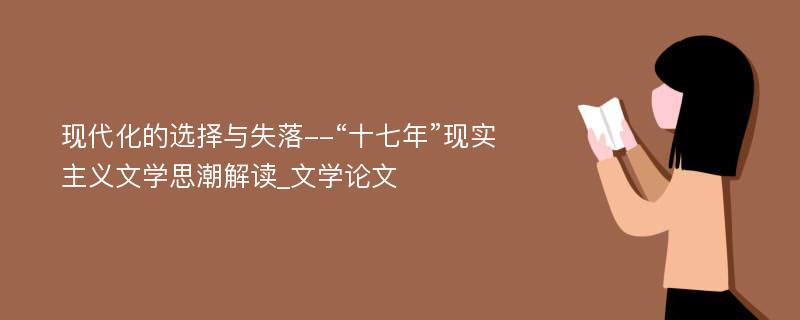
现代性的选择与失落——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阐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思潮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文艺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1—0145—05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主流文学作品是在革命话语体系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规范下,依托“革命战争”和“合作化运动”两大主题的展开,在历史的向度上追求着新中国谋求发展的宏大叙事。它们基本上固定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代表着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力量在英雄人物的带领下,经历一番曲折,最终战胜了落后势力。这种创作模式的确立使得“十七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
从这一时期文学文本中所锁定的“旧社会将人变为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翻身”、“解放”这些语码来看,这一叙事模式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这一起点上现代性诉求的最直接表达。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发现其现代性诉求是以抽象的社会本质力量的实现为目的论,而现代性所要求的“人的生成”却被忽略了。这致使“十七年”整个文学文本中“圆形人物”的缺失,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残缺,也在深层次上悬搁了革命话语本身具有的现代性内涵。这一切可以说都是通过对“现实主义”的改造实现的。
一、“写灵魂”的受挫
建国初期,中国文艺思想界对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进行了批判。胡风有关现实主义的诸多观点中,“主观战斗精神”说是被指认为“反现实主义”的一条重要依据。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学说将“锐敏的感受力”、“燃烧的热情”、“深邃的思想力量”看作是创作的源泉。他认为“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的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1]20
胡风的“主观精神”说虽然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有些差异,但它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并不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力,论者所追求的只是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丰满、生动。在他看来,任何没有真正沉淀到作者情感深处、被作者充分感受的客体只是无意义的外在形式而已。因此,胡风的现实主义观便格外重视作家的主体,尤其关注作家的灵魂拥抱客体时激荡起的深刻变化。这也并不是胡风的创见,早在1920年代,鲁迅就提出了“写灵魂”、“以主观性介入现实主义创作”等与当时的“写实派”显然不一样的现实主义观。鲁迅极为推崇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剖析人的灵魂时将“自己也加以精神苦刑”的做法,无论是他的《狂人日记》,还是《阿Q正传》、《在酒楼上》、《伤逝》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观下的创作实绩,而这批作品在当时都受到了好评。
如果说鲁迅更多的是通过译介作品和自身的创作来呈现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那么胡风所做的是将这一观点理论形式化并应用于当时的批评实践中去。但胡风活动家的政治激情始终妨碍着他周延、系统、深入地阐述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他对鲁迅现实主义观的发展,在于一方面他将之凝练化为“主观战斗精神”,另一方面他将鲁迅作品中展示的“现实的历史内容”解释为现实的最高层面。
鲁迅在和梁实秋、林语堂的论争中,言辞坚决地表达了他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但正如胡风评价他时所说的:“先生底搏战不用说是‘心照不宣’地和南方的革命怒潮互相呼应,然而,由于先生底从全民族生活底地盘在人类史上争生存、争进步的视野,也由于所谓‘新’文化阵营底某些队伍第一次用着显著的行动投向了反动势力底怀抱,他就不能不超过一时的‘政治的兴奋’而进现实生活底深处,而禁不住唱出了他的沉痛的哀歌。”[2]92 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历史长河中沉积的一切奴役人的灵魂的文化传统的逼视。胡风对鲁迅的追随表现在他把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作为现实历史的重要体现。他俩都一致地将打破中国民众的精神枷锁、争取人的自我觉醒作为创作的现实诉求。
“写灵魂”的现实主义观努力实践的是对“人的本质”的追寻,而不是对社会本质的把握,它指向人的精神自由的全面实现。作者以小说主人公的主体性作为他对现实人生进行理性审视的重要对象,将人精神上的受奴役、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作为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依据。人道主义是这种现实主义观的哲学基础,在审美倾向上,它更多地倾向于“审丑”,在对“丑”的冷峻解剖中显现作者理性人格的强大以及对构建强健、美好人格的渴望。即便是其塑造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也是在与内心灵魂搏斗中以非凡的理性力量超越着“自我”,在痛苦的蜕变中完成了“人”的改造。在这种现实主义观影响下的创作,是在人物人格的分裂、异化和对立中表达自己对人的现实处境的理解和对他们未来出路的思考。阶级对立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人类社会本质上的矛盾,他们更关注由此而产生的人的精神内部的对抗。他们将人自身的精神自由看作是社会迈向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指标。
建国初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严厉批判,不能不说也是文艺思想界对“写灵魂”这一派现实主义观的否定。建国初期文艺思想界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恰恰是片面强调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阶级的对抗这一客观事实,抛弃了“写灵魂”这一派的现实主义观。这使得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回避了历史与社会的转型对人物内心深层次结构的改变,也就回避了个体的复杂性造就的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偶然性。最明显的就是在建国初期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批作品中,农村青年村干部和富农的形象的塑造,他们作为英雄形象和落后形象,都贴满了所属阶级的标签,少有反映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文化氛围对各自内心世界的影响,他们只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指向完成着各自角色的历史使命。虽然表面上看它们是对“现实主义”所承载的书写迈向现代化的新中国这一目标任务的直接呼应,但在这些作品中历史的向度并不是在时空的坐标系中自然显现,历史实际上已被抽取了具体的丰富的内容,而成为抽象的概念。这些作品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只是简单的叠加,使文学作品变为“斗争哲学”主题的直接演绎。这一时期,一批生动反映日常生活本身的小说,像《小巷深处》、《红豆》、《在悬崖边上》等,无一例外地受到批判。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趋向完全被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操纵,人物失去了主体性。
二、“典型”的变形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性文本都有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即将文学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思考置换成了对社会的发展本质的思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在于这种现实主义观抓住了“典型”这一概念的可改造性。
“典型”是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正如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所言,“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而“典型构成了联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社会理解之间的桥梁”[3]232。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对史诗格调的追求提供了便利,但“桥梁”角色的担当,也易造成作为典型的艺术形象本身个性的损害,使之成为一种指向性的符号,所以“典型”的个性与共性是一对非常难处理的矛盾。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典型”的个性化因为典型与作者的倾向性与社会理想的紧密结合而消失殆尽。在中国,早在1930年代,胡风和周扬已就“典型”产生了争论。周扬虽最早对“典型”的个性化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他更为注重“典型”的社会性、思想性内涵而将“典型”的个性化问题搁浅了,倒是胡风在争论中逐渐克服了自己对“典型”的个性化忽视的弱点。他们日后的分歧恰在于周扬将典型的社会性、思想性内涵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而胡风则以对主观性的强调在追求典型的个性化方面做努力。
“典型”作为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明晰地被阐述过。长期以来,它只是在恩格斯的对一些作品的经典性评述中被意会着。但在恩格斯的这些评述中,明显地存在着文学的和政治的两种尺度,也即一方面他强调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个”的独特性,主张“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4]454,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满意于哈克奈斯未能反映出代表时代主流和社会本质力量的“典型环境”的特征。这就是恩格斯所批评的“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5]462
从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立场来看,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即使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展现受压迫者抗争的力量也是张扬他们健康人性的重要内容。然而,像“伦敦东头”的消极群众也确是存在的。若在他们的精神确实还没有转变可能的情况下,强调他们转化的趋势,那就成为了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实际上“这一个”所反映出的典型的个人性,与反映社会本质力量和时代主流的环境之间完全有可能是不和谐的。这里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批评表明,当这两者不一致时,他更强调典型环境的呈现,这就在一定程度否定了典型中所蕴含的“这一个”这一重要内涵。巴尔扎克的成功正在于他没有受到所谓“典型环境”的束缚而专注于许多“这一个”。可对广大无产阶级作家来说,更切合他们自身世界观的典型环境更容易吸引他们,使他们多少会忽略环境中丰富多样的个体。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将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反映社会本质力量方向的因素,充分突出它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地位,却忽视了典型人物的个性层面的内涵。如果说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论断内含了文学和政治视角的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完全以政治视角取代了文学视角。这就改变了文学对人的丰富性、生动性的叙述,而使典型发展成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符码。“典型”在创作中的作用也就从作品的主体变为了演绎某种观念的工具。
在新中国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被确定为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这里新的英雄人物即是指具有先进世界观的一代新人。这些人物像梁生宝(《创业史》)、朱老忠(《红旗谱》)、秦德贵(《百炼成钢》)、刘洪(《铁道游击队》)等人无不从一开始就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高洁的品格,胸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出个人历史的印记。作品回避了在新的环境下,对旧“我”的审视,在将他们供上神的祭坛时,却使他们丧失了人的丰富性。
中国广大民众饱受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几十年的战争弱化了五四精神启蒙的主题,建国初期我国低下的生产力、小农经济的形式都决定了具有高度觉醒意识、现代意识的民众形象并不可能是出现在中国建国初期这一历史维度上的真实面影。这样一些乌托邦话语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新中国对自身在国际格局中劣势地位、对自身现代化之途漫长而艰难的焦虑。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典型”本身的训谕功能扩大到了极端,使典型化为了政治典范,丧失了它的个性内涵。
除了胡风的“主观战斗说”,我认为建国后十七年中,从理论上对典型个性化的实现做出努力的是邵荃麟提出的写“中间人物”论。“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6]20 这就从审美意义上肯定了这些“中间人物”的存在意义。梁三老汉(《创业史》)、“吃不饱”、“小腿疼”(《锻炼锻炼》)、赖大嫂(《赖大嫂》)、谭婶(《静静的产院》)这些人物,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有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但他们意识不到身上自私、保守的小农意识妨碍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越是沉溺于自我狭小的天地,幸福就会离他们越远。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典型的个性因素呈现得越充分,就越有助于打碎对旧的社会秩序的幻想。
但是在建国初期,这些被充分个性化的典型在“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误导下,他们的典型性遭受怀疑,这就影响到对这些人物审美性的公允评价。由此邵荃麟指出:“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中,还是要写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也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7]。对这些艺术形象典型性的肯定就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论调。这绝不仅仅是拓宽了作家创作的题材领域、邵荃麟在倡导写“中间人物”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理论,表明了他对典型的个性化之于现实主义深化重要意义的理解。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并不见容于那个过于高估个性的离心作用的时代。
从胡风到邵荃麟,我们看到了他们基于对人的尊重、对文学的尊重以对典型的个性化的强调,来修正被扭曲了的现实主义的努力;我们同样看到了在政治强势话语下他们的势单力薄。在这以后,典型的个性化因素每一次稍被提及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直至文革文学中典型的样板化,以致文学除了演绎政治神话,它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价值已荡然无存,这也使在中国“个性”的确立更为艰难。由此看来,胡风、邵荃麟的厄运不仅使对“典型”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形象模式化,它还模糊了我们迈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
三、现代性品格的失落
“写灵魂”的受挫、“典型”的变形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体系规范下表现出来的文学内部因素的变异,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外部的批评活动也强化了文学内部因素的变异。
建国后“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唯一合法地位的确立是以与政治权力话语合谋的方式获得的。贯穿十七年的文学批评活动就是一场确立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权威的轰轰烈烈的话语规范化运动,它特别重视的是对自由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的话语体系的改造。这场话语改造运动在建国后“十七年”间是经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完成的。建国初期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文学批判运动是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的。武训为兴办义学不惜受尽种种屈辱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却遭到了权力话语的严厉批评。这部影片首先被否定的是武训为了取得宣传封建文化的合法身份而卑躬屈膝的态度,其次还有影片对农民阶级斗争的否定性态度。这场批评活动一开始就挑明了话语改造的主题,那就是一个人拥有怎样的知识比他是否拥有知识更为重要;社会革命的成功从来就不可能靠一些知识分子改良完成,只有靠人民群众发起的阶级斗争。紧接着的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的批判运动进一步突显了这一改造主题。
其实这场声势浩大的话语改造运动早在建国前夕就拉开了帷幕。1949年8月开始,上海的《文汇报》上掀起了一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讨论的话题本身就已说明了对作家创作权利的轻视,何况讨论的结论还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下,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逐渐改变为以写工农阶级及其干部为主……而不可能只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8] 何其芳虽仍给小资产阶级人物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一席之位,但之后开展的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等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作品的批判以及随着开始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都宣告了小资产阶级题材业已成为创作的禁区。
相当一部分作家由于过于急切地想融入工农兵生活、掌握工农兵的话语方式而迷失了自我。此时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在阶级属性上被贬低,“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9]409 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势力其实在中国从未强大过,但建国初期人们在政治言论的反复宣传中,还是普遍沉浸在对资产阶级假想性的怨恨和警惕中。资产阶级属性的确定,使知识分子从内心滋生对社会的愧疚和自卑感。
这一时期,文学领域内展开的是以行政干涉方式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争鸣活动,政治标准取代文学标准,且动辄给作家以政治惩治。胡风、路翎锒铛入狱,文学理论家吕荧因坚持胡风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遭隔离审查一年;刘绍棠由于发表了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否定性的意见被打成“右派”;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为首的江苏文学青年团体因“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方法”[10],全部成员被打成“右派”,等等。
建国十七年的文学批评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即无产阶级群众对文艺作品的意见受到空前关注,并作为文学作品价值衡定的重要标准。在一篇对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的批评文章里,虽然这位工人作者一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但这并未妨碍作者批评言语的自信,不妨碍文章受到文艺批评家的极大重视。这些批评文章多从阶级的角度,从他们的情感需要和自身审美习惯的角度对作品作出评判,这其中更多的是非文学的因素。他们要求将自己仇恨的敌人、地主阶级统统丑化,希望作家在作品中能写出无产阶级胜利的乐观前景。在这两种批评力量的交相挤压下,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从自己熟悉的话语体系中抽身而出。但他们却只有极少数人能顺利进入主流文学的话语体系,而这也是以泯灭自我作为代价的,大部分人就此失语。
正是如此的话语改造运动摧毁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建国前几十年的战争已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洞穿“批判的武器”的软弱,失去了“五四”时期置身于广场中心振臂高呼时的从容与自信。不过我们也可看到,战争虽促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过“五四”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铁肩担道义的思想意识,尤其是在国统区作家那里,启蒙的主题就没有中断过。建国后,新中国走向工业化的过程本该也是对小农经济形式造就的封建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的一个过程,而且中国若想迈向现代化,就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创造出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但建国初期党的高层领导人头脑中夸大了的阶级意识、斗争意识错将政权的巩固放在了制定国策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夸大了新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关系,将较多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为被放逐者。知识分子的失语导致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理性的缺失,而知识分子群体自主意识的重建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就文学而言,作家自主意识的丧失带来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思考的弱化,是文学的人学意义的消解,也使作品内部的革命话语成为一些空洞能指。这与文学的现代性品格是相去甚远的。
收稿日期:2006—09—16
标签:文学论文; 胡风论文; 文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现代性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