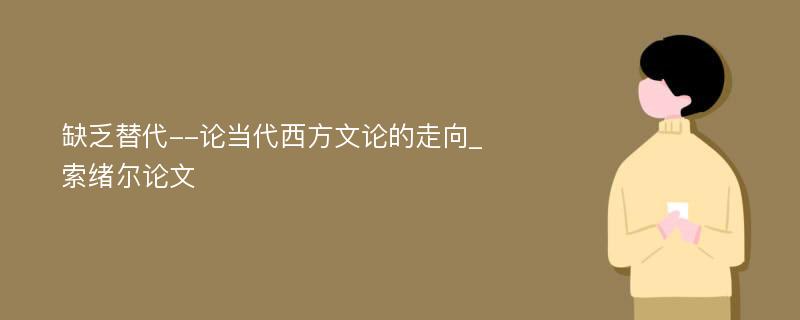
补替中的缺失——当代西方文论走势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缺失论文,走势论文,当代论文,补替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语言:救赎与言说
记得艾耶尔(Aayer)曾说过,整个西方现代哲学是从背离黑格尔开始的。这一断语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那就是我们是否可以把黑格尔理解为一种象征,一种传统的象征?或者理解为一面旗帜,一面在整体上与20世纪的理论精神相左的旗帜?在黑格尔的对照下,我们是否可以更加确切地理解当代人文科学的基本精神?无论如何,黑格尔的理论具有集大成式的典范意义。
加达默尔(Gadamer)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试图把科学和哲学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把握的最后的巨大努力”。[①a]黑格尔的理论逻辑表征着唯有科学思想才可能具有的整体性原则、严格的逻辑分类原则、明晰的主客观统一的原则,这种对科学精神的把握是通过人来完成的,是人的理性力量的结果。所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精神从根本上暗示着一种人对自身的自恋和自信。在黑格尔背后,我们不难发现站立着一个人,一个十分自信的人,这种自信不仅表现在他已经把这个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表现在他坚信人的理性可以包容一切,涵盖一切,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性和不证自明性。那么,人何以这般从容不迫、傲视一切?这里固然早已没有了中世纪年代里那种神的意志和辉光,但神的启示犹在,“灵魂不死”的自慰和“绝对理念”的自足犹在,而且现世中,人始终处于一种主宰和超越的地位,他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科学所赋予所支撑的理性、信心和能力。人在科学中走向他本身的哲学境界。倘若用“背离”二字来形容黑格尔身后,黑格尔的幽灵确实已经远离了我们,因为今天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胡塞尔在分析20世纪哲学危机时说,哲学危机实际上反映了人的危机,反映了“对理性信仰的崩溃”。[②a]尼采和弗洛伊德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两个名字了,他们一个是诗人兼哲人,一个是精神分析学家兼哲人,他们对20世纪人文科学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把昔日包裹在理性光辉中的人还原为一种永恒的生命冲动和一种无意识的生命暗区。尼采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只有艺术真正表征着人,因为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命冲动,因为“艺术使我们想起动物活力的状态;它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①b]尼采认为人沉醉的极致是“裸舞”,这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尼采对人之本质的认识的生理学和生物学的企图是明显的,他欲把人本体、艺术本体都生理化和生物化,让它们统统返回到最初的生命本能上去。关于弗洛伊德的思想,马尔库塞(Marcus)说过这样一段话,弗洛伊德眼中的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②b]文明的缺憾就在于对人的本性(本能)的抑制。弗氏的这种认识是与他对人的本质性结构(本能结构)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人本质的分析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生物学、病理学方面,即所谓的“伊得”(id),它是人的本能的中心所在,从种族遗传史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它是一切心理能力的基本源泉,它的唯一机能就是消除机体的兴奋状态,实现生命的第一原则,快乐原则。[③b]人类的一切艺术活动不过是伊得的升华而已。所以,尼采和弗洛伊德对传统的人的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颠覆。在他们眼里,人的大写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人连他自己都难以认识、难以抑制、难以存放,又有什么资格获得唯我独尊的特权和地位呢?当人本身变得扑朔迷离之时,与他相关的一切必然变得晦暗不明,人又如何从自身出发去获得一种科学真理性的价值评判呢?20世纪人性的危机及其影响不仅仅在于人本身遭到解构,而且意味着与之密切联系的一切价值观遭到质疑。
当然,人的弱点、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是一种追求终极的动物,终极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人之确定的怀疑、对人之理性的绝望,并没有阻止人对终极的向往。自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家园之后,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一个梦,那就是家园之梦。人时刻需要一个稳定的家来保存自我、确证自我。这种对终极感的认定和追求使得今日焦虑之人把对确定性寻找从自我身上挪开,投向了一个新的场所、一个貌似稳定、客观之物——语言。利科(Ricoeur)指出“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④b]实际上,人的衰微与语言的崛起不仅是当代哲学的主题,而且构成了西方当代文论走势的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正是由于语言被置于前景,才可能真正形成文学向文本的转换,创作向写作的转换,才可能生成由结构而解构的当代西方文论基本思维模式的转换。
确切地说,语言对西方文论的根本性影响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所谓“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⑤b]转向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一方面强调了索绪尔语言中的能指/所指的二分学说,能指即是音响意像,所指即是概念,从而把语言的现实对象排斥在语言参照之外,使语言的意义停留在语言内部的差异性之上,表现出一种语言心理主义;另一方面强调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共时/历时的二分学说,提出共时生成了语言的结构性特点,共时中的纵聚合与横聚合赋予语言以意义,从而语言成为了一种缺乏历史深度的符号系统,流露出形而上学痕迹。在此基础上,当代西方哲学把语言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颠倒,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了语言对人存在的先在性。海德格尔有一段名言,“是语言在言说。人只是在倾听语言的呼唤并回答语言的呼唤的时候才言说。在我们人类存在物可以从自身而来并和自身一道成为言说的全部呼唤中,语言是至高无上的。语言召唤我们。”[①c]语言成为一棵新的救命稻草。那么,语言真能解救人存在的危机吗?我们如何在语言中挽回人的价值体系的颓势呢?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走势就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深深地卷入了人所面临的危机和救赎之中,卷入了意义的寻找和飘零之中。
文学/文本:弥漫与悬搁
我们把文学退场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显得有点不可思议。文学,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艺术观念,何以会退场?它那旺盛的生命力、奔涌不息的血脉,何以会在今天嘎然而止?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
文学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承接下来的文学概念足以使我们对文学本身的把握一目了然。首先,作品是作者的产物,作者不仅赋予作品以形式,而且赋予作品以意义,作者对作品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导权。所以,韦勒克(Wellek)、沃伦(Warren)说,“从作家的个性和生平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研究方法。”[②c]其次,作品与对象的镜式关系,把文学推到了一个不断追求真实的境地,这种镜式关系既存在于作品与作者之间,又存在于作品与关照的对象之间,它规定了文学获取意义的途径,规定了文学的真实本质。再次,语言作为工具的从属性,使得作品内容上升到主宰地位,即使在雄辩术十分发达的古罗马时期,语言也只能是作为一种突出内容的修辞技巧,形式(语言)的从属地位从未动摇过。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这既是合情合理的,又是天经地义的。总之,传统文学观念具有一套公认的完整而统一的规则,它以真实为核心,强调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强调主体在发挥自我的真实本性中对真实的服从,强调主体的力量在于能够发现和传达真实的信念。它的意义在于人与自然的有效对话中。
然而,背景的转换导致了一种传统观念的式微。卡勒(Culler)说,今日文学之危机,“其主因在于文学本身已经完全被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占有,同时今日之文学放弃了对文学真义的发掘,而视一切文学阐释为均等有效。”[③c]卡勒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即文学的文本化。文本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与背景转换相呼应的替代性的核心概念。然而,要问文本意味着什么?这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因为我们感到,与充实、固定、统一的文学相比,文本简直就是一个空洞,一个万花筒似的想象空间。文本(text)取代作品(works)耐人寻味。作品的字义简单明确,即指作家的产品(output);而文本的字义则出入甚多,语境也复杂得多。艾布拉姆斯(Abrams)说,在“新批评派”的眼里,文本中的作者只是一个无人称的媒介,文字释义只是一个无人称的阅读过程。[④c]由此开始,对文本的挖掘一步步深入,不仅涉及到了主体的权威性,而且对文本与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对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等统统进行了拓展。如克里斯蒂娃(Kristeva)提出的互文性概念,设定了一文本与他文本的互鉴关系,把文学的根源推到文本之间(包括不同质的文本)的联系之中,把传统文学中的对象性关系冻结起来。克氏说,互文性“在社会和历史中设置文本,这一社会和历史通常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并且通过对它们的重写,作家把自我镶嵌进去。历时转化为共时,由于这一转化,线性历史表现为一一种抽象。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一种读写过程,即通过对一个意指结构与另一个与之相连或相对的结构的读写,超越这种抽象”。[①d]克氏的表述是与传统文学的表述极为不同的,它首先设计了一种文本的优先性,社会和历史也是文本化的,是一种文学书写和印刷的社会和历史。人只能通过读写有条件地“镶嵌”其中,这意味着结构生成结构,文本生成文本,人与历史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文本对文本的关系,从而封杀了人的主导性和现实存在的价值。德里达(Derrida)则把文本完全封闭起来,对意义的操作只能在文本内部进行。他称,在文本中,“没有其他的要素作参照,任何要素都不可能作为符号起作用。这种相互交织导致了每一个要素都是在这一基础上构成的,即在它之内的该系统和链条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构成的。这种交织所形成的文本是另一个文本转换的结果”。[②d]所以,文本成为了在场和缺场不断变幻的场所,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差异中分延意义的链条。那么,文本到底是什么呢?在结构主义眼里,文本是一套特定的书写规则,任何主观的东西陷入其中都会泥牛入海;在解构主义眼里,文本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无休止的阅读场所,任何阐释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认可的意义,文本决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意义……或许,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这些已经足够了。无论我们怎样去寻找,其结果看来只能是越来越纷繁、越来越难以把握。我们在这种纷繁中所能辨认的恐怕只有一条,即文本就是文本,文本就是一切。
文本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对一切书写形式的有效性,文学必然消除在文本的汪洋大海中。文本弥漫而导致的意义悬搁,这一走势已经定格于今日的当代西方文论。
创作/写作:缺场与游戏
创作与写作之间的张力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又一个焦点,也是我们所论的走势的一个更为内在的层面。倘若说,文学文本化从客体的角度揭示了文学存在方式的变化,那么创作写作化则从主体的角度表现了文学主体在审美、体验乃至存在方面的变化。创作与写作,两者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大相径庭。前者表征着一种深刻的文论传统,后者则是对这种传统的否定,一种颇费心思的掏空。
创作的意义通常展示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即美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创作的美学层面集中表现为风格。巴尔特(Barthes)曾对创作中的风格要素进行过精采描述。他说,风格是一种自足的语言,它浸入到作家个人的和隐私的神话学中,浸入到这样的一种言语的形而上学中,在这里形成着语言与事物的最初的对偶性的关系。风格是一种冲动的而非一种意图性的产物,它很象是思想的垂直的和单一的维面。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的或个人经历的水平上,而不是存在于历史的水平上,它是作家的事物、光彩和牢房。风格永远是一种隐喻,是作家的文学意向和躯体结构之间的一种等阶关系。[③d]所以,风格构成了创作的基础,创作的一切内涵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在风格上。创作的历史层面集中表现一种规范和责任。首先,创作所运用的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作家共同遵守的一套规则和习惯,它象是一种自然,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却又不留任何痕迹。语言结构是一种行为的场所,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和期待。与其说它是创作的基础,不如说是极限,因为语言结构是一种历史凝聚的结果,具有文化的规约性。其次,创作意味着一种历史责任。就如同福克纳所言,“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描写这种精神。”[①e]创作的最高的哲学层面证明了人的存在。创作始终是以人的存在为根本目的和旨归的,没有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因素和人格魅力,文学就难以获得它应有的价值。创作反映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它是人所特有的,它把人对事物的理解与人的审美冲动联系起来,把人的美感与人的悟性联系起来,同时,人每时每刻又通过一种目的的设定把自我与外界融合起来,把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潜在地纳入到自我的存在中,从而不断地创造着创作存在的形而上意义。总之,创作意味人的力量和人的特性,创作把人强化为真正的人的存在。
人的缺场意味着文学主体意识的丧失,意味着一种文学信念的丧失,创作随之衰落。
那么,在今日的所有文论书刊中充当主角的写作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写作一词来自巴尔特。霍桑(Hawthorn)说过,尽管写作在日常法语中很普通,用来指一种“书写”或“写作的艺术”,但巴尔特旨在提出一个新概念,使之与传统的文学(我在这里着看强调的是创作)相对立。[②e]这或许从动机方面提示了写作产生的某种原因。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写作出场的革命性意义,这就是巴尔特所谓的“零度写作”(writing degree zero)论。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是非语式写作”,“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它完成了一种‘不在’的风格”,于是写作“被归结为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其中一种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了,而代之以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形式状态”。[③e]可见,写作是一种无色的创作。它通过把人的命运委托给一种基本言说来摆脱创作,同时把写作从正统的文学语言程式中解放出来。班菲尔德(Banfield)说,“写作意味着一种缺场,一种文学标志的缺场,一种人的能力的缺场。……今日之写作是与人、与人的活动离异的产物。”[④e]班菲尔德的这一分析乍一看让人有点不解,因为离开了人,文学能够存在吗?实际上,班氏旨在指出这样一种情形,即人在写作中已经丧失了昔日之精神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写作中人的缺场确切地说是一种至高至上的大写的人的缺场,是一种人的理性精神的缺场,人在场如同缺场。基于这一点,写作超越创作,写作解构创作。
德里达对写作的解放也是颇有意味的。表面看来,德里达垂青写作是着眼于根除索绪尔扬语言、抑书写的痼疾,据说这是恣虐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之一,这一点与文本所讨论的论题似乎相去甚远。然而,我总觉得这里暗藏着某种东西需要挖掘出来,它与本文的论题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东西又该是什么呢?德里达笔下的写作意味着一种分延,一种踪迹,一种游戏。写作是一种线性时间里的符号排列,它通过索绪尔所谓的差异把符号的意义一点一点地向后推移,作家也就在这种推移中获得他的快乐;写作中的每一个符号都具有一种垂直的暗示性,它可以不断地在自己的垂直轴上寻求替换,而每一个符号又都是一种历史的凝聚,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共同作用的混杂不清的意义,作家操纵每一个符号都是在进行一次历史的冒险,都在一种琢磨不定中自由驰骋;所以,从根本上说,写作是一种游戏,是一种作家参与其中但无从把握自我的游戏。作家迷失在自我设置的游戏中,实际上,作家也在这种游戏中走向缺场,因为游戏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人做游戏,而是人被游戏。游戏是写作失去了创作中的风格意义,失去了创作中的历史规范和责任,从而也就失去了人的存在。
结构/解构:多极与断裂
在西方,结构和解构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思潮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这里重新提起的结构和解构,不仅是指它们的过去,而且是指由具体的历史形态演化而来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精神,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踪迹,一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它们表征着今日文论基本走势的思维特征。
把结构主义与当时科学上出现的新方法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相联系是理解结构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把结构思想如霍克斯(Hawkes)那样追溯到17世纪的维科(Vico)时代也不能说是离奇古怪。对于结构主义,许多大师如皮亚杰(Piaget)、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雅各布森(Jakobson)、杰姆逊(Jameson)、卡勒等都进行过大量论述。我相信巴尔特的一段话,“我们必须追溯到诸如能指/所指、共时/历时这样一些对立,才能接近到结构主义之所以与其它思维模式相区别的根源。”[①f]杰姆逊则进一步表述了类似的意思,“结构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对能指的关注,它的最基本的操作是把作为研究对象的能指与所指区分开来,结构的基本场所就在能指本身的结构中”。[②f]应该说,把结构主义本身套在索绪尔头上是欠妥的,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索绪尔思想的一种现代包装。杰姆逊已经指出过,索绪尔之所以把共时观念突出地提出来,是因为要以此来克服当时流行的新语法学派词源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唯历时观念,但真正把共时本身作为一种确定的方法,使它获得一种方法论意义,则是当代人的一种需要所致。我相信,结构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人文科学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状态的一种焦虑情绪,萌发出对确定性的需求和寻找;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科学对整个社会当然包括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反映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我能力的信心。恰恰就是这种焦虑和信心再次搅动起古老的形而上学之活力,再次使其成为了一种人类神圣的目标。那种整体的、中心的、明晰的结构意识无疑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翻版。
结构的力量在对索绪尔的重新阐释中弥漫于几乎所有领域,普洛普(Propp)的民间故事研究,雅各布森的诗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拉康(Lacan)的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格雷马斯(Greimas)、托多罗夫(Todorov)、巴尔特的叙事学研究,等等,都成为结构活动的一部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的寻找,就是对一种中心结构的寻找。托多罗夫说过,“不仅一切语言,而且一切指示系统都具有同一种语法。这种语法之所以带有普遍性,不仅因为它决定着世上的一切语言,而且因为它与世界本身的结构是相通的。”[③f]巴尔特试图把服装、汽车、菜肴、行为、电影、音乐、广告、家具、报纸标题这些异质之物统统归结于符号之下,因为它们都具有统一的符号特性。[④f]我们仅以格雷马斯的一项操作为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以此领略一下结构的基本思路和思维模式。格雷马斯在普洛普关注单一要素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归纳出一种普遍的叙事“语法”。他把普洛普的七种“行动项”(1.反面角色;2.捐献者〔施主〕;3.助手;4.公主〔被寻找者〕和她的父亲;5.送信者;6.英雄;7.假英雄)简化成三对相互对立的给合,即主体/客体、送件人/收件人、帮手/对手;这三对组合描述了可能出现在所有叙述中的三种基本程式:1.愿望,搜索,或目的(主体/客体);2.交流(送件人/收件人);3.辅助的支持/阻碍(帮手/对手)。以此来分析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底浦斯王》比起普洛普的范畴具有更大的穿透力。1.俄底浦斯寻找杀死路易斯的凶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寻到的却是他自己(他既是主体又是客体)。2.阿波罗的预言预示了俄底浦斯的罪恶。特莱萨额斯、尧卡斯塔,送件人和牧人,无论知道与否,都承认它是事实。这幕剧就是关于俄底浦斯对信息的误解。3.特莱萨额斯、尧卡斯塔试图阻止俄底浦斯发现凶手。送件人和牧人无意帮助他寻找。俄底浦斯本人妨碍了对信息的正确理解。[①g]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格雷马斯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采用归纳概括的方法把叙事抽象为几种简洁的组合规则,寻求和确立一种普遍法则。这与斯特劳斯所寻找的神话素,巴尔特寻找的符号通则异曲同工。这种对结构性的强调表现出了十足的反人道倾向,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如塞尔登(Selden)就提出结构主义直接抛弃了文学作品是作家之“子”的观念,抛弃了我们可以通过作品进入到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世界的观念,还抛弃了一部好的作品讲述着人类生活的真实的观念。结构主义的主张是作者已经“死”了,文学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等。[②g]结构主义的反历史倾向也是昭然若揭的。兰蒂里夏(Lentricchia)说,“结构主义所遵循的是索绪尔系统概念的反历史主义一面,它反复强调的是产生具体化差异和历史变迁。”[③g]所以,结构的“结构性”,或者说是它自身存在的一种结构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德里达所敏锐地观察并指出的“把存在(being)确定为全部意义上的此在(present)”。[④g]
任何理论范式都是一种历史精神(其核心是哲学精神)的凝聚。在黑格尔及其以前的时代,文学观念囿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观,即崇尚权威,追求终极。它作为文学范式的最基本内涵规范了文学自身的和谐、统一、秩序、明晰的特点。这无疑是历史上存在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直接影响的结果。然而,今天的理论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科学的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替了牛顿力学,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则”在微观领域强化了爱因斯坦的思想,这就从科学基础上对那种凝固的、单极的思维模式给予了毁灭性打击;二是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对人本身的还原以及对人的异化本质的揭示,把人及其理性从至上的神圣地位拉了下来,撕毁了人的一切面具;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的一切传统价值观念,导致了一种普遍蔓延的人性虚无、理性虚无、真理虚无的怀疑主义情绪。显而易见,由笛卡尔提出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发展的哲学范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经验。布来奇(Bleich)指出,“库恩的研究表明,我们可能要放弃向前的进化以及绝对真理的观念,因为科学的历史证明,新的范式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满足当前的认识需要,或者是创造出这一范式的那个时代的认识需要。范式的形成是有机体适应性的人类形式,其目的是使人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能作为一种生物而更好地生存下去,对于这一目的来说,客观真理的想法是多余的,把人类发展视为趋向完美的进步的观念是多余的。”[⑤g]这段话非常关键地道出了形成今日理论范式的特点:多极性替代单极性,灵活性替代凝固性,策略替代战略,纷杂替代秩序,等等。鉴于此,昔日的结构主义那种公理式的观念必然难逃解构的命运。
于是,当我们从这里走向解构之时,就已经明白了解构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对发生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这一十分重要转折,它的理论特点、它的思维模式的架构方式,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有了一个起码的认识。解构首先是对结构开刀的,是以德里达对斯特劳斯提出的挑战为开端的。德里达对结构的理论特点和思维方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结构是一种先验模式,一种写作秩序,它的中心的中心性地位决定了结构的存在方式。中心的作用在于引导、平衡和组织结构,无中心的结构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也恰恰就是这一中心不仅主宰着结构,而且又逃离了结构,这样一来,在结构之外就存在了一个不受结构控制的绝对物,“所有与本质原则,或与中心有关的命名总是标明了一种此在的恒量——理念,元始,终结,势能,实在(本质,存在,实质,主体),真实,超验性,知觉,或良知,上帝,人,等等。”[①h]这就构成了所谓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替换,是由这些隐喻和换喻构成的。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就表现出这种对结构的信赖。然而,德里达就是在斯特劳斯的神话话语中发现了摧毁神话结构的力量:“神话没有统一性或绝对本源。神话的焦点或本源总是闪烁不定、不可实现、并不存在的影子和虚像……这种无中心结构的话语,亦即神话,其本身是不会有一个绝对的主体或绝对的中心的。”[②h]德里达对结构的解构还从语言的层面上进一步展开。语言是结构的根基,也是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根基,解构结构必然解构语言。语言的结构性肇始于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德里达对索绪尔的分析复杂而曲折,非本文所能引述,但是诚如斯特加尔(Strozier)所言,德里达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与形而上学紧密地联系起来。[③h]面对索绪尔,德里达起码做了两件事:一是颠覆“语音中心主义”,一是粉碎语言单义性幻想。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就是极力强调语音的重要性,视语音(言语)为意义的最直接、最可靠、最完整的表征,而文字则是一种语音的替代品,如同柏拉图“床”的比喻,与真理隔了两层,处于一种被放逐的边缘地位。由于对文字的排斥,哲学将自身构成了一种关于思想和理性的学科,而言语成为了它直接的表现。正是这种言语的中心性、权威性使得它本身与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难解难分。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把思想、真理、理性、逻辑都视为是自生自在的、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自明性,所以它们时刻处于哲学的中心地位。正如阿特肯斯(Atkins)所说,“逻各斯中心主义”设定了一套二元对立的把戏,“如真理/谬误、在场/缺场、相同/差异、言语/书写、存在/虚无、生/死、自然/文明、心灵/物质、灵魂/肉体、男人/女人、好/坏、主人/奴隶等等,斜杠左侧是处于高一等级的命题,从属逻各斯,居于优先地位,而斜杠右侧则标示一种堕落,它是前者的泛化、否定、显形或瓦解。”[④h]德里达在《立场》中表示,“要想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必须颠覆这种等级秩序。”[⑤h]可见,等级秩序是德里达结构的焦点,中心是德里达瓦解的目标。他正是通过分延、踪迹、补替等概念的阐释彻底摧毁了“等级秩序”的根基,事物的二分架构。其次,逻辑中心论,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把单义性作为语言的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语言的目标。没有任何哲学放弃过这种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所以要用某种放弃这种理想的方式来从事阅读和写作。美国的两位文论家德·曼(de Man)和米勒(Miller)对此做出了决定性的演示和推进,这里无法展示。[⑥h]但是,我们所应该把握的是,一旦语言的单义性的理想破灭,我们又从何处寻找所谓的中心呢?对中心的放逐从根本上表明了对一种思维模式的放逐。德里达的意义和力量到这里就可以说完全显现出来了。解构使我们获得的是一种平等、一种多元、一种交融、一种互浸,乃至一种无序、一种难解、一种危机,等等。
塞尔登说,“如果把结构主义视为一次企图控制人造的符号世界的冒险行为的话,那么,解构主义就是在拒绝这种承诺中上演的一场反冒险的喜剧。”[⑦h]所以,在解构的理论思路和思维模式余音袅袅的今日,一种主潮文化的时代已经寿终正寝了。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一幅斑驳、众声喧哗的景观。赵毅衡先生在谈到当代西方文论的这种走向时,指出了西方“后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是一种集团利益的体现,是“部族化”的产物的见解。[①i]尽管他对此嗤之以鼻,但可以说他已经道出了其中的要旨。其实,在当代的西方何止是这“三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少数民族主义、东方主义等都可以说是解构精神的产物,都从解构那里秉承了一种无中心、无权威、多极化的精神实质。这一理论思维模式已经把结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构成了当代文论的奇观。
100多年前,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谁也不会知道没有上帝的将来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又该怎样过。上帝消亡后,它的幽灵和气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存在着,尽管已经落花流水,人却还在按照上帝的意志制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心、高峰、理想、目标,但它们的存在又都不断地“灰飞烟灭”了,留下一个又一个深深浅浅的历史踪迹。我们固然还可以追问,德里达的“英雄主义”精神还能维持多久?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能是在人两种存在方式上寻求,即人的家园式的生活方式和人对现实需要的响应。
注释:
①a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②a 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①b 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1页。
②b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可参阅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b 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章。
④b 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7页。
⑤b 关于“语言学转向”,可参见盛宁的《“语言学转向”》(载于《思想》文综第1期)一文。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实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语言转向”,它包括分析哲学把传统的哲学问题重新加以表述为“语言逻辑”问题,使“语言”取代了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意识”以及“经验”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也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反思,而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是我们在60年代以后所看到的,它的基本内容是把语言学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模式。
①c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②c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8页。
③c 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Cornell UP,1982,p19.
④c 参见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1,Text and Writing条目。
①d 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Columbia UP,1980,p65.
②d Jacques Derrida,Positions,trans,Alan Bass,U of Chicago P,1981,p26.
③d 参见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载《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8页。
①e 《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8页。
②e 参见Jeremy Hawthorn,A Concise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Edward Amold,1992,p53.
③e 罗兰·巴尔特《写作零度》。
④e 转引自Jeremy Hawthorn,A Concise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p54.
①f 罗兰·巴尔持《结构主义活动》,载于《最新西方论文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②f Fredric Jameson,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Princeton UP,1972,p111.
③f 托多罗夫《(十日谈)的语法》,转引自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④f 参见Roland Barthes,The Semiotic Challenge,trans,Richard Howard,Basil Blackwell,1988,p157.
①g 这里的分析取自Raman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Literary Theory,UP of Kentucky,1985,p59-60.
②g 参见Raman Selden,A Readers'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p52.
③g Frank Lentricchia,After The New Criticism,The Ahtlone Press,1980,p115.
④g 见《最新西方文论选》中盛宁译雅克·德里达的《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一文。
⑤g 大卫·布莱奇《主观范式》,载于周宪等编《当代西方文化艺术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①h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p279-280。中文采自盛宁译文。
②h 同上书,p286.中文采自盛宁译文。
③h 参见Robert M.Strozier,Saussure,Derrida,and the 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Mouton de Gruyter,1988,p161.
④h G.Douglas Atkins,Reading 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ve Reading,UP of Kentucky,1983,p20.
⑤h Jacques Derrida,Positions,P41.
⑥h 可参见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部分第6节的有关分析。
⑦h Ramman 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p72.
①i 赵毅衡《“后学”与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载于《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
标签:索绪尔论文; 德里达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巴尔特论文; 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