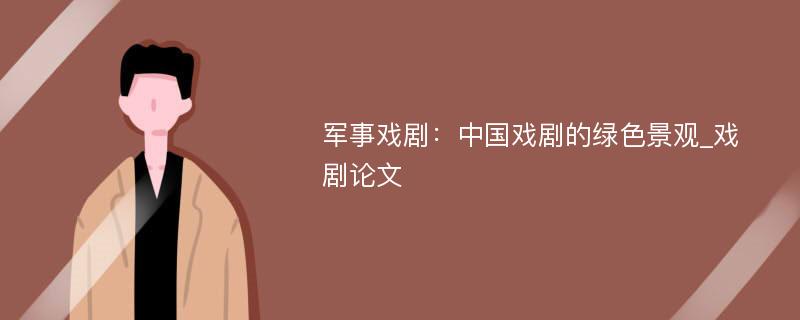
军旅戏剧:中国剧坛的一道绿色风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军旅论文,风景线论文,中国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从存在样式还是从存在状态方面说,军旅戏剧都是中国剧坛一道不容忽视的绿色风景线。在戏剧创作和演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普遍不甚景气的今天,军旅戏剧始终以数量和质量基数的双保证,频频引起戏剧界和广大观众的广泛关注,并在首都及各地舞台不断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军旅戏剧不仅是部队宣传、文化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剧坛一种引人注意的现象。
1992年全军第六届文艺会演之后,部队戏剧创作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沉寂阶段。1994年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会议和全军剧本创作研讨会为迅速打破这个局面提供了重要契机。差不多以这两次会议为标志,一大批新近创作的军事题材戏剧,以及一些曾上演过但又经过较大修改、锤炼,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剧目陆续走向舞台:《李大钊》、《苏宁》、《徐洪刚》、《摸天》、《窗口的星》、《结伴同行》、《李闯王进京》、《大漠魂》、《甘巴拉》、《空港故事》、《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桃花崮》、《这里通向天堂》、《青春涅槃》、《许永楠》、《飘落的雪花》、《昆仑雪》、《最危险的时候》、《海风吹来》、《热血甘泉》、《都市军号》、《湘江、湘江》,歌剧《阿来巴郎》,音乐剧《芦花白,木棉红》,京剧《香江泪》。如果我们把在这之前就以较大影响赢得剧坛普遍好评的歌剧《党的女儿》,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抗天歌》和《冰山情》等优秀剧目计算在内,那么,军旅戏剧的确展示出了一幅蔚为大观的景象。
剧目数量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军旅戏剧繁荣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军事文艺创作领域,军旅戏剧在全军一盘棋思想指导下,摆脱了各自为阵的传统窠臼,以集中精兵强将,协作攻关方式,努力推出高质量作品,最早迈出了摆脱低谷、走向健康发展的步伐。精品战略口号的提出和各项激励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剧目开始投入了创作。军旅戏剧创作已经进入了演出、排练和创作配套的良性循环阶段。近4年来,部队戏剧工作者以旺盛的热情和执著的追求,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形式与题材取向不尽相同的作品。军旅戏剧创作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行业行为或题材择取上的单一认同,在文化品性的建设方面也获得了更多意义。
三年多来,军旅戏剧形成了几次较大的发展冲击波,这一过程基本上以年度为单位,鲜明地表现为时间顺序上的三个层次,而其质量及重点则各显千秋;1994年可称为初步繁荣期,以剧目数量众多为标志引起戏剧界和观众的广泛关注;1995年当为平缓发展与酝酿期。这主要体现在各戏剧团体对已成型作品的反复锤炼、多方演出,以及为重新“薄发”而做“厚积”之准备;1996年的显著特征是,注重选题质量,集中优势兵力,发扬协作精神,向精品目标奋力冲刺。为纪念建军70周年和中国话剧运动90周年,部队话剧团体将在今年推出一批新作,其中正在创排的总政话剧团的《男人兵阵》,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虎踞钟山》,沈阳军区前进话剧团的《炮震》,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宋王台》,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的《老兵》,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的《兵妹子》,空政话剧团的《豪情盖天》,以及总政歌剧团的《血谷》等剧目已显露出良好的迹象。
军旅戏剧在努力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创作进程中,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歌颂现代军人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描写与塑造“英模”人物以及增强剧作的纪实性方面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突破,人物更加贴近生活。譬如,话剧《徐洪刚》在展示英雄见义勇为事迹的同时,提出了新的英雄观问题,即,英雄不仅有着平凡的过去和辉煌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还有着需要长久发展的未来。由于徐洪刚在剧中不仅被当作英雄、而且更多地被当作艺术典型来塑造,所以,平凡与伟大,过程与瞬间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徐洪刚身上便集中体现为一贯以之的正直品格的养成,而这出戏给人启示的恰恰是这种朴素而又实事求是的新英雄观。
相同类型的话剧《热血甘泉》则避开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戏”必写“典型大事”的不成文惯例,从大处着眼,于小处落笔,尽力捕捉那些与揭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相关的平凡小事和每每令人动情的生活细节,展示“英模”人物平凡、真实,与常人更易相通的一面。剧中对李国安与母亲、妻子、儿子亲情关系的生动描述,就显露出较强的人文关怀精神,体现了经过艺术加工后生活所应该具有的某些特质。我们在剧中看到,家人间的真挚和温情替代了空泛的豪言状语,战友间的平等交流与诚恳相待替代了居高临下的教悔,观众看到的首先是一个充满善意、颇具人格力量和正直色彩的“好人”。
在继续保持与发扬军旅戏剧创作优良传统的同时,努力拓宽审美视野,在艺术上不断创新方面,部队戏剧创作业已显示出色彩斑斓的局面,初步形成了南北两片各有侧重的特殊格局:南片风格细腻,着重“写事”、北片风格粗犷,着重“记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作品,以浓烈的地域意识和时代赋予的人文观念,致力于表现特殊地区(如特区和西藏地区)部队生活,其作品普遍注重戏剧情节与人物关系构筑的完整性。如《青春涅槃》、《空港故事》、《都市军号》等;北片则显出另一番景象,沈阳军区前进话剧团、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空政话剧团、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的作品,则多以纪实手法频频推出个体或群体的“英雄大写意”,着力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譬如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徐洪刚》、《甘巴拉》和《热血甘泉》等剧目。
部队各戏剧团体在坚持弘扬主旋律和以军事题材为主的基础上,在艺术追求方面,已经把多年来铸就的强化团队自身优势和建立地域特点等传统作为更加明确的目标取向。
部队戏剧团体的现存格局是与各军区、军兵种的分布相吻合的,这就决定了各团在生活层面的接触和表现方式的选择上除了应该具有军旅的一般共性外,还应建立自己独有的属性,如空军之于蓝天,海军之于大海,兰州军区之于中国西部无垠的大漠和壮阔的冰山,广州军区之于经济发达的特区,成都军区之于西南民族风情和西藏雪域高原,等等。区域特色的展示不仅仅是为了艺术表现时的与众不同,也是生活对戏剧创作者的基本要求,因为特定的“区域”已经同那里的守卫者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作为一个例外,总政话剧团则努力选取更高、更开阔的美学视点来建立自己的风格类型,地域对其已不再体现为某个局部,全方位地观照军旅生活构成了它责无旁贷的“本份”。从总政话剧团多年的创作实践,特别是从近年来创作的《决战淮海》、《李大钊》、《中国:1949》、《最危险的时候》等剧目看,追求戏剧风格上的大气与恢宏已成为其重要标志。
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总政话剧团创作排演的大型全景式话剧《最危险的时候》,是军旅戏剧乃至整个中国剧坛值得一书的事情。这部纪实性剧作以大气的风格和扫描式的审视,比较全面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期间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革命武装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其场面之大,所涉人物之多,表现时间跨度之长,在新时期以来的话剧创作中实为鲜见。创作如此规模的戏剧,即便对“兵强马壮”的总政话剧团来说,也构成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大到对抗战期间党史、军史中重大事件、重要战役的恰当分布与阐释,小到众多特型演员的选定以及每个细节与重大事件的有机连接,都需要主创人员作出精心处理。编导在作品的宏观把握上,采取了以典型事件的逐一表现为基础的散点构剧方式,以凸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戏剧精神主线,较好地满足了戏剧艺术和历史表现的双重需要。
近年来,部队文艺团体在狠抓戏剧创作繁荣和军事题材深化的同时,也注意了艺术形式和艺术种类的拓展,在话剧创作的主流之外,音乐话剧、京剧、音乐剧、歌剧、小歌剧等形式都有所涉猎。例如,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大型京剧《香江泪》在京剧样式做了大胆探索和尝试,在保持和发扬京剧特性的基础上,吸收了话剧和歌剧的优长,明显扩大了观众面。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的被命名为大型歌舞诗的舞剧《雪花·雪花》,以抗联女英雄赵一曼事迹为基本素材的舞剧,依托东北林海雪原的背景,用浓烈的诗化手化,塑造了刚柔兼济的女主人公雪花的形象。紧凑的剧情、适时的插曲、充满诗情的画外音与较为细致的舞蹈编排等因素的有机交融,使全剧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型音乐剧《芦花白,木棉红》是近几年部队推出的重头戏之一。之所以将其定位于音乐剧,并在剧、舞、歌等音乐剧基本要素构成上做了精心处理,并非单纯出于戏剧样式选择的考虑或追寻时尚之举,很大程度上是对纯歌剧作为小众文化某种非广普品性的回避。为使其尽可能具有大众文化色彩,剧之流畅,舞之优美,歌之动人,以及它们彼此之间以民族风格表现为基础的有机结合,成为该剧遵循的基本原则。军嫂芦花为支持丈夫安心服役,独自承受了家庭困难与重担,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一原本沉重的话题却是用充满民俗风情与都市气氛的内容,及与之相应的舒缓紧凑相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舞蹈《芦花舞》、《上大梁》和主题歌《芦花花》、《四季歌》以及伴之出现的舞美设计都显示了一种带有沂蒙乡间特色的纯美意境,而舞蹈《背媳妇》则渲染了欢快的浪漫主义气氛和对生活充满企盼的昂扬理念。白色作为全剧前半段舞台背景的基本色调凸现了主人公芦花品德的高洁,诠释着军嫂身上负载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现今改革开放社会中的特别意义。即使直接表现芦花带病运送苹果的场面多少含有令人“辛酸”的成分,也因众退伍兵将红花别在苹果车上,以及一曲动人的《嫂子之歌》唱出的“但愿天下当兵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妻子”而具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蓬勃向上的情绪感染力。
从部队官兵的实际接受需要考虑,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音乐话剧的探索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们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连续创作了《征婚启事》、《青春涅槃》和《海风吹来》等3部音乐话剧,在新时期军旅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一个话剧团体创排融歌、舞、剧于一体的作品,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他们不仅要超越自己的戏剧观念,还要超越“唱”与“舞”——这些属于他们专业以外的因素所带来的更大困难。尽管话剧界和歌剧界对话剧加唱加舞尚有不同看法,而且以西方音乐剧作为一切衡量准绳的人们对如此探索或许还颇有微词,但令人欣慰的是,部队官兵和广大社会观众是乐于接受的。人们愿意看,也的确好看,难道不是一种标准吗?
地处南中国开放前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多年来把反映特区部队在特殊环境下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光荣本色视为本职。他们推出的大型话剧《都市军号》把当代军人形象的塑造始终置于矛盾重要的漩涡之中,坦诚地展现他们的痛苦、思考与不懈的奋斗。同北片的“英雄戏”经常涉猎的诸如“奉献”、“牺牲”一类军人传统价值观问题相比,《都市军号》展示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军营所面临的新问题。例如,李粮食、区吉祥是来自贫困和富裕地区不同类型的士兵,前者质朴勤奋,却为家庭经济窘境所困绕,后者接受新事物快,反应机敏,但缺乏吃苦精神,因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便有了差异,这种差异在特区军营中所造成的心理波动或许更为明显,而发生在营区里的“荔枝事件”则折射出了相当一些官兵失衡的心态。
从编织故事的角度说,以这部剧作为代表,可以看出南片的作品普遍注重戏剧情节与人物关系构筑的完整性。程成与安静,方原与梅子,柳江南与程母……每一组人物关系都蕴含着一个与全剧主线有着密切关联的故事,而这些对我们所强调的“可看性”来说,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部队戏剧创作是富于成效的,求精与热情是戏剧艺术家们表现出的共同特点。但进取中面临的问题也是相似的:军旅戏剧的可看性与题材的深化依然构成我们的难点。超越军旅戏剧既定的模式和尊重部队官兵的审美习惯及条件是一对矛盾,保持部队戏剧特色、传统与向全国一流剧目看齐有时也是一对矛盾。当然,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日益变化和发展着的军营生活不断向剧作家们提出了挑战,消除隔膜,缩小差距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