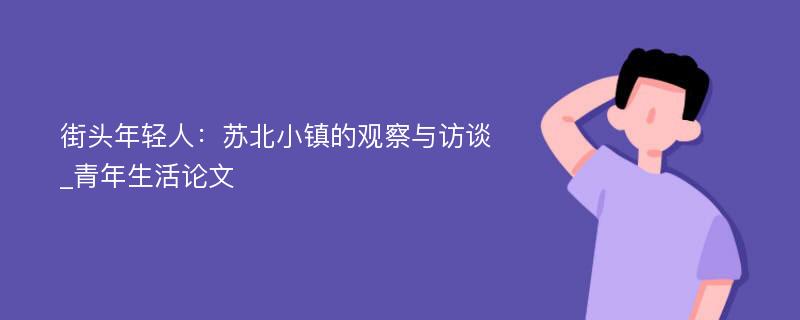
街角青年:来自苏北小镇的观察与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街角论文,小镇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街角青年”画像
在我们那个不大的苏北小镇街头,总有那么一群人不时晃在人们的眼前:他们,男,一般在四人组以上,十七、八岁的样子,有的脸上分明还挂着幼稚。夏季将至时,他们早早换上刷有英文字母的花花绿绿的衬衫或T恤,甩着火红色披肩长发,或晃着金黄色“板寸”,或摇着“寸草不生”的脑袋,吞云吐雾,迈着“外八字”步,游逛在街头巷尾。
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特别抢眼:耀眼的着装,“过旺”的人气,故作的坏笑,以及时下最流行的“先声夺人”的中英文粗话。
他们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某个中学的校门口,然后某个“倒霉蛋”要等着“挨扁”了。本分的学生见了他们多有“老鼠见猫”般的惊恐,常常目不斜视地快步穿越他们,能多快就多快,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当然,也有那么一小群人远远地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痛快地扔掉书本,尽情地“潇洒”、“玩酷”。
他们的身影更是频繁地出现在舞厅、酒吧、网吧和游乐场内,小小年纪的他们放纵地玩,不熟识门路的新老板往往胆战心惊于他们的“拍拍屁股”走人,更怕一个不留神,哪个人翻了脸,自己的店铺成了“练兵场”。
逢年过节,这些“快活”的小青年更爱成群结伴地走上街头,点上冲天大雷朝垃圾箱、马路中心一扔,然后望着被大雷炸开的乌七八糟的垃圾,望着捂着耳朵惶惶而逃的人群,爆笑!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上了年纪的老人过节时已很少出门了……
就是这样一群让长辈们“深恶痛绝”的小子,就是这样一群社会对他们都有点无可奈何的小青年,他们终日游荡,嬉戏于街角,“街角”成为他们生活天地的一个重要支点。
“街角青年”的研究与界定
“街角青年”是一全球性现象,无论在非洲、大洋洲,还是在亚洲、欧洲,因此引起国外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在1936年到1940年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成员的身份,参与到他们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在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最后得出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纳米比亚社会学家彭佩拉尼·穆福恩针对南部非洲街头青年不断增加的状况,从“街头青年”的身份背景、引发原因,以及政治制定上进行分析,提出整治“街头青年”现象需要走多部门综合治理的道路。
我国目前的有关研究还不多,主要是张园对某城镇街角无业青年的调查,里面涉及无业青年的身份特征、街头生活方式等,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街角无业青年的面貌。
尽管在“街角青年”的研究上有一些成果,但对于“街角青年”的定义,研究者之间却存在分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对“街角青年”应视其与照管他们、为他们提供住所的成年人的关系而分门别类,分为“街上的青年”和“街头流浪青年”。“街上的青年”,指那些参与经济活动的青年,如乞讨、替购物者拎包、擦车,以及贩卖小商品。他们在街上干活,非常显眼,据说他们有家可归,并且向家里交钱,在某个家庭或家户里有归属感。而“街头流浪青年”,则离家更远,他们与家户或家庭的关系断断续续,即使有也非常冷漠。许多人想要离开家或者监护的成年人,到外面生活(彭佩拉尼·穆福恩,2001)。
本文中所研究的“街角青年”,更接近于上述的“街头流浪青年”。其内涵的基本要素是:(1)长时间呆在街头;(2)游逛街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3)没有从照管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监督,但保持一定的联系。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苏北小镇上的一支“街角青年”群体(出于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称其为“L帮”)。他们共有七十多人,年纪在15-22岁不等,文化程度总体不高,绝大部分是初中以下。他们中好多人怀有“一技之长”,譬如某某地区赛上的“散打冠军”、某某“台球高手”等。“磊哥”是“L帮”的老大。“狮子头”、“小斌”、“三块钱”(以上均为化名)是经常“拧”在一起的几个人,也算是掌管“L帮”的第二、三把手。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人士大都加以排斥,他们被清一色的称作不学无术的“小痞子”。而“L帮”置身于街头巷尾,却自得其乐,对外界的指手划脚往往极端敌视。
国外研究表明,关于“街角青年”的可靠资料很难搜集,原因在于他们过着一种隐蔽、流动、不可预测的生活。鉴于此,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们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滚雪球抽样,从朋友的亲戚(“磊哥”)入手,通过他认识、熟悉在这个圈子里混的孩子们,运用“访谈法”和半参与式观察法,获悉了“L帮”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故事。在材料整理上,我们尽可能通过回忆,将当天访谈的内容详加记录,并进行归类,一些零散、隐晦的东西往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补充问询。同时,我们也试图结合十多年来所看到和所了解的“街角青年”状况,记下脑海中突然出现的闪光点。
街角权威的树立
“L帮”是以小磊为首。小磊年纪不大,才十七、八岁,文化程度也不高,小学都未毕业。很奇怪,如此的他如何成为“一帮之主”?我们曾暗自猜想:他是不是因为早早加盟了某个小团体,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那个团体老大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成为“一号接班人”,才大红大紫起来。小磊听后摇了摇头,潇洒地吐了个烟圈,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已写满了老成:
“是这样的,小时候成绩不好,实在厌倦了天天挨‘老师’骂,挨‘爸妈’板子的日子,很想好好地玩——从偶尔逃课,到时不时地来个离家出走,到最后我不走人家都要赶我走,我不满11岁就完完全全地离开了课堂!”他苦笑了一下,突然问道:“你说那时候有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有没有权力说不要就不要我了?你能说我一定就是歪才吗?”他接着讲下去,“那时候虽不懂事,却也真正结交了几个患难朋友,小斌就是一个,我们是在逃学路上认识的。这不算是臭味相投吧?”他笑着问——“我们也陆陆续续地跟过几个‘老大’,远远地跟着他们去玩、蹭饭吃,可他们一般不理会我们,有时莫名其妙的火还会发到我们头上,少不了受罪。其实,他们算什么,初中生而已,仗着块头大点……”
“不知不觉,就在社会上混了三四年,吃了不少苦头,有时也曾想再回学校读书,可学校根本就不可能再要我,我也很怕再回去受罪……这样时间久了,爸妈对养了我这样的儿子也认了,只求我不要再惹事就好。我比就放心地把玩得要好的朋友带回家,他们对我爸妈都很尊敬,我们这群坏孩子也因而能吃到热菜热汤的。当然,天天呆在一起,彼此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的事情,我通常就成为调停人。他们因为我做事比较公平,处事也挺稳重,索性联名提议让我做他们的老大。”“就这么简单,我们有了自己十几个人的小团体,也因为我们大伙处得比较好,我从不打骂下面的兄弟,不摆老大的样子,于是,朋友的朋友过来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过来了,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现在有七十几口子了。怎么样,号召力还算可以吧?”
“义气就是面旗,我讲义气,他们就跟我走了!”小磊是这么说的,他让我们想到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手下这么多兄弟跟我,为的是什么,是有口饭吃,是不被人家欺负。所以,只要我有好处,我就一定留一份给我的兄弟们;不论是我的兄弟遇上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帮他摆平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太讲理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有说话的份量:一个是‘钱’,一个就是‘拳头’。当然,我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对兄弟们好,我也绝对放心他们对我忠心,而且我的拳脚功夫也差不到哪里去,不然会当上武术学校的校长吗!”。
“磊哥”的义气,在我们和“三块钱”(“L帮”核心成员之一)的交谈中也得到证实:“我开始时不是跟磊哥的,我做别人的小弟。每逢打架,他们就要把我支到第一线去,可等到吃的时候、玩的时候就根本记不得我了。不像‘磊哥’,有好处的时候他一定会带上我们这些小弟兄。有几次我们和别的小帮派冲突,他都把我拦到后面,嫌我年纪小……”说到这里“三块钱”又是感激,又有点不满,掳了掳袖子,亮了亮他的肌肉——“我已经和‘磊哥’说了,下次我一定要上的。让他一个老大冲在前面,像什么话?”
从上面的交谈可以看出,“街角帮”的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长时期的经常交往,其核心可以追溯到成员们的青少年时代。由于住处相隔不远,使他们有了最初的社会交往机会,慢慢通过街角场域发展成为“街角帮”,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通过在教室里或学校操场上的交往而形成(威廉·富特·怀特,1943)。“街角帮”的权利结构呈金字塔分布,居于顶端的“领袖”拥有很高的权威,受到所有人的佩服与推崇(张圆,1997)。但要想成为“街角帮”的“领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有成员都指望他履行他的个人义务,因此往往需要当事者为人公正,敢于主持“正义”,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对待兄弟十分义气,为人够品;具有极强的能力,能给手下兄弟带来好处和实惠等。如果他做不到这几点,就一定会引起混乱,并危及他的地位。因此,从统治类型上讲,它属于马克思·韦伯笔下的“感召型”统治,即其统治不是靠正规的法律、制度,而是凭借个人的魅力、感召力。
街角活动经费的由来
在“街角青年”的群体活动中,家的作用很小。除了吃饭、睡觉或生病外,他们很少呆在家里,如果朋友间要找谁,也总是首先到街头去找(威廉·富特·怀特,1943)。当然除了经常出没的街角外,他们还有一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活动场所。
常常看到小磊这帮人去游乐场、泡舞厅、下馆子(通常还是镇上数一数二的酒店)。遇到太热、太冷,或阴天下雨的话,他们就聚在小磊租的房子里,看看古惑片,唱唱卡拉OK,打打牌,抽抽烟,彼此间并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偶尔不知因为什么,集体一阵爆笑。
他们玩的时候往往还带上一两名女眷,很大方地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马子”。那些看上去泼辣而又任性的“小美眉”的加入,再度活跃了他们聚会的气氛,打情骂俏声和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语连成一片。
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离开学校,他们的家庭是不愿意提供什么钱供他们瞎玩的。因此,可以推断“L帮”的活动经费不能通过“会员费”的形式获取。那么,他们休闲娱乐的经费从何而来?如果在群体冲突中某一成员再“光荣负伤”的话,医疗费用又从何而来?
眼前的小磊穿着名牌衣装,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租的)、家具和家电,还拥有自己的面包车,与一般流浪街头的“小混混”的落魄情形相比,实在是大相径庭。对此,我们很是诧异。“放心吧,我可没有拦路抢劫、杀人放火,那个太小儿科……”他格格地笑,过了一会,一脸凝重地说:“我在给一位老板做事情。”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老板”才是小磊他们的“衣食父母”,也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也就是说小磊他们靠青春、靠力气在吃饭,他们就是这镇上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的贴身保镖,替这位老板守护他的产业、维护他的地位,当然难免也会充当债权人的代言人,去“出差”,去“讨债”。小磊有时也叫累。他常说虽然年纪比较小,但心烦的事特别多,心理年龄已经很老了。他是堂堂“L帮”的老大,必须考虑和担负群体活动的全部经费,必须为七十几个小弟兄们安排好出路。小磊与这位雇主老板的结识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虽然在替人办事时难免有过无奈和不满,但毕竟金钱money的诱惑力是无穷的。他们之间的合作至今看来还比较愉快。
不仅如此,小磊还积极去开铺子。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多多少少地也积聚了些“社会资源”,比如,认识某条街道的管理员、某个饭店的经理、某个社区的保安等。于是,他便利用这些关系,顺利地筹办起“服装店”、“音像店”、“茶室”。他让小弟兄们去管理店面,可这些正经生意据小磊的说法是“开一个砸一个”。显然,“街角青年”的懒散、不懂经营管理,以及形象不佳,导致客源稀少,生意越做越窄,最后只得关门大吉。
小磊他们去当保镖,这是我们不曾预料到的,事实上也应在情理之中。以小磊为首的这帮人吃饭、穿衣、娱乐等,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而这些根本不能指望父母、亲戚给他们。与镇上“名流”的合作,则解决了这一经济难题;而且在相互利用中,还可以传扬自己的名气,工作上相对比较清闲,无非充任“打手”的简单角色,符合“街角青年”的性格特征。
“街角青年”的归路
对于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街角的这一帮人似乎多年来毫无变化,但实际上,变化却一直在不断发生:一方面,有新的青年通过朋友介绍进来,加盟这支队伍;另一方面,有老成员由于种种原因脱离这支队伍。
当“街角青年”接近或进入成家立业之年,他们不可能再吊儿郎当的……这时他们的父母会焦急地为他们张罗起人生大事——婚姻。小磊压了压喉咙,说道:“我的兄弟们有的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们自己一点不急,可他们的爸妈却闹翻了天。”曾经有一个玩得要好的兄弟整整围着他转了三天,什么也没说,终于在第三天的晚上,他跪了下来:“‘磊哥’,我妈帮我找了个对象,我要结婚了,以后不能再玩了!”小磊一把扶起了他:“别这样嘛,都快成家的人了。其实我也早想和你说了,你要玩的话,我也不会让你瞎玩了,好好过日子吧!”显然,处于人生这一阶段的“街角青年”应该做的是“安家立业”,谋取适当的职业,以便养活自己和全家老小。即便他们还继续在街角闲荡,但他们的兴趣和活动已与“街角帮”分道扬镳。
如果说“街角之路”是年轻人走的一段歪路,那么从军当兵似乎已经成为家长让孩子洗心革面的一把利器——“划出人生的又一道起跑线,把生命交给绿色,生活浓缩为简单的口令,军装裹紧所有的信念,将深深的思念交给远方”。艰苦而充实的军营生活,对于增长“街角青年”的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军营生活也为“街角青年”身上镀了一层金,为其以后的发展谋取了一份“政治资本”。于是,有的“街角青年”到部队当了兵。
听“小斌”讲当时他们送别另外一个好兄弟“阿剑”时,小镇的大操场上一大早除了穿军装佩锦花的,就是他们“L帮”众多弟兄。他们相继和“阿剑”击掌、拥抱,呼唤着他的名字,“叫骂”着让他留下来……我们能想象出当时感人的场面,也能想象出“阿剑”噙着泪花作别终日相伴的兄弟时,绝对有比离别亲人还大的痛苦。因为小弟兄们的身影实在太熟悉了,而他将独立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也想不玩了,早想把事情交给‘狮子头’。可你知道他们怎么着?他们很委屈的:‘磊哥’,你用我们的时候就找我们;不用了,就让我们回家——还当我们是兄弟吗?我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我现在和亲戚在做生意,走一步,算一步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磊哥”也如是说。
应该看到,“街角青年”在脱离街角社会的过程中,往往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无形之网牢牢罩住。对此,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即使能够摆脱,也存在一定时间的新的社会适应问题,特别是开始阶段。正如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街角社会的活动模式是固定的,成员们每天聚在一起,频繁发生作用。无论他是位于最高层,在集体事件中发起行动;还是位于中层,服从领袖的提议,并为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发起行动;或是位于群体的底层,在集合事件中总是追随别人——每个成员都有一种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稳定的,并通过群体长期不断的活动而固定下来。如果谁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就必须保持他与别人相互作用的方式。他需要使他的活动按照习惯的渠道进行,否则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威廉·富特·怀特1943)。“街角青年”通过结婚、参军而脱离街角社会,其生活方式仍需一段时间的调适,而调适往往是某种体验痛苦的过程。
街角社会的思考
就这样结束了对“L帮”的实地调查,对这个神秘的“街角社会”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感情,心中产生诸多感慨:
1、被人遗忘的“街角青年”
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匆匆过往的街角,却是小磊这群人长期社会化的场域。虽然他们早早地踏入社会,但是他们的社会化过程绝对是不完全的,因为缺少家庭关爱和学校教育这两个重要的社会化要素。
社会学认为,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开端,并为个人一生的社会化奠定基础。父母的权威形象和亲子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家庭对个体的心理和观念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塑造力。任何一个对孩子负责的家庭,绝不会轻易放他们走向街角。“街角青年”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问题家庭”,有的是父母感情不和而离异,有的是家长终日忙于自己生意或游乐于麻将桌上,对子女缺乏责任心。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长期遭受“亲情冷落”,他们渴望寻求一片“眼不见、心不烦”的自由,于是走出家庭,放纵自己玩乐,向街角倾诉心声。“三块钱”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爸爸、妈妈天天只顾着打麻将,家里乌烟瘴气,他在外边玩,刚好免得看到,也乐得没人管的清闲,省得再和父母顶撞上了。
我们的学校不能说毫无责任,但很多老师不喜欢“差生”,尤其痛恨那些“害群之马”。在谩骂与责罚仍不生效的情况下,老师们出于保证整体教学质量的需要,出于维护师长的自尊,必须把一些“无药可救”的学生遣送回家。还有部分学生不能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竞争,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排斥,在“分数至上”的教育体制下,他们无法建立足够的自尊和自信,无法获取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专门技能和价值观念,使得他们的个体社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以不健全的个性品质走向社会(张园,1997)。
此外,放眼今天的电视、电影、VCD、网络,铺天盖地的是警匪片、言情片、暴力片。它们对尚没有足够自控力的孩子来讲,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他们常常高呼“酷毙了”、“帅呆了”,去模仿他们的组合,去“弘扬正气”,去发泄自己。国外一项关于电视暴力的研究已经证明,电视暴力确实导致了观看此类电视节目的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两者之间有强相关关系。
当这样一帮孩子“拉帮接派”地走上街头,他们也不会想过对那些压抑许久的在“好”与“坏”边缘挣扎的孩子有多么大的感召力,那些蠢蠢欲动的孩子亲眼看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潇洒”与“哥们义气”,于是“滚雪球效应”出现了,小镇上的这类“街角青年”成放射状膨胀。
2、被人误解的“街角青年”
提到街角青年,十之八九的“正派”人士会咬牙切齿、不屑一顾,然而有没有人真正思考过:这一畸形群体的形成,有家庭的错,有学校的错,有社会的错,有媒体的错……学校容不下差生,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也不可能为这些“盲流”留有职位,“街角青年”的容身之所似乎窄得只有街头……他们被社会深深地打上了“坏小孩”的标签,似乎出路只有被自然淘汰。幸而他们有的结婚了,有的参军了;但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参军,又无人替他们操办婚事,在社会上混得不如意的人来说,如果社会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们,结果只可能会加深“街角青年”与社会大众的隔阂,加速“街角青年”自我沉沦与毁灭的步伐,间接地把“街角青年”送上犯罪的深渊。反之,社会如能换一种视角看待他们,家庭、学校、媒体都能挑起一份责任,多投入一点关爱,那么“街角青年”总有一天会自觉地重新走回社会的主流。
3、“街角青年”余思
在与小磊这帮人的接触中,我们了解到不少人有很强的心愿跟着“磊哥”,把他们共同的事业做大。“L帮”核心成员之一的“狮子头”,每每向我们提及电视里“古惑仔”的侠肠正气时,情绪就特别高涨,他说:“我当初选择古惑路谁也阻拦不了。选定了这条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们的世界很精彩。我们有‘磊哥’这样的老大,我们的事业一片辉煌!”“事业”与“辉煌”——可他们期待的是怎样的事业?怎样的辉煌?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忠实于街角群体?为什么会忠心于街角权威?
可以说,小磊这个“老大”是分散的小青年在组建群体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街角青年”大多处于人生的“第二断乳期”,在叛逆、追求无拘无束之外,他们物质上、精神上都需要一个成熟、稳重的“老大”为他们撑起半边天。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权钱交易阻断了亲情、友情、爱情,而在这方街角天地里,他们确能感受到群体协同作战的快乐,感受到义气的温暖,于是他们安于享受这种看似无忧无虑,却有着极大负面作用的生活。所以,改造街角社会现状,要从影响街角权威着手,同时适当注意这个年龄段青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
标签:青年生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