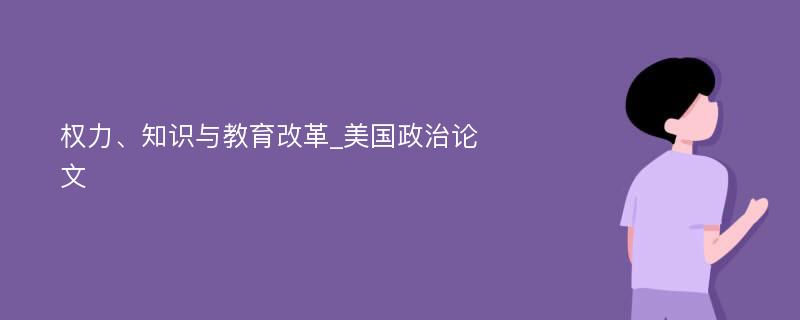
权力、知识与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权力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说明:今天的美国教育正处在一个保守时期。众多的学校被责之为失败的机构,因为它们远没有适应美国社会的环境变化。许多人甚至把美国公立教育视为经济效率低下、失业、贫困和国际竞争力丧失等的替罪羊。这种责难实际上是对平等主义准则与价值的攻击,它表明当代美国教育正出现一个右转的倾向。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把上述人们分为四个部分。作为右翼联盟的四个基本构成部分,尽管其各自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和动力机制,但是,它们却投身到一个共同的保守性运动之中。该四个群体分别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专制的民粹主义以及作为正呈向上流动趋势的专业和管理新中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部分。
中图分类号:G57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6)01-0003-14
导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教育的保守时期。众多的教育机构被视为是失败的机构。高辍学率、“功能性识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的下降、规范和纪律的丧失、在传授“真正知识”和经济实用技艺方面的无能、在标准化考试中可怜的分数,如此等等,人们把所有这些问题的罪责都指向了学校。我们被告知,正是以上问题导致了经济效率下降、失业、贫困以及国际竞争力丧失等。只有回归“共同文化”,让学校更有效率、对私营部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有如上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在这些诉求的背后,平等主义的准则和价值受到攻击。尽管是批判者浮丽的话语具有隐蔽性,但在本质上,他们实际已经把“太多的民主”——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视为我们经济和文化正在衰落的主要原因。很明显,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在英国撒切尔政府中的前教科部大臣肯尼思·贝克(Kenneth Baker)的话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保守性的程度。他针对教育领域近10年来右翼的成就而评论道:“平等主义已经过时了”。[1] 在说这句话时,贝克语气非常肯定。
由这些攻击所构成的对平等主义的威胁,通常并非那么直白,因为它们总是被表述为“改革”教育系统(目前被视为整体处于危机之中)的竞争力、工作、标准和质量这样的话语。在目前的英国“新工党”政策和美国的相似政策中,都不乏如此清晰的话语表述。两个国家的教育政策甚至以更多的方式,在延续着由早期保守主义政府所倡导的走向。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所发生的这一切视为主流经济精英们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到教育上的结果,就未免太简单化了。众多的攻击尽管表达了它们欲把教育重新整合到经济议程中的意图,然而,它们并非是简单地回归经济,而是触及到了文化战争以及与阶级集团和阶级权力相一致的种族、性别和性倾向方面的斗争。[2]
教育是一个斗争和妥协的场所,在此,围绕关于我们的学校应该如何做,服务于谁以及应该由谁来决策等,人们争斗不休。然而,它又是一个重要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哪一种资源、权力、意识形态、资金、课程、教学以及教育评估被认可,各种冲突也频频上演。因此,教育既是因也是果,既是决定性的也是被决定性的。[3] 为此,在一个很短的篇幅中,我无法对教育的复杂性予以完整的勾画。相反,在此我仅希望围绕教育能对当下美国正在走向保守主义方向的一些主要冲突提供一个大致的轮廓。复数“方向”(directions)在此是一个关键词。正如我在他处所特别加以详解的是,加上这个“s”对于我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4] 因为,在右翼转向中,存在诸多的而不是单一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趋势。
尽管在此我的关注点更多地聚焦于国内,但如果不把它纳入到一个国际语境中,要理解美国当下的教育政策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掩藏于高标准、更刻板的考试、为就业而准备的教育以及加强教育与经济间更为密切联系等这些诉求背后,是人们对在国际竞争中落败、把工作岗位和金钱更多输给日本、持续增长的“亚洲虎”经济、墨西哥以及其他地方所产生的恐惧。[5] 同样的一种情形是,在美国正出现一个明显的重塑共同文化观(有选择性的)的趋势,该趋势强调“西方传统”、宗教和英语,这实际上折射了人们对拉美、非洲和亚洲文化的恐惧。我的探讨将就此背景而展开。
美国右转趋向是右翼为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基础联盟的努力的结果。这个新联盟在某些方面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赢得了“达致共识”的战果。[6] 正如,在有关社会福利、文化、经济和教育等议题上,它已经创造性地弥合了不同社会倾向和诉求间的鸿沟,并且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领导之下。它在教育和社会政策方面的目标就是我所称之为的“保守主义的现代化”。①
在这个联盟内部有四个基本构成部分。尽管每一个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和动力,但是,它们作为不同的支流又共同汇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洪流。这几个构成部分包括:新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专制的民粹主义者以及一个更为特殊的部分——正处于上升状态的专业和管理新中产阶级。在此,我将对前两个部分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是它们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目前正主导着教育的“改革”。然而,我并不想忽略后两个群体的影响力,关于它们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妨参阅我的《以“正确”的方式教育》(Educating the" Right" Way)(Right在此具有“右”和“正确”的双关含义——译者注)一书。[7]
新自由主义:学校教育、选择机会和民主
新自由主义者是联盟内部支撑保守主义现代化的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他们推崇弱国家观。在他们看来,凡私有的就必然是好的,而公有的就必然是坏的。像学校这样的公共机构就是一个“黑洞”,钱投进去,然后就消失了,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足以让人满意的结果。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有一种理性的形式,它比任何其他的都有效,这就是经济理性。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的“伦理”是压倒性的标准。所有人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行动。的确,经验意义上的看法也对这一立场提供了支撑,即所有人的行动都是理性的。然而,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动机世界的中性描述,不如说它实际上是对一个带有获得性等级标志特征世界建构的说明。
支撑这一立场的便是作为人力资本的学生观。即所谓这是一个存在高强度经济竞争的世界,学生作为未来的工人,必须给予他们必需的技艺和品行,以有效地去应对竞争。② 进而言之,把钱花费到那些没有与经济目标直接联系起来的学校是令人生疑的。事实上,就像是“黑洞”,如目前这样被组织和控制起来的学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正在浪费那些本应该进入私人企业的经济资源。因此,不仅公立学校没能为我们的孩子成为未来的工人而做准备,而且如所有其他公共机构一样,他们正在吸食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这是“生产者掌握”(producer capture)的结果,学校是为教师和政府官僚而不是“消费者”建立起来的。它们只是满足职业人员和其他自私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需要,而不是对它们还有指望的消费者。
“消费者”的观念在此十分关键。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消费者的选择机会”是民主的保障。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教育仅仅被视为如面包、汽车和电视一样的产品。[8] 通过学券和可选择性计划,以市场介入的方式,教育便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自我管理的轨迹。因此,民主也变成了消费实践。在这些计划中,公民的概念被置换为购买者。可以想像,由此而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如此以来,我们与其说民主是一个政治意义的概念,不如说它被完全转换为一个经济意义上的概念。这种政策要义我们最好称之为“算数方法崇拜主义”(arithmetical Particularism),在此,独立的个人被作为一个消费者,被剔除了他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特征。[9]
消费者和超级市场的隐喻在此再恰当不过了。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确实有能力进入超级市场,并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自己的所需。也有些人仅仅具备我们最好称之为“后现代”消费的资格。他们只能站在超级市场之外“消费”着关于商品的意象。
新自由主义者的一揽子工程是同一个更大的进程相联系的,在此进程中,优势群体不断地对政府和穷人发泄着不满。毕竟,做出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把工厂迁到那些控制力度弱或者无工会、缺少环境管制、具有专制性特征政府的国家的决定,不是政府,也不是失去工作和工厂的劳工阶层和贫穷的社区,因为正是这些决定让他们绝望,让学校和社区处于危机之中。做出合并和融资买断,并裁减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人中很多人曾经在学校中表现很好)选择的也不是上述两者。
由于关注的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必须被视为是一个对政府雇员更为广泛攻击的一部分。具体到教育领域,他们抨击教师工会,认为它太强大太昂贵。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完全有必要把它解释为一种长期以来对妇女劳工进行攻击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与众多其他国家一样,妇女也占美国教师的绝大多数。③
在新的霸权联盟中,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创意多种多样。其中大部分要么关注教育与经济间更为密切联系,要么就是把学校纳入市场。前者代表性体现在“学校便是为了工作(work)”、“教育便是为了就业”的广泛动议上,以及对“臃肿的政府”压缩成本的刻薄要求上。后者虽不具广泛性,但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具体体现在正在推行的全国以及各州层次上的学券和选择性项目上。[10] 这些项目包括向私立和宗教性质的学校提供公共资金(尽管这些提议还存在激烈争议)。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的计划就是把市场竞争准则强加给学校。在整个美国,随着一系列关涉公共资金通过学券机制流向私立或宗教学校判例的产生以及人们对此密切的关注,这种“准市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备受争议并造成众多分裂的政策议题。④
一些赞成“选择”的支持者认为,增加父母的“声音”和选择,会给少数族裔的家庭和子女提供“教育救助”的机会。[11] 例如,莫(Moe)便声称,通过建立一个“非正统联盟”(unorthodox alliance),可以为穷人获得“离开差的学校并选择进入好的学校”的权力带来希望。[12] 只要他们与共和党和旨在改革体制的最为强大商业组织联盟,穷人也可以成功。
正如我和其他人在别处所表明的,有经验证据显示,在教育领域,“准市场”方案的进展,已经导致了当下阶级和种族分化的加剧。[13] 越来越多可信的证据是,尽管学券和选择性计划所假定的目标是给穷人离开公立学校提供了权利,而一个最终的长期效果可能是为白人子弟逃离公立学校、并进入私立和宗教性质的学校增加了机会,为富裕的白人家庭可能拒绝为公立学校纳税创造了条件。而这些公立学校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危机。最终结果是加强而不是弱化了教育的种族隔离。⑤
威第(Whitty)通过对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的综述认为,尽管可选择性计划的倡导者确信,竞争会提高学校的效益强化学校的责任,并为弱势家庭子女提供目前他们所缺少的机会,但这可能是无望的。这些预期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在一个不挑战深层的社会和文化不平等的广泛政策背景下”,他进一步说道,“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决策似乎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但是却把决策的责任由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这将挤压了旨在改善教育质量而集体行动的空间”。[14]
赫尼格(Henig)也赞同这一观点,通过仔细审视教育选择的倡议,他指出,目前教育改革运动的可悲且带有讽刺意味之处在于,考虑通过激进改革解决社会问题的健康冲动被引向了将瓦解有意识的集体性回应方向上。[15] 当这一点与实践中可能再生产传统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搅和在一起,这将造成我们改革进程的中断。[16]
第二种新自由主义愿意把更多的政府和私人的金钱投入到学校中,其条件是当且仅当学校满足由资本所报答的要求时。因此,资源要有效地应用于那些旨在建立教育系统与我们更具竞争力经济间联系的“改革”和政策上。通过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管窥这一立场的实质。在很多州,立法机构已经通过有关指导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加强它们与商业经济间联系的有关议案。以威斯康辛为例,所有教师教育项目必须包含为未来教师提供可以清晰确认的“为就业而准备的教育”的经验;所有州公立中小学的教学都必须在其正式课程中包含为就业而准备的内容。⑥
第二个例子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因果联系,但事实上,它是把教育政策和实践整合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议程中的最具说服力的陈述。在此,我所要谈及的是一个营利性电视网1频道,它的网络现在已经遍及美国中小学,面向超过40%的美国中学学生(这些中学中相当部分正面临财政压力和危机,即使有些州目前存在预算节余)。在这一“改革”中,学校被提供以“免费”的卫星电视大餐,2台录像机,每个教室由私人媒介公司装配电视监视器。该公司还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新闻联播。作为对这些设备和新闻的回报,所有参与学校必须签订一个3—5年的合同,保证它们的学生每天要看1频道节目。
这看起来很仁慈。然而,不仅仅是“有线”技术保证了1频道可以并且是唯一被接收到的节目,而且是通过合同,要求学生必须能够看到与新闻捆绑于一起的强制性广告,主要是快餐、运动衣以及其他公司的产品宣传。在本质上,学生被作为受制约性的观众被卖给了公司。因为,按照法律,学生必须呆在学校中,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意识允许把它的青少年作为日用品卖给公司的国家之一,这些公司之所以甘愿向1频道付出昂贵的广告费用,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观众得到了保障(观众是受约束的)。因此,在众多的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学校,包括学生都被转换为市场中的日用品。⑦
如我所提到的,保守主义教育政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转换了我们关于什么是民主、是否我们是私人占有性的个体(消费者)以及最终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市场的运作,等等方面的共识。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和社会政策总体上是基于市场的基本公正和正义的信念。市场将最终根据成就有效而公正地分配资源,它最终将为需要工作的我们创造工作机会。它是保障所有公民(消费者)拥有一个更好未来的最好机制。
为此,我们当然要质疑新自由主义立场中作为最高支配者的经济究竟是什么。迄今,新自由主义为我们所勾画的图景远远未能实现,在这一图景中,技术先进的工作将取代苦役,如果把我们的学校和孩子放给市场,众多人们正饱受未充分就业和失业之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不幸的是,很明显,市场反而是作为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力量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17]
关于新自由主义者要求把有偿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系统更为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不妨举个例子。尽管与高技术相关的工作岗位比例在增长,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将被提供的还是不需要很先进技术和工艺、且并无品位的工作。在零售、贸易和服务部门的低报酬重复性工作将是有偿劳动力市场的主流。事实再清楚不过了。2005年,新增加的收银员工作机会将高于计算机科学家、系统分析师、临床医学家、操作分析师和放射科技师等加起来的总和。事实上,据预测,新增加的95%的就业岗位是在服务部门。该部门包括个人看护、家庭健康服务、社工(因为社会福利的缩减,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或已经失去工作)、旅馆和酒店服务、餐饮业、运输业以及商业和书记服务等。据预测,在今后10年新增加的工作机会最多的前10个行业中的前8位是:零售业销售员、收银员、办公室职员、卡车司机、服务生、护理/勤杂工、食品配制工和门卫。很显然,以上工作岗位中的绝大多数并不需要高层次的教育。它们大多是低报酬、非工会组织化、临时性的、部分时间制和低收益或者无受益的工作。许多是同现存的、正在加剧的劳动力种族、性别和阶级分化密切相关。[18] 这就是我们正面对的经济现实,而不是游说我们信赖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所勾画的那种过于罗曼蒂克式的美景。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是社会价值的最终裁定者,市场将减少我们教育和社会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环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合理性。效益和成本分析将是社会和教育转型的引擎。然而,如此的“经济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最终后果,实际上是要使得我们介入以持续加剧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平等为特征的社会更加艰难。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以这种方式阐释了这一过程。
在男权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政治的”通常是参照什么是“经济的”和什么是“家庭的”和“个人的”维度来界定的。然后,我们能够确认两套主要的将社会话语去政治化的制度。它们分别是:第一,家庭制度,特别是被名之为现代严格的男性主持的核心家庭标准家庭形式;第二,正式的经济资本主义体系制度,特别是有偿劳动场所、市场、信用机制和“私人”企业以及公司。家庭制度是以个人化和/或家庭化来将具体事务去政治化。它把这些事务视为私人家庭或者个人家庭事务,而不是公共的、政治性的事务。另一方面,正式的经济资本主义体系制度是通过经济化而把具体事务去政治化。在此所探讨的议题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准则,或者作为“私人品”所有者的特权,或者是管理者和规划者的技术性问题,所有这些都不同于政治事务。两种情形的结果都是省略了阐释人民诉求的相关环节,这种阐释环节省略的意义在于阻止“家庭的”和“经济的”事务突破与政治的边界之间。[19]
去政治化的过程使得那些拥有极少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人们的诉求很难被倾听并按照问题的真实程度来处理。对弗雷泽而言,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诉求”话语被重新转换为市场对话和由“私人”所驱动的政策。
在此,就我们的意图而言,我们要谈谈两种主要的诉求话语。第一种是对抗性的需要诉说形式。当部分受压制群体形成一个新的对抗性认同,诉求从底层被政治化,这种话语就出现了。如此,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私人的”的事务,现在就被放置到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中了。譬如,在有偿劳动中的性侵犯、种族和性别歧视,教育和经济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就是把这些“私人”事务目前已经外溢为不再限于“家庭”领域的例子。[20]
第二种诉求话语是我们称之为恢复私有化的话语。作为一种对新近突然出现的对抗性诉说形式的反映,它的出现是试图把这些形式压回到“私人”或者“家庭”领域。这种诉求的目的是废除或者削减社会服务,解除对“私人”企业的控制,或者中止看起来似乎是“失去控制的诉求”。因此,恢复私有化话语的意图是把如家庭暴力这样的议题界定为纯属家庭内部事务而限制它成为公开的政治话语。或者它认为工厂的关闭并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过是私人所有者无可置疑的特权,抑或是非人格化市场机制的无可争辩的准则。[21] 在此情形中,这套话语的目的是挑战可能爆发的“失去控制诉求”,并把有关议题非政治化。
在美国的教育政策中,关于这样的进程有大量典型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代表。一个禁止肯定性行动政策在州政府和大学招生政策被采用的捆绑性公民投票被压倒性地通过,恢复私营化倡导者们在广告战略中额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该广告给肯定性行动贴上的标签为“失去控制”、政府不适当地介入“私人价值”。它作为始作俑者在众多州产生了连带效应。教育中的学券计划,这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诸如应该传授谁的知识,由谁来控制学校的政策和实践,以及应该如何资助学校,是否留给市场来决定等,该计划是试图把教育诉求去政治化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最终,关于“工作技艺”界定这样的基本责任交给了私人部门:一项法案以这种方式消弥了为人所责难的可能性,它认为工作是建构性的、受约束的和有回报的,如此一来,工作被定义为既是“私人的”的事务又是无可争议的纯粹的技术性的选择。所有这些都表明,恢复私营化话语的力量日益凸显。
在理解以上所发生的情况时,有必要区分一下“价值”(Value)和“意义”(sense)的合法性。[22] 这两者为不同的策略,分别指涉强有力群体和政府的合法性。在第一个(价值)策略中,合法性实际上是通过国家给予人们所承诺之物来实现的。因此,民主国家可能会为人们提供社会福利以赢得他们的持续支持。在此,国家要这样做是对抗性话语的结果,在社会舞台中,这种对抗性话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并有更多的权力去重新界定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
在第二种(意义)策略中,政府和/或支配群体试图改变社会诉求的意义,使之与真正的社会诉求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绝不是提供满足人民所表达意愿的政策。因此,如果那些缺少影响力的人们要求更多的民主以及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时,该策略的目的不是满足人民所要求的“价值”,尤其是在它可能导致失去控制的诉求的情形下。毋宁说,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改变作为民主的含义。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中,民主就被重新定义为作为无束缚市场选择的保证。在本质上,国家倒退了。“诉求”含义的转变以及它所被接纳的程度,显示了在重新界定公共与私人领域间界限恢复私营化话语的成功,也表明在一个经济和意识形态危机时代,人们的共识是如何被转向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方向。
新保守主义:真的知识教育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保守主义的联盟,我还要提起该新联盟中的第二个重要部分:新保守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对弱国家的强调,新保守主义通常倡导强大国家观。这在关于知识、价值和身体等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新自由主义的根基可被视为一种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突生性的”意识形态集合,而新保守主义则扎根于新自由主义的“残余”物。⑧(经济之外部分如文化传统等——译者注)。虽然不是全部,它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的赞美,这个过去代表“真的知识”、至高无上的道德,在此人们“各安其位”,它是一个由自然秩序所支配的稳定共同体,该自然秩序保护我们免于社会灾祸。[23]
基于这一立场,保守主义提出了强制性的国家与州范围内的课程和考试政策,“回归”高标准,复苏“西方传统”、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品格教育。然而,新保守主义对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潜在威胁绝不仅仅在一个泛泛的“回归”上,更重要的也是本质上的,在于它对“他者”的恐惧。⑨ 它对标准化国家课程支持,表明了它对双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以及对提高标准的持续性吁求。⑩
新保守主义倡导回归传统价值和“道德”已经引起广泛的呼应,在过去10年中威廉姆·本奈特(William Bennett)的《道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成为最畅销书籍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24] 本奈特是前保守党政府教育部的部长,他认为,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已经放弃了做正确的事情并听任对智力和道德标准的挑衅。”作为对此的反击,我们需要“重建对卓越、品行和基础的责任”。[25] 本奈特的书旨在为儿童提供“恢复”对“传统价值”责任的“道德故事”,这种传统价值如爱国主义、诚实、道德品格和事业心。这种观点不仅以相当有影响力的方式正成为我们的共识,而且它部分地构成了特许学校运动的内在驱动力。这些学校得到的许可是,它们被允许避开政府的一些要求而根据受托人的意愿自主开发课程。尽管这种政策在理论上尚待更多的评判,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特许学校目前已经变成了保守的宗教激进分子以及其他人们为自己的学校赢得公共资金的一种方式,而这原本是被禁止的。[26]
在这种政策背后,存在一个清晰的所谓“丧失”的含义,即信念的丧失,想像的共同体的丧失,一个在那里人们共享规范与价值、“西方传统”至高无上带有田园风格想像的丧失。它多少有点像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关于“纯洁”与“危险”的探讨,在她那里,作为想像的存在是神圣的,而“污染”是令人恐惧的。[27] 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主宰了这种话语,“他者”的文化令人恐惧。
这种文化污染观可被视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越来越刻毒的攻击(文化多元主义本身是一个包纳众多政治和文化立场的宽泛范畴),[28] 它具体体现在该主张所强调的向“非法”移民乃至合法移民子女提供的学校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利益之中,体现在保守派的唯英语运动之中,也体现在保守派试图围绕一个特殊的西方文化传统建构而对课程和教科书重新定位的意图中。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保守主义对传统课程、历史、文学和价值“衰落”的哀叹,他们的一系列关于“传统”、关于什么才算是合法性知识的社会共识以及文化优越性的历史假定。[29] 然而,最为关键的是,我们要牢记,对“传统”课程衰落如此痛心哀叹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漠视了美国人口是由众多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中美和南美以及北美土著等多个群体组成的事实”。[30] 它主要关注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来自北欧和西欧民族人们的狭隘文化观,而完全置所谓代表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更为庞大更为多样复杂的人们和社会熔铸”的事实于不顾。这种狭隘的风俗和文化反而被视为我们每个人的“传统”的胚胎。它们不仅要被纳入到教学中,而且要凌驾于所有其他风俗和文化之上。[31]
如劳伦斯·列文(Lawrence Levine)所提醒我们的,一个选择性的、错误的历史理解会助长新保守主义的乡愁。经典和课程从来就没有稳定过,它们总是处于一个持续的修订过程之中,“由于怒火中烧的维护者的坚持,改革就只会引起它迅速的衰微。”[32] 事实上,甚至如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也仅仅是在漫长而剧烈的斗争后才进入美国学校课程之中,任何一方在围绕目前应该传授谁的知识的论争中是不相上下的。因此,列文指出,当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者要求“回归”“共同文化”和“传统”时,它们过于简单化地歪曲了这一点。就今天的中小学和大学中官方知识的扩展和更新情形而言,正在发生的一切“也并无特殊之处,它当然也不见得就是以过激的方式违背了固有的(教育)历史逻辑,即一个持续的、充满争议并不断斗争的课程和经典扩展和修订史。”[33]
当然,为了维护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改革”运动中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这种保守主义立场不得不采取一种妥协。在历史课程中正显露出来的话语,特别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建构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34] 在这一霸权话语中,出现在美国史中的每个人都是移民,从第一批据推测可能是涉水穿过白令海峡,并分散于北、中和南美各地的印第安人,到后来移民潮中来自墨西哥、爱尔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俄罗斯、波兰以及其他各地的移民,再到最近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其他区域的移民,等等。尽管美国是一个由全世界各地人组成的,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文化才如此的丰富和充满生机,但这样的视角抹掉了历史记忆。对某些群体而言,他们是戴着镣铐来到美国的,并惨遭政府所赋予合法性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几百年。其他人则饱尝我们最好称之为身体上的、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破坏之痛。(11)
在此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如何,在新保守主义的国家课程和全国考试尚未建立起来时,他们会充分考虑到妥协的必要性。为此,甚至作为新保守主义教育项目与政策的最强硬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支持至少要部分地考虑到“他者的贡献”的课程创设。(12) 此外,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到美国缺少明显强大的教育部,而具有州和地方控制学校教育的传统这一现实。“解决的方法”是在各个学科领域“自愿地”开发出国家标准。[35] 的确,我上述提到的关于历史的例子就是这种自愿性标准的结果。
在各个学科领域,因为是由譬如数学教师理事会这样的专业组织来开发国家标准,标准本身就是协商性的并因此比新保守主义所期望的更具有弹性。这一程序确实对新保守主义政策插手知识领域具有阻绝意义。然而,在教育政策领域正在浮现出来的趋势却表明,前景并不乐观。学校“改革”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新保守主义如“标准”、“卓越”和“问责”等话语并为其所主导。因为标准的最有弹性部分实施起来被证明太昂贵,从而引起了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13),于是围绕标准的对话最终反而强化了新保守主义关于加强对“官方知识”的控制、“提高学业成绩门槛”等措词的力量。这种会导致学校间更严重分化的结果及其社会影响不能不令人担忧。(14)
然而,新保守主义的冲动力不仅仅是在其对合法性知识的控制方面,通过它旨在加强对教师的国家管理的政策。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它强大国家的理念。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变革是教师的工作正在由“认可的自治”到“规章约束的自治”,并更趋于标准化、理性化和“被管制化”(policed)。[36] 在被“认可的自治”的状态下,一旦教师被给予适当的专业资格认可,他们在一定限度内基本是自由的,在课堂情景中基本按照自己的判断而行动。这种制度的支撑是对“专业人士判断力”的信任。在“规章约束下的自治”状态中,教师的行为则是根据过程和结果而接受更多的审查。[37] 事实上,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州不仅限定了教师教学的内容,而且还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具体规章要求。凡采取非规章要求的“适当”方法要承担行政制裁的风险。这种控制制度不是建立在对教师信任,而是对教师的能力和动机的怀疑基础之上。对新保守主义而言,这才是新自由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生产者掌握”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市场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看法,新保守主义更认同一个能够看管住“合法性”知识和教学方法的强大的、好干预的强大国家。这种管制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指向教师和学生的广泛性全国考试。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到了这种管制所带来的教师“去技艺化”、教师工作的强度、教师自治和尊严丧失的问题。因为保守主义的这种动机源于对教师的不信任,他们对教师所主张的能力特别是对教师协会采取攻击就一点也不值得惊讶了。(15)
对教师的不信任、对所谓失去文化控制的担忧、对危险的“污染”的感受,就是这些众多的文化和社会恐惧推动了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形成。然而,如我早前提到的,支撑这些立场的是关于种族中心主义、甚至是种族化(racialized)的世界观。赫斯坦因(Herrnstein)和默里(Murray)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或许再清晰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38] 在这一被卖掉几十万本的册子中,作者为种族(乃至性别)的遗传决定论张目。在他们看来,确信教育和社会政策最终能够导致更为公平的结果是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因为智力和学业成绩差异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最聪明的决策者应该也能够接受这一结论,并规划出一个认可生物性差异的社会,而不是为穷人和弱智的人们,当然这其中大多是黑人,提供“不切实际的期望”。显然,该书不过是种族主义的老调重弹,这种种族主义观很长时间以来便在美国的教育和社会政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39]
与那种视种族是完全社会性的,一种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族群以不同方式来运作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分类观有所不同,[40] 由赫斯坦因和默里所提出的观点,是试图为那些此前已经多次被认为缺乏理智的政策话语赋予似乎科学的合法性。构成该书的动机据报道是作者接受了新保守主义基金的大笔款项,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新保守主义是如何为其议程提供理论支撑点的,不仅如此,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在公众面前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这种立场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显现在教育政策领域,而且显现在与这些政策相关的更为宽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由此,我们也便会发现一种这样的主张:穷人缺乏的不是金钱,而是一种“适当的”生物遗传特征以及有关的纪律、勤奋工作和道德品质。[41] 典型的例子如“学习福利制”(Learnfare)和“工作福利制”这样的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无论你的情形是如何的窘迫或者即使孩子的照看和健康福利不是由政府提供,如果孩子逃学太长时间,他们的家庭就损失一部分福利待遇,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低报酬的工作,将得不到任何福利。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因袭了早期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非常流行的极具破坏性的“济贫院”(Workhouse)政策。[42]
我在该部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综述了美国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观。它与新自由主义达成同盟,该同盟与其他群体协调一致,正在极有影响力地改变美国政策结构格局。然而,即使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影响再大,如果他们不与专制的民粹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保守的福音派结成共同的联盟,他们也不会成功。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一特殊的群体。
专制的民粹主义:上帝所期望的学校教育
或许与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不同,如果不给予“基督教右派”更多的关注,要理解美国的教育政治是不可能的。(16) 在关于媒体、教育、社会福利、性的政治、身体和宗教等方方面面,“基督教右派”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之大超出人们的想像。这种影响来自它内部激进分子的大量承诺、它雄厚的财力基础、它带有语言浮饰色彩的民粹主义的立场,以及在推动自己进程方面的勃勃雄心。“新右派”专制民粹主义分子的教育和社会政策观总体上是植根于特定的圣经权威、“基督教道德”、性别角色和家庭。例如,新右派把性别和家庭视为“男性的利己与女性的无私”的有机的、神圣的统一体。
如亨特说道:
因为性别是神圣的和自然的……,这就不再为合法性的政治冲突余留空间……,在家庭中,女人和男人——稳定和动力,是如此和谐地融合于一体,当她被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及世俗人文主义所干扰,这就不仅直接威胁到男人的阳刚和女性阴柔之气,而且还会连带地影响到儿童和青少年……“真正的女人”就是安分于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女人,将不允许家庭的圣洁受到自私的威胁。如果男人或女人挑战他们自身的性别角色,他们就是违背了上帝和自然;当自由派、女性主义分子和世俗人文主义分子拒绝这种角色时,他们就破坏了社会所端赖的神圣和自然支柱。[43]
在这一群体中,公立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充满危险的场所。如保守主义激进分子拉哈伊(Tim Lahaye)说道:“现代公立学校教育,在宗教、性、经济、爱国和身体等意义上,是儿童生活中最危险的力量。”[44] 这一点与新右派对学校教育与家庭间联系存在缺失的理解相关。
直到最近,新右派才发现,学校是家庭以及传统道德的延伸。家长把孩子委托给公立学校,是因为学校是地方控制的,并代表了圣经和家长的价值观。然而,由于被外人、精英力量所接管,现在学校将它自身横亘于家长与子女之间。许多人们感受到家庭、教堂和学校的统一体正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因此对日常生活、孩子和美国都失去了控制。为此,(新右派)认为,只有家长控制的教育才是符合教义的,它是上帝的设计,青少年教育的主要责任应该依赖于家庭并直接由父亲负责。[45]
这种“外人和精英控制”的理解的精确解释是有关与教义联系的中断、“天赐”家庭和道德结构的破坏,而正是这些方面推动了专制民粹主义的进程。这一进程在关于学校应该做什么、它们如何得到资助以及谁来控制它们等的冲突方面的影响正持续扩大,这种影响并不仅是在言词风格意义上的,而且是在资金意义上的。这个议程涵盖但又超越了性别、性和家庭的议题。它扩展到大量并更广泛的关于什么才算是学校“合法性”知识的问题上。在更为广泛的涉及学校知识大全的舞台上,保守主义的激进分子极尽所能,向教科书的出版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改革,并对有关教学、课程和评估方面的州教育政策进行变革。这非常关键,因为在美国缺乏明确的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出版是商业化的,受单个州的购买意向以及州权威对课程含义界定的左右。(17)
例如,在关于出版商所参与的“自我审查”方面,这些群体的权力运作清晰可见。在保守主义的压力之下,许多高中文学选集的出版商虽然收录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的讲演,但前提是关于美国狂热的种族主义文献注解却被删除了。[46] 在课程的政策层面上,更为醒目的是关于教科书的立法,德克萨斯州要求教材内容必须体现爱国主义、对权威的服从以及对“异端”的排斥。[47] 因为大多教科书的出版商在考虑到教科书的内容和组织时,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少数人口规模庞大州的认可,从而使他们的教材能够向全国推销,这无疑是授予了如德克萨斯(和加州)这样的州,在整个美国决定什么才算“官方知识”上以巨大的权力。(18)
因此,与保守主义联盟中的新保守主义部分相呼应,专制民粹主义宗教激进分子对课程政策和实践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只有把权威、道德、家庭、教会和“正派”等议题重新纳入教材内容的中心,学校才能克服我们周围的“道德衰退”。只有回归创世论者关于教义的教学,并营造(或强制性地推行)提倡全新的教学的氛围,我们的文化才能得以挽救。(19)
尽管许多州及其学校制度已经为迎合以上压力而建立了相关的运行机制,正如我在《文化政治与教育》、《国家与知识政治》两本著作中所表明的,许多学校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在总体上所带有的官僚化本质,实际上已经为可能并不认同新右派意识形态倾向的家长和其他社区成员,信任新右派并参与新右派对学校教育内容以及组织的攻击,创造了条件。[48]
在专制民粹主义致力于课程和内容的斗争热情正持续高涨之时,对公立学校的不信任又助长了他们对新保守主义的如学券与教育选择计划等政策的巨大支持。如民粹主义阵营这样的新右派,并不真正信任资本的动机和经济意义的设计。毕竟,这些右倾的民粹主义者对经济萎缩、失业和经济重构的效应也有所体会。然而,即使对全球竞争和经济重构有部分偏见,他们也注意到教育的市场化和私营化作为一种方式,不妨加以利用以实现自己的“改革”意图。无论是通过压缩教育的税收,还是通过公共资金向私立和宗教学校的再分配,这都会有助于围绕他们深信的已经失去的、并更具道德意味的“想像共同体”,进行一系列学校的创建。(20)
这种“想像共同体”的寻求所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围绕教育政策而形成的恢复私营化政治言论。在拒绝反对方诉求的合法性过程中,恢复私营化话语实际上会倾向于把更多的议题政治化。这些议题的论争由此也便带有更多的公共性,而不是“家庭的份内之事”。确实,这种自相矛盾的恢复私营化言论也会引发关于他者诉求的深层次公共论争,但它反而不利于如女性主义、种族意义上的受压制群体和其他被剥夺权力的群体。甚至于,如此的政治化在事实上会引发各种新的社会运动高涨和众多新的社会认同形成。这种新的社会认同的基本目的恰恰是要把他者的诉求推回经济、家庭和私人领域。如此一来,一个新的、更保守的联盟便得以形成。
这就是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国度,一系列恢复私营化话语“以专制民粹主义的语调”,与一系列不满民众的希望特别是恐惧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促发了一个带有支持恢复私营化共同立场的强大联盟(虽然内部也存在紧张)形成。[49] 如果在右翼群体没有成功地以这样方式变换了民主这个核心概念的含义情况下,所有的一切也不会发生。基督教右派就是这样,在保守主义的联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专业与管理新中产阶级:更多、更频繁的考试
因为该群体的力量有限(但正在持续增长),在此我仅做简短的介绍。这是对保守主义现代化政策提供支撑的最后一个群体。新中产阶级中的专业人士是基于专业技术的运用而在经济系统乃至整个国家内部获得了他们的活力。这些具有管理和高效技术背景的人们主要是为有关的问责、考量、“生产控制”和评估提供技术性的和“专业化”的支持。以上各方面正是在教育领域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政策和新保守主义强调加强中央控制政策支持者所要求的。
正处于向上流动状态的专业和管理新中产阶级未必相信保守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立场。事实上,在有关生活方面,他们可能具有更为现代和更为“自由”的政治倾向。然而,作为效率、管理、考试和问责的专家,他们为保守主义现代化政策提供合乎他们需要的专业技术。他们的活力依赖于专业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控制、测量和效率等专业意识形态的扩张。因此,他们通常为有关政策提供“中性的工具”,即使这些政策本身并不存在中性的目的,该群体依旧会对之报以忠诚。(21)
为此,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要意识到,目前学校所承受的诸如高标准考试、更苛刻的问责形式和更严格的控制等压力,并不仅仅来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需要,而且也部分地来自教育管理者和官僚机构,他们深信如此控制是正当的、是“好”的。这种控制形式在教育领域不仅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严格控制、高标准考试以及问责制等方法使管理者成为最强有力的角色。(22) 它促成了管理者投身于一个所谓的道德正义运动,并在此同时提升了他们专业知识的地位。
然而,在一个为证书和文化资本而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如此回归强制性标准使分层机制的力量持续增强,它也为增加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中产阶级子女的机会提供了一种机制,与其他孩子相比,中产阶级子女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这套旨在将众多人们予以分层的系统引进,会增加证书的价值,新的中产阶级更可能完成他们已经拥有的文化资本的积累。(23) 我不认为这是蓄谋已久的,但是该系统的功能确实为中产阶级的子女流动增加了机会,中产阶级子女的发展所依靠的不是经济资本而是文化资本。
在这种情形下,我相信,新中产阶级群体与右派的意识形态转型间不无瓜葛。面对来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攻击所产生的恐惧,新中产阶级必定也担心自己的子女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世界中的社会流动。因此,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公开地向保守主义联盟的立场靠拢,特别是对那些强调传统“高资质”、更关注考试、更强调学校作为一个分层机制的立场颇为青睐。在许多州,来自该群体的家长支持特许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关注传统科目的成绩和传统的教学实践。该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在将来是否会对这些政策提出疑义尚待观察。正是他们在意识形态倾向上还存在矛盾,右派才通过为他们将来的工作以及子女的前景制造恐惧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思想动员。(24)
结语
鉴于美国教育政治的复杂性,我在此以更多的篇幅分析了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该运动对有关教育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政策和实践争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意在表明,保守主义的教育现代化是由一个众多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相互抵触的力量组成的联盟主导的。
这个联盟至为关键的本质是,以保守主义现代化为基础的联盟在克服其内在矛盾和成功地实现激进的教育政策和实践的转型方面,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主张弱国家而新保守主义要求强大国家,这种明显的矛盾却能以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得到缓和并使两者走到了一起。正在凸现出来的关于集权化的标准、内容以及有些荒谬的强化控制,便是通过学券和选择性计划而走向市场化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一旦州范围和/或者国家课程以及全国考试被纳入正规,有关学校的资料就被以一种与英国公布的学校业绩“排行榜”相似的方式对外公布,以便于学校间进行比较。也只有实现内容和评估的标准化后,市场的活力才被释放出来,因为如此一来,“消费者”便可以根据所谓“客观”的数据来判断哪些学校是“成功的”,哪些学校是失败的。依此,基于“消费者选择”的市场理性会让好的学校得到更多的学生,而差的学校便会自然消失。
我在别处已经揭示了这种政策以及与之相类似政策对现实学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50] 但是,在此所要说明的是,这些影响结果之一就是穷人不得不“选择”那些位于内城或乡下的、资金投入不足且正在处于衰落之中的学校。(在城市公共交通每况愈下和价格上升、信息贫乏、时间紧张以及贫民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形下,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现实选择)贫民也将仅仅被责之为是他们个人或者集体性地做出了坏的“消费者选择”。恢复私营化话语和可计算的推崇论将为这种生产和再生产性的结构性不平等提供合法性。正是以这种荒诞的方式,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政策最终获得了专制民粹主义者甚至众多专业性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尽管他们看起来彼此之间存在矛盾,但长远来看却是彼此呼应。[51]
迄今,尽管我已经指出了目前教育政策的领导权为该联盟所操纵,但我不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一个印象:霸权联盟的这四个组成部分没有受到人们的抵制或者它们总是成功的。情况绝非如此简单。如众多人们行动所表明的,在整个美国的地方层次上,一些反霸权的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甚至整个学区面对来自保守主义复兴群体的意识形态攻击和压力,开始予以强有力的回击。许多教师、学者、社区活动家和其他人们已经创设了一些具有教育学与政治性解放意义的项目,并为之而抗争。(25)
事实上,我们也开始看到,(保守主义)联盟的权力也正以一种我们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而分裂。例如,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学生开始拒绝许多州已经实施了的强制性考试。该行动也获得许多教师、管理者、家长和社会活动家群体的支持。(26) 很明显,某些东西正在浮出水面,它们所带来的影响远非“有趣”二字所能概括。
然而,说到此,要指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构成大规模的旨在为维护进步政策运动的障碍。我们需要想到,在美国没有强大的教育部。教师协会在全国层次上也比较弱(通常教师协会为进步而实施的行动也不能得到保障)。在教育政策中关于什么是“适当的”进步议程也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在涉及种族、性别、性、阶级、宗教以及“能力”等方面,正在亟待形成的议程存在极为复杂的多样性(不幸的是,有时候,这种多样性背后带有竞争性)。因此,为形成进步主义的政策和实践,要形成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全国性运动还存在结构性的困难。
故而,大多的反霸权工作是在局部和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的。然而,目前出现的一种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我们最好称之为“去中心联盟”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如全国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以及围绕“重新思考学校”而形成的组织,正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7) 这些组织的活动没有如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专制民粹主义群体那样在背后有雄厚的财力和组织上的支撑。没有能力如新保守主义群体那样,通过媒体和基金会资助方式将他们的情况公之于“众”。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如保守联盟那样,在全国迅速调动一批骨干去挑战或者推行某项特殊的政策。
然而,面对以上各种结构性的、财政的和政治的两难选择,众多群体依旧没有被整合到霸权意识形态保护伞之下。甚至他们在局部创造了另外各种可能性的事实,也无疑表明,最深入人心和充满活力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并不是按一维的方向前行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富于多样性的例证也表明,保守主义的政策绝不会保证永远成功。在一个忽略什么是教育题中应有之义的时代,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
阎光才,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译者简介:阎光才(1966—),男,汉族,山东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育社会学研究。
注释:
①引自Roger Dale," The Thatcherite Project in Educatio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9( Winter 1989/1990) ,pp.4-19.鉴于美国的复杂性,我不可能关注到所有美国正在实施和存在争议的政策与动机,更为深层次的描述分析参见William Pink and George Noblit,eds.Continuity and Contradiction:The Futures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resskill,New Jersey:Hampton Press,1995) .
②关于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目前所强调的,可能是鲍尔斯与金蒂斯关于《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一书中所描绘的教育与资本主义间关系情形,它是还原论的、经济决定论的和要素主义的,该书出版于1976年,荒唐的是,它的内容更准确地反映了今天的情况。See,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1976) .For criticism of their position see Michael W.Apple,Teachers and Texts( New York:Routledge,1988),Michael W.Apple,Education and Power,seco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1995) ,and Mike Cole,ed.Bowles and Gintis Revisited( New York:Falmer Press,1988) .
③Apple,Teachers and Texts,pp.31-78 and Sandra Acker," Gender and Teachers' Work," in Michael W.Apple,ed.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ume 21( Washington: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95) ,pp.99—162.更多的新自由主义关于教育和经济中的性别内涵参见Jacky Brine,Under-Educating Woman; Globalizing Inequality( 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 and Madeleine Arnot,Miriam David,and Gaby Weiner,Closing the Gender Gap:Postwar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England:Polity Press,1999) .
④See Amy Stuart Wells,Time to Choose( New York:Hill and Wang,1993) ,Jeffrey Henig,Rethinking School Choi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Kevin Smith and Kenneth Meier,eds.The Case Against School Choice( Armonk,New York:M.E.Sharpe,1995) ,Bruce Fuller,Elizabeth Burr,Luis Huerta,Susan Puryear,and Edward Wexler,School Choice:Abundant Hopes,Scarce Evidence of Results( Berkeley and Stanford:Policy Analysis for California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Stanford University,1999) ,and John F.Witte,The Market Approach to Educ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
⑤See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especially Chapter 4,该部分内容对目前社会和教育政策正在加大种族间鸿沟的方式有全面描述。
⑥然而,很多时候,这些动议实际上是“无资助强制性的”。这就是说,这些要求是强制性的,要达到它们没有额外的资助。教育系统中教师劳动力的紧张正是因为这种情形所造成的。关于教育就业的历史参见Herbert Kliebard,Schooled to Work:Voc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76—1946(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9) .For clear and thoughtful analyses of other effects on higher education,see Geoffrey White,ed.Campus,Inc.( Amherst,NY:Prometheus Books,2000) and 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Leslie,Academic Capitalis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
⑦关于频道1详尽分析参见我的Official Knowledge,pp.89—112.也参见Alex Molnar,Giving Kids the Business(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 .典型的例子是ZapMe,它为学校提供免费的计算机设备,作为回报学校提供孩子的统计信息。当然,也发生了对频道1抗拒的情形。UNPLUG,一个学生领导的组织也曾经抵制过学校的商业化,更戏剧性的是如我在Educating the" Right" Way一书中所讨论的情形,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组织都参与了反频道1的运动。
⑧关于“残余的”和“突然显现的”意识形态形式的探讨参见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
⑨我已经探讨过,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保守主义现代化基础是基于未被认可的具有种族意义的合同。更多细节参见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
⑩See,for example,E.D.Hirsch,Jr.The Schools We Need and Why We Don' t Have Them( New York:Doubleday,1996) .For an insightful critique of Hirsch' s position,see Kristen L.Buras," Questioning Core Assumptions:A Critical reading of E.D.Hirsch' s The Schools We Need and Why We Don' t Have The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9( Spring 1999) ,pp.67-93.See also,Susan Ohanian,One Size Fits Few:The Folly of Educational Standards( Portsmouth,NH:Heinemann,1999) .
(11)For a counter-narrative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see Howard Zinn,A People' 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9) .See also Howard Zinn,The Howard Zinn Reader(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1997) and Howard Zinn,The Future of History( Monroe,Maine:Common Courage Press,1999) .
(12)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一个“提议”的过程,在该提议中课程和文本包含了妇女和“少数民族”贡献的材料,但从来不允许读者通过受压制群体的眼睛去看世界。或者如“我们都是移民”的情形,做出一种折衷以便于建构一个历史相似性的神话,而在此同时,经济分化却日益加剧。参见Apple,Official Knowledge,pp.42-60.
(13)面对各方的批评,NCTM最近已经通过合法的程序投票认可,回归更为关注传统数学内容以及传统教学方法。参见Anemona Hartocollis," Math Teachers Back Return of Education to Basic Skills,"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5,2000,p.A16.
(14)This is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in Apple,Power,Meaning,and Identity( New York:Peter Lang,1999) and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See also Ohanian,One Size Fits Few.Mary Lee Smith认为,太多的讨论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象征政治”的形式,这种话语倾向于一个所谓的“每个人的文化”和“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际效果是在根本上复活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See Mary Lee Smith,et al,Political Spectacl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n Schools( New York:Routledge,2003) .
(15)See Apple,Education and Power,Apple,Teachers and Texts,and Acker," Gender and Teachers' Work."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性别间和阶级间的对抗,其中一个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16)For a much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tendencies within the authoritarian populist religious right,see 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especially chapters 4 and 5.
(17)The power of the text and its contradictory impulses have been detailed in Apple,Teachers and Texts and Apple,Official Knowledge.For more discuss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struggles over the textbook help mobilize conservative activists,see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pp.42-67.
(18)The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the state' s role in defining official knowledge and in textbooks is developed in much more depth in Apple,Teachers and Texts and Apple,Official Knowledge.See also,Cornbleth and Waugh,The Great Speckled Bird.
(19)See Delfattore,What Johnny Shouldn' t Read,Ralph Reed,After the Revolution( Dallas:Word Publishing,1996) ,and Fritz Detwiler,Standing on the Premises of God(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 .
(20)Although he limits himself to a discussion of the nation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I am extending Benedict Anderson' s metaphor to include religious communities as well since many of the attributes are the same.See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York:Verso,1991) .
(21)Basil Bernstein make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fractions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who work for the state and those who work in the private sector.They may have different ide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mmitments.See Basil Bernstein,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New York:Routledge,1990) .For more on the ways" intermediate" classes and class fractions operate and interpret their worlds,see Erik Olin Wright,ed.The Debate on Classes( New York:Verso,1998) ,Erik Olin Wright,Classes( New York:Verso,1985) ,Erik Olin Wright,Class Count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and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
(22)For more on this,see John Clarke and Janet Newman,The Managerial State( London:Sage,1997) .
(23)See Bourdieu,Distinction,Pierre Bourdieu,Homo Economicu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and Pierre Bourdieu,The State Nobili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
(24) A combination of the work of Bernstein,Wright,and Bourdieu would be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this class.A satirical,but still interesting,analysis of a segment of this class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 of the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 David Brooks.See David Brooks,Bobos in Paradise(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 .
(25)See especially Michael W.Apple and James A.Beane,eds.Democratic Schools( Alexandria,VA: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1995) ,Michael W.Apple and James A.Beane,eds.Democratic Schools:Lessons From the Chalk Face( Buckingham,England: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 ,and Gregory Smith,Public Schools that Work( New York:Routledge,1993) .Also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here is the work on de-tracki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by Jeannie Oakes.See Jeannie Oakes,Karen H.Quartz,Steve Ryan,and Martin Lipton,Becoming Good American Schools( 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0) .
(26)See Jacques Steinberg," Blue Books Closed,Students Boycott Standardized Tests,"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3,2000,pp.A1,A22.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is will grow.It is also unclear whether children of the poor and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disenfranchised will participate widely in this.After all,affluent children do have options and can compensate for not having tests scores.This may not be the case for the children of those this society calls the" Other."
(27)See,for example,the journal Rethinking Schools.It is one of the very best indicators of progressive struggles,policies,and practices in education.Information can be gotten from Rethinking Schools,1001 E.Keefe Avenue,Milwaukee,Wisconsin 53212,USA or via its website at〈www.rethinkingschools.org〉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