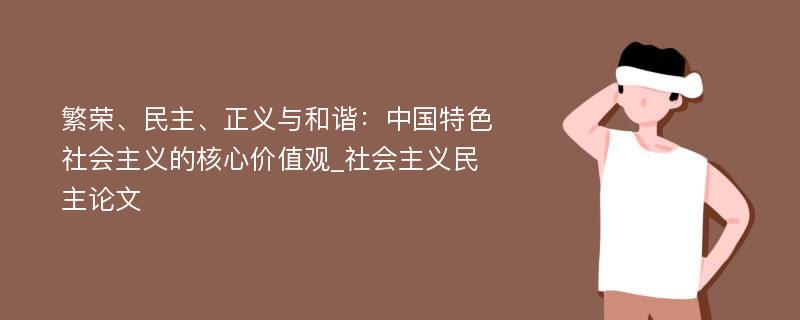
富裕、民主、公正、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裕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公正论文,民主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1)03-0006-04
一
价值理念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念中的理性化和理想化的内容,是一定主体的各种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而核心价值理念则可看作是价值理念的核心部分。一个人有其价值理念,一个民族国家也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说在个人的价值理念中,其核心价值理念往往也是其最高的价值理想、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而且是能够统摄其他各种价值理念、能够调节它们彼此间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矛盾或冲突的东西,那么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由于国家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个人构成的,其核心价值理念就不单要照顾到作为长远的共同理想的一面,还得照顾到现实的基本价值或共同价值诉求的一面,照顾到作为各种主体的不同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不能只顾及其“理想化”的一面,更要注重其“理性化”的一面,要通盘地考虑各种主体的价值诉求和满足这些价值诉求的实际能力。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这确实可看作是人格价值实现的表现,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就决不能不顾实际地为了某种理想,无论这种理想在道德上多么高尚,而不惜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包括一些宗教战争或所谓“圣战”,一些强行改造社会的“工程”,就往往是为了某些领导人的理想,或在某种理想的名义下发动的,实际造成的多是一些人间悲剧。
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尽管离不开思想家们的加工提炼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但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思想家们从自己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把各种美好的观念加以搜罗予以综合的结果,它是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在这个民族、国家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基础上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价值诉求的集中反映。离开了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民心民意,离开了人民群众创造价值、分配价值和享受价值的实践活动,这些生编硬造出来的美好理想,如所谓的“上古之世”、“大同世界”、“理想国”、“天国”等等,就没有根基,就是只能停留在书本上、宣传口号上的东西,也根本就成不了、压根就不是这个民族、国家所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一种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的东西,构成了整个民族生活的一种意义来源和文化背景,塑造着民族成员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对于人们形成比较广泛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未来生活理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从产生的根源还是从普遍接受的角度,也无论是就形成共同理想还是就最基本的公约数方面,讨论和确立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结合民族文化传统,都要与民族文化传统形成较好的衔接,从实际内容到表达形式都得具有民族的气派和特色。
除了民族特点,时代特征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这不仅是说一定价值理念的民族特点并非一成不变,总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是说民族特点作为一定时代条件下的民族特点,受着时代特征的规定。这个规定就包括了优点和缺点的评价和转化。真正说来,在各个民族都在孤立的地域自行发展的时候,彼此之间缺乏交往和比较,各自都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但因为缺乏参照系,这些民族特点也就不作为特点而存在。只有到了世界历史时代,到了世界性交往而形成的现代文明时代之后,各个民族的价值理念才由于彼此的比较才显现出自己不同于“他者”的“特点”,而且在现代文明的总体坐标系中显示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同样的,这些特点既具有某种“独有”、“特有”的一面,也具有因借鉴吸取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受先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影响而形成的“共同”或“普遍”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在现实中是无法割裂开来的,特殊中有普遍,普遍中有特殊,是理论家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将它们抽象地看作是某种分离着并对立着的东西,要么只看到特殊、只强调特点,甚至不惜脱离现代文明的总体坐标,把前现代的某些东西当作特点,要么只看到共性,只强调普遍,或者是把普遍当作是脱离特殊的抽象的普遍,或者是把自己的或别人的某种特殊直接等同于普遍,总之都是忽略了特殊与普遍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规定。所谓“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以及它们的斗争,就是这种各执一偏并各执一端的结果,是在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产生的。从理论的角度说,这种争执、斗争是针对着围绕着一个“伪问题”、“假问题”而进行的争执、斗争,除了制造理论的混乱外并无任何积极的意义,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会导致有害的结果。
二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首先应明确,第一,这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某个政党的价值理念,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理念,是这种社会价值理念的核心;第二,这种价值理念的基本性质或特质不是前现代的封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第三,它立足的是当代中国实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它的主体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走了很大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结我们的经验,包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国家的经验,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对自己的国情实际,对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方位,要有一种科学的认识;对人民大众真正需要什么,基于现实条件和能力能够实现什么,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解和把握。社会是人们活动的总和,国情的核心是“人情”,生产力本质上是人们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与这种能力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脱离群众必然脱离实际,离开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愿”、“所能”而确立目标和政策,必然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必然犯以空想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左”倾主义的错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拨乱反正为前提的,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这种“拨乱反正”着实不易,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改革的每一步,每一个重大关口,都会出现“左”的和右的观点的干扰,而尤以“左”的观点的干扰为重。这种“左”的东西,表现在价值理念上,就是以维护“社会主义”纯洁性为名,以脱离甚至鄙视大多数群众的实际要求、总是要教育和教训人民群众的所谓“理想”或“先进性”为旗号,以想方设法“管住”、“管好”人民群众的思想为特征,总觉得要是没有他们这些“教师爷”的耳提面命和精心呵护,人民群众就天然地难免受到“资本主义”的“污染”。
他们不是以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的一致性为基本前提来思考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反,总认为人民群众想过好日子的要求只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所以,只有用各种办法“管住”他们,并强行地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提升他们的道德境界,才能够保证国家按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下去。
现在我们一些人仍是按着这个思路来理解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在这些人看来,之所以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后人们都太关注实际的物质利益了,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了,人们的思想很混乱,很不统一;而要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主要的根本的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形成之后再“灌输”给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思想能够统一到这个“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上来。总之,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合理性不是看它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理想,是否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赞同,而是相反,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合理,则要看这些要求是否符合他们制定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理念”。
这些同志中不少是忧国忧民之士,但这种思路和逻辑完全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思路,是精英主义的表现。按照这种思路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即使是各种美的善的应该的东西的汇集,因其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的基础上,而是站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天然不一致的立场上,骨子里渗出的是一种“批判”和“训导”人民群众的态度,自然就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的。由于这些东西没有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不反映人民群众的“所要”、“所想”、“所愿”的内容,人民群众当然也就不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也不会按照这些理念来进行选择和行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嘴上说说、纸上写写来应付,实际行动中遵循的是另一套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念。
三
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价值理念,其核心内容应包括如下几项:
富裕 这里所说的富裕,首先是与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物质生活的富裕。但它又不仅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充裕,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样,是精神生活方面的富裕或优裕。富裕还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或社会关系方面的应付裕如,一种“免于恐惧”基础上的安全感或信任感。
富裕的基础当然是国家财富的总量,但更意味着这些财富的合理分配,是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是一种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定就是“共同富裕”,既不是多数人贫穷而少数人富裕,也不是“国富民穷”。国富民穷从来就是与少数人富裕而多数人贫穷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是人民群众的所愿,相反从来都是人民群众的“所怨”、“所恨”。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的毫无差别的“同等富裕”,物质生活方面不能如此,精神生活和社会社会生活方面更不能如此。
民主 民主是现代文明的一项基本价值,一种基本价值理念,但又是被弄得最为混乱、歧义最多的一个概念。民主的本质或实质与其具体实现形式之间是有差别的,实质是一,具体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则是多,不能把民主的某种实现形式当作是民主本身,把民主具体实现形式的差别当作是是否民主的差别。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民主是对专制的否定,民主的实质或本质规定,也只能从它的反面即专制中,从它与专制的对立中获得理解,这正如运动只能从它的反面即静止中获得理解一样。前现代的国家理念是君权神授,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私器、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万物都是皇帝的家产,各级官吏都是皇上的家臣,所有的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在这种理念下,无论君主是否开明,也无论皇帝是乾纲独断还是大权旁落,是一个人决断还是一群贵族或大臣共同决断,这些都是形式的区别,本质上都属于专制。民主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理念和制度,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种公共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各级政府的官员都是依靠人民的赋税而获得薪俸的,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向人民负责。至于人民如何实现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因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区别,尤其是人民本身力量的发展程度的区别而有所不同。这就表现出民主也是一个过程,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是同步的,也是同质的,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内在特质,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伪现代化,至少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属于现代文明,二者在反对专制认同民主的价值方面是有共同性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的基本的利益诉求,现代化意味着富裕,也包含着民主的诉求。而且只有富裕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现实的真正有意义的民主。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过程的先行者,正如在经济管理、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一样,在社会管理和民主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民主实现方式方面的某些不同,倒是应该更注意其本质的共同的方面,求同存异,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民主诉求得到更好的实现。
公正 与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民主不同,公正可以说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为人们一直追求的一种价值,但在不同的时代,公正的基础和内涵却有所不同。如果说,前现代意义的公正,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公正,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则以民主为基础,是对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权利)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制度化的合理解决方式。与民主一样,自由和平等都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而存在的。如前所说,在君权神授的专制制度下,等级差别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天经地义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就不可能作为社会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念而存在。而在民主理念颠覆了传统的专制理念之后,作为国家之主人的人民之各个分子,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要求才具有了安置之处。或许从历史发生的次序上说,人人平等、自由的要求作为对等级特权的否定先于民主而提出,甚至被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的权利形式成为民主(制度)的前提,但只有在民主战胜了专制——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层面——之后,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将之确定下来,并得到法律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平等和自由无论是作为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还是作为权利规定,在其具体实现的过程中,它们之间是会出现矛盾和冲突的。它们作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平等交换和自由贸易的内在要求在观念上的反映,作为保证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而持续地运行而以立法形式作出的权利规定,都是从前提和规则方面来着眼的,而实行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使得人人平等成为形式的东西,因为在形式平等下掩盖了大量的实质的不平等,一些人实现自己的自由权利以另一些人的不自由为代价;而为了限制或减少这些不平等,就需要限制一些人的自由。但该不该限制、如何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为宜,都需要借助公正作为原则。所以,公正作为制度安排方面的首要价值或首要原则而存在。公正是平等和自由的合题,既以是它们为基础,又为解决它们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式。公正也与民主法制联系在一起,是民主法制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调节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和谐 和谐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也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连续性的价值观念。这里的和谐,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人们对一个国家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状态的愿景,也是对国际关系合理状态的愿景,还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愿景。从个人角度说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身与心的和谐,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从社会来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和谐,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从国际关系方面讲,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和谐。和谐的愿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内在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如果说在以往时代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只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的和谐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以公正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的和谐,是包含了维护民族平等协商和国际和平等内容的和谐。正因其具有很广泛的包容性,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和拥护。
总之,富裕、民主、公正、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较好地表现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国人民处理国际国内矛盾的总体价值原则,既符合理想化的要求,也合乎理性化的规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照顾到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因此容易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同和遵从。富裕、民主、公正、和谐这几个方面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支持,共同作用,如将它们拆分开来,孤立理解,单兵独进,那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结果,甚至背离了原来的方向。如和谐,若不是建立在富裕、民主和公正基础上,那就很可能成为一种以强管强制为手段、以不出现问题为目标的假“和谐”,就违背了和谐本来的价值取向。
[收稿日期]2011-01-15
标签: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