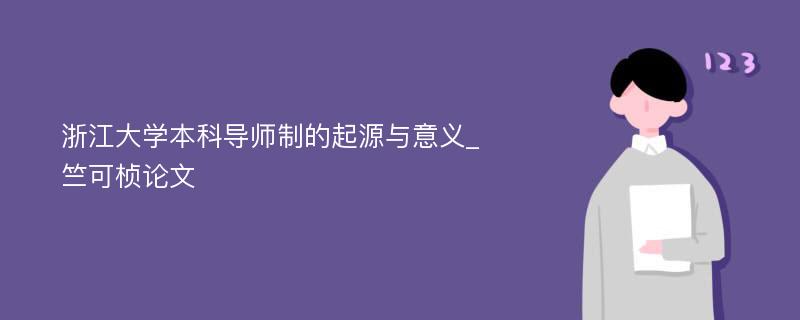
浙江大学本科导师制度思想渊源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渊源论文,大学本科论文,导师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科导师制度在目前中国的高校中得到普遍的实施。浙江大学较早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实施了本科导师制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浙江大学在短时间内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察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科导师制度实施背景及其思想渊源对当今高校的本科导师制度的运作依然有重要借鉴意义。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文献:一是对西方本科导师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二是对于本科导师制度的内在机理作理论探讨;三是对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科导师制度作专门的研究。其中,张家勇、张家智(2007),杜智萍(2006)、谷贤林(2003)主要对西方大学特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本科导师制度的特征与历史沿革作了介绍;而孟宪军(2004)就本科导师制度的运作和对学生培养的内在机制作了理论上的深入讨论,介绍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模型;杜祥锋、何亚平(2003)围绕竺可桢先生的教学理念与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科导师制度特征展开了讨论,就研究对象而言该文献和本文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它没有对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科导师制度思想渊源和实施背景作深入的讨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厘清一种制度得以成功实施的基本条件,为当今高校的本科导师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一、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科导师制度实施基本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军长征,先后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与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等地。浙江大学于1937年年底在迁移建德的过程中全面推行导师制度,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另行选择,规定每周导师召集学生谈话一次。三迁宜山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导师制度五点具体办法:(1)各导师每周到学生食堂就餐一次,留意学生生活并与接谈;(2)全体导师每月开会一次;(3)每一导师领导学生以12人为限;(4)三、四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为导师;(5)导师应随时与学生谈话,解答启导。这些具体办法使得导师制度更加正规化。对于实行导师制的目的,竺可桢谈到:“有人可能问为什么我们要实行导师制?所谓熏陶人格,这句话还是空的,对于这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1]在竺可桢看来,导师制度承载了实现他本人大学教育理念的功能,以及他对于中国传统书院师生关系的诉求。上述五点具体办法包含了以下一些信息:(1)这个制度实际上是由两层关系构成,第一层关系是学生和导师的关系,要求导师主动与学生接触,了解学生情况,第二层关系是学校和导师的关系,它通过每月一次的导师会议实现,通过导师会议使得学校决策层能够及时了解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状况,这为学校有效地开展教学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来源,导师要求每周到学生餐厅就餐一次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生活状况的高度关注。(2)导师制度的实行有质量要求,导师所带学生数量的限制一方面是保证导师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同时也保证导师有足够的精力来指导学生,和学生开展比较深入的交流,双方的交流还有一定的频率要求。(3)而对三四年级导师选择要求说明,导师制度对于不同年级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高年级学生的思想相对比较成熟,导师制度对高年级学生的主要作用是学业的指导,因此要规定以本系教授为导师,以方便学业上有针对性的辅导;而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则没有这个限制,因而对低年级学生导师制度的功能更侧重于人格的熏陶和情感的交流。这种分年级的导师制度兼顾了知识教育和人格教育两个方面,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学校非本系教师接触,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从而体现了竺可桢先生注重通才教育的理念。(4)导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导师有为学生提供服务的义务,导师要“随时”与学生谈话,解答启导,这种对学生的关心不受时间的限制。 我们可以归纳出当时浙江大学导师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1)制度正式化:对于导师制度中师生接触频率、接触方式等有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2)高度的弹性和科学性:学生可以随年级的变化和自己的学科兴趣选择不同的导师,它符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 (3)平等服务性:指导教师在时间上要求保证和学生的接触,并随时对学生的学业等问题进行关注,对疑问作出解答。 (4)人性关怀;导师制度除了要求导师关注学生的学业和思想外,还特别要求对学生的生活加以关怀。 该导师制度实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空间较小。鉴于当时浙江大学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办学,交通的不便使得教师不可能居住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为导师制度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保障,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教师接触,讨论学术和人生问题。导师制度实施中教师和学生居住的空间距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是导师制度成功的必要条件。鉴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都采用学院住宿制的方法,学生和教师被安排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从而保障交流的充分性。对照现在高等学校的导师制,教师和学生之间居住空间的隔阂足以让该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竺可桢校长推行的导师制度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交流活动,学生各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疏解,使得学生安于学习,教师安于教学和科研,有助于形成浙江大学务实求真的良好学风。导师制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得浙江大学西迁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成为学界中流砥柱的优秀学子。浙江大学的社会声誉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规模不断壮大。因此在浙江大学西迁发展史中,导师制度的有效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有效地促进了浙江大学的良性发展。 二、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科导师制度的思想渊源 浙江大学是国内较早实行本科导师制度的高校,该制度并不是对西方导师制度的单纯模仿,而是与中国传统书院制度中注重学生德育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浙江大学的导师制度影响非常深远,使浙江大学人才辈出,对浙江大学的崛起起到重要作用。下面从西方导师制度、传统书院训育制度两个方面来讨论浙江大学导师制度的渊源。 1.西方大学导师制度与浙江大学导师制 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实施的本科导师制度是由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推动的。竺先生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1915-1918),这个时期正处于哈佛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哈佛大学经过化学家出生的艾略特校长(1869-1909)科研型大学的系列改革,已经完成了从落后的英国传统式贵族培养学校向现代大学的转型。艾略特继任者劳威尔(1909-1933)在此基础上强化了对本科教学的改革,看似与前任改革相矛盾,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改革,因为艾略特时代哈佛大学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以科研带动学校整体实力,从而为哈佛大学赢得了社会声誉;而劳威尔校长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本科生教学质量,从教学质量角度进一步推动哈佛大学的发展。而竺可桢先生在哈佛就读期间正好处于哈佛大学的劳威尔校长就任时期,他对于哈佛大学的本科教学理念,以及本科教学的管理可谓耳濡目染。如果说艾略特为建立选修制而奋斗,把培养专家作为目标的话,劳威尔则要重建自由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认为:“学院应该培养智力上全面发展的人,有广泛同情心和判断能力的人,而非瘸腿的专家。”“自由教育的精髓在于使学生具有正确的态度,熟知思考的方法,具有应用信息的能力……”[2]劳威尔对哈佛大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行课程制度改革;二是建立学习社区;三是重建本科导师制度;四是实行荣誉学位制度。当时建立导师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准备从1914年开始实施的集中与分配课程的考试,因此,每一部门配备导师的数量依学习集中课程的学生数量而定。其次,导师制是一种职能,而不是职称。不但年轻的教师要作导师,资深教授也要作导师。他们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以谈话和辅导的方式进行非正式的教学,从而减少了学生正式上课的时间,增加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这样就达到了劳威尔少教多学、增强学习气氛的目的。在劳威尔离任之前,“导师制不仅使哈佛的导师们树立起了更好地培养有抱负的学者的信念,也使学生们对学习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成绩,每个毕业班大约有40%的学生在专业领域获得了荣誉学位”[3]。同时,辅导员通过和学生的非正式接触,建立了个人的友谊,无形中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等,使哈佛文化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仍坚持这一制度。除了哈佛大学外,普林斯顿大学也早在20世纪初开始实行本科导师制度,当然该制度更是它的发源地——剑桥大学的本科教育制度的核心部分。20世纪早期,导师制度在西方著名高校中成为一种普遍实施的教学管理制度。 美国的留学生涯使得竺可桢先生深谙西方大学的导师制度,对此他评价“从哈佛大学历年校长报告,我们可以晓得该校行了导师制后,学生成绩比以前优越,至于训育方面,行导师制更易见效。”[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竺先生非常重视大学教育的训育功能,他认为这种制度弥补了美国传统高等教育中对训育不重视的弊病。竺先生认为当时国内高等教育最大的缺陷是:“学校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造成优良的教育。”[5]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推行本科导师制度体现了他重视人格教育的教学理念。他批评当时的教育:“专重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6]因此在竺可桢先生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间教学理念的核心内容就是注重学生人格教育。1938年11月在广西宜山城外举行的浙江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他作了题为《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并明确指出:“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是造成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犹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7]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思想。这个教育思想和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校长劳威尔的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而竺校长尤其强调大学教育中对学生人格的塑造。 2.传统书院人格塑造与浙江大学导师制 竺可桢先生出生于1890年,求学时期正处于近代中国新旧教育开始转型的阶段,幼年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熏陶,小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小学里“中学”内容较多,以读经、修身为主,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他的人文视野:“西学”比重虽小,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窗口,使他有机会接触自然科学知识,为以后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家乡人文环境的陶冶,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加上随后接触的新式教育和在美国的留学经历,使竺可桢对中外文明有着较为深切的理解与体验,造就了他致知力学、忧国忧民的传统品质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分离出来,成为一名兼具传统士大夫优秀品质和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型学者,成为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相结合的典范。也正是由于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并蓄的教育背景,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深感中国大学教育的理念必须和国际先进的潮流相契合,同时认为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与现代教育并非都是相悖而不相融。1936年,他在浙江大学作《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8]从中我们看到他的大学教育理念强调了对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浙江大学导师制度的实施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具体操作,它很大程度上继承发扬了中国书院制中注重学生人格熏陶的优点,弥补了当时国内外大学教育中重知识教授、轻人文精神熏陶的缺陷。 自宋、元、明以迄清代,中国书院的发展中始终以人格教育为日的,而“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9]。传统书院教学基本模式就是会讲制度,它主要是一种师生间相互讨论和启发的教学方式,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以教学相长为目的,科研和教学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推动了学术昌明,各种学派因此而兴。书院的办学目的除了推动学术研究外,人格教育也是书院的重要办学目的。例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明确指出“圣贤所以教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意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书院实际上是儒学修齐治平人格思想传承的重要平台,通过强调人的品格修养来达到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境界。基于这样一种办学理念,书院具有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各派可以自由辩论,相互争鸣。和官学不同的是,学院通常也是比较开放的,学生不受地域或学派的限制,可以自由择师、自由入学或中途易师。中国传统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特征正好弥补了西方高等教育重视智识训练而忽视训育的特点,因此竺先生认为:“中国向来的高等教育,除了太学或国子监以外,就算书院……书院制的特点,就在熏陶学生的品格,我们只要看朱晦庵、陆九渊或王阳明的遗书,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师生中切磋砥砺的状况。”[10]“在中国书院制度,德育较智育尤为重要,而现行中国大学学制模仿美国,如考试制度,学分制度,但美国学制对于训育全不注意。国际联盟前三年所派几位专家……均不赞成美国制,即美国本国教育家……亦拟更张制度,如哈佛、耶鲁均用导师制,要有知道学生行为之任务。中国不必取法于任何一国,而现行制度有改良之必要乃不可掩之事实。”[11]因此,他融汇中西方教育体制中的优点,把教育的目标定在具有创新精神的通才和专才的培养。他在浙江大学所推行的导师制度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是对中西方优秀教学理念的传承和发扬。 三、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科导师制度实施背景 导师制度的实行除了前面谈到的导师和学生居住的空间距离比较接近外,至少还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批爱护学生、学识渊博、追求真理的教授;以及制度所承载和发扬的明确的教学理念。 竺可桢先生于1936年4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时尚不具备推行导师制度的条件。对竺可桢先生而言,此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聘请真才实学的教授,教授数量和质量是导师制实行的重要基础和核心。竺可桢先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养出博学笃行的学者。”[12]竺可桢先生上任后首先是觅得一群志同道合的教授,开始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想办法请他们来学校执教。对于海外留学归来的、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竺可桢都委以重任,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任校长之初,竺可桢极力邀请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胡刚复出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邀请因与胡适辩难“新文学”驰名一时的“学衡派”首领、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的得意门生、“桐城派”嫡传、东南大学外国语系主任梅光迪先生到浙大担任外文系主任,后担任文学院院长。农学院院长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吴福桢担任,史地系主任则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张其昀担任。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科导师制度固然是由竺可桢先生着力推动的,但是如果没有一大批志同道合教授的着力推行,它的效果也未必理想。胡刚复与竺可桢意见一致,认为要成功办学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此后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六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胡刚复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而随着梅光迪的到任,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前东大学生的郭斌和(白璧德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迁移至浙大。郭斌和掌中文系,外文系则由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有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当时文学院知名教授若钱穆、钱基博、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张其昀、贺昌群、夏鼐、郭斌和、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刘节、田德望等等济济一堂,可谓星汉灿烂。在竺可桢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他们都各有专长,有不同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好共处,在学术辩论与交锋中一同发展,达到极其难得而可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境地。大批教授在浙江大学的云集使得学生能够有很大的余地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导师,导师制度的有效实施得到了师资力量的保证。 大批教授的聘请使得浙江大学的师资力量大为增强,浙江大学于1936年秋步入正轨。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西迁过程中的全校师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抗战成为竺可桢校长加快推行本科导师制度的一个因素。在西迁的艰苦环境中,师生更需要发扬“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以竺可桢先生一贯秉持的教育理念,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能磨炼人的品格。他把《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作为1938年新生入学演讲的题目。在他看来阳明先生在极端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不忘追求真理,探讨儒学遗留的重大命题,而置自己生死于不顾的精神正是当时的学者和学子所应追求、继承并发扬光大的。阳明精神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求是”精神,同年浙江大学校务会议决定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不仅仅和浙大历史上的求是书院有关,更是阳明先生的“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体现。对于求是精神的内涵,竺可桢先生在1939年2月对新生作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有深刻、精辟的阐述: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求是校训体现了竺可桢先生强调学生人格塑造的教育理念“求是”校训一旦确立,它所承载的精神力量通过各种制度、活动不断地渗透到浙江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身上,使得浙大的师生很快在动荡的岁月中形成坚毅卓绝、追求真理的优良学风。 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导师制度的成功所具有的一些共性问题值得我们讨论和借鉴,教育是需要用科学和谐的理念来引领和发展的。导师制度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和谐的理念。它具备两个硬件和两个软件。所谓两个硬件:一是有一批热爱学生、学识渊博、追求真理的师资和它呈现出的师资力量;二是学生和教师之间要保持足够的接触频率,保证导师和学生之间能得到深入有效的交流。两个软件:一是学校必须有一种精神的诉求,它能够体现学校的人格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负责导师制度的承载和实现功能,并通过导师制度加以发扬光大;二是导师和学生之间平等民主理念的确立,只有确立了这种理念,师生之间才能相互砥砺,相互启发。尽管浙江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导师制度的成功以战乱为背景,但战乱本身只是加快学校实施导师制度的原因,而不是其成功的因素。竺可桢校长人格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的办学理念及相应的求是精神的确立是该制度成功的重要条件。师资力量、学校的精神诉求以及平等民主的理念都是教育科学和谐发展的核心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