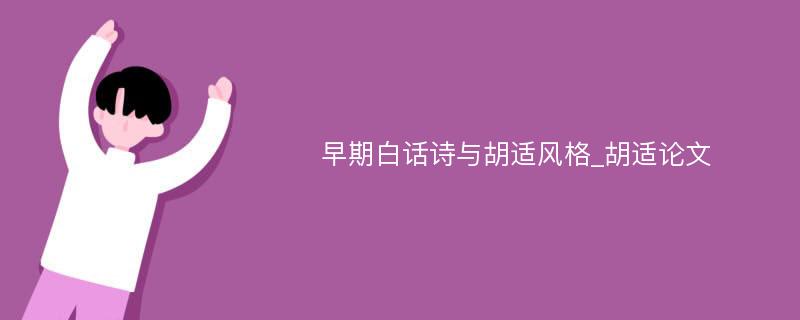
早期白话诗与“胡适之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白话诗论文,之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中有体正如文之有类一样,乃是其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人们常常对其多有忽视以及误解。其中最主要的误解就是把诗体仅仅当作所谓的形式。它的发展和演变被认为仅仅是由所谓内容来决定,因而自身变得无足轻重。但在我们看来,诗体作为诗歌的具体存在方式,并不等于那种仅仅用于装载所谓内容的体裁,而是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这种诗体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协调构成:一是诗人的主观审美倾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人的主观作风及其对于表现材料的选择;二是诗人所选取的题材和主题,它们将从一个方面影响和制约作品的审美品质;三是诗人所创造的言语结构,它既是一首诗作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内涵的载体,它本身所形成的文体风格又是作品总体美学风格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诗体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形式,而是还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直接和间接参与了诗歌作品思想情感内涵的形成。从这样的诗体概念出发,我们对于现代新诗的发展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描述视角。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的确受到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存在“流派”的事实。但我们发现,也可以把新诗的历程看作是若干种诗体运动和流变的过程。不同诗体之间的相互转化,形成一种内在的诗的秩序。这既是一个新诗史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的命题。早期白话诗中的“胡适之体”即为这一命题之中的一个典型的范例。本文试图就此作出一些新的说明,以加深对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解。
一
白话自由诗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适则被称作是新诗的老祖宗。但胡适对于新诗的意义究竟何在?这还得从早期白话诗的兴起说起。
中国现代新诗自何时起?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第一段回答了这一问题:“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适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朱先生的上述话语颇有历史结论的意味。说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根据主要是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和胡适后来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但这不能否认也有其他人同时或更早在尝试新诗。胡适在1920年《尝试集》初版自序中说:“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5年7月,到民国6年9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人。”实际上,当时尝试做白话新诗有影响的,还有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以及郭沫若、周作人、康白情等人。只是胡适的“尝试”显得特别典型且有史料可稽。胡适在上述《尝试集》初版自序中就用了很大篇幅追述了自己尝试做新诗的过程,颇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早期白话诗形成的艰难。
事情要追述到1915年夏天,当时胡适正与另几位中国留美学生任叔永、 梅光迪(觐庄)、 杨杏佛等人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Ithaca)度夏,并常在一起讨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文学和文化等问题。据胡适讲,“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地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度完暑假,梅光迪要到哈佛大学继续读书,胡适就作了一首58行的七言诗送行。全诗共3段,其中第2段写道: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1〕
所谓文学革命的口号,第一次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但胡适此诗实际上是一首打油诗,其中较为特别的是使用了11个外国词语的音译,风格较为怪异。同来绮色佳度夏的另一位朋友任叔永看到此诗后,把其中的外国字连缀起来,又做了一首游戏诗送给胡适,以示挖苦之意,诗曰:“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胡适当时正要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在火车上沿用任叔永的诗韵作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诗《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伐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光迪见此诗又写信批驳胡适:“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 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也。”任叔永也来信不同意胡适的主张,使胡适觉得自己很孤立,但胡适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并填了一首《沁园春·誓诗》的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胡适说这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所以口气颇为狂放。第二年夏天(1916),胡适再次路过绮色佳,再度与任叔永、梅光迪等相遇。胡适与梅光迪等人再次就新诗新文学问题争论不休。于是胡适写了一首百余行的白话打油诗《答梅觐庄——白话诗》。诗中开篇描摹争论的情景: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胡适又写自己: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诗中还写到胡、梅二人的对话:
老梅听了跳起,大呼“岂有此理!
若如足下之言,
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
而非洲黑蛮亦可称文士!
何足下之醉心白话如是!”
老胡听了摇头,说道,“我不懂你。
这叫做‘东拉西扯’。
又叫做‘无的放矢’。
老梅,你好糊涂。
难道做白话文章,
是这么容易的事?”诗的最后胡适写道:
人忙天又热,老胡弄笔墨。
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
我岂敢好辩,也不敢轻敌。
有话便要说,不说过不得。
诸君莫笑白话诗,
胜似南社一百集。
胡适此诗写于1916年7月22日, 被香港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称作是第一首白话新诗。胡适自己则认为此诗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但胡适的那班朋友却大不以为然。梅光迪来信大加嘲讽:“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又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叔永也来信说,“足下此次实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并且认为,“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两位朋友的反对意见,进一步促使了胡适用白话做诗的决心,加上实验哲学的影响,使胡适陆续写出一系列白话诗,并将其命名为《尝试集》。“尝试”二字虽然得自于陆游的一句诗,却又准确道出了早期白话新诗产生的艰辛历程。胡适本人对于早期白话新诗的开创之功实在不可低估。
二
但是,胡适对于早期白话新诗的尝试之功并不表明他的新诗创作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胡适的诗歌主张及其创作实践虽然开一代诗风,然而胡适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之成为新诗的老祖宗,真乃一场历史的大误会。
胡适的诗歌创作大约始于1907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期间。胡适名利心甚重,有认真做日记和赋诗应酬的习惯。但早期所作均为文言旧诗。今《胡适诗存》录80余首。〔2〕胡适的旧体诗词, 内容上多表现少年人的积极有为或忧时愤世的情怀,也难免旧式文人的伤感,有不少诗作则为酬唱甚或游戏之作,间有清顺可读者,大都风格平实。胡适最早的白话诗大约是前述1916年7月所作的《答梅觐庄——白话诗》, 又于1917年2月首次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白话诗八首”, 计有《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和《孔丘》。但这八首诗可以说基本上都不能算是新诗。胡适自己后来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认为其中的《蝴蝶》(即《朋友》)和《他》可算是新诗,实际上也只能当作白话韵文看待。如其中的《朋友》,诗前有小序云:“此诗天憐为韵,还单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低一格以别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据说此诗当时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称呼胡适为“黄蝴蝶”,又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可见白话新诗的初创殊为不易。胡适在此诗中则表现出因创作白话新诗不被朋友理解而感到“孤单的情绪”。
1920年3月, 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诗集《尝试集》,收胡适1916——1920年诗作共75篇,其中真正的白话新诗胡适自己认为只有14首,包括3首译作。它们是:《老鸦》、 《老洛伯》(译作)、《你莫忘记》、《关不住了》(译作)、《希望》(译作)、《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等。〔3 〕可见它们在《尝试集》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加上胡适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因此,《尝试集》在新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多次再版,两年内发行一万册以上,到1940年出至16版。其中,1922年的第四版曾经周作人、鲁迅、俞平伯等人删定,为后来流行的主要版本。因此,《尝试集》中的作品,虽然真正的白话新诗不多,但毕竟开一代诗风,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胡适早期白话新诗的时代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乐观有为的精神。这既是新文学运动所需要的精神,也是新一代历史开创者勇气的体现。如他的《一颗遭劫的星》:
热极了!/更没有一点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把那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那块云越积越大,/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遮尽了一天的明霞;/一阵风来,/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满天的星都放光了,/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此诗同《乐观》、《上山》等诗一样,表现了先进必将取代腐朽、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乐观进取精神。胡适早期白话诗的时代精神还表现为对于个性解放、反封建、劳工神圣乃至科学观念等思想主题的弘扬。如《威权》讴歌奴隶们对反动威权的反抗,《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歌颂辛亥革命的烈士,《双十节的鬼歌》更是直接表达对统治当局的不满,要“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此外,《人力车夫》对劳动者的些微同情,《平民学校歌》对劳工神圣的肯定,《我的儿子》、《礼》中表现的新型家庭伦理观念以及《一念》中的科学观念等,均可看成是“五四”那个时代的精神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的体现。
胡适早期白话诗作中还有一类作品,表现生活中的情趣、朋友之间的友谊、自然的景色以及微妙的心理等,虽不直接表现重大的时代主题,仍然别有一番风味。如他的那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恼他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每回吵过也就好了。/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这是胡适少有的一首“赠内”之作,诗中相当真实反映了胡适生活的一个侧面,曲折地表现了对旧式婚姻的妻子的顺从、不满而又无奈的心理,然而又于不满之中能写出一点情趣,颇耐人寻味。《一颗星儿》、《蔚蓝的天上》等诗在景物描写上亦清新可诵,《老鸦》、《应该》、《梦与诗》等则颇有理趣,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因此,即使从思想主题的角度讲,胡适的早期白话诗仍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积极意义主要就是表现为对于新的时代精神的张扬和推进。它们既对“五四”时代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直接推波助澜的作用,又从一个侧面对于新诗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胡适在新诗领域内所进行的活动,“除文学形式上的‘改良’而外,思想可取者是并不多的”〔4〕。这种评价显然有失公允。 但与稍后另外一位重要早期白话新诗人郭沫若相比,胡适早期白话诗作中的时代精神的确既不够深广,也不够强烈。所以人们一般都认为,郭沫若《女神》中的作品比胡适《尝试集》中的作品质量更高,影响也更大。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女神》刚出版不久就发表了《〈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给予热情的评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5〕这当然不意味着对于胡适早期白话诗的全盘否定,却多少暗示出胡适早期白话新诗的某些局限。
《尝试集》后,胡适因忙于其他事务,无暇更多创作新诗,以后也没有再出版新诗集,似乎正应了他自己的“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说法。但胡适仍然非常关心新诗的发展,并时有诗作在报刊上发表。胡适在《尝试集》以后的诗直接表现现实问题或鲜明时代主题的较少,大多数作品只是反映身边的随感或个人的经验情趣,但在诗的语言方式上普遍比“尝试期”的作品更为凝练含蓄。如胡适1923年夏天在杭州烟霞洞疗养时所作的一首《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踏月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此诗含蓄地披露了作者一段隐情,语言亦相当简洁凝练,为胡适白话诗中的上乘之作。胡适作于1938年8 月的《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则有更为严肃的主题。诗中这样写道: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此诗系胡适在抗战爆发后从国外寄给当时留居北平的周作人的。诗中隐晦劝戒周作人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在民族大节上要注意“识得重与轻”,反映了胡适在国家民族大节上的严正立场,是胡适后期较有影响的作品。
上述作品表明,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确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形成自己的特征。但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仍有自己内在的一贯性,并且在《尝试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体式特征。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胡适之体”。这种所谓“胡适之体”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诗中最早的一种诗体创造,具有从旧诗到新诗的划时代转折的意义,而且对整个早期白话新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胡适之于新诗的意义更主要还应从诗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和重新发现。
三
“胡适之体”的说法最早见于陈子展1935年12月发表在上海《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略谈“胡适之体”》。 陈子展对胡适在“五四”以后逐渐放弃新诗和文学创作不甚满意而又有所期待,于是在文章中提出:“胡先生呵,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此文当时一度引起较为热烈的反响。《申报·文艺周刊》先后发表子模的《新诗的出路与“胡适之体”》、任钧的《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梁实秋的《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等文,就此展开积极的讨论。胡适后来接过这一话题,在1936年第12期《自由评论》上发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就此作了较为充分的阐释。胡适在文中说道:“‘胡适之体’只是我自己尝试了20多年的一点小玩意儿。在民国十一二年,我作我的侄儿《〈胡思永的遗诗〉序》,曾说:‘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我在10多年之后,还觉得这几句话大致是不错的。至少我自己做了20年的诗,时时总想用这几条规律来戒约我自己。平常所谓某人的诗体,依我看来,总是那个诗人自己长期戒约自己,训练自己的结果。所谓‘胡适之体’,也只是我自己戒约自己的结果。”胡适接下来便谈到所谓“胡适之体”的三条戒约: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胡适的这些主张与他早期在《谈新诗》等文以及晚年一些谈话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大体上体现了上述主张,又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具体说来,“胡适之体”的诗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胡适之体的最大特征可说是语言风格上的“明白如话”。这一特征源自胡适“诗体大解放”和“作诗如作文”的诗歌观念,并且在他的大部分早期白话诗作中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胡适在前述《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一文中还专门就此解释说:“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又说,“我并不是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要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在这一观念支配下,胡适的早期白话诗创作大都以明白如话的语言风格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其中少部分佳作能够在清浅的白话里传达一些悠远的言外之意。如胡适自己颇为满意的一首《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在月光的地上微晃;/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此诗原载1921年1月1日《新青年》第8卷5号,后收入《尝试集》第四版。胡适自谓此诗颇近于他欣羡的“平实淡远”的意境。但胡适早期相当部分的白话新诗则白胜于诗,以至过于浅白笨拙。如他的那首《看花》:
院子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
红的花,紫的花,衬着绿叶,映着日光,怪可爱的。
没人看花,花还是可爱;
但有我看花,花也好像更高兴了。
我不看花,也不怎么,
但我看花时,我也更高兴了。
还是我因为见了花高兴,故觉得花也高兴呢?
还是因为花见了我高兴,故我也高兴呢?——
人生在世,须使可爱的见了我更可爱,
须使我见了可爱的我也更可爱!
此诗原收入《尝试集》初版。胡适后来已感到不满意,在第三版中将其删去。但据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讲,康白情认为此诗很好,俞平伯也认为此诗可存。由此可见,“胡适之体”与早期白话体诗的标准相当一致,甚至也可以说就是早期白话诗的典型代表。胡适的这种“明白如话”的诗歌观念及其创作实践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就其打破文言的束缚、促进白话新诗的形成而言,其积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但它也给早期白话新诗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对于白话的简单强调忽略了诗的语言与非诗的语言、诗与散文的界限,由此带来早期白话新诗过于直白的弱点。所以,穆木天后来在《谭诗》(1926)中认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它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 verse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在事隔几十年后,胡适的弟子之一的周策纵先生也就此发表评论说,“他(胡适)立志要写‘明白清楚的诗’,这就走入了诗的魔道,可能和那些与极端不能懂的诗之作者同样妨碍了好诗的发展。”因为“明白清楚的语言,却不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诗,而且最好的往往是最不明白清楚的诗”。〔6〕
其次,“胡适之体”的另一特征是诗的平实化。所谓平实,一方面是指胡适的诗在题材上大多是反映普通的生活琐事,基本不涉及崇高的领域,具有平民化的特点;另方面是胡适的白话诗在方法上多采用实录和直写的方法,即所谓诗的经验主义。胡适有一首《梦与诗》,诗中写道:
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此诗可说是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典型表现了胡适诗歌平实化的特点。胡适此诗还有“跋”云:“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诗的经验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诗只能写诗人感知和体验过的东西,而不能转述和说教。这是符合诗歌艺术的感性本质的。对于现代新诗后来所出现的某些严重的贵族化、概念化弊端而言,“胡适之体”的这种平民化和经验主义特色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但它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诗歌缺乏深挚的情感和瑰丽的想象,导致诗歌的写实主义和平庸化。这也正是胡适早期白话诗的特点之一,并且引起不少诟病。周策纵就指出胡适诗最大的缺点是欠缺热情或挚情。如他的《我的儿子》自述“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显得颇无情;《素斐》一诗中把亡女临死前的呼声写作“一声怪叫”则很不近人情;又提到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胡适最要好的朋友,但他哭悼他们的诗,也都没有热情流露感人之处。〔7 〕至于瑰丽的想象更是胡诗的罕有之物。这些都与“胡适之体”平实化的特点有关。经验主义加上平民化,使胡适的诗偶尔还显得有些随意化和粗鄙化。胡适写过不少打油诗,而且欣赏那些不甚优雅的歪诗。周策纵先生认为这是受小说和说书的影响,实际上仍可看成是他的诗的平实化特征的体现。从这一角度出发,“胡适之体”又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先驱。
第三,“胡适之体”在诗的体式结构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既有较为一致的语体风格,又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格式”。胡适曾称他的白话新诗创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刷洗过的旧诗”——“变相词曲”——“纯粹的白话诗”。但如果从新诗诗体的角度着眼,胡适早期白话新诗的诗体探索似可概括为我们所理解的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文白杂糅的新诗,带有明显的旧体诗词的痕迹,包括胡适所说的“刷洗过的旧诗”和“变相词曲”,如《鸽子》、《人力车夫》、《新婚杂诗》等,甚至也包括胡适自认为是真正“白话新诗”的《老鸦》、《一颗星儿》等篇。在《谈新诗》和《〈尝试集〉再版自序》等文中,胡适多次谈到他采用了不少文言旧诗词的句式,又采用了双声叠韵一类的方法来帮助所谓音节的和谐,并且承认他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另一种情况是几乎毫无诗体规范的白话自由诗。这是胡适早期白话诗的另一个极端,即,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典型的例子如《看花》、《一念》以及稍后的《南高峰看日出》等。后者的自由奔放句式已与郭沫若早期新诗语体风格颇为相似。试看其中的一段:
山后的月光仍旧耀着,/海上的日出仍旧没有消息了,/我们很疑心这回又要失望了。/忽然我们一齐站起来了,/起来了,现在真起来了。/先只象深夜远山上的一线野烧,/立刻就变成半个灿烂月华了,/一个和平温柔的初日冉冉的全出来了。/我们不禁喊道,这样平淡无奇的日出!/但我们失望的喊声立刻就咽住了,/那白光的日轮里忽然涌出无数青莲色的光轮,/神速地射向人间来,/神速地飞向天空去。/一霎时满空中都是青色的光轮了,/一霎时山前的树上草上都停着青莲色的光轮了。胡适的这一类诗作在早期白话诗中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对于打破文言旧诗体的束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们在语言体式上则还显得很不成熟。除遣词造句的简直粗糙外,周策纵先生还指出胡适喜欢用“了”字结尾,实在缺乏语言艺术的韵致。据周先生统计,胡适的新体诗中有68首以“了”结句,共101行“了”字句。 周先生还戏作《好了歌》一首为证:“胡适诗写好了,/人忙天又黑了,/周公数了“了”了,/总算一了百了。”〔8 〕胡适的这一类作品可说是一种纯粹的白话,诗的意义则很小。胡适早期白话诗创作在诗体的实验方面还有一种情况,可称作较有规范的白话自由诗。这类作品在白话新诗的“新”体特征方面比第一类更成熟,在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方面比第二类更规范,是“胡适之体”中较为成功的一类,也是整个早期白话体新诗中较为成熟的一类。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认可的他的14首“白话新诗”大体上都属于这一类。此外前文所举到的《我们的双生日》、《十一月二十四夜》、《秘魔崖月夜》等,也当属这种较为规范的白话自由诗。胡适早期还有一首题为《回向》的诗,似不大为人注意,但该诗从语言到意境均可视为胡适早期白话新诗中较为成熟的作品之一。以下是该诗的全文: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爬向最高峰上去了。/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没有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想起了风雨中的同伴,/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他们,/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风雨。/“也许还下雹呢?”/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他终于下山来了,/向着那密云遮处走。/“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该诗本是胡适1922年10月所作的一首赠泰戈尔64岁生日祝寿诗,却通过佛经中“回向”的概念获得一种更为深邃和普遍的内涵。语句的凝练整饬和灵活的押韵则显示了早期白话诗语言方式的初步成熟。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曾称《关不住了》一诗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9〕然而该诗与另一首《老洛伯》均为胡适早期翻译的英美诗人的作品,且都有较为规范的诗体。这似乎表明,西方自由诗的诗体规范,对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诗体规范的形成,当有某种直接的影响。
总的来说,早期白话诗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我们不应满足于现有的结论而应作进一步的开拓。胡适之于早期白话诗的意义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命题之一。如果仅仅着眼于某种主题思想的阐释,胡适的早期白话诗创作的确难以列为最优秀的代表。但如果从诗体创造的角度看,“胡适之体”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诗最早也最重要的诗体创造,不仅具有白话新诗体的开创之功,而且对后来的新诗诗体流变影响深远。其中的文学史内涵及理论内涵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注释:
〔1〕此诗各版本文字上略有出入,此处从胡适《尝试集》第4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2〕《胡适诗存》,胡明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3〕〔9〕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见《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
〔4〕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第1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5〕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7〕〔8〕周策纵《论胡适的诗》, 转引自唐德刚《胡适杂忆·附录》,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