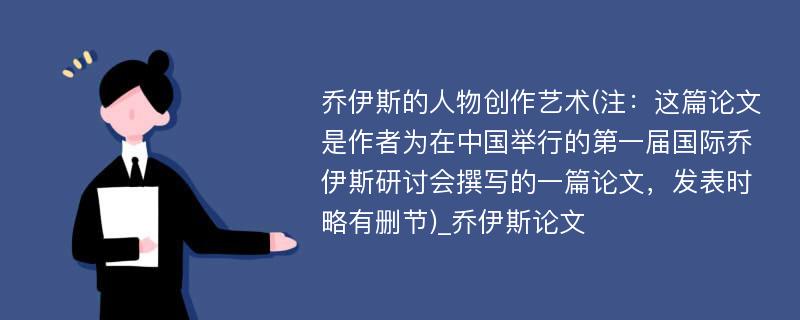
乔伊斯的人物创造艺术——(注:本文是作者为中国首届国际乔伊斯研讨会写的论文,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伊斯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本文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乔伊斯的主导思想
研究《尤利西斯》主题思想的学术论著多得不胜枚举,其中不乏整部的专论。乔伊斯自己说的“一部两个民族的史诗”最足以说明这书的整体性质;可是关于他创造其中人物的主导思想,我们只能从他自己的另一席谈话中获得信息。那次谈话发生在他开始写《尤》书三四年后,内容等于是《尤利西斯》的一个题解,但是因为记载这一谈话的文字用的是回忆录体裁,写得比较松散,限于篇幅,这里及文中的有关引文均出自我在一篇文章中做的转述(注:《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以下简称《奇书》),原刊《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第232页,后载《尤利西斯选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期间,和他的朋友弗兰克·巴津谈到自己的主导思想时,特别强调这样一点:他欣赏荷马的尤利西斯,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全面的人:既是儿子,又是丈夫、父亲,同时也是朋友、战士、领袖;他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可是在战场上对敌人又比谁都坚决(乔伊斯不喜欢流血斗争,但是赞成精神上的不屈不挠);他不但在战斗中足智多谋,而且善于创造发明,又有艺术气质。他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全面的人,一个好人。这样全面的人物,在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等的名著中都找不到,在整个文学领域里是难能可贵的,而他(乔伊斯)就决心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现代人。”
由此可见,乔伊斯之所以用希腊史诗中一位英雄的名字作书名,是因为他准备将书中的主人公写成“一个全面的人,一个好人”。而这位主人公的素材,他在开始写作以前十年就已经在心中酝酿。据艾尔曼传记的记载,一九○四年六月,年轻的乔伊斯在都柏林的街上,曾因为和一位姑娘说话而被她的男友打伤,乔自己的朋友袖手旁观,而一位只有一面之交名叫亨特的中年人,倒是来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并送他回家。这事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听说亨特是一个受人歧视的犹太人,家里还有妻子不忠贞的苦恼,亨特的精神使他深深受到感动。他先想用这题材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打算叫《尤利西斯》,但是一面积累材料,一面继续酝酿,十年之后终于真正动手,写成的就是这部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了。
现在,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小说的最主要的高潮,就是以戏剧为形式的第十五章内一个场面,其中的中心事件,就是青年斯蒂汾在街上和一个妓女说话,被妓女陪伴的英国兵打翻在地,与他同游的老同学看到形势不妙早已开溜,而和他家仅稍有点头之交的中年犹太人布卢姆却挺身而出,尽其所能地对付英国兵,对付警察,照料他。场面的全部情节,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众多的人物加上意识流幻象,简直使人眼花缭乱;但是就其基本情节而言,几乎和乔伊斯亲身经历的事件一模一样。这足以说明:布卢姆就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他要写的“一个全面的人,一个好人”。
在小说所描写的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小说主人公布卢姆做了好几件乔伊斯显然认为值得歌颂的事,其中有一些不见得能获得所有读者的同意,但是另有一些肯定是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一致赞扬的高尚行动。除了上述见义勇为救助斯蒂汾事件以外,这类高尚行动还有为亡友遗属捐款、协助解决死者人寿保险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带领盲人过马路、毅然反击反犹言论、探望难产妇女、排除讥嘲妇女谬论等等。而这一切高尚行动,又都是在他本人不断遭受歧视、嘲笑的情况下,以出乎本性要求的自然状态实现的,这就更显难能可贵。
乔伊斯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并非偶然,而是从他对文学的原则性立场出发的。他在一九○二年的一次大学讨论会上的论文中就曾经说过,后来又在《尤》书第十七章内通过斯蒂汾之口申述:文学的价值,在于“对人的精神起永恒性的肯定作用”。(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九○四页;九歌版第一二二○页)布卢姆作为一个受歧视的小人物,却能够处处想到别人,帮助别人,代表的正是这种值得肯定的“人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写作意图创造的人物,应该说是可以获得最严格的卫道士的赞许的。然而乔伊斯反对简单化、公式化。他把美化人物的写法称作“罗曼蒂克的东西”,断然拒绝走这种主观唯心的人物创造道路。他说:“搞现实主义,就是要面对现实。世界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大自然本来是很不罗曼蒂克的,只是我们硬要把罗曼蒂克的东西塞进去。这是一种虚妄的态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主义总是荒唐可笑的。我写《尤利西斯》,就是要力求合乎事实。”特别是针对那种女主人公总是“美貌、纯洁、忠贞”,男主人公则多半“四肢灵巧、肩膀宽阔、面目开朗”的文学作品,他说:“不错,那样的年轻人确实非常罗曼蒂克,起初使人看着感到舒服,然而过一忽儿就使人厌倦了。天知道……也许真有那样的人,可惜我没有见到过,正如挪威那位刚去世的先生说的。”(转引拙论《奇书》百花版第二八页。)
“挪威那位刚去世的先生”指易卜生。乔伊斯最钦佩易卜生面对社会现实的精神,认为他比莎士比亚还高出一头。他自己创造的人物,就是采用易卜生式的毫不留情的揭露方法,可是他所揭露的不仅是他要批判的现象,也包括他要歌颂的人物的“阴暗面”。他认为这样才符合“大自然”。这样的正面人物,表面看来已经超过了文学史上已经出现的“反英雄”,所以有些读者感到难于接受,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二)别开生面的正面人物
乔伊斯通过他那大规模而且灵活使用的意识流手法,将小说三位主要人物布卢姆、斯蒂汾、莫莉的内心世界充分显露在读者面前,达到了文学史上空前的深度,这是读此小说最大的享受。但是,乔伊斯从他的面对现实的精神出发,在这些主人公的意识流中,也包括了许多平常所谓“见不得人”的东西。这当然是最刺眼的地方,也是卫道者抗议的焦点。但是即使是在比较一般化的叙述中,乔伊斯也是采用同样不留情的写法。例如,布卢姆这位全书最主要的正面人物,乔伊斯给他的亮相,却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这样一句话:
“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先生吃牲畜和禽类的内脏津津有味。”
(拙译人文版第八六页;九歌版第一五九页)
此话的原文是:
Mr.Leopold Bloom ate with relish the inner organs ofbeasts and fowls.(Ulysses 4.1)
话并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考虑到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在书中初次露面,这样的一个介绍实在是太突兀了。我曾想把ate with relish译为“爱吃”,意思似乎差不多,和下文两句“喜欢”和“喜爱”贯通,可以减少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别扭。可是乔伊斯说的偏偏是“吃”,而事实上布卢姆又并不在吃,这就明明是利用出人意外的语句,强迫读者注意布卢姆这一不雅相。乔伊斯惟恐读者忽略他的用心,还特地在第十一章内又略加变化地重复了“吃……津津有味”这句话(人文版第四一四页;九歌版第六○一页),而且在那里也是很突兀的。
乔伊斯之所以要将布卢姆“吃内脏”一事放在这样突出的位置,关键在于西方社会中,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许多人认为动物内脏不洁。所以,这样一个亮相马上会使大多数英语读者觉得这人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角色,正是福斯特所说的“卑琐”。这也就是“反英雄”的特色。“反英雄”并不是乔伊斯的创造,乔伊斯的创造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甚至似乎胸无大志的角色,以独特的手法表现了他认为值得歌颂的人的品质。
有一位好心的记者曾经问我:我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把牲畜内脏叫做下水?这里有两重考虑。第一,“下水”就是食用的牲畜内脏,没有人把它叫做“牲畜的下水”,更没有人说“牲畜和禽类的下水”;第二,说下水,我的联想是美味,恐怕很多中国读者都会有同感,因而“津津有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会想到里面有什么问题。那样就完全违反了乔伊斯突出布卢姆的不雅相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在这一段的末尾还点出,布卢姆最喜爱的羊腰,吃到嘴里还有尿味——简直是有意刺激读者的反感了。半夜布卢姆进入夜市区时大概是准备充饥,乔伊斯又让他买了猪脚、羊蹄各一,也是同样的意思。
作了这样一个不雅的亮相之后,布卢姆开始了他的活动。什么活动呢?捅炉火、坐水壶、摆盘子,在厨房里准备自己和妻子的早餐。这又是和传统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大相径庭的琐碎家事,自然也是“反英雄”的一笔。但是乔伊斯从这一笔已经深入布卢姆的性格。西方有许多人喜欢在床上吃早餐,把它当做一种享受,然而从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说,丈夫伺候妻子在床上用早餐是少见的,在妇女惯于服从丈夫的爱尔兰更是如此。后来在第十八章内可以看到,莫莉认为布卢姆临睡要她第二天给他做早餐(实际上布卢姆是否这么说了,还是一个问题),她还吃了一惊,由此引起了很多的思想活动,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布卢姆在厨房为妻子准备早餐这一行动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着实表现了布卢姆性格中善于关心人、体贴人的一个方面。
特别具体地表现布卢姆这一特点的,是原文第四章开头不久的两个softly。第一个softly形容布卢姆在厨房里来回走动的姿态;一页半之后,他要出去买点东西,隔着卧室门对仍睡在床上的妻子关照一声,乔伊斯又用这词加以形容。为什么 softly? 第一个地方是他估计妻子还在睡觉,他要尽可能把声音弄小一些。第二个地方更妙:他想告诉妻子自己要上街,惟恐她仍在睡觉,怕推房门吱呀一声惊醒她,所以轻轻地隔门问她,这是又要她听见又不希望吵醒她。所以这两个softly表面上是说他的动作,实际上却更是说他的心灵。
像softly这样普通的字,恐怕多数译者都不会在这上面费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不考虑乔伊斯的用意,就很可能失去原著这种韵味。第一处,“轻柔”太过分,“轻快”不着边际;我试译“轻手轻脚地”(人文版第八六页;九歌版第一五九页)。第二处,“安静”不合适,“温柔”太过火,“悄悄地”又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这不是怕别人听到的悄悄话;我试译“轻声轻气地”。(人文版第八八页;九歌版第一六一页)原文两个softly,译文用了四个“轻”字,希望是比较忠实地传达出乔伊斯从人物外形写到内心的力量。
就在这两页内,还有一个在其它作品里少见的关于猫叫的文章。猫的叫声向来都是“喵喵”,英语中相应的拟声词是 mew。乔伊斯在叙述过程中也使用了mew这字,然而在表示猫本身的叫声时, 却用了一些没有人见过的词,而且一个和一个不同:Mkgnao!Mrkgnao!Mrkrgnao!Gurrhr!为什么他要用这些独特的词代表猫叫?显然,通过这些一声和一声不同的猫叫,他要迫使读者注意到猫的情绪在变化,因而注意到每一声不同的猫叫,引起了布卢姆的不同反应:他倾听猫叫的声音,细心地辨别叫声中的含义,从中观察、理解猫的要求,和猫说话,琢磨猫的心理状态。应该说,这四个代表猫叫的词,虽然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来究竟该怎么念(大概只有猫知道),实际上是布卢姆倾听猫叫,努力分辨猫的心理的记录。可以说这是他在一场人、猫思想交流中的意识流,反映了他对动物也非常细心的性格,和第八章内对海鸥、第十五章内喂狗是一致的。我试用音译“嗯嗷!姆嗯嗷!姆库嗯嗷!咕呜!”(人文版第八六至八七页;九歌版第一六○至一六一页),当然也是希奇古怪的词组,我只能希望它和奇特的原文一样,保留着读者可以体味的余地,愿意深追的人可以看到其中和人物性格的联系。
乔伊斯的人物创造艺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他的文字处处都是活的人物。猫叫反映人的性格并非例外。在第四章的末尾,布卢姆听到一串钟声(参见拙译人文版第一○七页;九歌版第一八七页),这是乔治教堂报时的钟声,它的实际声音和伦敦的“大本钟”相似,是一种乐音音句。可是乔伊斯描写钟声所用的词,一连串六个 Heigho 根本不是钟鸣的象声词,而是代表布卢姆被钟声引起的心情。这同一情况在第十七章又重复出现时更明显,因为那时布卢姆和斯蒂汾面对面站着,明明听到完全相同的钟声,可是乔伊斯却写出两串完全不同的“回音”(参见拙译人文版第九五三页; 九歌版第一二八七页)。这时情况完全清楚了,Heigho!Heigho!和斯蒂汾听到的拉丁文,都是钟声在他们各自心中唤起的意识流,译者如果凭自己的猜想,用千篇一律的通用中文象声词代替,译文看起来好像容易理解,实际上是既违反事实,又破坏了意识流和人物形象。
这一切,要是按通常的小说写法,简直都是不值一提的枝节,然而在乔伊斯的笔下,却都有了丰富的内涵。他几乎没有任何辞藻,就依靠这些细致的白描加上意识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很快就出现在读者面前了。这人物似乎没有什么太突出的长处,甚至仿佛有些磨磨蹭蹭婆婆妈妈,但是他已经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他已经现出了思想活泼而细致、办事不嫌麻烦的特点,特别是有一副善于体贴人、爱护人(以至动物)的善良心肠。这个轮廓,已经为以后布卢姆种种助人为乐、挺身而出救人苦难的行动作了准备。
(三)乔伊斯人物的质朴自然和喜剧性
布卢姆的那些高尚行动,实际上正是人类普遍向往的优良品质,和传统的文学作品所歌颂的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乔伊斯完全摆脱那些使人感到高不可及的豪言壮语和英雄姿态,倒是从人物最不起眼的方面写起。不仅如此,即使在涉及那些高尚的行动本身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渲染正面人物的崇高思想,倒是采取了两种可说是与之相反的写法。
一种手法是淡化。乔伊斯交代那些事情是那么平淡,仿佛布卢姆的这些作为和日常琐事没有什么不同,不值一提。最典型的例子是布卢姆为亡友的遗孀遗孤捐款的事。这是他在小说中的第一个慷慨助人的实际行动,可是乔伊斯对这件事本身没有作一个字的正面交代。从小说其它章节的上下文判断,布卢姆慷慨解囊的场面大概是发生在第六章的葬礼之后,可是乔伊斯在那一章内虽然写了葬礼的全过程,从头到尾着重的是布卢姆遭受冷落以至鄙视的情况和他的意识流。唯一提及有人正在凑钱帮助死者家属度过难关的地方,是另一个人在和赛门交谈时说的,赛门含含糊糊应付过去,一个钱也没有掏,布卢姆并未听到。后来在第十章内人们看捐款名单,才发现布卢姆已经捐了一笔大家认为数目不小的钱。人们对此感到惊讶,那显然是因为布卢姆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而读者也不免吃惊,却是因为葬礼的事原来以为全知道了,不料还有完全没有影子的事。就在第十章那一节内,布卢姆本人根本不在场,乔伊斯重点描写的,倒是募捐者找一些社会名流处处碰壁的情况。
乔伊斯对这件事可以说是采用了一种“中心空白”的手法。他写了问题开始提出时赛门的躲闪应付,写了人们对布卢姆捐款的惊讶,写了社会名流对捐款的冷漠态度,后来又写了别人毫无根据的污蔑(第十二章内,正当布卢姆要帮助死者家属解决保险金问题,有人来问布卢姆哪儿去了,另一人顺口就说“骗孤儿寡母们的钱去了呗”。——人文版第五一一页;九歌版第七二九页),可是布卢姆慷慨解囊的场面本身,小说里始终只有一片空白。从读者效果来看,乔伊斯这一着可以说是此时无言胜有言,比啰②半天更能给人深刻的印象。
乔伊斯本人更重视的,大概是他的喜剧手法。他曾经强调《尤利西斯》是一部喜剧性的小说。这喜剧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人物形象。有的人物仅仅出场一次,如第十二章内的窦冉,醉眼惺忪的听说狄格南去世,突然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尽管他本人表现严肃悲痛,可是读者看了却肯定忍俊不禁,想不到悼念死者会变成笑剧。那一章整章都是笑料,甚至悲壮的刑场也在特别庄严的仿古文体的描绘下使读者不能不发笑,观刑的外交官们和主持刑场的指挥官个个都是滑稽的庄严人物。但是全书最逗人发笑的是主人公布卢姆。
布卢姆的喜剧性,不仅限于众所周知的爱尔兰的民族性幽默。爱尔兰人最爱开玩笑、说俏皮话,《尤》书中的赛门(斯蒂汾的父亲)就是那种爱尔兰民族性幽默的代表。布卢姆这个人物的喜剧性,却主要是在乔伊斯的笔下,他不断地在思想中和行动上无意间流露出各种可笑的东西。让角色出洋相是喜剧的一项重要手段,乔伊斯对他的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布卢姆和斯蒂汾都没有放过。对于思想深刻的斯蒂汾还稍好一些,他虽然也有不少尽情奚落的地方(尤其是在斯蒂汾最狂放的第十四章),还常常是通过斯蒂汾的自嘲自讽,似乎是斯蒂汾现在已经颇有自知之明,已能对过去的狂妄幼稚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可是对于这位他认为值得歌颂的主人公布卢姆,却很少放过一个可以让他出丑的机会。这类情况几乎是每逢布卢姆出场必然出现。
布卢姆这种遍及全书的出洋相,表现最为突出、最为集中的一章是第十五章。这章中有写实,更有大量幻象,而幻象之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斯蒂汾的以外,大部分都属于布卢姆。不论是实事还是幻象,都有相当多的成分是表现布卢姆的高尚的思想行为的。如他贯穿全章的整个行动,从深夜追踪斯蒂汾到妓院,直至在妓院内保护他、在街上解救他,完全是难能可贵的无私行为。表现他的下意识活动的许多幻象中,也有不少正面的东西,例如导致他成为“皇帝总统兼国王主席”(参见人文版第六八九页;九歌版第九四七页)的契机,就是他脑子里常有的社会改革思想——这正是布卢姆性格中可贵的一面。但是总的精神是喜剧性的暴露,其中既包括这类反映他的好思想的“皇帝总统兼国王主席”事件(这个头衔本身就是鲜明的讽刺),当然更贯穿于那些涉及性生活的见不得人的胡思乱想。甚至他内心的最大的痛苦,即他今天上午发现莫莉要与鲍伊岚私通的事——这个已经缠绕心头一整天的痛苦,也变成了一个他亲自伺候鲍伊岚,会她,并亲自观看的场面。这场面的心理学意义也许可作各种不同的分析,但是它的喜剧性质是无可置疑的。
意识流和下意识幻象中的可笑情节往往接近闹剧,更能触及人心的喜剧性内容,是实际言行中的荒唐、笨拙、幼稚可笑处。乔伊斯甚至在着力歌颂布卢姆的时候也不放松这一节。例如,在第十五章的末尾,斯蒂汾被打昏在地后,布卢姆好容易把鄙视他的巡逻支走,独自守着仍未苏醒的斯蒂汾,又想唤醒他又怕惊了他(不免使人想起早上的softly),这是一个很动人的场面;可是当斯蒂汾在半昏迷状态中吟诵自己最喜爱的叶芝著名诗篇《谁与弗格斯同去》中的诗句时,布卢姆显然不仅对名重一时的叶芝诗篇一无所知,而且连爱尔兰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弗格斯也没有听说过,因而听到斯蒂汾念叶芝诗句中描写海面波涛翻滚的“白色酥胸”,还以为斯蒂汾是想念一位名叫弗格森的姑娘的酥胸,认为斯蒂汾是爱上了一位姑娘。他深有感触地喃喃自语道:“不知是哪儿的姑娘。对他是最大的好事……”(人文版第八二七页;九歌版第一一三○页)一片好心,可是纠缠着一团糊涂认识,变成了荒唐的推测,真教人哭笑不得。
乔伊斯嘲笑布卢姆在文学方面的浅薄无知,是从布卢姆早晨露面以后就开始的:在第四章内写他上厕所时看报,看到获奖的作者拿到稿费,他就羡慕不已,幻想自己也能凑一篇。拿布卢姆的拙劣文才出洋相最集中处在第十七章。在布卢姆和斯蒂汾交谈过程中,布卢姆提到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写的三篇东西,都是这类幼稚可笑的东西,其中之一是布卢姆将自己的姓名拆开重组的游戏,变来变去,终于从自己的名字里头变出了一个M.P.,即Member of parliament(国会议员)。在智力成熟者的眼中,这样的文字游戏不仅幼稚可笑,而且有些无聊,可是对于布卢姆这个人物的形象而言,这是重要的一笔。在翻译过程中,因为中文的布卢姆姓名拆不出一个“国会议员”来,所以如果要保留它,就得破坏文字游戏,将原文整个五行诗变成考古研究似的东西。可是对于乔伊斯的人物形象来说,在这里的上下文中,重要的不是国会议员这个具体的幻想职务,而是布卢姆在可笑的文字游戏中表现自己的童稚的野心,这才是这一段原文的韵味,也是它的艺术精华所在。“国会议员”和原文的韵味二者不可得兼,我决定舍议员而取艺术,利用“了布德”=“了不得”的谐音,试译成:
利奥波尔德布卢姆
奥尔波卢利布德姆
卢波布德姆尔奥利
布德尔波利奥卢姆
了布德的波利奥卢姆
(人文版第九一八页;九歌版第一二三九页)
乔伊斯的文字游戏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卖弄文字技巧,而是他的人物创造艺术所用的多种多样的手法之一。这里他是借布卢姆少年时期的幼稚的文字游戏,嘲笑他现在人到中年还是趣味不高,我认为译者也惟有采取同样的手段和风格,才有可能达到类似的喜剧性的暴露。
有意思的是,在乔伊斯的笔下遭受了各种各样无情暴露的布卢姆,在读者面前倒是比传统文学作品里一些正人君子更显得真实可信,因而也真能对“人的精神”起更大的肯定作用,无怪伦敦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把《尤利西斯》夸作“反英雄文学中至今为止最伟大的杰作”。
(四)信笔点活芸芸众生
《尤》书中人物众多,乔伊斯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写得像布卢姆、斯蒂汾、莫莉那样深入,甚至也不可能都写得像马利根、戴汐、赛门、公民、格蒂、水手墨菲等出场较多的人物那样细致,但是他的笔触所至,即使出场仅仅一两次的人物,也生动活泼,各有自己的个性。例如,十五章内斯蒂汾在街上遇见的两个英国兵,虽然没有说多少话,可是两人的性格就很不一样。动手打人的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斯蒂汾遇见他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另一个表面上似乎只是应声虫,实际上自有心计,虽然自己不动手,出的主意更毒,这是一名活生生的帮凶。在这场街头冲突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也不是一些没有个性的跑龙套角色,而是各有各的爱憎,其中有两个人还因为各支持一方而吵了起来。
有一个人物,本人在整部小说中一言未发,却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重点,这也是乔伊斯的一个独特的创造。这人姓布林,实际上不仅一句话没有说,而且连正式的露面也没有,可以说乔伊斯只让读者看到一个侧影。这其实又是一种中心空白写法,我们只能从别人的谈话和讥笑中归纳起来,知道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布林那天早上接到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只有U.P.这两个字母,也不知道是谁寄来的。布林决定找律师向那个匿名寄明信片的人起诉,要他赔偿一万金镑。这样的无头案件当然是没有律师愿意接受的,可是布林决不罢休,抱着两大卷法律书走遍了都柏林,他的太太不能不紧紧地跟着他。
事情的关键是U.P.(或是U.p:up这词组)究竟是什么意思?许多乔学家曾经对此进行推测,光是亚当斯教授一人就提出了六种可能的解释,大多是用up这个词和其它词配合而拼凑出来的。可是与此同时,他指出从乔伊斯的文字看不出应该是哪一种解释,并且强调了这样一点:“当然,决不能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也许它并没有任何意义;那样的话,布林就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注:见罗伯特·马丁·亚当斯的《表面与象征》,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页。)
许多欧洲其它语种译《尤》书,都把这个词组译成“你这疯疯癫癫的家伙”之类的意思。这种译法不能说没有根据,因为在小说的第十二章内,那些在酒馆里神聊的人们把布林找律师的事当做笑料,一位有律师身份(他本人正处在一筹莫展的窘境)的角色却发表意见,断言这词组可以有“智能不健全”的含义(参见九歌版第六九八页;人文版第四八八页),这一点也正是亚当斯提到的第六种可能的解释。
但是这类译法有一个大问题:原文U.p:up是一个疑团,英文读者都感到莫名其妙。第十二章那个角色的断言可能另有用意,而且他并未说明他的根据何在,显然不能改变疑团的性质——实际上他之所以提出一种解释(不论是什么解释),也正好证明了它的疑团性质。可是“疯疯癫癫”之类的译法,却完全消除了歧义的可能性,决不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或是想要解开疑团——因为它已经变成一句意义明确的骂人话,不成其为疑团了!显然,这样的译文,效果肯定是和原文大不相同的。
这一个效果上的差错,还不限于文字的韵味迥异,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性质。布林插曲之所以可笑而又可悲,在众人嘲笑的烘托下凸现了爱尔兰社会中一个小人物的悲剧,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明信片上的两个字母是没有意义或是很难说究竟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明信片上的话是含义明确的,不论是“你疯了”或是“你完蛋了”或是别的什么骂人话,情况显然就不一样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接到这么一张东西要设法调查一下,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能说是一个可悲的笑话了。
因此,明信片疑团实际上就是乔伊斯的人物创造的妙笔,翻译中必须保留它的疑团性质,要同样简单而又同样不知所云,同时也应该可容多种解释。早期的两种日文译本都采用不译的办法,即照录U.p:up字样。对于日文读者来说,这倒是一个疑团,然而日文译本中出现意义不明的英文,日文读者势必认为仅仅是他们自己不懂,小说中人大概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读者的这种错觉势必会破坏乔伊斯的艺术效果。
踌躇再三,最后我试用汉字的拆字办法,将U.p:up译成“卜一:上”。(参见九歌版第三六三页;人文版第二三六页)
在中文读者的眼中,“卜一:上”正如英文读者眼中的U.p:up一样简单而又不知所云,如果有人愿意推测,可以看作亚当斯教授更多的设想。例如,“上钩”、“上当”、“上吊”都是现成的。也可以仿照亚当斯的设想,说是暗示对方性能力不行的“你上不去!”根据布卢姆先生接过明信片后(显然是看着它说的)的话,我们可以理解明信片上的原始字样是“卜一”而不是“卜一:上”。那样,汉字拆开之后各个成分还有更大的活力,人们还可以设想“卜一卜,怎么样?”“卜不卜,一个样,你没救啦!”甚至“不上不下”、“下贱东西!”“下萎”、“下世”等等等等,有足够的供人瞎猜的余地。
这个具体的译法当然未必是最好的译法,但是如果不以乔伊斯的艺术为重,译文一味追求本身的“易懂”,读者面前的人物形象就不能不大为走样了。
乔伊斯写人物的手法之一,是利用怪名字和绰号。第六章内主持葬礼仪式的神父名叫Coffey,使布卢姆想起coffin(棺材),这种联想给神父一种阴森森的形象,如果译音就完全丢失。我试用一个在中文中有可能被采用的名字“关采”,以便布卢姆能合情合理地联想“棺材”,这是为艺术效果而不从一般的译名原则,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如此。当然,如果涉及重要历史人物等,不能不放松一些艺术效果上的要求。这位神父虽然在都柏林实有其人,可是对于小说的中文读者而言,他的名字和虚构的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情况在书中有好几个,如果都不能按照艺术的要求翻译,显然会给乔伊斯的人物形象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尤利西斯》中有两个明确无疑的反面人物,都有绰号。绰号和一般姓名的区别,主要在于绰号是一种明显的形象标志,构成人物的音容笑貌的一部分,给读者更加生动、更加深刻的印象。乔伊斯当然也是因此才采用绰号,麻烦的是,乔伊斯不像施耐庵写《水浒》那么明明白白地交代绰号的来由,对于这两个重要的绰号,都不具体说明它们的来源或是意义。这个不作具体说明的做法,和他的“中心空白法”异曲同工,可能比明白介绍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这种效果在英语读者是不成问题的,不论鲍伊岚的绰号Blazes或是马利根的绰号Buck,都是一看就知道其中的含义,不管究竟原来是否绰号,都会产生形象效果,这就达到了乔伊斯的艺术目的。但是译成中文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本名而译音,形象意义就会全部消失,如果作者原意是绰号,那样的译法对原著艺术的损害就太大了。显然,首先必须弄清作者的意图。
Blazes是个绰号,这一点从开头就没有任何疑问,因为它的形式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是本名。但是它的意义不明确,缺乏译意的条件,而我在八十年代前期选译的数章内这个名字也不太突出,勉强译音似乎还可以对付。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全译,第四章中米莉来信提到鲍伊岚,后面有一个括弧,原文是这样的:
(I was on the pop of writing Blazes Boylan's)
(Ulysses 4.408)
这是乔伊斯利用十五岁的姑娘既仍天真而又开始懂事的特点,间接而明确地交代了Blazes是个绰号,因为她的“差点儿写”而没有写,自然就是因为她已经明白小孩子喊成人绰号不礼貌的道理。她要是真的不写倒也罢了,但是乔伊斯又偏偏让她写下这个括弧里的话,叫我这译者不可能再拿音译糊弄下去,因为再把它译成正式名字就不像话了。不过,既然本来就没有问题是绰号,只是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含义,这里面本来就有非作不可的研究工作,乔伊斯将我一军,倒是迫使我钻研这一本来就不该躲避的课题,反而救活了这盘棋。第四章那句话现在的译文是:
(我差点儿写成一把火鲍伊岚)(人文版第一○一页;九歌版第一七九页)
我最初拟的绰号还不是“一把火”,还得感谢庄信正先生看了后提出“不像绰号”的意见,使我又一次模拟人们如何起绰号的生活情景,反复揣摩,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像绰号的绰号。鲍伊岚的朋友很可能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起这样一个绰号。我希望,现在这个名字“一把火鲍伊岚”在小说中出现数十次,和Blazes Boylan在原文中的数十次出现, 艺术效果可能比较接近。
马利根的绰号要麻烦得多,主要在于Buck这个字的特点:虽然懂英文的人都知道它不是教名,然而既然有人用它当姓氏(例如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英文姓名就是Pearl Buck),这就难于断定它不被人用作本名。因此我在八十年代前期作选译时,也是用音译。在选译的各章中这个名字出现也不很多,影响也不太大。
但是动手全译之后,发现这个名字在全书出现一百多次,光是第一章内就七十多次,英语读者每次看到Buck都有动物形象,而中文译音却每次都没有形象。这样一来,乔伊斯原著的意图究竟如何,就非得弄清不可了:如果原文本来并非绰号,这动物形象是翻译无法保留的弦外之音;但如果乔伊斯确实把它当做绰号,用音译就等于抹掉乔伊斯着意描绘的一百多笔,那就太对不起中文读者了。
在几年的过程中,我和几位乔学家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在座的几位乔学家,恐怕都被我反复提的问题弄烦了。这个问题最后的解决有一点儿戏剧性,我在一篇题为《壮鹿从何而来》的文章里作了介绍,这里只能举出这样一点:最后我在纽约乔学会作演讲,将这解决过程作为一个重点,获得了在座的数十位乔学家和《尤》书爱好者的热烈掌声,该会主席事后还来信赞扬,表明他们都同意这一个绰号在原著中的重要性。
实际上,译书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译完全书之后往往就清楚了。在第十四、十五章中,Buck是绰号的证据比比皆是。马利根的姓名凡是加上“先生”、“大夫”等称号的时候,都没有“Buck”的字样,说明它根本不是正式名字的一部分。尤其是第十四章中有一处提到马利根的全名,那是一串啰嗦的名字(英国和爱尔兰上等社会人物的姓名常常如此):“玛拉基·罗兰·圣约翰·马利根”,其中根本没有Buck。
译者的疑云消除,译文中就露出乔伊斯艺术的一些真面目,例如,马利根利用自己的姓名影射自己的性格,是很轻松愉快的:
——My name is absurd too:Malachi Muligan,two dactyls.But it has a Hellenic ring,hasn't it?
Tripping and sunnylike the buck himself.
(Ulysses 1.41—2)
正因为Buck是绰号,这词是一个普通名词,拥有这个词的充分的动物含意,所以马利根才能说like the buck himself这样的话; 如果把Buck看作马利根的本名,就变得非常勉强。现在我把Buck作为绰号译作“壮鹿”,这段话才有了马利根的轻松愉快的口气:
“我的姓名也是荒谬的。玛拉基·马利根,两个扬抑抑格的音步……跳跳蹦蹦,高高兴兴,正是壮鹿的意思。”
(人文版第三至四页;九歌版第四七页)
Buck本意泛指某几种雄性动物,包括鹿、山羊等,但中文没有一个恰好范围相同的词。如果将范围扩大一点儿,译为“雄性动物马利根”,虽然未必一定不能算是一个绰号,但是太泛,太啰嗦。尤其是如果这样长的一个名字在一章小说中出现数十次,显然会影响小说的风格。“壮鹿”的“壮”,不但和“壮汉”“壮士”等等一样使人联想精壮, 不但可以引起“蹦蹦跳跳、 高高兴兴”的联想,而且还可以和Buck一样,暗示“性欲强烈”,和第十四章中马利根扬言要建立一个“授精场”的荒唐设想相呼应。
同时,从马利根自己这段话看得很清楚,Buck是一个友好的绰号,他对之并无反感。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因为乔伊斯开卷第一句话里就是“壮鹿马利根”的形象:“仪表堂堂、结实丰满的壮鹿马利根从楼梯口走了上来。”(九歌版第四五页)
这是一个鲜明、生动的青年形象,下面乔伊斯还要写他的机智风趣、勇敢过人等等优点。这又是乔伊斯人物创造的一大特点:反面人物上得场来完全没有坏人的迹象,一眼看去满可爱。生活中不就是常有这种情况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