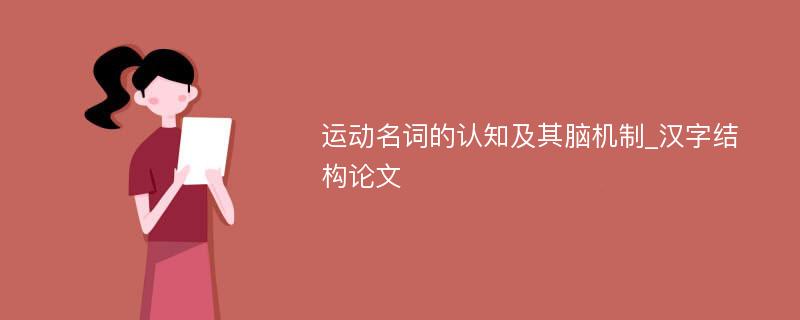
动、名词的认知及其脑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名词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名词在语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词汇数量和种类看,所有词类中,动词与名词在数量上所占比例最高,其子类别的多样性、形式的丰富性居各词类之首;从语义上看,动词表征动作和关系,名词表征物体和概念,动、静两方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维度;从句法上看,动词表谓语,名词表主语和宾语,主、谓、宾构成了最基本的句子结构。
不同学科对动、名词都给予了不同程度重视,其中以语言学最为充分。但近年来,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对之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如对动、名词获得年龄早晚的研究、认知表征和加工过程的研究、神经表征的研究等。本文将对近年来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有关动、名词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以求与各位同仁共享。
一、动、名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一)动、名词获得的早晚
动、名词是何时被儿童掌握的?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1)名词比动词获得早,体现出名词获得优势;(2)名词获得并不比动词早。
1.名词比动词获得更早的证据与解释
一些研究发现,名词是儿童最初词汇中最主要的词类,动词是第二大词类。[1,2] 1972年,Nelson对儿童早期词汇获得情况考察发现,英语儿童最初掌握的词汇依数量多少可分为4类:(1)名词;(2)动词;(3)社会术语;(4)修饰语。Gentner对16个不同语言儿童的调查得到了和Nelson类似的结果。她将这种现象进一步概化,认为名词不仅是所有儿童获得最早的词汇,也是早期语言中的主要词汇。Biglow也指出,在儿童最早的词汇中,最常见的名词有milk、dog、cat等具体名词,这些词所指代的物质,或是儿童经常接触的,或是物质本身变化、运动较显著的。陈萍等人[3] 对汉语儿童的研究也表明,汉语儿童的早期词汇中,名词最多,动词次之。目前对名词优势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自然划分”假设:Genter认为,[1] 动、名词获得早晚的差异来源于两类词概念表征本身的差异。名词常指代物体,包括人、地点、事件,词类的中心意义简单、基础,而且比较具体,较易把握。动词一般指向动作、状态和关系,词的中心意义复杂。除包含形、音、义等一般词汇信息外,还包括描述事件或行为所需的句法信息,如动作或事件的发起者、接受者、时间、地点等。同时,关系术语相对物质术语来说处于不断变化中,难以确定动态事件结果的界线,因而难掌握。这一假设和Nelson的观点[2] 不谋而合。Nelson认为,婴儿开始学习语言时就已掌握了关于物体的概念,但此时他们动作或关系的概念发展得不好。表征物体的名词与生活有密切关联,更易和简单的、事先存在的物品概念匹配,故名词先于动词获得。陈萍等人认为,名词标志具体事物,较易把握,动词标示的动作不太具体,所以识记较为困难。[3] 但Mandler等人经过研究指出,婴儿在发展早期就具有动作概念,甚至4个月大时就能理解因果运动与随意运动的区别。儿童早期同样能产生动词和其他关系词。[4] Leslie等人也发现,某些儿童使用动词的频率高于名词,甚至有些儿童先获得动词而不是名词。[5]
(2)“语义组织”假设:认为名词指代易知觉成整体的物质,语义有相互关联的层次结构,语义关系简单,更可预见。动词指代知觉领域的不同方面,语义结构以多种组织原则组成,语义关系比名词多而且复杂。[1] 动词的关键语义关系可预见性低,是以非层次维度,如变化、意向、因果等方式表征。这种结构使动词更难学,更易出错。
(3)语法解释:认为动词有较多的语素变化形式,如英语中-ed、-ing等形式,这导致儿童对这类词掌握困难。动、名词在句子结构中的典型位置和句法功能不同,动词在句子中担任更重要的句法功能。一些动词有着特定的句法变量结构,这不仅决定了相匹配的名词的数量与范围,也最终决定了整个句子的好坏。[6] 儿童对重读、非重读音节之间的差异敏感,他们习惯英语名词的扬抑格式,而对英语动词的抑扬格式不习惯。
2.名词获得并不比动词早的证据与解释
另有研究认为,除了名词获得更早的倾向外,还存在其他词汇获得模式,表现出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跨语言差异。Nelson发现,[2] 尽管从整体看,名词在儿童最初掌握的50个词汇中占多数,但个体之间有明显差异。对照组掌握名词的比率是60%,而实验组掌握名词的比率为33%。Twila Tardif通过考察10个完全在汉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验证Gentner认为的名词是儿童早期最主要词类的观点。[7] 他发现,当严格对名词分类时,9个孩子掌握动词的数量比名词多;当粗略对名词定义时,既未发现名词掌握早,也未发现动词掌握早的证据。儿童使用动、名词的频率没有差异。他同时考查了这些儿童的照顾者。结果表明,语言及文化因素在词汇学习中非常重要。Gopnik对9个英语儿童进行跟踪研究,得到与Gentner相反的结果。所有儿童不仅在最初记录中使用非名词,而且这些非名词的使用频率比名词高,甚至有些非名词比名词掌握更早。Levey和Cruz研究了双语环境中儿童的最初词汇,[8] 结果与单种语言环境下儿童的词汇发展既相似,又有差异。汉、英双语环境下的儿童产生名词比动词多,这和英语环境下儿童掌握词汇的趋势相同,但他们掌握的大多是汉语动词而非英语动词。而非英语儿童与英语儿童相反,掌握动词比名词多。对此有几种解释:
(1)结构差异说:英语动词通常出现在句子中间,汉语动词通常出现在突显位置-句首或句末。儿童常注意句子的突出位置,[9] 从而导致非英语与英语儿童的词汇获得情况不同。
(2)语言环境说:英语成人讲话时使用名词机会多,所以儿童早期词汇以名词为主;汉语成人和韩语成人与儿童交流时使用动词多,所以儿童早期词汇以动词为主。出生顺序、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儿童掌握名词的比例。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第一个孩子掌握名词的比例最大;母亲只受过中等教育,孩子掌握名词的比例最低。母亲使用哪些词类频率高,这一词类就可能成为儿童掌握的第一类词。[10]
(3)词形说:儿童掌握词类的早晚与语言的词汇形态有关。某些语言的某些词类,形态上更具单一性。如汉语与英语比,动、名词的词形变化少,即使有变化,也很有规律,不会明显改变读音。而英语名词比动词简单,有明显标示名词的后缀,如,“-tion”、“-ment”等。这样,英语儿童可能更易掌握名词,而汉语儿童对动、名词的掌握可能并无明显的时间差异。
(二)动、名词的心理表征
一些语言中,动、名词在词形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动、名词的加工?Avital等人采用启动范式研究希伯来语动、名词词根与语词模式在词汇通达中的作用。[11] 希伯来语以非联结性语素为构词基础,词形变化丰富。词语由两部分构成:词根和词形模式。词根通常由3个辅音组成,镶嵌在词形模式中,词形模式或者由元音组成,或者由元、辅音组合而成。词根包含单词中心意义,词形模式则标明词的语法信息和一些模糊的语义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名词词根对名词有启动作用,动词词根对动词有启动作用,动词词形模式对动词通达有影响,但没有发现名词词形模式对名词通达的影响。
(三)动、名词加工的影响因素
获得年龄是影响动、名词加工的因素之一。研究表明,获得年龄与词频的作用相互独立,尽管两者存在一定相关。目前,对获得年龄的作用还没有一致的解释。有研究指出,早期获得的词比晚期获得的词语音表征更完整,更易被检索。[12]
名词可能比动词更易记忆。名词比动词更具体,更富于形象。而动词意义的认知和回忆更依赖语境。研究表明,动词情境信息检索对记忆的影响高于名词。而且具体词比抽象词在不同任务上都有加工优势。对于具体性优势,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双重表征理论。[13] 具体词即可以形象方式表征,也可以语词方式表征,抽象词则只能以语词方式表征。表征方式越多,提取线索也越多,故名词比动词更易加工。另一种是单一编码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理解是根据情境信息进行的,情境信息使概念之间建立起关联。一般来说,具体词更易产生意义联系,情境信息比抽象词丰富,因而具体词具有加工优势。但Schwaneflugel等人发现,当抽象名词进入句子情境中时,其加工与具体名词没有明显差异。抽象词的认知缺陷可通过在刺激环境中提供语境信息(如段落、句子语境等)来弥补。因此,Schwaneflugel提出“情境可获得性”概念,认为情境可获得性是比具体性更重要的预测反应时的指标。[14]
动、名词在一些重要的非语义因素,如词形特征、音调变化的数目及类型上也存在差异。有人假设,类似意大利语的一些有丰富词形变化的语言,词形变化的多少将影响这些语言的加工。如果一个词根与许多不同的词缀关联,它就更可能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组成单位。意大利语中,动词的词形存在丰富的变式,因此动词的加工更倾向采用基于词形的加工模式。研究表明,词形加工是一种较慢的加工方式,这可能正是意大利语词汇判断中动词加工比名词慢的原因。此外,Traficante和Burani也发现,意大利语动词比形容词在语义与句义加工上时间要长。[15] 而意大利语的形容词在词形上与名词相似,只有2至4个词形变化的词缀。
90年代初开始,国内学者就对汉字义符在汉字词认知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张积家等研究了汉字义符在汉字词范畴语义提取中的作用。[16] 结果表明,汉字义符在汉字单字词的语义提取中有重要作用:当义符与词的上属意义一致时(如“女”对于“妈”),会加速汉字词范畴语义的提取;当义符与词的上属意义不一致时(如“女”对于“婿”),会对汉字词的语义提取起干扰作用。张积家、彭聃龄研究了汉字义符在汉字词特征语义提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汉字义符对汉字定义特征语义的提取有促进作用,但对词的特有特征语义提取没有影响。佘贤君和张必隐探讨了形声字心理词典中义符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汉字词心理词典中,存在两类线索:其一是义符线索,其二是音符线索。义符线索和音符线索作用不同,义符作用更大些。汉语动词也有义符,汉语动作动词大多有义符标记动作发出的器官或动作使用的工具。前者如“打”,后者如“刺”。张积家、陈新葵对汉语动作动词的研究表明,[16] 有标记动作器官或工具义符的动作动词的认知要快于无义符标记或者义符标记与词义不一致的动作动词的认知。他们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在对义符标记不同的动、名词分类时,对动词分类比名词快。这可能是由被试对动词熟悉性比名词高、汉语中标动词词类的义符比标名词词类的义符数量少、动词语义信息比名词丰富、动词与名词心理表征不同等原因造成。
二、动、名词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既然动、名词在认知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反映在神经机制上?研究者纷纷将目光投向动、名词的神经表征差异。脑成像、脑电技术被引入了动、名词研究,目前已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发现。
认知神经科学发现,大脑是按照语法词类来组织和加工词的。不同词类的加工有不同的神经网络,名词加工主要位于颞叶及视觉物体区,动词加工主要位于额叶及运动区。还有人认为,右半球更适合名词加工,左半球更适合动词加工,并发现了视觉区和词性的交互作用,即右视觉区、左半球参与名词的加工比动词少。这些脑区损伤可能导致动、名词的选择性损伤。对失语症患者的生理解剖及行为研究也支持这一神经表征专门化的观点。
为描述不同词类加工的脑区,Perani使用PET探讨了分类任务中阅读具体名词、抽象名词和动词时的脑活动。[17] 结果表明,广泛的脑区得到了激活,其中大部分位于左额叶和颞叶。但某些区域,如额背侧叶、颞侧叶、枕骨叶和顶骨叶,仅由动词激活,没有相应脑区对名词作更积极反应。进一步比较发现,抽象词加工有选择性激活,但同样没有脑区对具体词作更积极反应。词性和具体性之间没有显著交互作用。研究者认为,大脑激活似乎和特定语义内容有关。动、名词的分离发生在语义水平上。
Preissl等使用分类任务比较了动、名词的诱发事件相关电位(ERP)。[18] 结果显示,在200-300ms内,在左半球中央区,名词比动词诱发了更负的ERP。Pulvermüller等人发现,刺激呈现200ms后,动、名词在部分脑区上存在ERP指标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运动皮层和视皮层上。这种差异显然是由两类词不同的心理表征造成的。张钦等人采用分类任务和记录ERP方法,探讨动、名词的差异以及具体性对词性效应的影响。[18] 结果表明,动、名词的ERP差异从刺激呈现约200ms就开始了。在200-300ms和300-400ms两个时窗上,词性与具体性有交互作用,在两半球上具体名词诱发的ERP比具体动词更负。而在N400上,动、名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左、右半球额叶和颞叶。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动、名词有着不同的语义表征。具体名词与可感知的人、事、物紧密相连,具体动词则与动作程序密切相关,此外可能还包含有关施动者与受动者的信息。
还有研究者用神经生理知识来解释大脑表征的词性效应。动、名词可能有不同的神经基础。大部分动词的含义和运动神经通道相关,因而靠近运动区的额叶在动词加工中起作用。具体名词的含义和视觉通道相关,因此名词加工与靠近视觉区的颞-枕区有关。语言表征的神经生物学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动、名词加工为什么有不同的神经基础。该理论认为,神经元频繁的共同激活使一些神经元间形成较强连接。这些细胞团虽分布在各个皮层,但可以形成功能单元。如果一个词语频繁地与视觉刺激共同呈现并因此获得意义,外侧裂附近的神经元和视皮层神经元的共同激活将导致分布于外侧裂附近和颞-枕区的细胞团形成。这种细胞团可表征具体的与视觉通道有关易于想像的名词。同理,一个表征身体动作的动词与身体运动频繁地共同出现,外侧裂附近的神经元与运动区神经元共同激活可能在该区形成细胞团。
但是,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不一致情况。Chiarello和Liu在平衡动、名词具体性基础上,采用行为研究范式,使用不同任务及不同情境研究了动、名词加工的脑区左右不对称性问题。[19] 结果既未发现视觉区域与词类的交互作用,也未发现左右脑区在动、名词上的选择性优势。Bird等人的结果也与之相似。[20] 他们指出,词语单个呈现时,等级相当的动、名词加工不存在神经机制的差异。
三、研究展望
动、名词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位于词汇加工的哪一水平?各种语言中动、名词的差异具体又有哪些表现?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汉语作为一种表义文字,具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很多特点。汉语动、名词在字形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异。汉字虽无表示动、名词的词根,却有表义的义符。汉语和拼音文字动、名词的差异表现有何异同?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明晰语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我们认为,未来关于动、名词的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动、名词获得趋势的进一步探讨
研究表明,儿童掌握名词的趋势是由功能性、具体性、物质性的定义转向更抽象、概念化的定义。[10] 掌握动词的趋势是先掌握一些较为概括、可用于不同情境、指代不同动作的“轻动词”,如“make”、“do”等,既而转向更为细化的动词。从儿童概念获得角度看,儿童最初获得的名词概念是基本水平概念,如苹果、椅子等。基本水平概念处于概念层次的中间地带,既不是最抽象概念,也不是最特殊概念。它们能以最小代价包含最多的信息,具有最佳的信息量和区分度。基本水平概念在人类概念结构中具有特权,在归类中具有心理优势。由于基本水平概念在儿童认知结构中占有优势,所以,儿童掌握的名词也大多是具体名词,而不是像水果、家具等更高水平的词汇。然而,儿童获得的动作概念可能要高于基本水平,更具概括性。儿童动词发展是概念不断分化的过程。如儿童可能先获得“用腿走路”的概念,然后才发展出“走”、“跑”、“散步”的概念。当然,儿童早期获得的名词也有过度概括现象,如知道狗的结构特征后,他们会把长有4条腿的动物“猫”也叫做“狗”。随着对“狗”和“猫”的特征越来越分化,儿童逐渐正确学会“猫”和“狗”的概念。研究者还发现,儿童定义技能的发展缓慢,伴随还有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类别术语来定义名词,如“苹果是一种水果”。
以往关于动、名词获得早晚的研究,由于方法不一,控制因素不同,目前尚无定论。对英语儿童的研究大多得出名词比动词获得早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忽略了动、名词获得趋势的比较。我们认为,在动、名词获得趋势上,动词可能更倾向于分化,名词则更可能分化与聚类同时进行。如儿童通常先获得“吃”的概念,再逐渐习得“吞”、“啃”、“嚼”等分化的词语,而名词则一般先学习“苹果”、“香蕉”等具体水果名称,然后再学会“水果”、“红富士”这样的总类别或子类别名称。
(二)姓名、公用名、特有名
名词相对动词概念结构更为丰富。汉语中,姓与单字名、双字名组合构成了复杂的姓名系统。而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通常又有公用的名称,如“中国人”、“湖南人”、“广老”、“京片子”等。具有某些特征的人或事还有特有的名称。此外,汉语姓名中性别倾向较为明显。如“陈小红”通常是女性名,“李虎”通常是男性名。但也有一些中性的、看不出性别特征甚至是性别倾向颠倒的姓名。名字的不同是否会影响人们认知?共用名、特殊名、普通名在认知表征和加工上又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动、名词句法功能
以往对动、名词表征的研究,往往是研究孤立的动、名词,对动、名词的句法功能对动、名词表征和组织的影响考虑不够。动、名词有不同的句法功能。名词在句子中作主语和宾语,动词作谓语。汉语是词序语言,其主要的句法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结构(SVO),这种典型结构可能影响动、名词的区分。如果一个词出现在句首或句尾,它可能更快地被判定为名词;如果一个词出现在句子中间,它可能被更快地被判定为动词。但在汉语中,还有其他句子结构,如SOV结构或其他结构。因此,在判断非主流句子结构中词的词性时,反应时就可能变长。但在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典型的句子结构并不是SVO结构,而是SOV结构,所以在判定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时就可能和汉语不同。比较不同语言被试的差异,可以进一步明确句法结构对词汇加工的影响。
(四)汉字义符的句法倾向
汉字义符本身具有一定的句法功能,不同义符具有不同的句法倾向。一些义符更多出现在动词中,而一些义符则更多出现在名词中。今后应进一步对汉字义符的句法倾向性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对揭示汉语动、名词的区分,揭示语言的特殊性有重要意义。
(五)影响动、名词提取的因素
词频、获得年龄、具体性、情境可获得性、词根频率等是影响词汇加工的重要因素。词频和获得年龄存在相关,但不能完全等同。情境可获得性与具体性相关但也有不同。情境可获得性指通过词联想到的世界知识的多少。如“吃”可以联想到许多有关吃的情境、事件或知识,而“嚼”相对少得多。除词根外,汉字的义符也是影响汉语加工的因素。此外,汉语也是音调语言,音调和重音对汉语动、名词的区分有无影响?各个因素对动、名词加工的相对作用如何?各变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