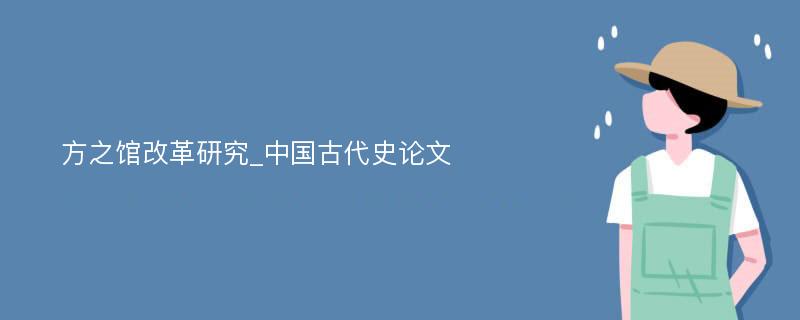
中国方志馆沿革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沿革论文,中国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自古至今各种类型的方志馆为传承民族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方志馆的来源及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宋朝以前,受史志同源等传统影响,大多为史志合一的官修机构,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方志馆。自宋朝起,方志逐步定型,编修事业日趋繁荣,大大推动了方志机构的发展,北宋的九域图志局则标志着独立志书编纂机构的正式成立。自此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特别以明清一统志馆和民国省级通志局等机构为标志,各种形式的志书编纂机构逐步发展,具有独立功能的方志馆日渐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地志博物馆的兴建标志着方志馆建设事业的正式起步。改革开放后随着第一轮修志事业的兴起发展,以上海通志馆等为标志,具有独立意义的方志馆开始出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国第二轮修志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繁荣,以江苏、江西、广西和北京方志馆等为标志,以收藏展示方志和现代化手段展示综合地情并举的当代新型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 一、早期官修史志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受史志同源等传统影响,功能完全独立的专业方志馆出现很晚,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大多与史馆等编修机构融为一体,相互间关系密不可分。为此,有必要以此为视角,考察方志馆的初始源头和发展脉络。朱希祖认为:“吾国历代撰史之所,其名约有六种:曰观、曰省、曰局、曰曹、曰馆、曰院”,但“史馆之名,称馆称院,各有所宗。称局者沿魏、隋,称院者举宋代,称馆者述唐制,而辽、金、元、清等之自桧。”①从而对其总体情况和发展脉络作了清晰概括。 方志馆的历史起源和初期发展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从图志一体到方志独立定型,是其产生的客观前提。先秦至秦汉,方志尚处于萌芽阶段,图为主,经为辅。六朝后期至唐宋,图与经并重,图的地位开始下降。南宋至清末,方志逐步定型,日趋成熟,图则逐渐成为附庸。②如北宋时以“志”命名的志书只有20多种,而到南宋已有200多种,大大超过了图经。因此,从“图志一体”到“图志分离”,不仅完成了地方志成熟定型的历史转折,也是方志馆等各类专业方志机构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二是史志合一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其成立的重要条件。由于方志与史学历来关系密切,以往学界也往往将方志归入史部地理类,而且它们在形式体裁上也存在较多的交叉重合,有时确难区分。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便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并举例说:“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榛杌》、鲁《春秋》……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此言是否确当自可商榷,但从中可见史志关系之密切。而且事实上,作为“官书”的地方志书,相当程度上依托各类史馆机构编修完成。三是志书从私撰到官修,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自孔子修《春秋》始“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我国的史书编纂便分为官修和私撰两种模式。但在“中国古代,官方始终从事着史学活动和史学建设,甚至将治史、修史作为必备的国务机制,这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独具的特色”③。方志同样如此,这与其“官书”性质是分不开的。志书从私撰到官修的转折点在唐朝,发展到明朝,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和严格控制,官修方志渐为主流,私撰方志日见萎缩,这也是以官修机构为主要形式的方志馆得以产生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以东汉兰台、北齐史馆等为标志:史志机构的肇始期 相传中国古代夏朝、商朝即有史官。大约在周代就有了专门搜集类似地方志等文献的官员,如西周已有太史、内史、史正等史官,东周则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等史官。不过,这些官吏的名称后人有不同说法,而且其职能并不独立,十分繁杂,包括保管典籍、记录时事、起草文书等职能,甚至还包括从事祈祷等宗教活动。④春秋时期,史官制度在各诸侯国基本得到延续。 西汉时期的史官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先为中丞,后为兰台令史,专掌史料图籍;另一类为太史令丞,专掌疏记撰述。研究表明,朝廷诏令史官修史,发轫于东汉初撰修《东观汉记》。光武帝刘秀修《南阳风俗传》,则开了地方修志的先例。此后,设馆修史制度逐步形成。当然也有研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汉、东汉都没有专职史官,东汉时所设兰台、东观等机构应为皇家档案书籍收藏场所,它虽承担修史职能,但与后来的专门修史机构仍有重要区别。⑤ 至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晋书·职官志》载:“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其职责为“掌国史,集注起居。”并有正郎、佐郎之分,前者担执笔撰史之责,后者行收集资料等辅佐之事。另有修史臣、校书郎等其他临时性辅佐官员。这也是中国古代设置专职史官的最早记录。 北魏以“修史局”为修国史专设机构,并创起居令史制度。继北魏之后,《唐六典》卷九《中书省》载:“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这是中国古代设立专门修史机构的最早记录,包括建立大臣监修国史等制度,都是影响后世的重大变革。⑥ (二)隋唐史馆史官:官修史志制度的正式确立 有研究认为:“朝廷设立修志机构,最早不是宋代,而起码应当是在隋大业年间(605-616)。”⑦当时曾沿南北朝著作制度,在秘书省设著作曹,主修国史、前朝史,开始把以图经、图志等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志编纂工作集中到中央政府加以管理,并在各郡志书的基础上大规模编纂全国性的图经和图志等,如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命秘书学士编成了1200卷的《区宇图志》,从而开了官府修志之先河。而且自隋唐统治者明令州府修志之后,皇家垄断史志纂修的倾向日益明显,魏晋以来私人编修史志之风至此开始受到抑制并渐趋衰落。 唐代沿续了官修史志的传统。一般认为,全国设置修史机构及官方修正史,始于唐太宗时编修《晋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令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唐会要》卷63《史馆上》记载:“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唐代馆修史志也以此时为盛。自此,经五代、宋、元直至元、明、清各朝,这一制度沿袭了近1300年。 除修史之外,修志也是当时史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如中唐时就有史官要求:国史修撰不仅要依据“行状”,还要广采“四方之志”,以充实国史。⑧唐太宗时期所修《晋书》“书中十‘志’追述至东汉末期,弥补了《后汉书》、《三国志》无‘志’的缺陷。”如“出自李淳风之手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记载了古代重要的科学知识,《食货志》多载重要的经济史料。”⑨贞观十五年(641),“五代史”修成后,朝廷又诏令于志宁、令狐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⑩而且研究也认为:“《唐会要》卷63、页码1092将书名误载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非‘记’,但其所指明确无误地是同一种三十卷的著作。此书原本是一部独立的著作,但后来并入了《隋书》,构成了它的志书部分。”(11)这都反映了当时史志合一、机构职能共担的实际情况。当然也要看到,正因史志关系如此密不可分,因而当时所编修文献有的虽以“志”为名,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方志;也有的虽未明确以“志”相称,但却带有一定的志书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代志书逐渐成熟定型后才发生较大变化。 二、从九域图志局到一统志馆:中国古代方志馆的发展 自宋朝起,方志日渐成熟,逐步定型,从而大大推动了独立方志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特别北宋九域图志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独立的志书编纂机构的正式成立。 (一)北宋九域图志局:方志馆的初始形态 宋朝同样十分重视史志编修事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开宝四年(971)即“重修天下图经”。朝廷还屡次下诏,要求尽收图籍,汇于京师。当时的史志机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等多种形式,它们各得其所,各有所长,其规模之大,功能之完备,为历代所不及。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初朝廷令史馆负责“重修天下图经”,“或为后来‘九域图志所’之滥觞”。(12)自隋朝起,历代史馆等机构多以修史为主,设局编志则始于宋神宗敕命编纂《元丰九域志》。元丰三年(1080),王存等修成《元丰九域志》10卷,后各时期又屡有增修。而且宋代又是中国方志发展的定型期,这对官方“设局修志”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九域图志局因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官方修志机构。当然,历来对其名称有不同说法(如还有九域图志所、详定九域图志所等名称),对其成立的确切时间也有不同意见(历史上即有“崇宁末”“大观元年”等多种提法),当今学者有的认为“可以推断‘九域图志所’之设立应在崇宁五年”,有的则认为应设于北宋“元丰三年以前,很可能始设于熙宁七年(1074)”,两者相差30多年;还有的从方志从属于地理书的传统角度出发,视其为“官修地理书之编撰机构”,等等。但综合各方意见看,九域图志局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并由北宋首设一说基本已成共识。(13) 九域图志局设立后,在校订州县户口数、核对州郡等第名号并奏准、校订全国州县并省废置情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史载:“尝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应典籍者为书,上于九域图志局”,而且,其对史料收集整理要求甚高,取舍甚严,如“流传鄙俗,难以书于地志”,从而对修志起到了直接的行政指导作用。 九域图志局终于宣和二年(1120),但这一传统仍得以延续。如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诏复置史官,以从官兼修撰,余官兼直馆、检讨”。起初史馆隶属秘书省,后机构名称虽几经变迁,但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并基本以“十年一造”的方式延续后世。特别是此时方志已呈定型状态,这对方志编修和方志馆建设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意义。 (二)元朝:依托翰林院开一统志编修之先河 元朝的史志编修既承袭史志合一之制注重修史,同时方志编修事业也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以《大元大一统志》为标志,开创了国家一统志的编修之先河。 元朝一统志由秘书监组织编修,由翰林国史院负责实施。(14)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命秘书监“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15)。二十三年(1286),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扎马拉丁奏请元帝,建议编纂大一统志,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命扎马拉丁和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主其事,于是秉承“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的理念,开始依托翰林国史院修全国总志。据载,此院与史馆原非同一机构,后合二为一。它位于“大内以北,傍依积水潭畔”,“其地高爽,古木层荫,与公府相为秘荫,规模宏敞壮丽。”(16)经过八年努力,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一统志》755卷编成。至大德七年(1303)又增为1300卷。该志首创“一统志”先例,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所提供的许多重要的史料文献,对之后明清修一统志和全国各地修志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明一统志》“其义例一仍〈元志〉之旧,故书名亦沿用之”。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与翰林院、国史院等史志编修机构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三)明朝:始设一统志馆,官修史志工作强力推进 明朝尊崇“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十分重视修志。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令中书省:“将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胜,亦皆已成书,藏之内府,以垂永久。”同时又命儒臣魏俊民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的《大明志》(后由英宗赐名《大明一统志》)。此后,又于洪武十六年(1383)、洪武十七年(1384)和洪武二十七年(1394),多次诏令编修方志。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也曾“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并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从而使“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僻郡下邑,率多有志”。至天顺二年(1458),英宗认为“修志乃国家大政所关”,故命敕李贤等修《大明一统志》,以“继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此志也于天顺五年(1461)修成。“尤其是《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编修,设立了一统志馆,并设有总裁、副总裁、纂修、催纂、誊录等人,形成一套系统的编写班子,这一模式不仅影响了《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而且使明及以后的府州县地方志书的编修有所遵循。”(17)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史、志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如注意到“志书修撰的好坏往往是正史成败的关键。所以明史馆在撰修元史志书时一反厌元态度,对元史的地理、河渠、食货、兵、刑法、百官等志倾注了特别的热情”(18)。有的史馆还直接承担了方志编纂任务,如明初修《元史》时,便有《天文》《五行》《职官》《兵》《刑》和《河渠》等诸志。另“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19)。又如,为强化“一统志”的编纂工作,明初由翰林院组织编修,而至景泰五年(1454),代宗又专设一统志馆,这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疑把方志馆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四)清朝:以一统志馆为标志,史志机构全面繁荣 清朝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方志馆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数百年间,方志馆从原来的史志合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职能逐步分离并日渐清晰。 谈及史馆等史志机构的发展,自然应提及《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大清一统志》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一统志馆开局纂修,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三修,历时157年,其耗时之长,费力之巨,为历代所仅见。它不仅强力促进了一统志的编修任务,是清朝史志编纂事业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对各类史志机构的发展起到了直接而又重大的推动作用。纵观清朝数百年历史,官修史志机构形式十分丰富,超过此前任何时期。具体可分为常开、例开、阅时而开以及特开等四种类型,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和特开为辅。“常开之馆”常设不闭,持续进行,有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等;“例开之馆”即定期开设,书成即撤,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等便属于这种类型;“特开之馆”为修辑特定史籍而开设,书成馆闭,不再重开。这种形式最为普遍常见,如《明史》馆、《八旗通志》馆、《通鉴辑览》馆、《西域图志》馆,等等;“阅时而开之馆”则根据具体情况开办,修纂具有明显接续性系列的史籍,会典馆、一统志馆即属此类。这四类机构,以实录馆、国史馆、方略馆等常开、例开之馆为主体,其他各种形式相辅,自顺康时期开始形成并逐步趋于稳定,而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从而形成了历代延续、规模日益扩大,机制日趋完备的官修史志编纂体制,这样的格局也为中国古代史所仅见。(20) 清顺治元年(1644)曾沿袭明制,始设翰林院,但组织规模都更为庞大,且《清史稿·职官志》中载明翰林院要“修实录、史、志。”康熙十二年(1673),即下令各省编修通志,以备将来修一统志之需。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学士明珠等奏:“《一统志》关系典制,自应催令速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敕命“纂修《一统志》”,“以著一代之钜典,名曰《大清一统志》”,并以特开形式专设一统志馆,委任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官,内阁学士徐乾学等为副总裁官,翰林院侍读20人为纂修官。之后又相继在洞庭山、嘉善、昆山等地开设纂修《一统志》书局。(21)但当时一统志并未修成。 至雍正朝,“世宗宪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采择”(22)。并于雍正三年(1725)再组一统志馆。而且当时一统志馆极具权威,如雍正六年(1728)十月诏谕各省,要求对有关事宜应“详查确实,先行汇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且此事“当速行办理为是”,如“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即从重治罪”。雍正十一年(1733),一统志馆为详查直隶各省府州县户口、田赋、市镇、文武职官等事项,也照会户部,令转行各省,限于三个月内查清造册报部送馆。照会后还附有“行查事项”十四条,要求逐条行查上报。(23)尽管如此,当时一统志也未修成。 乾隆八年(1743),一统志又改为由方略馆编修,并历时57年,完成自康熙朝以来的第一部共356卷的《大清一统志》。方略馆等机构在承编一统志的同时,还初步修成天文、时宪、地理、舆服等十四志。经长期努力,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完成为424卷的清朝第二部一统志。 嘉庆十二年(1807),经奏请国史馆得到旨准续修,全面恢复了帝纪、十四志等的纂修。嘉庆十六年(1811)又命重修一统志。当时国史馆一份名为《现在纂办各种书籍》的报告中也载明:“一统志全书于嘉庆十六年正月由方略馆奏交本馆纂办……立限二年将全书纂校进呈,俟钦定後咨送武英殿刊刻。”并规定了具体的编纂要求和时间期限。(24)嘉庆二十三年(1818)为完成《一统志》的重编任务,国史馆又再次行文敦促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可见国史馆与方志编修关系之密切。 道光四年(1824),国史馆奏准以十四志作为馆内常行功课,即与列传一样每季进呈一次,每次四卷。道光十六年敕命续修,至二十二年(1842),清朝第三部一统志也告完成,全志共560卷,所记内容始于嘉庆继位,终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25) 纵观这一过程还可发现,清朝起初沿续旧制,史志机构融合,职能相互兼顾,关系十分密切。国史馆等机构不仅承担着国史的重要编修任务,而且实际承担了一统志等大量志书和相关历史文献的编纂工作。从其设置的十四志处、长编处、总纂处等机构名称和承担职能看,显然它不仅为国史馆所必需,也与方志编纂的性质与功能基本适应。这种延续发展的史志融合体制和运行机制,不仅有效保证了一统志等志书的编纂,而且为方志馆的独立设置和逐步发展提供了先期经验,打下了扎实基础。发展到后期,随着方志专业价值地位的日趋显现和统治者对方志事业的日益重视,史志分离的趋势逐步呈现,并促使方志馆等专业方志机构开始以“通志局”等形式独立设置并日趋完善。 在中国方志史上,论及方志馆的历史,自然要提及章学诚的《州县请立志科议》。作为方志学的创立者,又身处乾嘉盛世,他不仅为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方志机构的系统理论。章学诚在代表作《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提出:“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他强调:“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他还对志书编纂班子作过以下分工:“职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报谋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从而“各不相侵,事有专职”。从设置志科的必要性到人员职责分工等问题,都提出了系统创见,从而为方志馆的建设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学术引领。 三、民国方志馆的艰难时世 民国时期各种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事业自然也受到极大影响,黄苇先生为此称之为“乱世修志”。但各时期仍通过颁发政令、建立机构、编纂志书等举措,试图强化地方志的官修地位,推进事业发展,其中各种形式的方志馆在艰难时局中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一)浙江通志局与民国方志馆建设事业的发端 1914年春,浙江省督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决定续修《浙江通志》并设立浙江通志局。1915年制定的《浙江续修通志局组织大纲》第一条“定名”载明:“本局定名为浙江通志局。”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省级方志机构,它的创立为中国近现代方志馆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就主要功能而言,浙江通志局仍是一个形式单一的志书编纂机构,与方志馆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与我们今天所设计的以综合地情为主的方志馆仍有相当差别。 浙江通志局由沈曾植创办主持。同时聘有总纂一人,委任提调一人,另有纂修、分修、协修、征访员及文牍员、会计兼庶务等人员约20多人。王国维、徐定超、刘承干等人均参与纂修。1915年8月,提调徐定超等“赴省议会旧址布设通志局,开始应办各事宜”(26)。随后拟定征访细则和政府公文,要求分门别类整理官牍档案资料,以补旧志和采访之不足。1915年9月,他还以浙江巡按使公署名义,发文要求各地从发文之日起五个月内,将乾隆到宣统年间的疆域分并、城署桥梁、运河堤岸、人口增减等各种资料分门别类、明晰起止时间,造册备案之后送到通志局,供修志人员参考选用。(27) 当时政府也十分重视通志局和《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1915年10月,浙江巡按使公署专门发文,制订《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共二十二条,要求各府衙配备一名专职征访员,且务必品学端正,留心掌故,三十岁以上。如果有人借修志之名招摇撞骗,必须立即辞退。规定还要求征访员要广为征访各种与修志有关的文献,无论已刊刻或未刊刻的,无论官方文献还是私家著述都要广加收录。并鼓励征访员补充建议,集思广益。(28)省都督吕公望还要求各县“迅速补送备纂,毋任延缓”。1916年11月,因有的县对修志态度消极、行动迟缓,省长公署又多次发布训令,再次强调“事关重要”,应从速办理。 然好景不长,自1916年夏季始,因政局动荡,军政长官更替频繁,报纸有缓办通志消息刊布,《浙江通志》编纂工作便显现颓势。如1916年1月,王国维在一封信中便报怨说:“今年经费尚未全有着落……颇复悲观。”最终因国运飘摇,时局艰难,编纂难以为继,人员陆续离职,《浙江通志》编纂经三度延期仍未完成。1923年5月,浙江省议会通过了省长咨文《结束浙江通志局追加经费案》,标志着浙江通志局正式裁撤。 (二)民国方志馆的发展沿革 浙江通志局的率先成立,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示范效应。自民国初年起,各地便成立了不少方志编修机构。如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便曾会同教育部通咨各地编修方志。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关注地方志事业。1928年10月,刚就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向国民政府主席呈文,提出:“各省省志、县志失修已久,长此不加整理,必至事实湮没,似应令行各省设局修理,并谕各县一律修理。”此议随后为第11次国务会议采纳,内政部和各省政府先后接到行政院训令,各地的修志工作就此得以全面展开。特别是内政部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中对通志馆建设所提的明确要求,更对各地方志馆的建设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以训令形式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明确指出:“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通志馆成立日期、地点、暨馆长、副馆长、编纂略历,并经费常额,应由省政府报内政部备案。”“通志馆成立后,应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送由省政府转报内政部备案。”“通志馆应酌量地方情形,将本省通志成书年限,预为拟定,送由省政府转报内政部备案。”(29)等,从而从机构名称、人员配置、经费安排等行政要务,到志书凡例、分类纲目等业务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由此构建了一套国民政府内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通志馆运行体制,大大推进了当时的修志事业和通志馆等方志机构的建设进程。 《修志事例概要》颁布后,各级政府和各类官员普遍开始关注修志一事,有些地方行政长官甚至亲自主持通志馆的筹建工作。如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爰设通志馆于省府”,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上海市长吴铁城、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纷纷主持筹办通志馆,着手启动通志编纂工作。还有的行政长官干脆直接任职于通志馆。其中,张学良任奉天通志馆总裁、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任河南通志馆总监修、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任甘肃通志馆督修,而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云南省长周钟岳、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刘善锜、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肇甫等,分别出任各自所在地的通志馆馆长一职。 然而,这种局面很快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打破。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步好转,各地通志馆的筹建工作又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适时调整全国修志规划,经1944年5月行政院第660次会议通过,内政部颁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15年纂修一次”,要求“应由各省、市、县政府设立修志馆”,“修志馆组织规程另订之”(30)。与此同时,民政部还颁布了《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明确要求“市县政府得依本规程设置市县文献委员会”,“委员会以市县政府民政科长、教育科长、区乡镇长、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图书馆长、民众教育馆馆长及市县党部代表为当然委员,并得延聘熟悉地方掌故硕学通儒为委员,互推一人为主任委员,综理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文献委员会得设置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并得酌用雇员;总干事及干事一人委任,余由主任委员就县市政府及所属机关内遴员,呈请市县政府兼派。”(31)这似是一个与方志馆平行的政府机构,以从行政层面加大官修方志力度,客观上也助推了方志馆的专业工作。但在当时形势下,两者都未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共成立了23个通志馆,包括20个省级馆,2个市级馆。按时间顺序,抗战前成立的有15个,抗战期间成立的5个,战后2个。即于1927年前设立的广东、贵州、安徽、河南、江苏、福建、四川、甘肃、河北等省份的通志局(馆),于1929-1934年期间设立的山东、云南、广西、青海、陕西、新疆、湖北、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份的通志局(馆),抗战期间设立的江西、四川、宁夏等省份的通志局(馆),等等。其中开馆时间最长的是云南通志馆,前后维持了长达18年;最短的是台湾通志馆,成立仅一年时间便被改撤。就地域范围而言,华东以5个居首,西北4个,东北、华中各3个,华北、华南和西南各2个,台湾1个。(32)尽管当时名称不尽一致(如有的叫通志馆、通志局,有的叫修志馆、修志局等),规模条件参差不齐,职责功能繁简不一,存世长短时间不同,但都是各地修志事业的重要平台,也把方志馆的建设大大向前推动了一步,为中国方志馆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因篇幅有限,此处仅选介较有代表性的几家。 1.黑龙江通志局 在中国方志史上,黑龙江是最早设立省级通志编纂机构的省份之一(一说认为应早于浙江通志局)。早在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就设有黑龙江舆图局,并开展了《黑龙江舆图》的编修工作。进入民国后的1913年,黑龙江民政长朱庆澜专门上呈《呈大总统创修黑龙江通志谨陈筹办情形文》,同时制定了《黑龙江通志局章程》。1914年8月通志局成立后,由涂凤书任局长,巡按使公署次年还拟定了《黑龙江通志目录》。1919年11月通志局再次停办。1929年重新开局,但“九一八”事变后,通志局书牍及所成稿被焚无遗,有关总纂、纂修或去或病,通志局已无法再支撑下去。最后经已卸任的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等出资并多方努力,《黑龙江志稿》终于形成。黑龙江通志局几经起落,作为该省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志书《黑龙江志稿》编修前后经历竟达40年之久,且“不敢居通志之名也,曰《黑龙江省志汇稿》,方副其实”(33)。可见“乱世修志”之难。 2.安徽通志馆(34) 1920年,民国安徽通志馆始建,陈澹然任馆长。因时局动荡,经费不足,旋即关闭。1930年8月,省政府召开会议,到会委员提议援引江浙两省先例,设馆兴修本省志书。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安徽通志馆筹备处。9月通志馆在省垣安庆开馆。先是租赁安庆状元府街张姓私宅为馆址,但馆舍狭窄,昏暗潮湿,条件简陋。经通志馆呈请,1932年6月,省政府同意将教育厅教育成绩展览室的西侧两栋楼房中的17间给通志馆,办公条件大为改善。通志馆设正副馆长、总纂各一人,编纂和特聘编纂若干人,多时有60多人,均由省政府聘请。内设文书股和事务股两个机构,主任及职员均由馆长聘任。通志馆还编制了《安徽通志馆组织规程》,对修志机构作出具体规定。1938年,安庆沦陷前夕,通志馆将馆内藏书和各种志稿志材运至桐城县小龙山花山中方寺密藏。1942年,日军扫荡桐城,迎江寺住持率众僧将这批藏书秘密运回安庆,庋藏于迎江寺振风塔第三层,这批文献得以幸存。1946年,省通志馆在安庆恢复建立,但因经费等问题,通志馆与安徽省文献委员会龃龉一直不断。当年12月,省政府决定省通志馆并入省文献委员会。在战火不断、民生凋敝的时代,通志馆空耗经费、无所作为,亦难免招致报纸的挞伐、社会人士的指责和文献委的诘难,整理《安徽通志稿》的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1949年4月,安庆解放,通志馆为军管会文教部接收,馆藏文献最后辗转至安庆市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收藏。 3.奉天通志馆(35) 奉天通志馆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官修方志工作后第一个设立的省级方志馆。早在1907年清政府民政部给东三省总督下文,要求“酌量设局,重修通志”,但是应者寥寥。1928年张学良主政后,东北地区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景象,编修省志也被提到重要位置。1928年11月,张学良和奉天省长翟文选共同议定成立奉天通志馆,并联合署名下发通令在《奉天公报》全文公布,动员征集官府图书和私家著述,《奉天通志》编修工作随之正式展开。张学良亲任通志馆总裁,强调“盛京为胜朝发祥之地,志书为一省文献所关,续议纂修,实为巨典”。省长翟文选任副总裁,正副馆长及总纂、纂修等职务,均由省长延聘硕学名儒担任,如张学良恩师白永贞、著名学者吴廷燮、金毓黻等均曾参与其中并作出重大贡献。随着1930年奉天改称辽宁,奉天通志馆也改为辽宁通志馆,“九一八”事变后恢复馆务时,仍为奉天通志馆。 《奉天通志》编纂从1928年开始,到1935年编竣,历时7年。期间通志馆尽管因“九一八”事变曾陷于停顿,1932年伪满省长臧式毅也主持过通志馆的工作,但一批有“志”之士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日军曾请白永贞任地方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和伪满州国文教大臣等要职,被严辞拒绝:“国土沦丧,我痛不欲生,何惜一死?”他仍倾力于《奉天通志》的编修。最后经吴廷燮、金毓黻等共同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代巨著。 4.上海通志馆(36) 1928年,上海与江苏完成治权划分,成为特别市。1930年,市教育局首先向政府提出“设立市通志馆,兴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请求。同月市政府148次市政会议同意当年成立上海市通志馆,并成立筹备委员会,拟定《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组织规程》《编纂人选标准》等文件。1931年4月,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在市府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任市长张群在讲话中说:编修市志“是本市很重要而值得纪念的事”,本府和各位筹备委员“责任所在,无可旁贷”。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在收集资料、编制《上海史表长编》等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总体进展不顺利。 1932年1月,吴铁城任上海市长,准备正式成立通志馆,并请柳亚子出任馆长。开始柳亚子对此事一口拒绝,后吴铁城又请邵力子劝说,柳亚子表示:要担当此任,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一是志书编辑方针、通志馆人事,不受外界干涉;二是志稿须突破“官书”惯例,用白话撰写;三是通志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年号为辅,并表示当局完全接受这三个条件才会考虑任职。后经邵力子从中协调,吴铁城终于答应。胡道静认为:“柳亚子之所以接受此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和开拓性。……近代上海包容的就是这样一部矛盾交叉和关系复杂的历史,编志的意义非同寻常。”柳亚子说的十分清楚:“上海市通志馆,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料之首创者,允宜列为永久机关。”在各方努力下,上海市通志馆于1932年7月15日正式创办,馆址设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1号。 当时除馆长柳亚子外,还有副馆长朱少屏,下设编辑部(内有名誉编辑主任、编辑主任、编纂、特约编纂、采访员等多人,聘胡道静等人为编纂)、总务部(一说事务部,设有文书课、会计课、庶务课等机构),通志馆办有《上海通志馆期刊》,另外还成立了“上海通社”和“市年鉴委员会”等两个附设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通过研究上海地方史和编纂年鉴为通志编修服务。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志馆命运多舛。如1933年《上海通志馆期刊》发刊词便坦言:“工作进行不能如预期的顺利……处处觉有事倍功半之感。”原计划以一年为期编成至少250万字的《上海通志》,后改为四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共撰成志稿一千余万字并排出部分三校样清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通志馆重新开设,次年改为上海文献委员会,内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但直到上海解放,《上海通志》编纂任务仍未完成,所成书稿经多次辗转,由震旦大学图书馆移交给市文化局,最后由市博物馆收藏保存至今。 5.抗战时期的浙江通志馆 国民政府时期的浙江通志馆成立于1943年,在浙江史料征集委员会基础上改组而成。时任浙江省省长黄绍竑聘请余绍宋为馆长、凌士钧任副馆长,孙延钊、钟毓龙任总编纂。内设编纂室、秘书室、采辑室、总务课、会计室等机构,各时期分别约有20-40名工作人员。同时还在浙东临海县、浙西昌化县各设有一所办事处,并在各地聘有一批采访员、编纂员等专兼职人员。馆址设在浙西南云和县大坪村。 通志馆成立后,即编有“组织规程”等一系列文件规则,各项工作也都随之全面展开。但毕竟是“乱世修志”,当时至少面临断修时间长(之间间隔已长达二百多年,接续难度大)、时间紧、通讯不便和缺史料、缺人才、缺经费等六大困难。对这一艰难困苦的经历,余绍宋曾叹言:“窜身穷苦,茧足荒山,冲寒徒踱。莫漫多愁,天涯何处容安泊。”从中可见当时修志的艰辛境遇。(37) 抗战胜利后,浙江通志馆又随省政府迁回杭州北山梅庐。至1949年3月,前后共计六年,共编志稿125册(未分卷),约500万字,同时还采集了总量在五万件以上的史料文献。同年5月杭州解放。当时浙江省通志馆负责人、秘书谢邦藩个人署名并钤印的给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部一份报告,内称“全浙文献,求之不易,散失自属可惜,拟请指定有关机构接收保管”。5月11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军代表王鼎新率刘德山接管了浙江省图书馆、博物馆等场馆,所纂《重修浙江通志稿》也一直交由浙江图书馆保存至今。(38) (三)民国方志馆的主要特点 民国时期所建方志馆,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官”“学”并举。即不仅如前述:一批政府要人重臣直接入馆担当重任,而且十分注重聘请名宿硕学担当总纂及纂修,如金毓黻等人主纂《奉天通志》,吴宗慈主纂《江西通志稿》,李泰棻主纂《绥远通志稿》,余绍宋主纂《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等。各通志馆聘用的编纂人员,也多为硕学之士。(39)同时一些文化团体也纷纷参与,如近代拥有一千多人并散布于全国各地的著名文学团体“南社”,其社员普遍置身于当地通志馆并参与方志编纂。其中,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曾任江苏通志局局长,黄节担任过广东修志馆馆长,赵式铭、李书城分别为云南、湖北两省通志馆馆长。(40)柳亚子在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之前,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从馆长到馆员,全部为南社、新南社的成员。(41)将通志馆移交大学办理,也是民国时期方志馆的显著特色。如1932年,经由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致函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正式移交该校,校长邹鲁亲任馆长,广东通志馆一度也被称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同样河南通志馆1934年移交河南大学后,根据《河南通志馆组织章程》,馆长一职也须由河大校长兼任,等等。 二是“建”“研”并行。大批文化名人、学术大家的入行,不仅大大提升了地方志书的质量水平,促进了方志学理论的发展繁荣,对方志馆由实践层面提升到学术高度,也有积极促进意义。如广东通志馆纂修朱希祖对“通志”定义就作过诠释:“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讫于当今,是名曰通。”(42)1935年,分别任职于绥远通志馆的李泰棻和河北通志馆的傅振伦,也相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志学》和《中国方志学通论》。此外,湖北通志馆总纂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江西通志馆总纂吴宗慈的《方志丛论》,河北通志馆纂修甘鹏云的《方志商》,等等,都是当时方志学的研究力作。这种学用结合的实践,有效推动了方志馆事业的发展。(43) 三是“内”“外”并重。即除方志馆自身发展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与方志馆关系密切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场馆,或以融为一体的运行机制,或以性质相同的管理经验,也为方志馆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借鉴经验,其中尤以早期藏书楼、近现代图书馆与方志馆关系最为密切。如自民国5年至民国25年约二十年间,北京图书馆(旧称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共收全国各类方志达6000余部之多。1915年11月,教育部商议各省区,请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艺文。一年后,再次要求各省图书馆于搜藏中外图书之外,尤宜注意于本地人士之著述,以保存乡土艺文。1944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图书馆(1947年改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也明确要求要把收藏“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作为图书馆的重要任务。(44)等,这都反映了当时各地图书馆对方志的重视程度和收集力度。1926年由张元济创建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当时是东亚最大的图书馆,收藏地方志达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占全国方志总数的48%,国内外图书馆均难以企及。但绝大部分毁于1932年的“一·二八”战火,但它为中国方志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却永不可灭。(45)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民国各时期所建各种类型的“通志局(馆)”是当时方志馆的主要形式,但它们与“方志馆”还不能完全划等号。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就志书概念本义而言,“通志”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一般是指贯通古今的省志。尽管自古至今一些市县州府等志书也有贯通古今的形式,甚至有的市县志书本身就贯以“通志”名称,如仅浙江省历史上就有陈训慈所主编的《鄞县通志》等,但方志界多不视其为“通志”,这也是历来对“通志”约定俗成的共识。二是从各类修志机构看,当时名称十分丰富,并不都冠以“通志馆”名称,如1914年成立的“广东修志馆”,而且也不仅仅限于编纂省志。三是其职能大多限于修志,与今天所言的综合性地情展示有较大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方志馆”不仅在名称上与“通志馆”不同,而且其功能和涉及范围也不一致,应当说当代新型方志馆的职能更为丰富,内容更为宽泛,收藏展示手段也更为现代化,这是前者所难以企及的。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馆的建设发展过程 建国初,山东地志博物馆的建立拉开了新中国方志馆建设事业的帐幕。改革开放后新建上海通志馆等一批方志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方志馆事业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进入新世纪后,以北京、广东等方志馆为先导标志,表明中国方志馆事业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日渐成熟,日益完善。 (一)山东地志博物馆:新中国方志馆建设事业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事业包括各种形式方志馆的建设发展。山东地志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方志馆事业的正式起步。这是一种借鉴当时苏联地志博物馆的建设经验,以当地自然资源(包括地理、生物等)、历史发展和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绩)等三部分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又称综合性博物馆。(46)1977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还专门编译出版了前苏联《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该书有《古代黑龙江沿岸地区》等一批珍贵翔实的地情资料,客观记述了黑龙江流域原属中国的区域变迁历史。也许今天会有人对其“方志学会”的称谓存有疑义,但从方志馆专业角度看,“地志博物馆”作为综合性地情馆的创始地位和价值无疑是应值得关注的。而且直到现在,俄罗斯一些地方的博物馆还保留着这样的称呼。 受其影响,1953年10月,作为地志博物馆试点,文化部发文决定率先筹建山东省博物馆,并调集全国十几个省的专业人员协助筹建。1956年2月,《山东地志陈列》在山东省博物馆西院(原济南道院)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地志陈列,也是全国第一个地志博物馆,并在各地引起积极反响。(47)当时文化部在《对地方博物馆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中即明确指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和综合性的。”当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暨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交流会就在山东召开,并出版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交流会议汇刊》。一年后,在全国已建成的73个博物馆中,地志性博物馆就有31个。可见,“地志博物馆”与方志馆,特别是以展示综合地情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方志馆,确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全国各地近年来纷纷新建综合地情馆,不如说是方志界对我国已有传统形式的传承和创新。 不仅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而且现实中有的方志馆与其仍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如同样是山东省,2010年建立了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以“博物馆”命名的“山东省史志博物馆”。其馆藏、陈列主要分为三类:地方志成果、旧志和反映山东省自然、人文以及历史文明的各类资料与实物,包括旧志编纂与传承、新方志编纂与管理、年鉴管理与出版、方志馆建设等各方面内容,共展出9万余册各类志书及历史文献,3000余件史志文物,1000余幅图片。尽管这在目前全国方志界包括博物馆界尚属个例,尽管我们也尚未考察过山东史志博物馆与山东地志博物馆的渊源关系,但它确是以志书收藏和展示为主,同时兼及其他形式的一种创新,因而对全国各地方志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示范意义。 (二)上海通志馆及浙江建德方志馆:改革开放后方志馆建设事业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全国第一轮大规模修志热潮,新时期的方志馆建设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1990年3月,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省地方志学会、建德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征集地方志筹建方志馆的通知》,随后,“浙江方志馆”在该县白沙镇正式挂牌建立,馆舍借建德县档案馆库房,存放征集到的志书。新华社为此向社会播发通稿:《我国第一家专门收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专门机构——浙江方志馆在建德建立》,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方志馆的建设热潮。(48) 1992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正式向市计委提出《关于申请建立上海通志馆的报告》并得以批准开工建设。1996年,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通志馆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馆建筑总面积5800多平方米,总投资近一千万元,主要功能是方志编纂、成果展示、资料收藏服务、业务培训和学术研究、方志文化交流。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省级方志馆,它的率先建成,对当时的方志馆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之后,1994年武汉方志馆落成开放,1998年苏州方志馆和湖南方志馆相继建成开放,2000年湖北方志馆竣工开馆,等等,它们都成了改革开放后全国方志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印迹。但这时各地所建方志馆,大多仍以收藏志书为主,同时兼及编纂、办公、展示等功能,因而从总体上看,当时全国地方志馆建设事业正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化的转型期。 1997年8月,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强调:要研究和开拓志书的应用工作,要积极探索志书使用的新经验,要在图书馆设志书室。在他的直接推动下,1999年12月,“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在建于明嘉靖年代、中国现存最早(同时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正式建立。这是方志馆建设的又一种模式途径,在双方资源整合共享、优势互补的同时,也节省了大量财政资金。这对各地后来借助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场所共建方志馆,具有积极的借鉴示范意义。 (三)当代新型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持续深入,特别是伴随着公共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格局,各地方志馆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近年来,以国家方志馆和江苏方志馆、江西方志馆、广西方志馆、北京方志馆的陆续竣工开放为标志,各地方志馆建设持续升温。而且呈现出日益注重综合性地情展示,注重运用现代化手段,注重与其他单位资源合理配置、共建共享,以最大限度发挥效益等特点。 首先,综合性地情展示是当代新型方志馆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与传统方志馆不同的特色亮点。如2011年竣工开放的江西方志馆,除有传统的志书收藏展示功能外,还通过以下七个方面内容展示本地的综合地情:地理(包括行政区划、人口民族、自然资源等内容)、生态(包括生态保护区、鄱阳湖区域生态等内容)、经济(包括农业、工业、旅游、商贸和金融业等内容)、社会(包括科技、教育、卫生等内容)、文化(包括地方文化、红色文化和陶瓷文化等内容)、人物(包括古代、近代名人和英模等内容)和“十二五规划蓝图”。可谓覆盖全面,特色鲜明,这种布局理念和展示内容也是当前和未来方志馆建设的发展趋势。 其次,不仅是省级馆建设,近年来全国各地市县级方志馆建设热潮同样如火如荼。如山东省于2009年召开全省方志馆建设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加快方志馆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部署并掀起了建馆热潮。到2011年,全省已建成市级馆14家,县级馆95家,馆舍面积达2万平方米,馆藏志鉴书籍50万册。其中东营、泰安、威海、滨州等市及所属县(市、区)方志馆已全部建成,很多馆还有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编制,从而在全国方志系统起到了很好的先导示范作用。2013年下半年开馆的浙江余杭区(县级)方志馆,在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且近年来人气不断提升的旅游古镇塘栖建馆,与京杭大运河相伴,与古镇现存乾隆御碑、太史第弄、栖溪讲舍堂等景点相映成趣,短短几个月内就有约四万名游客入馆参观,平均日流量达到约500人次。不仅有力助推了当地旅游和经济发展,而且有效提升了方志事业的影响地位,被誉为目前全国最好的“县级方志馆”。 第三,各地新建方志馆还普遍注重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其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准之高,与以纸质形式和收藏方式为主的传统方志馆有天壤之别。如被列为2013年南京市政府为民办实事10大重点工程之一的市方志馆(与市档案馆合建),设计技术等级和质量要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其放置文书、声像、实物、珍藏等档案以及光盘库、音像、微缩拷贝片多媒体等电子档案的库房,对恒温、恒湿,防火灾级别等都作了最高处理,这也代表了当前和未来方志馆发展的重要趋势。 2007年3月,广东社会科学中心暨广东方志馆在广州天河奠基。该中心总投资2亿元,共有18层,地上16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达4.25万平方米。其中拥有近万平米的广东方志馆,目前已进入布展阶段,落成后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方志馆,也是当代中国方志馆建设事业的重要标志。 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上半年,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49)而且,部分已建在建或正在规划设计中的方志馆,纷纷从史、志、情、人、物等五个方面,力求突显地情型主题、延续性脉络、全景式展示、现代化手段等当代新型方志馆的特点气派,中国方志馆的建设事业正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 注释: ①朱希祖:《朱希祖文集》之《史馆论丛》,中华书局,2012年,第189-191页。 ②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 ③乔治忠:《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载《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④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⑤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⑥参见牛润珍:《北齐史馆考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 ⑦诸葛计:《纠正方志史上一个流行的错误说法》,《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 ⑧商慧明:《中唐史馆探微》,《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 ⑨李福长编著:《20世纪历史学科通论》,齐鲁书社,2012年,第30页。 ⑩朱清如:《论唐初史馆》,《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1)[英]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黄宝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12)潘晟:《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3)参见潘晟:《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诸葛计:《纠正方志史上一个流行的错误说法》,《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 (14)杜锡建:《元、明、清〈一统志〉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7期。 (15)《秘书监志》卷四《纂修》,转引自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4-325页。 (16)萨兆沩:《元代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7)张英聘:《论〈大明一统志〉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8)商慧明:《明代史馆考述》,《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 (19)尹直:《謇斋琐缀录》卷2,转引自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0)乔治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93-94页。 (21)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 (2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畿辅通志》提要”中语。 (23)参见《雍正修志上谕》,《雍正内阁一统志馆行查事项》,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678页。 (24)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1995年第39期。 (25)参见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上)》,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00-202页。 (26)《省通志局之开幕》,《申报》1915年8月15日。 (27)(28)参见徐逸龙:《徐定超和浙江通志局》,《浙江方志》2012年第5期。 (29)原载民国34年8月《浙江通志馆馆刊》第1卷第3期,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影印版。 (30)原载民国34年2月《浙江通志馆馆刊》创刊号,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影印版。 (31)原载民国34年5月《浙江通志馆馆刊》第1卷第2期,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影印版。 (32)曾荣:《民国通志馆述略》,《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 (33)柳成栋:《黑龙江方志考略》,《2013年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下册)。 (34)江贻隆:《漫谈民国时期的安徽通志馆》,《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35)董慧云:《〈奉天通志〉续写151年辽沈历史》,参见“辽宁档案信息网”。 (36)分别参见陈鸿:《上海市通志馆的发展变迁及其运作》(《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8期)、金建陵等:《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7期)、胡道静:《序跋题记·学事杂忆》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胡道静:《上海通志馆及上海通志稿》(《上海地方志》2012年专刊)、袁燮铭:《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上海地方志》2012年专刊)等文。 (37)云和县史志研究室:《浙江省通志馆在云和(1943-1945年)》(内部刊印本)。 (38)见许小富主编《杭州历史大事记》,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540页。 (39)(43)曾荣:《民国通志馆述略》,《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 (40)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7期。 (41)胡道静:《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608页。 (42)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44)邹华享:《中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概述》,《图书馆》(长沙)1998年第6期。 (45)分别参见张喜梅:《张元济与地方志藏书》,《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6期;《闸北之战,东方图书馆毁于战火》,《文史参考》2012年2月号(上)。 (46)姚安:《博物馆12讲》,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47)郭思亮:《筚路蓝缕 薪火相传——山东省博物馆发展史》,《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2期。 (48)见1990年3月13日新华社电讯稿:《我国第一家专门收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专门机构——浙江方志馆在建德建立》。 (49)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A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