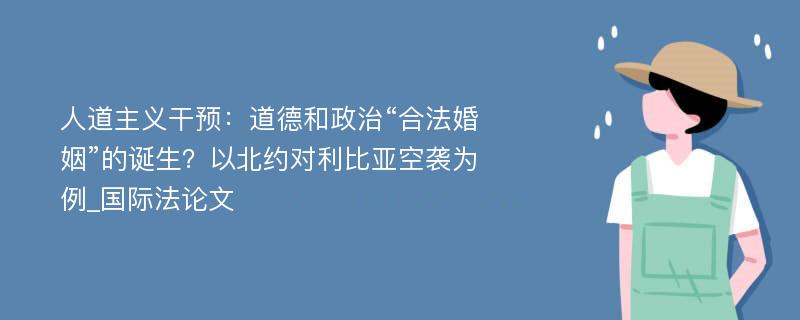
人道主义干涉:道德与政治“合法婚姻”的产儿?——以北约空袭利比亚为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比亚论文,北约论文,产儿论文,人道主义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2月,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延及利比亚,局势进一步发展成利比亚反对派与利比亚政府之间的武力对抗。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针对利比亚通过了以“保护平民”、“设立禁飞区”等为主要内容的《第1973(2011)号决议》。① 2011年3月19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部分成员国开始空袭利比亚,成为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他国使用武力的最新事件。该事件再度引起了世人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关注。众所周知,人道主义干涉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往往涉及道德、政治与法律等各方面。那么,道德与政治又是如何相互作用,致使西方国家决定实行或不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呢?其中,法律又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即法律是何时以及如何对人道主义干涉起到约束作用的呢?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以超越国际法学之更广泛的学术视野,采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交叉学科的方法加以研究。
一、无从发生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从表面上解读,人道主义干涉的逻辑似乎是,有了一国人道主义危机之因,便有了来自外部的武力干涉之果。其实,这样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因为此等逻辑隐去了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主因——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即通过使用武力所获的自身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人道主义干涉已达至需要使用武力之最高层级,因此,是一种“高级政治”。在“高级政治”中,权力与利益上升到了主导地位,道德则成了地地道道的配角,乃至沦为权力与利益的“遮羞布”。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美国“政策精英们的言辞被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尤其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道德原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②
一般而言,政治的中心要素是权力和利益。就权力因素而言,当下西方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远远超出被干涉的弱小国家。对西方国家而言,从手段上保证人道主义干涉所需的武力优势当无问题。因此,对于权力因素这个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必能满足的前提,本文不再讨论。于是,需要探讨的人道主义干涉之政治只剩下干涉国的国家利益。除道德与政治外,法律是另一个独立的变量,扮演着约束人道主义干涉的角色。总之,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复杂过程。
在本部分中,笔者所要讨论的是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第一种情形:仅有道德考量,而无政治意愿,武力干涉将无从发生。虽然这种情形下人道主义干涉有无引发与法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将其解读为此乃所谓的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之“权利”处于不行使的状态,便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在西方国家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历来就是两种“元理论”。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推崇人权、自由等价值观,而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权力、利益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仅以表象观之,人道主义干涉缘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而现实主义的权力行使(武力干涉)只是其手段。其实不然,除了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尚无西方国家在没有国家利益的情形下发起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实例。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曾断言:“实际上对一国仅仅是出于真正的人道目的而干预的现象是罕见的。19世纪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其后在欧洲,没有任何一国这么做的”。③ 美国国际法学者洛贝尔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道主义军事干涉的历史表明,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秩序很容易被滥用,‘人道主义干涉’起到的是为主张霸权提供新原理的功能。该历史充斥着强国或其联盟援用该原则隐藏它们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种种事例……此外,基于霸权国的国家利益,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是且将继续是高度选择性的”。④
可见,人道主义干涉是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凡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人道主义干涉,需要有道德(人道主义考虑)的由头,而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国家利益的动因)更是必不可少。俗语日:“无利不起早”。在实践中,即使他国真的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如果没有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也绝不会付出巨大的战争成本去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喻言之,在人道主义干涉中,单身的“道德”女子绝不可能有“武力干涉”之产儿。例如,肇始于2011年2月的阿拉伯世界动荡波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在西方国家看来,叙利亚和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远甚于利比亚。既然如此,为何北约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专挑利比亚下手,而放叙利亚和也门一马呢?此乃西方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使然:利比亚地处北非,通过人道主义干涉拔掉卡扎菲这颗钉子,不但有利于保护和扩大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石油投资等经济利益,而且对维护和扩大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势力大有裨益。而叙利亚虽然也是西方国家的眼中钉,但其地处中东要害部位,西方国家投鼠忌器,担心武力干涉的结果会点燃中东乱局的火药桶;也门则是西方国家的反恐前哨,一旦以武力推翻长期与西方国家合作的该国现政府,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可能会趁乱坐大,这对西方国家来说后患无穷。毋庸置疑,仅有道德考量,而无政治意愿,西方国家绝不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这样的逻辑转化为他们的法律语言即是人道主义干涉是一种可行使也可不行使的“权利”。当然,一旦坐拥国际法赋予的捍卫人权之“权利”,西方国家便有了作为“人权卫士”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对于人道主义干涉,西方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首先需要保证留权在手,至于该权利是否行使,则全凭本国有无重大利益之因素去定夺。此等选择性的“权利”行使,恰恰使得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大打折扣。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批判西方国家自利的选择性人道主义干涉之“权利”,贬损其正当性,意在表明,对这种武力干涉应严加控制乃至彻底禁止,当然不是支持将其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必得承担的一种“义务”或“责任”。
二、需要严控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本部分将要讨论的是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第二种情形:一国的确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西方国家又有自己的利益,那么,武力干涉就有可能发生。对此,法律应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呢?⑤ 喻言之,道德考量与政治意愿的联姻,可能会怀生人道主义干涉的产儿,这时法律是否要为它们发放“准生证”呢?
除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外,《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还明确禁止各国在国际关系中擅自使用武力。然而,在既有人道主义危机之由头(道德),又有国家利益(政治)驱动的情形下,西方国家实行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的可能性最大。例如,1998年西方国家欲以科索沃存在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盟)实行武力干涉,但因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安理会未通过授权动武的决议。然而,西方国家在巴尔干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战略利益的驱使下,1999年3月,北约公然绕开安理会开始对南联盟实行军事打击,开启了冷战之后单边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
笔者认为,国际法决不应当允许一个国家自发“准生证”而单方面对他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且有悖于法律以及政治、道德之原则。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实行军事打击之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为单边人道主义干涉辩护的狂潮,但它们的论述皆为道德“神话”,有意识地隐去了其背后的国家利益之要素。对政治因素的掩耳盗铃,使得西方学术界对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释论显然是“跛足”的,不足以证立。既然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绝非出于单纯的道德考量,那么必有国家利益于其中。这就表明,作为干涉国的西方国家是利害关系方,法律禁止任何利害关系方自证情势对他国是否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等自己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和证明。其实,这也是道德和政治原则的要求。亨金指出:“法律反对单边主义干涉也许首先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道德—政治上的结论,没有哪个国家可被信任拥有做出明智的判断和决定的权力”。⑥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42条的规定,可以授权使用武力的只有安理会。支持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的西方国际法学者往往高唱维护基本人权的道德律令是绝对的,使用武力无需他方签发“通行证”。⑦ 然而,如前所证,既然西方国家实行的原本就是有选择的人道主义干涉,那么何来这方面道德的绝对性。也就是说,既然西方国家有“权利”基于本国的私利决定是否进行人道主义干涉,那么代表国际社会的安理会当然也有权对西方国家这种选择权的行使进行审查,进而予以否决。
除道德之外,人道主义干涉还关乎政治,但这里的政治绝非仅仅表现为西方国家以权力界定一己私利的自家政治,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此次北约对利比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其目的路人皆知,就是要推翻利比亚现政府。⑧ 而一旦该国政权更迭,必然会引发有关国家在利比亚进行的大量石油投资等经济利益的维持和再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一国对他国使用武力,攸关现行国际体系的稳定。且不论西方国家滥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如果他们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轻易打开反恐先发制人、反制域外网络攻击、人道主义干涉等可对他国动武的“潘多拉魔盒”,那么世界将无宁日,国际社会将完全失序。既然西方国家实行的人道主义干涉兼涉道德与国际政治,那么就需要一个权威的平台对这方面国家间政治与道德以及国家间政治本身做出应有的平衡。无疑,安理会是法定的、也是最合适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安理会又应在何种情形下作出可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授权呢?按照《联合国宪章》第42条的规定,安理会只有在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时,才能授权使用武力。但是,该条并未直接规定可以对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人道主义事件进行武力干涉。据此,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安理会《第1973(2011)号决议》解释为包括了授权对利比亚进行武力干涉之内容。实际上,北约对利比亚进行的武力干涉超越了安理会的授权范围。⑨ 笔者认为,国际社会并非对一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麻木不仁,而是反对滥用人道主义干涉之手段。如果一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么安理会授权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就是合法的,同时也是唯一合法的情形。但是,作为《联合国宪章》第42条之特例,对这种情形应作严格解释。例如,1992年,安理会授权对索马里实施人道主义干涉,中国虽然投了赞成票,但强调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形。⑩
三、应予禁止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在“高级政治”的逻辑下,可能会出现本部分拟探讨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第三种情形:西方国家出于本国重大战略、经济利益的需要,夸大他国的人道主义问题,进而实行武力干涉。毫无疑问,残缺的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产下的必然是“武力干涉”之畸形儿,国际法决不能为之发放“准生证”。
现在,这种虚假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清除异己国家之基本战略的关键一环。为了颠覆某个国家的政权,西方国家首先会千方百计地培育该国的反对派势力,并抓住发生在该国的某一事件,充分运用媒体、互联网等各种渠道的软实力优势,煽动该国反对派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政府方如做出让步,反对派便会步步紧逼,直至现政权最终倒台。反之,政府方如强制平息事态,必然会与反对派支持的民众发生冲突。此时,西方国家便会左右国际舆论,夸大乃至编造该国的人道主义问题,并祭出两样“法宝”:一是针对该国政府,威胁实行人道主义干涉;二是针对该国领导人,威胁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此等双管齐下的结果有二:(1)如果该国政府对反对派不敢再“轻举妄动”,任由事态发展,那么就等于坐而待毙,终将难逃下台的命运;(2)如果该国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恢复秩序,那么西方国家就会伺机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帮助反对派强行推翻现政府。
目前,西方国家对他国使用武力,要么以行使自卫权的名义,要么主张反恐可以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面对强权,世界上还有几个弱小国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武力攻击西方国家或与恐怖组织合作?因此,借助自卫和反恐对他国动武并非西方国家的常用之计。而人道主义干涉之所以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是因为其实施可以是主动的。按照亨金的说法,任何国家总是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如果不论他国发生的人道主义问题严重与否,均可将之作为“入侵的前奏和理由”,(11) 那么人道主义干涉就可成为西方国家动辄对他国动武的工具。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如此大行其道的结果是国际社会又将倒退到欧洲“文明国家”对亚非拉“野蛮国家”实行“炮舰政策”的时代。在虚假的人道主义危机下,允许单边推行武力干涉等于承认“人权大于主权”包装下更为恶劣的“强权大于主权”的逻辑。国际法如任由国家主权这一基石严重松动,那么现行的“威斯特伐里亚国际体系”(12) 就有崩塌的危险。
就此次利比亚的内部动乱而言,也可能存在一些人道主义问题,但其否已经达到需要外部武力干涉的程度,值得怀疑。从北约空袭后的局势看,大量平民死于战争以及沦为难民系利比亚内战及北约空袭本身所致,而并无确切的证据证明利比亚政府一方仍在故意实施非人道行为,而此时北约并未停止武力干涉。就此,世间舆论普遍认为,北约发动空袭乃自己的战略、经济利益等使然;北约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推翻卡扎菲政府,并非出于消除人道主义危机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所谓的“保护平民”只不过是给西方国家赤裸裸地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穿上了皇帝的新装”而已。鉴此,我们决不能轻易地把《第1973(2011)号决议》解释为安理会已经授权对利比亚实行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
对于这种虚假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安理会理应予以否决,而不应通过授权决议为之背书。然而,西方国家在安理会大搞政治运作的结果,最终有可能会形成像《第1973(2011)号决议》中那样措辞模糊的条款,(13) 从而为西方国家滥加解释并据此实行武力干涉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在安理会中,对于一国是否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应当建立一套公正的证明程序,以防止西方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获得对他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授权。在此次安理会讨论《第1973(2011)号决议》的过程中,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说明为何投弃权票的理由时明确指出,不能在“可信信息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对利比亚进行武力干涉。(14)
不要说他国真的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情形),即使安理会判定该国并未出现这样的危机(本部分讨论的情形),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西方国家也会恃仗绝对的权力优势,发起单边的武力干涉,导致国际强权政治最终抛弃国际法。就此,“人们广泛相信,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旦诉诸战争,国家便不会在意国际法。在国际活动的所有领域,战争的利害攸关度最高。因而,国家不会纠缠于法律的细节。它们必须去做为保证国家利益需要去做的任何事情”。(15) 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国际法之类的镇静剂无法压制西方国家在强大的国家利益刺激下引发的武力干涉之狂躁,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抵制和反对所形成的社会压力,或多或少可使西方国家感受到单边人道主义干涉不是可随意动用之利器。实际上,西方国家在从事违反国际法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后,也不敢轻易地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它们担心其他国家会起而效之。例如,虽然1999年未经安理会授权北约对南联盟采取了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但在事后北约成员国要么宣称这只是一个“特例”,要么干脆不表明此乃基于人道主义实行的干涉并提出法律上的辩解。北约成员国之所以如此“缩手缩脚”,是因为它们担心会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以人道主义为由单边干涉其他独联体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16)
四、可以阻却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在人道主义干涉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据此,当政治和道德因素都不是非常彰显,或是道德因素比较彰显而政治因素不是非常彰显时,即当西方国家对进行武力干涉与否的态度尚处在摇摆之中时,法律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干预变量。可以说,当政治与道德结合的动力本身并非十足,而法律又不承认它们为“合法婚姻”时,那么可能就不会有私生的“武力干涉”之产儿。此乃本部分所要讨论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最后一种情形。
即使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否认国际法对一国行为的边际影响力。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虽然主张在国际政治中权力至上,但他同时也认为:“必须区分正当权力——即其行使得到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和非正当权力。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必须区别于赤裸裸的权力。警官凭借搜查证搜捕我的权力本质上不同于强盗持枪所做同样行为的权力。这种区分不仅具有哲学意义,而且关系到外交政策的实践。其行使能够获得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比相应的非正当权力可能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正当权力比同等的非正当权力更能影响权力对象的意志,基于自卫或以联合国的名义,能够比通过‘侵略’或违反国际法更为成功地行使权力”。(17)
既然如此,在西方国家对是否实施人道主义干涉举棋不定之时,通过国际法的否定性干预,有可能会打消它们实施武力干涉的企图。亦即,有无安理会的授权可能会影响它们决策的结果:如获得安理会的授权,那么西方国家的行动便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能成为助推它们实施武力干涉的催化剂;反之,若安理会拒绝授权,西方国家的行动便无法做到师出有名,则这样的镇静剂有可能会抑制西方国家实施武力干涉的冲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任何未经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都是不合法的,但其不合法性的程度事实上又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安理会的所有拒绝授权,同为可降低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之兴奋度的镇静剂,但每一次所含的药物剂量可能又是不同的。这样的不合法性程度之差异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安理会的议事规程看,一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是,除提出方之外,一项人道主义干涉议案因遭安理会其他全部成员的反对而胎死腹中;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则是,其他安理会成员均予支持,但因一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人道主义干涉议案未获通过。在两者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其他情形。显然,前一种极端情形下未获安理会授权所带来的极强不合法性,对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的抑制作用会更大;而后一种情形下未获安理会授权所带来的较小不合法性,对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的抑制作用可能就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现行国际法中,迄今尚未发展出明确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体规则,安理会作出是否授权的决定基本上是国际政治过程的产物。因此,当安理会作出否决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的决议时,西方国家会认为这只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决议的正当性难令他们信服,从而使安理会阻却单边武力干涉的效用大打折扣。例如,1998年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北约意图对南联盟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安理会决议就被西方国家视为一种罔顾道义的政治决定,可以不必过度理会,进而促使他们绕开联合国,发动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
有鉴于此,我们应积极支持国际法发展出有关约束人道主义干涉的准则。(18) 一旦有了这些准则,西方国家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这些准则且安理会对人道主义干涉做出不予授权的决定,那么西方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成立,从而可在更大程度上阻却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为了不让自己被束缚了手脚,西方国家历来抵制在国际法中讨论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体条件。(19) 基于相反的考虑,中国政府以往对此也持反对的态度,担心加入这样的讨论会被认为预先已经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20) 然而,在安理会已屡对人道主义干涉作出授权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拒绝就此设置必要的实体条件,反而容易为西方国家在无直接国际法规则约束的情形下获得安理会的授权提供可乘之机。
就此次北约空袭利比亚而言,假设安理会的动议不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不完全明白就里的情况下提出的,且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投的是反对票而不是弃权票,《第1973(2011)号决议》没有通过,那么在未获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还会对利比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吗?虽然历史不能被假设,但这样的问题仍然可以探讨。如上所述,在此次北约对利比亚的武力干涉中,人道主义考虑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幌子,关键的问题是北约对利比亚实施武力干涉之利益和权力是否大到足以罔顾《联合国宪章》及安理会之权威的地步。笔者认为,北约此次对利比亚实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有可能属于本部分讨论的情形,即推动北约武力干涉的利益并非大到了十足的程度。鉴于利比亚多部族国家的特点和基地组织可能会乘虚而入等风险,西方国家对武力干涉利比亚的结果可能并无充分的自信。(21) 在北约对自身行动之信心尚有不足,若再加上没有安理会的有力授权,即行动不具有合法性且其程度又相当高的情形下,北约选择放弃或推迟对利比亚实行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五、结论
综上所述,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复杂过程。其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法律是约束性力量。从该“一主一次”之原因——政治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可以区分出以下四种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国际法作为一个约束性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分别为:
第一种情形是,只有道德之次因,而无政治之主因,人道主义干涉无从发生。虽然在这种情形下人道主义干涉的缺位与国际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西方国家将该情形下人道主义干涉的不实行界定为一种可凭私利加以选择的“权利”。从法理上看,其正当性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第二种情形是,既有政治之主因,又有道德之次因,人道主义干涉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虽然具备了道德和政治两大原因,但绝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可擅自采取武力干涉之行动,所有的武力干涉概须经由安理会的授权。此乃《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也为公正地判断人道主义危机等是否真实存在、平衡其他国家的利益、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所必需。当然,安理会如要作出授权人道主义干涉的决定,就应恪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其行动范围应固囿于其职权范围内的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情势。
第三种情形是,没有道德之次因,但有政治之主因,人道主义干涉仍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因为不存在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不言自明,安理会不应对西方国家作出实行武力干涉的授权。就此,国际法绝不能为连“人权大于主权”都无法粉饰的赤裸裸的“强权大于主权”之行径大开绿灯;否则,现行的国际体系危矣!然则,当国家利益非常彰显时,国际法可能还是无法阻止西方国家非法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尽管如此,法律并非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其终能使干涉者对自己的非法作为有所顾忌。也就是说,即使国际法无法使西方国家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无照驾驶人道主义干涉之战车“急刹车”,但从长远看,国际法开出的“违反交规通知单”仍有助于抑制他们毫无顾忌地滥用这种非法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并阻止相应的国际习惯法形成。
第四种情形是,政治之主因未达高强,道德之次因或强或弱,人道主义干涉与否处于摇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的介入可在边际意义上阻却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为了增大这种阻却的效力,需要提高西方国家实行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的违法性程度。就此,要求安理会其他会员国应加强协调,以更多的反对票及弃权票否决西方国家提出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动议;同时,还应支持国际法发展出有关约束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体条件。
注释:
① 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S/RES/1973(2011),2011年3月17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2011/s1973.htm,2011-05-26。
② See J.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 Company,Inc.,2001,p.25.
③(11) [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④(16) See J.Lobel,Benign Hegemony? Kosovo and Article 2(4) of the U.N.Charter,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9,1999.
⑤ 在人道主义干涉领域,从实体条件看,至今没有专门的国际条约,通常认为,也没有公认的、清晰的国际习惯法。在程序要件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的规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必须获得安理会的授权。因此,我们从“实然”的层面讨论现行国际法对人道主义干涉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关注的主要是安理会授权与否对西方国家决策的影响问题。
⑥ See L.Henkin,Kosovo and the Law of“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3,1999.
⑦ See F.R.Tesòn,The Liberal Case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J.L.Holzgrefe & R.O.Keohane (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al Dilemm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93-129.
⑧ 参见孙宇挺:《李保东大使:不能以保护一国平民为由卷入内战》,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5-11/3031005.shtml,2011-05-08。
⑨ 参见[德]诺曼·佩希:《武装干涉利比亚严重违反国际法》,《参考消息》2011年4月1日。
⑩ 参见[法]让-马克·夸克:《迈向国际法治:联合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回应》,周景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5页。
(12) 参见伏广存:《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2页。
(13) 作为该决议关键授权条款的第4段笼统地规定:“授权已通知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和与秘书长合作采取行动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管有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段的规定,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同时不在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请有关会员国立即通知秘书长他们根据本段的授权采取的措施,并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些措施”。
(14) 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498次会议临时逐句记录(S/PV.6498)》,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S/PV.6498,2011-05-21。
(15) See D.Armstrong,T.Farrell & H.Lambert,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36.
(17)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版,第58页。
(18) 拟议中的这些准则包括:(1)必须证明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情势;(2)干涉应当具有正当的目的,即为了结束人道主义危机;(3)使用武力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之前应用尽各种非军事手段解决危机;(4)采取的手段应与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程度相称,即应符合比例原则;(5)应权衡后果,即作出采取武力干涉不会比不采取武力干涉结果更坏的判断。See G.Evans,When Is It Right to Fight? In Survival,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Vol.46,No.3,2004;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http://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ch14.htm,2011-05-20。
(19) 参见[美]菲利斯·本尼斯:《发号施令:美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陈瑶瑶、张筱春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20) See N.J.Wheeler,Legitimat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2001.
(21) 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是,在北约国家中,德国对《第1973(2011)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出的理由是,“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了使用军事力量的选择——考虑了它的影响和它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有巨大的风险。不应低估大规模生命损失的可能性。如果拟议采取的步骤最终被证明无效,我们认为有被卷入一场长期军事冲突的危险,这将影响到更广泛的区域。我们不应该在快速取得结果而又伤亡很少的乐观假设上,卷入一场军事对抗”。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498次会议临时逐句记录(S/PV.6498)》,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inbol=s/pv.6498,2011-05-21。
标签:国际法论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利比亚战争论文; 法律论文; 联合国宪章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