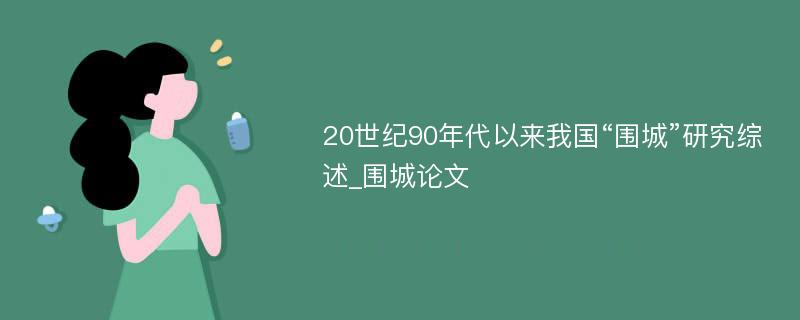
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围城论文,年代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城》作为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到十年,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论文达三百多篇;这些论文呈现出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或开掘了研究的深度,或触及了研究的盲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90年代《围城》研究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
一
岁月如流,距离钱钟书先生创作《围城》的日子一天天地远了;同样,距离产生过一代思想巨匠和文化昆仑的那个时代也一天天地远了。然而如同浮雕一般,背景的悠远使得精神实质更为突现,我们的评论家拥有了从容研究的心境和契机。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五十年的研究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对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究就出现于这样的背景下。
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的研究虽然不可抹杀它的认知价值,但毕竟流于肤浅。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拘泥于第一层面的批评几乎销声匿迹;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研究除各有发展外,还呈现出两相结合的趋势,即通过对文化层面的阐发,获得了对哲理意蕴的领悟。
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2期)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在与《子夜》的比较中,作者发现《围城》对背景的不同处理。在这里,背景描写并没有被作为人物行动的直接原因,相反,小说人物的生活及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氛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围城》就是通过社会历史时空与人物心理时空的这种矛盾组合,“塑造了中西文化合流中所产生的蜕变人格,表现了这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与民族时代精神的龃龉。”因为跳出了对作品细节与历史背景两相对照的机械罗列,作者的主题把握,从生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升华也就水到渠成了。文章最后一部分,借助对于方鸿渐悲剧成因的分析,宋延平继续将主题意蕴从对蜕变人格的讽刺扩展到了对于普遍人生的忧虑感伤,但整个论证过程稍嫌单薄无力。
陈子谦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注:《〈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3期)他认为尽管钱钟书否定了王国维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的断言,但他接过了“悲剧之悲剧”的概念,赋予它以愿欲说为中心内容的含义,并将其潜在意识成功地化为了《围城》的形象血肉。因此,杨绛在《围城》电视剧的片头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揭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围城心境”的悲剧心理,是对《围城》主题和方鸿渐形象深层的思想意蕴的准确把握。
从社会学的角度,瞿学伟提出了别具一格的看法。(注:《〈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围城”》,《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2期)他指出《围城》小说的主题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转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围城”。就“围城”的本土含义而言,这座城堡特指中国人的脸面观。所谓“脸”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人格特征及理想,其内涵为知耻,而“面子”则表示中国人所讲究的一种关系状态,其内涵为自我掩饰或虚饰。钱钟书在书中通过对留洋博士方鸿渐的遭遇描写,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为脸面观而进出两难的——没有者欲获得之,获得者又为其所累。并在展示中国知识分子在脸和面子之间所处的紧张性和困境的同时,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一群学者对前者的放弃和对后者的追逐。
张明亮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围城》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红楼梦》在主题上相通的文化意蕴——都是探讨人的生存意义或人在成长过程里社会化与个性化的两难二悖。作者认为,人是应该长大成人的,但莎菲陷于自爱兼自厌中长不大;宝玉却是不肯长大;而立之年的方鸿渐比莎菲宝玉成熟多了,却也陷入了“无出路境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的失败是由于他并不坏或未能修炼得不惮于坏。方鸿渐显得尤为孤独与脆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使他正直地做人。作家借方鸿渐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无尽的舛讹与磨难的悲悯,故方的悲剧能最强烈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注:《从莎菲说到贾宝玉再说到方鸿渐——对“文学面相学”的一个思考:表情与感情,兼论人的“社会化”过程》,《钱钟书评论》卷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张清华的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将对文化意蕴的提炼与对文化成因的探讨结合起来。他的《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4期)一文把《围城》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准确敏锐地洞见钱钟书不同于前人的新的文化策略,并在为这种文化策略的出现提供背景和寻找原因中,注入了对钱钟书的深刻理解。在对现代文学话语方式的整体把握下,张清华看到,出于对前代知识分子文化操作的情感色彩的理性反省,钱钟书选择了殖民文化视角的二元论批判。在《围城》中,钱钟书不但破除了任何理想神话的痕迹,而且揭示了中西文化的畸形对接所带来的深刻的矛盾悖论与分裂状态。殖民地文化心理的剥示和批判,是《围城》中最为广泛的批判内容。方鸿渐同世界文学长廊里众多“多余人”形象一样,他的悲剧是文化错位与“落空”状态下人的精神悲剧。作者认为,文化解构中的文化批判也是最后的批判,因为绝对的意义已不存在。从这种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充分地理解钱钟书的文化态度的策略性、逻辑合理性和现实意义,而不会因为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景的灰色文化而感到过分。
从以上述评可以看出,尽管“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研究者们都能自觉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或向文化里追根溯源,或从哲学上寻找理论支撑,从而将《围城》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
二
90年代以来,《围城》研究一改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出现了采用多种批评方法的新景观。这主要得力于研究者们对20世纪西方诸多文学理论的逐步消化吸收和融汇贯通。以下试从对各种批评方法的具体应用中介绍《围城》研究的状况。
1.比较文学与《围城》研究
“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注:《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著)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往往能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获得对作品自身价值的发掘。
张文江的《〈围城〉分析》(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6期)和张先飞的《作为哲理小说的〈围城〉》(注:《江汉论坛》1996年9期)都运用了影响研究中渊源学的方法。
林海发表于1948年的《〈围城〉与"Tom Jone"》第一次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指出《围城》与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传》的渊源关系。对此,张文江、张先飞先后撰文发表异议。张文江将《围城》的主要渊源扩展到整个西方的文化和文学。由此发现它不同于中国现代其他小说,“《围城》已是一部探索一条新路的真正实验。实验成功的标志是跳过了五四,直接接通了中西文化的渊源。”张先飞通过《围城》与流浪汉小说在“旅游”型叙述的结构模式中不同的时空观以及在精神实质方面的不同的比较,肯定“《围城》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哲理小说,而非流浪汉小说。”并进而追溯《围城》的渊源。认为《围城》与“欧洲出现的以萨特、加谬、波伏娃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小说以及卡夫卡的寓言体小说创作,同属于20世纪现代主义哲理小说。“其传统直接继承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哲理小说”。看来,渊源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对《围城》的理解。
刘新华的《同处20世纪风雨中——〈围城〉与〈洪堡的礼物〉的比较研究》(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2期)属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研究。他认为《围城》与美国现代作家索尔·贝娄的长篇名著《洪堡的礼物》能够对话,“是因为他们都以本民族的生活为题材,共同表达了人类对20世纪风雨人生的体验,体现了一种20世纪的文学精神”。通过比较,刘新华证明了跳出时代的局限,重新认识《围城》的可能性。
2.接受美学与《围城》研究
接受美学研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纵览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围城》的评论,“从热闹到寂寞,又从寂寞到热闹”(注:《浪打〈围城〉的回声——40年来的〈围城〉研究及其他》,解志熙著,《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9期增刊),阴晴变迁,耐人寻味。
王卫平的《论〈围城〉的三次接受高潮及其嬗变》(注:《钱钟书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中肯地分析了《围城》三次接受高潮呈现的特征、高潮形成的原因以及评论界的反应。第一次接受高潮是《围城》初版的时代(1947~1949年)。这次高潮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广大读者热烈阅读,另一方面评论界则毁誉不一。高潮出现的原因除了作品在艺术上的吸引力之外,首先在于方鸿渐性格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意义,其次是作品的艺术视界与战后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读者的经验世界有相契合的地方。1980~1987年出现了第二次接受高潮。这次接受高潮反映在评论界是对《围城》评价的高度重视,认识和争论的焦点是对《围城》历史地位的确定。此外,还对“围城”的题旨、象征意义进行了探寻。第三次接受高潮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至今仍有持续不衰的趋势。除了电视传播媒介这个外在的动因而外,《围城》所体现出的现代意识,文化意识和喜剧意识是联接当代接受者的精神纽带和桥梁,是《围城》出现第三次接受高潮的基本原因。这次高潮反映在评论界与前两次又一个明显不同是接受者已经超越了功利性,而进入审美期待和理性思维层次。
3.结构主义文学方法与《围城》研究
结构主义看重决定着表达方式的深层结构——语码(使语言能被理解的密码),而不是被表达的具体项目。
在《你看一盘散沙,我看一船珍珠——论〈围城〉的结构》(注:《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2期)中,张明亮运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发现《围城》琐屑散漫的叙述下隐藏的深层结构。
皮亚杰强调“结构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而是“一个若干‘转换’的体系”。由此,张明亮体悟到《围城》以方鸿渐为贯串的主人公,而写其他人物及鸿渐“过去的我”随时不断地fade out,恰就是《围城》最抽象的意义层次上的结构,即结构人的生存境况和心灵境况的动态结构过程。小说如此结构就反映出作家对人生的如此领悟。依“耗散结构”理论,《围城》全局性的动态结构过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故《围城》全书的情绪每况愈下。
这一时期,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围城》研究的还有吕芃的《作为形式要素的旅行——论〈围城〉中旅行的功能》(注:《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2期)、张明亮的《〈围城〉有个奇异的小“漏洞”——论小说的“僭述”与“虚构城”》(注:《作品》1994年8期)。前者着重分析《围城》中作为形式要素的旅行的功能,后者通过考察《围城》中一处“僭述”,于钱钟书的“意更危苦”心有戚戚焉。尽管都是从小处落笔,却也意味隽永。
4.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围城》研究
后结构主义亦可称为解构主义,是现代西方人文文化的最新思潮。
胡河清的《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注:《撩动缪斯之魂——钱钟书的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注意到钱钟书对这一思潮的关注。不仅钱钟书的主要学术著作如《管锥编》、《谈艺录》显现出语言颠覆的倾向,而且他的小说《围城》,也包涵着解构主义因素。伴随着方鸿渐的出城、进城,全文依次“解构”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官派性文化,分别由体面士绅和迂腐型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城话语系统”,以及海派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正因为《围城》这种全方位的文化解构,作者认为它已经具备了后结构主义的一切特征。
5.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围城》研究
由于男权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久已根深蒂固,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采用就显得尤为困难。如同攻克一座防守森严的城堡,稍有不慎,就会遭致丢灰弃甲、束手就擒的惨败。
在《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注:《上海文论》1992年1期)一文中,倪文尖面对凛然不可侵犯的“围城”,从男性女性关系的视角,采取一定的女性主义阅读策略,进行着机智的拆解工作,其胆大心细酷似骑士遗风,常常令我们拍案叫绝。
倪文尖首先不失公正地指出:《围城》在“至爱又至恨”上对男女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他同时敏锐地发现,以男性主角方鸿渐为视点为中心的叙述方式的采用,对鲍、苏、唐、孙四位女性形象就显得不那么公平了。
在方、鲍关系的叙写中,由于鲍小姐始终被予以沉默的处理,使得方鸿渐能够俨然以“女人先来引诱他”这一传统受害者形象坦然接受叙述者的同情。苏小姐作为叙述者“结构性”的工具,最终印证了男性文化的一大话语:“女人是祸水”。尽管叙述者偏爱晓芙,但由于视点中心全在鸿渐,她也免不掉是一位“迫害”男性主人公的“女性”形象。孙柔嘉的成功虽然是对男权文化的一个绝妙反讽,但这种批判没有能够贯彻于叙事始终。在最末两章,她作为一个创设“围城”式生存境遇的障碍“物”,主体性被忽略殆尽。
经由层层剖析,批判水到渠成:如果《围城》是相当自觉地探究男/女权力关系的文本,那么,成为文本的《围城》叙述的只是女性“围”男性的历史,小说《围城》讲的是一个男人被女人们“围”进“城”的故事。余音缭绕,发人深省。
纵观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从新的批评角度着手研究,往往能独辟蹊径,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同时,方法的运用只有与对文本的细读相结合,才能于细微处见深意,不致流于空泛。
三
半个世纪以来,对《围城》缺陷的批评经历了有趣的变化:1946年初版以来,一致的批评都指向它对时代主潮的游离——一个大得几乎不容辩白的责难。80年代多次再版以后,批评又集中于“吊书袋”、“比喻失当”等具体琐碎的文字操作上。前者过于武断片面,后者又太肤浅浮面。相形之下,胡河清和舒建华表现出独立谨严的治学态度,他们能跳出时代和作品的局限,从钱钟书创作心理的角度为《围城》的不足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
胡河清在他的博士论文《钱钟书论》(注:出版时名为《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胡河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凭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深刻体悟,指出:钱钟书对中国传统天命观冷峻彻底的批判,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非凡的气概。但是,对天命观过于绝对化的批评,却对他的艺术创作构成了微妙的影响。胡河清认为,“学究天人”的精神对于人类文化是具有永恒性的精神价值的。正是由于曹雪芹怀着对人生神秘性的深刻感受,所以他的小说始终带着一种梦幻的色调,人物的命运犹如星空般地深邃难测;而《围城》却始终贯穿着钱钟书极其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似乎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秘密了,作者把什么都看透了。因此,就整体气势而言,“《红楼梦》终不失为一部如大泽有蛟龙藏、能知往鉴来、极深研几的神明之作,而钱钟书的《围城》却始终跳不出寓意相对贫弱的学院派小说之格局”。
舒建华将钱钟书置于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通过对钱钟书在文学创作上两次心理转型——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细致分析,对《围城》的不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舒建华以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这次心理转型的结果是,钱钟书作为一个能真切进入哲学思维境界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创作获得了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独特的心理优势,即诗与思的谐和。但是,钱钟书从非理性主义到理性主义的第二次心理转型,由于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给他带来了一些创作心理障碍:诗与思冲突带来的“紧”的心理态势贯穿《围城》的创作,不仅以理抑情,而且情来扰理,终使整部小说在创作心理抑制和抑郁中,匆匆收场,留下读者的遗憾和作者日后持久的不满。(注:《文学评论》1997年6期)
胡河清和舒建华的研究不仅摒除了专横的外在标准的干扰,而且将研究的视线伸向了作家深层的心理结构,为《围城》创作得失的研究提供了一块亟待开垦的广阔领域。
四
如果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人文主义和形式、结构主义两大体系的话,那么,从以上综述中我们看到,近十年来,国内的《围城》研究大多集中于人文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这种理论思路的最大特点是将作品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阐发得淋漓尽致。比如宋延平的立论就建立在对《围城》中人物心理时空与社会历史时空的矛盾组合的认识上;张清华对《围城》的文化策略的反复申述旨在明确作品出现在当时的全部历史合理性;舒建华通过对钱钟书文学创作心理障碍的条分缕析,完成了他关于作家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主潮相偏离的指责,并且试图据此鉴示我国文学未来的基本走向;即使是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刘新华也认为《围城》与《洪堡的礼物》能够相互比较的前提就在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时代大背景,即同时产生于20世纪的风雨中。正是在这种对作品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的评论家寄予了他们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就为这种研究本身注入了永远跃动的生命活力。
但是,人文主义批评体系往往因专注于人在文学作品中生存方式的研究,忽略了对文学自身结构的关注。因此,在与形式主义的对峙中,有时难免出现捉襟见肘的尴尬。同样道理,尽管关于《围城》主题、人物形象等的研究见仁见智,但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仍逐渐显露出它的危机来。不难看出,由于缺乏文本结构的支持,以上论者各自相当不错的艺术感受竟产生了严重龃龉。比如:陈子谦视《围城》未能为方鸿渐指出一条理想出路为一大遗憾,刘新华则认为“作者的严肃思考已经指示了超越绝望的希望”;张明亮针对司马长风对作品“才胜于情”的观感,指出《围城》正是钱钟书“运冷静之心思,写热烈的情感”之范本,舒建华则从钱钟书与鲁迅的对比中得出钱钟书缺乏鲁迅所有的炽热情感这一相反结论;再有,陈子谦提出《围城》对方鸿渐的处理恰好完成了对作品的哲学主题的揭示,舒建华却认为作品对生存困境的揭示没有完全到位……如果说各种文学观念的兼收并蓄曾经令沉闷的研究空气空前活跃,那么,众说纷纭的表面终因缺乏来自作品内部结构的支撑,潜伏下裹足不前的危机。
看来,只有借鉴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对作品表层与深层结构的细致分析,不仅从中倾听作家独特的声音,而且据此洞察隐匿其后的心理内蕴,为《围城》的人文意义寻求得自作品的依托,《围城》研究才可望获得突破性进展。
“求心始得通词,会意方可知言”。《围城》研究呼唤的是投入生命体验的治学精神。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短暂而伟大的,它含蕴的巨大思想能量急待后学挖掘和汲取,研究《围城》,重要的不是对它作出或褒或贬的定评;通彻先生之“深文隐旨”,为的是能与一个人以至一代人相沟通。文本不会因阐释而有所增损,而我们却在不断地“说”中获得。能够面对这样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围城”世界,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
标签:围城论文; 钱钟书论文; 方鸿渐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 读书论文; 胡河清论文; 张明亮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