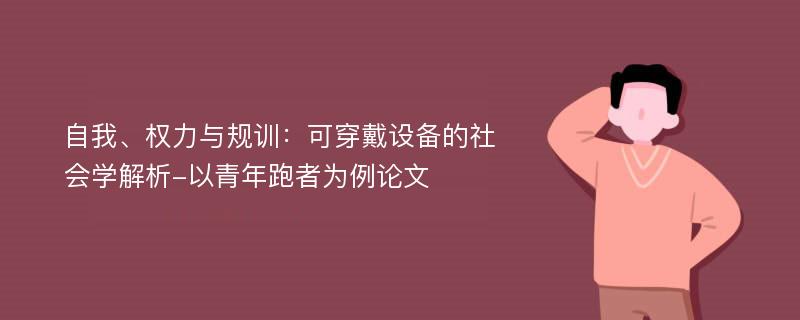
特别企划 Te Bie Qi Hua
移动互联时代的青年健身与身体规训
□ 选题策划、主持编辑/汪永涛
股骨头坏死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给患者日常生活带来影响。股骨头坏死发生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缺血,且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对于此类患者来说,其发生病理改变主要有2个阶段,初阶段,由于患者细胞缺血,骨髓细胞与骨细胞会大面积死亡,从而导致股死亡;修复阶段,患者骨与血管会再生,骨小梁吸收[3-4]。因此,患者在发病初期,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发生症状时,已经确诊为晚期,导致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影响其预后效果及生活质量。临床资料显示,股骨头坏死患者的治疗效果,会受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坏死范围影响。所以,只有早日诊断疾病,才能尽早接受治疗。
自我、权力与规训:可穿戴设备的社会学解析——以青年跑者为例
身体的数据化:可穿戴设备与身体管理
在失控与控制之间:新技术嵌入下青年人的日常健康实践
权力规训视域下的健身实践——以健身房为例
自我、权力与规训:可穿戴设备的社会学解析
——以青年跑者为例
□ 王 健
摘 要: 个体利用可穿戴设备进行自我量化的日常实践已成为一种自我追踪文化。以“通过数字了解自我”为特征的量化自我成为人们自我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可穿戴设备生成的数据、符号、图像等表征手段,个体实现了作为虚拟主体的身体叙事,满足了人际交往等心理需求。在跑步健身中,可穿戴设备促进了跑者的自我赋权,这也间接使得自我量化成为一种数字劳动。具有后全景敞视结构特征的液态监控则一直嵌入其中。可穿戴设备作为自我量化的重要媒介,不仅反映了个体自我管理的理性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科技对于自我的“赋魅”。
关键词: 可穿戴设备;量化自我;赋权;数字劳动;液态监控
数据主义(Dataism)是指人们的行为可以通过定量和大数据手段得到充分表示的一种共同信念。“数据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即通过在线媒体技术对各种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客观量化和潜在追踪”[8]。数据主义正在成为“对人类行为知识新的黄金标准的信仰”。可穿戴设备的流行,让跑者在健身运动的日常实践中实现了从纯主观体验到客观可视这一考量自我运动状态的转变。通过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咕咚等应用,佩戴运动手表或智能手环等设备,跑者可以把日常乃至参赛时的运动状况直接转化为数据和图像。只要条件允许,跑步健身中的任何动态都可以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内容。因此,由可穿戴设备形成的“数据自我”,逐渐构成了跑者们有关理想自我的重要部分。
可穿戴设备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他人的凝视,成为个体主动接受的凝视装置。也正是由于这类科技的发展,当代的监控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鲍曼因此提出了区别于福柯理论的“后全景敞视结构”—液态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其特征在于对个体的监控范围更广、效率更高并且方式更隐蔽[31]。因此,当代大众已经深陷液态监控的场域中,监控已经从可见或有形的单一方式,转变为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以信息为主的复杂模式。个体的量化自我的构建过程,也就成为液态监控实时运作的过程。可穿戴设备的规训作用就使个体发展出了不同的自我追踪形式。
我就觉得这个数据蛮好的,它能告诉你一周达标多少。当时设定的目标是8000步,是系统设定的运动量的标准,不是我自己设定的,如果你超过8000,它就会告诉你达标了。这个就成为我每天评估自己的一个量。(F01)
随着全民健身风潮的兴起,可穿戴设备也被人们广泛用于城市长跑运动之中,越来越多的跑者喜欢采用可穿戴设备记录有关自己的跑步日常。相关调查结果表明,跑者中采用智能手机、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记录数据的比率分别达到了81%、91%和57%,可穿戴设备已经逐渐成为跑者的标配[6]。因此,本研究结合对青年跑者的质性访谈资料(共有7名青年跑者参与了深度访谈,其中3名男性,4名女性;男性编号首字母为M,女性编号首字母为F)以及网上相关信息,主要围绕由可穿戴设备所带来的个体自我追踪实践展开讨论,深入分析可穿戴设备所体现出的量化自我、技术赋权以及身体规训等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
一、我“晒”故我在:可穿戴设备中的量化自我
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通过符号和图像取代了现实和意义,人类的经验与其说是现实本身,不如说是对现实的模拟,即拟像[7]。实际上,通过可穿戴设备所生成的包括图像和符号在内的数据信息,已经成为有关个体不同生活方面的拟像。可穿戴设备让个体可以与他人在线进行有关自我和现实的及时呈现与高效互动。在跑步健身过程中,跑者线下的运动实时传递到了线上,通过跑步数据所建构起来的量化自我成为网络时代有关跑者真实自我的“最佳复制品”。正是由于便捷的移动科技和酷炫的数字技术的加持,相比传统的自我表达方式,由可穿戴设备构建的量化自我就拥有了更大的吸引力,也成为网络传媒和众多商家机构所积极投资的领域。总体而言,跑者在跑步健身中使用可穿戴设备所生成的量化自我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数字化、同步性、互动态、娱乐化。
在教学实践上,百色学院紧密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和地方经济、文化的需要,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才为目标,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形成了“科研促进教学”和“立足边疆、服务边疆、走向东南亚”的鲜明特色。为了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实践性和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学校和有关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分别与靖西县旧州村、田阳布罗陀文化研究会、那坡吞力黑衣壮村寨、田林壮剧团等达成了合作关系,摸索成立研究和教学实践基地的路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和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了平台。
1.数字化
随着移动科技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智能化的手机、手表、手环等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在大众生活中迅速普及。这一现象的出现导致自我追踪(self-tracking)成为一种普遍的数据生产实践,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出现在了线上和线下等各种媒介中。自我追踪和量化自我,也被称为生活记录、个人分析和个人信息学,个体通过特定的装置或设备生成与自己相关的日常习惯、行为和感觉等方面的数据和图像,而后被定期收集、记录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优化自我的生活[1]。这些数字化信息已经成为自我表征、社会交流乃至商业推广、公共决策的重要依据。
当我决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就建了一个相册。相册底部是2016年的7月份,到现在已有三年。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备忘,因为定了个目标,就邀请了40位好友,相当于让他们来督促我跑步,促使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相册到目前为止已经记录了1193张照片。(F01)
进而,可穿戴设备收集到的个体数据成为可以与生产这些数据的主体相分离的人工制品,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和说明着个体及其生活。有学者就曾将这类个人数据称为数据翻倍(data double)[9]。数据成为跑者了解自我和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跑者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我追踪的数据,让自我实现了“身体去物质化”[10]。通过可穿戴设备所具有的多种功能来“分享”隐藏的身体,也就让个体在赛博空间中构建出了一个理想化的身体和“健康的存在”。
图式最初由康德提出,他把图式看作是“潜藏在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技术、技巧。而皮亚杰认为,图式是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是一种动态可变的认知结构。作为教师实践性知识表征的图式兼具康德与皮亚杰所指图式的特点,其既是一种动态可变、有组织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又是一种带有个性化的经验组织的技术。职校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图式类表征包括意象、隐喻、行动规则和实践原则四部分。
2.同步性
可穿戴设备和运动软件的出现,让跑者无须拥有相应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就可以及时获得想要的数据。可穿戴设备的这一特点,让跑者的运动生理状态和主观心理感受实现了同步连接。这同时也让跑者在认知负荷严重过量的当代社会,获得了难得的些许放松。
这个软件到1公里就会提醒你,“你已经跑完1公里了,用时多少多少”,然后快到2公里的时候就会有“加油”,完成2公里的时候就会说“太棒了,你已经跑完两公里了”。所以,这个东西也会鼓励我。因为自己有个目标,比如今天我就定好5公里,不用自己数,就等着它报就行了。(F02)
进一步,通过可穿戴设备的同步功能,跑者可以将自己运动健身的所有信息上传至网络空间,使得现实的运动状态得以扩展到其他跑者甚至更广的生活世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让跑者碰触的生活边界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延展,跑者的生命宽度仿佛也得到了扩展。同样,其他跑者也可以实时参与到发出信息的跑者的生活状态中,并在这个共同的兴趣平台上进行更有效的交流。比如,借助于可穿戴设备所营造的线上马拉松(即在网络上举办的马拉松。在马拉松活动当天,参加者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根据活动要求,完成赛事固定的跑步距离,即可获得官方授权的完赛奖牌、赛事奖品或电子完赛证书)就为跑者提供了一种无须亲临现场也能和同时参赛的其他跑者一较高下的虚拟场景。这种场景也就成为一种“虚拟共同体”,个体可以在那里与志同道合者会面,摆脱了身体共同在场时的局限,“具有多重性、解放性、平等化的特点,从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共在体验”[11]。这也正是可穿戴设备所具有的重要吸引力之一。
3.互动态
在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中,个体的日常生活变得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早已变得支离破碎。不过,当代的长跑健身运动俨然已经成为凝聚个体的一种流行的运动景观[12]。法国哲学家德波认为,景观(spectacle)不是图像的集合,而是由图像调节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3]。在跑步健身中,通过可穿戴设备生成的数据,就成为跑者之间进行持续的线上互动的重要资源。
跑个10公里啊,然后在群里打个卡。大家一看谁谁打卡了,都有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我看你今天打卡了,我不打卡的话,我自己会感觉比较愧疚,所以我就不能吃完晚饭在家里打游戏啊,或者躺在床上啊,这时我要出去流汗了。(M02)
除了围绕跑步主题所进行的交流之外,调侃生活、自我暴露等也成为跑者交流互动的题材。相互“点赞”成为一种有效的线上人际互动。这就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吉登斯所言的“存在性焦虑”,让个体有了一定的集体归属感和社会融入感。同时,由于上传和交流的内容完全依赖于跑者个人的生活实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跑者的主体性需求。因此,线上分享有关量化自我的信息,成为个体追求自我知识和自我优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经常令人感到愉悦和有趣的互动模式。
4.审美化
我之前认为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我现在做到了,就是给自己带来了成就感,会让我更加自信。跑完之后给自己带来精神状态的一些改变,也会促进自己自信。(F02)
今晚跑出了个大刀,希望跑友们的跑步水平永远宝刀不老。(M01)
今天是跑步四周年纪念,巧的是,咕咚显示我的跑步总里程正好达到了5000公里。截图保存,以示纪念。(M01)
因此,在全民健身的社会宣传背景下,可穿戴设备附加于跑步健身之上的各种抽象价值,极大影响了跑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自我呈现方式。可穿戴设备所具有的数字化、实时性、互动态以及审美化特征,让当代社会的青年个体有了更丰富多元的自我呈现方式,也让跑者拥有了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双重身份。
联合会等美国各大评估协会同加拿大评估协会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准则特别委员会,紧接着制定了《不动产评估改革》,这是美国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所颁布的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文件。自此以后,美国资产评估行业开始走向正轨。
由以上论述可以发现,量化自我背后反映的是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建构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已有调查报告表明,来自中产阶层的个体占据了跑步健身人群中的主要比例[15]。可穿戴设备所生成的信息,也就成为这一群体借以释放压力和焦虑的“安全阀”,这也是量化自我出现的重要前提。因此,通过可穿戴设备,青年跑者获得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得的积极体验,同时也契合了当代青年群体追求自我完善的价值观。
二、我的身体我做主:可穿戴设备中的技术赋权
人的身体不仅是一种肉体单位,或者是物质性的自然器官,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生命单位[16]。由于“从外表可以当成是内在自身的反映的角度来看,忽视身体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可接受性,也是一个人懒惰、不够自重(low-self-esteem)甚至道德失败(moral failure)的一种标志” [17]。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作为美好生活标志与文化资本标识物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的兴趣。同时,“身体的美、对衰老身体的否定、对死亡的摒弃、运动的重要作用以及保持身体健康的普遍道德价值,是人们尤其关注的焦点”[18]。因此,消费文化通过对身体表现力的强调,进而影响了大众对身体的关注,这就激发了人们倾向于掌控身体来满足消费文化所提出的要求。
受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群体,通过运动以提升健康成为对自己负责的一种重要实践行为。国家也鼓励个体积极从事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使其成为可管理的、有生产力的资产,而不是社会的负担。个体为自己的健康利益不断进行着努力,从中实现的利益也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相应地,身体不仅是实现这些利益的技术手段,而且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19]。莫斯在对人类行为的外部环境转化为主体的活动和行为的研究中,就将身体视为个体首个最自然的对象,将技术视为在特定物质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效”行为,并采用“身体技术”一词来表明人们了解并使用身体的各种方式[20]。福柯借鉴莫斯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进而提出了“自我技术”的概念[21]。这一术语是指“个体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22],从而打造出一种“驯服的身体”。
可穿戴设备的流行,代表着人们采用科学和工具化的方式对身体所进行的一种管理。规训技术因此也就扩展到了人们的闲暇领域。在跑步运动中,跑者的身体屈服于个体有效的量化管理模式之下,跑者掌控身体、心理和自我的能力也就通过这种技术规训而得到了增强。
1.身体边界的扩展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已指出,媒介是人之身体的延伸[23]。在他看来,媒介不限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形式,他把人与环境产生关联的任何工具、符号以及互动方式都归入到媒介的范畴。这些延伸就强化了人的能力。比如,当代的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实际上与传统的纸质日记相似,“用当代的传媒方式与他人探讨、反思、交流和分享”[24]。技术进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人体和技术形成了一个新的经验实体。在跑步健身中,可穿戴设备就与跑者的身体产生了融合,并作为身体的一种具体延伸而被体验。
最早的条码技术包括条码标识、扫描器、边缘定位线圈和译码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现代条码技术由编码技术、标识符号设计技术、标识识别技术以及计算机管理技术四块组成。条码技术的使用原理为:扫描器发射光线至条码上,测出条码的反光强度,产生与接收光强度成正比的小电流,输送矩形波至译码器,对此加以识别之后,完成整个扫描过程[1]。
我跑步时往往是戴耳机的。因为有专门的跑步音乐,它有节奏,我在里面选几首,一开始什么节奏,后来什么节奏。跟着节奏跑的话,就像跳舞一样,感觉到浑身放松。你跟着节奏跑下来,根本没什么厌倦或者劳累的感觉就跑完了。(M03)
上课之前,教师必须认真研读课文,与文本对话,整体把握,抓准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找到教学的“点面结合点”,即突破口,或一个字、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以此为切入点,牵一发动全身,顺藤摸瓜,层层深入,理解文本,实现教学目标。
被利用的自我追踪通常表现为一些公司利用推广给消费者的应用程序来获取有关消费习惯、品牌认知以及社交互动的数据。有的网络科技公司会通过终端智能设备,如手环、手表、血压计等,将用户数据传输到云平台上,来间接收集有关客户的身体健康数据指标。针对跑步运动而言,跑者在手机中通常装有自己常用的跑步应用程序。在笔者所访谈的跑步爱好者中,咕咚是最常见的运动软件。跑者们平时就会通过这个软件来记录日跑量、周跑量、月跑量乃至年度跑量。
2.外显身体的控制
实际上,跑者往往会把可穿戴设备视为一种服务于身体的工具,以增强自己对身体的控制力。跑者经常在有关跑步的叙述中谈到对身体控制和策略的选择。可穿戴设备技术以及由此生成的有关自我的数据为跑者了解身体以及增进跑步水平提供了客观指标。在此意义上,可穿戴设备就赋予了跑者一种更有效控制身体的力量。
年主导风向:10 m高度主导风向W,次主导风向WSW,主导和次主导风向的风频分别为14.64%,11.57%。年平均风速为100 m高度6.37 m/s,10 m高度4.60 m/s。显然,平均风速随高度增高而逐步加大。
1)将样本数据集M={m1,m2,…,ml}中的样本点存入邻距离矩阵Ndm=Nn×Nn中,其中Nn为数据集合M的数据总数,矩阵的每一行表示数据集M中的数据m1与其他数据间的距离.之后对粒度变量Gv初始化.
此外,移动影像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个体更多控制外显身体的能力。从只能看影像却不能记录的镜子,到可以记录图像也能看到自身的传统相机,再到完全可以把自己拍进场景中的可穿戴设备,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自由呈现自我的时代。跑者完全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这样一种最常见的可穿戴设备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反思。其所具有的删除旧图像和拍摄新图像的便捷功能,就在另一层面上展现了跑者对外显身体呈现方式的控制。
3.内隐心态的调节
通过可穿戴设备上的运动社交APP,跑者不断分享和吸收着有关跑步领域的知识,这有助于跑者获得更高的睡眠质量、情绪调控能力、更好的人际关系。其中,个体也在积累着关系资本、文化资本,从而逐步提升自我效能感。同时,跑者通过可穿戴设备将收集到的数据传输到其他数字设备、应用程序和平台,增加了有关自我的知识,共享了运动数据,进而获得了一种自我革新的能力。比如,跑者通过可穿戴设备收集到的信息有助于改善精神生活、实现自我意识的优化。
2.3 特色的身体文化传承 作为身体运动形式之一的峨眉武术,不仅拥有显著的地域人文特色,而且还拥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显著文化标识、思维意识(坚韧不拔)与行为意识(尚武崇德)。由于峨眉武术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人,峨眉武术文化的发展的载体也是人,习武之人不仅要学习其相应文化知识,还要动用身体,模仿并掌握其技术的外在形态,所以人在峨眉武术传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即便是枯燥乏味的数据,也可以得到丰富多彩的可视化展现。可穿戴设备中的跑步软件所具有的自动追踪功能,可以使跑者实现运动痕迹的可视化。因此,在朋友圈晒出一张有着特殊形状或美感意义的运动线路或者数据信息,也成了彰显自我审美的一种途径。有研究发现,在用于跑步和骑行的量化软件中,用户会通过选择具有特定形状的路线来绘制数据。这也被称为审美好奇心式的量化[14]。有跑者会刻意跑出一个具有美感意义的运动轨迹,或者截图保存具有纪念意义的跑量记录等。
因此,借助可穿戴设备管理身体已成为跑者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内容,它能帮助跑者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以及个人自我管理的“权利”伦理决策。诸多研究表明,个体的量化自我的过程,既是一种可以有效管理自身事情的证明[26],也是一种借助技术管理身体进而减轻自身压力的方式[27],运动消费也就具有了自反性的作用[28]。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观点,个体对这种自反性的解释构成了一种“他人导向”的自我[29]。个体为了应对当代社会的变动不居,可穿戴设备就起到了类似“雷达”的作用。这种雷达能从外部获取社会线索,个体通过感知可穿戴设备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就会在不熟悉的情境中更容易寻找到方向。
作为“首都餐饮业品质提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提升首都餐饮业品质的重要举措,同时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具体要求,中国烹饪协会制定并发布了《北京市餐饮业就餐区和后厨环境卫生规范》、《北京市餐饮业客用卫生间清洁卫生示范导则》、《北京市餐饮业文明服务导则》和《北京市餐饮业品质餐饮示范导则》。“一规范三导则”是中国烹饪协会在履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工作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组织职能的实际行动。
总之,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受计算的理性支配的”,那么他就可以获得社会对自我控制的认可,自我控制本身就是受到社会高度重视的一种品质。于是,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身体的管理实际上反映了韦伯提出的理性化,个体试图通过科学手段来解释和控制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可穿戴设备可以被视为吉登斯所言的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在内的脱域机制的一种具体媒介。在可穿戴设备的助力下,身体成为跑者最忠诚和可靠的领域,个体通过把问题解决过程内部化,从而完成了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自我赋权。
三、后全景敞视主义:可穿戴设备的液态监控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曾提及边沁对轮形监狱的设计,这种建筑结构将使囚犯自动保持纪律,始终按照监狱看守人的要求行事。这其中反映的监控实质被福柯称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其中,福柯的这种自我规训需要依赖于一种“凝视”装置,一种主体在其面前想象自己的他者视角[30]。
实际上,作为工具的可穿戴设备以及作为其结果的量化自我,已经演变为技术嵌入到个体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的消费实践。社会文化、商业目标和关系伦理都在这种现象中交互缠绕。通过可穿戴设备所生成的海量数据和信息,个体实现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凝视和互动。其中,人们以大量数据、符号以及图像为媒介,进行着虚拟自我的呈现和“脱域”的人际交流,从而满足了自我的各种精神和心理需要。自我的量化逐渐变成了移动互联和网络社交时代的重要特征。然而,当前国内对可穿戴设备及其所导致的量化自我这类现象的探究,还只是局限于教育技术[2]、消费行为[3]、信息管理[4]、健康促进[5]等领域的解读。由于可穿戴设备早已深入到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所以就有必要从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在可穿戴设备的功能加持下,根据当代研究者勒普顿对来自外部自我追踪的区分,跑步健身实际包含着其中的三种形式:被推动的自我追踪;被强制的自我追踪;被利用的自我追踪[32]。进而,长跑健身也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锻炼,诱导性、被动性、商业化等特征也深深嵌入其中。
1.被推动的自我追踪
在被推动的自我追踪中,那些鼓励他人参与这些实践的个体往往会通过查看或使用他人的数据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兴趣不只是由技术驱动,还会受到同一群体内的使用者的督促。具体到跑步健身中,跑者为了获得一种集体归属感,或者是为了一种更好的人际互动需求,往往会加入固定的跑团。很多跑者都会指出,跑团所起到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就在于跑友之间的互相督促。这实际上是跑者主动引入了一种来自他者的凝视。跑者经常谈及的最有效监督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在跑群里互相“打卡”晒跑量。
跑团就是有激励作用,你打卡我也打卡,大家都在积极督促自己跑步。一个跑量,一个跑的速度,慢慢会提升自己。比如我今天打卡跑个10公里,明天他打卡跑个10公里,大家都在互相激励嘛。一个人跑,跑跑就不想跑了,跑时间长了就不想跑了。人多的话,大家一起跑,跑的时间可以更长。(M02)
2.被强制的自我追踪
可穿戴设备的自我追踪功能,成为众多社会主体针对特定群体进行监督考核的手段。作为可穿戴设备的用户,往往会在两个方面体验到这种监控: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劳动者。作为消费者,个体试图监视和控制自己的身体;作为工作场所中的劳动者,管理者会将监控方法纳入对劳动者的管理中,如平时常见的公司或企业打卡考勤等行为。
优质杂排水是城市建筑中水回用当中主要考虑的杂排水资源,因此本文在进行建筑中水回用系统设定时对优质杂排水的会用流程进行分析。常见的回用有生物氧化和混凝沉淀两种方式。其中生物氧化主要借助格栅和调节池等设施,对原水进行生物接触样化处理,并通过沉淀、过滤和消毒等步骤,使其转化成为可被再度利用的中水资源;混凝沉淀处理同样需要在调节池当中进行,其中间需要借助活性炭进行杂质吸附,从而实现中水的获取。
同样,当代机构和组织的管理者也会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规章,强制要求个体进行自我追踪。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就严格执行着有关积分落户的政策。很多学校为了监督和确保学生的体育锻炼的量达标,往往也会强制要求学生佩戴装有计步芯片的设备或者心率监护仪,用所测得的数据进行个人或班级间的比较。在城市马拉松运动中,有一些国际热门赛事,比如美国的波士顿马拉松,会要求跑者具备一定的赛事经历和成绩标准。由此产生的影响,则可能会出现如中国田径协会近期处理的马拉松比赛积分造假等此类不良事件[33]。
3.被利用的自我追踪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晚期现代自我的边界已经逐渐脱离了集体性的社会仪式的纽带,转而围绕着个体化的消费行为,侧重于“身体表面及其感官感觉”[25]。跑者根据可穿戴设备所提供的指示,就在运动环境中实现了不间断地感知自身状态和身体行为的目标。
我用的是咕咚软件。它上面有一些关于跑步的知识。它里面还有运动周报、月报、年报。我从2015年开始用。……我是两个软件进行比较,我还用悦动,是因为软件有时的记录不一致,我想比较一下哪个更准确些。(M03)
如同“摄影就是权力,拍照就是把拍摄的东西放在适当的位置。它意味着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感觉像知识世界的某种关系中。每一次使用相机都隐含着侵略性”[34]。以上三种不同形式的自我追踪都暗含着来自他者的权力。由于个体很难或无法随意删除这些自动生成的数据,这就导致个体的数字痕迹远远超出了自我可控制的范围。
不过,与福柯认为制度和个人监控是生产规训社会秩序的关键技术的观点不同,吉登斯认为监控是行动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及重新配置社会生活必需知识和资源的途径[35]。有学者就指出液态监控不同于全景敞视主义的最重要一点,在于人们似乎并不关心这种监控并且也不会有意控制行为[36]。因此,以上的监控形式也就成为跑者乐意接受的事实,跑者通过分享个人跑步数据来监控自我,不断吸引着“喜欢”自己和有相同爱好的“追随者”的加入。这种具有自恋主义特征的来自他人的凝视,会进一步强化跑者的自我监控实践。这也就成为鲍德里亚所言的个体在消费社会中所选择的一种自愿奴役的新形式。
四、科技的赋魅:数字劳动中的自我再生产
贝克和鲍曼都曾分别用自反性(reflexivity)和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来描述个体积极寻求信息以及对生活做出选择的现象。晚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聚焦自我、关注身体的个人主义,革新的观念和实践已经成为私人生活和组织的中心[37]。对身体的管理是为了个人成长、事业成功、健康福祉而进行的一种变革。自我追踪就可以视为一种实现自我革新的方法。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的数据追踪集中于自我,就可以理解为通过科技手段对自我的一种赋魅。个体根据自我的数据做出关于未来行为的选择,既符合自我工作和自我完善的概念,也是自我重塑的一部分。
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和身体正逐渐作为一种信息系统,身体成为一种可识别、可存储和可处理数据的存储库[38]。这些成为身份概念核心的数据需要通过监视、测量和管理加以约束,通过记录并生成某种视觉形式,才能够被个体解释和理解。数据成为一种资本,自我表现出了商品化,数据所代表的虚拟自我被抽象地分割并进行买卖[39]。因此,大众通过使用可穿戴设备间接生成的数据以满足个人娱乐、健康、消费等各种所需的实践行为,已经构成了学者所谓的“数字劳动”。
意大利学者泰拉诺瓦把数字劳动放在了免费劳动这一概念中探讨,指出在互联网经济中因个体消费知识文化附带而来的生产性活动,此种活动被个体愉快接受的同时又被无偿地剥削[40]。这一过程反映了社会机构和商业组织的规范和要求。这也使得个体对自我的量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他人量化”。可穿戴设备背后的商家为了维持个体生产数据的能力和积极性,以所谓更利于个体健康和关心个体的自我宣传语来留住用户,甚至会在程序中设置主动提醒,让个体把这种数据生产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商家在体育锻炼中所标榜的对自己负责、努力奋斗等价值观,就为这种无偿劳动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合法性[41]。就跑步健身运动而言,跑者在线下通过携带可穿戴设备间接完成了数字生产这样一种劳动。由此,可视化的数据成为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或“可信”的象征符号,量化自我成为“一种对知识的幻想或者说完全的知识”的代表。跑者通过这些数据和图像来不断激励自我的改变,可穿戴设备已经成了可以信任的“人格化自我”,成为可以制造有关自我的“忠诚复制品”的工具。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一直以来都是管理部门关注的重点。由于房屋建筑工程实际施工期间极易受到环境因素及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风险事故发生,因此就需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施工流程的安全性进行全面监管,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出安全管理及任务,切实提升施工期间的安全指数。
由于跑者对运动的投入程度不同,其制造数据信息的能力就会因人而异。一些具有更多数据生产能力的核心跑者要维持相应的社会认同,就会在跑步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满足群体间的互动。同时,背后的商家或者媒体也会助推这种典型跑者的自我表现。
对一个马拉松爱好者的过分宣传,一次一次上电视,一次一次上报纸,你就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境界中,然后他就下不来了。……他本来的目标是100个马拉松,被架得太高了,现在说要跑300个马拉松。(F03)
鲍德里亚认为现实正在逐渐被假想的符号和模型所取代。有研究指出,在当今的算法文化中,过滤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隐喻;它可以是技术的、文化的或认知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它暗含着技术可以删除特定内容以及改变文本、图像和数据的呈现方式[42]。同样,在自我追踪程序和社交媒体广泛应用的背景下,身体、数据和精神之间的区别被重新调整,尤其当身体被还原成数据,就会容易导致个体对身体和健康概念的过度简化,由此很可能会建构出一个不真实的自我表达。因此,个体对自我的重塑标准就应该从“什么是正常”转变为“对我来说什么是正常”。
五、结 语
晚期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知识的极大丰富性,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全面了解和掌控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作为一种专家系统同时又是其他专家系统之产物的可穿戴设备,拥有着可以帮助个体有效掌控自我生活的作用。凭借可穿戴设备,个体在科技层面上对现有自我进行符合社会期待的量化,指导着身体在生活实践中的重新塑造。进而,这种理性控制和消费实践就有助于量化自我这一新型自我的发展。量化自我成为可以将个体定义为一个负责任公民的有效话语策略。自我追踪实践所产生的数据也就成为评估和代表个体自我价值的最佳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数据作为高级知识形式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总之,在当前强调自我管理和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缺乏自律往往意味着自身能力和人际吸引力等方面的不足。通过可穿戴设备来监控身体和优化生活可以培养自控、理性、坚韧等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所推崇的品质,这也就使得自我量化和自我追踪成为个体自愿进行并且感到愉悦的一种生活实践。因此,蕴含着大量社会功能及文化意义的可穿戴设备,就拥有了塑造个体生活和认同的重要作用。当然,关于可穿戴技术在复杂的理性化自我管理和科学意识形态形成中的更多作用,以及如何促进了个体主义和自我创造文化等问题,还需要未来更多的探讨。
政府、家族、民间组织和个人都是孤儿救助服务的提供者,在世界社会福利服务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下,政府和传统家族孤儿救助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孤儿的需求,民间组织和个人介入其中是一个必然的社会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公民、企业、团体等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国家通过在政策体制环境上对孤儿救助体系进行整合,形成个人、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合力,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儿童福利事业的多元参与的理念。
参考文献:
[1]Lupton D.Self-tracking cultures:towards a sociology of personal informatics[C]//Australia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Conference on Designing Futures:the Future of Design,2014.
[2]张文,李子运.量化自我技术支持的智慧学习设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6(6):107-112.
[3]李东进,张宇东.量化自我的效应及其对消费者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J].管理科学,2018(3):112-124.
[4]王巢琛,徐跃权.量化自我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18(17):44-52.
[5]吴丹,马乐.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医疗健康数据生命周期管理与服务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8(4):17-29.
[6]尼尔森.马拉松热潮带来巨大商机[EB/OL].https://www.nielsen.com/cn/zh/insights/report/2016/businessopportunity-looms-as-marathon-mania-sweeps-across-china,2016-01-29/2019-06-12.
[7]陆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8]Van Dijck José.Datafication,Dataism and Dataveillance:Big Data betwee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Ideology[J].Surveillance & Society,2014,12(2):197-208.
[9]Ruckenstein Minna.Visualized and Interacted Life:Personal Analytics and Engagements with Data Doubles[J].Societies,2014,4(1):68-84.
[10]ElmerGreg.A Diagram of Panoptic Surveillance[J].New Media and Society,2003,5(2):231-247.
[11]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新浪跑步.中国田径协会重磅发布2018马拉松数量达1581场[EB/OL].http://sports.sina.com.cn/run/2019-03-11/doc-ihrfqzkc2909416.shtml,2019-03-11.
[1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Gina Neff,Dawn Nafus.Self-tracking[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6:74.
[15]爱燃烧.2015中国跑者调查报告[EB/OL].http://iranshao.com/pages/12,2016-04-27.
[16]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7]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8]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19]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M].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20]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2]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4]Gina Neff,Dawn Nafus.Self-tracking[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6:15.
[25]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6]Lupton Deborah.The digitally engaged patient:Self-monitoring and self-care in the digital health era[J].Social Theory & Health,2013,11(3):256-270.
[27]Askild Matre Aasarød.A Dislocated Gut Feeling:An Analysis of Cyborg Relations in Diabetes Self-Care[D].Aarhus University,2012.
[28]Adams Matthew,Jayne Raisborough.Making a Difference:Ethical Consumption and the Everyday[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0,61(2):256-274.
[29]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M].王崑,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0]Dean Jodi.Blog Theory: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0:54.
[31]Zygmunt Bauman,David Lyon.Liquid Surveillance:A Conversation[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9.
[32]Deborah Lupton.The diverse domains of quantified selves:self-tracking modes and dataveillance[J].Economy and Society,2016,45(1):101-122.
[33]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关于对2019波士顿马拉松成绩异常的中国籍选手吴兆峰、赵宝莹和张建华的处罚通知[EB/OL].http://www.athletics.org.cn/marathon/tzgg/2019/0418/234506.html,2019-04-18/2019-06-12.
[34]Sontag Susan.On Photography[M].New York:Picador,1973:3-8.
[35]Banner Olivia.Patient 2.0:Biomediated Illness and Digital Intimacies[C].Identity Technologi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2.
[36]Siva Vaidhyanathan.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and Why We Should Worry)[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37]Anthony Elliott.Reinvention[M].London:Routledge,2013.
[38]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39]Gina Neff,Dawn Nafus.Self-tracking[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6.
[40]燕连福,谢芳芳.福克斯数字劳动概念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2):113-120.
[41]Till C.Exercise as Labour:Quantified Self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ercise into Labour[J].Societies,2014,4(3):446-462.
[42]Alice Marwick.Status Update:Celebrity,Publicity,and Branding in the Social Media Ag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社交娱乐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与引导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SJB417)和常州工学院校级重点项目“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社会成因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YN1654)的阶段性成果]
王健:常州工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永涛
标签:可穿戴设备论文; 量化自我论文; 赋权论文; 数字劳动论文; 液态监控论文; 常州工学院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