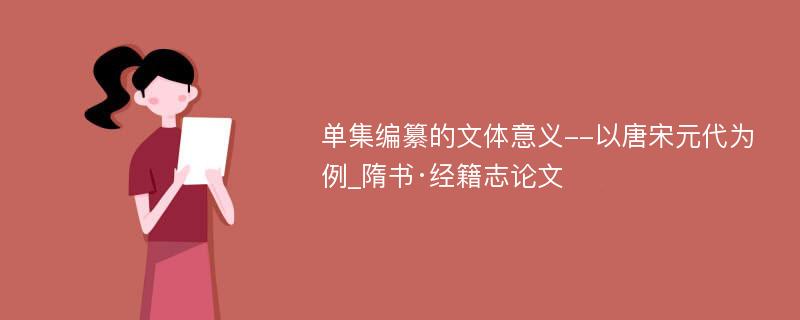
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以唐宋元时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集论文,唐宋论文,为例论文,文体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5-0008-08
历代总集编纂和文体学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文体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这是因为二者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隋书·经籍志》首次在四部分类中确立了集部,并作了别集、总集的区分,其论总集缘起及作用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②《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则进一步归纳了总集的两大功能:“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③无论是“网罗放佚”,还是“删汰繁芜”,都是为了“属辞之士”的“取则”,也都具有文体学的意义。
总集是“众家之集”的汇聚,其编纂的核心因素则是文体。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总集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就是按照这一顺序先后排列的。以《文章流别集》和《文选》为代表的多体总集,(有的学者称之为《文选》类总集)其文体学意义已得到较多的关注和挖掘,而大量单体总集却尚未引起充分注意。本文试以唐宋元时期为例,对这类单体总集的文体学意义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探索其在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唐宋元单体总集编纂概貌
单体总集编纂缘起甚早,汉武帝命淮南王为《楚辞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④,已肇其始。只是《隋书·经籍志》将《楚辞》类与别集、总集并列,掩盖了其单体总集的性质。以下先对唐前单体总集编纂的情况作一简单回顾。
唐前四部文献的流传情况主要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之中。考《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共著录总集107部,加上“梁有”(即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而编纂《隋志》时已亡佚)的则共计249部。从《文章流别集》至《文章始》共24部,加上“梁有”已亡的则为33部,均为多体总集(包括《文心雕龙》、《文章始》等文论)。而《赋集》以下直至《法集》200余部均为单体总集,其汇集的文体依次为赋、封禅、颂、诗、乐府、箴铭、诫训、赞、七、弔文、碑、论、连珠、杂文、诏、表奏、露布、启、书、策、俳谐文等20余种,其中以赋、诗、乐府、诏、碑、表奏等体数量最多。这些单体总集除了《玉台新咏》等极少数流传下来外,大多散佚不传,难见其实况。但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看,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单体总集的数量远大于多体总集,可见单体总集的编纂是基础;二是从总集名判断,“网罗放佚”的单体总集多于“删汰繁芜”的,可见其功能尚以汇聚作品为主。此外,其著录编排有序,反映了唐初编修《隋书》时学者对总集体例的观点。
承继六朝总集编纂的传统,唐代的总集编纂继续呈现旺盛的态势,且有一些新的拓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人所编总集约100种,但实际数量远不止此。卢燕新博士在吴企明《唐音质疑录》、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详考文献,考定唐人编选的诗总集174种,文总集58种,二者总计230余种,另有待考的约80种⑤。这些唐人编纂的总集中,多体总集仍占少数,主要为《文选》的音、注和拟、续以及《芳林要览》、《丽正文苑》、《文馆词林》等新编总集;而单体总集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单体总集中,又以诗总集数量居绝对优势,其余文体仅涉及诏、策、表、奏等公文文体,这与《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六朝单体总集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唐诗创作的高度繁荣,从初唐至晚唐,各类唐诗选编本层出不穷,留存至今的尚有佚名《搜玉小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令狐楚《御览诗》、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觳《才调集》等10余种⑥。这些选本多为选编者根据自己的诗歌主张和爱好编成,大多关注诗坛风会和审美趣味,从文体演变角度切入的不多,仅有倪宥的《文章龟鉴》等个别总集着眼于文体⑦。另一类十分繁盛的单体总集为诗人唱和集,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元白继和集》、《刘白唱和集》、《名公唱和集》等就有20种之多,它们多为汇聚作品,而不涉文体辨析。此外通代的诗歌总集如惠净《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郭瑜《古今诗类聚》等,数量也不多。
两宋的诗文创作继续繁盛发展,在文人别集数量大增的基础上,宋人总集编纂较之唐代有更多新的开拓。《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宋人所编总集约250种,其中大部分已佚。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著录存世的宋代总集85种,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又著录180种,二者相加之数与《宋志》略同。在85种存世总集中,多体总集近30种,单体总集50余种。单体总集中,诗总集仍占半数以上,另有词总集11种、古文总集7种,其余涉及的文体有诏令、奏议、碑志、论策、判文、回文、四六等,其文体较之唐代有较大扩展⑧。
宋代诗总集的编纂有许多新的发展:在唐代诗人唱和集的基础上,发展出流派诗总集,如《九僧诗集》、《西昆酬唱集》、《江西宗派诗集》、《四灵诗》、《江湖集》等;编纂出许多专体诗总集,如《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乐府诗集》等绝句、律诗、乐府诗总集,《昆山杂咏》、《京口诗集》等地域诗总集,《增广圣宋高僧诗选》、《洞霄诗集》等僧道诗总集,以及题画诗集(《声画集》)、动植物诗集(《重广草木鱼虫杂咏诗集》)、诗集附诗话(《诗林广记》)等等。这些总集兼及诗体和题材,门类繁多,富于开创性。宋代词体创作呈现一代之盛,《草堂诗余》、《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词总集的编纂层出不穷,更出现了《百家词》、《典雅词》等大型词集丛刊。单体文总集中,除了传统的诏令、奏议集外,值得注意的有三类:一是一系列题为“古文”的总集的产生,如《古文关键》、《迂斋古文标注》、《崇古文诀》、《古文集成》等,标志着“古文”作为一类文体已被文坛接受;二是四六文总集如《三家四六》、《四家四六》等不断被汇聚,反映了四六与古文逐渐分疆的现实;三是科举文体总集的大量刊印,如《论学绳尺》、《十先生奥论注》、《擢犀策》、《擢象策》、《指南赋》、《指南论》、《宏词总类》等,说明文章总集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宋代单体总集编纂的不断拓展,体现出各别文体研究的不断深入。
元代承袭两宋,总集编纂又有新发展。明修《元史》未立《艺文志》,清人钱大昕撰有《元史·艺文志》,补录元一代文献,兼及辽、金之作。其集部总集类共著录80余种,而骚赋、制诰、科举、文史、评注、词曲均另外立类,其中亦有大量实为总集者,如《古赋辨体》、《论范》、《策学统宗》、《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花草类编》等。故元代虽立国时间较短,但总集数量依然可观。
元人总集之中,除了元好问《中州集》、苏天爵《国朝文类》、郝经《原古录》等多体总集之外,单体总集仍占多数。除了大量的地域集、流派集和唱和集,值得注意的是有较多的唐代诗集,如《唐诗鼓吹》、《唐诗选》、《唐音》等,尤其是《唐宋近体诗选》、《三体唐诗》、《唐律体格》等,明显着眼于诗体,说明辨体已成为元代的潮流,而《古赋辨体》更成为赋体辨析的力作。此外《论范》、《策学统宗》、《翰墨大全》、《万宝书山》等科举类、应用类单体总集也值得关注。
从以上唐宋元三代单体总集编纂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其发展趋势有二: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这两方面的趋势,都指向“属辞之士”“取则”的需求,至于其在文体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还需要作进一步具体、深入的探析。如果说,多体总集,尤其是《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现了编者对各种文体类别、性质及相互关系等的全面探索,那么,单体总集的编纂更多地表现出编者对各别文体的细类、特点乃至具体作法的深入探究。对全部文体的宏观把握固然是文体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对个别文体的深入观察同样是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
单体总集选录作品的体制,可以细分为系人(作者)、系时(时代)、分类(题材)、分体(体裁)等多种形式。如《唐人选唐诗》中的总集,大都以诗人为纲,每人选录若干首诗作;《古赋辨体》则按照赋体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选录代表作品;《瀛奎律髓》将唐宋律诗依不同题材分为49类,每类下选录若干作品;《松陵集》将诗歌区分为若干细类,再分别选录诗作。这些均是不同体制的单体总集之例。从文体学的角度着眼,这些单体总集对文体研究的深入程度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细化文体分类
以诗体分类为例,自六朝后期“新体诗”逐渐形成,到初唐时期近体诗的成熟,诗歌体类渐趋完备。但是,诗歌体类的确立和定名,则要到中晚唐时期。唐人选编的唐诗集通常以人系诗,并不分类或分体。专门研究唐代诗集的万曼先生在《唐集叙录》中说:“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目。”⑨韩愈长庆四年(824)冬去世后,其门人李汉编定韩集,作《昌黎先生集序》称:“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⑩李群玉大中八年(854)上呈《进诗表》称:“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11)这是唐代别集中较早区分诗歌体类的例子。可以说,李汉、李群玉已将诗坛上早已认同的诗体分类贯彻到别集的编纂中。而稍后编成于晚唐咸通年间的单体总集《松陵集》则将这一诗体分类进一步固定下来。《松陵集》是晚唐诗人皮日休咸通十年(869)前后任苏州刺史从事时与陆龟蒙的唱和诗集,“凡一年为往体各九十三首,今体各一百九十三首,杂体各三十八首,联句问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12)极为可贵的是,皮氏在《松陵集序》中对春秋以降诗体的沿革做了详细回顾:“春秋之后,颂声亡寝,降及汉氏,诗道若作……盖古诗率以四言为本,而汉氏方以五言、七言为之也……逮及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始切于俪偶,拘于声势……由汉及唐,诗之道尽矣。”(13)《松陵集》的编排是卷1至卷4为“往体诗”(即古体诗),卷5为今体五言诗,卷6至卷8为今体七言诗,卷9为今体五七言诗,卷10为杂体诗。这样的编排顺序体现了诗体的发展历程,也成为后来诗集分体的一般规则。皮氏在卷10“杂体诗”前撰有《杂体诗序》一篇,更对各类杂体诗的缘起和发展作了全面考察,文中提及的杂体诗有联句、离合、反复、回文、叠韵、双声、短韵、强韵、四声诗、三字离合、全篇双声叠韵、县名、药名、建除、卦名、百姓、鸟名、龟兆、藁砧、五杂组、两头纤纤等20余种,并称:“由古至律,由律至杂,诗尽乎此也。”(14)这是两篇诗体学的重要文献,体现了皮日休对诗体分类的自觉探索,并带有总结性,为到唐代已成熟定型的诗歌体类区分奠定了基础,在文体学上值得充分重视。单体总集编纂对文体分类细化的作用在这里体现得十分典型。又如宋末元初的方回所编《瀛奎律髓》是一部专选唐宋律诗的总集。它沿袭《文选》在诗赋各体下再按题材分类的传统,将唐宋律诗依题材(少量依作法)分为:登览、朝省、怀古、风土、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共49类,每类前冠以小序评述,其类目较之《文选》大大细化,对分类揣摩作品的效果十分明显。至于《文章正宗》将“明义理切世用为主”的文章,以“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的原则区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4类,是一反传统的功能分类法,而主要着眼于文章的表现手法,更是古代文体分类史上的一大创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梳理文体发展
每种文体都有萌芽、生长、定型、发展的历程,对成熟文体发展过程的梳理,是文体研究深入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心雕龙》文体论“原始以表末”讨论的就是这一过程。用文集选录作品可以使这样的梳理更为直观,能更好地指导写作。但是,别集和多体总集都不合适承担这一任务,只有单体总集最适合进行文体发展的梳理工作。前述《松陵集》就是将诗体沿革的探讨和作品的编选结合在一起。更为典型的例子则是元代祝尧所编纂的《古赋辩体》。祝氏述其编纂宗旨是“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从而达到“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的目的。全书以《诗》为赋体源头,强调“诗人之赋”的特征是“吟咏性情”;《诗》以下,赋体的发展历经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几个阶段,其中“骚人之赋”尚能“发乎情”,“形于辞”,“合于理”,其后的“词人之赋”则愈趋追逐辞与理,完全丢弃了诗人之义;失之情而尚辞不尚意的演变为俳体赋,失之辞而尚理不尚辞的演变为文体(即散体)赋,而俳体中又衍生出律体赋,“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祝氏大力倡导“祖骚而宗汉”的古体赋,强调“欲求赋体于古者必先求之于情,则不刊之言自然于胸中流出,辞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于俳;无邪之思自然于笔下发之,理不求当而自当,又何假于文”(15)。全书以“情、辞、理”串起赋体的演变线索,并以之为标准,将赋体体式区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诸类,并对各阶段体现其体式变迁的代表作进行评点,体现了编纂者鲜明的宗旨。《古赋辩体》通过梳理文体沿革总结其演变规律,借由作品编选达到辨析文体的目的,《四库提要》评价其“采摭颇为赅备”,“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16),从而成为赋体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也为用编纂总集深入研讨文体树立了典范,对后代文体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探索文体作法
研讨文体的根本目的是指导文章写作,单体总集能在选录某种文体范文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这种文体的作法,从而起到多体总集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宋代魏天应编、林子长注的《论学绳尺》。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中,试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还延伸到部分铨选考试,“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17)。因此,《十先生奥伦》、《指南论》、《宋贤良分门论》等试论选本层出不穷,而《论学绳尺》则在编选试论范文时,从写作角度区分为78格,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等,并通过题注、夹住、尾评等形式加以详尽的评说,用以指导模仿写作,所谓“专辑一编,以备揣摩之具”(18)。这种形式的实质,是将传统的“诗格”、“文格”类著述体式,融于总集编纂中,将研读具体作品和探索文体作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将总集指导文章写作的文体学意义发挥到极致;又因为它着眼于单种文体,更能做到集中和深入,避免泛泛而论,故效果更为明显。类似的例子还有宋代周弼的《三体唐诗》,所谓“三体”指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周氏将律诗句法区分为虚、实两种,抒情为虚,写景为实,认为一首诗内须虚实搭配。据此,他将七绝和五律各分为7格,七律分为6格,分格系诗,汇成一部诗选。这样分体、分格选诗的意图也是深入探究诗歌作法,用以指导写作。《四库提要》认为,所列诸格虽“不足尽诗之变,而其时诗家授受,有此规程,存之亦足备一说”(19)。
(四)集成成熟文体
古代文体的演进发展,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有的文体形成后就一直“热门”,创作不断,历久不衰,如古体诗、近体诗、词以及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一些实用文体;但有些成熟文体则因为环境变迁、本身局限等各种原因,在经历了创作高潮期后就逐步走向衰歇。而这类文体的集成总结工作,往往由单体总集来承担。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乐府诗由于与音乐和乐府机构的特殊关系,在古代诗歌中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类,《文心雕龙》中有《乐府》篇进行专题论述。其后南北朝乐府和唐代新乐府又有新的发展,只是自晚唐词体成熟后,乐府诗的创作渐趋式微,后人偶有仿作,已难成气候。《乐府诗集》对历代乐府诗创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按照其音乐特性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12类,分题集成其作品,并用小序和题解的形式探讨其源流演变,评论其代表作品,使之成为乐府诗一部集大成的总集。《四库提要》称:“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诚乐府中第一善本。”(20)此外如宋代桑世昌编《回文类聚》,汇聚历代回文作品,序文考述其源流、体制,也成为回文这一特色文体的集成之作。
单体总集编纂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
古代文体学源远流长,唐前文体论著的体式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经史注疏、论文著述中的片言只语,这是文体论的早期形态;二是诗文、著述序等专文,如傅玄《七谟序》和《连珠序》、萧统《文选序》等;三是总集编纂附专论,如《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论》、《翰林集》及《翰林论》等(根据《隋志》的著录,总集与专论应是分别单行的);四是文体学专著,如蔡邕《独断》、任昉《文章始》、刘勰《文心雕龙》等,其中《文心雕龙》尤是体大思精的集大成著作。唐宋元三代,随着文体学的繁荣,文体论著的体式也有新的拓展,如诗词文话以及诗格、赋格等,但开拓创新最为明显的则体现在各类总集的编纂中。
由于多体总集多承袭《文选》传统,面广体多,往往只是分体系文,排比作品,其文体学价值主要集中在文体分类领域;而单体总集则体类单一,便于细化深入,因而其体式的变化层出不穷,其价值也向文体学的多个领域拓展。单体总集开拓的文体研究新体式有下述几种。
(一)首冠总论
在总集卷首冠以总论,对该类文体的渊源流变、代表作品、写作要领等进行论述,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引导读者结合选录的作品,反复咀嚼揣摩,把握规律。这一总论可以由编者自撰,也可辑录前贤的相关论述而成。编者自撰总论的如《古文关键》卷首,有吕祖谦撰《看古文要法》一篇,分为“总论看文字法”、“论作文法”、“论文字病”三部分,对如何阅读所选各家文章的原则和要点以及应领会的具体作文手法、文字病犯作了要言不烦的提示。又如《文章正宗》卷首亦有编者真德秀自撰《文章正宗纲目》一篇,揭橥全书“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的选文主旨,并分别对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文体进行了总括性的概述。《论学绳尺》卷首的总论《论诀》一卷,则是属于辑录型的,它包括“诸先辈论行文法”(辑录吕祖谦、戴溪、陈亮等8人相关论述)以及“止斋陈傅良云”、“福堂李先生《论家指要》”、“欧阳起鸣《论评》”、“林图南论行文法”五部分,共计12人对于试论结构体制方面的论述,核心是确立试论的“定体”、“定格”作为写作的绳尺,从而为以下的数十格范文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二)分列序题
序为小序,题为题解,分别列于总集各类(卷)、各组(题)作品之前,对该类、该组作品的流变、特征等进行概括,更具体地指导阅读,可以看作是总论以下的分论。总集的这种体式在唐代尚不多见,宋代开始较多出现。如谢枋得《文章轨范》7卷,各卷前均有简要小序,提示本卷选文的特色和需要关注之点。郭茂倩《乐府诗集》于12类乐府诗之前,各撰小序详述其源流沿革,而在不少乐府诗题之前,再用题解考述诗题的来龙去脉及代表作品。方回《瀛奎律髓》则针对49类律诗题材,各撰成小序发掘其内涵,画龙点睛,要言不烦。最为典型的则是祝尧《古赋辨体》,该书“假文以辨体”,并将小序、解题与选文结合起来,以“辨体”为核心,小序着重梳理各类赋体的沿革流变和相互关系,解题则紧密结合作品展开细致的辨析,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一个体系严整、富于深度的辨体批评体系。《古赋辨体》一书对明代以后总集的辨体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分列序题的体式,其实是承袭了《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论》的传统,并将选文和附论合为一体,依体立论,就文辨体,从而成为文体学著述的重要体式(21)。
(三)添加批点
批注评点是在作品篇首或篇末针对全篇的批评文字以及篇中针对段落、文句、字词的注释、点评文字。这类体式始于吕祖谦编《古文关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古文关键》二卷,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22)此后问世的《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古文选本,大多承袭这一体式,普遍添加批注标抹,进而扩展至其他诗文选本、小说、戏曲文本,成为富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23)。这些批点往往关注作文技法,亦有部分着眼于文体,如《古文关键》评韩愈《谏臣论》“意胜反题格。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评柳宗元《捕蛇者说》“感慨讥讽体”(24);《崇古文诀》评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辨难攻击之体峻洁有力”,评王禹偁《待漏院记》“句句见待漏意,是时五代习气未除,未免稍俳,然词严气正,可以想见其人,亦自得体……似箴体”(25)。这类批点或揭示体性,或辨析语体,或比较体裁,广泛涉及文体研究诸领域,较之总论、序题,是更为具体、细致的文体辨析和批评。
以上几类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其共同特点是密切结合作品文本研讨文体,无论是总论、序题还是批点,都是将总集所选文章从文体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从而促使文体研究走向具体化、精细化,避免了泛泛而谈。宋代以降,总集的编纂形式大为丰富,创新鲜明,其文体学价值得到了深入一层的开掘。
单体总集编纂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
文体的发展历程,一般都须经历萌芽初创、成长成熟、定型确立等阶段,并进入创作繁盛期,产生一批代表作品。单体总集的编纂,或网罗放佚,汇聚作品;或删汰繁芜,选留精品,从而成为新兴文体确立并取得文坛最终认同的重要标志。唐前大多数成熟文体,都在《隋志》中有多种单体总集的著录,即是一个明证。唐宋时期词体和古文总集的兴起,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文坛的规律。
成熟于晚唐的词体,其最早的集结形式,不是别集,而是总集。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说:“唐宋词籍中,以总集问世最早,总数不下数十种。重要的总集,为词开宗传派,影响甚巨。《花间集》宋时被视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它与《草堂诗余》在明时同是学词的入门之书。即使是名家词,亦往往因载入总集而流传更广。中小词家则更依赖总集而其名其词得以传世。总集的这种作用,不是一般别集所能替代的。”(26)可以说,词体的确立和被认同,是以最早的一批词体总集如《云谣集》、《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的问世为标志的,这批总集都是作为唱本出现的,其性质都是当时的歌曲集,而编纂目的在于满足应歌的需要,因为词体本就是为适应并配合燕乐演唱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其后,才有词别集乃至词集丛刊的大量涌现,而南宋时期《复雅歌词》、《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大批词总集的编纂,“大多则专尚文藻,目的在于尊体与传人传词”(27)。
作为文章体类概念的“古文”,其确立和被文坛认同,也是同一大批明确题为“古文”的文章总集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8)。吴承学先生曾在《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一文第二节“从总集看宋人的古文观念”中对宋代“古文”的内涵做了精彩的阐述(29),见解独到,极具启迪性。笔者拟从“古文”作为文类的角度再作申发。
唐代韩愈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开始文体革新,创造了“古文”这一新的文章体类,并在骈文主导的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但由于对作为新体类的“古文”还缺少明确的界定,而韩门弟子或尚理,或尚奇,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终使古文创作衰落下去。北宋欧阳修再倡古文,他较好地处理了文与道的关系、散体与骈体的关系,摒弃艰涩险怪的倾向,倡导平易流畅的风格,并身体力行,奖拔后进,共同用创作实绩探索“古文”的体类规范。然而,北宋党争,尤其是后期“元祐党禁”的压制,使得欧、苏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虽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却未能取得社会权威的认同。宋代古文主要是与骈体相对立的语体概念,其作为新兴体类的外延和内涵仍未确立。
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至宋末元初,题名为“古文”(或题“文章”)的一批总集相继问世,今可确考的约有8种(略按时间顺序排列):吕祖谦《古文关键》2卷,楼昉《崇古文诀》35卷,真德秀《文章正宗》20卷、《续集》20卷,汤汉《绝妙古今》4卷、《斅斋古文标准》,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78卷,谢枋得《文章轨范》7卷,黄坚《古文真宝》20卷(30)。这些选本对古文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其选文标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古文”这一体类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一部题为“古文”的总集是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吕氏为主编《皇朝文鉴》(即《宋文鉴》)的文章大家,他为初学者选录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张耒共8家以议论类为主的文章60余篇,并首创评点标注(31),题为《古文关键》体现了他对“古文”范围、性质、特点的认识。随后,其弟子楼昉所编《崇古文诀》(亦称《迂斋古文标注》)选文达200余篇,时间前溯到先秦、两汉和六朝,但仍以唐、宋大家为主,文体包含少量辞赋和骈体,类别除议论文外,还拓展到记叙文、抒情文,显示其“古文”观念有了较大的拓展。其后,真德秀《文章正宗》首次将经、史典籍(如《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部分段落辑出成文,作为文章的源头经典,且数量大大超过唐代,(其不选宋文)另外又选入不少古体诗赋。汤汉《妙绝古今》则将选文进一步扩展到《孙子》、《列子》、《庄子》等子书的节录篇章。其他古文总集的选文标准多在这些基础上有所增损。
总括起来看,宋代多种“古文”总集体现的“古文”体类概念虽各有特点,但其外延和内涵大体包括:以时间论,古文主要包括先秦两汉和唐宋时期的文章,魏晋六朝仅有极少数篇章入选;以作品论,古文主要以汉、唐及北宋的作家作品为主,上溯先秦经、史、子典籍中部分节录成文的篇章,下及部分南宋作家作品,而尤以后来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为典范,韩、柳、欧、苏四家所占比重最重;以语体论,古文主要以单句散行的散体行文,但不排斥文中穿插俪语偶句,个别通篇骈体的篇章,甚至部分古体诗歌,也可包含在古文之中;以体裁论,古文包括了流行的大部分文体,与四六类和时文类文体也有部分的交错(如表、启、策、论等);以内容论,古文以阐明儒道为主要思想倾向,但也不绝对排斥掺杂佛、道思想的篇章;以表现手法论,古文广泛使用议论手法,但叙事、抒情也多有发展,并常有多种手法的融合;以总体风格论,古文以“雅正”风格为主导,也包容多种风格的存在,但排斥浅俗、柔靡、雕琢的倾向。
由于古代文论向来缺乏对概念的明晰界定,宋代“古文”概念经历了由语体向文类的发展过程,由上述古文总集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古文”体类渐渐为文坛所认同,并继续于元、明、清三代沿用不绝。元代吴福孙《古文韵选》,明代归有光《文章指南》,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康熙《御选古文渊鉴》、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古文观止》等一大批古文总集,虽然各家选文仍有差异,但依据的共同标准则不出宋代古文总集所涵盖的古文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体类的确立,确是宋代古文总集编纂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并深深影响着元明清三代文章体类的发展和文体学的进程。
从上述三方面看,单体总集编纂在唐宋元三代的文体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文心雕龙》之后,古代文体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体系严整、论述精详的专著,加以骈体文学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逐步被取代,唐宋元三代文体学发展中,文集编纂成为举足轻重的形式之一。其中的单体总集数量众多,体式纷繁,紧密结合作品的选录,多方面细化文体研究,多层次创新研究体式,促进了新兴体类的确立,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两代的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只是对这一领域的初步梳理和探索,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