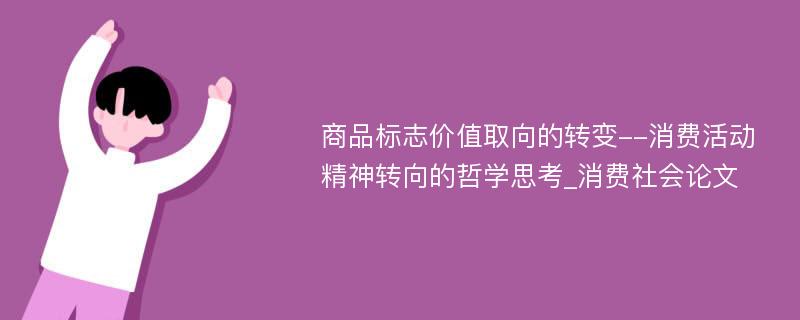
论商品记号的价值取向的转换——关于消费活动精神性转向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号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一开始就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博德里亚,第1页)欧美靠工业革命和殖民地的掠夺,最先进入富裕的消费社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变化。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被越来越猛的商品洪流所包围;对中国人而言,消费社会已经来临了。
一、消费社会的出现及其问题
消费是在人们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人类生活中,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但并不是对所有需要的满足都是消费;消费只与生产出来的或需要交换的东西——商品相联系。没有经过人们劳作或经营的东西,即使人们通过它满足了某种需要,也不是消费。譬如,农村的儿童在池塘内游泳并不是消费,但是城市的儿童到游泳池嬉戏就是消费:池塘和游泳池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是商品而后者是。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有消费活动并不一定就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消费活动对每个阶层和每个人都变得具有普遍性之后的产物。严格说来,在工业社会之前,人类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消费社会,因为以往的社会不能够生产过多的剩余生活资料。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人们的生存条件只是比动物稍好一些而已,在许多方面人的活动仍然近似于动物性的活动,人的需要也仍然近似于动物性的生存需要。因此,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社会道德是为了调节种群或部落以便一起获得和分配生存必需的猎获物。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之中,剩余的生活资料只能够满足极少数人的奢侈需要,或者只能让极少数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利用闲暇从事脑力劳动或精神生产。早在1899年,维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毫无节制的消费,尤其是高档用品的消费,通常属于有闲阶级的专利。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超出生存底线的所有消费,都专属于有闲阶级。”(转引自罗钢、王中忱,第6页)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社会道德更多的是鼓吹等级制度和禁欲主义,让大多数人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把享受和精神活动留给极少数特权阶层。
就消费的实质而言,只有摆脱了生存意义上的“消费”,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消费。因此,只有当人们不断追求超越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消费,而且大多数人都能够进行这种意义的消费时,消费社会或消费时代才真正到来。这个时代是从大机器工业可以批量生产大量产品时开始的,原来少数人的奢侈品此时变成大多数普通人都可以购买和享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时代的到来是具有反等级特权的平权主义意味的:很多过去是特权阶层才能享用的东西,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消费对象。
然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使人出现享乐主义倾向:人们的消费不再是为了健康的生存,反而健康的生存似乎是为了消费。为什么人的生理需要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是因为生活资料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而商品可以体现为货币,货币又发现了其代表——纸币。纸币作为价值符号冲破了人们占有财富的有限边界,开辟了人的欲望的无限空间。实物财富必须有堆放的地方,而且易于损耗,货币符号却可以在观念上占有一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之前,都以个人对物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物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它本身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它只代表一般,纯粹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1页)人们在追逐金钱中丧失了自我存在的界限感。
对于消费的无限膨胀,当代西方学者另有解释。譬如博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消费现象,认为消费必然导致对记号进行积极的操纵。在“商品-记号”系统中,能指的自主性意味着通过诸如广告和电视这样的媒体对记号进行操纵,使记号游离其原有商品物体本身,反而转向了文化的意义。文化可以突破人的生理需要的界限:由于不是基于基本的生理需要,而是幻觉似地占有,人们就可以在符号的文化享乐中追求似乎无穷无尽的消费,这就必然导致人们所说的过度消费。在解读博德里亚时,美国学者凯尔纳指出:“在商品的购买和展示中,符号价值被认为和交换价值起着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且符号价值现象已经成为消费社会中商品和消费的最重要的成分。”(凯尔纳,第5页)凯尔纳没有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实际上,马克思说的原因是消费欲膨胀的实质性机制,而消费的符号化是消费欲膨胀的特征性表现,我们没有必要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但是必须清楚:金钱的符号化是商品消费符号化的原因和基础。过度消费来源于过度的金钱追逐,反过来又刺激着后者。
过度消费的习惯把人们从小就宠坏了,这就必然使社会上出现铺张浪费和骄奢淫逸的现象。在消费社会,似乎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消费。正如利波维茨基等人指出的,“时尚和消费理念已经占据越来越大的公共和个人生活空间”。(利波维茨基、夏尔,第21页)在这里,价值观的飘浮替代了系统话语的强硬,无规范约束的“意义”替代了具有先验绝对性“框架”的束缚。人类“进入了意义的非神圣化和非实体化的无尽程序,这个程序确定了完全时尚的统治”(同上,第20页)。追逐时尚成为消费主义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超级消费社会中,不是没有了价值,而是价值的颠覆和流变造成人们的焦虑。在时尚变幻的情景中生活和思考,使一切固定的东西变成在变化中不断调整的东西。我们越来越追求变幻不定的时尚,而且美其名曰不断创新。似乎消费越来越成为提升自己或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这是个崇尚轻浮和空洞的时代,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喜欢一鸣惊人、见异思迁和新奇的消费活动。这就造成了过度消费和无实质性积极意义的消费。
但是在过度消费中人们并不能得到满足。在暴殄天物和穷奢极欲的消费活动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现象,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继续为消费主义唱赞歌,提出“我消费,故我在”。对此,人们有理由断言:“超级消费和超级现代性时代宣告了意义的宏大传统结构的衰亡和通过时尚与消费理念获取意义的途径。”(同上,第111页)有的人则发起反消费主义运动,譬如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政治行为艺术家利夫伦德·比利提出“什么都不买,感觉真是好!”,呼吁把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定为无消费日。我认为,这两种反应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反对消费主义,但是不能反对消费活动本身;我们可以批评消费主义,但不能拒绝消费本身。合理消费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问题的解决:消费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关键
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之后,消费是不能压抑的,我们也不能再主张禁欲主义,更不能限制消费主体的人群范围。主张禁欲主义是反文明的,而限制某些物品的消费主体的范围是反平等的。消费文明不是禁欲,而是实现人民普遍的合理消费。因此,消费活动的性质和追求指向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科学发展观及其转变发展思路的角度看,我认为,消费不能压抑,但可以有某种指向性的转变。超越消费主义的唯一出路是使消费活动的指向转变,即促使人们的物质性消费转向精神性消费,把物质的占有和花费转向精神的追求和享受。我认为,消费活动的这种转向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既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人性价值的。
首先,消费时代出现的可能性就包含着消费活动精神性转向的必然性。现代工业生产为普通人的普遍消费提供了前提:它不仅使当前的消费普遍化成为可能,而且还不断为人们生产出新的需要和消费对象。大量商品的出现就为人们享受超出满足自然生物需求的东西创造了条件,按照博德里亚的话说,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多的是对记号的操纵或对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的追求。既然人们的生理需要得到了满足,进一步的消费就必然带有文化的特征。一方面,是非物质形态的商品,如好莱坞大片、流行歌曲的CD、图书、动漫等等,在消费社会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传统物质商品也越来越渗透着文化或非物质因素,如建筑、家具中审美的因素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显然,符号象征的文化正是消费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果以往的社会是崇尚实物的社会,那么消费社会就是越来越崇尚记号、影像与信息的社会。
消费活动从本质上越来越从物质的东西转向文化的东西。博德里亚所说的“商品-记号”游离的可能性,既可以唤起人们无穷的消费欲望(即使在这里,人们与其说是消费物质,不如说是消费物质商品所体现的文化符号),也可以促使人们转向某种精神性的追求。实际上,当人们必要的生理需要满足之后,任何新的需要都包含着精神性或符号式的形式。古代的炫耀式消费和今天有地位的人住“总统套房”,更多的不是生理需求的满足,而是身份的宣示和资格的认同。身份的炫耀已经是精神追求了,尽管不是完全合理的或积极的精神追求。可见,消费主义的内在悖论就在于:愈是追求更多的物质消费,也就愈是远离人的物质生理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时代的到来就蕴涵着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的可能。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把精神性转向纳入积极向上的轨道。
其次,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也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主要不是以自己的生物性功能立足于地球,而是靠自己的思维创造力的外化成为世界主宰。人靠智慧创造了超出自己身体功能而又延伸了身体功能的工具。精神的灵光是人的力量的源泉,因此人的精神性消费是最具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消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真正人的需要是自由和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实质上就是体现精神性生产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在精神取向的消费活动中,知识的吸取、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熏陶、情感的传达,它们既是愉悦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精神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
第三,消费的精神性转向也是由资源有限所规定的。在始源意义上和存在意义上,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活动能力是自然本身的功能。但是,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1)人仅仅利用现成的自然物,简单地将其改造为工具如石器、木棍等等;(2)人利用自然本身存在的现象如火,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把自然矿物质冶炼锻造成更加有效的工具;(3)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自然或生物的人通过改造自然物为工具来改造自然的状况,如电、核能、信息技术,可以说是以逼迫的形式让自然形态所内涵的能量释放出来。目前,人的力量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人对自然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人对煤炭、石油的开采显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逼近自然可能的边界。技术创新也不能永无止境地解决问题,而往往是拖延问题的解决或带来新的问题。我们不能再破坏性地消费自然,而应该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所以,我们必须把消费的欲望转向精神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要而言,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人们的消费欲望。随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提高,不仅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快,而且使用精神文化和符号意识消费的群体迅速增长。原来的热量、质量、数量等消费退隐到幕后,而通过消费类型的命名所获得的格调、优雅、气质等成为新消费群体关注的焦点。这些新消费群体考虑的往往不是实惠,他们更加热衷于体验。这个消费群体的出现为消费的精神性转向开辟了可能性的空间。目前出现的红色旅游、农家劳动旅游以及国外的监狱旅馆等等,就是消费精神性转向的证明。
最后,消费的精神性转向并不是对物质消费的否定,而是对物质消费的升华。消费当然包括物质消费并且永远以物质消费为基础,但是,人们毕竟可以把这种消费转化为文化和精神的享受。对在时空意义上都是有限的人来说,生活的物质需要也是有界限的,他并不能够真正占有或消费无限的物质。因此,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对人的生存而言,物质的追求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了。问题在于,人在本质上又是超越的,或者说,人是不断向前的、创新的。人们的能量必须有合适的途径得到宣泄。在物质的生存达到基本边界之后,人的真正有意义的追求只能是社会的、知识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提升。这就是消费时代的精神性转向的人性动力。
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思考发展目的、转变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模式,才能保证中国社会全面、持续和协调地发展。在没有吃饱之前,人只有一种苦恼;在吃饱之后,他却有可能出现无数种苦恼。把吃饱后的苦恼消解或转移,这大概就是人文精神对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所在,也是任何社会希望能够妥善构建的文化功能的原因。我们必须通过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建设节约性社会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解决人自身发展的内心矛盾及其和外部环境的矛盾。
三、精神性消费的意义
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促使消费活动发生精神性转向,对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首先,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可以促进转变发展模式,降低物质资源的耗费。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也必须从过分依赖出口转变到消费提升带动的轨道上来,这些都需要提高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合理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在保持合理的物质消费的同时,我们怎样去避免无谓的物质耗费,避免把宝贵的资源转化成过剩的产品?消费动力是很难控制的,也许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消费行为的精神性转向。费瑟斯通指出:“一个永远变化的商品洪流,使得解读商品持有者的地位或级别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形下,品位、独特敏锐的判断力、知识或文化资本变得重要了。”(费瑟斯通,第25页)因为能否在消费中感受自我肯定,全在于人们能否理解消费活动的文化涵义。某些关注生态问题的新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令人满意而又有意义的生活所追求的品质上的目标被视为比定量的价值更为重要。人的发展和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需要的满足被视为比经济增长更有意义。……需求应超越物质生存的需求的层面,并且包含了文化的福祉。”(文森特,第394页)由此,按照新的经济指标,积极的精神文化满足和身体健康也就取代了钱财、物质享乐和经济增长。也可以像布尔迪厄所说的,“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务,比如烹饪、服装或装饰”(转引自罗钢、王中忱,第48页),提高其精神内涵,而不是扩大物品的提供。可见,有了精神指向,也许就可以达到“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的境界。在这里,物质的消费就不是根本的了,根本的应该是内在的体验和喜悦。当生活以思想和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思想和艺术就成为一种美好的生活。
其次,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可以转变人们的欲求指向,使人从物欲追求转到内在的提升和发展上来。人的欲望是不能压抑的,但却是可以转变方向的。消费活动精神性转向后的社会类似于弗洛姆所说的“存在”的社会,而不是“占有”的社会。如果大家都想“占有”,那么再多的资源也不够;如果大家只想“存在”,那么社会资源就能够得到合理安排。这是消费活动价值取向的彻底转换,也是人性范式的转折式变革,是人性美德的巨大提升。这样的消费是绿色消费,是低消耗消费,是合理的、可持续的消费。问题的关键是让商品的交换价值服从于人的精神目标、审美体验和高雅的文化追求,而不是让人的精神世界服从于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是服务于人的需要的,而不是人的需要服从于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的进程。人们在休闲时是去声色犬马之地,还是去书店、博物馆、图书馆、剧院、音乐厅、体育馆,就表现了不同的消费指向:前者是物质欲望导向的,后者则是精神追求导向的。精神导向的消费活动,在消费的同时不仅获得了文化消遣,而且可以获得文学、艺术、音乐的熏陶。人们在获得精神享受的同时,还可以锻炼自己的身心、提升自己的修养、增长自己的知识、砥砺自己的思维、提高自己的能力。
最后,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使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就激发着精神生产,消费过程直接就成为精神生产过程。实际上,艺术消费和知识消费都可以“鼓励文化商品的膨胀,不断利用艺术和知识的潮流来刺激人们,帮助人们通过手头的工作来建立创造艺术与知识的新条件”(费瑟斯通,第53页)。在此,有必要谈一下大众文化问题。有些人出于精英文化的视角,对大众文化持批评态度,断定大众文化侵蚀着文化的成色,影响到精英文化的根基。我认为,大众最初有能力消费的文化只能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毕竟比没有文化强;大众就在自己能够欣赏和理解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增长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欣赏力和文化修养。我们的责任是逐渐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内涵,而不是采取藐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大众文化是群众消费活动精神性转向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精神性文化消费提升的一个重要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