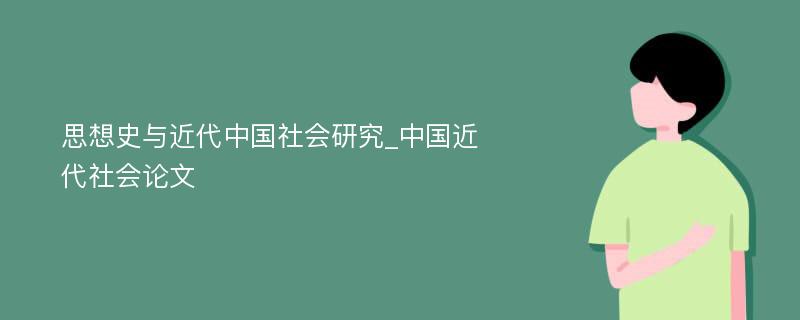
略论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心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2)02-0086-04
一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社会史著作不断涌现,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对深化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我国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很多理论还不成熟,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影响了社会史的整体研究,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心态,或者说整体(群众)心理研究的不足。历史学中“心态”、“社会心理”等概念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根据著名史学家勒高夫考证,法语的“心态”一词来自英语,英语的“心态”一词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最初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而在法语中该词却被很快广泛应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心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后来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1]
尽管早在希罗多德写下《历史》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时,社会史就已经诞生了,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社会史的确立是在年鉴学派产生之后。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的叛逆者,年鉴学派在创立伊始就主张长时段、整体史的研究,以揭示真正影响社会发展的,在历史大海深处不为人知的广大人民的历史。1924年年鉴学派第一代大师布洛赫出版了《巫师国王:论王权的超自然性》,这部书探讨了法国民众对于国王有治疗瘰疬病(淋巴结核)能力的信仰和对这一信仰的维持。布洛赫不是从传统的王权政治观念入手,而是选择了深入考察民众的集体心理状态这一方式,用类比的方法具体分析了民众的信仰内容,揭示了中世纪王权的社会基础。1932年法国史学家勒费弗尔在勒帮《民族心理学》(1894年)和《集体心理学》(1895年)的理论指导下,运用集体心理理论和方法,从广大农民、市民的心理状态与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等具体条件的复杂联系出发,写下了《1789年的大恐慌》论证法国大革命确实受集体心理状态的左右,1938年另一位年鉴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发表《心理学》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集体心理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明确地将集体心理(心态)研究与美国心理历史学(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影响)分开,最终奠定了现代心态史研究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什么是心态史研究呢?勒高夫说:“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菲利普·阿里埃斯也认为“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的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2]伊格尔斯也说:“历史的心理研究就是要用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某些观念、方法和研究成果研究过去。”当每个历史学家宣称“我已创造了过去”时,历史心理学家则坚决地加上一句“而我向你说明了历史的精神……我将看到过去的人,看到他的精神赋予他的生活。”[3]这些表述在语言上虽各有不同,然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重视历史上人民群众无意识的“意识”及其对应的生活方式。归纳起来,所谓心态史就是通过发掘人口统计、日记、报刊杂志、档案、遗嘱、田契、诉讼记录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材料,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人类过去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通过分析广大民众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心俗、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
当然,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社会史必须以分析具体结构为基础,关注社会特有细节诸如群体组织、家族、邻里组织、社团组织、商社组织、宗派组织以及联系这些组织的网络的性质和力量,个人在这些关系网和复杂阶层中的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变化。但同时“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表象上,还需要更深层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意识。”[4]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又是有思维、思想和情感的一个特殊物质,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参与其中的人必然具有社会心理的驱动,包含着思想、精神、感情的因素。这些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作用将愈来愈大,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告诫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要注意探讨广大民众、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思想动机及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动机。十分尊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学大师费弗尔也反复强调历史必须与心理学联合,取得心理学的支持,“历史必须由心理学家指点方向”[5]。由此看来,重视广大民众的心理层面研究与坚持唯物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尽管心态研究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可以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然而过去我们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此却很不重视,生怕有“唯心”之嫌。中国近代史由于在时间上距现在较近,在政治文化上对当代有十分强烈的影响,更由于近代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更使人们对此讳言莫深,而把注意力完全转到政治史的研究上,研究重点主要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条约及关键的历史人物。近年来社会史的崛起打破了这一现象,给近代史研究带来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心态史也应借此机会,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介入到历史研究之中,去说明以前其它史学理论和方法难以说清或解释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和中国社会对近代化的内在要求,其变迁十分剧烈。一波运动还未结束另一波运动已铺天盖地而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条约、事变、革命等接连不断,杰出的历史精英人物也应接不暇,历史学家的眼光往往被他们所吸引,着重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而对下层人民群众的关注则明显不足,以致于有一些问题如辛亥革命与农民的关系,城市贫民与近代城市化运动等的研究到如今还不太令人满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引入心态研究等方法,则一些问题的研究将会迎刃而解,一些以前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历史解释。由于心态是浸透于民族群体中的思想、感情、价值观、行为方式与规范的总和,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潜在的、无形的东西。在某一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变化很小而且传承性很强的东西。因此利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长时段的社会现象,而这正是近代社会史研究最为关注的。
比如在研究洋货进入中国摧毁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这个问题上,早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通晓中西商务的郑观应就曾写道:“洋药水、洋丸、洋粉、洋烟丝、吕宋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水果、咖啡……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针、洋线、洋伞、洋纸、洋钉、洋画……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此外更有电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好玩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6]甚至连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从汉口进货,供百姓消费之用,对此洋货之害中国人民早有觉悟,近代也有几次“拒洋货”运动,但洋货不绝且愈演愈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作过很多解释,其实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从中国广大农民的心态上寻找答案,在中国近代社会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低下,而将生活需求置于生活伦理的核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实用观念。衣食日用以廉价、实用为第一原则,而洋货的价廉物美则非常符合这一大众心理。如对于火柴,过去用惯火镰的群众就夸耀说:“纤纤寸木药硝粘,引起灯光胜火镰,莫怪粹奴夸利用,缘他工省价还廉”[7]。另外从社会精神需求看,中国人是一个重视社会地位而且从众性很强的民族,十分注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身份和地位,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很讲面子,哪怕家里吃得苦一点,在外面一定要讲排场,由此产生了大量为应付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社会需求。而一些洋货精巧、美观、新奇的特点正好适合了这种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所以吸引人们购买使用,形成洋货流行与崇洋之风。广大群众对洋货的尊崇心理在陈作霖的《炳烛夜谈》中有十分生动的描叙,他记道:在道咸年间“凡物之极贵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莆,挂灯曰洋灯,火锅曰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曰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曰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彭泽益也记叙当时的情形说:农民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平时习惯于穿土布,然而当“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布细密光泽者,以为外观美丽。”[8]从当时整体社会心理的角度看,除开广大农民,当时一部分仁人志士确已认识到洋货所带来的“无穷之漏厄”是洋人“拜我资材”的经济掠夺,然而他们却是社会的少数,其思想不具有整体心理的代表性,而恰恰相反,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对于洋货则明显表露出一股欣赏和羡慕的心态。这在当时流行的报刊、笔记及反映市民生活的《竹枝词》中反映十分明显。因此在整体的社会心理上广大民众对洋货是认同的,从中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近代外国商品在中国泛滥的原因了。
二
另外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加以研究。从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各省纷起响应的表象看,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具有戏剧性的味道。而它在胜利后又迅速走向失效则一直引起人们的思索。这一现象依然与整体的社会心态密不可分。从社会整体心理来看,当时农民、城市市民、军人、民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有一股强烈的反满思想,而民主革命的思想却没有前一种思潮那么普遍,因此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进行得十分迅速。然而一旦清王朝被推翻,传统思想上崇上、追求稳定的群众心理又占据上风,革命难以继续进行。如首义之区武昌在推出黎元洪这个旧官僚,革命有倒退迹象时,武汉的市民却是“欢声雷动”、“人民始为大定”,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心理动力。关于这一问题季云飞先生的《论辛亥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成败》一文已有详细论证,本文不再赘叙。[9]
此外在中国近代有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次是义和团运动。两者都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然而两者在斗争的组织形式、宗教观念、斗争范围及影响等问题上的区别颇耐人寻味。太平天国发源于两广入湖南后沿长江东下,在南京建都,建立了一个与清政府抗衡时间长达14年,势力范围波及18省的农民政权。在南方它发展得如火如荼,金田起义时其人数不过两万左右,而打到南京时已号称百万之师,在两湖太平军所向披糜,沿途群众纷纷加入。然而在北方它的影响却远不如在南方。1853年太平军出师北伐,不计后来派出的援军,总兵力在四万左右。北伐军虽然在初期取得很大战果,然而在力量上则增长有限,经常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最后也因弹尽粮绝,敌我力量悬殊而败,其境地与太平军在南方备受人民拥护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在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固然可以说太平北伐军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以及它不注意发动群众等种种不足,但有一点不能否定,就是南北农村由于传统观念及耕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带来的南北农民的群体心理状态的不同使他们在对待太平军及拜上帝教的态度上有所不同。36年后当北方掀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时,南方却异常平静,南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现象当然也不是一个“东南互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要想弄清真正的缘故,还必须分析南北社会特别是农村农民的社会心态。这一问题及其相应的其它问题如宗教、乡村教育机构、农村宗法制度等都值得我们下大力气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运用社会心态进行研究时,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任何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与任何事物一样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心态研究一方面弥补了传统史学只注重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缺憾,但同时它也复杂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渗入研究者的主观臆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类社会的不同意识、情感、精神包括宗教与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虚无飘缈的。它们都耸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上”[10],是一定的经济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社会心态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决不能以此替代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