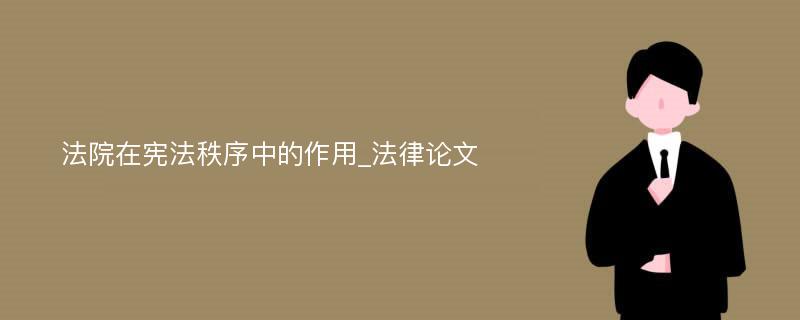
宪政秩序中法院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秩序论文,法院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07)03-0053-13
引言
如果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作为中国近代宪政发展的一个起点的话,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如果将1954年宪法的通过作为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的话,迄今为止,则是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在近百年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宪政秩序的实现一直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魂牵梦绕的理想。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在向宪政之路前进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期间的艰辛是非亲身经历过而难以品尝和体会的。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和新中国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宪法发展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和反复之后,中国宪法从幼稚逐步走向初步的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82宪法的通过并顺利实施20多年不曾间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方略写入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这标志着中国向法治国家迈进的一个新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算得上是走向成熟的宪政之路的开端。
而今,中国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动力;中国正处在一个奔向法治的时代,法治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各项事业成功的保证。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宪政秩序实现的过程中,对于法院的角色的忽视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从各国的宪政发展的历史发展,司法对于法治和宪政秩序的实现意义重大,而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在我们对法治和宪政还没有深入的认识的情况下形成并沿袭下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其制度性缺陷逐渐地显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司法制度的革新就成为我们实现追求宪政秩序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这是我们对中国宪政历程和法治发展有了深入全面认识之后所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特别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们的基本追求目标之后,其迫切性就更加显而易见。
一、法院的角色与司法决策
在现代国家中,法院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所行使的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基本内容。从孟德斯鸠提出完整的“三权分立”理论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政治体制设计时都对法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当然,“由于在客观上法院所处的宪法地位的差异,不同国家关于法院角色也许会有不同的认识,同时,对司法活动描述内在的不一致或含糊使得法院的角色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化,而且,对于司法过程和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种种设想,以及司法活动导致的普遍目标的提升,都将会使法院的角色受到不同的影响。”[1](P73)但是,伴随着法治的理想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法院逐渐占据了法治这一概念的中心位置,法院的角色成为各国法治发展中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法治国家,“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2](P361)法院将成为各种力量角逐并主张自己利益的一个崭新的舞台。而今,世界各国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各种力量的角逐必将空前的激烈和普遍,法院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这是各国都必须正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要理解法院的角色,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法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第二,法院的这些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传统的认识将法院的职能集中在纠纷的解决上,即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事实加以判断,对法律加以适用,从而化纷止争。然而事实上,今天的法院所要从事活动远非仅限于此。艾森伯格认为法院象其他复杂的机构一样履行着数种职能,但其中两项职能是首要的:第一项职能是解决纠纷,这是法院的中心职能;第二项职能是充实法律规则,这一职能不是完全自立的,而是法院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他认为即使认为解决纠纷是法院的唯一职能,那么也会出现以司法方式设立规则的情况,因为当法院在新的情况下阐明社会现存标准的适用、意思和引申含义时,它们无法同时避免创制以前没有宣告过的法律。他把法院确立法律规则的职能归结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副产品模式(the by-product model),即法院所确立的规则只是解决纠纷的附带产品;另外一种是充实模式(the enrichment model),在这种模式下,确立法律规则来规制社会行为被认为是法院自身的需要,是法院有意识地承担起发展一定法律体系的职能。[3](P5-7)有的学者则把法院的职能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解决纠纷,即法院是政府为当事人提供的一个解决纠纷的论坛;第二,行为塑造,即法院通过鼓励一些行为而惩罚另外一些行为来实现对社会的塑造;第三,资源的再分配,在民事、刑事等各种诉讼中,法院的判决将使一些人受益,而使另外一些人受损;第四,决策的职能,即创造并适用权威规则,当然从实践上来说,创造规则和适用已有的规则不是截然分开的。这四种职能对于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是有着不同的分配的,前三种职能主要由初审法院来完成,而上诉法院仅受理一小部分案件,所以前三种职能的直接发挥是有限的,但是其第四种职能——决策职能的发挥则使其显得更为重要。[4](P7-9)
事实上,从各国的宪政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尽管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异议,法院的司法决策实践还是基本上得到了法律界和整个社会的认同。一般来说,级别比较低的法院主要从事的是法律和规则的执行活动,司法决策在这个层次较少发生,而在级别较高的法院,比如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由于其判决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比较广,其影响力也比较大,司法决策活动常常在这个层次上发生。博登海默对此指出:“尽管我们应当坚持认为,法律改革的重大任务应当留待那些享有立法权的人或机构去完成,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同时也给予司法机关以权力去领导社会道德观,并给予其权力在司法审判中开创一种同人们所可领悟的、最高层次的知识和最真实的洞见相一致的新正义观念,那么我们的观点恐怕就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可能还是一种庸俗的观点。”[5](P559)
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在实践中积极制定司法决策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并且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它既有初审管辖权又有上诉管辖权,然而与其上诉管辖权相比,其初审受理的案件屈指可数,而其上诉管辖是由其自己决定的。联邦最高法院常常利用自己自由裁量权对于那些具有深远政治与社会意义的问题做出裁决,其早期审理的一些案件特别明显的说明了司法决策在塑造国家方面的重要性,比如: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此案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国会的司法审查权;1816年的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Martin v.Hunter's Lessee),此案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州法院的审查权;1819年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State of Maryland),此案确立了联邦法的最高效力;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Ogden)此案确立了联邦对州际通商的管理权,等等。这些经典性案例都是美国宪法的基本案例,它们帮助界定了联邦体制的特征、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决定了美国强调商业和发展的趋势。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通过对宪法的解释而创立了全新的政策,促进了联邦大厦的建立和稳固。有的学者称,它们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总体影响等同于甚至超出了联邦最高法院今天所作的有争议的判决。[6](P543)在进入20世纪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将眼光逐渐转向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诸多领域里,比如言论、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种族、性别、年龄歧视;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权利;平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和行政程序等等,联邦最高法院采取更为自由的政策,一些案件由此成为了公民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发展的里程碑,比如1954年的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Kansas)宣告了“隔离即平等”时代的结束,标志着美国民权运动的重大胜利。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Ohio),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联邦排除规则(即禁止把一切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用于法庭的诉讼)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各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有利于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在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削弱了这一规则的适用,使其在特定情形下加以限制,但是并没有推翻60年代确立的司法决策。1962年的贝克尔诉卡尔案(Baker V.Carr),对议会重新分配代表名额提出质疑,并对违宪审查中“政治问题”的标准进行了确定。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进一步肯定了新闻自由的原则,为大众传媒批评政府和官员的自由提供了充分的保障。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Miranda v.Arizona)确立了“米兰达规则”,①使刑事诉讼过程中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进一步得到加强。将美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角色相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联邦最高法院的决策作用显得格外的突出,它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所起到的引导和塑造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正如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生活情况之后写道,美国的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成为司法问题。在美国求助于法院解决问题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对重大的宪法问题存在争议时,法院的政治权力在于,它能很明智的利用其本身具有的制定政策的机会,因此,法院被认为是国家的‘良心’所在。” [7](P299)
在英国,其法律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主要是一种判例法。英国的判例不仅仅是法律实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法律原则的总结,因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中就认为,“在英宪中我们不见有各种权利的宣言或定义,当研究英宪时你可以发现,实是在法院判决之下确立的准则”。“在英格兰之中,宪法本身是以法律的判决为根据”,“所谓宪法原理是由法院涉及每个人所有权利的判决案归纳得到之通则”。[8](P240-241)英国在其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悠久的传统,即法官应该恪守其前辈所确立的判例原则,英国司法界甚至把这一传统奉为“判例主义”(Doctrine of the Precedent),这种作法的背后其实就隐含着司法决策。但是,也正是由于判例主义及其对判例主义传统的尊重,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英国法律发展较为缓慢,远远跟不上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之下,英国这个一贯以保守著称的国家也不得不进行法律改革,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伟大的法律改革家”,即丹宁勋爵。这位英国二战后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在其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以自己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积极、大胆地参与英国战后的法律改革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英国战后法律改革史上的划时代的人物。1959年,他在上议院(英国的上议院就是英国的最高上诉机关)发表的讲话和一系列演讲中主张,上议院应该在改变法律就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以自己的司法能力担负起改变法律的任务,而不是等待国会的行动。[9](P1)丹宁主张法官应该扮演一个更为创造性的角色,特别是在先例出现冲突或没有明确的清晰的法律方向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10](P368)他要求法官担任“法律改革的先锋”,要参与法律改革,而不能把改革仅仅看成是国会的事,法官只是执行法律而已。他指出,法律就象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编织材料来编这块编织物,是国会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法官当然“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11](P12)丹宁勋爵本人也是一位司法决策积极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其担任司法职务近40年间,他对宪政的理解和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司法实践对英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法学家特别指出,丹宁勋爵对英国法律改革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在英国是划时代的,如果没有他,那些最重要的原则至今也不可能建立起来。[10](P8)一些法律界的保守势力曾对丹宁关于法官参与法律改革的主张大肆攻击,称这是一种“超越国会的行为”,丹宁在上诉法院的一些判决还曾遭到了英国最高上诉机关上议院的否决。但是,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后,丹宁的一些曾遭上议院否决的判决被欧洲法院所确认,于是有的成为了英国法院新的判例和判案原则。
在德国,其司法决策活动主要集中在联邦高级法院,特别是其联邦宪法法院。因为尽管其他法院也参与司法政策的制定,在其作出一项重要判决时,也积极参与了国家议事日程的制定。但是,与政策制定牵涉最多的则是联邦宪法法院。虽然德国人对于法院的期望远远低于美国人,德国人也不会事事诉诸于法院以求得圆满解决,但是由于其联邦宪法法院只审理宪法性案件,而不是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最高审级,各种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关宪法问题的案件,都应该中止诉讼并将这一法律问题提交到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决定,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对有关宪法问题的案件行使最高司法权。[6](P530-531)联邦宪法法院主要通过其抽象与具体的司法审查权及受理宪法申诉权使其能够参与决策。另外,联邦宪法法院还可以宣布对某一法律的特定解释是唯一为宪法允许的解释,并且往往给予明确如何实施法律的指示,这一做法显然也可以被视为制定政策。据有关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法官已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包括制定政策。[6](P572-576)如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其宪法裁决,对德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德国法院传统的角色而成为德国政治权力中心之一。
法院是否应当制定政策以及法院是否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这在很多国家并非完全取得了一致的共识,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随着人们将向法院提交的诉讼越来越多,而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越来越先进,法院会不断遇到新的棘手问题。法院如何处理此类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决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少人也发出疑问,质疑法院是否有能力或资格制定基本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事实上司法决策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主要表现为:司法决策与立法或者行政政策相比,其范围通常要小得多;法院是被动的带有依赖性的决策者;法院通常无法检查自己判决的影响或效果,更不可能随时改变主意而把某项判决收回并加以更改;法院用于做出判决的信息是有限的;法院无法自己执行自己的政策。[6](P560-567)
但是,对于这些局限性我们也应该有全面的认识。“法律本身不能盖房子、不能防止事故的发生、也不能制止通货膨胀”,但是“通过说服或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法律就能够间接地对物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12](P87)法院也许不会参与很多重大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比如一个国家未来的科学发展规划,一个国家对外战争的发动。然而,对于这些决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法院可以发挥其影响的。比如科学发展规划问题中的克隆人研究,法院无法决定规划本身,但是对于克隆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应该有发言权。而在国家对外战争的决定上,法院当然不能直接参与决定,但是法院的判决可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之后战争问题的处理。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就曾经受理过因为总统的战争权和国会宣战权的冲突而发生的诉讼,在越战期间美国还发生过一系列和战争问题有关的诉讼,像1968年的“征兵登记卡案”(即合众国诉奥布莱恩案)(United States v.O'Brien),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奥布莱恩烧毁征兵登记卡的行为不属于“象征性言论”,因此不予以保护。而在1969年的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Tinker v.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学生佩带黑色臂章的行为属于“象征性言论”,应该纳入到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这些案件的判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另外,司法决策的被动性问题也是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言的,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其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是否重新处理某些问题并改变某项法律,行政机关也可以在连续执行政策的基础上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政策,而法院做出新的或者不同判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后来的被提交到法院的案件,而法院一般不会轻易推翻以前的裁决。这样,法院无法主动的制定政策,同时不能任意的确定自己的政策内容,而-且往往比较滞后。然而这些特殊的性质正好可以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决策形成互补,法院通过事后的判决来对社会产生塑造作用与立法机关事先通过对未来的设计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方式是相对应的。事实上,法院和其他的机关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产生各自独特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对于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和宪政秩序的形成会产生各自不同的效果。本杰明.卡多佐在其名著《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以文学化的语言描述其做法官的体验:“在我担任法官的第一年,我发现在我启航远行的大海上没有任何航迹,为此我一直很烦恼,因为我寻找的是确定性。”“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越来越多地反思司法过程的性质,我已经变得甘心于这种不确定性了,因为我已经渐渐理解它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渐渐懂得: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13](P104-105)因此,尽管司法决策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法院通过其判决所实现的决策功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种决策功能有一种放大的效应。从实际上来考察,我们甚至无法精确地估量法院的判决在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所产生巨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一些重要的判决除了对本国产生影响之外甚至会超越国界对世界各国的宪政发展产生强大的辐射力。一个成熟宪政秩序的形成需要法院塑造力和影响力充分的发挥。因此,在各国的宪政实践中,法院一方面需要重新塑造自己,另一方面也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去,成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塑造者。
二、法院角色的自我认同——在能动与自制之间
对于法院角色的深入思考,使我们必须超越对于法院行使司法权现实结果的考量,而且法院的角色也并非一个呆板的凝固物,而是法院在宪政体制下与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中逐渐趋于清晰化并获得认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寻找法院角色认同背后的支撑力,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一个动态的答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后罗斯福时代”和“沃伦时代”不同风格的实践都曾引发美国民众及法律界对法院的角色进行深入的思考。日本在近代法治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事件和案件,像大津事件、平贺书函事件、砂川案、长沼案等,法院对于这些事件和案件的态度则反应了其寻找自己适当的角色定位的摸索和尝试。相比较而言,我国法院对于自身角色的定位过程中显得较为冷漠,比如我国法官群体和法院在“李慧娟事件”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一致的具有司法职业特征的反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法院角色的自我认知及其充分的自我认同对于一个国家宪政秩序的完善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发展过程来看,法官群体共同法律意识的形成,其行为模式的确立及其对自己社会角色的清晰认知,无不无时无刻地对一个国家的宪政秩序产生着实在而又重大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考察,对于司法权的确定性的认识始于孟德斯鸠创立的权力分立学说。孟氏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而司法权是指“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的权力,他特别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4](P155-156)孟氏的分权学说是划时代的,但是也仅到此为止,至于三权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孟氏并没有做出精确的回答。1789年美国宪法深受孟氏分权学说的影响,但当时“在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中,很少有人能够直觉地预见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未来角色”。[15](P43)对于这一问题,汉密尔顿在稍后做出了更为超前的考虑和设想:“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对宪法授与的政治权力危害最寡,因其具备的干扰与为害能力最小。”“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6](P391)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宪法要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的限制,法院应该被授予司法审查权,即“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而且法官在互相矛盾的两种法律中作出司法裁决,这是一个经常遇到的事情。“具有同等效力的互相冲突的立法,应以能表达最后意志的法律为准”。“如互相冲突的法律有高下之分,有基本法与派生法之分,则从事物的性质与推理方面考虑,其所应遵循的规律则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在时间顺序上较早的高级法较以后制定的从属于前者的低级法其效力为大。因此,如果个别法案如与宪法违背,法庭应遵循后者,无视前者。”[16](P393)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就是汉密尔顿思想的生动实践,因此尽管美国宪法文本中没有关于最高法院未来角色的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美国法官司法审查的实践却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过去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地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司法理念:“司法能动”和“司法自制”,而且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理念及司法实践时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这两种理念斗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院过去和未来的角色。这其实就是法官群体在对法院的角色认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差异和不同路径选择,正是在不断的争论和尝试性的实践中,法院逐渐地找到自己发挥其独特作用的方式和舞台。司法能动主义认为法官制定社会政策具有合法性,法官不应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处理法律冲突,而是要敢于参与社会政策的形成,即使是与既定的政策和先例不一致。就像沃伦时代一样(1953-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积极地扩展了其在美国政府中的角色。[15](P322)司法能动主义者更认为,司法能动并非会导致司法独裁,因为伟大的法官必须在其所生活时代的社会需要与永恒的自由社会要求之间达致一种平衡。没有最后一点,法官确实会变成为独裁者;法官最终也将失去他们的权威,因为法官的权威在于人民相信法院确实是在“根据法律”而决策。[15](P128)事实上,美国法官从建国伊始就信奉司法能动主义。最明显的早期司法能动的例子是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确立司法审查权这一石破天惊的壮举。其后还有20世纪前期联邦最高法院对“洛克纳主义”的坚持, 30年代对罗斯福新政立法的否决,以及后来的沃伦法院将自由主义思想注入到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保障之中。通过诸如此类的实践,司法机关成为了法律和社会正义基本构架的探索者和积极塑造者,也使得美国今天的宪法实践已经与当初制宪者的设计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可以而且必须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中才找得出来,因此,要充分理解美国政府的复杂组织和社会的运作,我们不能只看宪法文本和法律规定,还必须认识到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时活跃的创造,理解其作出的一整套宪法性判决。相对于司法能动,司法自制主义则主张极度降低法官把个人的观点适用于其作出判决之中的程度,法院应当遵从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机关作出的立法决策。只有在发生显著违宪行为场合,法院才可以宣告该政策机关的行为无效。司法自我约束是一种关于司法作用的观念,这种观念限制司法权力的行使,而且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作为主要政策创制的适当渊源。司法自我约束论者基于以下几个原因认为法院充当较激进的角色是不适当的:第一,法院一般来说不对公众负责。对那些被任命的且终身任职的联邦法院法官尤其是这样。第二,法院在与其他机关对抗中很少取胜。实际上对于旨在限制法院权力的报复行动,法院往往是脆弱的。因而司法机关独立可能因司法能动主义者及其挑衅性的判决而受到威胁。最后,自我约束论者主张,要对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判决,法庭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论坛。[17](P353-354)杰斐逊就曾强烈反对司法能动,他认为“如果认为法官是所有宪法问题的最终裁判者。这将把我们置于一个寡头统治的暴政之下。”[15](P127)事实上,大多数法官总是承认某些种类和程度的限制,即便这些限制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我施加的。[15](P127)司法自制者认为,法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院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其权力是有限的,司法过于能动必然造成对司法权威损害并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布莱克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法院不应该将它们的社会与经济信仰来替代民选立法机构的判断。[18]在后罗斯福时代,立法至上与司法节制的哲学曾获得阶段性的胜利,在沃伦法院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逐渐地在往司法自制道路上靠近。
在司法自制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问题回避原则”的提出并得到大部分法官的认同,这其实也是法院对自己角色清晰认识的结果。所谓的“政治问题”,是指尽管冲突本身可能符合通常的“具体争议”要求,法院为了维护政府分权原则并尊重民主政府的其他分支,自动谢绝审查属于其他政府分支决定的问题,从而把它们归入“不可审查”争议的行列。[19](P74)该原则的提出表明了法院这样的一种立场:它宣称某些案件或某些案件涉及的问题不具有可裁判性,即不适宜司法解决,尽管这些案件或这些案件涉及的问题属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或者也符合法院受理诉讼的各项要求。[20](P118-119)早在1794年,马歇尔在众议院发言时曾指出:“宪法虽把司法权力扩展到所有法律与衡平案件,却从未被理解为授予司法部门任何政治权力。要进入法庭,问题必须采取法庭诉讼和司法决定的法律形式。诉讼必须存在进入法院的当事人,他们受到司法程序的约束,并且必须服从审判庭的最终决定。”即法院能够也必须处理公共政策问题——即政治问题,但是,法院不能以政治方式而只能以法律形式处理这些问题。[19](P74-75)在马伯里案中,马歇尔则提出,“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问题是永远也不能在法院提起诉讼的”。“政治问题”的标准是在贝克尔诉卡尔案(Baker V.Carr,1962年)的判决中被明确的:(1)宪法确定地将该问题赋予与法院有同等政治地位的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进行处理;(2)裁判上没有可以据以解决该问题的法院可以发现和适用的标准;(3)在解决该问题之前必须首先作出政策性决定,而该政策性决定不宜由法院作出,即必须先经过“非司法的裁量”之后法院才可能判断;(4)在解决该问题时会显示出对其他同等的有关政府部门的不尊重;(5)有必要对于已经作出的政治决定有加以尊重;(6)对于同一个问题,法院和其他部门不一致的决定可能导致混乱和令人尴尬的局面。[21]
对于“政治问题”原则美国司法界是有异议声音的,事实上到达联邦法院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政治性的。因此,“政治问题”原则有循环论证的味道。在尼克松诉赫尔顿案(Nixon v.Herndon,1926年)中,当事人主张案件涉及政党预选,因具有政治性而不宜进行司法审查。对此,大法官霍姆斯则指出,“这简直是在说俏皮话”。[22](P108)还有人认为“政治问题回避”原则并无宪法依据,该原则是反宪法的,他们还引用大法官马歇尔在科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案(Cohens v.Virginia,1821年)中的判决:“若法院不应当管辖的话,它就不会管辖,这一点不错;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它应当管辖的话,它就必须管辖……厚此薄彼,都是对宪法的背叛”。[20] (P128)他们还指出,“即使政治问题原则不是背叛宪法,那也可能背叛宪政。在把该原则适用到宪法问题上时,它就意味着司法机构放弃了它作为立宪体制监护者的角色”。“当法院拒绝裁决或审理总统僭越立法权力的诉讼时,它们就是放弃捍卫宪政和我们所达致的二元民主的职责;当它们拒绝审理总统控告国会僭越权力的诉讼时,它们也同样放弃了那个职责。而当它们拒绝受理个人对宪法权利主张的诉讼时,它们也在放弃其主要角色,即保证政府贯彻我们在二百多年前就宣布不证自明的真理:‘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了政府。’”[20](P127)而对于贝克尔诉卡尔案的判决,有人指出,虽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这一作法给政治问题原则赋予了新的生命,但结果并不是澄清了混乱,而是乱上加乱。[20](P127)
笔者认为,“政治问题回避原则”的提出及适用,对于解决宪法实践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权力分立、重大利益冲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方便武器。应该说,这也是法院的明智之举。因为置身于利益分化的社会,作为一个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法院来说,其权威的获得与其中立地位和公正形象的保持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法院来说,避免陷入政治旋涡之中使自己的权威性受损,“跳出圈外”可谓是一种理性思考之后的最优的选择。因此,“政治问题”原则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样的立场是法院在分权体制下采取的明智而理性的作法,法院作为宪政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它应该给自己找准位置,正确而适当的进行角色认同。对于一个国家的宪政发展和成熟来说,司法权绝对的能动并非是好事,司法权必要的自制也并非缺陷,不介入“政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法院自己对其权力范围的自我限制和约束。
与美国司法审查的实践相比,其他国家的法院在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过程中也时有能动与自制的分歧和波动,尽管没有那么的泾渭分明和强烈。在欧洲,作为现代政治基础的理论除了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之外还有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该学说对法院的论述很少,但对于法院角色的定位却影响极大。按照卢梭的意思, “主权本质上是一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23] (P116)因此代议制与直接民主制相比,后者才是真正符合人民主权的要求。卢梭的这种学说后来被法国的一些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同时囿于现代国家实施直接民主实践的条件限制,主权最后还主要是要通过议会来体现。这就造成了在实践中要求法院必须尊重立法机关的意志,在国家宪政体制中法院的地位要比议会低的结果。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官一直被置于一个“自动售货机”的位置,一方面“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分权制衡的体制”,[24](P127)另一方面是要避免司法权对体现人民公意的法律构成挑战。法国主流的法学思想甚至曾经认为,赋予法院充分的司法审查权会导致像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法官政府的统治”,这对于法国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1958年宪法所设计的宪政体制明显的表现了法院角色的不信任,一方面,法国继续保持司法二元体制的传统,即审理民事、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体系和审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院体系;另一方面,法国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负责事先审查法律、议会规程和条约的合宪性问题。该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属性曾经引发了法国法律界的广泛的争议,“司法机关说”和“政治机关说”各执一词。从现实意义上来看,宪法委员会的实际运作及其改革方向都展现了司法化的趋势,1971年结社自由案和1974年的宪法修改使得宪法委员会得以能动的介入到法国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后,宪法委员会的活动日益司法化,特别是1990年代由密特朗启动的宪法改革方案,将法院的一般诉讼过程与宪法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相联接,“先诉裁决制度”的设计和引进,使得个人在其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可能诉诸合宪性审查,这样的司法化的设计明显是对德国宪法法院实践的直接模仿。由于司法权对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渗透,宪法委员会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促使法国的宪政理念和实践超越了纯粹的议会民主阶段而进入真正的宪政民主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对法院角色的认识和设计早已经超越了孟德斯鸠、卢梭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
对于“政治问题回避原则”,欧洲国家亦有相应的实践。法国宪法理论中区分行政机关的两种行为,即“政府行为”(acres de gouvernement)“行政行为”(actes d'administration),前者是指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定的职责的法律行为。后者是指政府行使的直接源于宪法的权力行为,这是由政府自己来实施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授权。一般来说,行政法院是可以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审查的,但是对于政府和立法机关关系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政府和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关系问题则是例外,即避免通过诉讼实施审查,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宪法所确立的权力分立原则。法官应该拒绝对可能会因做出裁决而越权的情况,因为宪法已经把有关的问题规定给政府来做出处理。无论如何,法院应该避免导致法国政府“以两种声音说话”的危险局面出现。[25](P195-196)1962年的“公投修宪”和宪法委员会的62-20号裁决也是对“政府行为”理论的一次检验。宪法委员会则在其裁决中宣布,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调整机构,宪法第61条所规定的由其进行审查的法律仅限于议会立法,而不是全民公投通过的法律。全民公投是人民公意的直接表达,因此该委员会无权就参议院议长的要求做出裁决。[26](P127)这就意味着宪法委员会不认为自己有权来审查全民公决的合宪性。应该说宪法委员会的这一表态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非常明智的,对于一个本来就很“炙热的政治问题”,还是通过政治的途径来解决比较合适,这实际上是法国宪政体制下“政治问题回避原则”的生动应用。
在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没有明确地提出“政治问题回避原则”,但在相关的判决中,也能够看到该理论的影子,比如在1973年的“两德基础关系条约”案②中,宪法法院判决认为,法院在解释规范联邦与其他国家政治关系的宪法条文时,不能不考虑这些条文所设定界限的性质,也要留给政治上自由运作的空间。条约之法规审查应该于条约生效之前来加以判决,以促使所有宪法机关注意并配合修改。如果在某种例外的情况下,在宪法法院结束其诉讼程序之前条约已经生效,并致使法院无法拒绝行政部门之意见,此时,使之生效的宪法机关应该对其后果自负责任。联邦宪法法院在此自行设定了司法自制原则并不表示减少或削弱其前述的权限,而是放弃对政治之干预或插手政治,使其他宪法机关得在宪法保障之范围内保留政治之自由空间。那么,在这一判决中,宪法法院并未谈到“政治问题”,但有人提出,从宪法法院判决的本意来看,既然宪法法院已经认可了在条约生效之后法院可以例外地不对该条约进行合宪性审查,而仅仅强调行政部门自负责任,这实际上就是对法律问题规避判断,但是却以时间的先后或是否有先行的行政部门的行为来决定是否进行审查,因此,这意味着宪法法院已经承认了“政治问题”的存在。
在日本,其司法审查制度借鉴了美国,但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法院总体显示了司法自制的倾向,其司法界更是提出了“统治行为论”,对于一些政治问题予以回避。所谓“统治行为”系指在政治部门的行为中,对之法院虽有做成法的判断之可能,但有鉴于其性质具高度的政治性。故被从司法审查的对象中排除的行为。[27](P348)该理论的出笼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平野诉首相案③,当时,围绕“统治行为”是否构成司法审查的范围问题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统治行为肯定论和统治行为否定论。他们都认为法院对于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国家行为无权审查,而统治行为否定论则从彻底的法治主义出发,不承认统治行为的特殊性,但最终统治行为肯定论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即法院对于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国家行为不适宜进行司法审查。在苫米地案(1960年)④中,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对“统治行为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不是一切国家行为都无限制地是司法审查的对象,如直接关于国家通知基础的、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即使称为法律上的争讼,对此有效无效的判断在法律上即或是可能的,但这样的国家行为是在法院审查权之外,可解释为应任凭对主权者国民政治负政治责任的政府、国会等政治部门来判断,并最终地取决于国民的政治判断。这种对司法权的制约,归根到底由来于三权分立的原理。鉴于该国家行为的高度政治性,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性质,审判必然伴随手续上的制约等,虽无特别明文的规定,应把它理解为从宪法原则上对司法权的制约。”“众议院解散,是政治性极高的有关国家统治基础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审查法律上有效无效,应解释为在司法法院权限之外。”[28](P521-522)在其后的砂川案(1959年)和长沼案(1982年)中,最高法院对于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以及自卫队的存在是否违宪的问题,都以不适于行使司法功能为由拒绝行使司法审查,这实际上就是对“统治行为论”表示了间接或直接的接受。
司法能动和司法自制的两种理念和实践实际上并没有天然的分水岭,这只是法院在对自身角色进行认同过程中不同的尝试。法院在实施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必须学会适当得避让,司法的激进并不绝对意味着法治的成熟,有时却恰恰反映出实践者的初级和幼稚,司法适当的自我约束对于司法权的保护和法治的发展是必须而有益的。司法消极主义的提出和司法自制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法院对自身的角色正确而充分认同的结果。
三、重新审视我国法院的角色
我国的司法制度在建国之后也经历过一些调整,其中既有政治的考虑也有法治发展自身的需要。目前,中国已经启动的司法改革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司法机关面对新的挑战做出的积极主动的回应。对于这次司法改革,围绕司法权和司法改革的方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和建议,学者们曾经提出过司法专业化以及建立中国法律共同体的主张,司法独立也被提到很高的层次来认识,司法权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以及从保守、被动向开放、能动的司法转变也不断有人提倡,还有人提出了设立国家法院体系的设想,等等。从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各级法院在落实纲要的同时,各种各样司法改革的实践也在积极地展开:山东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之后各地法院纷纷跟上;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大胆进行了“辩诉交易”的实验;郑州中原区法院则提出了自己的“先例判决”制度;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申诉和申请再审的若干规定(试行)》,等等。总的来说,关于法院和司法的不少合理的主张在逐渐被接受并变成现实,我们对法院和司法的认识在逐渐的深化和拓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普遍展开的改革却表明我们在对司法权和司法改革实践本质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问题,而对于这一点我们恰恰缺少充分的认识。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司法权和司法改革进行认识。
首先,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即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基本环节,其独立地位的确立源于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完善,其本身作为国家权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法院通过其司法活动来实现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的塑造,进而促使宪政国家的最终实现。因此,对于司法权国家属性的认识是对法院角色进行认同的基点,“司法统一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理念在于:主权国家的统一系于法制的统一,而法制的统一则系于司法。” [29](P164)一个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其法院体系的完善及法院通过法律解释消除法律冲突的创造性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现代的法院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要在化解权力冲突和法律冲突的过程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在联邦制国家,统一的司法对于国家法制的统一和联邦的正常运作可以说至关重要,功不可没。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和德国的实践非常清楚的得到体现:美国有州法院系统和联邦法院系统之分,联邦最高法院在建立之初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使命:一个是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主要是通过攫取司法审查权来解释法律和宪法,进而挟宪法以自重,实施违宪审查;另外一个是就是塑造联邦,这一项使命的伟大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前一个,这可以说是挟宪法以令诸侯,逐渐的削弱州权至上的观念,一步步的建立联邦大厦。联邦最高法院在建国之初的弗莱彻诉佩克案(Fletcher v.Peck,1810年)宣布一项州法违宪,而在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Martin v.Hunter's Lessee,1816年)中则宣布其拥有对州最高法院作出的宪法问题裁决进行审查的权力。因此,就其司法审查权对于维护美国联邦体制的作用来看,我们可以说司法审查使联邦最高法院成为了联邦制的监护人。因为审查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在后来成为其司法审查的最重要内容,事实上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联邦的法律很少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但是却有数百件州和地方的法律被判定为违宪。这正如大法官霍姆斯所言,“假如我们失去了宣布联邦国会通过的某项法案无效的权力,我认为美国不会因此而结束。但是我确实认为,假如我们不能对一些州的法律宣布其无效,联邦就一定会陷入危险。”[30](P296)同为联邦制的德国,其法院体系的设计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它是按照专业化和权力分散原则设立的。实际上它没有独立的联邦法院系统,而各州都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体系,其联邦法院是作为各类法院的最高法院来设立的,即每一类法院体系的最高一级都有一个联邦法院。通过这样的法院设置实现了联邦法院对各种法律问题的参与和控制,确保了对德国法律的一致解释和协调发展。另外,德国还设立的有权力极大的联邦宪法法院,其主要职能是解释联邦基本法,维护联邦基本法的权威,这对于德国法制的统一意义重大。可以说,联邦法院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为德国的联邦制的成功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持和基本的法律保障。
与联邦制国家相比,我们这个单一制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则缺少基本的认识,对司法权的健全和司法权作用正常发挥的深远意义缺少富有远见的思考和充分的重视。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基本区别来看,单一制的国家机构形式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该更有优势。因为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地方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予,单一制国家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地方权力的分享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法院的设置以及审级制度的安排上缺少应有的考虑,造成了司法权易于地方化的倾向。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现行司法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司法人员的任免上看,我们很难将现行的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界定为‘国家的’司法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 [31]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博弈过程中,不少地方将司法审判作为纯粹的地方事务,肆意的加以攫取,一些仓促出台的改革措施则更容易加剧“地方势力的割据”。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着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畸变,妨碍法制的统一,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法院权威的确立,进而导致人们对法律信心的缺失并最终影响宪政秩序的实现。
其次,司法改革具有层次性的差别,特别是要区分结构性的司法改革和程序性的司法改革,对于不同层次的司法改革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
什么层次和性质的改革是可以由各地实验的;什么层次和性质的改革是可以由司法机关单独完成的;什么层次的改革是局部的,什么层次的改革是全局性的;什么样的改革是一般的诉讼问题,什么样的改革需要寻求宪法的支撑。事实上,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司法改革的很多问题涉及到我国重要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比如法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法院司法审查范围和深度问题的背后涉及到我国宪政体制的完善,决不是司法机关自身和各级地方法院就能够完成的,有的问题的解决甚至需要通过修改宪法才能实现。这些属于结构性司法改革的问题如果由司法机关自己来单独决定或任由各地方随便实践,那和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相悖离:一方面,宪法的至上性、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将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这样的司法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而这对于法治的实现来说是不可弥补的硬伤。法国在20世纪末启动的司法改革就是一例,其第一项举措就是寻求宪法支持,通过修宪以实现其关于改革最高司法会议的方案,然后通过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以实现对其他有关制度的调整。司法改革和其他的改革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其方式的特殊性,因为司法改革过程本身就是对法治的塑造和培养的过程,所以司法改革必须要用符合法治理念和原则的方式来进行。再看英国正在进行的宪法改革,包括贵族院的角色和职能的确定,下放权力,制定《人权法案》等,而法院的司法权特别是贵族院所扮演的司法角色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其中包括法院的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和议会、政府的关系,一个新的最高法院的设立的可能性,等等。2003年12月,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法律大臣⑤的职位被取消,这是为解决英国宪政体制下的大法官角色的复杂性难题所做必要的准备。这样,英国议会上院议长不再由大法官兼任,而是由议会独立任命,从此与司法体系无关。司法事务将由新设立的宪法事务部负责,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官也将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任命,而且还将酝酿成立最高法院。从英国的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发现,其司法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宪法改革有机组成部分,其司法改革是在宪法改革的框架下展开的。而我们却总是容易在宪法框架外去谈司法改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对司法权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我们对司法改革的层次和性质没有做出区分。
最后,司法改革的展开关系到法治建设的全局,其严肃性和整体性要求我们应该以审慎、保守和渐进的方式来推动,其本身的效果也需要充分的时间来显现。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实施的司法改革相比,我们对司法改革本身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和分析选择。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国家的司法改革是在充分酝酿,广泛参与,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司法改革决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的局部的变动而是涉及到整个法律运作系统的重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司法改革决不应该像决定“自留地”里种什么庄稼那样简单,而应该从整体上进行考虑和筹划。比如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行的司法改革,当时英国官方和民间成立了许多专门研究法律改革问题的机构,议会设立的法律委员会以及皇家法律特别委员会曾专门研究一些问题,提出报告,进而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各种公民私人法律改革团体也采用游说议会、利用媒体等策略影响司法改革。英国对司法改革的审慎态度和严谨做法,以及其对改革方案的选择为其他国家的司法改革提供了榜样。俄罗斯在20世纪末的司法改革则首先由其最高苏维埃通过《司法改革构想》作为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确立改革的目标:树立法律权威,确保公民权利、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在改革进行期间,俄罗斯曾经和一些国家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了对话和交流联系,并成立由联邦法院和行政机关、著名学者、法学家以及学术团体领导人组成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在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总检察院和律师协会等参与下开展工作,以促进司法改革逐步的向深入发展。[32](P68)相对而言,我们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性和意义之重大缺少充分的认识,因此,我们的司法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这种慎重和理性。
特别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们对法治的实现有一种“大干快上”的激情。在这种状态下,法治的理想的实现幻化成为一种日思夜想的期盼。曾几何时,司法改革成为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一个时髦的话题,大家张口“司法腐败”,闭口“司法专横”,各个方面都在给司法改革开“药方”。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冷静思考,慎重抉择,而是盲目实验,匆忙决策,则无疑是饮鸩止渴,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南辕北辙,也许我们的初衷是实现宪政,而最终则是离宪政的目标越来越远。我们必须铭记并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宪政是理性的事业,它需要一代代人对宪政的认同和不懈的努力,热切的呼唤和梦寐以求都不能代替宪政实践的积淀和历史自身的节奏!宪政在其发展的初期是很脆弱的,仓促之间出台的不成熟的措施往往会导致前功尽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盲动和狂热所造成的悲剧已经数不胜数。罗马建成决非一日之功,我们坚信法治和宪政秩序在中国一定会最终实现,但其过程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因此,对于司法改革我们需要审慎行事,我们应该选择有利的时机在那些已经比较成熟的环节进行突破和完善,对于那些既缺少必要的认识又没有充分的把握的环节则应该以充分的耐心。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宽松的制度空间和充分时间准备,更需要丰富的司法实践的积淀。
收稿日期:2006-11-06
注释:
①沃伦大法官在判决词中宣布:执法人员应该使用下列的事先警告来及时有效地提醒犯罪嫌疑人所应该拥有的权利和应该注意的事项:(1)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2)你所讲的任何话都有可能在法庭审判中被用作不利于你的证据;(3)你有权寻求律师的帮助,并要求在被审讯时有律师在场;(4)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政府可以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这些警告词即著名的“米兰达规则”。
②联邦德国于1972年和民主德国签署基本关系条约,国会于1973年6月以法律批准了该条约。该条约内容主要为:绝对尊重彼此领土之完整;两国主权之行使限于其领土范围之内,互相尊重彼此就其国内及国外事务之独立性与自主性。巴伐利亚邦政府认为,这一条约违反了维护德国国家完整以及宪法上统一之要求,加深了两德之间既存之隔离状态,并且使民主德国的人民无法受到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对于德国人民之保护养育义务,因此根据基本法第9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请求联邦宪法法院确认批准该条约的法律违反基本法。
③1947年5月,日本组成了以社会党为主导的片山哲内阁,平野力三被任命为农业大臣。由于平野在二战时是皇道会的骨干,其任职一事引发争议,后经过一番曲折,平野被开除。但他对此不服,并以首相为被告提起了请求确认首相决定无效的诉讼,并合并提出请求保全现有地位的假处分申请。东京地方法院在1948年2月作出了“停止该指令发生效力”的假处分决定。盟军司令部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其判决中撤消了东京法院的假处分,驳回了原告的假处分请求。
④1952年,吉田内阁解散众议院引发诉讼。在诉讼中原告主张这次解散违反了宪法第7条所规定的条件因而是无效的,所以其仍然应该具有众议员的身份,因而请求日本政府给付其议员工资。转引自[日]宫择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521-522页。
⑤英国的大法官亦即法律大臣,早在公元605年即开始设立,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是英国政府内历史最悠久的职位。大法官位高权重,不仅是全国司法界领袖,而且是内阁部长。按照英国的传统,议会上院议长也由大法官兼任。多年来,不少人对大法官一人身兼立法和司法双重要职多有质疑,他们认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像英国这样的情况绝对是落后于时代的。
标签: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法院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