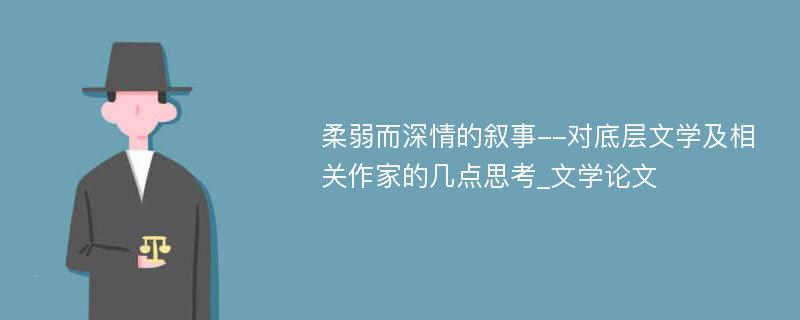
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乏力论文,底层论文,温情论文,几点思考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暴力、血腥、冷漠、虚无感、颓废感等叙事元素,在当代文学中似乎已经有了大大的收敛,与此同时,涌现了一批充满热情、富于诗意并且饱含悲悯情怀的文学写作潮流,尤以“底层文学”为最甚。然而,这些作品一旦合起来,在某一段文学史的大格局观察,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角度大同小异的叙事选择,马上就会映照出相同时代趋于强势话语的某种同一性趣味来。不妨以刚揭晓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若干小说为主,看一看这些同一性的趣味到底是些什么。
肯定诗意,也要看见主体性的乏力
底层文学不仅有力地改变着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结构的重新配置,而且也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扭转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既注重了底层者个体相当不堪和不得圆满的一面,也关注了个体内心世界油然而有的安详、宁静、爱意和善良等核心生命体验,以及美好的理想信仰。底层叙事虽可能肇始于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然而最终努力接通人类共性价值的诉诸,甚至怎样褒扬都似乎不过分。可是,由人的精神问题转向人的文化属性问题,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思想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恐怕是底层文学不能不警惕的一个价值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把民间视角变成民俗文化意义上的诗意呈现。
刘庆邦的多数短篇小说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在我的阅读视野内,他这方面题材的小说一经出炉,就马上被选刊看中。这至少说明,民俗文化内容他了解得多并且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这类小说可能更与以选刊为代表的某种文学标准有关。当甜腻的趣味,温软的抒情和内敛的私人意绪走俏的时候,底层文学或许就走向了它本意的反面。
比如他曾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鞋》,故事主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大体结构是《人生》中刘巧珍和高加林的翻版,即最终因为男青年的“进步”而与女青年在文化上拉开距离的恋爱悲剧。刘庆邦的着力点在“鞋”上,选鞋样、呵护鞋底、精心纳鞋底的过程,就是女孩子干净、纯朴和对他人世界不无天真的理解过程。注视人的单纯、逼视人简单的一面,这在人性越来越欲望化,越来越复杂难辨的今天的确值得一再强调并且给予充分肯定。但随之而来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单纯的土壤究竟是什么?结合刘庆邦为数不少的篇目会发现,刘庆邦的问题不只是重复自己,比如故事模式的重复,对人看法的重复等等,而且他是过于信赖民俗文化对人的发现了。《鞋》中的“鞋”实际上充当的是过去农耕文明的一个特定符号,也就是说,女孩子天真、纯朴、善良只能在既定的民俗文化内部是合理的,一旦走出这个圈子,离开以民间的名义定位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一切都将面临着打破。那么,女孩子的人性问题恐怕就要重新调整。这表明,刘庆邦的诗意、爱意、纯真其实是以从现实中撤退为代价的。《响器》中高妮对美的追随,《春天的仪式》中星采对“梦”的坚守,等等,几乎都无法把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尤其往往受外力作用的他者世界纳入其中。民俗文化视野中的单纯和简单不等于现实的残酷和无奈从此就消失了,情况可能是被遮蔽了。这里,刘庆邦利用民间已有的送葬仪式、布鞋情结,承载了人物传统的生命形式——这些深入其中的人物命运,只能在给定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具有悲剧性,无法离开那个文化土壤而存活。这也说明,民俗文化它代表民间社会价值取向时是有局限的,至少人物的深度还不能放置到现实中去一再拷问。这是把民俗文化秩序等同于传统的局限。它只能让思想顺延和臣服,而不能使思想具有“否定”的功能。因此,这类小说,它企图创造的正面肯定性形象除了提供回忆和伤感,它的审美诉求就不会有力地撼动现实的深层结构。人们从过去寻求意义,也总是会在对过去意义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义。这种常常处在意义与放弃意义之间的徘徊状态,也是众多作家退回到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困厄。只表明他们寻找自己意义的乏力,而不能说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新意义。进城农民的书写,走向另一个写作诉求,即他们需要求证底层者被迫碰到的“现代性”问题。这在本质上与退回到民俗文化没什么不同,都描写了当代中国底层者的尴尬与忙乱,或者宁静与自闭。
从这个角度,《吉祥如意》完全可以看做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产物。不同的是郭文斌知道儿童视角的局限,他也清楚完全地沉浸到封闭的民俗文化秩序当中对小说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吉祥如意》就基本上是在伤感而不失欢愉,怀旧而不忘祝福,凄怆而不失美丽,匮乏而饱含善意的抒情诗调子中,给即将面临危机的生命,给正在遭受困厄的情感,给已经囚禁了自由的人们,用心灵的温暖吼出来的赞歌。作者在末尾特意注明的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2003年端午(非典时期)草于鲁院”、“2006-7-26改定”。其用意,我的理解主要是包含了这样的意思:提醒人们,在平安的日子里不要对这个本来高贵的“吉祥如意”表现得过于麻木。面对突然降临的天灾——祝福吧!面对人祸——那些提防的眼神,那些恐惧的战栗,祝福吧!于是,小说中就出现了传说中能通血脉、能驱除瘟疫的艾草,就出现了童心透明的五月和六月。他们相互传递着艾香,他们相互传达着善良。然而,在更高的视界来看,即离开了孩子的领受能力和种种仪式制造的自洽氛围,沉重的生活是否还会节日般归来?
诗意、美好甚至甜美的确是《鞋》和《吉祥如意》的共同特点,但当我们把它们赖以赋形的美学形式——仪式般的民间文化模式去掉,让它们的人物走进当下的现实,女孩子还有心思耗费几乎全部的精神把玩一双在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鞋吗?走出童男童女期的五月和六月还会被艾草的芳香陶醉得不辨姐弟界限吗?也就是《鞋》的诗意,是以时间上的距离,造成了人们对美的追忆;《吉祥如意》以心理上的反差,还给人们心理上的补偿。放大了看,赋形于民俗文化形式的小说,之所以能给人一种情感上的震撼(当然,震撼是这类小说毋庸置疑的美学贡献),是因为人们在接受的时候已经十分明白它无力担当“现在”,它仅仅属于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与此在的命运、生存、冲突、变局毫不搭界的历史遗产,甚至一定程度上恐怕是以故事的形式充当着人们一再追思的传统文化模型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把本来有价值的民间视角转换成民俗文化本身,才使得来自历史的、时代的、现实的和各种意识形态网络中的人在文化的意义上寿终正寝了。因此,他们的诗学观都是以逃避的形式,封闭的事相,民俗文化的母题麻痹了人们对当下现实的自主判断。也不妨说,这类文学因放大了属性特征明显的文化,最终放弃了对人的追问。它们是说事的文学,而不是写人的文学。这也就部分地回答了当下现实为什么无法甜美的原因。因为一旦触及到当下现实的人,就必然要首先进入弱势者的生存世界,或者所谓优越者的存在世界。不管是底层者的物质问题,还是优越者的无聊问题,都不可能使一个有思想见地的写作者盲目乐观。
“温情”不只是技法,更是生命形式
“底层叙事”进入到一定阶段,当它们进入底层世界的方法论显得依然呆板,无法给人们提供足够多样的故事的时候,也即在当初开辟的伦理道德内容无法进入广阔的社会时代核心的时候,底层叙事中的“苦难”就只好蜕变成“苦难美学”——一种想方设法让苦难者在理想的层面完成人格的仪式活动。所以从现实的批判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温情叙事。温情叙事是底层叙事的高级形式。如果“在路上”的农民是写实主义,打工妹的城市爱情就是审美主义。从打工妹的私人空间打入城市的腹地,从凶残者或落难者的情感秘密讨要人性的健全,是我看到的近年来形成气候的一种格式化人文关怀。
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若按照他的自解,应该是表现几个无助者的孤独,特别是哑女的心灵“失语”感。当然这篇小说给人更大的冲击或许并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事象,虽然能否表现出弱势者的精神问题似乎成了新世纪以来作家们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田耳做出自己的申明即便有些多余,但也确实说明了当下语境中作家创作潜意识里靠拢某种风向的不自由状态。我以为《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灼人力量或许在反映公安生活方面,通过展示老公安老黄的郁郁寡欢,公安生活内部的诸种腐朽、不作为以及滥用权力的本相被清楚地推到了读者面前,“他者”世界肯定压倒了个体精神生活的分量。结合田耳其他的小说,通过类型人物的塑造,对“合理化”生存哲学的深入揭示,的确显示了他不凡的问题意识,在同龄人中他理应是佼佼者。这里暂且认可作者的原始意图,我们看一看作者是怎样呈现哑女的心灵秘密的。作者正是沿着“我们习惯上认为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可能很规矩,其实是个误区”的思维写哑女的。这样,哑女的劣迹就正常展开了,她与杀人犯厮混,杀人犯就是后来杀他哥哥的凶手,这是被同情者的恶;凶残者的善或者人性中的“温暖”也是以这个逻辑展开的,行刑之前对哑女的爱的表达和与哑女约定的大年夜的张灯结彩等等“嘱托”,是恶者的善。单独看,如此情节不仅可能而且是合人性的。然而,把不同作家表达这一人文意义的内容放置到一起,问题就显出了几分蹊跷。
《喊山》(中篇小说)的作者葛水平表达人性温暖的方式也如此,光棍韩冲与有夫之妇私通、名声搞坏无法娶上媳妇;杀人在逃犯、讨饭者腊宏强娶红霞为妻,红霞过着噩梦般的日子,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慢慢变成了“失语”的哑巴;韩冲、腊宏的这些行为体现的是底层者的“恶”。腊宏被韩冲炸獾时误炸致死,韩冲在处理腊宏丧事上的人情味和照料红霞母子三人的体贴入微、百般良善,是恶者的悲悯。的确,作家用心良苦想要表达的人性的复杂和丰富肯定有理论的强大支持,要体现的悲悯意识和人文情怀也毋庸置疑,要给文学提供正面肯定性价值的文学精神更无须否定。我表示质疑的是,非得通过偶然性来成全人性温暖的做法,恐怕只能说明作家对意义的不诚实,生活积淀的匮乏也同时成了大问题。
段崇轩对葛水平的创作有整体的研究,他用“强化小说的‘戏剧性’”①来解释葛氏小说的成熟技法。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偶发事件,动用戏剧性冲突,文学史上也不鲜见,决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为了进一步纠正我判断的片面性,当我找来近年来频频亮相于《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大刊,被评论界誉为“一匹黑马”、“中国文坛最抢眼的作家”、“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甚至把2004年的小说创作称为“葛水平年”的葛水平的其他作品,如《甩鞭》、《黑口》、《天殇》、《狗狗狗》。细读后还是觉得“戏剧性”并非葛水平的“技法”,而是其创作时善用、也用得几乎天衣无缝的精神“投机”。譬如《甩鞭》,王引兰先嫁给地主麻五,结果麻五在土改批斗中被“坠蛋”而死,后嫁给贫苦农民李三有,李又在一次干活时“坠崖”而亡。这很吊人胃口,有凶手吗?凶手是谁?包袱抖完结果出来了,铁孩机关算尽为的就是要成全他的爱,得到王引兰。作者用两条人命换来的就是这个蓦然回首的“爱”,“死——情”是葛水平追寻温暖或者残酷的叙事模式。再回到《喊山》,如果把情节梳理一下,仍然是以无辜生命换有限真情的技术。杀人逃犯腊宏如果不被炸死,他手里捏着的孩子平常喜欢吃的野酸枣就不会有人发现,他就肯定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冷血动物。包括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同样是非得让哑女变坏才看出其孤独的内心世界。说葛水平在技术上处理得天衣无缝,只是指她能够持续地调换读者的胃口,要么让人物死于非命,要么死于暗算,但死者和凶手毫无疑问都是真正的弱势者。从这个角度看,段崇轩说的“葛水平笔下没有单纯的坏人”真是一语中的。只是他在褒扬葛氏小说人物精神形象丰富的同时并没有看破里面的玄机,因为作为批评家,段崇轩对人性复杂的渴望程度并不比葛水平弱。
青年批评家李美皆给她的评论集起名为“最易搅浑的是我们的心”,实在有深意。征服人心的温暖、人性的复杂、价值的肯定性或否定性,不是拼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经历出来的。它呼唤的是耐心的体验和诚实的感受。
文学怎样观照“他们”及时代的尖锐问题
面向大多数的写作,就其本质而言,不应该理解为对个性的取消,对内心空间的挤对。这种文学最终所能达到的境界以及产生的效应,理应是一种坚定的文化行为,当然是马修·阿诺德意义上的“文化”。阿诺德说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并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②。读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篇)和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短篇),首先感受到的是作家在探寻什么在追寻什么。阅读的轻松使你入迷,掩卷的沉思促你联想。沉陷于她们的小说世界,思考最多的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个人性”、“内心化”甚至于“文学性”等一系列被视为重要发现的理论,从这些理论出发,这两部小说还留有巨大的阐释余地。至少,这两部小说虽然都从个体的内心生活切入,主题上都深关个人意义上的精神性问题,但最终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牵动了时代的尖锐矛盾和人类如何走出自我意识囿限的可能性。也就是它们最后达到的品质,不是提供给人们一种圆熟的结构技法,亦不是实践理论批评界一嘘三叹的某几套文学标准。她们的小说可能是聊天交流,可能是沟通对话,可能是假设反证,然而,本意却是现实如何可能或者不可能——不能不承认,胸中倘若没有时代的整体图景,个体领域的诸种难堪将何以有效克服。所以,这类小说推到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个摇头晃脑的审美问题,更是重新打量世界的认识论问题。
李建军说,“迟子建没有停留在过度个人化的叙事语境里,而是极大地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深入而真实地叙写了乌塘镇可怕的生存现实,从而使她的这部小说实实在在地成了‘底层叙事’。”又说“优雅的浪漫,正是这种在我们的文学中不复见久矣的精神,赋予了迟子建的小说以感人的力量!丰富的诗意,正是这种在我们的文学叙事中严重匮乏的品质,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成为一首庄严的安魂曲!”③。“实实在在地成了‘底层叙事”’的确是重要发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那种感人精神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在“怎么写”上迟子建袒露了她的“笨拙”,像她自己申明的那样是怀着一份“私心”来写的,“想给自己的伤痛找一个排遣的出口”④。但这种“私心”好像非但没被消除,反而更加沉重了,“我找到了吗?”现实中丈夫的突然离去,给“我”造成了不可抹去的严重创伤,这需要找一个适当的渠道把它宣泄掉,然而在乌塘镇,“我”很快被更加不幸者淹没了。苍凉的“鬼”故事,离奇的“嫁死的”,陈绍纯悲凉的歌声,蒋百嫂的怕黑,就算喜剧色彩的独臂人父子,你能道尽孩子幼稚的魔术表演背后的辛酸吗?“我”就是以采访者、民歌搜集者的身份介入到那个世界的,“我”不忘自我伤痛的掺杂着自诉、倾诉的讲述,最终被他人更加的不幸、更加的不测、更加的无助和无望融化了,收编了,稀释了。“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从自我到他者,从倾诉到倾听,从哀怜到哀鸣,从委屈到渺小,小小自我在无数次的多层面的他者世界的比照中实现了真正的超越。这部小说的精神气质,就是作家主体的精神气质,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强劲的观照力和出示精神品质的实践方式一再表明,人是由渺小长大的,人也只能在体恤他人中才能精神成人。
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成长的小说。那么,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则是通过乡下人王才王小才父子认识的不断打开,把想象变成现实的过程。一直以来,面对底层、面对城/乡,我们已经炼制成了一个权威的审视标准,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学叙事模式。有人通过打工妹别有用意的爱情意图发现了乡下人进城后身份确认的困难,有人给“在路上”的农民身上加上了过重的文化砝码。但“城市化”总还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会被“化”掉,对于这部分人而言,“留守”的孤独是事实,无效的折腾、无奈的呼号也是现实。然而,笔者敢于肯定地说,这类人群一定还有别的生活。比如理想,比如梦——我以为,不关注到这类人群的这些生活内容,打工妹的情感秘密、农民的进城,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打工妹和农民处境的简化。
一个城里人随手记上去的数字牵引着王氏一家进了城,并且住了下来,的确荒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昂贵的香薰精油价格对识字不多的人的吸引不仅可能而且真实。我自己也有过漫长的农村生活经历,最初我好好学习的动力就是有一天能够用精美的钢笔写字,这奇怪吗?范小青以平实的语言、语重心长的叙述、全知的视角,在亲历者亲历的眼里,在以己推人的联想里,呈现的就是我们意识中贫瘠、落后而又模糊的西部农村具象。范小青的主人公蒋自清丢失的那个账本对蒋来说已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他的一种心理需求。所以他才会千方百计地去找它,这样,他便成了王氏一家现实的见证者:道路的如何遥远,生活的如何贫苦,教育条件的如何不堪,等等。这时候,范小青面对王氏一家其实并没有背过脸去,只不过,她以蒋自清寻账本的亲历客观地展现了农村社会状况,体现了范小青真诚的写作态度。
《城乡简史》在一般的读者那里恐怕很容易被理解成“喜剧”,因为像王才这样的底层者,在一批批“底层叙事”的不无异化的描述中已经被脸谱化了。他们就该是灰头土脸、脑袋死板、表情单调、爱情卑贱、安贫守穷的模样。三流泡沫剧和晚报新闻十分热衷的是城乡之间那种尖锐的对抗、你死我活的仇恨,因为这样设计方便出戏。文学其实就是把这个被反复搜刮的苍白大地当做了它赖以发挥的“现实”:一个个滥情发廊女的眼神都带着某种政治攻势的意味,打工妹一次真诚的情感泄漏似乎都包含着巨大的身份危机,甚至为了成全某个空洞的理论、落实某个语焉不详的精神大词,不惜把认识城乡世界的切入口对准活生生的生命。哑巴所宣扬的失语程度,死亡所彰显的温情分量,其实暴露的恰好是作家的残忍和不人道以及浅陋。如此“底层叙事”看得多了,不妨说《城乡简史》是一部合格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其中揭示出的尖锐的时代问题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部以弱者生命为赌注的所谓“悲剧”小说。
本来千里迢迢去找的就是账本,为什么蒋自清后来又放弃了呢?原来当他寻寻觅觅终于摸到王才家门前时,王才门上贴的留言条打动了他。那个条子上特地注明自己借别人的钱一定要加倍偿还,但别人欠的债一笔勾销。“看到‘一笔勾销’这四个字的时候,他的心情忽然就开朗起来,所有的疙疙瘩瘩,似乎一瞬间就被勾销掉了,他彻底地丢掉了账本,也丢掉了神魂颠倒坐卧不宁的日子。”农民的大气究竟感化了城市人。范小青似乎在强调,城乡之间的精神沟通是可能的,相互间身份的确认、文化差异的缩小需要双方的用力才行。但前提必须是相互进入对方的世界,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就像小说中的蒋自清与王才做到的那样。在这个基础上,不管作家投注多少温暖的同情或道德的审判,还是文化的思索,它都是可信的并且能从平淡中震撼人心的。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的作家心里可能都装着不同的底层,也都有选择怎样写的自由。但要论到境界,论到文品和人品的诚实程度,路子似乎很窄也很难,那就是义无反顾地了解生活,心无旁骛地耐心体验生活,除此别无他途。从上述有限的作品我看到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底层思维是,理念很到位,就是要诗意、温情、温暖,但文学的实践却往往是通过对已有文化模式的封闭型缅怀,或者把解决的办法寄托在一个非常态的偶然性、戏剧性冲突上,以至于不无端地搭上几条无辜生命,那个所要的“精神”、“意义”就不足以明确。这是一种严重的写作误区,它使文学变得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可能有结构、有技术,写得也很巧,更有理论批评家想要的标准,但无论如何没有思想的分量和审美的冲击力以及现实的观照力。
注释:
①段崇轩:《打开小说的“可能”之门——评青年作家葛水平的小说创作》,见《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②[英]马修·阿诺德著,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第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③李建军:《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关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阅读报告》,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
④迟子建:《获奖感言:我与“他们”》,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