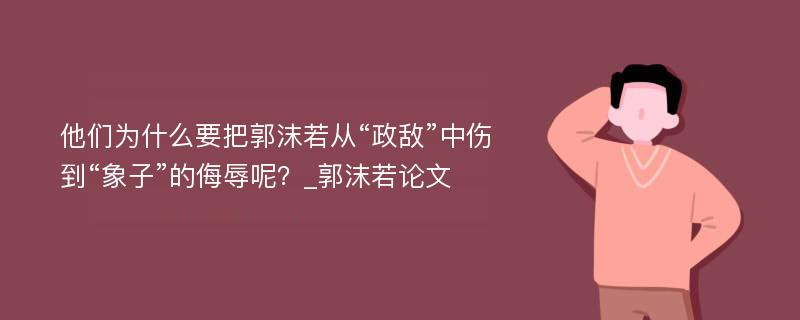
他们为什么要丑化郭沫若——从“政敌”的污蔑说到“乡梓”的辱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政敌论文,说到论文,乡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巨大成就和多方面的贡献,他对祖国、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及他那“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注: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1978年6月18 ),《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第2页。)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既有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科学论断,也得到了如茅盾、巴金、曹禺、夏衍、周谷城、侯外庐、周培源、华罗庚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的高度评价(注:参见《悼念郭老》一书。),而他生前身后以多种文字出版的《郭沫若文集》、《郭沫若选集》、《郭沫若全集》等作品,以及多种研究著作的陆续问世,都已经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注: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1978年6月18),《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第3页。)
如同任何杰出人物都会遭到攻讦一样,郭沫若也不断遭到攻击;特别是在他逝世之后的二十余年间,不仅攻击范围扩大、攻击手法恶劣,而且攻击者也由海外的“政敌”影响到内地学子:他们或蓄意栽脏或旁敲侧击,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或借口“反思”,大肆诋毁,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很值得警惕的。因为“政敌”不只是“论敌”,他们千方百计丑化郭沫若,不只是妄图推倒郭沫若个人,矛头是直指“中共官方学术界”的(注:金达凯《郭沫若总论·自序》。),所谓“揭露了郭沫若的脸谱,也就等于揭穿共党控制大陆文坛”(注:金达凯《郭沫若总论·自序》。),险恶之心何其毒也,也是完全徒劳的!本文一方面要揭露这些“政敌”的脸谱,另一方面也要分析某些内地学人“鹦鹉学舌”的危害,再一次用铁的事实来维护郭沫若的真实形象,粉碎“政敌”们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
一
要扳倒一个人,最狠毒的方法莫过于在人格、品质方面造谣惑众,予以根本否定。丑化郭沫若,最先便是污蔑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54年8、9月间,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6、7、8期连续刊载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士、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的余英时所写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诬称郭著“《十批判书》的确是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胡说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注:转引自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公正评价郭沫若》(曹剑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70页。)。尽管这些话危言耸听,但由于当时余氏既不是大学教授,更不是什么“院士”,不过是个在香港“新严研究所”的进修生,故未能引起多少反响。但余氏对此并未死心,时隔37年,又借纪念恩师钱穆先生塞进《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出版)(注:此次入书,余英时删去原来的正题,以原副题为正题,并在文字上也作了个别删改。),并在《跋》中再次宣称:“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又说“这一重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1992年余氏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继续诬蔑《十批判书》不但抄袭,而用抄袭得十分匆促而粗糙”,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年,余氏再一次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将1991年写的《跋》作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跋语一”,将1992年发表的《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作为“跋语二”一并置于《互校记》之后。
余英时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兜售他的货色,变本加厉地污蔑郭沫若,固然与他对郭沫若个人“有偏见”有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和郭沫若在政治上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上”(注:转引自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公正评价郭沫若》(曹剑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0页。)(着重点为引者加);换言之,余氏的所作所为,“说明它完全是在学术外衣掩盖下的一种敌对政治情绪的发泄”!(注: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公正评价郭沫若》第91页。)这除了已有海内外学者对余氏的造谣污蔑作了逐一的批驳外,另有林康先生《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之一、之二)的无情揭露。从林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余英时如何在其近著中与“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一唱一和,将中国人民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诬蔑为“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胡说“‘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概念”,恶毒攻击“中共所依赖的骨干分子主要便是所谓‘痞子’、‘无赖’、‘光棍’、‘流氓’之流”,是“靠民族主义起家,趁民族危机夺权”,而这个“民族主义”又是“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进而宣称“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这哪里是一个“中国史专家”说的话呢?更像出自“台独”分子之口啊!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即可进一步明白余英时为何一再污蔑郭沫若这位学者、作家同时又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注: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1978年6月18), 《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第1页。)的真实用心了!
由于“在政治上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上”,在台湾还出版过《郭沫若批判》、《郭沫若总论》一类“专著”(注:《郭沫若批判》系1954年由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史剑”,实为原《和平日报》总编辑马彬。《郭沫若总论》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作者金达凯。),对郭沫若进行了全面的人生攻击,后者还专门加上副标题“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以昭示其学术外衣下的政治宣传目的。前引“揭露了郭沫若的脸谱,也就等于揭穿共党控制大陆文坛”的话就是出自本书《自序》。此书还胡说郭沫若“投机”、“好色”、“献媚邀宠”、“刻薄成性”,是“文坛中品格最坏的不学无术者”,连郭沫若改医从文也被诬为是“军医学校的逃兵”、“在成绩上等于交了白卷”,又污蔑郭沫若“借《蔡文姬》的剧本替曹操翻案,来美化毛泽东的形象”,出版《李白与杜甫》是“迎合毛泽东好恶,违心之论”,还直接引用毛泽东1944年8月21日致郭沫若肯定《甲申三百年祭》的信, 污蔑郭沫若写此文是“影射艰苦抗战的中华民国,企图影响全国军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等等,对中国共产党则直接诬为“叛乱者”、“伪”政权。与余英时稍许不同的是,《郭沫若总论》的作者金达凯本身就是专搞政治的老手,不仅担任过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及系主任,又出版过《论中共文艺政策及其活动》、《论大陆高等教育》、《左翼文学的衰亡》、《中共思想改造》、《中共文化政策之研究》、《中共统战策略研究》等著作,可见他对郭沫若的全面攻击与丑化,“是在与政治敌人进行交火,根本不是学术评论,只能得出金达凯是个仇视共产党者的结论”!(注:翟清福《无法回避的争论——评〈郭沫若总论〉》,《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1期。)
老实说,余、金等人的诬说由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十分明显,本不值一驳,但某此大陆学人却不仅没有唾弃这些宣传,反而鹦鹉学舌似地跟着叫骂,例如署名“安迪”、“丁东”的人就分别在《一段公案》、《学术不能承受之轮》二文中诬称郭沫若“抄袭”了钱穆著作。反过来,某些大陆学者的臆断、瞎说又常常成为海外“政敌”们攻击郭沫若的材料,如说《甲申三百年祭》“学风不正”(注:杜渐《姚雪垠先生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转引自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第87页。), 此文是由于“某一领导人物的一句话”才“变成了‘权威’著作”(注: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文汇月刊》1981年第1—3期。);说郭沫若在“揣摩”毛泽东《淘淘沙·北戴河》一词后,才写出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紧接着《蔡文姬》也就粉墨登场了”(注:转引自翟清福《无法回避的争论》,原文出自1982年第2期所刊《我道曹公差矣》文。); 说《李白与杜甫》“贬低杜甫而抬高李白”,“原来因为某个领导人谈过他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注:张亦驰《杜甫“冤案”》,《北京晚报》1980年9月6日。)等等,都在《郭沫若总论》一书中有重复的宣传。这也许是这些大陆作者始料未及的事,但自己的“论敌”之言频频为“政敌”所用,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和真正的反思么!
二
可是,我们学界总有一些人喜欢利用被他们片面理解了的“学校自由”、“人格独立”一类主张去评判他人,不问青红皂白,不从实际出发,胡乱臧否一气,如连郭沫若遗嘱死后将骨灰洒在大寨也被说成是“对毛泽东的驯服”(注:廖明春《毛泽东郭沫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唱和诗索引》,《反思郭沫若》(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4页)。),有的甚至只是气急败坏地乱骂一通了事, 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弄清事实的真相,一任自己“自由”地胡说八道,或者挖空心思,专门选择一些于“我”有利、大唱反调的文章汇编成书,错上加错地传播不实之词,造成恶劣影响。1998后出版,署名“丁东”所编的《反思郭沫若》(以下简称《反思》)就是其中最“毒”的一种。说它“毒”,首先是因为编者胆大妄为,既敢编入连作者自己也感到已被他人批驳得哑口无言而未再置一词的错误文章,又敢置国家有关政策法律予不顾,搜罗对已被人民法院判决为败诉的人有利的文章在书中“第一次发表”(见本书《后记》)。例如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连同其二则“跋语”全部收录,并作为“学术存疑录”的首篇。前面已经揭露过余氏之作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而且是在1996年第3期的《中国史研究》上就发表过翟清福、 耿清珩合写的长文《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通过作者逐一查对两书的引用的材料,不仅说明《互校记》论据史实、矛盾百出,而且证明余文是蓄意诬陷郭沫若,而余氏对此至今并未作出任何反映。那么《反思》在《后记》中标谤要“对郭沫若进行学术商榷”,为何不收录翟、耿二人展示“真相”的反驳文章呢?又如,“书信真伪辨”中的10篇文章,除了列在第一篇的《郭沫若与陈明远》全是吹捧陈明远其人、与“书信”真伪毫不搭边,其余几乎全是站在陈明远这一边,指证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书信是“真”;既然是真伪之“辨”,就应该将说明陈明远伪造、篡改郭沫若书信的文章同时录入,但编者不仅没有收入郭平英首先揭露陈明远的文章《陈明远与郭沫若书信往来质疑》(《文艺报》1996年5月10日), 就连已编入本书的几篇文章作为反驳对象的“论敌”文章(除郭平英文,主要还有载于1996年10月21日《中华读书报》的王戎笙《评陈明远》〈新潮〉一书及其他》、王廷芳《〈新潮〉作者到底是谁》,及王戎笙的《伪造、篡改,铁证如山》和《移花接木,是非终有明辨;续貂之尾,难免自取其辱》,此二文分别刊于1997年11月4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北京青年报》)也不编入,让读者如何去“辨”真伪呢?编者在《后记》中煞有介事地说“如果追求平衡,书势必太厚,定价太高,就增加了读者的负担”,那么请问: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真伪辨”与“反思郭沫若”有何关系,需要拿出近四个印张的篇幅来再印这些引导读者只信其“真”的文章——何况1997年6月1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就郭平英诉陈明远假冒郭沫若署名侵权案,作出陈明远败诉的终审判决(事实查明),在已公布的69封信中,1956年以前和1963年以后的信全系陈明远伪造,1956年至1963年的信中也大量是赝品,或是经过任意删改的半真半假的东西,为此陈明远须公开登报道歉。)!编者欲盖弥彰的表白,只能证明其为丑化郭沫若而脑汁绞尽、不遗余力;这样做,原来只因为“不止一位学者对郭老晚年的反思都以这些通信为依据”(《反思郭沫若·后记》(着重点为引者加),而“郭老晚年”又是“反思”者们攻击郭沫若最甚的时期啊!然而,这些信的真伪已由人民法院做了公正判决,编者继续借此为作伪者辩护,难道不是对国家法律的蔑视么!
说《反思》一书很“毒”,另一个原因便是它搜罗的“有关”的文章大多是九十年代以来丑化郭沫若最凶、手段也最狠的文章,这从书中所谓“反思群言堂”一辑可见一斑。先看陈明远怎么在《湖边散步谈郭沫若》的吧:除了拣出学界众人皆知的《三叶集》中郭沫若那些“自责文字”,便是“我每年的观察”结果,即郭沫若“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甚至从“郭沫若的表情(可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也使陈明远这个当年受到郭沫若特别关照的“小朋友”感到“60年代以后”郭沫若“不得开心颜”了。陈明远还说,郭沫若“到了后期,居高位,享厚禄,荣华富贵,不可一世,但是,孤独、忧郁、心烦意乱”。事实呢?一点没有,尽是想当然的瞎说!再来看看“丁东”其人的“高见”:他在《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中骂郭沫若“阿谀”毛泽东,接着便大引已由法院判明属伪造的1963年以后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断言“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又在《难以澄清的“谜团”》中不怀好意地散布郭沫若是“骗子”,别人写好文章“院长(按:指时任中国科学院长的郭沫若)要看,派人取走之后,却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了”,虽毫无证据,作者仍“相信她说的事不是空穴来风”。凡此种种,完全可以看出丁东“反思”郭沫若是假,传播污蔑、丑化郭沫若的谣言是真!辱骂郭沫若出语最刻毒的恐怕还是一个自称是郭沫若“乡梓”、署名为“余杰”的文章:《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此文不仅武断“1964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郭沫若已“退化到和毛和作旧诗的文学弄臣”,而且宣称“早在五四时代……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认为“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而魏连殳这个“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文中充斥着像“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写出《李白与杜甫》、“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一类毫无根据的臆断瞎说,连郭沫若作《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词,也被作者拿来大骂一通,说郭“骨子里依然是奴隶”,“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就连郭沫若生前被安排居住的处所,作者也用来辱骂奚落郭沫若,胡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和废墟之上的‘欢乐颂’”。总之,在这位“乡梓”眼中,郭沫若是“把文学和学术当作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任何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也不会说出这样的昏话!据说这个“余杰”曾做过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如此不顾事实、如此刻薄地辱骂早有公论的郭沫若,到底算是科学的“反思”,还是别有用心的攻击,该是一目了然的。《反思》还收了另一个四川“同乡”魏明伦的“自序”文章,骂郭沫若“拍“舵爷’马屁”,遗嘱将骨灰撒到“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注:魏明伦《〈巴山鬼话〉自序》,《反思郭沫若》第306页。 )。此人后来还在另一篇“序”文中用诸如“御猫”、“蜀犬”等更恶毒的语言辱骂郭沫若(注:魏明伦《天下四川人·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3 月版)。)。作为“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之一的魏明伦,前不久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进言”道:“文艺批评不是‘骂’,骂不能取代批评。有人一批评人,就痛打落水狗,不怀好意地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借骂名人炒作自己……”(注:刘琼、朱玉、王黎《把握良机,繁荣文艺》,上海《文学报》2000年3月9日的第一版。)用这段话来对照“丁东”、“余杰”等人,对照魏氏自己“批评”郭沫若的话,魏明伦委员说得是多么中肯啰!
三
从上面的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大陆学人丑化郭沫若与海外“政敌”敌视郭沫若,在方式上、用语上何其相似,尽管两者性质有所不同,但必须反思我们的立场和态度,绝不能使“自己”与“政敌”同流合污了!
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学术的“自由”、情神的“独立”。我们注意到,对郭沫若的“反思”者们在“反思”中特别热衷于谈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丁东在《反思》中收入的由他写的一篇长文中还专门照录了当年陈寅恪那封写给郭沫若、李四光拒任历史研究所长,主张“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不要学政治”、“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信(注:见《反思郭沫若》第239—240页。)。或者说,他们攻击、谩骂郭沫若,主要也认为郭是“独立人格的缺失”(注:见《反思郭沫若》第291页。),没有像他们所说的“从1949年开始, 30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注:转引自林贤治《读顾准》,《反思郭沫若》第290页。 )那样“独立”思考。有人竟然这样断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甚至敌视权力的”,因而郭沫若逝世后尽管“中共中央通过致悼词形式,再度宣告郭沫若为鲁迅之后的又一面伟大旗帜”,但“作为人格的典范,这个结论并没有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注:转引自林贤治《胡风集团案》,见《反思郭沫若》第51页。)。暂且不说这些奇谈怪论如何漏洞百出,我们只想问一句:难道与共产党执掌的人民政权保持“距离”、“甚至敌视”,就叫做“人格独立”吗?这是连陈寅恪先生也不会答应的事。在前面提到的那封“要为学术争自由”的信中,他同时就坚定地表示“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注:见《反思郭沫若》第239页。)!再说, 世上绝没有反社会的、不负任何责任的“独立”、“自由”,恰恰相反,“被注定是自由的人……他对世界和自己都是负责的”(注:萨特1975年11月10日答美国《新闻周报》记者问,转引自张金华、鲍宗豪《自由:追求与迷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1 1月版)第115页。)!连尼采也说:“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我责任的意志”(注:《尼采全集》第8卷第149页,转引自《自由:追求与迷误》第74页。)。而且除了社会性、阶级性,自由还要受法律、纪律、道德规范等多方面的约束,因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注:《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假借“反思”郭沫若实则把矛头指向现时“权力”,否定中共中央对郭沫若的正确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其立场已和诽谤、污蔑郭沫若的政敌靠近了,的确到了“反思”者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第二,评价人物必须力求最大限度的公正、全面,不能丧失良心。限于个人的条件,臧否人物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似不可能,但至少要尊重众所周知的事实,绝不可睁起眼睛说瞎说。例如说郭沫若“趋炎附势”,他在1927年“四·一二”惨案发生前夕拒绝蒋介石的高官引诱,写出了义正词严的讨蒋檄文,是何等勇敢不说, 就说“文革”中的1974年1月当回顶了张春桥对他在《十批判书》骂秦始皇的指责,2 月10日下午对江青登门威逼他写检查、写文章,批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即周恩来毫不理睬等表现,难道也叫“趋炎附势”!即使他写诗与毛泽东唱和,也不能这样贬斥,写诗纯属个人的创作自由,何况他并不只是与毛泽东一个人“和”过韵呢。什么事都有它产生的特定环境,不能用今天的主观猜测替代历史的具体事实。比如如何看待郭沫若在1976年写的诗词,就应仔细辩细。有人说那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糟糕至极”,为此“郭沫若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要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悲剧性的一页”(注:见《反思郭沫若》第43页。)。同一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五个月后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依然有不少标语口号式的内容”,“但是它确实集中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喊出了时代的心声”,艺术创造方面也“表现出诗人确实不愧为大手笔”,“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期数以万计的同类作品中,它无疑是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注:见《反思郭沫若》第44页。)。其实,前一首《水调歌头》中的一些“标语口号”当时是有特定的历史内容的,其“悲剧性”也不该算在郭沫若个人“政治生涯”的帐上。而如说创作《蔡文姬》、出版《李白与杜甫》等都是“迎合毛泽东”等无根无据的判词。“前期痛骂弄臣宋玉,后期则甘当宋玉,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注:见《反思郭沫若》第298页。 )所住王府花园也是“郭沫若致命的泥淖”(注:见《反思郭沫若》第283页。 )一类言过其实的评论,都不能说是令人信赖的意见,其结果也就只会令人一笑而已,作者们倒真是“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啊!
第三,最根本的还是要端正学风、做好人。如前所述,不少“反思”者都是以骂人为时髦的,除了无知、浅薄,学风不正,我们认为最要紧的还是骂人者们没有良好的人品。他们尽随意骂郭沫若这不是那不该,但他们没有事实依据的乱骂,本身就显示了他们人格的低下和卑琐,须知评论别人实则也是在“评论”自己哩!比如,我们在翻阅整本《反思郭沫若》时,固然对其中多篇文章中极为恶劣的骂语十分反感,但更可憎恶的还是“丁东”其人“编”出此书所显示出来的“人格形象”:比如“他为什么要选录这样一些文章?”、“他为什么明知已错还加倍犯错?”甚至连本书的“责任”编辑们,我们也有理由问一句:你们到底是依据什么出版“责任”出版这样的东西?当然,郭沫若不是完人,可以揭短可以批评,揭示他的“另一面”也是一种研究,但必须实事求是、主次分明,必须摒弃个人偏见,切忌人云亦云。对于某些人尤其年轻人,还有必要尽可能多读一点书,特别是那些已经批驳过错误观点且批驳得好的文章,专著无论如何是应该仔细读一读的,丰富的知识不仅是真的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也有助于提升自己治学的层次。例如,我们在“反思”郭沫若前,除了通读他的全部著作外,近期出版的《郭沫若评传》(秦川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郭沫若学术论辩》(王锦厚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版)、 《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以及《公正评价郭沫若》(曹剑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等书,都是不可不读的好书。
郁达夫在《怀鲁迅》中曾经这样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无论从哪个角度,郭沫若都是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做了重要贡献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虽然后人可以超越他,但他的著作、他的精神和他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确是不争的铁的事实,任何人企图予以否定,都无异于白日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