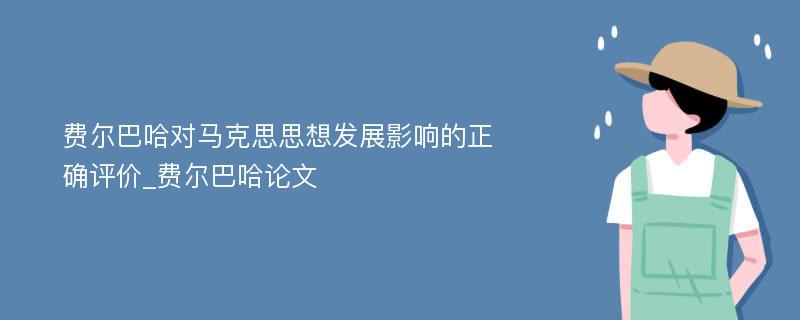
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马克思论文,正确论文,评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科尔纽、奥伊则尔曼和拉宾为代表的前苏东学者认为: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自然观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改造。从而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目前学术 界大都支持这一观点。这虽算不上错误,却极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马克思从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式的庸俗唯物主义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这既是对费尔巴哈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事实上,经过黑格尔 辩证法洗礼的费尔巴哈,其唯物主义不可能是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复辟,相反,把现 实的人作为哲学的基础,恢复了感性世界的权威,其人本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从而在逻辑意向上克服了英法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倾向。马克思也不是直接继承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是首先接受其人本学理论,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进行了进一 步的规定和说明,从而远远超出了人本学,建立了现代唯物主义。
一、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影响的反证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看,1837年夏,即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学习近一年后,参加 了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系统钻研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以及黑格尔著名弟子们 的著作,并同青年黑格尔派一起展开了反对宗教的哲学斗争。这一时期鲍威尔对他的影 响甚大。撰写于1838——1839年之交的《博士论文》,主要就是受到了布鲁诺·鲍威尔 和科本的“自我意识”哲学思想的影响,也运用了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 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根本上揭露了宗教和神学的虚幻,证明了只有人的意 识才具有最高的神性,从而为无神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也是借助于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发现伊壁鸠鲁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指出伊壁鸠鲁只知偶然不知必然,只知观念创 造世界、不知观念的界限等片面性,提出建立结构完备的自我意识哲学的主张。他批评 伊壁鸠鲁所追求的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认为应当追求定在中的自由,即追求社会生 活中各种现实的自由权利。此时费氏对马克思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作为哲学家的费 尔巴哈,马克思是了解的:其中《博士论文》中的一处,马克思直接从费氏的《近代哲 学史》中援引了伽桑狄对伊壁鸠鲁的评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23、27 1页)
马克思《博士论文》完成后的1842—1843年间,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 要》、《未来哲学原理》、《论哲学的开端》和《基督教的本质》(二版)等一批著作相 继出版,这时马克思才开始真正重视费尔巴哈,在若干观点上吸收了他的思想。但这种 影响并不象恩格斯后来(1886年)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评析: “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是存在于现象之中, 也就解决了。——这部分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得到。那时,大家都很 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 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理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 中看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麦克莱 伦指出:其实这是恩格斯的感觉。费氏的一般著作对恩格斯产生的影响要比对马克思产 生的影响更深远。因为马克思曾经特别仔细研究过黑格尔,他从来未摆脱黑格尔的影响 :相反,恩格斯是一个自修者,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受过同样的大学训练,因此较易接 受费氏质朴而通俗的文体。(《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8 —99页)
1843年《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刊出《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 》一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你们只有通过火流(即费尔巴哈)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 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这才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据此苏联哲学家梁赞诺夫 断言:1843年的马克思是一个狂热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但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哲 学的波兰哲学家兹维·罗森考证:这篇署名为“柏林人”的文章,其实是费氏自己的作 品。(参见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第249——251页)
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论者,他一直是用审视的目光来看待费 氏的作品。
二、费尔巴哈人本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曾说: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又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7卷,第443页)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断言:“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 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 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中也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 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 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2卷,第231页)据此,一种 普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秉承了费氏在自然观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所使用的“颠 倒方法”,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但实际上,马克思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受费 尔巴哈的影响:一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进步,使马克思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自 然观做出科学的解释:二是马克思用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方法”也并非仅源 自费尔巴哈。虽然马克思曾提到:“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 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5页)这与1842 年费尔巴哈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开头所特有的批判如出一辙:“我们只 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 、纯粹的、明显的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2页)但这种“颠倒 方法”不是费尔巴哈独有的,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已是十分普遍的方法,尤其在鲍威尔的 著作中是十分明显的,最先受到鲍威尔影响的马克思也是十分熟悉这一方法,如1842年 10月的《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中,马克思论述国家与私有制的关系时说:如果国家按 私有制的方式,而不是按自己本身的方式来行动,那么国家应该适应私有财产的狭隘范 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1页)很明显,这里国家从主 词变成宾词,而私有制则变成主词。相反费氏在19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对这种方法的使 用并不是十分明显。
应该说马克思是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性地吸收而接受唯物主义思想的,这表现 在:
第一,早在1842年2月马克思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就吸取了 费尔巴哈在《论对<基督教本质>一书的评判》中的“类”概念,把类与个体的关系作为 批驳书报检查令的基本哲学依据:你们一方面要我们尊重不谦逊,但另一方面又禁止我 们不谦逊,把人类的不完美硬加在个人身上,这才是真正的不谦逊。新闻检察官是特殊 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物则是类的体现。
第二,1843年夏秋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若干基础性的论点上同费尔巴哈二 版的《基督教本质》一文一致,或采纳了后者。首先,马克思特别继承和发挥了费氏“ 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费氏虽然主要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人,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估计到 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指出人的本质不仅是“自然本质”,而且也是“历史的本质、国家 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指出孤独的个体不具有人的本质,只有“共同体”,“人与 人的统一”才内含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6页)马克思在批 判黑格尔倒置主体与主体性关系的过程中,也谈及了人的“类存在”或“社会特质”, 指出“单一的东西唯有作为许多单一体才能成为真理”;“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就是一 个抽象,但是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7页)“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肉体的本性,而 是人的社会特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其次,该文还显示出了费 尔巴哈“异化”观念的影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几次运用了这一术语,马克思特 别用它来指谓政治国家和政治制度,认为政治制度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类”的 异化物。同时异化的意蕴被引伸到政治和现实生活领域,从而超出了费氏“异化”观念 的范围。
第三,《德法年鉴》时期,费尔巴哈继续扩大对马克思的影响,随着费尔巴哈在哲学 界声望日增,马克思为扩大《德法年鉴》的影响,于1843年10月致函费氏,约写批谢林 的专稿:“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须也是旨 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 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如果您马上给创 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 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4、445页)同时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期间发表的两篇文章, 也表现出在对待费氏学说上的一贯性。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采纳了费氏对犹太人及其宗教的说法。费氏认为犹太人 的原则和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事原则、是利已主义,并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已主义 ,利已主义就是那不容许自己的仆人吃亏的上帝”。(《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 ,第146页)马克思也认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 的世俗偶然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1卷,第446、448页)实际上费氏关于犹太教本质的论述意义在于:他已经以某种 方式将对宗教的批判与对尘世的批判、对上帝的批判与对利已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虽 然费氏对犹太人的利已主义的生活实践现实作了不正确的理解,并使之普遍化,等同于 社会实践的一般形式。但他却通过对犹太教本质的揭示,说明了理论中的上帝等于实践 中的利己主义,反之亦然。这里已暗含了有关人的物质生活异化思想的生长点。所以马 克思和赫斯几乎同时对此作了发挥,指出作为犹太人上帝的金钱,不过是人的异化的本 质。
《论犹太人问题》还接纳了费氏的“个体感性存在的”和“类存在”的关系问题,指 出:现实的人,即所谓基督教国家中的人,由于他们为整个社会组织所败坏,被非人的 关系和势力所控制,他们还不具有“类本质”,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4页)因此人类解放的实质就在于:把这种现实中的非类存 在物提升为“真正的类存在物”,“非人”提升为“真正的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 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 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 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那个 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从政治解放到 人类解放所蕴含的类的思想,就是费氏在《关于哲学改造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 》中“人是类存在物”的延伸。
与《论犹太人问题》同时问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清楚显示费氏的影响 。该文一开始就肯定了费氏的宗教的基本前提:是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了人, 换言之,宗教是丧失了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452页)文中马克思还肯定了费氏宗教批判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人是人的最高本 质”;并援引费氏关于人的本质是“头”(或理性)与“心”的说法,把哲学看作人类解 放之“头”,把无产阶级看作人类解放之“心”,认为“它是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 理论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461、467页)
但此文中有许多与费氏相类似的观点却并非来自费氏。如马克思关于“宗教是被压迫 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与费氏的说法:“上帝是灵魂深处无法描述的叹 息”、“基督命令发狂的自然平息下来,却只是为了要倾听苦难者的叹息”(《费尔巴 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55页)相类似,但这里的思想与其说来自费尔巴哈,不如说 来自鲍威尔,鲍威尔是马克思的导师,他在《自由的功绩和我自己的事业》一文中谈到 宗教如何在那充满破坏,上了鸦片瘾似的迷醉中侈谈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来世生活;在 《基督教国家》中他又谈到神学对人类的“鸦片般的影响”。此外,马克思关于“哲学 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虽然非常类似于费氏的“哲学应该把人看成 自己的事情,而哲学本身却应该否弃,因为只有当它不再是哲学时,他才成为全人类的 事。”(《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50页)但它却不是源自费氏,因为这段出 自费氏的《说明我的哲学思想过程的片断》的话是1846年才发表的。这一观点也可能更 多地来自鲍威尔。
费尔巴哈人本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留下了更深的痕迹,此文到处都 贯穿着费氏的影响。首先继续坚持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的观点。但马克思通过把 类本质、类生活归结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或“生产活动”,揭示出人的本质的普遍 性在生产中的表现。费氏通过类不仅揭示出人的自然的规定,也揭示出了人的社会规定 。循此,马克思径直把类存在物(类本质)理解为“社会存在物”,把类本质归结为人的 “社会本质”、“社会联系”,把实现类本质归结为社会主义的要求。
其次,马克思也吸取了费氏的感觉主义,把感性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在诉诸 感性存在时,首先把它理解为人的感性存在,认为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就是直接地感性自 然界。“直接地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 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它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 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129页)这里马克 思采纳了费氏关于“人是人自己的第一对象”的说法,但马克思区别于费氏的“人是自 然的类存在物”,而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第三,马克思也采纳了费氏关于对象化是感性实体、从而也是感性的人的存在方式这 一基本见解,把人明确地定义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费氏认为:“没有了对象,人就 成了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9页)马克思循此而言:“非对象性的 存在物就是非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马克思和费氏一样 相信对象化的必要性,认为它不仅是人的本质和感性的现实表现,而且也是人的本质和 感性赖以解放和发展的手段。费氏说:“如果你毫无音乐欣赏能力,那么即使是最优美 的音乐,你也只能把它当作耳边呼呼的风声,只当作足下潺潺的溪声。”(《费尔巴哈 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4页)马克思也说了类似的话:“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 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也不是对 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6页)
第四,《手稿》中马克思还明显地继承了费氏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马克思就 指出:真正的人本学是“庸俗唯物主义”(人属于自然的本质)和主观唯心主义(自然属 于人之本质)两者的统一,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 唯物主义,它是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手稿》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直到《神圣家族》马克思仍然保持对 费氏较高的敬意,广泛使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费氏的《未来哲学原理》一方面帮助马 克思提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早看法,特别是关于“基础”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使马 克思接受了人道主义等同于唯物主义的思想。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它的人本学理论,即使是自然观上的 唯物主义,也是通过人本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但马克思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费尔巴哈 的人本学,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论者。
三、马克思如何对待费尔巴哈——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分歧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转向和确立哲学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尤其是在1842——184 3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费氏很多的影响,但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狂热的费尔巴哈分 子。早在1841年3月(或4月初)致鲍威尔的信中,马克思就表示要斥责费氏,被鲍威尔劝 阻;1842年3月20日和1843年10月3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费氏的宗教观和自然主义 提出了异议,批评它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
在对人的看法上,马克思接受费氏的影响,又不断地摆脱这一影响。在费氏影响较重 的《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年轻的马克思含蓄地、未加点名地批评了费使用人本主义的 观点解释宗教时写道:“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 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 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马克思一面指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 判在当时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比费尔巴哈走的更远,他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变 为地上的批判,把宗教的批判转变为法律的批判,把神学的批判转变为政治的批判。因 此在论述人类解放时,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而不是抽象的人。
《手稿》沿用费氏异化观和类存在物的同时,又形成了劳动异化的观点;并从人的社 会性直接引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不 仅仅停留在费氏地感性直观,而提出了实践的概念,通过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在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持有根本的歧见。费氏对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均 加抛弃或否定,他虽然也有人学辩证法的思想,但更多的时候他是静止地观察历史,而 不是从运动、发展和实践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则不同意费氏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成神 学——哲学——神学的过程,从而单纯归结为哲学同自身的矛盾,而赋予其现实的内容 :第一,马克思还认为,黑格尔哲学以唯心主义方式表达了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或人重 新占有自己本质力量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页)第二,马克思肯 定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了对象外化 以及这种外化的扬弃,抓住了人的本质——现实的人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第三,黑格 尔逻辑学中的抽象概念,实际上表达了“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而当黑格尔让“绝对 观念”扬弃自身、外化为自然时,表明“抽象思维”意识到自己本身只不过是“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7页)
即使在1845年2月发表的对费氏充满敬意的《神圣家族》一书,马克思也并不完全赞同 费氏。就其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表明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批判的矛头形式上是针对 鲍威尔,但同样也是针对费尔巴哈的,此书中已很少利用费尔巴哈的观点,几乎完全克 服了异化的概念;并对仅仅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而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特点进行了批 判。
正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因此在1845年2月《神圣家族》出版后 ,春天就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正面看,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 论纲;从反面看,内涵了对费氏批判的一切要点。因此马克思才在1845——1846年撰写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把他与费氏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作了一个最后的总结,超越了 费尔巴哈。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看,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者转向新唯物主义,期间受到费氏 人本学理论的很大影响,但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思 想进程。促使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式”,到《神圣家 族》中的敬仰,再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批判”;从前者的人本主义 的历史观到后者的“新唯物主义”,其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思想变迁和逻辑跳跃。这一 变迁不仅仅是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也不仅仅是马 克思一开始就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的存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 “经济利益”这一苦恼问题的探索,使其明确地树立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方法论 ,从而在1843年7月至8月间,中断了同年3月开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转 而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使他有可能自觉地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从而在《 法哲学批判》中确立唯物主义原则。这时马克思所理解的“物”与费尔巴哈视作物质实 体的“物”有了很大区别,马克思已将“物”理解为私有制,理解为一种经济关系,从 而在历史领域中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但此时马克思仍然受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的内在制约:当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时,他实际上是 说“人的本质决定国家”,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或“ 人的本质的客观化”。可见,此时马克思只是走向“历史的”唯物主义,而决非历史唯 物主义。彻底摆脱费尔巴哈隐形的唯心主义影响,应该是1845年初写作的《评费里德里 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文中马克思把费氏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的 本质”的自然主义的观点、把人的本质的规定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 统一之中”这种抽象的人本主义的观点,纳入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通过经济学的 批判与研究第一次在“人”身上感触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作为生产力不仅创 造着财富,而且与自然力一起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成为炸毁资本主义工业制 度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8——259页)从此,马克思牢固确 立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即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 的这种关系的总和,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和主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显见,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并不在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而是 人本学。但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不是一个放弃已见的纯粹的 费尔巴哈论者。因此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本主义者,而是通过对人本学的解剖,赋 予了感性的人以现实的、历史的特质,从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待费尔巴哈 的态度一如他对待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态度一样,是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正因如此, 马克思才能克服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缺陷,克服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缺陷,发现唯物史观 ,建立新唯物主义。这其实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简言之,这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关系到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这对我们每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在当今如何对待我 们时代的思想家,也极具启迪意义的。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神圣家族论文; 哲学家论文; 德法年鉴论文; 鲍威尔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