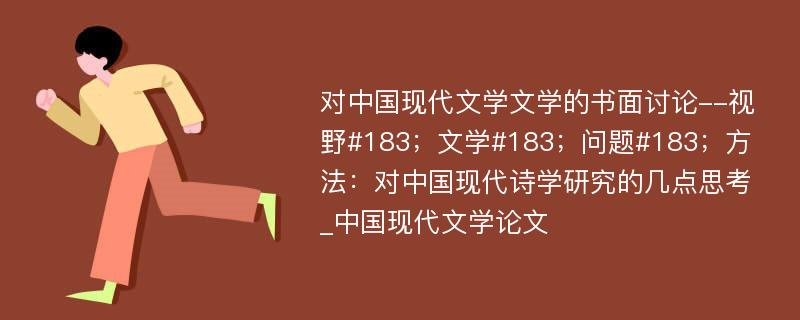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谈——视野#183;文献#183;问题#183;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献论文,笔谈论文,诗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理论的异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各分支领域中,诗歌理论批评即狭义的诗学无疑是最为发达、也最具理论深度的。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作为新文学和新诗开山的胡适后来曾有中肯的说明——
在那个文学革命的稍后一个时期,新文学的各个方面(诗,小说,戏剧,散文)都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第二是戏剧。这是因为新诗和戏剧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革命;诗的完全用白话,甚至于不用韵,戏剧的废唱等等,其革新的成分都比小说和散文大的多,所以他们引起的讨论也特别多。文学革命在海外发难的时候,我们早已看出白话散文和白话小说都不难得着承认,最难的大概是新诗,所以我们当时认定建立新诗的惟一方法是鼓励大家起来用白话做新诗。后来作新诗的人多了……于是新诗的理论也就特别多了。[1](P31)
这种诗论特多的趋势后来仍在持续,并且扩展到对整个汉诗的研究和更具普遍性的诗学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不少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著,以至于朱光潜先生在抗战爆发前夕的一篇文章中曾特地把“诗论发达”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大主要特征之一,并欣然首肯说:“这是好现象。”(注:朱光潜:《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编辑后记》,1937年5月出版。按,被朱光潜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大特征的其余三点是“接受外国文学的狂热与翻译的发达”、“文学语言受外来影响剧烈变化”和“新风格与新技巧的尝试”。复按:该文在被收入《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时,“诗论发达”一语误为“讨论发达”。)这的确是个好现象。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各部门,诗论或者说狭义的诗学不仅最为发达,而且颇多自成一家的诗论专家,其理论思考的深度、广度及其系统性直驾古典诗学而过之,比之同时外国——主要是西方现代诗学也并不逊色;至于发表过独特见解的诗论文字的人就更多了。这是小说、散文和戏剧等部门不可比拟的。所以,中国现代讲学是一笔值得我们特别珍视的理论财富和诗学遗产。
或许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这一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陆续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纵观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局限,即大多数研究者把中国现代诗学和中国新诗理论视为两个完全同一的、可以互换的概念。这是一个本不应有而又可以理解的误解。不待说,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理论确有同一的一面。因为正是新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一进程。就此而言,人们把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理论简单等同起来,是情有可原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新诗理论并不足以概括整个中国现代诗学。因为中国新诗理论所指称的只是关于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批评,而中国现代诗学则涵盖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诗学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就此而言,新诗理论只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部分——虽然是重要的、甚至可说是核心部分,但它并不能代表其整体。这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包含了发生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所有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批评、但又大于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批评一样。
这种异同的辨析至关重要。如此一来,不论现代诗论家们研讨的具体对象是新诗还是旧诗,是诗还是词,或者散曲,以至于是外国诗还是中国诗,都无关碍——只要这种研讨是从现代的诗学观念出发,具有现代的诗学意蕴,那就在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这样一来,我们才可能突破新诗理论主流观念的束缚,而将一些与新诗理论主流不同的诗学思潮,甚至一些与新诗理论无关的诗学流派和诗歌研究著述,纳入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在占有更多样、更丰富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得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判。自然,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扩大,并不是无标准地包容一切发生在现代中国的诗歌一诗学研究,仿佛贪多务得的老妈子那样“拣到篮里都是菜”。其实,中国现代诗学的概念在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意味着更高、更严格的理论要求:只有那些以现代的观点进行的、并且富于诗学理论含量的诗歌理论批评和诗歌研究,才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真正应予关注的对象。
当然,在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视野中,新诗理论各派——如白话一自由诗潮所信奉的自然—自由主义诗学,左翼一解放区诗歌所张扬的革命诗学,以及现代诗派所坚持的现代主义诗学——仍会以其显而易见的现代性或革命性而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但一个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者未必有理由把新诗理论主流作为诗学现代性的惟一标准,他还应该本着历史的同情,对那些居于新诗理论主流之边、之外以至相反地位的诗学思潮给予关怀,甚至也不妨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些非主流的诗学思潮是否也具有某种现代性。如果说历史真是所谓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矛盾的两面虽有主、有次,却没有哪一方能独占真理,那也就意味着现代诗学的现代性不是谁能垄断的独家货——新诗理论主流固然有较为充分的现代性,与新诗理论主流无关、甚至相反的诗学流派难道除了保守就别无长物了吗?事实上,某些反现代的运动就是现代性运动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反现代就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批评家至少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的存在,例如在美国现当代批评界独步一时的几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欧文·豪和马泰·考林内斯库,不都把反现代视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性相”吗?[2]
二、从文献做起和从问题入手:现代诗学研究的起步
面对丰富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遗产,一些前辈学者和同代的学术同行已为之倾注了10多年甚至逾20年的心力,但从严格的学术要求来看,真正学术性的研究也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对此,我是经过了一个从盲目自信到重新认识的过程的,这个重新认识既指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实际及其研究现状的认识,更包括对自己的学术能力的自我反省。经过这番重新认识,我深感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最好先从文献做起,从问题入手,并据此对自己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重心做了较大的调整。
回想起来,我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到朱光潜先生所谓“诗论发达”乃是中国现代文学一大标志的论断后,因为印象深刻,所以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和资料的,到90年代中期,自以为准备得差不多了,所以稍后便以《诗歌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获得批准后就开始准备写作。当时以为凭自己七八年收集的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不无新意的思考,是不难给中国现代诗学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的,所以企图写一部通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著作。但殊不知一旦真正下笔,便发现困难重重,问题复杂,远非自己当初想像得那么容易。
所谓问题复杂,乃是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理论的异同之辨所导发的——现代诗学在扩大了学术视野的同时,也使许多事情必须重新考虑了,而最费斟酌的便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问题。这里再补充几句。这个问题起初是由如何处理新诗理论主流与非主流的诗学流派如《学衡》派诗学主张的紧张关系引发的。我一开始也是简单地把中国现代诗学等同于新诗理论的,但一旦稍微深入下去,我便发现自己实在不能把新诗坛主流的诗学主张作为中国现代诗学之现代性的惟一标准——那样一来,除了一笔抹杀之外,将无法给予诸如《学衡》派和其同道者以及新儒家等非主流派的诗学主张以公正的历史评价;进而又发现自己也实在没有多少理由把俞平伯、顾随、浦江清、闻一多、缪钺、钱钟书、傅庚生、程千帆等人对古典诗歌与诗学的研究,把冯至、叶公超、罗大刚、杨周翰、王佐良等人对外国诗歌与诗学的研究,拒之于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视野之外,难道就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或外国的?但既然我们不能想像一个研究汉代诗学的人把汉代的《诗经》学如《诗大序》拒之门外,而只讨论汉代人关于汉代诗歌如汉乐府和五言古诗的理论批评,既然我们也从未见过一个西方学者会把T.S.艾略特论但丁、莎土比亚以及玄言诗的文章,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剔除出去,那么,我们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以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把上述内容拒斥于门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讲了。不待说,由于认识的改变和视野的拓展,我觉得上述内容以及其他相关现象就必须纳入研究的范围,但那样一来,所要研究的问题之繁多和复杂,就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预计和自己的能力了。
所谓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个开辟较晚的研究领域,基本的学术积累不足,许多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都还是些有待发现的问题,大量的现代诗学文献还处在尘封和湮没状态。而由于我原来的研究计划是从诗学流派的角度梳理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脉络——其实只是新诗理论批评的概要,资料准备也限于这一范围。视野拓宽后,原先的设计和准备也就远远不够了。再看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基本限于我自己原来的认识程度,加上这是个较晚开辟的研究领域,学术积累不厚,尤其是现代诗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还很不如人意,除了杨匡汉和刘福春二先生编选的《中国现代诗论》上册(花城出版社,1985)及个别大作家有较可靠的全集、文集外,其余大量文献都得从头搜集。当然,勉强以我当时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写一本中国现代诗学概论之类的书,也不是凑不出来,事实上,类似的著作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推出,但我不再想凑这个热闹了。
在认清了问题所在和研究现状之后,我觉得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从头做起——从诗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做起,从专题性的诗学问题研究入手。既然如此,我自己就不能坐享其成、坐等分红,首先得勉力从自己做起,所以便痛下决心,调整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和工作进度。调整后的工作重心自然地集中在我以为应该加强的两个方面。
一是决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现代诗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上,努力在这方面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由于我后来调入北京工作,比较便于接触原始资料,更觉责无旁贷,所以我这几年在现代诗学文献的搜集上花了大量精力而乐此不疲(粗略地统计一下,我近几年搜集的再加上过去积累的现代诗学文献,已有三百多万字),以至于学术的兴趣无形中也发生了转移,甚至觉得搜集散佚的现代诗学文献比我自己写一两本可有可无的论著更有意义,也更为迫切,因为这些散佚的史学文献凝聚着前辈们的心血,任其湮没,实在可惜,有负于前辈们的苦心。当然,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殊费精力和心力,例如,单是为了搜集和校理于赓虞的佚诗、佚文,我和我的老师王文金先生就耗去了近三年的光阴。不过,发现散佚文献的快乐也是别的工作所没有的。仍以于赓虞为例,他生前早就编定了自己的《诗论》集准备出版,却一直未能如愿,以致散佚各处,迹近湮没,所以他的诗学主张从未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野,而我们几年来从各种旧报刊翻检他的诗论,既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恼,也不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之喜。终于找到的于赓虞诗论达21篇,已超出了他当年编定的篇目,因而为之重新辑校,收入我和王文金先生合编的《于赓虞诗文辑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但这仍不完整——就在该书出版的前几天还找到他的一篇重要诗论,幸好还来得及补进即将出版的《于赓虞诗文辑存》中。
二是决心放弃贪大求全的研究、写作计划,坚决收缩讨论的范围,以便集中精力对自己比较有把握的现代诗学专题进行探讨——收缩后的探讨范围大体集中在五四及19世纪20年代这一段,集中在这一段的四五个重要诗学流派和关键的诗学问题上。其实,在决定自己到底“写什么”问题的同时,也包含着对“怎么写”的考量。如前所述,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曾经有过贪大求全的痴心妄想,后来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感受到问题的复杂性,并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只能脚踏实地、量力而行,所以自觉地放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妄想,而将研讨和写作的计划收缩到如上所述的范围。至于“怎么写”的问题,由于中国现代诗学本来就是些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对它的研究和论述常见的并且是学界乐用的做法,是对之作进一步的理论发挥和水平提升,并尽可能地用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论话语对它进行再阐释,以彰显它或者说赋予它某种当代性与深刻性。但我是个对时新东西比较迟钝的人,所以没有能力、也不大乐意这么做——说实话,我一直都搞不明白所谓理论前沿是什么意思,是最新的、最流行的?还是最好的、最先进的?而满天飞的深刻话语更让我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所研究的虽然是一些理论主张,但它们都是文学史上的理论,对这些已“作古正经”的理论,我应做和能做的就是将它们从历史的尘埃中收集起来,对它们当年发生和发展时难免的纷乱略做梳理,并尽可能将它们发生、演变的前因后果,及其相互之间本来就有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不太明了的关系,揭示出来、叙述出来,让人看过之后觉得“事情大约就是这样子吧”,而不是“你不说我还比较清楚,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也就够了。因此,在写法上,我尝试以叙述和考辨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个理论问题,而且决定只对那些文献史料准备较为充分、考虑得比较清楚、因而真正已被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的问题”加以叙说,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决不强为之说。
坦率地说,在学术上如此处理文学史上的理论问题,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不少中外学界前辈都是这么做的,尤其在一些学术积累较少的研究领域,与其一窝蜂地抢做整体性的研究或刻意深刻的发挥,还不如大家分头搜集资料,先进行专题性的考辨和叙说,这样不仅比较切实可行,而且于公于私都更有益些。我最为心仪的两位现代学者——朱自清和R.韦勒克,就是典范。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开创不久,来自清就致力于此,但他只选择了几个批评史上的概念做专题考辨,并表示“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3]。西方批评史至迟到上个世纪初圣茨伯里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出版(3卷,1900——1904),就建立起了令人钦敬的学术界碑和学术传统,40年后R.韦勒克又花了近半个世纪的心力进行研究,撰写出了更为精深博雅的多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但人们往往只看到R.韦勒克的最终成果,而常常忽视了那是他半个世纪里艰苦扎实的专题研究之日积月累的结晶,其中的一些专题研究论文曾先后单独结集为《批评诸概念》及其续编二书。不矫情地说,比起他的批评史的皇皇巨著,更给我深刻印象和影响的乃是这两本专题研究论文集,它们对西方近代批评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辨析,不仅在现在不可或缺,而且在不短的将来可能也是无可替代的。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能也不必与朱自清、R.韦勒克攀比,但就学术论学术,我对他们二人的治学方法确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所以我愿意老实承认,自己中途放弃写中国现代诗学通论的想法,固然是反复审视这一领域研究现状和自我审视后不得不从头做起、量力而行的学术调整,但朱自清和R.韦勒克的影响也是促使我放下包袱、尽其可能、从头做起的原因。
三、仓促中的一点收获:中国现代诗学源头初探
经过这样一番调整,研究工作算是走上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路,但整个课题的进度却大大延迟了。并且由于把大量精力花在散佚诗学文献的搜集上,这样留给写作和文献整理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现在勉强拿出来的这点东西,确是仓促中的一点收获:5篇专题研究论文,2部现代诗论集的整理。由于这些问题和文献都主要与五四及19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相关,而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发源时期,所以循名责实,或许只能称做“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诗学探源”。
几篇专题论文对这一时期主要诗学潮流或诗学概念进行了一些探讨。这些论文所探讨的问题之间当然也有着事实上的联系和理路上的关联:白话一自由诗学是中国现代诗学开头的开头,它所标举的自然—还原主义和自由一自发主义两大诗学信条,确实彻底地把汉诗从旧诗规范及其理论教条的重重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不仅带来了“诗体的大解放”,而且从根本上解放了诗的创造力,使汉诗写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同时它们作为一场真正的诗歌革命的理论所难免的极端性、片面性和简单化,势所必至地导致了新诗创作的危机——由于诗歌这种高度精微的语言艺术几乎完全被还原、等同于自然的日常言语行为,创作应有的自由被极端地推崇到几乎不需要任何艺术规范和艺术经营的自发性写作,所以新诗在一度盛行之后必然地盛极而衰,用当时明眼的批评者的话来说,就是新诗的极端“安那其”(无政府)导致了新诗的“自杀”;并且在白话—自由诗学主导下的对古典诗歌与诗学的简单重估,当然也有失历史的和艺术的公正,而新诗潮与生俱来的旨在参与社会改造的功利主义倾向,稍后也片面发展……要之,白话—自由诗学既以其自由为后来者留下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余地,但它的极端性和缺陷也必然引发出纠正、补充和反拨。稍后发生的新形式诗学、纯诗观念、新传统诗学倾向以及左翼的革命诗学,都发展或修正着它的或一方面。早期的新形式诗学与白话—自由诗学“和而不同”,它针对白话—自由诗学的弊端,强调诗的语言“不类常言”,强调诗是一种艺术,不能与自然等同,诗的创作也不能一任自由,它必须有形式上的规范和艺术上的经营。纯诗观念的兴起同样是对白话一自由诗潮及其理论主张的反拨,由于不满后者日益增强的功利主义倾向,它转而张扬“为诗而诗”的纯粹性,并一步一步地高蹈于惟美—象征之途,引导着新诗潮向艺术的自足和无为方向发展。新传统主义诗学倾向包罗甚多,但其早期代表《学衡》派及其后学梁实秋、胡梦华等的接连崛起,也同样导发于对白话—自由诗学的不满,他们强调诗的“文字”与日常语言的不同,强调诗作为一种人为的“美术”与自然的区别,强调应以善的理性节制诗歌的感情抒发,以及中外诗歌传统对现代的意义,都有其合理性,但错误地将模仿古典置于艺术创造之上以及在诗歌语言上的保守性等也无可讳言(按,新传统诗学倾向后来一直延伸到五六十年代的港台,里面的问题繁难,该部分虽然材料与观点都已具备,但未及写出全文,此处只写出一个简略的论纲,因为它多少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总体情况。我实在深感惭愧,但还是不揣简陋地一并提交,以便参阅)。此外,早在1923年就已经能够听到革命者对“新诗人的棒喝”了,但左翼的革命诗学之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还是后来的事,所以在此暂未论述。
两部现代诗学文献整理成果——潘大道的《诗论》校补和于赓虞的《诗论》重辑——只是从已搜集到的文献中整理出的一小部分,放在这里不过举例而已:前者是中国现代第一部(1924年初版)具有现代意义的诗论集,它和它的作者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后者是于赓虞《诗论》集的重新辑集,这些诗论大多写于1925年之后的5年间,它们可以证明于赓虞是胡适、郭沫若之后和梁宗岱、朱光潜之前最重要的现代诗论家。其余文献只能留待以后整理了。
鲁迅先生在谈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强调说在文献史料上“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4](P229)。这种独立准备资料、独立思考问题的学术品格是我们的楷模。我很惭愧未能按期完成最初的研究计划和学术承诺,而只勉强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初步”做了一点初步的研究。而差堪自慰的是,呈现在这里的一切,即使有与时贤相同处,也只是某些研究对象相同,至于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都出自我的独立准备和独立思考。
当然,不论是在文献上,还是在观点上,我都难免失检和不当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标签: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献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诗论论文; 学衡论文; 现代诗论文; 诗歌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