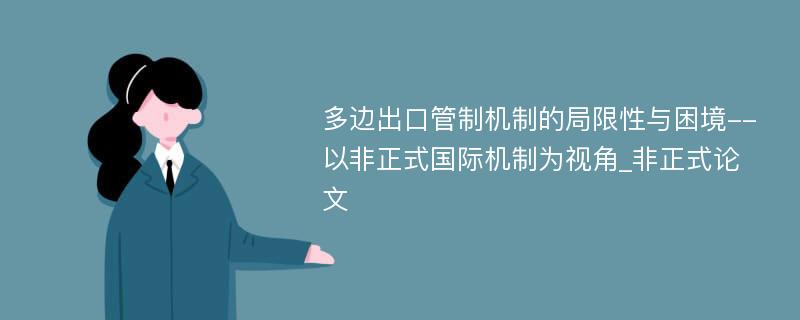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局限与困境——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视角论文,困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之一。为应对和治理这一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机制。这些国际机制既包括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生物武器公约等有国际法约束力的正式国际机制,也包括一些没有国际法约束力的非正式国际机制。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亚集团和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等多边出口控制机制①就属于后一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非正式国际机制。②关于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已有的文献主要从外部挑战、机制缺陷和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分析,③但在分析过程中却没有关注到机制的非正式性与机制缺陷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从机制非正式性的角度,分析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局限和困境。
一、机制遵守行为的非约束性
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之间,仅存在着一种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型的承诺关系,各成员国对特定敏感物项是否发放出口许可是在其“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决定。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成员国对机制规定的遵守行为是一种以政治或道德承诺来维系的“主权性权利”(sovereign right),而不是一种国际法义务。机制遵守行为的非约束性,使各成员国在对某种敏感物项是否发放出口许可的问题上常常出现不相一致的情况。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某个成员国政府根据机制规定拒绝发放某种控制物项的出口许可,而其他某个成员国政府却可能违反机制规定批准该控制物项的转让。尽管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制定了“互不损害政策”来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但由于这一政策本身也并不对成员国构成国际法义务,成员国是否执行这一政策也是在“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决定,其实际的作用就变得极其有限。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机制成员国的政府决策者往往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或外交政策利益的考虑,以机制赋予的“国家自由裁量权”做出不遵守机制规定的政策选择。
(一)规模经济效益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所控制的军民两用物品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④这些产品具有固定资本投入大、技术研发成本高的特点,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即随着产量的增加,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平均成本将不断降低。⑤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只有少量的市场需求,其平均生产成本就会很高,产品就只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从而导致市场需求进一步缩小。这就会极大地限制企业的壮大和发展,甚至可能出现无法收回固定资本投入和技术研发成本的局面。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获得足够的市场需求支持,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产品就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争得更多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使企业不断发展和壮大。这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军民两用品产业作为国家科技和经济实力的体现,推动着社会整体生产力的进步,同时又为国防工业提供直接的技术和武器部件支持,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这些战略性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一国政府会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包括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扶持本国的战略性产业,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规定其成员国企业对军民两用品实施出口控制,这使军民两用品企业的海外市场受到限制。受限制的海外市场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意义不同。对于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家来说,其意义明显小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对于前者来说,即使没有海外市场,国内市场也可能满足企业的规模经济需求,大量的生产导致单位成本下降和销售量上升,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使企业盈利;而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不利用海外市场,狭小的国内市场就使企业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生产规模小导致单位成本增高和销售量萎缩,从而出现亏本甚至生存问题。⑥因此,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机制成员国来说,政府如果遵守机制规定,对军民两用品实施严格的出口控制政策,就会影响这些战略性产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这一情况,国内市场狭小的机制成员国可以采取两种政策手段来扶持这些战略性产业:一是直接提供经济补贴;二是不遵守机制规定,放松出口控制政策。前一种政策手段在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限制下难以长期维持;后一种政策手段则可能对安全利益造成损害。从安全利益的角度看,成员国不遵守机制规定的政策不会被轻易采用。但如果某项军民两用品的进口国与机制成员国的安全关系不明确,或者并不构成直接而紧迫的安全威胁,机制成员国政府就会出于战略产业发展的需要,做出不遵守机制规定、放松出口控制的政策选择。
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中,欧洲国家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其军民两用品产业对海外市场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出于扶持战略性产业的考虑,欧洲国家政府在本国企业向与本国安全关系不明确的国家转让敏感控制物项时,有时就违反机制规定,对本国企业发放出口许可。比如,20世纪80年代,为促进本国核电产业的发展,法国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遵守上就曾出现一连串的不良记录。在对许多与本国安全关系不明确的国家出口核材料和核技术的过程中,法国政府没有按照机制规定实施全面安全保障。这包括向以色列转让迪莫纳核反应堆和再处理工厂,为巴基斯坦和韩国建造后处理工厂,向南非转让核电反应堆和核燃料,在美国停止对印度的核燃料供给后向其提供核燃料,在海湾战争前向伊拉克提供奥希拉克反应堆和武器级核燃料,向巴基斯坦出口锆(Zirconium)和专用特殊钢材及向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转让核电反应堆等。⑦德国政府也因照顾本国企业的发展需要而在1988年至1989年被揭露出数起不遵守核供应国集团的机制规定的丑闻:在没有全面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向伊拉克、印度和巴基斯坦转让后处理工厂和重水等关键材料和部件。在美国和英国的强烈抗议下,德国议会对这几起核出口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德国并不缺乏核出口控制的规章制度,但政府官员出于对本国企业的同情而没有认真执行。⑧再比如,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国家与伊拉克的安全关系尚不明确期间,许多欧洲国家没有遵守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规定,批准了本国企业向伊拉克转让可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两用技术和物品。根据有关报道,有86家德国公司、18家英国公司和17家法国公司在得到本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后,向伊拉克转让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两用技术。有来自24个国家的企业与伊拉克进行了240项有助于伊拉克导弹和核武器计划的两用物品和技术交易。大部分西欧国家都曾对本国公司发放了出口许可,使其参与了这些交易,英国甚至在1990年7月仍然没有遵守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规定,批准了有助于伊拉克发展导弹和核设施的两用物项转让。⑨
(二)外交政策利益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在执行某项外交政策时,可能会出现对某个合作对象国进行军事和技术援助或帮助其提高军事能力的利益需求。而这种外交政策利益与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遵守行为之间存在着冲突。为保证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有时就放弃了对机制规定的遵守。这一违反机制的动因在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领导者自居的美国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为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巴基斯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出于巩固这一安全合作关系的考虑,美国在巴基斯坦进行无安全保障的铀浓缩计划时,仍然没有削减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默许了巴基斯坦的铀浓缩计划。⑩由于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违反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准则向以色列的箭式反战术导弹系统的设计和生产提供了直接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有分析家指出,美国曾在1988年保证对箭式反导系统80%的开发成本提供资助。(11)对于这一违反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准则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官员辩解道:“美国政府通过国务院和商务部主管的许可程序对箭式反导系统的部件和技术进行出口控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程序是无效的,也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不履行其终端使用保证的承诺。”(12)事实上,所谓的终端使用保证根本无法确保以色列不会将美国转让的技术用于弹道导弹的设计和制造,美国之所以找不出不相信以色列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增强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有助于美国实现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出于外交政策利益的考虑而不遵守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做法,还表现在海湾战争以前放松对伊拉克的出口控制政策上。20世纪80年代,为扶植萨达姆政权反对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政权,美国给予伊拉克一系列军事和技术援助,其中包括在军民两用技术上放松出口控制政策。里根政府总体上鼓励对伊拉克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老布什政府初期,并且与伊拉克保持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利益在老布什政府初期还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1989年10月,老布什总统发布了第26号国家安全令(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 26),号召与伊拉克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以加强美国对萨达姆政权的影响。(13)这一外交政策利益所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从1985年到海湾战争爆发前的时间里,批准了总共价值15亿美元的767项转让给伊拉克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而仅仅对伊拉克拒绝发放39项总价值为2600万美元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14)在美国批准转让的两用物项中,有数起转让是直接出口到伊拉克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导弹开发复合体的。(15)
在规模经济效益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推动下,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有时表现出不遵守机制规定的行为。由于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机制遵守行为并不是成员国的法律义务,这就使得成员国可以在“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为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外交政策利益而放松对某些潜在扩散者的出口控制政策,从而使多边出口控制合作在某些成员国身上出现可能的漏洞。
二、机制规定的模糊性
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协议文本中,存在着一些意义模糊的规定。例如,在核供应国集团的伦敦准则提出的防扩散原则中写有,当供应国仅仅在对转让不会有助于核武器扩散的情况感到满意时,才可以批准控制物项的出口。根据机制准则的规定,成员国需要自己对敏感物项出口被转向军事目的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这就使成员国在决定是否对某个国家进行敏感物项转让时可能出现不同的风险评估结果,有的成员国可能认为对某个国家的敏感物项转让不会有助于核武器扩散,其对扩散后果的风险评估较低,故认为是可以令其“感到满意”的情况,可以批准出口许可。而其他成员国则可能认为扩散风险较高,不属于可以令转让国“感到满意”的情况,所以不应该批准出口许可。伦敦准则虽然列出了敏感物项的控制清单,但却没有列出不能令供应国“感到满意”的国家清单。这就使不同的成员国在对某个国家进行敏感核物项转让是属于遵守行为还是不遵守行为的问题上,可能产生不同的意见。这种对扩散风险的高低规定模糊的情况,在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和澳大利亚集团中也同样存在。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对扩散风险实行“强推定”(strong presumption)原则,但“强推定”的决策权由每个成员国自主掌握。在这些机制规定的模糊地带上,成员国围绕某种转让属于遵守行为还是不遵守行为的问题发生争议,就变得在所难免。
本来,机制规定的模糊性在正式国际机制中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语言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意图,条约的起草者并不能预见许多可能的适用情况——更别说它们的前后发展的背景了,而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在条约谈判时往往还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在正式的条约机制中,也常常会产生一些模糊地带,其中很难说明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16)但是,正式国际机制一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因机制规定的模糊性而产生的国家间争议问题:一种途径是将机制规定的解释权授权于一个独立机构,由这一独立机构对有争议的模糊规定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化学武器公约中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OPCW)就属于对模糊协议内容具有解释权和裁定权的独立机构;另一种途径则是通过全体会议的集体决策做出权威性的裁定。(17)
然而,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并不存在具有协议解释权和裁定权的独立机构。同时,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为保证各成员国在集体决策中享受充分的国家自由裁量权,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在这一决策原则下,对模糊规定持有不同看法的各个成员国很难形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而即使勉强达成一致意见,也因机制的非正式性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样,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就无法通过全体会议的集体决策对模糊规定做出权威性的裁定。
由于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某些规定的模糊性,以及成员国无法通过集体决策对模糊规定做出权威性裁定,成员国在对某些模糊规定的具体执行上就出现了一些宽严程度不相一致的情况。例如,澳大利亚集团和导弹技术控制机制都对成员国提出了实行“全面控制”(catch-all controls)政策的要求,即成员国需要对不在控制清单之内,但仍可能有助于生化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计划的物项的出口发放许可证。但与控制清单物项的明确规定不同的是,出口控制机制对什么是可能有助于生化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计划的清单外物项没有清楚地界定。大多数成员国虽然都实行了“全面控制”政策,但在政策执行的具体方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成员国对本国出口企业违反“全面控制”政策的解释是,出口企业在有绝对把握肯定某项出口将会支持生化武器和弹道导弹扩散活动时,就需要获得出口许可。而美国等另一些成员国的解释是,政府在有理由相信出口企业知道某项出口将会支持生化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计划时,企业就需要申请出口许可。(18)后者的严格程度明显高于前者,但毋庸置疑的是,两种执行方式都是对“全面控制”政策合情合理的解释。对“全面控制”政策的不同解释方式影响了成员国在该项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出现宽严程度不相一致的结果,这一结果显然不利于各成员国在多边出口控制合作上的相互协调。
机制规定的模糊性不仅导致成员国在同一政策的执行上缺乏相互协调,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某些成员国在机制协议的模糊地带做出不违反机制的具体规定但却违反机制目的和宗旨的隐性违规行为。(19)由于从含义模糊的机制规定中无法直接推导出这类隐性违规行为的禁止性要求,发生隐性违规的成员国就可以将其行为合理地辩解成是遵守机制规定的行为,并以此反驳其他成员国的批评和指责。俄罗斯与伊朗的核合作,就是俄罗斯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模糊地带做出隐性违规行为的一个典型实例。
1995年1月,俄罗斯原子能部与伊朗签署了一项总价值为8亿美元的合同,该项合同规定俄罗斯为伊朗在布谢赫尔建成一座核反应堆,提供与反应堆运转相关的一整套服务,为伊朗培训核科学家等。这一合同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开指责。(20)美国总统克林顿试图劝说俄罗斯取消这项合同,美国国会甚至发出威胁称,俄罗斯如果执行这项合同,就停止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随后,在美俄两国的首脑会晤上,克林顿向叶利钦提供了伊朗正积极寻求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设备和技术的情报报告,并明确指出俄罗斯对伊朗的技术援助将会帮助伊朗秘密发展核武器。(21)尽管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俄罗斯仍然没有停止与伊朗的核合作。
西方国家根据所获得的情报信息,认定伊朗有从事秘密核武器活动的高度嫌疑。由此,它们认为俄罗斯向伊朗转让核技术属于核供应国集团准则所禁止的将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核武器扩散风险”的情况,是违反机制准则的行为。面对西方国家的指责,俄罗斯官员提出,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且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检查了伊朗的核设施后,没有发现伊朗从事秘密核活动的证据。因此,向伊朗提供核反应堆不属于核供应国集团准则所禁止的将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核武器扩散风险”的情况,俄罗斯有充分的理由判定这一转让并不违反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基本原则。同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规定,任何缔约国有义务“独自或会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促成核能和平使用之进一步发展,尤应在非核武器缔约国领域内促成此项发展”。通过援引这一规定,俄罗斯官员甚至提出,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援助是其对国际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而并不违背任何国际承诺。(22)
由于核供应国集团准则对什么情况属于“不可接受的风险”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西方国家以其所掌握的情报信息为判定依据,俄罗斯则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结果为判定依据。不同的判定依据,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向伊朗转让敏感核技术是否违反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从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基本原则看,如果有确切情报反映出伊朗正从事秘密核武器活动,对其采取谨慎、严格的出口控制措施是符合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目的和宗旨的必要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向伊朗转让核技术是违反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目的和宗旨的。然而,由于机制准则对什么情况属于“不可接受的风险”没有给出明确的判定依据,俄罗斯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结果来制定和实行相应的出口控制政策并不违反机制准则中含义模糊的规定。同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向伊朗的核技术转让定性为违反机制规定的共同看法在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下并不构成权威性的裁定,这就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争议无法获得最终的调和或解决。由此,西方国家难以通过机制本身的决策程序推翻俄罗斯根据含义模糊的机制规定所作出的自我辩解的合理性,俄罗斯得以在遵守机制规定的合理辩解下做出向伊朗转让核技术的隐性违规行为。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成员国围绕机制协议的模糊规定所发生的争议无法实现权威性的裁定。这一方面导致了成员国根据模糊规定的不同解释实行宽严程度不相一致的出口控制政策,从而使成员国在同一政策的执行上缺乏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又使某些成员国的隐性违规行为难以通过机制内部的决策程序进行有效制止。无疑,这两方面的消极后果都会降低多边出口控制合作的有效性。
三、机制目标与成员国范围的不相合性
作为一种供应方控制手段,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只有将更多的技术供应国引入其合作体系,才能减少潜在的扩散者从机制外供应国手中获取相关技术的可能性,提高供应方机制的控制效果。然而,各成员国之所以选择非正式机制的安排,既有保持更高的灵活性的考虑,也受到初始成员国在防扩散合作议题上政策偏好趋同的大力推动。由于政策偏好上的“志同道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成员构成选择,在这些非正式机制的创立初期,许多全面掌握或者部分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生产技术的非西方国家,并没有参与到多边出口控制合作中。而多边出口控制机制要达到充分的有效性,客观上要求所有技术供应国的集体参与。因此,将其他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生产技术的非西方国家扩展为机制成员国是更好地实现机制目标的内在需要。
随着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曝光,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迫切地认识到扩展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范围的必要性。为吸引主要的非西方供应国加入到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以美国为主导方的西方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可以为加入国带来经济和技术收益的转移支付(side-payment)政策。这些转移支付政策包括:
1.以取消对涉嫌技术转让公司或国家的经济制裁,换取非西方供应国的防扩散承诺。
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少对机制成员国中涉嫌非法技术转让的公司实施经济制裁,而机制外国家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则会遭受经济制裁。(23)例如,根据1990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导弹技术控制法案,如果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以外的国家提供、获得或者向不遵守机制准则的国家共谋转让受控制的导弹技术,国会将授权总统剥夺该国或涉嫌转让的外国公司获得美国控制的军火和两用产品的权利。1991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消除法案,授权总统对向伊拉克和伊朗提供化学、生物武器及其相关技术的国家和外国公司实施制裁。(24)为促使机制外的非西方供应国遵守多边出口控制准则,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对承诺遵守准则的国家取消经济制裁的利益诱导政策。据西方国家的有关报道,1992年,美国在劝说中国提供遵守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准则的书面保证的接触过程中,采用了取消对向巴基斯坦转让M-11导弹技术的中国公司的经济制裁的交换条件。(25)1995年,克林顿政府为诱使俄罗斯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同意只要俄罗斯不再继续向巴西转让与卫星运载火箭相关的技术,就取消对俄罗斯公司的制裁。(26)
2.对遵守多边出口控制准则的国家放松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控制,使其可以凭借机制成员国身份在合作体系中分享相关技术。
1992年,美国国务院决定允许美国出口商在没有取得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向澳大利亚集团成员国出口化学前驱体,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集团成员国可以不受限制地从美国获得化学两用品技术。(27)1993年,美国在坚持不支持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以外的国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技术的同时,同意可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on a case-by-case basis)向机制成员国出口用于和平计划的控制物项。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要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就可以从美国和其他成员国手中获得机制准则所控制的空间发射技术。(28)1994年,美国国会又对出口管理法案进行了修改,新法案规定美国将根据进口国出口控制体系的优劣状况来决定是否对其发放敏感两用物项的出口许可,如果进口国的出口控制体系较为完善,美国就可以放松对该国的出口控制。同年,日本也采用了类似的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在这一程序下,日本可以向建立起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的贸易伙伴发放出口许可证。(29)新的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鼓励非西方国家为获得西方国家的高新技术而建立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西方国家向建立起完善的出口控制体系的国家提供特殊的许可证收益(special licensing benefits)。而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以外的国家如果建立起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就具备了成为机制成员国的资格。通过这些对机制成员国的“优先待遇”政策,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机制成员国创造出相互分享高新技术的特殊机会,其目的是对机制外国家形成“磁环效应”(ring-magnet effect),诱导其建立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并最终加入到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
3.向有意愿加入机制的国家提供民用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并向其提供建立出口控制体系的技术培训和援助。
例如,俄罗斯是否遵守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准则,就被美国确定为是否给予俄罗斯进入美国民用卫星发射市场及允许其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前提条件。(30)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劝说巴西放弃弹道导弹计划的过程中,也将解除对本国公司选用阿尔坎塔拉中心进行商业卫星发射的限制作为一项收益可观的“未来红利”向巴西开出。为吸引前苏联和前华约国家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将其是否建立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与能否获得北约新成员国资格以及欧盟特惠贸易伙伴资格相挂钩。(31)在为有意愿加入机制的国家提供建立出口控制体系的技术培训和援助方面,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从1992年开始就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培训班和其他国际会议,为国家出口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作提供专业指导和培训。美国在这些技术援助项目中表现得最为积极,超过30%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都由美国提供。(32)美国牵头组织的技术援助项目主要包括美国商务部实施的国家出口控制合作项目(National Export Control Cooperation Program,NECC),美国能源部实施的国际核出口控制项目(International Nuclear Export Control Program,INECP),以及美国国务院负责协调和提供资金支持,国防部、海关等部门共同参与实施的出口控制及与其相关的边境安全援助项目(Export Control and Related Border Security Assistance Program,EXBS)。(33)这些项目的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从而为其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创造条件。
通过上述的转移支付政策,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范围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扩展。前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前华约国家及巴西、阿根廷等技术实力较强的非西方国家,都已成为部分或全部的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从理论上说,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将主要的武器和技术供应国纳入成员国范围,会取得优于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的控制效果。然而,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由对防扩散议题具有趋同性政策偏好的国家所组成的初始状况,在机制成员国大规模扩展后却已不复存在。这对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有效性构成了新的威胁和挑战。
作为在防扩散议题上“志同道合”的国家,西方国家都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视为国家安全的共同威胁。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正是它们为应对这一共同威胁而积极构建的产物,西方国家在防扩散议题上“志同道合”的相互认知又是促成其选择非正式机制的制度形式的重要动因。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非西方供应国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却并非都是出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安全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获取技术和经济实惠的利益动因。
理查德·丘皮特(Richard Cupitt)、叙泽特·格里约(Suzette Grillot)和村山雄三(Murayama Yuzo)在一项分析国家发展出口控制体系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对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果显示: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并认为武器扩散对本国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构成了间接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的必要之举;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则认为本国参与防扩散出口控制合作,是为了展示其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国的意志和决心;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则认为本国发展出口控制体系,是因为担心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限制和政治孤立。在研究中,作者没有指出每一种表态所对应的具体国家名称和政府官员姓名,也没有给出每一种表态所对应的国家数量。(34)因此,这一访谈结果尚不能清晰地显示各个非西方国家寻求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具体原因,但从这一结果中却可以看出,一些国家出于经济或政治动因而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根据约翰·贝克尔(John Becket)和迈克尔·贝克(Michael Beck)的研究,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属于为获得转移支付而不是为满足核心安全目标的需要而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国家。例如,两国积极寻求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就是为获得西方国家技术和卫星发射市场而采用的工具性的政策手段。(35)巴西寻求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也是为获得成员国资格所带来的技术收益。这一动因可以从巴西一名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发表的讲话中看出:“通过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机制,我们将获得可以无保留地为我们提供其他国家所掌握的技术的通行证。”(36)哈拉尔德·穆勒(Harald Muller)还指出,匈牙利和波兰发展核出口控制体系是为加入欧盟准备条件,并且受到全面进入西方国家市场和获得西方国家技术等因素的激励。(37)
作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新成员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已建立起良好的出口控制体系。根据美国佐治亚大学国际贸易与安全研究中心对国内出口控制体系的评分,(38)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分值在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之势,并已基本达到出口控制的程序性要求。不过,这一评分结果只能反映这些国家建立了实施有效的出口控制所必需的程序、法规和科层结构,而不能说明其实际的出口控制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对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遵守。(39)约纳斯·塔尔贝里(Jonas Tallberg)认为,“国家在认识到其利益在于签署机制协议,而不在于遵守机制协议时,就会主动选择不遵守。”(40)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等为获得转移支付而加入机制的非西方供应国而言,出于安全动因而遵守机制、有效实施出口控制政策的自我激励并不存在。在这一情势下,签署机制协议是其利益所在,而遵守机制协议就不一定符合其利益需求。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在苏联解体后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以武器和两用物品出口换取硬通货和经济收入的需要对其产生了放松出口控制政策的巨大压力,(41)这就使其可能出现放松机制控制物项的出口控制以获取经济收入的不遵守机制准则的行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恶劣的经济状况还导致了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而来的庞大的军工体系陷入研发经费和生产资金短缺的困难境地,使其在新一代武器的研发上难以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在更新换代武器的生产上也举步维艰。在此情形下,通过武器和两用物品的出口来获得资金就成为保持新一代武器的研发进度和加速已有武器更新换代的迫切需求。(42)这一迫切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俄罗斯政府官员批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技术的转让。
在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军工体系经费匮乏的双重压力下,俄罗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遵守机制的内在动力。前文提到的俄罗斯向伊朗转让核技术的隐性违规行为,正是在这一内在动力的推动下对机制准则模糊地带的策略性利用。除隐性违规行为外,俄罗斯还表现出显性的不遵守机制准则的行为。2001年,俄罗斯向印度转让浓缩铀的事件就属于这种既违反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目的和宗旨,又违反机制准则的明确规定的行为。
印度既不是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也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按照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规定,俄罗斯不应向印度出口浓缩铀。在2000年12月的特别会议上,当俄罗斯提出这一转让计划时,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机制成员国都认为这是违反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反应强烈。(43)美国国务院于2001年2月对俄罗斯的转让行为提出了如下的公开指责:“对于俄罗斯联邦违反其防扩散承诺向印度的塔拉帕核电反应堆提供核燃料,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作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俄罗斯做出了不同任何没有让其核设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安全保障的国家进行核合作的承诺。在2000年12月的核供应国集团会议上,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都对俄罗斯向印度转让核燃料的计划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因为它们都认为这与俄罗斯的承诺不相符合。我们同其他核供应国一起呼吁俄罗斯取消这项供应安排,并遵守其防扩散承诺。俄罗斯不顾其在核供应国集团中的承诺,先后对伊朗和印度提供敏感核材料,这对其是否支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机制目标提出了严重的质疑。”(44)
由于印度的核设施没有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安全保障,俄罗斯无法利用机制规定的模糊地带对其转让行为进行辩解。面对其他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国的批评和指责,俄罗斯做出了如下回应:“由于印度已在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印度基本上已经宣布了其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地位。因此,核供应国集团在向印度供应核装备或核材料的政策上应当做出宽松的解释。”(45)显然,这一说法无法在机制准则中找到依据,因而不能对其核转让行为提供合理的辩解。
由于缺乏与西方国家“志同道合”地支持防扩散目标的安全动因,为从核交易中获得经济利益,俄罗斯既出现了隐性违规,又出现了显性违规的不良记录。就为获得转移支付而加入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非西方供应国而言,恶劣的经济状况还可能推动其出现类似的不遵守机制准则的情况。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机制规定并不对成员国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利用机制本身所赋予的“国家自由裁量权”选择不遵守机制的可能性。
西方国家为加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控制效果,做出了一系列的转移支付安排,以吸引主要的非西方供应国加入机制。这些转移支付政策虽然在扩展机制成员国范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为获取转移支付而加入机制的非西方供应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像“志同道合”的西方国家那样,从国家安全的内在需求出发支持防扩散目标,这使它们在加入机制后可能因受到国内恶劣的经济状况的内部压力推动而做出隐性或显性的不遵守机制的行为。而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非正式安排又难以对这类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遏止,这就使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在成员国范围上的扩展仍然难以从实质性意义上提升其控制效果。
进一步讲,尽管主要的非西方供应国已在转移支付安排的诱导下加入了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或承诺遵守防扩散出口控制准则,但朝鲜和巴基斯坦等部分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游离于这些非正式机制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用其掌握的“劳动”导弹技术交换巴基斯坦掌握的铀浓缩技术,在获得了核武器制造技术的同时,也给予了巴基斯坦在中程导弹开发上所需要的技术帮助。(46)由于两个国家都不是出口控制准则的遵从国,其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换也不受供应方集团技术阻禁的影响,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无法对这一机制外国家之间的“扩散链环”(proliferation ring)形成制约。对这些不愿接受防扩散约束的国家向外转让其已部分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生产技术的扩散行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仍属不完全的供应国范围决定了其实际表现的无能为力。
四、机制的非正式安排对普遍性国际规范扩展的制约
国际机制是通过对成员国行为的规制来发挥其治理功能的。对于机制以外的国家,国际机制并不具有法律或政治上的约束力。然而,如果一项国际机制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发展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国际规范,就将对任何机制以外的国家产生道德上的约束力。此时,国际治理行动的参与主体将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扩展为国际社会中的所有国家,从而使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实现质变性的提升。
国际规范之所以具有将国际机制成员国的合作治理转化为全球社会共同治理的深刻意义,是因为它是“行为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是一种社会结构,它构成了国际共同体的共享理解和意图”(47)。从对行为体的作用机理来看,国际规范通过两种方式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一种是制约性影响(regulative effect),另一种是构成性影响(constitutive effect)。(48)
制约性影响是指国际规范界定了适当行为的标准,规定了什么行为是合适的和正当的,行为体违反国际规范将会损害其国际形象和地位,使其在国际社会中遭到孤立。在国际规范的制约性影响下,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会考虑到规范因素,并意识到违反规范的社会毁损后果,从而对其形成外部的道德约束。例如,人权规范就定义了国际社会中“文明国家”所包含的意义,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加入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在违反人权规范时,也会对其国际形象和地位造成消极的影响;构成性影响则是指国际规范规定了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即规范的行为方式内化到行为体的意识当中。在国际规范的构成性影响下,行为体对规范的遵守不再是出于外在的约束,如赏罚和功利的计算,而是行为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感。如果规范的力度十分强大的话,国家决策者甚至都不会产生违反规范的任何动机。(49)例如,主权规范就是当代国际社会中一种力度十分强大的国际规范,国家遵守主权规范并不仅仅是出于强制性力量的驱使或自利考虑的结果,同时还出于对其正当性的内在认同。(50)
一种普遍性国际规范的形成一般需要经过规范出现(norm emergence)、规范扩展(norm diffusion)和规范内化(norm internalization)三个阶段。(51)国际机制的创建使其内含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规范在国际社会中出现。国际机制的初始成员国成为国际规范的最初接受群体。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初始成员国借助国际机制的组织平台向其他国家传播国际规范,不断促进国际规范的横向扩展。在第三阶段,当规范扩展到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集体意向时,国家就会将国际规范视为理所当然,此时,国际机制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就演化为普遍性的国际规范。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说服是国际规范扩展和内化的主要动力机制。说服不是操纵,而是通过争论来改变他者的信念、态度和行为。通过这一过程,观念成为规范。(52)就处于规范扩展阶段的国际机制而言,强制或利益诱导手段并不能对机制外国家产生说服作用。初始成员国只有通过让其他国家认识到机制准则和机制决策的正当性,才能说服其接受和认同国际规范。
具体到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由于其非正式特征,机制准则和机制决策都存在着有损其正当性的不合理安排,这就使防扩散出口控制规范的横向扩展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内在阻力。
在机制准则方面,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对军民两用物品实行技术阻禁。这一机制准则虽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必要举措,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技术阻禁是一种歧视性安排,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垄断,防止商业竞争对手的出现。(53)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批评导弹出口控制机制不仅有防止导弹扩散的目的,还带有阻碍他国发展正当的太空发射能力的目的。(54)不结盟运动国家更是将澳大利亚集团指责为西方国家借以维持工业优势地位和控制全球市场的阴谋。(55)作为非正式机制,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缺乏对扩散风险作出权威性评估的集体决策方式,这导致其无法根据权威性的评估结果,在满足低风险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权利的情况下,对高风险进口国实施选择性的技术阻禁,从而向其他国家展示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机制目标。因此,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成员国无法通过不带单边主义色彩的法理程序,消减发展中国家对机制准则正当性的批评和质疑。
在机制决策方面,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实行非正式的协商一致原则。这一决策原则虽然保障了成员国在非正式安排下享受充分的国家自由裁量权,但却导致了决策结果的非约束性。由于缺乏有法律约束力的决策结果作为各成员国的集体行动依据,美国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本国对机制准则的解释对它所认为的违反机制准则的国家实行单边制裁。美国的单边制裁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出口控制规范被其他国家指责为美国借以实现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工具。如果制裁行动在正式的机制决策程序下授权实施,并且得到其他机制成员国的共同参与,其正当性缺失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地解决。因为,在正式的多边决策程序下,任何国家,即使是强势国家——美国的政策自主性都受到制度性的约束,决策结果将获得程序上的正当性,从而避免制裁行动的单边主义色彩。(56)
然而,这一多边主义程序的缺失却使美国难以回避其他国家以“实为美国单方面意志”的话语来指责美国的制裁行动,进而导致出口控制规范的正当性遭到质疑。由于经常遭受美国的单边制裁行动,俄罗斯的反应颇为强烈。例如,针对美国在导弹出口控制事务上的制裁行动,俄罗斯外交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将来,导弹出口控制机制将受到意图将其火箭产品推向世界市场的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政治目标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在每一个具体个案中,实际的决策都将取决于美国与特定国家的关系。这将导致导弹技术控制机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工具。”(57)这也说明了俄罗斯虽然在后来加入了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但出于对美国单边制裁行动正当性的质疑,俄罗斯并没有对出口控制规范产生内在的认同。
由于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在机制准则和机制决策上存在着上述这些缺乏正当性的“外部形象”,出口控制规范难以发展为普遍性的国际规范,这就使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难以通过机制规范的横向扩展进一步提升其有效性。
五、结论与启示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求也逐渐上升到国际安全议程的显要位置。从客观上说,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建立和运转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际社会的防扩散治理需求。然而,这些机制的非正式性带来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其有效性的提升,使其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问题的治理上表现欠佳。
由于从非正式机制向正式机制转变涉及较大范围的谈判和协调,这一转变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就提高这些非正式机制的有效性、增强其对国际防扩散治理的积极作用而言,更加可行的做法是对其决策程序进行制度化的调整,设立遵守评定体制和出口政策审查体制。
遵守评定体制在各国共同接受的决策程序下,根据清晰的标准对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中的模糊规定作出解释,并对有争议的机制遵守行为作出评定。尽管遵守评定体制的集体决策并不对成员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其解释和评定结果可以提供相对客观的参照依据。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国因机制规定的模糊不清而发生争议时,成员国在模糊地带是否有不遵守机制的行为就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导引性参照。根据遵守评定体制的解释和评定结果,没有遵守机制规定的国家将受到广泛的批评,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政治和道德上的“遵守压力”(compliance pressure)。除上述的争议解决作用外,遵守评定体制还有助于对美国在机制决策中的主导性权力形成制度性的制约,避免或缓解机制外国家以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来理解多边出口控制合作的局面,使机制准则的实施获得更高程度的正当性形象,从而为出口控制规范的扩展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
出口政策审查体制对各国的出口控制政策进行定期的审查,审查报告在国际范围内公开发布。通过审查报告,各成员国对机制准则的实施状况可以得到公开、透明的反映,相关国家在国内出口控制政策上与机制准则不相符合的情况也将显露于国际社会。这样,国际社会可以根据审查报告的信息向这些国家施加“遵守压力”,促使其改善出口控制政策。在国内出口控制体系建设方面,联合国1540号决议也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采取和实施有效措施,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58),但这一决议只是以国家自我报告的透明度措施来加以实施。显然,与自我报告方式相比,集中化的出口政策审查体制更加有助于揭示国内出口控制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漏。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联合国安理会从1540号决议的实施要求出发,设立相应的专门委员会,履行出口控制政策审查职责,出口控制规范就可以突破现有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成员国范围的局限,逐渐演化为普遍性的国际规范。
当然,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问题得到根本地解决。从根本上说,国际社会还需要在全球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建立防扩散标准的制度性框架、促进深度裁军等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
注释:
①瓦森纳安排也是一项多边出口控制机制,但它以常规武器、敏感两用物品及技术为主要控制对象。本文关注的是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故不将其列入讨论范围。
②成员国之间是否意图在相互之间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本质区别。国际机制的协议文本是管制性安排界定和承诺关系意图的有形体现,针对一项特定的国际机制,要判定其是正式机制还是非正式机制,需要对其协议文本中的关键用语进行解读。通过对各项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基础性协议文本进行解读,可对其非正式性作出判定。这一判定工作可参见刘宏松:《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论文,2007年12月,第37-52页。
③这些文献主要包括:Aaron Karp,"Controlling Weapons Proliferation:The Role of Export Control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6,No.1,March 1993,pp.18-45; Jing-dong Yuan,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 in the 1990s:Multilateral Regimes,National Policies,and Implications for Canada's Defense Industry,Kingsto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Queen's University,1994; Kathleen Bailey and Robert Rudney,eds.,Proliferation and Export Control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3; Jeam-Francois Ridux,ed.,Limi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The Role of Supply-Side Strategies,Ottawa: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Andrew Latham and Brian Bow,"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Bridgi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3,No.1,Summer 1998,pp.465-486; Michael Beck,"Reforming the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Vol.7,No.2,Summer 2000,pp.91-103; Michael Beck and Seema Gahlaut,"Creating A New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 Arms Control Today,Vol.33,No.4,April 2003,pp.12-18.
④如核工业产品、化工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航天产品和生物医药产品等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⑤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主编:《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周宝根、李彬:《规模经济与出口管制政策》,《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7-8页。
⑦Paul Leventhal,"Nuclear Export Controls:Can We Plug the Leaks?" in Jean-Francois Rioux,ed.,Limi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the Role of Supply-Side Strategies,Ottawa: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42.
⑧Harald Muller,After the Scandals:West German Non-Proliferation Policy,Fankfurt:Peace Research Institute,1990.
⑨Douglas Jehl,"Who Armed Iraq? Answers the West Didn't Want to Hear," New York Times,July 18,1993,p.E5.
⑩Paul Leventhal,"Nuclear Export Controls:Can We Plug the Leaks?" p.43.
(11)Brahma Chellaney,"The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Its Challenges and Rigors For India," in Francine Frankel,ed.,Bridg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Divide: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p.199.
(12)Ibid.,p.219.
(13)Alan Friedman,Spider's Web:the Secret History of How the White House Illegally Armed Iraq,New York:Bantam Books,1993,p.321.
(14)Richard Cupitt,Reluctant Champions:U.S.Presidential Policy and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s,New York:Routledge,2000,p.3.
(15)William Burrows and Robert Windrem,Critical Mass:The Dangerous Race for Superweapons in a Fragmenting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p.193-199.
(16)艾布拉姆·蔡斯、安东尼娅·蔡斯:《论遵约》,〔美〕利莎·马丁、贝思·西蒙斯主编:《国际制度》,黄仁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17)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4.
(18)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Nonproliferation Strategy Needed to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October 2002,p.20.
(19)关于隐性违规行为的详细论述,参见刘宏松:《浅析国际机制中的隐性违规现象及其理论含义》,《欧洲研究》1005年第3期,第66-79页。
(20)S.Goldman,K.Katzman and Z.S.Davis,"Russian Nuclear Reactor and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Ira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y 23,1995.
(21)Daniel Joyner,"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Present,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Regulation,Vol.10,No.3,Summer,2005,p.89.
(22)Ibid.,p.90.
(23)Richard Cupitt,Suzette Grillot and Yuzo Murayama,"The Determinants of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A Membership-Fee Explanation,"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Vol.8,No.2,Summer 2001,p.73.
(24)Henry Sokolski,Best of Intentions:America's Campaign against Strategic Weapons Proliferation,London:Westport,Connection,2001,p.69.
(25)Wyn Bowen,"U.S.Policy on Ballistic Missile Proliferation:The MTCR's First Decade (1987-1997),"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Vol.4,No.3,Fall 1997,p.29.
(26)"U.S.Waives Russia-Brazil MTCR Violation," Arms Control Today,Vol.25,No.8,July-August 1995,p.27.
(27)Henry Sokolski,Best of Intentions:America's Campaign Against Strategic Weapons Proliferation,p.72.
(28)Wyn Bowen,"U.S.Policy on Ballistic Missile Proliferation:The MTCR's First Decade (1987-1997),"p.30.
(29)Richard Cupitt,Suzette Grillot and Yuzo Murayama,"The Determinants of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A Membership-Fee Explanation," p.73.
(30)Adrew Lawler,"U.S.Sanctions Imposed,India Deal with Russia Still On," Space News,May 18-24,1992,p.14.
(31)Michael Lipson,"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Problems of Capacity or Organized Hypocrisy?" http://alcor.concordia.ca/~mlipson/Lipson_APSA2004rev.pdf,p.6.
(32)Igov Khripunov,"Export Control Assistance to Russia and Other FSU States," in Robert Einhorn and Michele Flourney,eds.,Protecting against the Spread of Nuclear,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An Action Agenda for the Global Partnership,Vol.2:The Challenges,Washington 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3,p.147.
(33)Michael Lipson,"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Problems of Capacity or Organized Hypocrisy?" p.7.
(34)Richard Cupitt,Suzette Grillot and Yuzo Murayama,"The Determinants of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A Membership-Fee Explanation," p.71.
(35)John Baker,"Nonproliferation Incentives for Russia and Ukraine," Adelphi Paper 309,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ichael Beck,"Russia's Rationale for Developing Export Controls",in Gary Bertsch and Suzette Grillot,eds.,Arms on the Market:Reducing the Threat of Prolifer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77-224.
(36)"Brazil Admitted to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BBC Summery of World Broadcasts,October 14,1995.
(37)Harald Muller,"Nuclear Export Controls in Europe:An Introduction," in Harald Muller,ed.,Nuclear Export Controls in Europe,Brussels: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5,p.26.
(38)这一评分体系的满分为100,一个国家的分值越高,说明其国内出口控制体系越完善。关于这一评分方法的详细说明,参见Michael Beck and Seema Gahlaut,"Introduction to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 in Michael Beck,ed.,To Supply or to Deny:Comparing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 in Five Countries,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p.1-27.
(39)Suzette Grillot,"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Framework,Theory and Method," in Michael Beck,ed.,To Supply or to Deny:Comparing Nonproliferation Export Controls in Five Countries,p.57.
(40)Jonas Tallberg,"Paths to Compliance:Enforcement,Management,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Summer 2002,p.611.
(41)Gary Bertsch and William Potter,eds.,Dangerous Weapons,Desperate States:Russia,Balarus,Kazakhstan,and Ukraine,New York:Routledge,1999,p.3.
(42)U.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roliferation Concerns:Assessing U.S.Efforts to Help Constrain Nuclear and Other Dangerous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7.
(43)Daniel Joyner,"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Present,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91.
(44)Ibid.,p.92.
(45)Daniel Joyner,"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Present,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92.
(46)Gaurav Kampani,"Second Tier Proliferation:The Case of Pakistan and North Korea,"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Vol.9,No.4,Fall/Winter 2002,pp.107-116; Chann Braun and Christopher Chyba,"Proliferation Rings:New Challenges to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2,Fall 2000,pp.5-49.
(47)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48)Peter Ka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
(49)Jeffery Legro,"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t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1,Winter 1997,p.35.
(50)Jan Hurd,"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2,Spring 1999,pp.393-399.
(51)Martha Finnemore and Ka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Autumn 1998,pp.887-917.
(52)Ibid.,p.914.
(53)Andrew Latham and Brian Bow,"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Bridgi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3,No.1,Summer 1998,pp.465-486.
(54)Michael Beck,"Reforming the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p.96.
(55)Brad Roberts,"Export Control and Biological Weapons:New Roles,New Challenges," Critical Review in Microbiology,Vol.24,Fall 1998,pp.235-248.
(56)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p.107.
(57)Michael Beck,"Reforming the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 Regimes," p.96.
(58)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2004年4月28日安全理事会第4956次会议通过,全文参见: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4/s1540.htm.
标签:非正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