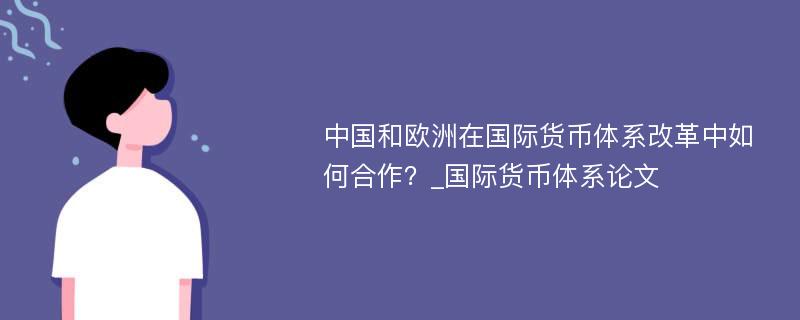
中欧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国际货币论文,体系论文,如何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欧关系而言,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让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提前”进入双方关系发展议程。中国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更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中国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另一方面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事务;欧洲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加强全球性金融监管,让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运转更符合“欧盟规则”。中欧双方的诉求实际上都触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将这一议题放在由法国担任主席国的G20峰会上进行讨论。毫无疑问,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中欧共同努力。那么,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能够展开合作吗?双方合作的动力来自哪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是什么?是否存在可具操作性的合作路径?这些都是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合作的动力
2010年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参加会议的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恩当日向媒体透露,中欧就改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了一致。① 虽然会议并未公开双方达成共识的具体内容,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和欧盟都认识到了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并给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在跨越国家疆界的交易活动中,为支付和收款所形成的一系列协定、规则、惯例和制度安排。②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美元本位制,各国自主决定各自的汇率制度,美元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枷锁”,美联储不再担负将各储备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纸币兑换成黄金的义务,美元也不再和任何贵金属、实体商品或者价值单位挂钩,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并承担全球储备货币的职能。这与二战前金本位和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黄金或者可兑换黄金的纸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安排有着本质区别。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经济交往中广泛承担着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等功能,保持币值稳定应当是其第一要义。但事实上,由于没有外部的“硬约束”,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方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就业和增长,将国内利益置于国际义务之上,这是现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内在矛盾。无论是之前直接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格林斯潘时代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现今伯南克为下一轮全球通胀埋下种子的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储备货币“币值稳定”的原则都被抛在脑后,美国以本国利益为取向的货币政策根本不考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要承担的责任。当美元价值改变时,其他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条件就会改变,这常常成为其他国家间贸易冲突的重要诱因。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困境”和“n-1问题”在美元本位下无法得到解决。所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超越美元”,③ 重新思考国际储备货币的安排。
一个稳定、健康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中国与欧盟的共同利益,这是双方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合作的动力源泉,这种共同利益主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约束美国不负责的货币政策是中欧共同诉求。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而中国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双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中欧都希望世界主要贸易国的货币价值保持稳定。由于当今扮演着“锚货币”角色的美元持续贬值,各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公开表示,2007年至2010年期间,美元贬值给其造成了30亿欧元的损失,因为空客的大部分成本是以欧元计价,但收入全部以美元计价。④ 对中国而言,美元贬值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风险,而且也使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不断缩水,造成国家财富流失。此外,美元贬值还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为全球通胀埋下隐患。正因为如此,当美联储公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提出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试图通过开印钞票刺激经济复苏时,遭到了欧盟国家的强烈批评。
其次,中国和欧盟都希望避免出现美元突然崩溃的危机。在美元本位下,美国可以用两种方式创造清偿能力:通过购买他国的商品和服务输出美元,或者通过对外投资来输出美元。美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因此实际上美国主要通过前一种方式来输出美元,这就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持续巨额赤字。同时,美国依靠其世界上最发达、最具深度和广度的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吸引其他国家将大部分美元储备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为美国的生产消费提供融资,这一循环造就了美国持续的大量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2008财政年度结束时,美公共债务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到2010年,美公共债务已超过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2%。如果美国未来继续实施减税措施,且政府开支占GDP份额保持2010年水平,那么到2020年美公共债务将可能达到GDP的100%。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使美国背上沉重的利息负担,美国要支付的利息将从2010年的197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7780亿美元。⑤ 一个国家的债务若无限度扩张,其主权信用破产并非遥不可及。为了避免美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情形,美国财政部目前正敦促国会提高政府债务的上限(14.3万亿美元),以允许美国在未来数月获得更多借款,从而避免出现危机。但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不可能永久持续,一旦美国债务规模的积累超过了债权国能够容忍的程度,美元信用就会瞬间出现危机,美元资产将被大量抛售,全球各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将遭受重大打击。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这种极端方式得到纠正的情形是中国和欧盟都竭力避免的,它们希望能够以相对公平和平稳的方式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为此,中欧双方在全球财经金融政策层面进行协调合作是必须的。
最后,中国和欧盟各自的金融战略需要对方的支持。欧盟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主张加强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包括经营机构、资本流动、杠杆率等要素,以及开征“系统性风险”税;主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国际机构作为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治理的主体。⑥ 欧盟的目的在于借此发挥自己在软实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同时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体制化”,融入以IMF和FSB等国际机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多边治理结构,避免这些国家凭借自己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另起炉灶”,建立地区性或者双边性金融机构或机制与之竞争,致使欧盟在国际金融货币事务中被边缘化。⑦ 另一方面,欧盟也希望人民币汇率变得更有弹性,从而能够扩大对华出口。而中国在经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更为坚定地迈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希望人民币逐渐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需要将人民币尽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货币中,同时稳步扩大人民币的跨国使用范围。中国还要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治理,增加自己在IMF、FSB等国际机构中的发言权,逐步掌握规则的制定权。虽然中欧双方的金融战略目标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双方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对方的合作。
二、中欧货币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金融被称为现代经济运行中的“血液”,如果中欧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能够让“梦想照进现实”,双方关系的发展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要实现这“惊人一跃”,中欧双方还要面对诸多挑战。
第一,中国和欧盟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承受的压力有差异,因此双方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不同。对美元霸权,欧洲人有着更早也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戴高乐就曾抱怨美元享有“过分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和美国政府的不流眼泪的赤字。美元币值动荡让当时欧洲各国货币饱受投机之苦,美国可以轻易通过借债和开动印钞机弥补欧美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赤字。尼克松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面对欧洲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诘难,一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让欧洲人心痛,欧洲国家更坚定了走货币联合之路的决心。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当时的欧共体采取了成员国货币固定汇率制,统一对美元浮动。欧元的问世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使欧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美元霸权的阴影。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欧盟国家可以不必积累大量美元来应付国际收支。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私人机构不断增加欧元储备,推动了欧元的国际化进程,使欧盟国家的融资能力大为增强。欧盟国家可以通过低成本发行债券和征收国际铸币税等方式获得充足资金,这让欧盟国家获得了相当大的空间来推迟或者转移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负担。虽然欧盟官方一向对欧元国际化表态谨慎,坚持欧盟绝不主动推进欧元国际化进程的立场,并认为欧元的国际地位应由市场力量决定,欧盟也不太愿意承认它从欧元国际化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但实际上,欧盟对欧元国际化在行动上并不消极,欧洲央行在2002年欧元现钞进入流通领域时发行500元的大面值钞票就是一个例证。尽管这种500元大钞在实际生活中使用非常不便,且遭到许多欧盟国家的超市和加油站拒收,但意大利央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2年,50元面值的钞票占欧元流通货币总量的34%,500元的占23%;而到了2010年2月,500元的占比升至36%,50元的则下降到31%。⑧ 2002年,流通中的500元钞票总额为308亿欧元,而到2010年则达到了2850亿欧元,年增长率达30%。⑨ 为什么这种在正常交易中很少被使用的大额钞票其规模和发行量增长如此之快?事实上,对500欧元大钞的需求有两类,一是游离于各国政权体制之外、基于现金交易的全球“地下经济”(毒品交易、走私等),二是金融系统脆弱或者社会动荡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发行500元大钞不仅使欧盟获得了可观的铸币税收入,同时它也成了欧元“曲线国际化”的重要工具。
科恩(Benjamin J.Cohen)将国际货币权力区分为“自主力”(Autonomy)和“影响力”(Influence)两个维度,前者指在货币事务上能够隔离外部压力,独立决策;后者指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在这两个维度中,前者是根本和基础,后者是从前者发展出来的。正所谓一种货币可以有自主力而没有影响力,但不可能有影响力而没有自主力。⑩ 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欧元基本上具备了自主力但是影响力欠缺;相比之下,人民币在这两方面都欠缺。中国在国际上一方面面临强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是让中国承担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负担),却无法有效转移或分散这种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又面临不断贬值的风险,正如克鲁格曼所形容的,中国掉进了“美元陷阱”。(11) 也就是说,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欧盟承受的压力要小于中国。双方在货币金融方面“疼痛点”和“疼痛程度”的差异,增加了彼此在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难度。
第二,欧元在信用支持和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让中欧货币合作变得复杂。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或者“法币”,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仅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它之所以能够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作为清偿手段被普遍接受,在于其背后国家主权的强制力和信用程度。国家在通过发行货币获取收益的同时,货币使用者也就默认了国家负有在危机时刻维持货币价值和提供及时有效的债务清偿手段的义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来保持国内稳定和抵御外部入侵,其发行货币的价值和被接受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一样,其背后有一个单一的中央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支持,而欧元则是一种没有主权国家为依托的货币。(12) 欧元诞生于欧盟成员国政府之间一系列政治谈判后所达成的协定,这些纸面上的文字如何维持人们使用欧元的信心?假如欧盟面临外部威胁,谁来出面“摆平”?在欧元解决中央政府缺位的问题上,蒙代尔给出了答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只要欧盟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靠美国的军事联盟,即使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欧盟也足以对抗任何外来敌人。(13) 北约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欧元信用的一个重要支撑,用欧洲人自己的话来说,欧洲为美元霸权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是为美国向欧洲提供军事保护所付出的必要军费。(14) 在中欧货币合作问题上,美国必然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外部因素,这就增加了中欧合作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此外,欧元的对外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欧盟实行单一货币后,设计和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和制度以确保欧元顺利运行,但关于欧元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却相当分散,欧盟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对外代表欧元。始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欧元问世后面对的第一次严峻挑战,也使得“谁代表欧元”这一问题再次凸显。2010年4月底,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IMF总裁卡恩在向满腹狐疑的德国联邦议院解释德国加入救助计划的重要性时,态度之恳切让很多观察家想到了2008年底美国财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恳请议员们通过备受争议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几次打电话给德国总理默克尔,以确认德国将支持援助计划;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eble)也成了美国财长盖特纳唯一要与之会晤和讨论欧洲债务危机的欧元区财长。在这次欧元危机中,各国政府、政策分析人士和市场的目光都跳过了那些理论上欧盟和欧元的代表者,焦点集中在一个国家和它的领导人身上:德国和默克尔。不少政要甚至认为,默克尔才是欧盟和欧元区事实上的主席。(15)
因此,中国在与欧盟进行货币领域合作时,面对的将不是一个单一的欧元代表机构,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状的和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以欧元在IMF的代表权为例。IMF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货币与金融事务机构,也是中欧在国际金融货币事务进行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欧盟正式负责IMF事务的有两个机构,一个设在布鲁塞尔,是部长理事会所属经济与货币委员会内的一个部门,被称为SCIMF(the“Sub-Committee on IMF),主要负责为经货委员会准备关于IMF或与之相关的工作。SCIMF通过的文件没有约束力,成员国在IMF的执行董事可以不按SCIMF的意见行事。另一个机构欧盟IMF代表团(EURIMF)设在华盛顿,是一个非正式组织,由欧盟成员国在IMF的代表组成,主要功能是成员国之间交换信息和协调立场。(16) 在欧元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机构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集团,但前者在IMF中只有一个观察员席位,而后者仅是欧盟的一个非正式组织,这两个机构在IMF的话语权非常有限,无法作为谈判对手。实际上,欧元在IMF的代表权非常复杂地分散在隶属不同选区的成员国和欧盟机构手中。欧洲学者曾提出将欧盟成员国在IMF的席位合并为一,或者分为欧元区和非欧元区两个席位,以增强欧盟在货币事务上的谈判能力和便利处理与他国的金融货币合作问题。(17) 但目前来看,这两种方案在欧盟内部都遇到了阻力,小国担心席位合并后失去在IMF的话语权,而大国则害怕其影响力被稀释。面对欧元复杂的治理结构,中欧货币合作仅在技术和程序层面就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欧盟对于中欧货币合作抱有较强的戒备心理。中国对于同欧盟在各个层面的合作一直抱着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但欧盟近年来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和怀疑情绪不断增强(18)。在欧洲人看来,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中国人吃苦耐劳、工作勤奋,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努力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并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巨大,发展过程充满着不为欧洲人所掌控和理解的不确定性,欧洲人目前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工作岗位正因这一进程的庞大规模和不断加快的速度而减少。这种消极的“中国观”使得欧洲领导人经常对来自中国哪怕是善意的举措也都以恶意去揣测,致使许多有益于双方的合作都因缺乏政治意愿而无法实现。货币金融合作虽然潜力巨大且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由于其在政治经济运行中牵一发而动全局,也就更容易触动欧洲人敏感的神经。希腊在爆发主权债务初期曾主动和中国接触,希望中国为其国债融资提供帮助。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在欧盟引起了非理性的不安情绪和强烈质疑,一些欧盟政要和媒体指责中国要将希腊变成自己在欧盟内的特洛伊木马。直到希腊危机愈演愈烈并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信任危机时,欧盟的态度才逐渐变得务实,不再把国债问题泛政治化。2010年7月,欧盟贸易委员古赫特(Karel de Gucht)公开表示,中国购买了约4.2亿欧元希腊和西班牙发行的债券,并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投资选择。尽管如此,欧盟内部担心中国通过大规模持有其成员国债券而增强对欧盟影响力的忧虑仍然普遍存在。
三、中欧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
由于货币所具有的天然权力属性,国际货币合作注定将是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既能为合作双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最容易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和猜忌。所以,合作路径的选择尤为重要。中欧货币合作有两种可选路径。第一种可称为战略导向型,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将直接导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如此,双方将更多地采取政治合作方式,比如在改革IMF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协调双方在IMF中的立场,共同推动SDR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增加,特别是通过用SDR作为部分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稳定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实现SDR在私有部门的使用;也可以通过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转换双方外汇储备和贸易往来所使用的币种,改变目前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第二种路径为需求导向型,是指在互利原则下通过解决彼此在金融货币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主要采用经济合作方式,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但主要以市场力量推动。
很显然,第二种路径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不太容易遭遇政治阻力,并且合作主体是中欧双方的企业,中欧之间庞大的贸易量和不断增长的相互投资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需求空间。从可操作性来考虑,中欧货币合作应以第二种路径为主,同时辅之以第一种路径。对中国而言,可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更为积极和主动的作用。虽然欧洲的危机整体上对中国并未造成伤害,但我们不能因此抱着一种看客心态。一方面,欧元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输欧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欧元计价,欧元暴跌将给中国出口商造成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欧元的存在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分散化投资中多了一个选择,而欧元崩溃会使中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承受更多压力。另一方面,欧债危机为开启中欧货币合作打开了一个“机会窗口”。随着希腊、爱尔兰先后陷入债务困境,欧盟传统的“一事一议”危机处理模式使其疲于应付,应接不暇。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与其他欧洲国家主权债务信用违约掉期(CDS)价格相比,近期欧盟成员国中的“援助大户”德国成为CDS价格增幅最大的国家之一,法国、荷兰等其他欧盟核心成员国的CDS价格也急剧飙升,这些国家与包括丹麦、挪威和冰岛在内的非欧元区成员国的CDS利差扩大至欧元面世以来的最高值。(19) 这意味着经过连续不断地“输血”,市场对德国和法国这些财政状况良好国家的信用支付能力也开始担忧,对它们的还债能力提出质疑,这将加大这些国家未来的融资成本,使整个欧盟财政能力下降。欧盟也在考虑建立一种永久性的危机解决机制,比如一些欧洲领导人倡议发行欧盟统一主权债券(E-Bonds)。但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涉及如何融资筹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支持欧盟的危机应对措施,并要有所作为,如鼓励欧盟机构或者其成员国到中国发行债券,或者由中国的金融机构向欧洲金融系统提供融资。这样做既能解决欧洲的资金问题,也符合中国投资分散化的总体策略,同时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债权国地位将大大加强中国在处理对欧关系时的谈判实力。
第二,鼓励欧洲企业和个人持有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摆脱美元霸权的根本出路,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基础部分一步步做起。其他国家央行是否具有储备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并不受我们控制,但却同这个国家的企业和私人的投资偏好具有密切关系。如果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某种货币或者以这种货币计价的流动性资产,那么央行自然需要进行储备以保证国际收支正常。因此,通过市场力量鼓励和引导国外企业和个人储备、使用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相当高水平,这为双方在金融货币领域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逐步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为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中国于2010年9月对2005年制定的《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按照之前的规定,债券发行人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只能用于中国境内项目,不得换成外汇转移至境外;而修订后的《办法》规定,发行人可以将所筹集的人民币资金直接汇出境外使用,也可以在中国境内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后汇出境外使用。《办法》的修订意味着今后欧盟的开发机构可以在中国募集其发展项目所需资金,而中国也可以借此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减少外汇储备。又如,自2010年以来,外国企业已被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而之前只有中国的金融机构才有此资格。8月份麦当劳(McDonald)第一个在香港成功发行了2亿元人民币债券,美国推土机制造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也将在香港发行两年期总计10亿人民币的债券。这两家都是在华经营多年的美国跨国公司。欧洲在华企业也很多,如果它们直接在香港发行企业债,不仅融资成本低,还能有效避开汇率风险。此外,人民币的跨国结算业务也在不断扩展,更多外资银行获得了经营资格,汇丰、渣打、西班牙对外银行等欧洲银行都在其中,这为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选择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提供了便利和条件。(20) 最后,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的具体政策措施也正在加紧研究和筹备中,一旦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发行股票,更大规模的人民币资产将被国外企业持有和使用,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积极参与IMF治理结构和职能转变盼改革。在此次金融危机前,IMF的处境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一则由于许多借款国提前还清了贷款,而新兴国家因为普遍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没有贷款需求,IMF所依赖的利息收入下降迅速,其为解决国际收支问题所能动用的资源严重不足;二则IMF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亚洲国家开出的经济紧缩药方和苛刻的贷款条件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IMF的名誉和公信力遭到严重损害。但全球金融危机使IMF的作用被重新发现,IMF再一次回到了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心位置,加强IMF的监管监测职能和提高对IMF的注资额度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可以预见,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很多规范未来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则和制度将在IMF框架下制定执行,IMF必定成为大国间利益博弈的重要战场。同样,IMF也是中欧货币合作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IMF治理结构已经不能反映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改革势在必行。一个基本的改革共识是欧盟国家目前拥有的投票权大大超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份额,需要让渡一部分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欧盟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中也确认要让出在IMF执行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中国的投票权将提高。但欧盟国家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让出投票权,相关决议的最终落实将是一个艰难的讨价还价过程。在IMF职能转变问题上,欧盟希望加强它的多边和双边宏观经济监测职能,这也是中国所赞成的;但在增加IMF自身财政资源方面,中国鼓励IMF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为自己融资,同时扩大SDR的使用范围,而欧盟对此态度并不积极,双方还需要凝聚更多的共识。
结语
中国和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进行合作对双方都是一个新课题,但却是一个拥有巨大空间和潜力的合作领域。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让本国的货币制度更具效率和竞争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这其中的核心仍然是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巨额融资”能力(capability of high finance)。(21)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进程中,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开展对外金融货币合作。鉴于欧盟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国需要它的先进经验和战略合作。对于欧盟而言,积极推进中欧货币合作不仅能够巩固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可以分享这种合作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更广泛的角度讲,中欧货币合作无疑将有利于充实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注释:
① “中欧经贸以和为贵,牵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新华网,http://news.xjnhuanet.con/fortune/2010-12/22/c_12906683_2.htm.(上网时间:2010年12月25日)
② Rober Solomon,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1945-1976,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7,pp.5-6.
③ Paola Subacchi,“No New Bretton Woods,but a System in Flux”,Paola Subacchi and John Driffill eds.,Beyond the Dollar: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Chatham House,March 2010,p.4.
④ “空客:美元疲软令公司三年损失30亿欧元”,《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www.cn.wsj.com/gb/20110118/BEU006023.asp.(上网时间:2011年1月19目)
⑤ “Federal Debt and Interest Cost”,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December 2010,p.26.
⑥ Garry J.Schinasi and Edwin Truman,“Reform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Brugel Working Paper,2010/05,pp.6-16,31-35.
⑦ Alan Ahearne and Barry Eichengreen,“Exter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y:a review and a proposal”,in Andre Spir ed.,Fragmented Power:Europe and Global Economy,Bruegel,2007 July,pp.129-130.
⑧ “500-Euro Bill Lifts Crime,Terror,Tax Risk,Bank of Italy Says”,Bloomberg,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0-04-19/500-euro-bill-lifts-crime-terror-tax-risk-bank-of-italy-says.html.(上网时间:2010年12月19日)
⑨ “‘Criminal’500 euro bills contribute to ECB profits”,Financial Crime Online,http://financialcrimeonline.com/archives/1010,(上网时间:2010年12月10日)
⑩ Benjamin J.Cohen,“Currency and Sate Power”,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to honor Stephen D.Krasner,Stanford University,December 4-5,2009,p.4.
(11) Paul Krugman,“China's Dollar Trap”,The New York Time,April 2,2009.
(12) Otmar Issing,The Birth of the Eur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28-234.
(13) [加]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14) Pierre Defraigne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题为“作为全球合作伙伴的中国与欧盟”研讨会上的发言,2010年11月22日。
(15) Wolfgang Proissl,“Why Germany fell out of love with Europe”,Bruegel Essay,July 2010,pp.5-6.
(16) “European Coordination at the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 Question of Harmony?” Eurodad,January 2006,pp.8-10; Alan Ahearne and Barry Eichengreen,“Exter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y:a review and a proposal”,in Andre Sapir ed.Fragmented Power:Europe and Global Economy,Bruegel,Brussels,July 2007,pp.135-136.
(17) Lorenzo Bini Smaghi,“A Single EU Seat in IMF?”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2,No.2,2004,pp.244-246; Peter Brandner,Harald Grech,“Unifying the EU Representation at IMF—A Voting Power Analysis”,Federal Ministry of Finance,Working Paper,2/2009,pp.16-24.
(18) 周弘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08~2009):欧盟“中国观”的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19) “欧盟酝酿建立永久性危机解决机制”,《中国证券报》,2010年11月30日。
(20) 汇丰银行在20lO年8月完成了第一笔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并表示愿意更多地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参见HSBC News Release,30 September 2010.
(21) 阿瑞吉等人在解释18世纪到20世纪世界霸权兴衰中运用了“巨额融资能力”这一概念,参见:[美]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第43页。
标签: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货币国际化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欧盟成员国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欧元兑人民币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美元欧元论文; 国际债券论文; 外汇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