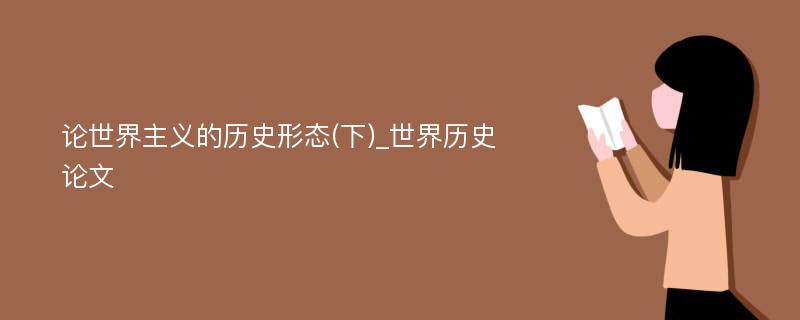
论世界主义思想的历史形态(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主义论文,之二论文,形态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世界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取向
黑格尔之后,世界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新史学多元研究方法的诞生,世界主义思想与行为的耦合由欧洲、美国走向全世界,同时又形成学术思想的不同形态:政治取向、学术取向与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分别以自己的形态走到历史的前台。在这些取向当中,尤以政治取向的世界主义的影响最直接,而且效果也最显著。
第一,柯林武德、霍布斯鲍姆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在学术取向的基础上对世界主义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术取向的世界主义突出历史的思想性质和理性精神。柯林武德认为,自然的过程可以被确切地描述为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这是因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它是由一些思想过程所构成的,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注:参见[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273页。)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得益于两个方面的证据:一是得益于历史事实本身。柯林武德说,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问题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着上帝与人的关系。从16世纪到19世纪,思想的主要努力关注于奠定自然科学的基础,于是哲学就把这种关系即把人类心灵作为主体而把它周围空间的事物的自然世界作为客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做自己的主题。(注:参见[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5页。)二是得益于人类历史过程与自然进化过程的比较。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人被认为是历史过程的惟一主体,因为人被认为是在想(或者说在充分地想,而且是在充分明确地想)使自己的行动成为自己的思想表现的惟一动物。(注:参见[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24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缘由,柯林武德认为,思想是历史的惟一对象,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注:参见[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344页。)由此,世界主义也就只能是一种人类思想的产物。
其次,学术取向的世界主义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并且用全球的目光看问题。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经验作为一个整体被设想为过去事件的一个体系。(注:参见[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74页。)霍布斯鲍姆则认为,历史学家不论属于那一个微观世界,他们都有着普世主义的义务,这不仅是出于对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向往的某种理想的忠诚,而且也因为这是理解人类局部历史乃至全部历史的必要条件。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一种人类集体都是一个更广阔和更复杂的世界总体的组成部分。(注:参见E.J.Hobsbawm,“Identity History is not Enough”,in Below (ed.),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s Press,1997,p.277。)关于西方史学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基本模式,至少在十月革命之前,它应该是人类惟一的发展模式;即使到了20世纪,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主动的、原创的发展模式,而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模式都属于被动的、衍生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但同时也渗透着在西方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因素。
斯塔夫里阿诺斯则主张用全球历史观来阐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全球通史》所研究的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注: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4页。)众所周知,历史发展到19世纪,几乎整个世界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当代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世界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因为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冲突之中。从总体上看,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问题,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解决自己的问题。由此可见,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问题都要多、都要复杂。《全球通史》是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它论述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文明进程。该书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确立了当代世界历史的全球意识。巴勒克拉夫说,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注:参见[美]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发展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5—246页。)可见,当代世界主义已经超越欧洲与美国的区域,与全球史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以阿多尔诺(又译作阿多诺)、汤因比和巴勒克拉夫为代表的世界主义是一种道德取向的历史观。
首先,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是与学者的良心和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尔诺就曾明确地反对黑格尔所主张的世界主义观念的建立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历史观。阿多尔诺说,当黑格尔在思考历史时,他的确为历史付出了很高的“关税”,但他的思想也接近了这样一点:当他把民族精神实在化时,他也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把民族精神相对化了,他认为可能有一天世界精神可以放弃民族精神,从而为世界主义留下地盘。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新的民族精神都是在征服世界精神上迈出的新的一步,都是赢得它的意识和它的自由的一步。民族精神的死亡是向生命的过渡,但不同于自然界中一个生物的死亡将带来一个与它相似的生物的生命。毋宁说,世界精神从低级的规定性前进到更高级的原则和它自身的概念,前进到它的观念的更充分的表现。(注:参见[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02—303页。)阿多尔诺是有良知的思想家,如果拿他的观点来影响世界政治,那将保全许多珍贵的生命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他早就认清世界主义的性质及其历史变迁的状况。他认为,世界精神概念中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从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不合理性借来的,但它仍然是一种拜物教的精神。阿多尔诺说,像命运的内在性一样,世界精神充满了苦难和错误。(注:参见[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第340—341页。)正是由于阿多尔诺认清了以世界精神为内核的世界历史或普遍史的本质,因此他的态度是批判的、建设性的。
其次,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在体现整体意识的同时,突出对于生态文化的关怀。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史是人与生物圈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非另一个极端意义上的全体,而是我们所称的某一群人类。(注:参见[英]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页。)因为这两点原因,汤因比主张人类应当在觉醒之后,正视5000年文明中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之间的鸿沟,而不至于因为对地球犯下弑母之罪而导致自身的毁灭。(注:参见[英]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30页。)
再次,平等观念也是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主义的史学研究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目光投射到世界的每一个区域和每一个时代。(注:参见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5,p.27。)他认为,“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地失去其有效性,事实上“欧洲老大”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其影响范围正由于其他强国的崛起而不断收缩,对于全球政治结构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欧洲均衡体系。(注:参见Geoffrey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Pelican Books,1967,p.107。)因此,巴勒克拉夫的世界主义观念在放眼世界、展示全球的背景下,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整体意识和平等的人文精神。
当然,学术取向和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还有其他特点,比如宗教理念和不同程度的欧洲中心意识。霍布斯鲍姆就认为,20世纪的人类文明完全建立在19世纪文明的基础之上,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文明开始崩溃了。它的特征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宪政结构上的自由主义,欧洲是这种文明的中心。他甚至认为,这一模式是世界惟一的代表进步的发展模式。还有一些欧洲学者则认为,是欧洲人将世界连成了一体,而且这一联合被认为是技术上的显著进步。其部分原因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森林和荒地的时候,欧洲在这一时代已成为非常先进的地区。因此,他们认为这是欧洲对近代世界的贡献,并且把欧洲人在1500—1763年之间铺平了19世纪统治世界之路看成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注:参见Irene Karpisek (ed.),A Global History,Allyn and Bacon Inc.,1979,pp.79,96。)
除此以外,巴勒克拉夫的富有历史责任感的世界主义观点也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一些阶段,而不可能走向终结。比如,引起世界秩序空前紊乱的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学家来说, 没有其他事件比之更能明显地显示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它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巴勒克拉夫认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不同步的。1914年至1945年欧洲列强的敌对与冲突导致“欧洲中心”的瓦解,然而这一瓦解实际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他认为,1890年至1960年期间,人们面临着连接两头的历史过程,即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欧洲列强的冲突在说明一个时代的终结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注:参见[美]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8、23页。)对于整个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来说,巴勒克拉夫认为,它的主要阶段应当是“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植根于欧洲历史的各种问题正在失去其紧迫性,欧洲民族主义时代的价值观念已趋消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成为几乎毫无意义的存在,世界历史的重心已经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注:参见[美]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第14、33页。)尽管巴勒克拉夫对于世界文明的划分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其后果依然可以将美国人的视线由地中海、欧洲、大西洋进而转向太平洋,更何况巴勒克拉夫的文明阶段理论是建立在“从欧洲中心到世界范围的政治体系的转变”的观点之上的。(注:参见[美]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第11页。)因此,即便是对于学术取向和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观念,也要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和批判吸收的方法。
第三,政治取向的世界主义是诸多世界主义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事实上,从雅典人到日耳曼人,世界主义总是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传达给人以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只是在传统史学的语境中形成的。到了19世纪,兰克最早在现代史学的语境中为世界主义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与理论体系。兰克在晚年编纂、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的《世界史》是一部集中书写以拉丁、日耳曼等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它体现了欧洲人在近代社会中凭借理性与科技不断崛起的历史进程,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第一次把哥丁根学派的“欧洲中心论”拓展为贯穿古今的“西欧中心论”,以此构成现代史学语境与意识形态背景下世界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基本路向。
东欧风波的爆发,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的发展中,弗朗西斯·福山是“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富有代表性的世界主义理念。
福山是从康德、黑格尔、柯耶夫那里获得思想资源的。他们的具体观点是:其一,康德指出,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也就是说,历史有一个蕴藏在人目前的潜意识中并且使整个历史具有意义的终极目标,这个终点就是实现人类自由。因为一个根据外部法所获得的自由社会是与不可抗力的权利(即一部充满正义的公民宪法)高度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是大自然给人类提出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因此制定一部正义的公民宪法以及这部宪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就成为我们判断历史的标准。如果把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都考虑进去,一部世界普遍史所要回答的问题应当是:是否存在一个总的理由来说服全人类,共和制政府(即我们当今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进步的?(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5页。)其二,当黑格尔宣告历史在1806年普、法耶拿战役后就已结束时,他显然不主张自由国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种胜利甚至在当时他所居住的德国乡下也是不确定的。他所要表达的是,自由、平等这两个现代自由国家必须遵循的原则已经被发现并在最发达的国家内得以实行,而且没有其他原则或社会形态即政治组织比自由社会或组织更优越。换言之,自由社会不存在早期社会组织形式中特有的矛盾,历史的辩证法因此画上了一个句号。(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其三,柯耶夫说:观察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思考一下耶拿战役之后世界发生的变化,我们理解到,黑格尔把这次战役视为所谓历史的终结是正确的。在这次战役中并通过这次战役,人类的先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终点和目标,即人类历史的终点。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罗伯斯比尔—拿破仑在法国付诸实践的世界革命的延伸。从真正的历史观点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先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只有一个作用,即把周边地区的文化提升到最先进的(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欧洲的历史水平。(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75页。)
在康德那里,历史的终结既是一种理论预设,又是一种宗教伦理上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康德出于对自由力量的彰显,用预设的方式对历史给出一个可能性的设计;另一方面,为了表现出对于道德沦丧的感受,康德才在《万物的终结》一文中提出了宗教伦理上的价值判断。相比之下,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根源更多的是在于一种哲学体系的完成,而不是实证的历史研究或科学规律的揭示。柯耶夫则用“虚拟”的方式在学理上把学术引向歧途。福山对康德、黑格尔和柯耶夫的观点和盘接受,这正是福山理论在学术理路上的缺陷。
在诸多学说中,黑格尔的理论是最受福山重视的,因此笔者只想解剖一下黑格尔的普遍史学说和世界主义思想。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是以他的理念学说为根据的:从纯粹理念出发,通过否定自身到达现象界,然后再凭借对现象界的否定实现对绝对理念的回归。也就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历史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有”高于“无”,“无限”高于“有限”。因此,否定之否定并不是一种中性状态。“无限”是肯定的,只有“有限”才会被扬弃。(注:参见[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1页。)从黑格尔心灵哲学体系的开端便可以观察到历史思想的完成。黑格尔说:开始思维时,除了无规定性的思想外,没有别的,因为在规定性中已包含“其一”与“其他”;但开始时,我们尚没有“其他”。最原始的无规定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这种“有”是不可感觉、不可直观、不可表象的,而是一种纯思,并以这种纯思作为逻辑学的开端。(注:参见[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0页。)也就是说,纯粹的、自由的思想、理念或精神,是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始,因此“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注: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468页。)
尽管“历史终结论”出自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成,然而黑格尔却是一位伟大的、负责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因片面维护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失去一位思想家的真理意识与道德精神。黑格尔认为,哲学史有责任去确切指出哲学内容的历史开展与纯逻辑理念的辩证开展一方面如何一致,另一方面又如何有出入。(注:参见[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第191页。)因此,在充分肯定世界历史之前,首先确立其具体的实在性和多元性。黑格尔说:“景象万千、事态纷呈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证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和现在发生的种种事情,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注: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468页。)对于正当性问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应该体现它的普遍性。其原因在于,世界历史超出于这些观点之上。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观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这种环节作为自然原则所归属的那个民族,在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发展进程中,有执行这种环节的使命。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它在世界历史中创立了新的纪元,但只能是一次性的。(注:参见[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3—354页。)在黑格尔的视阈中,这个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性的民族。仔细地思考一下历史,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法兰西、日耳曼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性质的民族,都一次性地进入了世界历史。
尽管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的过失在于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然而后来的思想家们依然不会轻易放手,而是给予有力的批判。阿多尔诺说:正如数学的自然科学史曾激励过康德的哲学一样,世界史概念的有效性也激励了黑格尔的哲学。统一的世界越是近似于一个总过程,世界史的概念就越成问题。一方面,实证主义推进的历史科学瓦解了关于总体性和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概念;另一方面,先进的哲学肯定注意到了世界史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受挫折的生活的不连续性。(注:参见[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第333页。)阿多尔诺不仅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割断了的”辩证法,(注:参见[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第318页。)而且揭示出近代世界主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本质特征。
事实上,世界主义只是历史的某一种特性,既不是惟一的特性,也不可能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特性。原因很简单,存在的本原在于历史的个性。整体不是全部历史的主旋律,而仅仅是史前史的主题,而且通常是作为史前史的简单的前提和限度而存在的;(注:参见Agnes Heller,A Theory of History,St.Edmundsbury Press,p.215。)即便是在史后史中有可能出现,它也不是历史的主旋律,更何况福山的“后历史”只是以“虚拟”为依据的。
福山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弊端是:严格地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一部很不纯粹的学术著作,意识形态宗旨才是这部书的本质精神或根本目的。简单地说,《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根本宗旨是:从历史上有关世界主义思想的资源中选取有益于美国意识形态的东西,避开综合历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美国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推行所谓的自由主义,从而实现“把周边地区的文化提升到最先进的(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美国的“历史水平”(借用柯耶夫语)。其实,福山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东欧风波和美利坚给他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已。正像对待历史一样,福山是在用其左手打他的右手,即用世界主义打综合主义,从而为美国的意识形态而奔走效劳。
福山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是:1806年以后,罗伯斯比尔—拿破仑已成为世界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的核心便是自由;此后的历史只是自由历史的完善与延续;东欧风波证明,社会主义、集权主义没有出路,自由主义已成为人类历史最后的也是惟一的旗帜,而且美国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因此美国人有责任用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无论是用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方式——来规范这个世界,由美国人来书写当代世界史。他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是这样的:
第一,东欧风波,特别是苏联解体,证明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是正确的。历史终结则标志着自由主义的最后胜利。面对诸多历史现象,福山认为,人们必须从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过去几个世纪中真正世界文化的出现,而世界文化则以科技主导的经济增长及生产和维系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核心。即使曾经寻求抗拒这种“融合”的社会,从德川家族的日本到奥斯曼土耳其、前苏联、中国、缅甸和伊朗,也只能坚持一两代人。这些国家没有被占优势的军事技术所打败,却倒在现代自然科学的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中。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消费至上的社会,但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社会不以此为目标。原因很简单,规模与实力极其强大的前苏联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42页。)
第二,自由主义的使命就是要消灭专制主义。实际上,在福山的话语中,专制主义就是伊斯兰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说:专制主义国家除面临政治危机外,经济领域也在发生更悄然、更巨大的革命。 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两大危机只留下惟一的竞争者作为具有潜在的全球价值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民主制度。(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36—37页。)福山是如何理解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呢?他说: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伊斯兰教确实战胜了自由民主制度,即使在伊斯兰教没有直接掌握政权的国度中,它也对自由构成极大的威胁。实际上,从长远看,在伊斯兰世界中伊斯兰主义终究无法与自由思想相匹敌,因为这种自由主义已经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穆斯林。(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51页。)福山又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按需而不是按贡献大小分配及消灭人类天生的不平等,借此来推行牺牲自由的极端的社会平等形式。将来试图超越“中产阶级社会”建立社会平等的设想,都必须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这一设想在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因为如果要根除那些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肯定会创造出一个魔鬼般的国家。他还以柬埔寨、前苏联等国的社会主义历程为例说,共产主义制度必然产生新阶级的党魁和官僚。(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332页。)福山认为,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并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真正的选择,而是成为通向灭亡的历史岔道;这些最正宗的专制主义尽管造成了无数的人成为它们的牺牲品,但其寿命都很短(希特勒主义在1945年、斯大林主义在1956年寿终正寝)。(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43页。)由此可以看出,福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其实他很清楚,正是马克思主义把法西斯主义送进了历史的坟墓。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第三,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为纯粹的名誉而殊死战斗,这显然是为霸权主义、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提供“合理的”依据。福山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典范,它有责任承担这一使命,即:领导“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为消灭专制主义、为获得认可的欲望而血腥战斗。福山借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观点说,在人的本性中,有三个导致战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为荣誉,而正是荣誉会使人为一些区区小事——不论是直接涉及本人还是涉及其家族、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民族、他们的职业或他们的名字——而变得有攻击性。于是,为了美国人的所谓荣誉,福山倡导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黑格尔的血腥战斗和福山祖国的武士道精神。(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67页。)黑格尔所说的认可或承认,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民族是在由游牧民、部落群体向国家状态过渡的过程中,尚未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状态下出现的:一方面是毫无利害感觉的愚昧的天真,另一方面是为获得形式上的承认而斗争的勇气和复仇的勇气。与此同时,文明民族意识到“野蛮人”所具有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是不相等的,因而把他们的独立当做某种形式的东西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战争和争端,是争取对一种特定价值的承认的斗争,这一特征给这些战争和争端以世界历史的意义。(注:参见[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355—356页。)显然,这为以推行“自由”和“民主”为借口而发动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可见,福山的所谓世界历史观的目的是用武力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推向全世界,而且首先推向伊斯兰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美国、以色列便可以肆意屠杀伊斯兰民族,肆意践踏人权和主权。相比之下,究竟哪一种是野蛮现象,哪一种是法西斯主义呢?
四、世界主义对当代历史发展的启示
笔者认为,福山看到的东西,阿多尔诺也看到了。然而,阿多尔诺的发现的背后是一个学者的良心,他不仅确认世界历史与区域历史并存,而且避免世界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福山则不然,他的发现的背后是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的野心正好可以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旗帜下发挥其威力。笔者认为,世界主义背景下的历史终结论,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范畴,自由主义只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完成,即封建主义的终结,而不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终结。黑格尔把这个现象看成“最高成就”。他说,这个最高成就,它必须而且注定要完成,但是这种完成同时也是它的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另一个世界历史纪元的发生。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达到全体联系——达到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注: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第113页。)即便有一天,人类完成了历史的大循环,世界也将依然向着更高级次的未来升迁。福山的观点不仅是形而上学的,而且是违背世界伦理的,它不仅阻碍人类文明的进展,还将导致世界的混乱。事实上,福山著作的意识形态性质太明显了。在福山的所谓民主国家的谱系中,根本就找不到伊斯兰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55—57页。)其立论之宗旨可谓昭然若揭。
在世界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可以直接感受到世界主义思想对世界与大国决策的影响。
首先,世界主义思想直接影响着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比如,经常被人们认为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智慧之举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尽管威尔逊对于国际和平组织予以鼎力支持,但真正的结果是来自于世界许多意见相近的政治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出的决定)的共同努力。(注:参见Norman Lowe,Mastering Modern World Hist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2,p.197。)到了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替代了不可信的国联并消除了因其失误所导致的郁闷。苏、美、中、英1944年在美国的敦巴顿橡树园提出的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在旧金山获得正式通过。(注:参见Norman Lowe,Mastering Modern World Hist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2,第367页。)
其次,世界主义思想对大国间的政治也会带来明显的影响。1997年1月,克林顿在第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因此美国将领导实行民主制的整个世界。(注:参见李剑鸣、章彤编,陈雅丽等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6—489页。)2001年,新诞生的美国布什政府以为,东欧风波与科索沃战争已经将欧洲摆平,所以一边靠以色列制衡中东,一边把中心移向东亚,尤其是中国。布什政府一边将中美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下降到“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系,同时把美国的巡航导弹和核潜艇的部署由夏威夷推进到关岛。突发的“9·11 ”事件使发懵的布什政府把军事目标重新瞄准伊斯兰国家。同时,根据美国人的意志从伊斯兰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圈出“邪恶轴心国家”、“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国家”,并准备随时采取单边行动,企图先发制人。显然,从克林顿的演说可以感受到但丁的民族优越论,而布什政府的行为则充分体现了福山的世界主义思想。
从古典文明到当代文明,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世界主义从思想到实践、从民族优越理论到当代世界霸权话语的历史进程。显而易见,传统社会的世界主义在地域上主要存在于西亚和南欧,在内涵上是以神性为背景的,或者说是以上帝为核心的,而且思想与实践常常处于交叉与错位的被动状态之中;近代社会的世界主义在地域上主要存在于西欧和美国,在内涵上更多是由于哲学解构宗教不仅成为可能,而且科学、技术的崛起尤其是宗教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主义的品质,并使之转换成为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文明合二为一的、富有张力的理念和霸权话语。世界主义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和历史的危机。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的世界主义以其绝对的优势几乎压倒乃至取代学术与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因此,在当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于以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以美国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世界主义,如果不能以平等和辩证的方式加以调整并使之获得存在的正当性的话,那么世界主义必将给伊斯兰文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越来越深重的灾难。笔者认为,世界主义经历了由西亚向南欧、西欧并经过欧洲向美国方向的进发,以及由西方向全球化方向的拓展。世界主义的合理性有待于学术与道德取向的世界主义的崛起,有待于民族史乃至综合历史及其本质精神的崛兴。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代、区域与整体、一元与多元、世界与民族的普遍悖立、互补的状态之中,重建学者的真理意识和道德精神,以虔诚的学术良心和真理的推动力加快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建设,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当代民族国家及其社会发展的共存与互融问题,让世界主义问题的研究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向着和谐、进步与幸福的方向发展。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的观念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弗朗西斯·福山论文; 小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