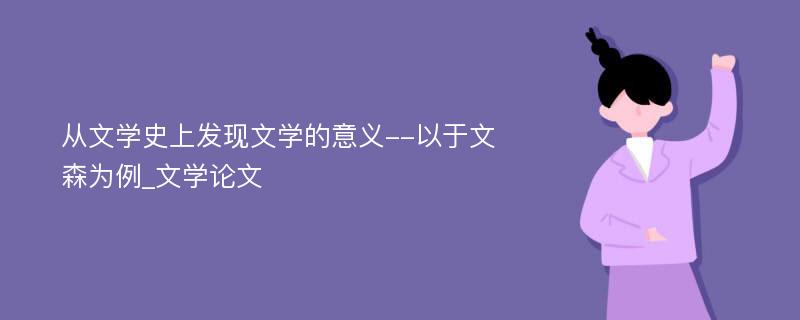
从文学史发现文学的意义——以宇文所安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文学史论文,宇文论文,意义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9;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6-0031-0
对宇文所安来说,文学的意义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中心,文学史研究应该凸显文学的当代价值,由此,文学史研究必然是诠释性的。在他看来:“只有在诠释中、也只有通过诠释,事物才拥有价值。”[1]为此,他在文学史研究中突出个人体验的重要性,突出现代人的情感与古典诗歌的沟通。这种方法使得古典诗歌成为完全现代意义上的作品,他看重的是古典作品的文学意义。他将古典的东西当作一种活生生的审美对象予以感受。
在《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一文中,宇文所安说:“‘中国文化’一词的创造,使得曾经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国有的财产”,而“在19世纪的动荡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而不是视为国家性的”。[2](P.345)晚清以前的中国文人对自身的文化具有高度自信,他们在“天下”的观念中理解中国文化,以此认为文明的边界不在地理,而在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共同对话。在宇文所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们可以提出问题,并呈现不再可能存在的表现与描述。它们提醒我们现代的局限,它们离我们很近,但是却又不可企及。它们是一种遗产,但它们是人类的遗产,人性的遗产,而不是民族国家的”。[2](P.350)
宇文所安清醒地认识到,人文学术在现代性的语境里面临的是如何反省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以中西对立的思维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处理的学术研究方式,从根本上错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只有真正走出中西对立的二元化思维,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自由的比较,在中西文学之间尽情地享受他们的艺术美感。“来自不同传统的诗歌可以彼此交谈”[3](P.4),这是在打破这种二元化理论思维之后的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宇文所安致力于这样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有没有什么途径,使我们可以把中国诗和其他国家的诗歌放在一起阅读,对它们一视同仁地欣赏,同时也从新的角度看待每一首个别的诗?”[3](P.3)上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来自宇文所安对全球化背景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与可能性的思考。
我们今天读文学作品,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尤其是普通人)仍然热爱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哪些东西仍然吸引我们,仍然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对宇文所安而言,这是在进行古典文学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民族文化遗产,还在于它蕴含的审美感受具有永恒的价值,能够慰藉现代人日益干枯的心灵,其中的美感意识较之现代艺术更能感发人的心灵。田晓菲这样理解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虽然文学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写散文和学术论文的风格、路数都不一样,“但是,就古典诗歌而言,我常常觉得研究也是很有诗意的一种创造,因为诗本身就是一种美”。相对于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宇文所安更喜欢在考证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古典诗歌、文字的美。“如做不到这样,古典诗歌研究对我而言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每当我具体分析一首诗歌时,我总希望能把它的美传达出来。我觉得这种研究和我写诗、喜欢诗是结合在一起的。”
宇文所安自己投身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并乐而忘返,就是源于其中的美感。因此,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全人类;如果以民族主义的心态对待中国传统,使其“遗产”化,就忽视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人类的命运都面临现代性的困境。他对“五四”的批判,其意就在于反对用文献的方法将传统博物馆化,使其成为历史的木乃伊。宇文所安试图打破传统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古典研究中的实证考据风格,以西方散文具有的议论性抛开习见的论述话语,以浮现古典文学应有的美感。在这样的还原文学的审美动力之下,他的写作也强调一种散文的风格,这里的散文其实就是指论文写作的文学性,强调将“思想与文学的融合”。《追忆》是他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性进行混合而成的创作:“唯一的希望是,当我们回味某些值得回忆的古诗文时,就像我们自己在同旧事重逢一样,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得到快感,无论是经由什么样的道路,要领悟这些诗文,要靠一条路是走不通的。”[4](P.2)《追忆》《迷楼》的写作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文学创作;他试图以这种方式让古典诗文复活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宇文所安认为,文学研究如果没有丰富的审美感受作为基本的支撑,就会在架空其理论之后,只剩下没有意义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从而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文学不能强行纳入理论的结构,按照一种预先设定的脉络,寻找其中的内在必然规律;否则,文学史将风干成一系列历史的线条,最终丧失其应有的鲜活品格。
对宇文所安而言,“我们的任务是创造那样的一个全球性文化,它将怀有对真正全球性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这应该通过翻译来实现,但也必须通过一种人文的话语来实现,这种人文话语应该可以阅读所有的传统,并看到其中宝贵的东西”。[2](P.351)跨文化研究将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就在于能够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提供一种人文思想,从而以传统的美感来激活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凸显审美感受作为传统内化与转变的可能性与意义所在。“每个时代都向过去探求,在其中寻觅发现它自己。”[4](P.24)以杜甫为例,宇文所安满怀诗意地说:“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那时,每个学生都会在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不得不阅读他的诗篇而叫苦连天,但是到他们四十五岁的时候,却会充满温情与爱好地,回忆起这些同样的诗篇。”[2](P.351)论及这种研究方法,宇文所安特别突出个人体验的重要性,突出现代人的情感与古典诗歌的沟通。田晓菲的这一观点可以视为对宇文所安的补充:“我们急需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语言对之进行思考、讨论和研究。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次杀死我们的传统,使它成为博物馆里暗淡光线下的蝴蝶标本、恐龙化石:或与现实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罩,或是一个庞大、珍贵的负担。”[5]宇文所安强调中国古典的文学作为活生生的力量,从比较诗学的角度阐释其中具有人类共同性的情感。以审美的方式进入传统诗歌,其意义就在于以审美来抵抗知识;传统不能固化为知识标本,否则与心灵无关。这就是田晓菲所批评的现象,现今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有时候太理性”了。“很少见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很激动地讲述一首诗为什么美,我觉得大家应当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所在。”①文学不是知识,文学应该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感在其中,文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美。文学研究者应该带着个体的审美感受进入古典文学的作品之中,领悟其中的美感。这样的文学研究是充满了激情的,是那种将文学处理为资料性的文字的考证性研究所缺乏的。惟其如此,文学史研究才能使古典文学克服仅仅属于几个学者的讨论的局限,成为对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生活具有活生生影响力的东西。这正是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这种研究必然“希望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古典文学研究”。
“五四”一代的中国学者深受现代性意识之影响,其古典文学研究是在“整理国故”心态下展开的,其方法是效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其内容是以文献学为中心,其目的是视传统为“遗产”,有古董的价值而无当下之意义。宇文所安对此的批评是:“……过去(被)涂抹上防腐的油膏,做成一具木乃伊。这个涂抹了油膏的过去,乃是‘五四’一代的学者一手造成的。”[2](P.350)宇文所安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颇有微词。他认为文学史是一个建构过程,在此建构中,文学史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做了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建构。因此,他强调文学史是流动的,古典文学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文学史的意义——对传统的现代理解,使得传统鲜活起来;不应把文学史作为僵死的历史真实,而应力图将其带入当代人的生活情境,使其转化为现代生活的精神需求。
由于身处汉语之外的语言体系,汉学家可能对中国思想的知识了解和材料的占有上不如中国的学者,但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国内学者对文献材料的考证辨伪兴趣过多,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常常停留在文献材料的实证面上,而忽视了对中国思想的阐发,忽视了思想的价值对现代的意义。而从一种非汉语思想的角度思考,汉学家往往能够发现中国思想与他们自身传统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对汉语思想的阐发,并不一定要发现更多的地下材料。因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已经体现在基本的经典文献中。从宇文所安等人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发现,他们虽没有占有更多的材料,但是他们对中国思想的理解有独到之处。可以说,他们对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差异有着更深层的理解。说句实话,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对基本的经典没有理解透彻,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他的话语意思、基本的内涵,但是我们没有理解其中包含的意味;思想经典中超出文本的东西,我们没有把握到,而汉学家们反而触摸到了。对思想经典的深层意味,要的是体验工夫,进入古典思想的能力,这是超越考据和训诂的东西。因此,宇文所安虽然将中国文学定位为一种具有非虚构特征的诗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研究方法是考证与索隐,而应仅仅将人的真实情感与欲望作为文学阅读的目的;人性才是文学研究应关注的主题。
宇文所安坚信,作品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人们内心真正的欲望。通过写作,人首先确立的是与他人的关系:“有了身份,有了在我们世界中的‘位置’,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4](P.47)在中国的山水诗里“大自然变成了百衲衣,联缀在一起的每一块碎片,都是古人为了让后人回忆自己而划去的地盘”。[4](P.32)而在回忆中,“作家们复现他们自己……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看一个作家是否伟大,在某种程度上要以这样的对抗力来衡量,这种对抗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想要逃脱以得到某种新东西的抗争,同那种死死缠住作家不放、想要复现的冲动之间的对抗”。[4](P.114)对作者的动机的怀疑,认识到在任何崇高的理由背后都怀有个人的欲望,这是推动作者写作的动机,这种解构的阅读策略,目的虽然在于揭示人对自身欲望的习焉不察,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对真正超越功利主义的审美期待。艺术家通过不断的创造,与自然与人发生关系,将自身与广大的世界建立了联系。对艺术家而言,回忆是自身存在的证明,用诗、词、文将自己的回忆定格,通过文字创造不朽,使自身在其所创造之物中被铭记。正如宇文所安所说“诗歌企图引导你迷途而不知返,它的意图是以言辞怂恿你,是让你为自己沉闷呆滞的生活感到羞愧,是引诱你变成另一个人,是让你反抗对社会的每一次屈从,是让你做非分之想,并因为得不到满足而饱受痛苦”。[3](P.6)诗歌总是使人在矛盾中挣扎,诗歌不断地引诱人们进入一个虚幻的空间,一个由自己创造和享受的空间。从根本上说,艺术往往是欲望遭受挫折、终止的产物,而欲望之不得实现乃是人生的真相。宇文所安在《迷楼》中这样论述:“在日常情况下,外在于诗歌的那个现实世界将羞耻感和屈从心之类的清规戒律强加在人心中的野兽身上,诗歌顶着这些清规戒律逆流而上,并从中汲取力量。社会用言词束缚我们,而诗歌也用言词迎头反击:用无懈可击的言词,模棱两可的言词,轻重权衡的言词,与通常被社会驱使得单调乏味的言词相对抗的言词。诗歌用这些言词对我们诉说,并且不动声色地试图侵蚀所有不小心听它诉说的人。”[3](P.5)诗歌唤起了人类爱自由以及反诸内心世界的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代表了人类自身的根本力量。
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个体,没有欲望的生命是一具木乃伊。因此,我们不能否定欲望,也不能放弃艺术。而艺术能够唤醒生命,欲望通过艺术而呈现,生命本身孕育艺术,但真正的艺术却警醒地避开欲望的终点。因此,我们并不否认文学创作来自欲望,欲望是推动文学不断生产的强大动力。我们承认,对诗歌的迷恋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文字美丽和优雅,可能更因为自我内心的骚动不安。艺术并不是一味地表现感官、欲望之美;相反,感官与欲望只有在艺术中得到升华,才具有审美价值。“我们在诗歌所经历的精神实验,对社会并不造成立竿见影的或实实在在的危害,但是,它们可以使人类心灵潜移默化;它们以饲料喂养那只野兽,使之不致死于社会习俗之手。我们生活在清规戒律当中,无情的自然与人类社会将这些限制强加于我们,而这个人类社会总是千方百计地渴望与自然的必然性分庭抗礼。”[3](P.5)但是,诗歌呼唤内心沉睡的野兽,从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欲望的各种方式,窥视各种隐喻和象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只野兽,它不喜欢身上的镣铐。诗歌用言词饲养这只野兽,唆使它恢复反抗和欲望的本性。”[3](P.5)艺术并不是让人沉迷于感官欲望的东西,艺术是对感官欲望的净化;越深入越是无法自拔的是感官,不是艺术。在宇文所安看来,艺术不能没有欲望;既然欲望作为我们完整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将其排斥在外显然有违人性。
宇文所安并不否认,艺术在改变人心,鼓动人性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但他并不因此认同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将艺术视为理性的对立,以致需要将其放逐于理想国之外的观点。在宇文所安看来,艺术对政治的妥协总是在表面顺从的背后,又压抑不住地显示自身,“艺术依然是对上述那种劝说的一种威胁;它表面上很安全,因为,正如尼采所说的,它只是提供了某些可选择的权力的影子,但它依然令人不安地体现了那些被镇压下去的反抗和那些非法的欲望,这些反抗和欲望拒绝被阐释结构所包容吸收。艺术能够将我们纳入像所有历史性的现在的现存关系一样活跃的那些关系之中,这些关系不仅活跃,而且更有诱惑力,因为艺术致力于诱惑我们,而不是征服我们”。[3](P.291)最终,在诗歌中人获得了自由:“社会用言词束缚我们,而诗歌也用言辞迎头反击:用无懈可击的言词,模棱两可的言词,轻重权衡的言词,与通常被社会驱使得单调乏味的言词相对抗的言词。诗歌用这些言词对我们诉说,并且不动声色地试图侵蚀所有不小心听它诉说的人。危险的状态会被我们看成理所当然,而不理智的激情一时间可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激动。这些言词能在某些形象周围洒下一缕欲望之光,而让其他形象去面对愤怒与厌恶。尤其重要的是,诗歌可以用反抗的自由来诱惑我们,从而使所有彼此矛盾的、未曾实现的可能性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烈的对抗运动。”[3](P.5)
一般认为,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阐释深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宇文所安相信通过对文本的探析,能够揭示文本背后作者的真正意图,了解作者真正的心理与欲望。这种观念其实来自中国诗学,是建立在中国文学之非虚构特质上的。按照西方诗学的模仿论,文学是对理念的模仿或表现,文学作品是作者虚构与想象的结果,与作者本人的内在心理与个人的真正人格无关。宇文所安对诗歌背后人性与欲望的关注意识,在中国古代思想里就有体现:在中国传统里,从孔子开始文学被理解为知人的一种方式,他建构了一种非虚构的解释学诗学;其后,中国传统的诗学其根本也在延续此种非虚构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孔子关于观察人的行为、动机和基本性情的原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运用到孟子关于‘知言’的主张之中。语言是外在显示的最终形式,它最完美地(尽管也存在问题)体现了内与外之间的相应关系。”[6](P.21)
宇文所安认为,“孟子的‘知言’不仅指理解语词的意义,当然也不仅指理解那只是反映了或再现了说者所认为的语词的意义。孟子所说的知言是指值得语词隐藏了说者的审美、暴露了说者的什么。‘佊辞知其所蔽’:没有任何字典、语法或对概念的哲学反思向我们讲授这样的‘知言’。语词仅仅成了一种外表,其外形揭示了隐藏在内的东西”。[6](P.21)因此,要理解人的言行,其前提是必须重视具体的情景。这种情景不是我们社会历史分析中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或宏大叙事结构中的大的背景,而是一种生活的细节构成的能够给人活生生的体验的情景;对人的言的理解就要落实于此种复杂的情景网络之中。故而,“孟子所开列的各种语言表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听者能明察秋毫。最为重要的是,说者在话语里流露出来的东西是非自觉的,也许它根本不是他希望流露的东西。在这里,错误和欺骗不是独立范畴。它们从属于知人:它们不过是无知或是一种想欺骗的欲望的体现,因此对我们来说,它们成了我们听他人说话时的某些重要证据”。[6](P.21)因此,在中国文学里,其解释学诗学对读者存在着深刻的期待。因为,对于作品而言,“识别真相还是认可错误,被欺骗还是不被欺骗,取决于听者的能力”。[6](P.21)
进而,宇文所安指出,与中国不同,西方的柏拉图/苏格拉底注意到,一个演说家以及一个在大庭广众面前背诵荷马史诗的人具有强大的力量,能把观众卷入迷狂状态以致“丧失理智”。“西方的‘audience’(听众/观众/读者大众)概念使读者/听者作为集体的一个匿名成员而存在;即使在单独出场的时候,也享有某种使自己迷失在民众的那种热情之中的自由。人们一直希望能从文学之中找到这样的自由,渴望被卷走(ekstasis)。”[6](P.22)与柏拉图来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及演说辩论的听众(观众/读者)经验不同,孔孟来自《诗经》的阅读经验里,“孟子的‘知言’描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寻求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相反,他试图去理解另一个人”。[6](P.14)从宇文所安的文本解读实践来看,他表现了强烈的进入文本之中,了解作者作为人的欲望。就此而言,宇文所安本身乃是中国式的读者,而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被狂热所席卷的“audience”。
中国的非虚构解释学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模仿”与“再现”二元模式,由于它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表达,它期望的是:“一切内在的东西都要走向外在显现,内与外是完全相符的。”[6](P.217)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如其人”就是这种文学观念的发挥,在《体性》篇中他所提出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观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定势》则说“绘事图色,文辞尽情”。宇文所安由此发现,在中国文学里,“‘情’而非‘言’是文学作品的媒介”,“情”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终极价值。这就完全不同于构建在模仿论与理念论基础上的西方诗学,它们将言作为文学价值的指归。情是“把‘所以’、‘所由’和‘所安’统一起来的方式”。[6](P.314)“文辞尽情”:当我们在读一个文本的时候,读到的不是“言”,而是“情”。[6](P.241)在宇文所安看来,“这是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信条,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就是在这个基础原则上发展起来的”。[6](P.217)宇文所安之所以对中国诗学传统备加推崇,就因为其中有着对人性的强烈关注,对人世间情感的珍惜,而西方文学传统恰恰非常缺乏这种关注。
在宇文所安看来,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悟性的高低,就在于其对历史情景细微之处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能够通过历史的想象力把握历史的层次从而还原历史的细节。在这种历史的细节中领悟文学生长的意义,把握文学在各个时期独有的魅力。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写作,依照尽可能的证据,重构唐诗写作生成的历史情境,使读者仿佛身处其中,能够切身感受到作者的情感酝酿和作品的诞生。由于读者似乎与唐诗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对于读者来说,他对唐诗的那种情感体验会显得更加深刻,而不会显得陌生。当然,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唐诗之生活世界的重构并不因此而变得无关紧要。虽然由于时代和资料的限制,我们仅能了解他们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是这个片段仍然是比纯粹的理论构想更为鲜活生动,更能贴近读者的生活世界。
如何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文学,将文学的意义从层层叠叠的注释里打捞出来,避免将中国古典文学博物馆化,是中国当代古典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训诂考据和以西方理论为依托的文学阐释,让人们感到越来越疏远于使文学最具魅力的审美感受;当研究者无法从审美的感性层面进入历史场景的时候,他只能在现代理论话语建构的概念丛林中寻找自己的出口,从而使文学研究陷入话语的圈套。
纵观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大多学者认为宇文所安受到西方后现代的解构理论的影响。虽然他的看家本领是美国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但正如其所言,对文本的细读应该视为文学研究的基础,即便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本的细读也是必要的方法。因此文本细读并非宇文所安的独门武器。对宇文所安,研究者都很明了他对中国文学研究带着深刻的西方理论的视野。对此他并不避讳:“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工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比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7](P.2)众所周知,我们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古典文学的学术传统,其根底就是文献考证乃至索隐;除此之外,我们观察文学的角度其实也是来自西方,运用西方文论解析中国文本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固然宇文最重要的手段在于通过细读解析文本,但他的分析意在文本背后的人。对作者行文背后意图的揣摩是其文本分析的落脚之处。也就是说,宇文所安关注的不仅仅是写什么,更专注于探析如何写:他致力于凸显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之间的错位,文本间的缝隙是人性意味深长的流露。在某种程度上,《迷楼》里对诗歌和人性欲望的关注与之前的《追忆》一脉相承,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激情和不懈的阐释之所以有别于中国学者,其实就在于他观察中国诗歌的位置始终立足于人,对人性的见微知著。宇文所安将古典文学中的作家还原成了活生生的普通人,他对古典文学的阐释之所以生动,就在于他复活了其中充满的欲望。人在文学中意味着,“在写作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落入关系、区别和欲求之中”。[4](P.163)也就是说,在宇文所安那里,人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人性与欲望之间充满张力存在,这个观点贯穿于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之作者的理解过程中。
在宇文所安看来,“诗歌,散落在博物馆地板上的碎片,是在某种人类交流中使用的古老的符号。拾起这些碎片,我们就陷入了这种交流。这些交流,像人类的所有交流一样,是两面性的:它们是揭露,是赤裸裸的真实,是丢失盾牌而迫使诗人剖白自己;与此同时,它们又以言词填补了空白,取代那些已经失去并正在渴求的东西——失去的荣誉,在丢失盾牌的过程中失去的社会地位。抒情诗,因其承受暴露和隐瞒的压力与焦虑,比史诗或戏剧诗与我们的生活情境更直接相关。当诗人向社会剖白自我的时候,这一行为已经不自觉地掺入了所有这些压力和焦虑。在我们心中有某个东西在微笑,它已被这些言词所吸引,并作出了回应”。[3](PP.12-14)
在一切皆为商品的现代社会,诗歌已经失去了其曾有的光彩;诗歌在当今时代的尴尬处境,正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萎缩的标志。在宇文所安这里,没有诗歌的生活难以称为美好的生活。“置身于艺术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不知为什么我们就不再是从前的我们。诗歌可以唤起我们心中渴望迷失的那一部分。作为一次真正的迷失,当它不仅仅是某些可以预见的对日常规范的超越,或者仅仅使某些已经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阴暗面变本加厉时,它是最强有力的。当我们屈服于这种迷失,就会遭遇到一个不期而至的他者;而它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3](P.7)诗歌的意义在于能够唤醒人在世俗生活中的迷失的心灵,恢复人性的本真,揭穿世俗生活中的种种伪装,“那些诗句不停地向我们反逼过来,默默地嘲笑那种兢兢业业地履行社会职责的平庸乏味的生活,抑或在平凡的邂逅中激发欲望,这欲望是如此触手可触,让人如饥似渴。当我们站在盾牌阵中,这些言词在我们耳边喃喃低语,怂恿我们大胆地向前猛冲,或者扔掉盾牌,逃之夭夭”。[3](P.7)
对现代人而言,我们的困境在于真正的人性之美被遗忘,欲望的长驱直入使得人们在充满欲望的同时麻木不仁。诗歌唤醒了内在的人性,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欲望,“诗歌可以唤起我们心中渴望迷失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循规蹈矩,社会用代表集体意志的强硬言词束缚我们,而诗歌也用言词迎头反击:用无懈可击、模棱两可的言词,与通常被社会驱使得单调乏味的言词相对抗的言词。诗歌用这些言词对我们诉说,并且不动声色地试图侵蚀所有不小心听它诉说的人。危险的状态会被我们看成理所当然,而不理智的激情一时间可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激动。这些言词能在某些形象周围洒下一缕欲望之光,而让其他形象去面对愤怒与厌恶。尤其重要的是,诗歌可以用反抗的自由来诱惑我们,从而使所有彼此矛盾的、未曾实现的可能性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烈的对抗运动”。[3](P.5)
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人的欲望毫无节制地以自由的方式释放出来,而缺少对自身欲望的节制,从而使人沦为欲望的奴隶。真正的自由却是来自人对自身欲望的节制。欲望对人而言不可或缺,但如何能够将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领域,对现代人而言是一个问题。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诗学基于一种诗教诗学,历来将诗歌的品格定位为温柔敦厚,从而使诗歌具有驯服欲望的功能。对诗歌而言,其本身就是通过表现欲望来驯服欲望。但在现代艺术中,欲望却引导着人本身,以对自身欲望的刺激来寻求创造,欲望因创造被挑逗起来,因其泛滥而伤害自身。在欲望无限膨胀的今天,身体成为肉欲的对象,惟其如此强调身体的灵性显得尤其重要。创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物质上的肉体——肉体经过了艺术转换,具有伦理性。这才是欲望对于身体而言的意义。
宇文所安曾说:“对我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并不完全是一种纯客观的研究对象。而同时是一种我希望从中发现某种理想的感情形态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学最吸引我的,是其中充满着那种可以被整个人类接受的对人的关注和尊重。我所喜欢的诗人,不是那种带有神性的高高在上者,而是一个能和其他人进行平等对话的人的形象,我认为,在中国文学中,深刻地体现生活与写作的完美结合。”[8]顾彬在谈及自己从神学转向中国文学研究时也说,因为他觉得在中国的孔孟思想与文学中可以找到人:“孔子、孟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到现在还是”,“这就是为什么汉学的吸引力这么大”。[9](P.206)这或许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当代的意义。它让我们重新发现人,尊重人,因为真正的爱的温暖只能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给予,而不是上帝。
注释:
①《宇文所安与田晓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http://blog.sina.com.cn/u/56d8c740010007ah。
标签:文学论文; 宇文所安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化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古典文学论文; 人性论文; 迷楼论文; 知言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