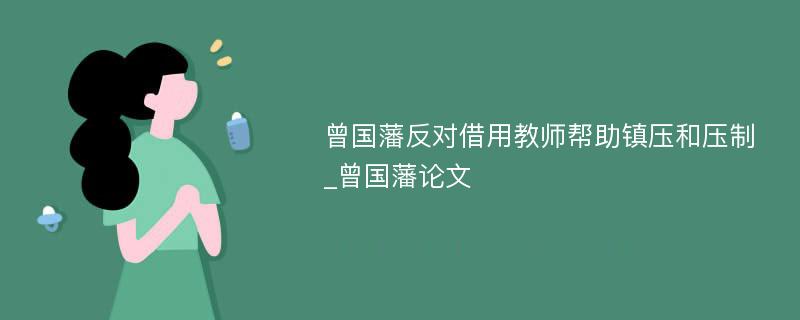
曾国藩反对借师助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借师助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史学界几乎一致公认曾国藩是借师助剿的积极鼓吹者。笔者对此定论,不敢苟同。本文试图就此问题略谈浅见。
一
西方列强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掀起的革命运动,始终视为洪水猛兽。1853年太平军刚刚定都南京,就有美国人对向荣提出:“愿派兵前来助剿”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为了自身利益更迫切要求尽快消灭太平军。1860年11月,俄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提出俄国愿派三四百官兵和船炮来华助剿;法国驻华公使也表达了此意。清廷对此征求意见时,曾国藩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并说:“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时此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②”他对俄法派兵来华助剿持否定态度。
1861年冬,太平军攻占苏、浙大片土地,中外商贾云集的上海亦成孤城,危在旦夕。聚集到上海的苏浙大地主们迫不及待地要借助在沪洋人力量,进行疯狂反扑。1861年11月18日,户部主事钱鼎铭带着署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及苏浙地主殷兆镛、潘曾玮、顾文彬、杨庆麟等人给曾国藩的呈请借师助剿的信件到安庆。曾国藩这时仍不以借师助剿为上策。1862年1月7日他给潘曾玮的信中说:“借助外国,自古为患。”“上海、宁波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只宜借守沪城,……至于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③。潘曾玮听不进曾国藩的衷言相劝,是年仲春伙同大地主龚橙(孝拱)搭船北上,直接去找清廷哀求借师助剿了。曾国藩对潘的执意北上,“亦未便强行劝阻”,他“想总理衙门自能折衷群议”④。曾国藩给潘曾玮写信的同时,又给庞钟璐、江苏布政使吴煦及江苏巡抚薛焕等人写信,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然而,薛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意见,直接向朝廷奏请“借师助剿”,且在上海设立了会防局。曾国藩对于薛焕的所为,一方面向朝廷上奏表明:“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⑤;另一方面则对其部下薛焕予以严厉批评:“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还说,如果“必欲攻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⑥。
清廷根据潘曾玮、龚橙的请求和薛焕借师助剿的奏疏,于1862年4月12日谕令曾国藩“允洋人助剿苏常”,并要曾“与洋人联络声势,冀收速效”⑦。然而,1862年4月22日,曾国藩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的一贯态度。并以历史上的教训来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总得靠自己的力量,认为借师助剿等于借西人参加科举考试,要朝廷拒绝他们的会剿要求。他给奕、桂良、左宗棠、李鸿章、周腾虎、吴煦等人的信中,都表明了同样的观点:“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轻;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⑧其态度可谓坚决之至。
二
曾国藩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谕旨,借洋人势力尽快镇压太平军。然而他却始终坚持只可助守上海,不可助剿内地的一贯主张。
曾国藩之所以只认可借兵助守上海,首先是因上海自开埠以来,“人民千万,财富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保其富庶。⑨”“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守之。”其次是因上海每年为湘军提供了100多万两白银的军饷,是湘军主要财源之地。所以他“必设法保全上海”⑩。再次是因他考虑“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上腴,于用兵则为绝境”(11),只宜防守,不宜出击。如光靠清军防守,又“非二万劲旅不可”(12)。当时,他无法抽调这么多兵力,虽已决定派李鸿章率兵前往,但“非二月不能成行”,他“恐缓不及事,不得不借西洋兵力”了(13)。这是他在“别无良策”情况下的最后选择。
曾国藩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中,始终坚持不与洋人勾结去镇压内地的太平军。
1862年1月7日,他写信给潘曾玮:“今日泰西各国,久已遍行内地,又非初入中原者可比”,若借师助剿内地,“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14)。2月24日,他又致函给潘:“除上海外,无论所向利钝,概不与闻。(15)”他认为借师助剿,只能是“借鬼打鬼,或恐引鬼入室;用毒攻毒,或恐引毒攻心,不可不慎也。(16)”所以尽管他对清朝廷执意“借师助剿”勉为应允,可仍坚持“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17)。
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刚到上海,在沪的“洋人常至李鸿章处催促进兵,约期会战,聒聒不休”。曾国藩对洋人的这种纠缠无已的情况,极为反感,他要李鸿章“以婉言谢之”(18)。他对左宗棠在浙江起用法人日意格组织洋枪队会剿太平军,认为“系左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19)”5月至6月,洋枪队在嘉定、青浦惨败后,“不肯罢休”,决定从印度调兵来华。曾国藩得此情报后,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闻英吉利、法兰西二国将调印度兵大举会剿,江浙人民从此殆蹂躏无噍类耳,为之喟叹!(20)”7月18日,他复奏朝廷,指出洋人只不过是“借助剿为图利之计,借起兵为解嘲之词耳。”并断然指出:“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不允许洋人来“蹂躏中国之土地”,并申明他“始终不愿与之会剿”(21)。态度十分坚决。
1862年,曾国荃率湘军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可又遇到李秀成20万太平军的猛烈攻击。湘军危急万分。正当此时,曾国藩接到廷旨:“俄国兵船愿来助剿。”他不好明白拒绝,只好同意,“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仅作“遥壮声威”(22)之用,不直接参与攻剿南京。11月8日,他又接到李鸿章决定派常胜军前来救援之信。他对李的好意没有表示什么感谢,反而说这“非余本意”。后来这支队伍因其统领白齐文为闹饷问题没有去成,曾国藩说“不来金陵,亦自无害,来亦未必果有裨益”(23)。
1863年3月,英国侵华军头目士迪佛即将离任回国,他妄图在回国前说服曾国藩,由英国另组一支洋枪队帮助攻剿南京。士迪佛经过多方设法,于3月19日终于在裕溪口见到了曾国藩。士迪佛大谈其建军计划,说愿以英国之将领统带中国之兵勇,每月支付英军头目军俸58180两。又要曾国藩拿出地图,指点太平军的活动区域,然后恬不知耻地说,只要曾国藩同意这个计划,“他们一定包管克服金陵、苏浙”。曾国藩听后,只是说“须函商总理衙门夺定”(24)。4月18日、26日他分别致函李鸿章与官文说:“同募中国之勇丁,同隶鄙人之部曲,又岂可多寡悬殊、苦乐不均?虽面订作书面请求总理衙门,而鄙人固已期期知其不可矣。(25)”可见他“须函商总理衙门夺定”。只是搪塞之词罢了。
1862年3月,清政府在英人赫德的怂恿下,决定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用以进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并委托正在英国养伤的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在英国购得军舰七艘和趸船一只。1863年1月李泰国又背着清政府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为期四年的合同,规定阿思本拥有对舰队的指挥权及用人权,他人不得干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合同。1863年5月7日,他针对李泰国与阿思本的合同,致函恭亲王奕和桂良说:“其意欲全用外国之人,不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至于攻剿太平军,则“发匪之猖獗在陆而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否定“购船剿贼”之必要(26)。次年1月21日他在给奕信中,结合金陵地理形势,说:“今以新购轮船进剿九洑洲,实未敢信其确有把握。(27)”再一次否定了买船助剿一事。曾国藩始终坚持:若买船,就要由中国官员指挥,要么就不买。但后来清政府答应让阿思本独领舰队,中国营官仍带自己的舢板炮船,同其一起停泊。清政府这种出卖主权的投降妥协行径,又遭到曾国藩的反对。他在给奕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指责总理衙门这种出尔反尔,屡次变更主张的作法,并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与其如此,宁愿白白扔掉二百余万两白银的代价,也不要这样的舰队(28)。
至于李泰国提出的瓜分天京财富的条件,更为曾国藩所反对。李泰国与清政府议定:若阿思本舰队独破天京,所得财富30%归清政府,70%归舰队;若与湘军合伙攻破天京,清政府抽成不变,湘军与舰队各得35%,奕对此方案甚为满意,可曾国藩却绝不允许阿思本插足攻破天京分享天京财富之事。1863年10月9日给曾国荃的信中鼓励其弟“以实情剀切入告”,说湘军与太平军“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皆可切奏。(29)”
由于曾国藩的坚决反对,清政府只得于1863年12月10日下谕:宣布退回所购轮船,并撤掉李泰国总税务司的职务。闹了近两年的阿思本舰队事件,终以曾国藩满意的结果告终。
三
曾国藩敢于在借师助剿问题上与朝廷大相径庭,这中间包含着诸多思想因素。
“助守”与“助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助守”总是被动的防守,其范围又只限于上海一城之地。而“助剿”则是主动的,即不管太平军在什么地方,洋人都可以主动出击。曾国藩对借师“代复中国之疆土”是持反对态度的,在他看来,大清的天下,理应由大清臣子去保卫,怎能去借助于洋人势力呢?因而他反对外国人干预中华内政。曾国藩虽然坚持地主阶级立场,血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但他这种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内政、维护民族主权的思想仍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可贵的。
曾国藩的仇夷、鄙夷思想,是他拒绝助剿的原因之一。他满腹儒家思想,忠君至上,凡有损于君主的外扰内患,他都会挺身而出履行他身为封疆大臣的职责。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虽身在北京,可他十分关注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天津,他说“洋鬼猖獗,……实为可虑。(30)”侵略军攻打北京,他自愿要求带兵北上勤王。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可以将全部精力对付太平军了,可被他视为“洋鬼子”的洋人却又偏偏要参加太平军助战,并不断接济围困在安庆和南京的太平军,这使他十分恼怒。他对洋人护照上写着“有叛逆地方不准前往”的字样,却又偏偏要去的作法,十分愤慨。
曾国藩对洋人盛气凌人的恶劣态度极其反感。1862年7月,他曾租得英国轮船威林密号,准备从汉口装火药2万斤去上海,但英国船主嫌其太多,只允许“装火药五千斤赴沪”,并将派去装火药的中方人员“逐出,不准在船”。他对洋人“凶猛如此”的态度,“殊为可虑”(31)。1863年4月16日,法国传教士罗安当为了南昌教案问题,带着总理衙门和奕给曾国藩的信件去安庆。罗安当在曾面前盛气凌人,耍尽无赖之能事,给他以极坏的印象。次日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罗教士之气象,不过如中国之无赖痞棍”(32)。他在日记中对洋人在华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枪杀中国无辜,多有记载。这些无不说明曾国藩的内心深处对洋人的仇恨,对洋人“凶猛如此”的忧虑。他对“一心崇奉”洋人的苏浙人士的态度,颇为担心,他“恐一二不靖之徒自神其媚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33)。他对那些“奉洋如神明”的买办极为反感,看不起“名为洋人,实皆广东、宁波之人”的冒牌洋枪队常胜军。当白齐文为军饷问题痛打杨坊,抢去400万两白银的事件发生后,他认为这“足使挟洋人以自重者爽然自失”,而白齐文实为“可恶”,应“奏请军法予以处置”(34)。
曾国藩不是唯武器论者,在人和武器的两个因素中,他认为人是主要的,“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35)。他为只要士兵素质好,既使武器差一点也无妨。同时,他认为外国“轮船之速,洋炮之利”,被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国则震于所罕见”,但中国“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36),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只要中国“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中国人就会“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洋人“夸其所独有”的东西,中国人亦能为之,那时“谁敢侮之”!他那种既不迷信西方武器,又不排除学习并进而掌握制造这种武器的先进技术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
既然人的因素重于器的因素,因此曾国藩认为“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自立为体。(37)”因此当曾国荃在南京吃败受伤,李鸿章决定派白齐文率常胜军去救援时,他叮嘱曾国荃:“危急之时,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38)”“求人不如求己”(39),强调立足于己。他也嘱咐李鸿章:“派人交洋人训练,断不可多,愈少愈好。(40)”这些都反映了他的“自立”精神。
注释:
①②⑤⑦(21)《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271、1270、2060、2143、2390-2391页。
③④⑥⑧(11)(12)(13)(14)(15)(18)(22)(23)(25)(26)(27)(32)(33)(34)(36)(37)(39)(40)《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359、2570、2554、2683、2363、2554、2387、2359、2523、3175、3395、3577、3598、2683、3402、2666、2879、2999、3642、2999、2077、2918页。
⑨⑩(16)(19)(29)(30)(35)(38)《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03、794、618、1801、1031、572、869、880页。
(17)《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201页。
(20)(24)(31)《曾国藩全集·日记》第755、888、759页。
(28)《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7页。
标签:曾国藩论文; 太平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李鸿章论文; 李泰国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史记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