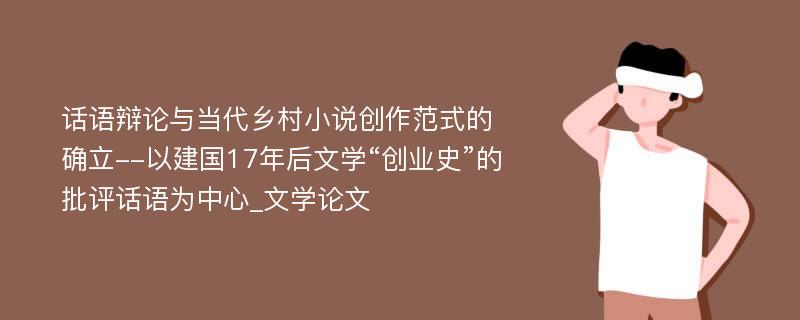
话语论争与当代农村小说写作范式的确立——以建国后17年文学中对《创业史》的批评话语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创业史论文,范式论文,中对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文艺批评,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文学创作而言,建国后17年的文艺批评起到了对文艺创作进行训诫与规范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文艺批评的训诫和规范,使得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几乎都经历了修改再版的过程,而这些修改主要是根据文艺批评提出的意见来进行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这种奇特的性质,洪子诚先生论述道:“它(批评)并不是一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一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在许多时候确实演化为一种‘斗争’手段。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毛泽东将文艺批评的这两项功能,形象化地概括为‘浇花’和‘锄草’。”[1] 对于建国后17年文学中的经典文本——《创业史》,“浇花”的声音成为主调,而批评家严家炎的质疑则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和塑造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文艺论争。可以说,《创业史》这一文本正是与其批评话语一起,共同建构了当代农村小说写作的典型范式。
一、赞扬:新的美学标准的确立
《创业史》出版以来,得到批评界几乎一致的赞扬。除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外,《创业史》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人物形象中,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被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尺。冯牧认为,“在《创业史》众多的正面人物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2] 批评家都为梁生宝身上所具有的崭新的农民品质所激动。周扬在批评《三里湾》时指出,赵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在梁生宝的身上,这种“巨大力量”得到很好的体现。梁生宝的性格正是民间优秀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思想几乎“理想”地结合,他被看作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与赵树理笔下的“新型人物”相比,梁生宝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产生的理想的农民形象。这一形象的“成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进入“当代”以来,新兴的文化领导权为巩固其意识形态地位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文学进行“等级”划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等人的论述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生成的直接源头,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之所以是“继续”,是因为五四启蒙文学的性质。在权威分析中,五四启蒙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开始就向着社会主义文学方向发展的文学;之所以是“发展”,是由于“当代文学”解决了五四启蒙文学没有解决好的“文学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所以“假如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3] 这种判断包含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秩序形成的重要依据就是“当代文学”是和“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4] 当代文学与社会制度的紧密联系,使它获得了文学等级秩序中的最高级别。文化领导权同时对“当代文学”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当代文学应该创造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英雄人物。这样的人物应该与当代文学一样,与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具有最先进的思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批评家为梁生宝形象的出现而表现出的欣喜。因为“梁生宝是一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青年农民的高大而又真实的形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形象。他高大,他真实,他有光辉,正是因为他无产阶级化了,理想化了,正是因为他的步伐稳稳地踏在祖国农村的坚实土地上,他在现实斗争之中成长,他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也不是农民气质或农民意识的体现。”[5] 梁生宝具有以往的农民形象从不具备的社会主义品质。在《创业史》之前的农村写作中塑造的新人物形象,都可以看作是对梁生宝形象的铺垫和准备。与以往的农村“新型人物”相比,“无产阶级化了”的梁生宝自然应该处于人物典型的等级秩序中的最高级。
按照批评家的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力,给读者一种崭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干的事业是紧接着民主革命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事业,读者从梁生宝每一个胜利中都看见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阻挡的力量,当然就更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充满生命力。在这种分析推理的逻辑中,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五四启蒙文学所认定的“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与人物所代表的先进的社会思想相联系。这里已经隐隐体现出文化领导权对批评话语的渗透,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套与写作方式、文本内容的变化相适应的、评价艺术典型的新美学标准。
可见,新的美学标准使梁生宝这类艺术典型,不仅从文本中获得生命力,而且从文本的外围、从人物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中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高度认可。这样,理想人物与一个时代热切的社会理想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对这样的艺术典型的价值及其等级意义发生质疑,就等于在质疑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动摇人们真诚的社会理想。所以,在对梁生宝的一片赞扬声中,严家炎先生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典型的不同评价,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和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激烈论争。
二、论争:启蒙话语对文化领导权的“偏离”
1961年至1964年,严家炎先后发表了《〈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等文章,对大多数批评家从梁生宝形象来肯定《创业史》的成就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肯定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对梁生宝形象有所保留。这种评价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众多批评家纷纷撰文进行反驳。这场论争围绕着两个焦点问题来进行:如何理解和评价典型人物的意义和价值;在塑造典型人物时,如何体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在第一个问题上,严家炎与其他批评家有比较明显的不同。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梁生宝形象:“从作品本身说,梁生宝形象确实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农村新人的光辉品质,不仅概括了一定的时代内容,而且艺术上也站得起来,比同类题材作品中那些较为单薄而只有某些性格侧面(如急燥或爱钻研技术)的青年革命农民形象有了很大进展。”[6] 可见,严家炎对梁生宝所代表的时代意义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表示:“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高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7] 虽然梁生宝是《创业史》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人物就具有最高的艺术价值。严家炎通过对梁生宝活动的具体分析,得出这一人物在形象塑造上“三多三不足”的特点: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严家炎紧接着表明:“‘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6] 理念活动、外围烘托、抒情议论赋予梁生宝先进的思想,却使这一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农民的性格和气质。这样的写作方法,使作家不能如描写自己熟悉的老一辈农民一样,触及人物的灵魂,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而对人物进行充分的性格刻画,把人物放在冲突中去表现,对人物进行客观描绘而非主观意念的叠加,这可以说是与五四启蒙文学建立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一脉相承。严家炎“三多三不足”的评断标准,实际上是五四启蒙话语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一种体现。
与大多数批评家高度赞扬梁生宝形象不同,严家炎从艺术价值的角度高度赞扬《创业史》里中间人物的代表——梁三老汉。“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7] 作为老一辈农民的代表,梁三老汉从抵触、怀疑、动摇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思想变化过程。解放后,分得十亩水稻田的梁三老汉一心想要发家致富,但儿子梁生宝却把全部心思投入到互助组事业中,要带领大伙儿发社会主义的大“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家”思想自然引起父子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与儿子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梁三老汉特有的忠厚、天真、倔强的个性,得到了极为传神的表现。严家炎认为:“也许从作家的主观上,梁三老汉并不是他所要着力刻画的人物。但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7]
对梁三老汉形象从艺术价值的尺度(而非思想水平的角度)进行高度的肯定,更清楚地表明:在对人物形象的评价上,严家炎实际上坚持了与当时大多数批评家不同的美学标准,即五四启蒙话语建立的“艺术价值”标准。而众多批评家实际上正在文化领导权的支持下,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五四启蒙话语的另一套崭新的美学标准来评价人物形象。新的美学标准更注重从人物的思想性角度确立典型人物的等级关系。这种新的美学标准的生成与确立,表明文化领导权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与渗透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严家炎对梁三老汉形象的高度肯定,实际上形成了对这种新的美学标准的挑战。
因此,严家炎对《创业史》中人物形象的评价,引起了包括作者柳青在内的激烈反对。作为一名严肃的作家,柳青对写作和生活都有着极为真诚的态度。为了响应党的文艺政策,他扎根陕西皇甫村14年,过着与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这样一位真诚的作家,对于《创业史》其他方面的批评都保持了沉默,惟独对严家炎关于人物的评价表现出激烈的反对。他认为,严家炎的批评,“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8]
柳青针对严家炎的批评,提出了六个问题进行反驳。柳青的反批评以捍卫主人公梁生宝的价值和地位为中心。梁生宝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他实质上代表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理想的农民形象的一种期待,是作家忠心拥护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直接体现者。因此梁生宝形象的地位是决不允许降低的。降低这一人物的地位,就是对人物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怀疑。也正因为如此,梁三老汉的形象即使塑造得再成功,也不能成为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人物——他最多只是以往作品里中间人物的一个综合与总结,他无法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的崭新品质,因而也就无法在新的美学标准中处于最高的等级。在此,作家对梁生宝形象的捍卫,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捍卫。
严家炎从人物丰满的性格、真实的农民气质来肯定梁三老汉形象,但柳青对人物性格有自己的理解。柳青指出:“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这样,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描写时,就必须有意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的情节里头。”[8] 可见,柳青对人物有着自觉的分类意识。梁生宝形象无疑具有很强的理想性,因为他身上可能具有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已经被作者附加到别的人物身上。梁三老汉就是这种“盲目性”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应当归属到作者要描写的“次要人物”的行列。梁生宝却必须处在人物典型秩序中的最高级,按照作者的主观意图,要把他“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他的行为和思想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重要的领导作用。如果对梁生宝形象的价值发生质疑,就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质疑。所以柳青理直气壮地反诘道:“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的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她?”[8]
双方评价人物典型时,使用了不同的美学标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话语力量之间为争夺“规范”地位而进行的较量。
这场文艺论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虽然论争的双方都肯定这一创作方法是对以往各种艺术方法的一个重大的革新与进步,但是具体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如何结合,双方却有不同的看法。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提法的前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年,前苏联文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口号正式进入中国。1934年,在第一次前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其经典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9]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定义中,本身即包含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要真实地描写现实,这是以往的现实主义都具有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真实”地描写又必须承担起特殊的思想教育任务:以社会主义的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典型人物的塑造,以新英雄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浪漫主义”是完成典型人物塑造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于旧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
可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究竟应该如何结合才是“理想”的?或者说,应该如何来塑造新英雄人物?这成为建国后17年文学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1952年5月,《文艺报》开辟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专栏,掀开讨论的序幕。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得到深入。周扬在大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对能不能写新英雄人物的缺点等问题,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一文中,把这一问题提到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上加以探讨。以后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在论争过程中,政治批判的意味越来越浓,新英雄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大大突出了浪漫主义的作用和地位。严家炎与柳青及其他批评家之间关于梁生宝形象的论争,可以看作是建国以来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讨论的继续。这场论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周扬、邵荃麟等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激进的文艺路线进行调整的时期,所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可以说是第二次文代会前后那次讨论的继续和呼应。
具体到《创业史》,梁生宝形象是如何实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这种结合是不是成功,成为论争双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梁生宝的艺术原型是柳青散文特写中的先进农民梁家斌。梁家斌具有勤劳、谦逊、朴实、淳厚的优秀品德,同时对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一腔忠诚,充满热情。但是他曾经打算买地,说明他仍然有农民的私有思想;他也不能一下子理解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说明他的政治觉悟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战士”的水平。但是,柳青以这一人物为原型,运用浪漫主义方法,对这一人物加以理想化,塑造了无产阶级战士梁生宝。大多数批评家都对这一加工过程加以赞扬,认为梁家斌“这样的人物,不能说没有典型意义。但是,为了更集中、更强烈、更理想地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好,作者让小农经济的改造问题,体现在另外的人物——如梁三老汉身上了;对于梁生宝,则通过革命理想的照耀,对广阔的生活进行概括,把当代英雄的先进因素集于一身,创造出一个比原型更典型的革命的理想人物。”[9]
可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梁生宝这样的英雄人物产生的必要方法。严家炎也同意运用两结合的方法,但是他又强调“提高而不脱离基础”,也就是说,梁生宝不应该脱离农民本身的“气质”,否则就脱离了人物的“真实性”。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在当代文学“规范”的确立过程中,“写真实”往往被作为协调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个方法而提出。在现实主义的维护者那里,“真实性”是维护文学本身特质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浪漫主义的强调者那里,“真实性”却更多地与作家的世界观相联系。它关系到作家如何去发现和描写生活的“真实”,并把它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远景结合起来,这是另外一种对“真实”的理解。这样,“真实性”因为其不可确证性,成为建国后17年文学中一个争论不休的命题。
那么,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究竟哪一个人物形象代表了“真实”的农民?我们无法给予简单的回答。梁三老汉的“真实”,延续了五四启蒙文学对于“真实的农民”的想象;而梁生宝,则可以说是新兴的文化领导权对“真实的农民”的全新建构。严家炎和柳青及其他批评家关于人物典型的论争,体现了启蒙话语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化领导权一定程度上的“偏离”。
三、结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建国后17年文学研究,开始注意到建国后17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曲折而隐蔽的联系。建国后17年文学表面上呈现出与五四启蒙文学相异的面貌:无论作品的题材、风格,还是批评的性质,都出现高度统一的“规范化”、“一体化”。这是否就意味着建国后17年文学是对启蒙五四新文学的一种断裂、是完全由政治力量支配的一种文学形态呢?
洪子诚先生指出:“这30年的文学,从总体性质上,仍属‘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产物,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矛盾、焦虑和希冀的文学。”[10]
这说明,建国后17年文学与其他的文学传统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即使在《创业史》这样的经典文本中,也存在着多种异质性话语的冲突,而围绕文本展开的批评话语之间的论争更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点。
标签:文学论文; 创业史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