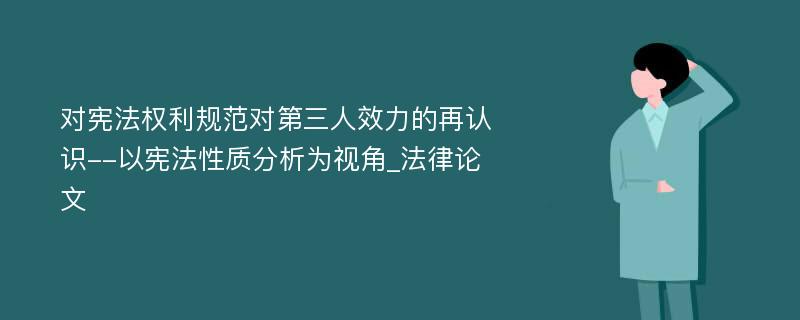
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再认论文,以对论文,视角论文,效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51(2006)02—0049—07
2001年的齐玉苓案对中国宪法学界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宪法的关注,同时也促进了宪法学理论研究,尤其是与违宪审查相关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齐玉苓案件促使宪法学者们思考宪法能否在司法中直接适用,思考我国应采用什么样的违宪审查制度,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该案涉及的是私人间争议,它已经促使学者们探讨和研究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问题。面对宪法在司法中是否能直接适用的问题,我们不再简单地回答“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的探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②,并且,难能可贵的是,大都注意到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研究[1]。笔者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这一理论?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从公、私法的划分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出发,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对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对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产生
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尽管美国的政府行为理论(state action)与间接效力理论处理的是相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行为理论实际上坚持的是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具有效力的观点[2], 因此在探讨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时笔者将集中探讨德国的情况。通过对德国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及相关规范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除第九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结社自由外,均应直接约束“国家权力”,基本法的任务专注于“对国家权力侵犯之防卫”上[3]。换言之,也就是制宪者认为宪法权利条款原则性在私人间不具有效力。如同下文中将要进一步分析的,这也正是西方宪政国家在近代宪法观下对宪法效力范围的共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路特案、联合抵制周报案、魔菲斯特案、单身条款案等案件为契机,德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是否具有效力,如果具有效力是具有直接效力还是具有间接效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以尼伯代为代表的直接效力说和以杜立希为代表的间接效力说等不同的观点。
尼伯代从人类尊严构成基本法的最高目标出发,认为基本权利是最高层的规范,因此,基本权利条款应在私人间得到直接的适用。而杜立希则从坚持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强调私法的独立性以及私法的法典独自性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与宪法基本权利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从这种“二分法”出发,杜立希完全否认了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同时,为了保证基本权利对私法的效力和一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杜立希提出以私法中的概括条款——善良风俗条款作为私法实现宪法之基本权利的理想媒介,即主张宪法规范在民事案件中只具有得到间接适用的效力[4]。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德国劳动法院基本上采取了直接效力说,但德国宪法法院却采取了间接效力说。尤其是1954年的路特案,也就是“联合抵制电影案”,由于确立了间接效力说和“客观价值秩序”概念,为德国宪法学界对待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定下了基调。为方便以下讨论的进行,笔者将对路特案相关内容作一简要介绍[5]。
在路特案中,宪法法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言论自由在遭到来自私人的侵犯时是否能够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法院做出的回答是: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可以通过民法的概括条款,以对民法发生“辐射作用”的方式产生间接效力。宪法法院首先从基本权利以拘束国家公权力为目的出发,指出劳动法院采取直接效力说的做法失之过宽。随后,宪法法院针对在基本权利在私人间效力上存在的两种极端立场,即无效力说和直接效力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建立了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这项价值体系的中心,在于社团中自由发展的人类个性之尊严,且必须被视为影响所有公法或私法领域的基本宪法决定。……因此,基本权利显然影响私法的发展。每项私法条款都必须符合这项价值体系,且都必须根据其精神而获得解释”[6]。因此,宪法权利条款在私人间应该具有间接效力。
由于宪法法院的上述判决是在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的条件下做出的,因此不但其确立的间接效力说具有重要意义,判决中所提出的“客观价值秩序”的概念由于为宪法在私人间发生效力提供了过渡桥梁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正如Qint所指出的,“客观价值秩序”在德国宪法原则中已成为了一个核心概念,当法院指出基本权利确定了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时,就等于承认这些价值由于其极端重要性使得它们必须脱离于具体的法律关系而独立存在[7]。
此后,确立于德国的间接效力理论为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所接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01年齐玉苓案的发生使得所谓“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私法化”的问题凸现在中国宪法学者的面前。相比于此前笼统地讨论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学者们对宪法的法律性基本达成共识,即普遍认同宪法具有适用于司法裁判中的效力之后,意识到了齐玉苓案(包括此前发生的多数直接适用宪法条款的案件)私人间争议的特殊性质,从而开始对宪法在私人间的效力进行认真的思考[8]。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由此进入了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视野。
二、理论基础分析——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
深入研究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产生与法学界对于宪法性质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众所周知,公、私法的划分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而对于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产生过利益说、权力说、新主体说等多种学说。其中,利益说认为法律若以追求公益为目的,则属于公法;若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则属于私法。权力说以国家高权地位及其权力作用为基础,主张凡是规范上下服从关系者,为公法;反之,受规范之当事人若立于对等关系者,即为私法。新主体说是以个别法律条文规范或指涉的“对象或主体”为关照重心,认为公法是仅以高权主体为法律所定权利、义务之归属者;反之,任何人都可适用的法律则属于私法[9]。然而,无论采取哪种学说的划分标准,宪法当归属于公法、民法当归属于私法却是没有疑义的[10]。即使是在属于普通法系的美国,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公、私法之分,但是在事实上也同样是严格坚持宪法的公法性质的[11]。据此,宪法并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它与民法各自具有不同的调整领域。另一方面,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出发,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宪政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克制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市民社会领域,则主要是由自古罗马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用以解决私人间纷争的由制定法、判例、民法解释学等组成的完整、协调的高度发达的私法体系来调整,私法自治是这一领域内必须坚持的原则。由此可见,宪法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背景下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划分各自的范围并对政治国家进行直接调整,至于市民社会领域则是宪法所不能直接涉及的领域,它是由以民法为核心的私法直接进行调整的。用日本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来概括就是,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③。
那么,在作为公法核心的宪法与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宪法和作为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之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协作”的演变过程[12]。根据日本学者山本敬三的总结,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异质论、并立论和融合论[13]。作为民法学界对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比较传统的看法,异质论认为宪法与民法无论是在调整的对象上还是在规范的内容上都存在极大的不同,二者是性质完全相异的法,是互相对立的存在;宪法并不构成民法的基础,民法也无需服从于宪法。相反,二者互不干涉,宪法的效力仅及于政治国家领域而不能深入至市民社会的领域,即民法调整的领域。依此观点,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能发生任何效力。而这,也正是传统宪法学界对于宪法权利规范效力范围的认识。
并立论和融合论则是产生较为晚近的观点。并立论者同样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是社会的基本法,但是并不认为民法与宪法是对立的、性质完全相异的、毫无关系的法;相反,并立论主张民法与宪法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因此民法与宪法从规范到价值都应是协调一致的。至于这一共同的价值基础的具体表现形态,学者们则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是自然法,有的认为是人权,有的则认为是近代法理论。日本民法学界泰斗星野英一认为这一基础是体现了近代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的人权宣言,或者说是保障人权的思想。他指出,人权宣言是同时超越于宪法典和民法典的基本原理,宪法与民法都必须体现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基本原则[4]。至于融合论,则是在承认民法对调整市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承认私法自治的基础上,强调宪法对于民法在规范和价值上的统率作用,认为民法并不是与宪法并立的存在,民法应该遵循宪法。融合论与并立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并列论者认为宪法与民法共同的基础是自然法(人权宣言),而融合论者则认为是内化于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用芦部信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二战之后各国宪法以个人尊严为基础确立了人权的实定化,这一价值(人权的价值)构成了实定法秩序的最高价值,它作为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内的全部法秩序的基本原则,统领所有的法律关系领域[15]。
应该注意到的是,无论是并立论还是融合论,它们都为宪法与民法搭建了互相协调的基础,这无疑是对异质论反思的结果。异质论将民法与宪法放置在同等地位并且认为二者之间毫无瓜葛,这必将导致民法不必遵从宪法的结论从而使得一国法律体系失去协调一致的保证。此外,在国家作用发生变化和公、私法之间产生融合趋势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对抗的认识已显得不合时宜。具体说来,在国家作用上,现代宪法普遍规定了包括福利权在内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这种权利与传统的自由权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仅要求国家的不干涉,而且还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以实现公民的权利。此外,由于这种权利的性质也逐渐辐射至传统的自由权[16],因此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更是日益得到强调。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公、私法之间的划分也不再是那么清晰和确定无疑的了。此时,再坚持民法与宪法毫无瓜葛的看法就显然已是不合时宜而且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了。那么,民法与宪法统一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作为近代法/现代法,无论是宪法还是民法都必须体现人权保障的原则,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宪法与民法是不是统一于人权基础上的同格的存在?实际上,虽然承认了民法与宪法具有统一的基础,并立论仍将导致与异质论相似的结果。按照并立论者的观点,由于宪法与民法都以人权为价值基础,宪法保护的价值与民法保护的价值也就具有诸多相通之处,由此在规范层面上宪法与民法也就应该是互相协调的而不应该出现矛盾。但是,当民法和宪法是体现共同价值的同格的存在的时候,就很难证明二者之中何者在法律效力上应该具有上位法的地位。虽然在理论上二者在价值上是统一的,因此在规范上也应该是协调一致的,然而实践中总是难免会出现二者在规范上背离的情况。而这种背离一旦出现,应以宪法为准还是以民法为准将很难得出答案。据此,笔者认为,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上以融合论的认识较为妥当。
而根据融合论的观点,尽管宪法的效力范围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由于内化于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因此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也必须服从于这一价值基础。换言之,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连接国家的基本法——宪法与社会的基本法——民法的桥梁。不难看出,其与德国的间接效力理论以及“客观的价值秩序”的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上所述,德国宪法法院之所以承认宪法在私人间具有间接效力,就在于法院认为《基本法》确立了一种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客观的价值秩序”,而这一“客观的价值秩序”应体现于整个法律体系,包括民法在内。另一方面,路特案的判决所确立的原则同样是尊重了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尊重了“私法的历史传统”显示出来的“巨大的力量”[17]。
概言之,即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宪政国家在坚持公、私法划分的传统的基础上,认为宪法属于公法,构成国家的基本法,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足性的民法属于私法,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宪法并不能直接调整市民社会,因此不能直接在私人间发生效力;然而由于宪法中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体系构成了“客观的价值秩序”,形成了宪法与民法共同的价值基础,它也就必然对民法产生统率的作用。据此,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只能通过民法的概括条款,以影响民法解释的方式产生间接的效力。而这,正是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在公、私法划分的背景下产生的理论基础。
三、在我国背景下对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
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在西方宪政国家多产生于二战后,在我国却是近年来才逐渐成为宪法学界研究的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将宪法认同为政治法,否认其法律性,从而使得宪法长期以来不能在司法裁判中得到适用,以致最终丧失了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产生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我国并不存在“宪法是公法”的观念。受苏联法学思想的影响,我国法学界把公、私法的划分作为资产阶级法学和资本主义法制特有的现象,认为“法是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公法’与‘私法’之分”,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性”,因此否认公、私法的划分[18]。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传统宪法观念并不认为宪法仅仅是公法,而是认为是超越了公、私法划分的“国家根本大法”,强调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19],笼统地认为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在任何领域都应该具有效力④,而没有注意到宪法效力范围的问题。甚至是在“宪法是控权法,主要针对的是国家权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对于宪法性质的这一传统认识也仍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⑤。在这种赋予了宪法“超越公私法分界的基本法”地位的观念影响下,宪法的效力自然及于私人间,宪法不仅仅是国家的基本法(构成法),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构成法)。于是,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也就成为了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的伪问题⑥。
因此,如果要在我国讨论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首先就必须对宪法的性质进行重新思考,而这一任务首先是由民法学者承担的。如同上文所述,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从意志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将宪法视为可以调整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根本大法”和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总章程、总纲领,从而一方面抹煞了宪法的法律性,另一方面也抹煞了民法的特殊性,无视民法这一部门法长期发展所形成的自足性和独自性。这就使得无论是民法还是宪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抑制。由于民法所调整的是相对而言未涉及根本的经济生活领域,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民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提出了要求,因此民法学者率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并为自己的部门法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反思一方面表现为对公、私法划分的重新提倡,指出民法属于私法,应当确立私法自治的原则[20],另一方面表现为引入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立的理论,主张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律。其中,较为早期和集中论述这一问题的当数徐国栋。徐国栋在《市民社会与市民法》一文中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截然分立的观点出发提出国家由宪法调整,市民社会由民法调整,而“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为社会整体的二分之一(另一半为政治国家),因此民法是与宪法并列的存在,高于其他部门法,为根本法之一”[21]。在民法学者的推动下,我国法学界逐渐确立了民法为私法的核心,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律的观念。进而,宪法的公法性质也逐渐为人们所意识到并得到了初步肯定。例如,李琦提出了宪法不是“母法”而是“公法”的观点[22];张千帆指出“要把宪法完全视为一部凌驾于普通公法与私法之上的囊括一切的法律,未免就抹杀了宪法的基本特点以及宪政与法治的区别”,并且指出几乎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承认宪法的公法性质[23];张翔则在考虑现代公私法融合这一趋势的背景下提出宪法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私法性质的公法⑦。正是由于对宪法的公法性质进行了重新认识,我们才意识到了宪法的效力范围也应该受到限制。换言之,宪法不及于由民法调整的市民社会领域,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具有直接效力。由此,宪法对第三人效力才具有了讨论的余地和空间。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法治建设上的后进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上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存在着深厚悠久的民法发展史,民法构成了自足而成熟的体系;而宪法相对产生得较为晚近,宪法观念可以说是从民法及其培育的市民社会中演进出来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民法视为与宪法同格的存在,并否认宪法对于民法的渊源和上位法关系。这就导致了在宪法对私人间争议上的“无效力说”。但是在我国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历史。相反,宪法与民法在我国的(近代化)发生史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宪法由民法演进而来的问题,二者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对于民法的上位法地位就更为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宪法被视为整个国家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的基础的观点也就较为不可能受到挑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的产生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德国为例,其传统法学观念即认为宪法是公法,民法是私法,宪法的效力仅及于政治国家领域,市民社会则应坚持私法自治的原则而由民法予以调整。德国后来之所以会产生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力量的发展、公私法的融合和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等原因。社会力量的发展使得某些个人或组织具备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公司即有可能对雇员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而公私法的融合和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则使得宪法与民法的调整领域发生了交叉和融合,从而导致宪法与民法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竞合[2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才得以孕育而生。而我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如同上文中所分析的,我国传统宪法观念并不认为宪法仅仅是公法,而是认为宪法是超越了公、私法划分的“国家根本大法”,其效力及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正如张千帆所指出的,这种将宪法认同为凌驾于普通公法与私法之上、囊括一切的法律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利于宪政建设的:不恰当地扩大宪法效力的范围会削弱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及法律效力,并可能影响立法机关作用的发挥和导致司法专制[25]。只是在民法加强了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和初步确立了宪法的公法性质的今天,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才得以借齐玉苓案的契机浮现出来。因此,在我国之讨论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与其说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发展、公私法的融合和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等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宪法的公法性质、限制宪法的效力范围和明确民法的市民社会基本法地位。正如郑成良所指出的,现代文明的出现主要是借助了两种力量,一种是科学技术,另一种力量就是契约。契约的出现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个人在社会面前取得了独立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私法传统中的契约和私人自治的理念构成了对宪政的某种支撑。而由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国家观起着很大作用,民商法传统中所强调的契约、私人自治就非常有效地起到了抵消泛道德主义的国家观念的作用[26]。因此,从促进宪政建设的角度考虑,由于我国缺乏“控权法”观念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立的传统,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私法体系的完善、私法自治的保障对于促进公民增强权利意识、形成法治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笔者认为,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之下思考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时应该首先明确的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约束公权力,建立起近代立宪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对峙关系,以利“私法自治”的形成[27]。也就是说,我们应强调民法的独立性,对宪法调控的范围进行适当的限制。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能矫枉过正,而必须坚持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即应在协作的基础上强调分立。进而,在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将重点放在限制宪法效力范围、确保私法自治上,而不是如德国、日本等国家一样强调宪法对私法的渗透。事实上,我国有许多文章在谈到宪法对第三人效力时都考虑到了我国的特殊国情,指出不能生硬地将德国的间接效力理论照搬过来[28]。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所产生的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应该靠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和我国的民事立法来解决。在我们思考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的时候,必须记住私人间的相互侵权不受宪法调控,个人侵犯个人权利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标的物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宪法原理[29]。
综观我国宪法学对违宪审查这一课题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其研究对象经历了从宪法的法律性到违宪审查具体模式再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继而到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对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宪法学研究摆脱了对前辈的研究做重复劳动的状况,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并不是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唯一的理论基础,国家作用的转换、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发展等同样构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基础。本文只是试图提供另一种分析视角,从而使得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更深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5—11—27
注释:
① 本文为向2005年宪法学年会提交的会议论文的修改稿。由于宪法中只有基本权利条款会产生在私人间是否具有效力的问题,因此本文中“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与“宪法对第三人效力”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② 参见郑贤君:《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该文对“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做了极为深入的分析。http://www.calaw.cn/include/shownews.asp? newsid=6124.于2005年9月17日访问。
③ 这里的“基本法”意同“构成法”,指的是对相关领域的组织、构成、基本行为规范规定的法律。参见山本敬三「法システムにおける私法の役割」,法律时报76卷2号。
④ 例如在比较早期的谈到宪法权利规范司法适用问题的文章中大都认为宪法在私法领域同样具有直接效力,参见费善诚:《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探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姜峰:《论我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陈焱光:《论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载《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⑤ 例如童之伟就是持“宪法是超越公、私法划分的基本法”的观点,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1年第11期。而张千帆虽然提出了应明确宪法的公法性质,但却同时同意“宪法并不仅仅是一门特殊的‘公法’, 而是超越简单公私分界的基本法”的观点,见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⑥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张翔同样也注意到了我国宪法传统观念对于宪法对第三人效力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影响,与笔者不同的是,他是从“宪法的国家取向”和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在我国从来不曾确立“控制国家”的理念,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是统一于集体利益的,因此“国家与社会由二分重新走向同一”,“‘公民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问题的逻辑前提就不存在”了。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J].中外法学,2003,(5)。
⑦ 根据张翔在年会上的发言,其已经修改了这一观点,即否认了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私法性质,而认为宪法是纯粹的公法。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J].中外法学,2003,(5).
标签:法律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日本宪法第九条论文; 德国民法论文; 民法调整对象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民法基本原则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民法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