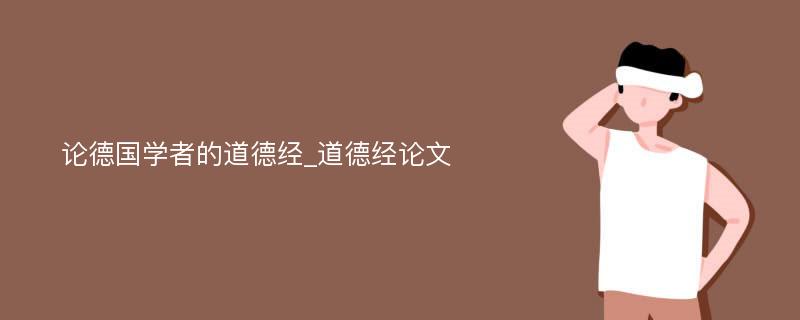
德国学者论《道德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经论文,德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镇东 李道湘 译
要重新理解和翻译像《道德经》这种已经常常传用并被译成了许多种语言的著作,乃是一种需要一定证据的难以办到之事情,因此我们就把L′·D·贝尔纳教授那句朴实无华而富有意义的话放在本书的开头当作解释:“在有所发现中的最大困难,不是在于进行那些必要的观察,而是在于观察理解中要摆脱传统的观念”(《历史中的科学》,柏林1967年版,第38页)。《道德经》对于每个认真研究它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发现。作者采用的那些概念显然都是可作多种解释的;作者本身几乎也是不知道的;在整部著作里就没有一些专有名词和其他任何说明能使一种时间编排成为可能,因此该著作编写的时代就只能按照文体标准(但是原稿和构想就不一定非在同一时期不可)近似地确定在某某“世纪”,也即确定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或第五世纪。这些客观困难还要包括翻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于汉语注释家,而汉语注释家本身又跟他们时代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潮、儒学思潮、新儒学思潮、法家思潮和其他流派有着明显觉察得到的依赖关系,因此就会有意无意地歪曲或纂改《道德经》学说的思想内容。
欧洲的翻译者也都缺乏观察。法国学者Abel Remusat的观察就暗示并不是所有的观察对于理解著作都是无条件必要的,他竟无中生有地硬说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第14章中“i”、“his”和“We”这三个汉字,而德国学者Victor von strauβ还同样认为这是正确的(《道德经》,莱比锡1924年版,第62页及下几页)。
这种受到偏见束缚去理解原文的极端情况颇为清楚地表明,象《道德经》这样一种措词简约和含糊不清的本文提供给翻译者的观察可能性会有哪些了。
但是由于人们一般只能有限地摆脱个人的偏见,要说明这次重新翻译和解释《道德经》理由的恐怕只能是希望这些工作会稍稍有助于解开古代中国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总还埋藏在其下面的那层外壳。
还应对于汉语术语的发音和按发音改写的情况讲些话。每个汉字是念成单音节的。过去依据英语韦氏音标系统音译的“Tao”字对于德国的读者来说出于两种原因是表明为使人产生错觉了。第一,“a”和“O”在念的时候并不产生双元音——而中国人就会象“schau”(看)一词中的双元音“au”那样发“a-o”的音;第二,开头的辅音并不是清辅音“T”而是浊辅音“D”。因此,“Dau”(道)字要代替传统的“Tau”(套)。同理,英语的——在我们这里也往往成为习惯了的——“Te”字写法用以代替“De”(德)字也不必要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当然,“De”(德)字里“e”音在德语里是没有等值物的。它的发音大致就等于“Schneider”(裁缝)里的收尾音节“er”,因为那个结尾的辅音字母“r”是不发音的。
读者可能会奇怪在译文中除了道教术语“道”和“德”字外所有单词都是小写,而且一切标点符号(除了那些为理解非用不可的以外)也都避免使用。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古代汉语中没有我们语法概念意义上的词组和标点!所以我们就敢于试着从书版上抹煞名词和动词以及句首和句尾的差别,至少是用这种通过德语可以为我们效劳的唯一视觉方法使得这些差别更少引人注意一些。同时我们也还抱有这种希望:那就是要让读者自己尽可能地通过那些通篇都是小写和缺少标点或无标点的句子去寻找各种联系并从而仿佛是能解说似地参加到译者的工作中去。这种书版印刷形成上的视觉辅助手段,就我们通过自我批评所能获知而言,由于不纯粹是表面形式都可追溯到——我们说是——Stef an George,我们在主观上就还感到对于不适当地渴求些微创见是有过失的。那末到底为什么就不能从纯粹视觉上敦促读者在以上所说的明显具有多义性的情况下,通过思维和说明一起去完成认识过程呢?
谁在手中拿到《道德经》,谁就不由得会立即提出这个问题:“道”和“德”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专门名词在翻译中是通过按发音改写的方法表达的,因为任何硬译成德语单词的试图都会肯定地造成错误的观念。“德”这个字,正如它被道家和其他学派所使用的那样,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可也只有在我们对于“道”字的各种概念层次的形成已经有了某种认识时才能正确地理解。①在《道德经》的第一章里讲到“道”时写道:凡是深度最深的地方,就是一切秘密的入口通道。我们就要通过这条“入口通道”试图深入探究《道德经》的思想领域。
“道”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因为在众所周知是属于孤立语的汉语里——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一个单词或一个汉字是属于某种词类(按照我们的语法概念来讲)大都只能通过其在句子中的位置来识别。因此“道”字就可表示为“道路”的意思,也可表示“沿道而行”的意思。“道”之作为动词就能表示“领导”、“引导”、“治理”(一条江河),“调整”,就其作为名词而言就能表示“方法”、“方式”、“能力”、“原则”。此外,“道”字在《道德经》和其他古代著作中还往往具有“说出”、“告诉”、“列举”的意思,这种意义经过诸多世纪一直保留到今天(尤其是在小说中)。
在那本含有宇宙起源学方面观察并夹杂有占卜学套语和咒词的宗教法规《易经》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句子:“一阴一阳谓之道”。阴代表土地、月亮、阴性原理、被动之物、黑暗之物、潮湿之物、寒冷之物等等;阳则表示天空、太阳、男性原则、主动之物、明亮之物、干燥之物、温暖之物等等。“道”在这里就表示为两方面事物的综合。在该书中还继续写道:“乾和坤(象征天和地)就是变易的大门(比较《道德经》第一章),乾是阳的实体,坤是阴的实体。阴阳调和而成德,”——我们把这里的“德”就暂时翻译成“实体”——“从而就变成为硬物和软物(柔顺物)的基础。天地活动的各种过程都通过硬软清浊来体现。各种精灵的‘德’也通过软硬浊清而起作用。“我们在第一个引文中是把阴阳当作有其双重性时是与“道”同义、是潜藏在“道”之中,是内寓于“道”之中来认识的,而现在阴阳成了构成一切活动的基础——仿佛就是男祖先和女祖先——就是联合统一起来。阴阳在其还未分开的共同体中就是所谓双性的,就犹如阿斯泰克人的一个两官职者Ometecutli,就犹如伊特拉斯坎人中的Voltumna或埃及人中的Atum能通过自我交配生出空气之神“数”(在古代汉语里就是“气”——呼吸,空气,“普纽玛”——就其作为最细小的实体而言就是阴阳两力的基体,参看下面)。我们在东亚商、周(见下面)部落神话和楚国民族神话中、在朝鲜关于文化神人Dschnmeng或Dungming的神话中、在日本阿伊努人关于Tschitsani和年轻的天神等神话中,都能见到一些或多或少已经模糊了或者作了修正的天地两种实体配对的宇宙起源学方面之神话。就在其他大陆显然也有一些类似的神话土生土长的形成,例如在北美洲西南部的育曼部落就认为人们使用着的一切物件甚至人们本身和那些动物都有太阳和大地的交配行为。
但是“道”还有另外一种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不无重大的意义。在古时候,“道”是一种被注释家们与对祖先的献祭品同等看待的献祭品的名称。在《礼记》中,献祭品就表现为对于道路之神的献祭品。在坐车外出之前,就在城廓(或军营)前面堆起一个土丘和立起一个稻草人让车辆从上面滚过。相同名字的献祭品可能也与从祭礼上崇拜死去了的父母有关联。众所周知,对于古罗马人的祖先神灵就是同时也被当作道路之神和十字路口的幽灵来崇拜的。伊特拉斯坎人就在自己城市设施的两条主要街道交叉口挖掘一条他们称之为世界的井筒。这条井筒按照他们的想象就能通到阴曹地府,通向祖先的灵魂,而祖先们就是由于这种“灵魂石”才被阻止住在为已故者按规定献祭的时间之外上来打扰活着的人。这种对于死者神灵的态度一般都是产生于矛盾心理的;它们受到人们的崇拜和敬畏;人们要录求它们的援助,同时人们还要保护自己免受它们的危害,而且往往还用强力手段,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魔力在原始人看来似乎就是最重要食物(动物和植物)的布施者,因而跟死人的宗系是有“亲缘”联系的,先人们的幽灵就与也被看作部落祖先的那些死者幽灵融合成一体了。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在图腾崇拜中——而且也在中国——形成一种讲究礼节的敬奉祖先活动。这种对于“道”或“祖”的献祭品似乎是以这样一种夹杂着有益魔力和祖先崇拜作为基础的。那被车辆辗倒的稻草人还能让人看到崇拜植物或者田地魔力的痕迹。当然,我们不能再原原本本地仔细思考这种类型的献祭品如何是同道路之神的献祭品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根据历史的原始资料知道周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每逢出征时都要随身带着他们祖先的木雕像的。那种“超自然力量”——祖先和死者的神奇力量——不仅能在和平时带来丰饶,而且在战争中也会带来幸运。
“道”字是由“首”字和一表示“走”意思的所谓词根或限定词组成。由于“道”字经常是以该词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道路”意思出现,人们就很容易会满足于这种用法而不进一步深入探究更深的基本意义。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单字的组合也能说明这一点,因为这种组合就可进行如下的解释:头首用部分代表全体就是指的人,而这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向——按照所谓人脸部的突出部分亦即鼻子所指的方向——“走在一条道路上”(这“走”字就暗示着一条道路)。然而,这种汉字组合的重点本来就不在“走”或“道路”上,只是经过某种相应的意义演变后才给附加上词根“走”字,这种情况同样也是可能的。按照古代的文献,“首”字也以(拟声)“述说”即“表达”(自己感情)〈见《礼记》第37章〉的意思出现;就在今天的语言使用中也还保留着“首”字的这种次要意义,例如双音词“自首”的意思就如同“承认自己有罪”(“自己列举”自己的罪状)。如果我们现在认清“道”字在《道德经》和其他原始资料中往往用作“说出”、“讲述”、“告诉”、“列举”的意思,想到这类意义经过诸多世纪还一直保留到今天,那末有可能在这类概念范围之内去寻找“道”字的基本意义就是有前提的。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亦即刻在兽骨上的所谓“甲骨文”(公元前15世纪至12世纪)中,“首”字是以纯粹的表意符号出现,而且是以动物的头,确切点说是以动物的假面具形式出现。我们从有关许多部落的祭礼习俗方面的真实可靠报道中得知,戴上一种假面具就会使得这个假面具的人变成由他所表现的生物,因此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这方面一个熟悉的例子就是贝勃罗人部落(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的Kacina祭礼。有关超自然的生物或死者的精灵会在戴假面具的人身上显现出来,也会从戴假面具的人的嘴里说出话来。甚至我们那么熟悉的单词“Person”(个人)、“Personifixieren”(拟人化)等等也是源出于表示(演员)假面具意思的拉丁词“Persona”。那种从假面具嘴巴开口处发出来的声音,就不再是演员的而是属于被表演的角色了。从演员嘴里讲出话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是另外一个人在“通过”假面目“滔滔地讲”;因为名词“Person”(假面具、然后又指角色、人物、个性等等)是以动词“Personare”——滔滔而语——作为基础。除了这种强加于演员另外一种“个性”的外在形象亦即假面具以外,这另外一个“人”也会通过演员所说出或所吟诵的话语——借助于祭礼仪式、咒词咒语或者召唤鬼神——而起作用。因为这种话语的威力和类比魔力对于原始人来说会具有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多得多的意思。在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中就还保存着这方面观念的令人信服的见证。埃及人就曾认为蒲塔神(ptah)是通过话语创造了世界,蒲塔神一说出事物的名字,那些事物就会马上成为现实。古代印度人认为“说话女神就是宇宙的创造主和生命力”(W·鲁本:《印度哲学史》,1954年柏林版,第68页)。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还相信一种生物或者东西的名称就隐藏在自身内部作为看不见的核心。最后,圣经上的“开头是话语”也不外乎就是那种原始人相信话语全能的一种回响——那种人有伟大创造的一种回响——那种人有伟大创造的一种回响;因为有了这种伟大创造才使人类从动物界中显得突出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能支配自然力的存在体。作者在《道德经》的第25章中说道:“人们可以称之为一切事物的始祖,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就称之为‘道’。”这“道”在作者看来真的已经就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一种哲学概念了吗?或是在“道”的外面依然还裹着一些比较古老的,还是来源于有魔力、很神秘事物的外壳呢?
我们在这里想首先总结一下:“道”字的原始意义可能是在“说出”、“讲述”、“告诉”和“列举”这些概念范围。因为从这里按照上述意思就能产生一种或多种祭礼行为的名称(献祭品及其所说宗教仪式的名称)。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里,各个不同的学派对于“道”字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甚至把这一术语大都用作(管理国家、社会)“正确道路”意思的儒家学派,有时也把“道”字与上天的活动或意愿等同起来。就连主张明确表述概念的法家和实用主义者韩非子也是不能摆脱那种深深围绕着“道”字的有魔力、很神秘之束缚。他在那本以他的名字起名的著作《韩非子》一书)的55章里,就用了两章(第20章和第21章)的篇幅解释了《道德经》的一些段落,当然,他是按照战国晚期(公元前403年至221年)的法家思想(见下面)往往又以明显悖理的方式加以解释的。我们在书中看到:“智者观看黑暗的、看不见的东西(字面意思:黑暗的空洞之物),应用它的循环运动并且勉强地给它一个名字而称之为‘道’。因此只有在谈论到‘道’时才是可能的。(在《道德经》的第一章里)写道:‘道’是可以表达的。(在《道德经》的第一章里)写道:‘道’是可以表达的,但却不是永久的。”“道”这个概念在宇宙起源学和天体演化论方面的有魔力、很神秘之性质,在道家学派的著作里就表露得更为强烈。比如庄子(大概在公元前365-286年)在其按他命名的著作《庄子》的第六章中写道“道有现实性和可靠性,但是道既不会活动也不具有形态。道能进行传达,但是不能加以讲授(?),道能被人感知,但是不能让人看见。道是来源于和植根于自身。道是先于天地存在之前的,因为道向来就持续存在着。道能赋予死者的幽灵和祖先们以魔力,道能化生天地……”除了一些合理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诸如使人想起了阿那克西门多(Anaximander)的原质或原理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概念的现实性(“成”字在这里“大概”表示现实;确切的规定毕竟在任何的注释里都没有找到)和可靠性(指合乎法则的自然活动、世界事件的进程)以外,如象道跟死人幽灵的祖先们的神奇力量之直接联系的观念,就表明那种作者跟那古老部落的巫术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还没有能够断开。而我们不是刚刚提到了“道”字可能就来自“巫术语词”的概念范围而且道就是一种献祭品甚至是祖先的献祭品?
郭据原始人的朴素表象,属于部落组织里的不仅是指部落的人成员,而且也有部落的食物布施者、死者的牲口和死者的植物等等这些作为祖先或祖祖先都是被包括在部落之内的。随着部落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部落的概念也就扩大到周围世界一些信任人的现象上。于是宇宙就变成了人类的大部落。这种一直受到部落概念改编和影响的宇宙之表现就会按照人的观点服从于同一的社会秩序和礼仪秩序,因为人的部落生活就是基于这种秩序之上的。人的祖先曾是那些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使得一切每天发生在部落亦即宇宙中的事物最初得到创立或成为可能的人。这种事情的一般而有把握的进程,在人看来可是只有在祖先的创造力经常得到更新时才会有所保证。要达到这一点,部落的礼仪就要得到认真而准确的遵循,年青人就要接纳仪式。在从事农业的民族那里,古老的部落礼仪是同巫术上“事先注意”四季的一般进程相联系,而这种事先注意从巫术发展到原始科学的思维中就产生了气象的观察和日历的创立。作为一种分工的结果,一个萨满或祭司就承担起关心自然活动在宗教礼仪上的“需要”这个任务。《道德经》中的智者由于他能让诸事物日益增长(第二章)而做出业绩——这些业绩在人民看来似乎是自行产生的(第17章)——就还带有负责“事先注意”牲口、五谷、下雨合乎规律的进程和日月星辰的运行那种人的特性。鲁思·本尼迪克特写到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贝勃罗部落时说:“在六月份快成熟的庄稼需要雨水时,……祭司们就静静地坐着集中思想考虑礼仪的事情……如果求雨的符咒成功,祭司们就会在大街上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就会向他们纷纷表示感谢。祭司们已经送更多的雨给自己的人民。他们已经维护了人民的一切生活形式。因此他们作为人民保护者的地位证明是正确的。”而祭司们就说:
“甚至每个小甲虫,
每个肮脏的小甲虫,
也要让我全都把它们牢牢抓住,
不要让一个小甲虫从我握着的手中滑脱。
但愿我的孩子们的道路
全能得到实现……”
(《文化模式》,1934年纽约版,第69、70页)而《道德经》是怎么说的呢?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智者就这样很好地保护着人们
智者对谁也没有忽略
智者很好地保护着东西
智者对物也没有忽略……(第27章)
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贝勃罗部落的祭司是在“静止地”起作用。而在《道德经》(第45章)中我们就能看到:纯粹的寂静会归还世界以真正的规模。
留心的《道德经》读者就会看到许多明显合乎这种观念世界和这种生活感受的东西是以道家智者的面目出现的。由此也就说明了在中国(但是也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区)为什么把自然灾害看作萨满君主或皇帝真正或者被误认为在宗教礼仪上和后来的道德上有过失的“自然”结果而要他们本人承担自然灾害的责任,在欧洲的火烧巫婆当中肯定也会含有类似观念的残余。
以后由于改善了生产资料和奴役了异族的部落,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条件就逐渐地扩大到剩余的生产,部落权力手段的体现者——那些负责部落宗教礼仪和进行战争的个人或团体——就从部落成员群众中显出特色来。他们纂夺了这种权力的王冠。占有祭礼物品就保证了他们在部落共同体中的一些特权。比如中国,首领和部落的萨满以及后来的诸侯、君主或皇帝就变成了全部部落财产“大一统”而高于那些小公共团体的象征(见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1953年柏林版,第376页)。这种通过一个个人或者一个由他领导的行政机关来体现宗教礼仪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之形成过程,在中国就由于扩大灌溉设施和整治河道的必要性而得到了促进。毫无疑问,道家是那么经常地选择“水”作为他们“道”的象征就不是偶然的。在那本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管子》全集(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的第39章里,水的意义就比较明显地是脱胎于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智者在自己通过漫游感化世纪的时候寻找着一种具有水域性质的解释(用以解释人民那些合乎道德的特性)。因为这种水域要是统一的,那末人民的心就是合度的……因此……智者就不力图说服个别的人,也不挨家挨户地去说教,而是去领会(自己合乎道德的漫游效果)在水问题上的关键。”因此,我们就不会惊讶“道”字能从“说出”、“讲述”、“列举”(“谈论”——巫术的祭礼咒语词)和“祖先献祭品”及“道路之神的献祭品”扩大到诸如“领导”、“引导”、“管理”、“整治河流”等等的概念。之后就产生了诸如“正确统治的方法”、“整治河流的方法”最后就是“道路”(按照抽象的意思就是:方法、方式、原则)和普遍“方法”之类概念作为下一个更高的抽象。
这里讲述的发展过程一经逆转亦即从观念上回归自己的起始点,就构成了早期道家著作的基本趋势。如果我们不看《道德经》的作者以及庄子和其他早期道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发生深刻动摇和变革的时代认为宣传“回归”——“回复”是朴素的原始状态——就是摆脱表面上好似无望的处境的唯一出路。《道德经》在它的一些根本特性方面对于我们来说就依然还是无法理解的。这些道家就可以假定他们还能亲眼看到那些生活在“朴素的原始状态中”的人的。因为在“南派”亦即道教流派盛行着的楚国土地上(在今湖南、湖北和江西省的地区),在当时甚至更后一些也还住着一些除了刀耕火种经济之外主要是以采集食物、捕鱼和狩猎为生的部落(见司马迁的《史记》,第129章)。
我们就让一位道家自己来说吧:“在那个时期(在‘至德之世的’时期),既没有小路通过大山,也没有船只或桥梁穿过水域。各种事物都在和睦地繁荣发展。各个行政区都是(松懈地)相互联系着……人们跟飞禽走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同一切东西构成一个氏族。人们难道能够知道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吗?大家都在同样无知的情况中生活,他们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德。大家都同样地没有欲求——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之为‘纯粹在道德上没有败坏’。只要这种“纯粹的在道德上没有败坏”还在持续,人们的天性就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东西。但当后来‘智者’拼命地致力于‘善’并且专断地谈论‘善行’时,就到处开始产生了怀疑。而当智者随后也把(祭礼、民间的)音乐任意改动和把宗教礼仪进行歪曲时,就开始在人们中间表现出(就会的)差别来了。因为人能制造献祭品的各器而不毁坏(材料-木头?)的最原始样式?雕制玉笏而不破坏纯玉?引进‘善’与‘善行’而不抛弃‘道’与‘德’?推行‘礼’、‘乐’而不夺走人民的本性?……为了用它造成物件而毁坏一种原料的最原始形式,这就是熟练手工业者的一种过错。但是为了从中造成‘善’和‘善行’而去破坏‘道’和‘德’,这可就是‘智者’的过失了……”(《庄子》第9章)。
在这段文字里首先引人注意的就是作者认识到或者预感到原始社会观念世界的一些主要特征,而这些主要特征由于教会方面教条主义的偏见对于人类学的研究来说仍然还是长期难以接近或模糊不清的。环境、宇宙、飞禽、走兽,“一切事物”,在这里都表现为跟人们“结成姻亲”“这些东西跟人一起共同属于那个大部落。”造成与自己宇宙和睦相处的人们中断了跟自己周围环境自然联系并且变成了支配“奴隶”的“主人”这一“罪恶情况”的过错,在这里也跟在圣经中一样是由“认识”亦即“知识”承担责任(参见《道德经》第(19、20、65、81章),只是真正的罪魁不是上帝或者具有魔力的撒旦,而是人自己——个突出在群众之上而现在要说教他的道德却不宣传自然道德的人:即“智者”。庄子这是指的什么样智者,乃是不难猜到的,因为在庄子的全部著作里也和在《道德经》中的情况一样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智者:即效劳于或体现着暴力的“专断”智者和跟“一切事物”和睦相处并且服从“道”和“德”而让“道德”在自身中,在人们中和在宇宙中“纯粹没有道德败坏”地起着作用的智者。
这种“罪恶情况”是在若干阶段中完成的:它以失去“无知”——失去人在自己跟就会存在、跟自己本身和跟自然的关系中的直接性而开始。这样人跟“一切事物”共同属于它的那个大“氏族”(大部落)就解体了。人就发觉(在这里就开始出现“有罪恶的”认识)自己个人的“德”(自己来源于“道”并跟“道”联合统一着的实体),这样人就失去了那种“协调地”去适应“道”的秩序的自然而无意识的能力。“知道”或“认识到”自己独特的本质性和其他人的本质性,不仅会导致差异化而且也会产生贪欲性,从而就把“道”这种“超自然力量”——那种在个别人身上起作用的原始力量——转变成不再为全体亦即大部落谋福利而是用来鼓励个别人对于共同体的需求之工具。人们现在要求“善”和“正直”,②是因为人们随着统一的瓦解就认识到有善也就有恶(《道德经》第二章)。因此就要吸收回来“真正的知识”,而这就只有在重又忘记了“错误的知识”才会产生。正如教施洗的约翰所说的那样:“他必须增长,而我必须减轻”,《道德经》就这样说到了那些努力追求“道”的人:谁专心从事于学,谁就每天有所得,谁专心从事于“道”,谁就每天有所失(第48章)。为了人民易于理解和铭记这种“善”和“正直”的新道德,“智者”就修改了“乐”——那些古老的宗教仪式圣歌和民族风格曲调——和歪曲了“礼”。这样一来不仅人们注定要脱离自己的自然环境,而且社会的统一也注定要解体。《庄子》和《道德经》就认为“智者”要对这种人类的衰落担负责任。在上面引文中提到“玉笏”的情况就说明了早期道家讲的这些“智者”是指的是谁:这就是指的那些打破了白玉(道德纯洁性的象征)以便从中形成权力标志的人。
谁细心阅读《道德经》的第13、17、38、39和49章,谁就不难认出上述的发展过程和把这种进程通过观念上的逆转引回到它的起始点上去的努力。当然,《道德经》由于自身格言式的简练在讨论这个问题当中就没有幅度更宽的“抒情诗式散文作家”(或者小品文作家)庄子那么详细。
我们已经选择了语源学(真正语义学)的道路来指明“道”字是那么深深地植根于古代巫术的表象,以便更清楚地阐述“道”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但是“道”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未因此而利用竭尽。犹如每一种哲学体系一样,《道德经》和庄子的著作也都是要力图面对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和自然方面一些难以解释或不能解释的现象达到自我谅解,认识和确定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概念式地理解社会和自然的整体性及其相互作用,并使别人也能理解这样所获得的知识——即在或大或小一些的基础上从社会实践方面加以利用。因此在“道”字概念中(也在“德”字和其他概念中),那些能被我们从这概念的总体中当作“巫术魔力”剖析出来的要素都是在参与的。可是这样一来,这种有魔力的要素就只会是整体的一种精选出来的组成部分,一种被剥夺了其功效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在这里想一开始就这么说——即使在传统上有条件和受制约的观念都能有助于早期的道家建立他们的思想大厦作为自然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急于使得这种古老的精神遗产合乎他们本时代的需要,尽可能合乎逻辑地扩充古老的精神遗产并且使之摆脱自身的限制。
注释:
①关于一种即使是暂时的,受时代制约的纯粹从形式上颠倒“道”先于“德”的情况,参看附录部分《论两种1973年发现的道德经不同文本》。
②汉字“义”——译成正直——可只是近似地相当于德语词。它本来的意思是指按照年龄、等级、身份对待或效劳于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地位较高的人的道德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