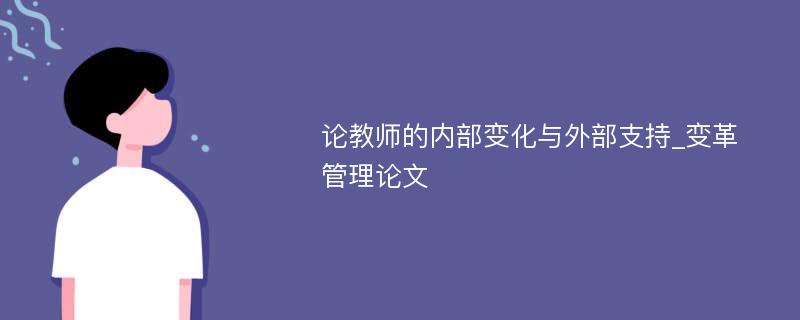
论教师的内在改变与外在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在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国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将改革重点从过去的体制变革转到课程与教学改革上来。在这一改革浪潮中,作为具体实践者的教师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或被认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被寄予高度的期望,或被视为改革的障碍而被要求自我改造。但无论如何,教师要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旧有的观念与行为,以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已不可避免。
一、学校改革及其困境
在现代求新求变的社会环境里,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教育改革计划,希望藉此改进学校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成就,最终建立起本国庞大的人才库,以确保在全球化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力。如美国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就前后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浪潮的洗礼。(注:第一次改革重点在集权、提高标准、推广考试和批评教师质素;第二次改革强调分权、教师的赋权增能、校本管理和择校;第三次改革关注系统化的学校结构重整。Saban.A.(1997).Emerging themes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refor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form,6(3),349-356.)同样,几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举起教育改革的大旗,都将教育改革和学校改进纳入政府优先考虑的议程。
就学校教育而言,要求其进行全面改革的呼吁不绝于耳。人们或者批评现行公共教育系统过时了,认为教师与学生在学校中的生活方式及其在课堂上的互动模式与百年前并无本质区别,学校完全在利用“现代”的内容和方式处理“后现代”的挑战,因而注定未能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增值”人才(注:根据Henry Levin的研究,高增值人才至少具有以下12种能力,即主动性、合作性、能在团体中工作、朋辈间培训、检讨、推理、解决问题、做决定、获取和使用资料、计划、学习能力、掌握多元文化的能力。Levin H.(1998)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change.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Series:Occasional Paper No.15.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或具有“兼容性”的新型人才(注:卢乃桂.信息社会的人才要求[J].教育研究,2000,(11).)。或者提出要用私立学校、学券以及完全自由的选择制度来作为公立教育体制的重要补充甚至替代。当然,是否一定要追求彻底的替代性变革,仍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学校都不可能一如既往地自我封闭,固守早已被科技、社会变革及其产生的巨大压力所冲破的领地。相反,学校若希望促进未来教育的发展,就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周围世界的繁杂、艰难和迅速变迁的现实,进而作出自身的调整和改革。
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学校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关注组织变迁、学校自我评估以及个别学校与教师对变革的归属感;第二阶段自90年代始,尝试将学校效能与学校改革这两个不同的关注点合并起来考虑;目前进行的第三阶段则更加关注具体教育情境,关注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由此可见,人们对学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了位移,开始从过去对体制等外在因素的强调转到对课程教学等教育核心因素的关注。
虽然教育改革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由于教育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和高度复杂性,其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理想中的改革成效很难轻易见到。换言之,虽然各种类型和名目的教育改革计划不断登台亮相,并在瞬间引人注目,然最终总是归于沉寂。如一项研究指出,各种关于教育、教与学的陈旧态度在改革之后依然根深蒂固,年级制度、分科教学、固定课表以及科层管理结构等“学校教育的基本元素”也未因此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注:Tyack,D.& Tobin,W.(1994)The grammar of schooling:Why has it been so bard to change?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31(3):453-479.)个别学校虽一度表现出色,显示出改革的巨大功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革的能量逐渐“损耗”,最终总是回归当初,与其他传统学校并无二致。(注:Fink,D.(2000).Good schools/real schools:why school reform doesn't last.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即使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却根本无法推广,始终不能在“规模”上突破。有人在总结前两个阶段的学校改进成效时也指出,这些改革“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对学生成就产生的影响远不如预期。(注:Hopkins,D.& Reynolds,D.(2001).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school improvement:towards the third age.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7(4),459-475.)
造成改革困境的原因很复杂,难以一一描述,但改革策略的缺失无疑是其关键性问题之一。过去30年来影响最大的教育改革策略包括以下4类:(1)整理部件(fix the parts),即关注课程革新和/或教学方法的实施;(2)整理人员,突出教师专业发展;(3)整理学校,强调学校自我解决问题之能量的发展;(4)管理系统,要求整个教育系统不同门类和层次之角色、规则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注:Sashkin,M.& Egermeier,J.(1993).School Change Models and Processes: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理想的模式自然是关注各层面的连贯性和连接性,将学校改进作为一项有机的整体来对待。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过去众多的学校改革措施是将着力点放在教育体制层面,而没有深入到课堂层面的教与学。这些改革基本上奉行一种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改革原则,是一种将教师排除在外的(teacher-proof)改革形态。在这里,教师仅仅被视为现成改革方案的执行者,而不是有关方案和计划的参与决策者和筹划者,改革本身被看作是一件产品,而忽视了它具有人性的一面。在此前提下,学校改革的不彻底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内在改变
教师专业发展本身属于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两者很难分开,因为说到改革结果的成与败总是分别指向教师发展的贡献或不足,而开展任何改革计划时,总是希望同时达到教师个体的成长和学校整体的改进两个目标。有人指出,“除非教师发展项目指向全校的改进,否则只会沦为一些边缘化的活动”(注:West,M.(1998).Quality in schools:Developing a model for school improvement.In A.Hargreaves et al.(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Change(Pp.768-789.)London:Kluwer)。还有一些研究者表示,在确定教师发展与学校改革两者之轻重缓急次序时,应该将前者置于优先地位,将后者作为其有益的延伸,而非相反。(注:成虹飞,黄志顺.从教师成长看课程改革的意义[J].应用心理研究季刊,1999,(1).)但事与愿违,教师,甚至是教学,一向都被教育改革所忽视。
将教师排除在外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事实上,任何组织、材料、课程以及教学策略本身都没有能力去自我规划、启动或推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只有改革实践中的人才有能力开发和执行计划,最终导致积极正向的改革。因而,无论是“外加式”还是“自发式”学校变革,都无可避免地与学校教师的知识、能力、态度和情感等因素纠缠在一起。
不过,这些似乎显而易见的道理却在改革实践中被忽视。是故,改革者必须要清楚地知道参与者的感觉,并注意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信。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西方重构学校运动的深入反思,关于改革的人性因素这一论题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者开始尝试在组织结构的再造和文化再生之间达致一种新的平衡,而文化的再生或改变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改变。只是凡亲身参加过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或者对教育实践有比较清晰认识的人都不会否认,在专业发展过程中,要改变教师的行为和观念异常艰难。即使在教学中引进“良策”,但由于教师常常不能“从实践中去理解设计背后的理念、导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和条件”,结果“环境一变,或是新计划一完结,教师又再面临困境而不知所措,或是故态复萌”。(注:汤才伟,陈可儿,赵志成.推动学校改进:阻力与突破初探[A].优质学术计划资料册[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校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2002,18-23.)
因此,普遍的观点认为,教师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是抵制或抗拒变革的。由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地带,有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和经验,在其中就会觉得安全、舒适和稳妥,一旦逾越,则可能会遇上困难、麻烦、危险和挑战。因此,一定意义上讲,大多数教师抵制变革是由于他们对未知的恐惧或对超越自我舒适地带的忧虑而造成的结果,他们本能地担心人际或组织的变革会给自己带来潜在的威胁和影响。
进一步分析,则教师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而抗拒变革:(1)缺乏对改革者的信任;(2)坚信变革是不必要的;(3)坚信变革是不可操作的;(4)经济利益受到威胁;(5)成本较高;(6)担心失败;(7)担心失去既有的地位和权利;(8)固有的价值和理念受到威胁;(9)对外在干涉的不满等。(注:James,C R & Connolly,M.(2000).Effective Change in Schools.London,Routledge Falmer.)另外,相对来说,选择教师职业的人更喜欢安定的生活节奏,崇尚精雕细琢的教学艺术以及体味独处的快乐,一旦改革影响到教师在这些方面的喜好,也会遭到他们的抵制。
那么,这是否表明教师在本质上一定是抗拒改变的呢?也不尽然。
关于教师与学校改革的关系,除了上面将教师改变作为学校变革的一部分,将教师作为变革的对象去理解外,还有一个关注视角是将教师作为变革的主角,甚至就是“革新者”本身。有研究表明,对于教育改革来说,依靠行政体制的力量只可获得片刻的改进,而充分发挥教师专业主动性则可保长治久安。(注:Firestone,W.A.& Bader,B.D.(1992).Redesigning teaching:Professionalism of bureaucrac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因而要积极发展教师领导的学校改进计划或内发式的学校变革方案。甚至于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呼吁政府把教师看作解决教育问题之出路的力量,而非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这直接成为美国第二次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内地,教师专业性或专业精神同样被一些学者视为学校改革或教学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认为它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和课程改革的成功。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从其日常经验发现,教师并非一定抵制变革,他们不是因循守旧的群体,而是无时不在改变,“他们重组课堂,开展不同的活动,试用不一样的课本,改变课程主题的次序,尝试不同的沟通技巧等”(注:Richardson,V.& Anders,P.L.(1994).A theory of change.In V.Richardson(Ed.),Teacher Change and the Staff Development Process:A case in reading instruction.(Pp.199-216),New York & London:Teachers College Press.)。教师自己也认为其改变是与时俱进的,他们会根据课堂中学生的不同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新活动以帮助学生更加投入学习,而且这些都是教师自愿进行的。
自愿进行的改变通常具有自发性,而非外来的、强加的。因此,有学者指出,依靠外力改变学校文化是不可能的,只能诉诸“文化的内在转变”。换言之,就是提醒改革者,应该设法将“自上而下的、自外而内的”各种改革计划转变为教师自己的需求,让教师自己去发动、指导和维持,并使他们在此过程中感觉到有能力和信心。许多研究已经显示,让教师自我制订专业发展的目的和自我指导专业发展活动,对于促进教学实践之有意义的、持续的改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帮助教师对实践进行反思,没有人向他们教授崭新的教学策略,没有人提供激化改进的元素,大多数教师不会在行为上发生改变。
这就关涉教师的内在改变与外在支持的问题,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政府或者学校在组织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期望从外面提供激化改进的元素,以促进教师不断进步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元素是否能够使教师产生信心和乐于尝试。因为一所学校最终改进的成功与否,“不在有多少‘外援’,而在校内教师的能量增长和学校协作文化的建立”(注:赵志成.怎样学得更好[N].教协报,2002,1-21.)。
三、外在支持的新范式:院校协作
在具体讨论院(大学)与校(中小学)建立伙伴协作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目前各国实施的、主流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即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指令性的教师发展模式,和由大学提供课程、工作坊、研讨会和讲座等形式的发展模式。从中不难发现,在由政府、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组成的决定教师专业发展之优先次序和目标,以及确定资源分配等问题的三角关系中,基本上还是由前两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设定在职教育的议程,教师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上述两种专业发展模式秉持的基本理念,在于分别将教师与学生看作现成知识的传授者和接受者,因此专业发展计划强调对固定答案的追求,采取的发展措施主要在于传递信息、提供观念和训练技能,而忽视了对教学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不断地尝试和实验,以及开展批判性反思和讨论等现代教育改革所主张的信念、知识和实践。另外,大学提供的课程过于学术化,与教师实际的工作情境相去甚远;工作坊和假期讲座的内容虽然跟实际情况密切一些,但在贯彻过程中又通常缺乏跟进和支持,参与的教师既无法保证会否付之实践,就更遑论去影响其他同事,改进整个学校的教学文化了。
总之,这两种模式所持的俱为技术性取向,即将教师的角色定位为“技术操作员”、“传递科层制订之课程的非人性的工具”的层面上。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计划通常是出于补救的目的而进行的,是以摧毁教师的既有信心为开端的,并在所谓“专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求教师接受一套现成的、权威的、“真理式”的知识,使教师固有的实践理论遭到忽视,固有的教学行为和观念受到批判。教师接受这种外接式的专业发展模式,无异于接受被“规训”的过程。
如果这些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在本质上只是“外加式变革”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能让教师从中获得赋权感,那么,我们对教师自觉自愿地改变自己的期望还有实现的途径吗?
在审视各国学校改进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学术界和一些民间团体也在利用自己的专业或经济力量为教育变革推波助澜。这些主要由大学主导的学校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政府主导之变革模式并驾齐驱的局面,它们希望通过“提供专业协助”和发展“校际支持网络”来扩展教育改革的成果。(注:Slavin,R.(1998),Sand,Bricks and Seed:School Change Strategies and Readiness for Change.In A.Hargreaves,A.Lieberman,M.G.Fullan,& D.Hopkins(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Change.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其中影响广泛的如美国的“精英学校联盟”、“跃进学校计划”;加拿大的“教育联盟”;英国的“面向全体儿童的优质学校计划”;中国内地的“新基础教育”研究,香港的“优质学校计划”等。
这些改革计划的共性在于建立了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伙伴协作关系,他们坚信,真正的变革应该基于研究形成的方案,然后通过大学专家与学校(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一起做”,而非“要他们做”,最终达致目标的实现。从一些具体的经验分析可知,成功的院校协作关系体现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共同探究、彼此沟通、平等对话、民主决策、共生共进、取长补短等特征。这种对待教育变革和教师的认知取向显然有别于前面提及的传统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此似乎暗示了在改革情境里面,教师可能面对的不同境遇。
院校协作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它不仅作为改革的手段和方式,而且其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据此将其粗略分为两类:
1.“院校协作”作为推动学校变革与教师发展的一种手段。它仍然以学校及其教师为主要改革对象,突出学校教师和领导在教育实践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从提高人的素质入手,最终使教育质量提升。大学专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在于向教师提供必要的专业帮助。从定一种视角出发,教育改革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强化教学专业的知识基础、鼓励教师对学校决策的参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鼓励教师从事教育探究等。
2.“院校协作”作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它强调机构或组织的变革,即不单关注大学专家与教师之人际间的结合,而且关注大学与中小学这两类不同组织之间的变革,希望通过这种制度性的变革,能为教师改变与学校变革营造一个支援性环境,这是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实现的难度也更大。
无论哪一种观点,从支持教师专业发展、促进教师内在改变的角度来看,都有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师的实践知识,希望在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建立起临床伙伴式,特别是共同学习式之合作研究模式,最终拉近长期形成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距离之深意。
在实践中,大多数院校协作式改革也都将学生的学习作为关注的最终目标,因此能直面课堂,针对具体教学展开工作。或通过大学专家的“建设性批评”,帮助教师自我反思;或采取共同上课的方式,一起体悟与交流,以促成共享的生成性对话,在沟通与交往中,促进教师新知识的建构。
当教师不再被视为知识的纯粹接受者,而是创造者,强调其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与大学专家的对话和互动时,则前面所言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对教师产生的“规训”作用将可能消解。这一点似乎可以通过更多的比较成功的“院校协作”关系提供经验上的佐证。
四、结语
虽然从理论上讲,大学与中小学建立伙伴协作关系,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内在观念的变化,而且相较于目前主流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它们还体现出一种范式的转移。不过其最终的实现并非易事,需要“院”、“校”双方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努力,小心经营,才有可能见到成效。
一些研究提醒人们注意,大学与中小学毕竟属于生产不同文化资本的不同“场域”,它们在协作过程中,会非常自然地在对“意义”之界定上产生分歧和冲突。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就大学与中小学这两个机构来说,大学更为保守,缺少负担,通过协作而发生改变的空间较小。就协作的人员而言,中小学教师倾向于将大学人员视为“专家”,而非讨论、对话的“诤友”;大学人员也似乎习惯于以“专家”自居,对中小学教师的一些意见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这种“有效沟通的缺失”以及传统科层体制的痼疾成为真正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形成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
至于如何建立和发展“院校协作”关系,一些建议指出,大学与中小学双方需要调整各自的角色和责任,超越各种可能的限制,通过开展行动研究、合作探究等不同的变革方案,以切实帮助教师的专业成长,充分发挥并落实其宣扬的理念,而不是限于口号式宣称和形式上的相似。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视角在于强调大学研究者与中小学工作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更,即从传统的诉诸权力(power over)转变为共享权力(power with),相信教师通过权力共享可以释放出更大的潜能,从而有利于学校的改进和学生学习成就的提高。
可见,院校协作作为教育改革和教师改变的一种外在支持方式,其本身的实现并非坦途,而需要吸纳更多的有效教师发展的元素来配合,如方式要植根于或直接与教学工作相关联、内容基于课堂教与学、注重发展教师的专业社群、要考虑组织的具体情境、要强调教师的反思和自身能力、学校管理从集权转向分权等。一句话,只有真正地增强教师的赋权感,使他们对各种教学活动充满信心,那么对教师最终实现其自身及学校文化内在转变的希望才不会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