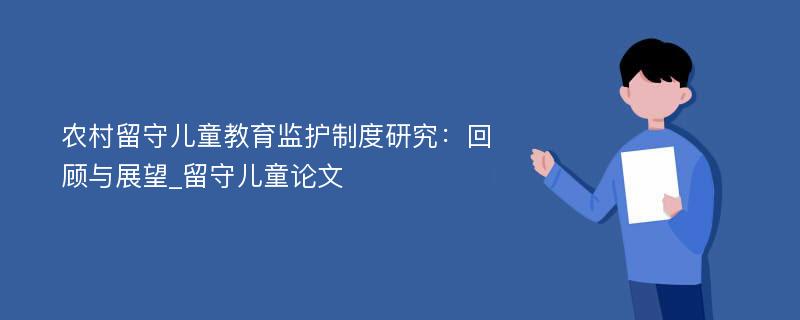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体系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教育论文,体系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统计,有两个口径:一是父母双方都在外打工,留守在家的子女;二是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留守在家的子女。按前一口径统计,目前我国农村有留守儿童大约2200万人;按后一口径统计,目前我国农村有留守儿童大约7000万人①。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严重威胁,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如江苏省妇联主席柏志英所言,“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留守儿童教育也不单纯是家庭问题,其实质是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在农民问题上深层次的反映,如得不到及时关注和解决,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矫正代价。”②
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针对留守儿童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研究也从宏观层面进一步深入到微观层面,有关学者对家长、学校、临时监护人、社区、政府和社会分别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试图指出各有关方面应该如何去做,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时,大家也逐步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决不是单纯哪一方面能够独立解决好的,需要社会各有关方面积极配合,于是,部分学者建议建立农村社区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体系。那么,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监护体系?在教育监护体系中谁能作为主导者整合各方力量等问题都需要回答与解决。为了将有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更好地为留守儿童及其家长和临时监护人提供切合实际的帮助,本文试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留守儿童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的相关研究作一梳理和展望。
二、建立教育监护体系的必要性
目前鲜见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社区教育监护体系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只是在部分学者对留守儿童问题一般性的研究中,我们能够见到作者对社区教育监护体系建设问题的简略论述。具体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而是各抒己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达方法。
一种是从系统论思想出发,主张建立某种综合性的教育体系。李庆丰于2002年最早提出应“建立农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增强和发挥农村社区教育的作用”。③ 之后,“教育和监护体系”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提法。第二种表达方法是从网络视角出发,主张建立某种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网络。林宏在2003年较早提出要“发挥社区综合教育功能,形成社区、学校、家庭立体式的教育管理网络”。④
在阐释关于建立监护体系或网络的必要性方面,研究者在出发点上均认为留守儿童的教育应视为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共同责任,但具体提出的论点又各具特色,归纳起来有下面八种不同的看法。
1.“缺位、补位论”
李庆丰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增多,“旧的家庭成员长期稳定不变的家庭结构已经打破,新的家庭成员经常性缺位的家庭结构已经开始形成,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区)教育就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⑤
庞文认为:“父母一方或者两人都不在身边,看管人对孩子的照顾和管理大都属于粗放型。在单亲家庭,留在家里的母亲或父亲角色缺位,上有老,下有小,农活家务一大堆,常常自己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再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导致‘管理缺位’。”他主张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或社区监护体系”,并由非政府组织(NGO)编织留守孩子服务网络从而加快构建面向留守孩子的更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⑥
2.“潜在危机论”
张捍东针对“农村‘留守孩’思想道德建设的潜在危机”提出有必要“建立和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工作体系”。⑦
3.“系统工程论”
殷世东、朱明山认为:“未成年人的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学校、家庭和社区合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共同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以消除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⑧ 许传新认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教育问题。要解决好如此多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决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想解决就能及时解决好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种力量通力合作,形成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⑨
4.“社区教育组织空白论”
陈子雷、乔卫景认为:“少年儿童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少年儿童的社区教育组织尚为空白,使得农村儿童的教育与成长根本缺乏社群的合力支撑。应当广泛建立农村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⑩ 段宝霞认为:“儿童的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的责任。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很少或没有相关的儿童社区教育组织,使得社区在农村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政府要考虑由乡镇教育办、学校和共青团牵头,联合妇联、工会、村委会和派出所,构建农村社区教育监护体系,从提供心理指导到学业关怀,立体地形成有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11)
5.“缺乏合作与沟通论”
汪志强,袁方成认为,“针对当前家庭、农村社区和学校之间缺乏有机的合作与沟通状况,要切实建立行之有效的家庭、社区和学校联动的运作机制”。同时,他指出“村委会应建立农户邻里管护网,做到每个留守儿童均有人照看,使留守儿童充分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家庭、村委会和学校之间做到各负其责,及时沟通、及时了解,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从制度上形成对留守儿童的最坚强有力的保护网,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12)
6.“条块分割论”
魏晨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提出“重新建立起群体性的情感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他认为:家庭功能的缺失,使得留守儿童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有效的沟通手段,留守儿童面对成长烦恼的时候,无人倾诉、无人帮助。同辈群体、家庭、学校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系内,留守儿童问题也被分割了,没有一个部门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就需要利用好现有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妇联、工会、团委建立专门机构与岗位,以县乡两级机构为基本框架,以学校为载体,设立专门人员,针对这部分群体进行专门的帮扶与沟通工作,重新建立起群体性的情感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13)
7.“综合性社会问题论”
陶菁认为:“由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仅靠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难以解决,需要各级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统一认识,积极配合,协同努力,进一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要“逐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的留守儿童教育管理体系”,“要建立农村社会化的未成年人教育和监护体系”。(14)
8.“家庭职能转移论”和“教师社会责任功能扩展论”
张春玲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职能的弱化给学校带来的结果是,家庭把固有的照管儿童的职能移交到了学校,使学校不仅要承担固有的教育职能,而且还要代替家庭承担附加的‘照管(未成年人)’职能。在现代社会,学校是执行教育的机构,但学校有时也扮演着社会其他机构的角色”。同时作者指出,留守儿童失去的一些基本家庭职能,可以暂时性地移置到学校。“为有效地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与管理,当务之急是建立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监护体系,这是从微观层面对留守儿童予以的具体关怀。”(15) 李星贵认为,“当前农村家庭教育的责任发生了转移,教师社会责任的功能得到扩展。因此,要求学校及教师代表社会担当更多的责任,履行更多的义务,发挥更多的教育功能。教育部门应该针对留守儿童问题,进一步研究和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强化学校对留守儿童的责任和管理,构建学校的监护网络。”(16)
三、关于教育监护体系构成及其主导者的讨论
李庆丰较早从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需求两方面阐释了建立农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监护体系的可能性。他在分析了建立农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监护体系的必要性之后指出,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的可能性和基础,一是因为基层党政机关有大量富余人员,中小学校有大量退休人员,他们中有大批人能胜任中小学生监护、教育和生活料理等工作。二是有部分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经济相对比较富裕,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建立某种机构,来管理和监护其子女,使他们能安心在外务工。(17) 遗憾的是,理论界在此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新的进展。其他研究者要么是对于建立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的可能性和基础避而不谈,要么是重复李庆丰的研究结论。而这个问题正是推动社区教育监护体系或网络的难点所在,也是目前学术界提出的有关建议缺乏可操作性的主要原因所在。在留守儿童社区教育监护体系或网络构成及其主导者的问题上,研究者见仁见智,归纳起来有以下六种不同的主张。
1.主张由基层学区、学校和共青团牵头
李庆丰提出,“在农村建立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以由基层学区、学校和共青团三家牵头,联合妇联、工会、村委会和派出所,共同构建农村中小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这必将对留守子女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全面提升农村教育教学质量。”(18) 吴霓提出“建立以农村社区教育为龙头的农村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教育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由农村基层学区、学校和共青团牵头,联合妇联、工会、村委会和派出所构建的农村中小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不仅能将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项具体的重要工作来抓,而且还能起到对农村社会教育进行有力推进的重要作用”。(19)
吴霓提出,建立农村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以考虑由基层学区和共青团牵头,联合妇联、工会、村委员、学校,共同构建农村少年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这些社区机构可由离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等人员构成”。(20) 之后,袁江鸿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及教育对策》一文中也基本上持该观点。(21)
2.主张以学校为中心
冯建、罗海燕提出建立“以学校为核心,社区、村组、临时监护人为辅的教育管理网络”,并进一步指出,“学校教育应成为影响‘留守儿童’成长的主渠道,这就要求,学校教育不仅要完成校内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而且要求学校教育应有意识地向‘留守儿童’的校外生活延伸,以弥补‘留守儿童’在校外的生活真空。”(22)
张捍东针对“农村‘留守孩’思想道德建设的潜在危机”提出“建立和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工作体系”。(23) 王旭光主张,“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体系。对‘留守学生’的教育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配合,但学校教育应起主导作用”。(24) 李正平、王朝勋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力量监管‘留守学生’的力度不大,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只是个别社区在搞试点,因资金、场地等原因,倡导社会监管‘留守学生’,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对‘留守学生’监管的重任就落在了学校、家庭之间,而学校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又起主导作用,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在这不完善的‘留守学生’监护网中起核心作用。”(25)
3.主张由各类非政府组织编织服务网络
庞文提出,“各类非政府组织应该一如既往地关心农村孩子的成长,除了捐助钱财物品、建设希望学校之外,还应在有利于孩子心理成熟、道德健康发展的新型工作方式方面拓展自己的实践空间,从而使各类非政府组织(NGO)有效地充当起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对‘留守孩’服务网络的编织者、促进者的角色,从而加快构建面向‘留守孩’更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26)
4.主张由党委、政府出面建设教育和监护体系或社会支持网络
田景正指出,“成立关心‘留守儿童’教育指导机构,建立农村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由乡镇政府牵头,学校组织,村民委员会、派出所及热心的退休教师等参加。”(27) 许旭提出,“逐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的留守子女教育管理体系”。(28)
尹永红提出,由“政府承担责任,建立‘留守孩子’的教育和监护体系”,“解决‘留守孩子’的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多部门的协作,国家和政府有责任、义务尽快建立其教育和监护体系。”(29) 魏晨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提出各级政府应出面协调“重新建立起群体性的情感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并进一步指出,“在未来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学习欧洲、美国以及我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先进经验,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向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来购买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服务,政府撤出机构,只进行服务监督。”(30)
陶菁也提出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教育、文体、广播、司法等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的留守儿童教育管理体系。(31) 张晓艳则提出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仅仅在建立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中发挥作用,在关心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同时,还要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家长进行引导和教育,在加大发展当地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为留守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发挥作用。(32)
5.主张由村委会建立农户邻里管护网或教育监护体系
汪志强、袁方成提出,“村委会应建立农户邻里管护网,做到每个留守儿童均有人照看,使留守儿童充分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家庭、村委会和学校之间做到各负其责,及时沟通、及时了解,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从制度上形成对留守儿童的最坚强有力的保护网,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33) 陈丽丽、甘美好也提出,“可由村委会牵头,联合妇联、工会、学校和派出所,充分利用党政机关富余人员、中小学退休教师以及青年志愿者,共同构建一个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以便于全面、动态地把握留守儿童的情况。”(34)
6.主张由基层教育部门牵头建立教育和监护体系
西华大学课题组主张“由基层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相关群众性组织,共同构建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化教育和监护体系,起到沟通家庭、学校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35) 吴凤丽也建议教育部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一步研究和出台相应的政策和规定,强化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的责任和管理,构建学校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网。(36)
四、评论与展望
1.对已有研究的评论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留守儿童的论文颇为丰富,在推进农村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建设方面,有两个方面研究进展较大:一是在建立社区教育管理体系(网络)的必要性上,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比较丰富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共识,即:留守儿童的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各方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二是列举了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的牵头者、主导者及参与者,对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从现有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对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建设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表层来看,有关论点被淹没在对留守儿童问题的一般性研究之中,以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为题的专题性研究少之又少,整个研究还停留在初步设想的阶段。
第二,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还不具备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双亲外出或单亲外出;寄宿制或非寄宿制;隔代监护与非隔代监护)的教育监护研究不足。同时,作为对策研究,对各地不同类型好的工作经验缺乏总结,对不同对策思路的效果如何也缺乏验证和衡量标准。
第三,从深层次来看,理论准备不足。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伴随农民工群体的出现而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因而农民工群体也将会长期存在,这就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长期性。家庭历来是儿童接受教育、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获得情感满足和亲子之情的场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的某些传统功能因为被其他组织形式取代而发生了部分转移。就儿童教育和照管的功能而言,随着核心家庭和双职工家庭的普遍化,许多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诸如托儿所、幼儿园、各级各类学校所取代。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结构转型衍生的问题,试图通过建设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变迁使得家庭的某些教育照顾儿童的职能向其他组织形式发生进一步的转移。其转移的机制是什么?能否顺利转移?需要怎样的社会建构?历史上的类似转移是如何实现的?有何规律性?这些疑问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回答。
2.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我们认为,从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建设操作层面上看,研究工作应在以下五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建设农村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的动力来自何处,这一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第二,农村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是否是一种组织形式,如果是,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以及它应遵循什么原则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解决或回答。
第三,需要思考由谁以及用何种手段和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启动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作为一个体系或作为一个网络,其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其成员靠什么来黏合?当家庭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为留守儿童或临时监护人提供帮助、支持或者直接为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和服务时,是否需要或存在互惠及社会交换关系?换句话说,如何分摊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第四,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中的各种群体、组织和个人各自应做些什么?职责如何划分?如何做?研究者们经常在研究中提到“教育”、“监护”、“呵护”、“监管”、“看管”、“关爱”、“服务”、“支持”等内容,那么,在哪些方面应直接帮助留守儿童,又在哪些方面帮助和支持家长和临时监护人从而使他们能有条件履行自己职责和义务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
第五,造成留守儿童成长潜在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父母的不在场或“缺位”,人们很自然地考虑到靠社区教育监护体系(网络)实现“补位”,那么家庭的情感功能、亲情抚慰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由其他形式取代这个关键问题也不可忽略。
注释:
① 谷生华,严敏.“代理家长”、“留守儿童”与“还原家庭教育”——重庆市南川区关爱留守儿童的理念与实践[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4):117.
② 柏志英.多措并举真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J].中国妇运,2006,(8):24.
③⑤(17)(18) 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02,(9):28.
④ 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34.
⑥(26) 庞文.关爱农村“留守孩”[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10):19.
⑦(23) 张捍东.试析农村“留守孩”思想道德建设的潜在危机及对策——以于都县农村“留守孩”现象调查为例[J].企业家天地,2005,(8):119.
⑧ 殷世东,朱明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皖北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6,(2):16.
⑨ 许传新.“留守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7,(9):90.
⑩ 陈子雷,乔卫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与对策[J].甘肃农业,2005,(12):70.
(11) 段宝霞.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管理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39.
(12)(33) 汪志强,袁方成.打工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与对策建议——来自湖北英山的报告[J].宁波党校学报,2006,(1):91.
(13)(30) 魏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J].社会工作(学术版),2006,(11)下:27-30.
(14)(31) 陶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对“两免一补”政策效应的调查与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7,(7):256.
(15) 张春玲.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关怀[J].教育评论,2005,(2):38-40.
(16) 李星贵.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探析[J].农村经济,2007,(8):122.
(19) 吴霓.关注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J].教育科学研究,2006,(2):16.
(20) 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2004,(10):18.
(21) 袁江鸿.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及教育对策[J].政策探索,2006,(6):51.
(22) 冯建,罗海燕.“留守儿童”教育的再思考[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4):41.
(24) 王旭光.“留守学生”的心理障碍及疏导[J].校长参考,2006,(5):40.
(25) 李正平,王朝勋.班主任在留守儿童监护网中作什么[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10):76.
(27) 田景正.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6,(5):15.
(28) 许旭.关注“三农”,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1):39.
(29) 尹永红.农村“留守孩子”教育问题的忧与思[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4):62.
(32) 张晓艳.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及应对策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0):109.
(34) 陈丽丽,甘美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J].理论观察,2007,(4):132.
(35) 西华大学课题组.关于郸县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6,(3):84.
(36) 吴凤丽.完善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机制的法律探讨[J].乡镇经济,2007,(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