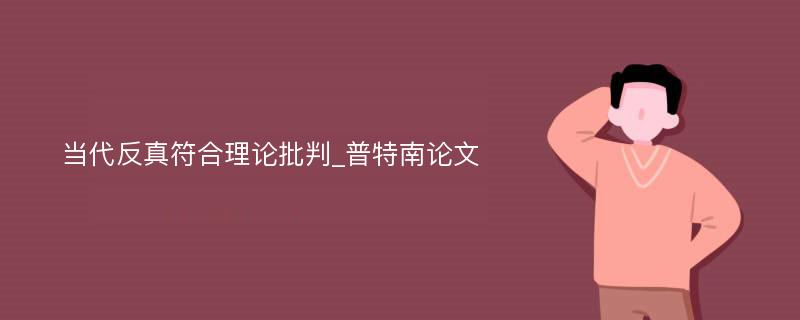
当代反真理符合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哲学研究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真理符合论就逐渐成为受到西方学术界批判最多的一种理论,尤其是自后现代思潮出现以后,对真理符合论的否决与批判,几乎成为西方各种学术流派的一种时尚。但是,通过深入研究与反思,我们认为,真理符合论并没有被真正驳倒,当代反真理符合论提出的各种责难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推出它不成立的结论。实际上,真理符合论只要作出适当的修正,就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一
所谓当代反真理符合论,是相对以往的反真理符合论而言的,在本文中主要是指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对真理符合论进行语言学消解和批判的一种理论思潮。受后期维持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以美国的普特南(H.Putnam)、罗蒂(R.Rorty)、戴维森(D.Davison)和法国的德里达(J.Derrida)及澳大利亚的埃利斯(B.Ellise )等为代表的反真理符合论者走上了一条语言消解和文本解构的道路,与传统的反真理符合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该理论不仅仅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拥有,也为一些非后现代思想家所支持,故本文称之为“当代反真理符合论”。从总体上看,它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对真理符合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批判:
首先,它从语言学角度否认了理论及命题与对象、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否认人类认识的客观性,具有典型的反实在论特征。
受哲学研究“语言学转向”影响,当代反真理符合论通常都把真理符合论表述为强调语言符号与外在对象具有严格的指称关系、对应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论主张,然后通过强调语义的内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否认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具有语义的单义性和指称性,进而否认语言符号表征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以德里达最为突出。
德里达认为,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符号的意义既然只能通过它与别的符号的区别来确定,那么,在语言符号的能指及其关系之外就不存在所指,或者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系统内部是不可区分的。事实上,为了确定一个能指的意义(所指),我们只能举出与这一能指有关的若干其它能指,而它们的所指又牵涉到更多的能指,这一过程是无限的,我们决不可能达到一个本身不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由此出发,他与拉康、福柯等都人都主张,“命题与实在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所指是被指示的,能指是占支配地位的,因此,命题与实在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确定关系。人们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语言的意义是通过大家的约定与共同的使用来支持,而非通过必然性来支持的”(转引自郑祥福等:《认识论死了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5期第11页)。 德里达甚至由此走上了语言学唯心主义的道路,公然宣称:“文本就是一切,此外无物存在”(J.Derrida, Of Grammatology.trans. G.C.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76.p.158),从语义学角度否认了客观真理存在的可能性,受到学术界的批判。
其次,它从反基础主义角度否决了真理符合论的认识论前提和科学基础。
罗蒂指出,真理符合论奠基于传统哲学“心灵是自然之镜”这个隐喻,以为心灵是一面镜子,可以精确地反映外在世界。可是按照当代哲学的研究,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观察,任何观察都要负荷着一定的理论,都包含着一定的理解活动,而理解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解释者偏见的影响,因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可靠的知识基础,心灵也不是自然之镜。况且“事实上,只要你停留在表象的思想方式上,你就仍然受着怀疑主义的威胁,因为一个人无法回答是否知道我们的表象符合不符合实在这一问题,除非他诉诸于康德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罗蒂谈当代西方哲学”,周晓亮译,载《哲学动态》,1990年第8期,第31页)。
在科学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罗蒂等人指出,科学并不拥有认识真理的特权,它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并不表明它比别的学科更加客观。因为在内容上,科学同其它的学科一样,也是在用隐喻表达自己的看法,理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实在。
第三,它从反本质主义角度否认人类认识真理的可能性。
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家族类似”(family resemblance)理论的影响,一些当代反真理符合论者否认事物存在所谓的本质。他们认为不仅语言体系只具有“家族类似”特征,缺乏固定的本质,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客观世界也缺乏固定的本质,其构成要素与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也只具有家族的类似性,否则说人不断地超越自我就不妥了。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事物有所谓的本质,在理论上也难以确认,因为从静止的角度说,事物的存在有很多层次、有很多方面;从动态角度说,事物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在理论上难以确认何为事物的本质。况且一旦承认把握事物的本质,就不利于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出发,他们坚决否认有所谓本质的存在,并进而否认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参阅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第四,它从社会学角度否认了真理符合论存在的合法性。
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真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人们去寻找并发现的东西,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甚至为了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利奥塔断言,并非所谓的真理性,而是权力的大小和强弱,即论证的力量,决定了话语是否真理,真理意志暴露出它是权力意志的一个特别狡猾的变种。由此他们断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所寻找的意义,所发现的真理,都不过是思维着的精神创造出来的神话”(参阅曼·弗兰克:《正在到来的上帝》,载《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1页)。
此外,他们认为,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一切知识都面临着信息化、商品化的问题,“知识的本性在这个普遍信息化的背景中不能不发生改变。仅当知识被译成大量信息时,知识才是适应于新的通道、成为可操作的。我们可以预言,在此意义上,任何不可转译成信息的知识构成体都将被唾弃,新的方向将为那些最终能转译成计算机语言的研究所领导”(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Knowled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4)。由此出发,他们否认了真理符合论存在的合法性。
第五,它从人类学的角度否认真理的一元性、绝对性,主张真理的多元性与相对性。
普特南指出,真理符合论的根本缺陷并不是尚未找出语言和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在于尚未找出那个唯一真的描述世界的理论,而是不晓得根本不存在唯一真实的对象关系和唯一真的描述理论,在理论上,它预设了一个神目真理观,抹煞了人类的认识发展和现实生活的作用。按照他的看法,语言记号必须在使用者的概念构架内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对象’不可能不依赖于概念构架而存在。当我们引入不同的描述构架时,我们就把世界分割成一些对象。既然对象和记号对于描述构架来说是内部的,我们就可以说出什么对象匹配什么记号”(H.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杨萃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从这种具有人类学性质的内在实在论立场出发,一些当代反真理符合论者主张真理具有多元性、相对性,认为“一切围绕一个太阳旋转的古老模式已不再有效,即使是真理、正义、人性和理性也是多元的”(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后现代主义》,第97页)。
既然如此,真理是否还存在呢?对此,当代反真理符合论作出了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解释。
以兰姆赛(F.P.Ramesy)、戴维森和斯特劳森(P.F.Strawson)为代表的真理否定论者认为,真理问题是一个伪哲学问题,是由于语言混乱而引起的。因为在日常语言中,“真的”与“假的”这两个语词只是起到强调或增添文采的作用,没有起到任何说明的用途。当我们在使用“真的”一词时,“我们是在肯定、赞同、承认、同意某个人说的话”,相当于“Ditto”(同意、同上、同前)。这是一种行动, 而不是在作出另一个陈述,说前一个陈述具有是真的这种属性。(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05页)由此出发, 他们对真理分别作出了冗余论和行动论的解释。
以库恩、普特南和罗蒂等为代表的真理肯定论者在肯定真理存在的同时,又对真理作了反符合论的解释。库恩认为,真理实际上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与工具,是科学家集团所使用的用以解除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工具只有好坏之分,无真假之分。以普特南、罗蒂和埃利斯为代表的具有人类学特征的真理融贯论者认为,所谓真理就是“某种(理想化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是我们的信念之间的以及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H.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62页),它是“认识上最应相信的东西”,并不表示信念与实在之间具有对应性,我们如何使用“真的”一词,是由我们种族现有的信念决定的(参阅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序第1—13页); 它是一种为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知识增长而协调人们的信念评估行为一种手段(See B. Ellis, Truthand objectivity,Basil Blackwell.1990.pp.2—15),真理的客观性就在于主体间的协同性。以达梅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则认为,我们说一个理论或陈述为真,是不能脱离其为真的证据或我们判别这些证据的能力而言的,“对于任何种类的陈述,理解其意义的最恰当方式就是对其作出证实,这个概念应该取代真这个概念”(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第300页)。?
如此说来,真理符合论是否就不成立了呢?下面,我们就来认真考察。
首先,就其核心思想来说,真理符合论主要是要求思想、命题或理论应与其所阐述的对象应具有相同的结构,或者说在构成要素上要与对象的要素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这是它们具有真理性的首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对于这一点,人们无论在逻辑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是难以反驳和违背的,因为它与人们的以下直觉是一致的:即判断一个论断的真假,就是看它的内容和所论断的事情是否一致。否则,真理就无法与想象和谬误相区别。
其次,从他们的批判中,我们并不能直接推论出真理符合论不成立的结论。
(1)就德里达等人从语义学角度的批判来说,如上所述,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语义的内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而这至多只能证明语言系统与外在对象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而不能证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我们就无法理解德里达等人自己的命题与思想,他们的命题与思想也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在这方面,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 )对谓词与共相关系的研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佐证。根据他的研究,谓词与共相的关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多多对应关系,有时甚至存在不对应现象,如空集谓词(See D.M.Armstrong,Nominelism and Re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56—64 )。他所分析的尽管只是谓词与共相的关系, 但因任何陈述句都可以被转化为具有某种谓词的语句,所以,他的分析可适用于任何语句及理论与实在的关系。由此可见,命题、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容否认的,传统理论存在的问题不是因为它肯定了二者之间有对应关系的问题,而是因为它忽视了其间的复杂性问题。德里达等人在此问题上犯了从一个极端挑到另外一个极端的错误。
(2)就其从反基础主义角度所作出的批判来说, 罗蒂的思想也只能证明,心对有关对象的知觉与反映,要受到主体的成见、欲望和过去的知识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它除了反映对象的有关特征以外,还要反映主体的有关心理特征,因此,“心并非只是自然之镜”,并没有证明“心非自然之镜”,并不能就因此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此外,罗蒂等人用隐喻论来说明其反科学中心主义思想,以反对对科学文化的迷信,这是合理的,但这只能证明科学理论与自然实在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只能证明科学并不拥有掌握真理的特权,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理论与自然实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3)他们从反本质主义、 社会学和神目观角度对真理符合论的否决也是难以成立的。就其反本质主义理论来说,从唯物辩证论的角度看,他们的问题在于夸大了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和持续性,而忽视了其相对性与条件性。此外,他们强调事物存在结构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只能说明辨别事物本质的复杂性,并不能由此而否认其存在。
就其从社会学角度所作出的批判来说,他们至多只是证明了真理标准的认可具有时代性与技术性特征,要受到政治权力、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真理符合论。就普特南从神目观角度作出的批判来说,它至多只是证明了传统符合真理论面临着检验问题上的困难,只能证明神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真理观对人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真理观才是可能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符合真理论。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们对神目观的批判,只是否认了人类对“大写真理”进行认识和检验的可能性,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大写真理”存在的可能性。
最后,他们提出的真理观也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如前所述,当代反真理符合论者在真理观上主要有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看法。对于前文提到的真理冗余论和行动论这两种真理否定论,因我国学者徐友渔先生已在有关著作中作了批判(参阅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第305—306页),本文不再重复,这里只着重谈谈对真理肯定论的看法。
至于真理肯定论,前文曾提到主要有库恩的实用主义真理论、普特南等人的真理融贯论和达梅特的反实在论真理观。从表面上看,这三种理论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把真理等同于理论的可接受性。它们分别把理论的真理性等同于理论的实用性、理论的一贯性和协调性与理论的可证实性,可是,后者只是理论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只是人类在理性上接受某种理论的三个条件,正如普特南本人所指出的,理性上的接受性和真理之间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关系,“一个陈述可以是理性上可接受的,同时又不是真的”。普特南已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解决,只能保留在他的“直觉”中。(参阅H.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原序第2 页)从逻辑学的角度说,这些理论共同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把理论成为真理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混为一谈,因为具有实用性、融贯性、可证实性的理论未必就是真理,它只是一个理论成为真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与对象的符合才是其充分条件,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三
不过,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当代反真理符合论毫无合理性可言,也不意味着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实际上,当代反真理符合论的问题不在于它对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进行了批判,而在于它没有对其陷入困境的根源进行恰当分析,没有把握其适用的边界条件,以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首先,我们看看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存在的问题。根据上述当代反真理符合论的批判可以看出,它主要存在下述问题:
第一,在真理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上,它把真理性的客观认识等同于康德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客观认识,忽视了认识主体在认识系统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经验论者为了追求真理性的客观认识,把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把主观等同于虚构,把客观等同于真理,等同于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客体的本来面貌,忽视了认识系统中的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识是不可能脱离主观而存在的。实际上,正如当代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所揭示的,“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的和不断的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并且这些结构还通过把它们结合到更大的范围之中(即使仅仅把它们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而使它们丰富起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页)。换句话说,认识系统中的主体与客体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它们在认识系统中的存在是一种建构的产物,与其在非认识系统中的存在不能完全等同。由此类推,主观与主体因心理上的成见、需求及价值观等因素而在观念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客体的想当然的虚构或投射物之间也是不可划等号的。
大致来说,客观认识应当等同于客体在以人类为主体的认识系统中呈现出的本来面貌,与单个主体因个人的观念或成见而自觉地或不自觉投射物截然不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客观认识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准确把握,就是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
第二,在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整体性与多维性关系问题上,它过于强调前者、否认后者,以前者来否定后者,忽视了人类认识的条件性与多维性,把二者不恰当地对立起来。事物的存在既有整体性,也有多维性,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性与条件性,因此,不可把它们对立起来。
第三,在真理与实在的对应问题上,它把“对应”关系等同于语言学上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忽视了语言与对象之间的复杂的多元对应关系。此外,受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它把真理性认识等同于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认识,等同于对纯粹的物理实在的客观把握,把认识系统中的客体等同于纯粹的、现实的物理实在,忽视了心理客体、观念客体的实在性,忽视了可能世界意义上的客体与理论实在的对应性(See:D.M.Armstrong,A Combinatorial theory ofPossi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50—57), 以致遭到当代反真理符合论的有力反驳与批判。
第四,在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它把认识论上的“真”与伦理学上的“善”及美学意义上的“美”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真与善、美之间的关联性以致陷入重重困境。
与传统的真理符合论相反,当代反真理符合论强调的是真理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多维性与条件性特征,它正确地认识到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特征、主观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历史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要受到主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它又忽视了真理的整体性、绝对性和客观性。究其根源,在于它没有区分不同的真理概念及真理概念的不同内含,没有把我们应当相信的真理与我们由于各种原因而信奉的真理、与我们用以识别真理的手段区别开来,没有把理论成为真理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以至以认识的人类学特征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否认宇宙学意义上的一元真理论对人类的意义。实际上,认识的人类学特征、主体性特征并不意味着宇宙学意义上的一元真理论就不存在,只是意味着它是人类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目标;也不意味着它对人类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人类认识追求和发展的方向。从人类文化发展史和儿童心理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的认识始终是朝着突破自我中心主义而向前发展的。所以说,当代反真理符合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以人类学意义上的真理多元论否决了宇宙学意义上的真理一元论存在的可能性与意义,具有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实际上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由此可见,当代反真理符合论并没有达到其企图从理论上彻底否决真理符合论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达到目的。我们只要对传统的真理概念作出适当的修正,真理符合论就可以应付当代所面临的各种责难与批判,摆脱目前的困境。
标签:普特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