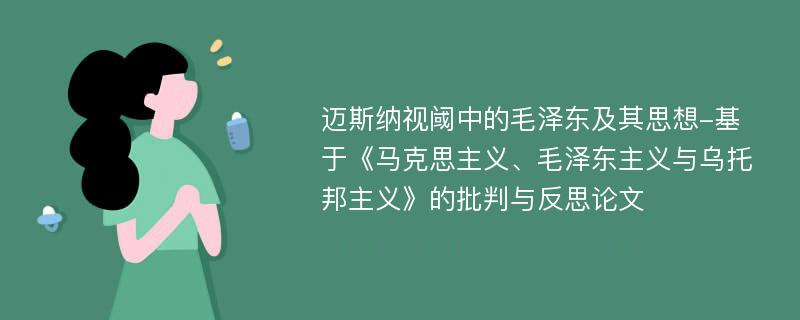
迈斯纳视阈中的毛泽东及其思想
——基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罗 馨
摘 要: 在美国学者莫里斯· 迈斯纳的理论视域中, 毛泽东充分保持了对以追求未知世界为特征的“ 乌托邦主义” 的冲动, 同时在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时将马克思主义与“ 民粹主义” 有机结合,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毛泽东主义”。 但实质上毛泽东并非是民粹主义者, 也并非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中具体化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者。 迈斯纳的这一内部取向也为当下透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反思: 切忌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代替毛泽东思想总体; 还原到毛泽东时代场域的原初语境; 注意区分开发展马克思主义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关 键 词: 毛泽东; 莫里斯· 迈斯纳; 乌托邦主义; 民粹主义; 马克思主义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① 莫里斯· 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1931-2012) 是国际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 曾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著有《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1982)、《 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7) 等。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2)一书中,以“一种‘构建悖论’的方式,将两个完全对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联系起来,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认识困境的道路”② 侯且岸:《 当代美国的“ 显学”—— 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77-178页。 ,并探讨了毛泽东晚年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的关系。由于深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该观点有其失当之处。鉴于此,有必要对迈斯纳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若干观点进行批判与辨析,由此则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并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提供方法论反思。
一 问题缘起:莫里斯·迈斯纳的基本观点回顾
莫里斯·迈斯纳从独特的政治科学理论视角出发,用自己的乌托邦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对中国问题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系统分析。
(一)发展战略:现代化道路中的民粹主义倾向
追根溯源,民粹主义(Populism)产生于19世纪后期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它的一大鲜明特征即厌恶现代资本主义、留恋乡村田园生活① [ 英] 以赛亚· 伯林:《 俄国思想家》,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第249页。 。而迈斯纳鲜明地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民粹主义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具体而言:其一,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将农民视为革命创造力的根本来源。而这一特性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尤其明显。在这一重要文献中,农民已然被提升至革命评价主体的高度上来。其二,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在处理城乡关系中重农村而轻城市。长期以来,在俄国民粹派的视角中,“城市落后,农村(村社)(mir)先进”是一种应然逻辑。与此类似的是,毛泽东也表现出对乡村发展和农民潜力的高度重视,反之却对城市生活持高度警惕态度。其三,迈斯纳认为,毛泽东表现出对精英主义、官僚主义的拒斥。而这种特质在“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格外强烈。即在此过程中,他试图焕发起广大弱势群众身上的强烈斗争意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城市精英主义、打碎现有的官僚组织体系。
(二)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中的苦行主义与唯意志主义倾向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品质与党性修养的经典教材,描绘出一幅勤劳、简朴、忠诚、为民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精神图谱。其中凝结的精神追求可被归纳为苦行主义价值观。而这也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反对作为城市资产阶级生活之特征的奢侈豪华,称颂艰苦朴素的美德”② [ 美] 莫里斯· 迈斯纳著:《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35-36页。 是相类似的。与此同时,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特别注重斗争、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禁欲主义价值观的内化,并由此判定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信念“并不是基于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而是基于相信他们能够焕发出目前潜在的强大的主观力量之上的”③ [ 美] 莫里斯· 迈斯纳:《 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第266页。 。
(三)未来目标: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定位的乌托邦与非理想化倾向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中,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历史科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可能性尺度。其终极目标内容指向“自由的王国”(Reich der Freiheit),在此过程中人类以指向未来的个人意志为前提,自由地激活自己的人性潜能,最终达到主体的自我实现。但在迈斯纳看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未来乌托邦设想的静止和单调无味,“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主义阻止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并且避开了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缓和化’过程”④ See Robert C.Tucker,The Deradicalization of Marxist Movements, in Tucker,Marxism Revolutionary Idea, p.172-214.,它创造出一种“具体而运动的乌托邦”,并激发出人对未来的美好期冀且产生一种不断向最终目标逼近的无限动力。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三大差别”,毛泽东选择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构高尚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非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对未来高度乐观的表现。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三大差别”,毛泽东选择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构高尚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非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对未来高度乐观的表现。
世家大族的非凡历史让沈从文不甘人下,激励着沈从文奋勇向前,探寻出路。1922年夏天,沈从文来到北京,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了报纸的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他的理想是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中国重新树立真善美的观念。孜孜以求的沈从文在文学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历尽磨折,最后在自我奋斗上总算开辟出了一条道路。沈从文对自己要求严谨,对后代也深寄厚望,他给长子取名龙朱,次子取名虎雏,一龙一虎,心意毕现。可以说,沈从文对家族的追根溯源与人生理想追求等,正是中国宗法制所规范的敬爱祭念、荣亲留后精神内核的具体表现。
二 “二重辨析”:迈斯纳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若干观点辨析
第一,毛泽东盲目崇拜农民,有“以民为粹”之倾向。但实质上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一个农民革命者。虽然马克思曾对农民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巨大革命潜力予以肯定,但总体上认为农民缺乏领导政治斗争的能力与视阙,强调“他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引者注)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①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82-283页。 。而毛泽东沿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坚持工人阶级对农民及整个革命的领导权的同时,也注重教育和改造农民以摆脱其固有局限性。再者,1927年以后,因为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使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道路与城市斗争被强制性分离,即“除了上井冈山没有其他的选择”② Schram, ed,Mao's Road to Power: Volume VII, 153.。因而毛泽东对于农民的依靠更多是历史环境所迫和客观因素使然。这一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主体概念的实践具象,贴合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实际,而并不是“以民为粹”的逻辑表征。
(一)毛泽东的思想是不是乌托邦主义
考虑跨区联络线交易计划的多区域互联系统分散调度方法//曾方迪,李更丰,别朝红,程海花,郑亚先,耿建//(16):32
同样,毛泽东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框架下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但由于被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局限,使其社会主义蓝图中“染上空想性”,但亦不可将其简单化约成乌托邦主义。实质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运动的产物,其理论内在矛盾的呈现与整合过程,反而总体上反映出一种对空想因素的“动态超越”。诚如马克思将生产力发展确立为历史前提,以生产方式的革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以科学的唯物逻辑取代抽象的思辨逻辑。而毛泽东也始终赞同经济力量的第一性,同时承认上层建筑在“历史的特定情况”下对社会变革有影响作用,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毛泽东总体性思想线索是唯物主义的,不曾偏移。
而迈斯纳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毛泽东主义在现实的革命与斗争中把对乌托邦的追求从“远景”变成“近景”,同时认可它有效抵制了官僚主义程式化及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新型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乌托邦主义”,彰显出人对生活“意义”和社会“秩序”的追寻。可见,他对“毛主义”中的“民粹性”和乌托邦目标的分析,重点不是“给‘现象’定性,而是显示其中的‘意义’”③ 萧延中:《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类型、 概念与意义》,《 教学与研究》 2003年第12期。 。但另一面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否认或忽视社会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过于依靠主观意志,是乌托邦思想的特定呈现,这一观点无疑是先入为主式的主观臆断,片面地将毛泽东看作是一位空想(农村共产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唯物的(脱离客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迈斯纳选取“乌托邦”和“民粹主义”作为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的特殊切入点,勾画出一幅独特的“异域理论图景”。但如前所述,这一分析概念和研究范式存在明显问题,其中凸显的若干理论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方法论反思。
(二)毛泽东的思想是不是民粹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内国外新形势的产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也开始向“一定的发展”以及“限制、利用”转变。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① 《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77页。 。1955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瓦解”的任务,继而催生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在合作化高潮推动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发展。可以想见,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对具体实际、基本国情、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能动性反映。而这显然与俄国民粹主义者基于抽象人性论而一味拒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主张“回到村社(mir)”呈现出天壤之别。
“迈斯纳在毛泽东的平民主义倾向与乌托邦冲动之间,建立起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将这两种思想列为毛泽东一生知与行的支配逻辑和‘总意识’”① 邱国兵:《 美国“ 毛主义研究” 理论范式的分殊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8期。 。而通过对迈斯纳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若干观点辨析,则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思想与当代中国提供教训与反思。
乌托邦作为一种超历史的范型,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弊病进行道德判断的准则。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乌托邦意识以潜藏在目前存在着的东西中的可能性为基准,去预想未来的人类现实”,“对状况的严密分析和预见未来的意识,一起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② [ 德] A·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136页。 。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一个理想构思是依托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现实性革命实践,以及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被赋予了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内在逻辑张力。
第二,毛泽东囿于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界限,以致跨越生产力而试图人为消灭资本主义,造成了重大失误。而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早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一方面正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历史进步性,另一面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透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其内在痼疾进行透彻而全面的批判。而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则呈现出一个渐变式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轨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深刻总结陈独秀右倾错误(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做一步走)③ 两 者错误倾向从本质上看都是在认识与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出现偏误。 的基础之上,明确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④ 《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83-684页。 。并且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也深入阐发了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长期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的广大发展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⑤ 《 毛泽东文集》 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22-323页。 即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应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同时注意团结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间阶层。这期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建党之初对资本主义的完全否定,到40年代的基本肯定乃至主张“广大的发展”的嬗变。
关于毛泽东是否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这一问题,始终是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式”。国外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施拉姆、伊萨克·多伊切等和国内代表学者李泽厚、朱学勤、胡绳等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而迈斯纳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其立论主要围绕两大关键点展开:
为了拓展活动空间,我们对幼儿园的环境、班级楼层设置进行了反复的调整,例如:加盖二楼和三楼露台的风雨棚、拆除大操场的舞台、移动大型玩具的位置、构建共享区等等,都是为了让孩子有较大的活动场地。同时我们注重每一个小角落的利用,在绿色长廊下面和操场、教室的四周、楼梯间,都有为方便孩子活动而投放的器材,即使在槐苑的树下都埋有梅花桩。
具体方法是将原料用调味品,如:盐、酱油、料酒、糖等调拌均匀,浸渍一下,或者再加上鸡蛋、淀粉浆一浆,使原料初步入味,然后再进行加热烹调。
三 “三重反思”:关于当下毛泽东研究的反问与再思考
(1)混凝土配合比选用不合理。按照规范要求,双块式轨枕脱模强度应不低于40 MPa,这就要求轨枕具有较高的早期强度。为节约成本,广宁轨枕预制场在轨枕C60配合比设计中采用了双掺(掺加粉煤灰和复合掺合料),试验证明混凝土中掺加粉煤灰有利于提高混凝土和易性和耐久性,但不利于其早期强度的增长,轨枕脱模时易出现挡肩裂纹。
(一)切忌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代替毛泽东思想总体
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曾指出,毛泽东不仅是理解中国过去的窗口,而且更是理解中国现在与未来的中介④ 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 Lexington Books, 2007, p.5.。因此,就历史铺展与现实呼应的双层维度而言,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绝非是纯粹的理论评析与历史评析,而是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与政治导向性的重大议题。但在迈斯纳的观点中,他却把我国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都作了肯定处理,并判定毛泽东的思想是一种“无限制的乌托邦主义”。诸如此类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它缺乏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整体历史性考察,并用晚年毛泽东的错误统摄其终生的理论与实践,这无形中扭曲了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实践的基本属性,也未能够对毛泽东晚年实践做出具体历史性的透视。此外,迈斯纳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理解也趋于片面性,侧重于毛泽东晚年错误(集中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探究以期管窥毛泽东的思想全貌,因而有以偏概全之嫌,这显然是一种以支流取代主流的反科学式推断法。
而在1958年以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不发达情况下,经济基础尚未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毛泽东却提出阶级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主张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这不能推定毛泽东就是民粹主义者。因为从毛泽东的思想的整体性线索来看,仅凭毛泽东晚年对阶级形势的误判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主旋律”是民粹主义是片面而武断的;再者,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根本缘由实质上在于“打破了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交互作用的张力格局,以理想目标的导向性取代现实的基础性”② 尚庆飞:《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科学统一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与未来走向》,《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等因素“多元决定”的结果。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体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切忌简单化、片面性,必须注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③ 许全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1页。 。因而局限在民粹主义框架中来界定毛泽东晚年失误无疑是不对的。
而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基于中国国情、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并在实践中得以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存在着曲折与失误,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始终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须臾不可偏废。对于今后的毛泽东研究,应当立足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应当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趋向理解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同时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来透视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而不可因为局部错误而抹杀毛泽东整体思想体系的科学性。换言之,“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功绩已经被历史所证实,这是任何人都无从抹杀的历史性存在,承认毛泽东‘成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是毛泽东研究科学推进所必须要牢牢坚持的政治与学术底线”① 张明:《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 第六次论战” 及其学术效应—— 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年第6期。 。这一“底线”关乎毛泽东研究的方向问题与立场问题,也关乎毛泽东研究范式的科学性、历史性与客观性问题。
(二)还原到毛泽东时代场域的原初语境
由于迈斯纳本身的研究视野限制与主观的理论预设偏差,使他陷入了“乌托邦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固有理论桎梏,还将马克思主义认识“主观定性”来透视毛泽东的思想,以致于抽象而片面地去探讨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部分具体理论的一致与否,而忽略了具体历史语境、具体国情与实践行动的考量。因为“在迈斯纳的视野中,所谓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仍然是传统观念中那些诸如消灭三大差别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② 杨永康:《 莫里斯· 迈斯纳视野中的毛泽东社会主义观》,《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7年第6期。 ,这无疑是在脱离历史语境而对马列主义做出“垂直性”的注解,从而使得多元深刻而立体的毛泽东思想肖像从具体语境中脱离而陷入“真空化”。
因此对于当下的毛泽东研究来说,一大重要原则即还原到毛泽东时代的原初语境,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中来定位“鲜活的毛泽东”。这就亟待我们正视历史合力的作用,正视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与历史环境之间良性互动的密切联系,并着力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中国革命实践史三重思想史线索对毛泽东的思想予以“立体式定位”,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③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3年12月27日。 ,而唯有如此方能规避历史虚无主义所预设的理论陷阱,方能在显性的文字中读出隐性的逻辑结构,进而探求到毛泽东的理论及其实践背后的内在精髓。
(三)注意区分开发展马克思主义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热门“问题域”。而迈斯纳则是持“背离观”的学者之一。但显而易见,迈斯纳是以“乌托邦”为中介,进而把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进行了对比。而这本身就是犯了教条主义与理论先验主义的错误,是对马克思主义辨证开放性特质的人为阉割。他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于方法,而非具体结论。诚如卢卡奇所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① [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第47-48页。 。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片区,位于贵阳市中心区域,人流量大,车况复杂,为有效解决行人过街问题,需修建大量人行天桥,其中遵义中路与延安南路交叉口的B联,由于上跨延安南路(宽45m)且道路两侧情况复杂,导致桥梁设计跨度为62.68mm,桥下净空高6m,桥面长度和宽度分别为63.68m和6.0m,另外,在该天桥两端,还需要设置两道人行扶梯。该人行天桥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地震设防烈度为Ⅵ度,设计荷载如下:桥面活荷载为3.5kN/m2,二期恒载均为3.2kN/m2;桥顶雨棚活载和恒载分别为0.5kN/m2、1.7kN/m2;风压标准值为 0.4kN/m2。
反思这一议题可以发现,这实则是一个关乎如何科学判定发展马克思主义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问题,而理性回答这一命题无疑需要三大“标尺”。其一,是否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② 《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02页。 ,它为实践行动提供了总的发展趋势以及规定了一般性原则。因而只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符合坚持的要求,但坚持不是盲目的坚持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本质地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其“农村包围城市论”虽然迥异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的“城市中心论”,但它实质上是基于特定历史语境下做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中国实践的现实境遇相结合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因而这绝不是对原理的背离反而是坚持与发展。其二,是否经过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真理颠扑不破,同时也适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范式。毛泽东也正是基于具体实际而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并以革命胜利的实际成果“否定了从文本原理出发讨论现实的经院哲学思维定势,破除了对‘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能保证革命胜利’的迷信”③ 黄力之:《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底线问题》,《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年第5期。 。其三,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实践成果的唯一检验主体。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对客观实际以及人民利益诉求的能动性反映,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结语
概言之,迈斯纳以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作为认识中介审视毛泽东的观点,并尝试摸索出一条全新路径来诠释毛泽东的思想与经典马列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但这一分析概念与研究范式明显存在问题。而通过对其系列观点的批判与辨析则可为当代毛泽东研究的进一步深耕细犁提供方法论反思:一是要秉持客观中立的历史态度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二是要对具体语境中的中国国情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把握;三是要坚持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角度看待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如此方能勾画出毛泽东的整体性思想肖像。
作者简介: 罗馨,女,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当代进展及其批判性阅读研究”(项目编号:17CKS006)。
(责任编辑:马纯红)
